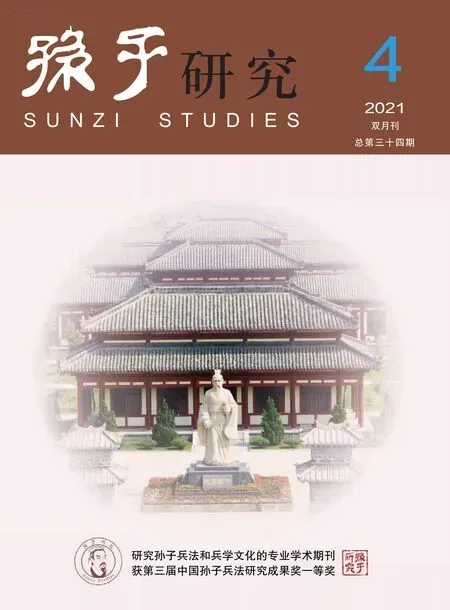《孫子》成書研究在當代的進展與挫折
——以銀雀山出土文獻為中心的考察
熊劍平
兵典《孫子》一直頭頂著絢麗的光環,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廣泛影響力,同時也留下了重重謎團。其中,成書問題堪稱“謎中之謎”,歷史上聚訟不已,始終難以達成共識。進入當代,隨著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竹簡的出土,出土文獻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大致能夠互相形成驗證,“春秋成書說”一度成為主流觀點,貌似迎來巨大進展。當然,也有學者根據銀雀山竹簡對“春秋成書說”提出更加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出土竹簡反倒更能證明《孫子》為戰國時期成書。也就是說,《孫子》成書問題尚且無法形成定論,還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一、成書之紛爭及學術史回顧
記載《孫子》十三篇作者及成書的歷史文獻,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乃至被很多人視為最權威的,都要數《史記》。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為孫武立傳,并將其與孫臏、吳起并列,合為《孫子吳起列傳》。所以,列傳所稱“孫子”,實則既可指孫武,也可指孫臏。〔1〕在這篇三人合傳中,司馬遷將有關孫武的文字排在最前。這應當是出自作者的一種有意安排,因為孫武所處時代較后二者為早。而且,司馬遷兩次提及“十三篇”,非常明確地一直把《孫子》十三篇的著作權劃歸孫武。司馬遷不僅在描寫戰爭場面時折射出“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的一般情形,還在《史記》中直接引用《孫子》字句。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主父偃初見武帝時曾有這樣一段對話:“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這里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即引自《孫子》。〔2〕也許在司馬遷的時代,或者說在司馬遷的眼中,《孫子》十三篇和孫武之間的關系是非常明確的,司馬遷可能閱讀過這部兵書并有選擇性地摘引。
從漢到唐,世人論及孫子其人其書,所本多為《史記》,而且很少有人對司馬遷的記載提出過疑問。這種情形一直到了疑古風氣甚濃的宋代才發生改變。
北宋仁宗時期,歐陽修在為梅堯臣《孫子注》寫序時,稱《孫子》為“戰國相傾之說”。〔3〕在他看來,孫子兵學思想與三代“王者之師”的兵學思想有著很大差異,所謂“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4〕。按照司馬遷的記載,孫子是春秋末期人。此時雖是禮崩樂壞,但畢竟還是周王封建時期、“三代”之末期。歐陽修將孫武的學說與儒家所艷稱的“三代”劃清界限,其實就是不相信司馬遷的有關記載。他的這番言論當時少有響應,但已徐徐拉開懷疑司馬遷的大幕。到了南宋,歐陽修的懷疑之說得到更多響應。葉適、陳振孫等都紛紛站出來對司馬遷進行反駁。他們認定的理由主要有:首先,《左傳》中未見記載孫子事跡;其次,孫武立說反映出戰國時代的特征;再次,《史記》所載“吳宮教戰”,更像是在說故事,非常奇險,不足為信。據此,葉適斷定《孫子》為“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5〕,陳振孫則認為孫子是“未知其果何時人”〔6〕。
宋代所開啟的懷疑之風,到了清代仍有延續。姚鼐同樣認為《孫子》其書反映出非常明顯的戰國時代特征。他說:“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為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7〕姚鼐還指出,《孫子》所總結的用兵之法,其實正是秦國人虜使民眾之法,而且“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8〕。清代學者姚際恒則將《孫子》列為“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9〕。其說見諸《古今偽書考》:“此書凡有二疑:一則名之不見《左傳》……一則篇數之不侔也。”〔10〕姚際恒對篇目數提出懷疑并不奇怪。依照傳統說法,學界一直將《漢書·藝文志》中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當成《孫子》十三篇,這二者之間篇目數差距很大,本該成為疑點。而他“名之不見《左傳》”之說,當受到葉適的啟示。清代另一學者全祖望也曾極力稱贊葉適的推論,認為葉適之說“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11〕。
到了近現代,懷疑《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仍不乏其人。梁啟超在談到史籍辨偽時,就曾對《孫子》做出如此結論:“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雖然,若謂出自秦漢以后,則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漢書·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齊孫子》之兩種:《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作,亦可謂之 真。”〔12〕錢穆更進一步,認為《史記》所載俱不可信:“蓋皆出后人偽托。”〔13〕他明確指出:“《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臏而誤。”〔14〕不僅如此,錢穆還認為齊孫子與吳孫子的事跡被后人混淆一處,孫武、孫臏可能本來就是同一個人,孫臏的“臏”字,是“臏腳”之意,本不是人名,而“武”才是人名。他說:“后人說兵法者,遞相附益,均托之孫子。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誤分以為二人矣。”〔15〕稍晚,則有齊思和繼續堅持葉適等人的結論。齊思和也將懷疑的矛頭直接指向司馬遷,對《史記》的可信度提出挑戰。他指出:“孫子之行事,不惟不見于《左傳》,且不見于一切先秦古籍。”〔16〕在齊思和看來,《孫子》十三篇中所見戰爭規模和軍制特點及寫作體例等,明顯都是戰國特點,因此他認為,“所謂孫武者既未必有其真人”“(書)為戰國中后期之著作”。〔17〕
二、竹簡文獻為司馬遷舉證
宋降學者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展開前赴后繼的懷疑和駁難,從《孫子》的成書年代,到其人其書的關系等,可謂步步緊逼,而且也已取得相當大的戰果,司馬遷有關《孫子》其人其書的記載,眼看就要遭到全盤否定。然而,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出土的漢墓竹簡,向世人展示了不少有利于司馬遷的證據,幫助《史記》掀起絕地反擊。《孫子》的成書研究,也由此而能在當代獲得另一番景象。
其實,《孫子》成書問題之所以形成持久之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信或不信。銀雀山竹簡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讓人們增加對《史記》的信任程度。因為這批竹簡中提供了不少有關孫子其人其書的重要信息,其中部分內容還可以和司馬遷的記載形成互證,可以反駁宋以來那些懷疑《史記》的立說。〔18〕
第一個證據是,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有一些竹簡文獻記載了與孫武有關的事跡,主要集中在《吳問》和《見吳王》,此外還有《黃帝伐赤帝》等篇。相比之下,《吳問》和《見吳王》這兩篇簡文更值得重視,主要內容都是孫武和吳王闔閭的問答。《吳問》中的孫武,借分析晉國的田制和稅制,分析和預測了范氏、中行氏等六大家族的命運。他準確地預言到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滅亡順序,但預言晉國將歸趙氏時,則完全說錯。這樣的一對一錯,讓一些專家將《吳問》的寫作時間定在春秋末期,甚至鎖定在智氏滅亡到韓、趙、魏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19〕這一結論一度產生了很大影響,也被竹簡整理小組吸收。鄭良樹基于此推論,將十三篇的寫作推斷為“孫武卒后的四十余年 間”〔20〕。何炳棣則將《吳問》考訂為與《孫子》同時期作品,“都是撰成于吳王闔閭召見孫武之年——公元前512年”〔21〕。關桐認為《吳問》正是孫武和吳王的真實對話記錄:“《吳問》是孫武與吳王闔閭或夫差的問答之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絕不是兵家者流假托吳王與孫武的問答之辭。如果是‘兵家者流’的‘假托’,理應是講戰爭、論兵法,不可能是政治議論。不是兵家的學者而偽托孫武與吳王討論政治問題,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也增加了《吳問》作為真實史料的可信度。”〔22〕此外,還有一些學者也視《吳問》為真實史料,甚至根據該篇簡文進一步推斷出孫武入吳的具體時間。〔23〕黃樸民也指出:“從預測的歷史進程絕大部分具有準確性質的層面加以考察,《吳問》的史實可靠性毋庸置疑。”〔24〕
另一篇簡文《見吳王》雖有嚴重殘缺,但還是可以看出其中不少內容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頗為相似,主要描寫的是“吳宮教戰”之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一度將其命名為《孫武傳》〔25〕, 一年之后又改而命名為《見吳王》〔26〕。有研究專家指出,《見吳王》中的情節描寫要比《孫子吳起列傳》更為詳盡,當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一種古本。至于《史記》或《吳越春秋》,“可以看作是依據古本取其大要”〔27〕。也有專家認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這些《孫子》佚文,正是司馬遷當初寫作《孫子吳起列傳》的原材料,“司馬遷對這些材料進行過研究”〔28〕。司馬遷是不是看著這批竹簡材料寫作《孫子吳起列傳》,怕是未必能夠如此肯定,筆者對此曾有專門討論。〔29〕簡文《見吳王》原有1000 多字,現存僅一半左右。《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有關孫武的記載,大多是在描寫“吳宮教戰”故事,約為350 字。主題大體相同,簡文所費筆墨卻是后者的3 倍左右,二者之間存在著差別是顯而易見的。〔30〕相比之下,《見吳王》中所記載的情節更加具體,更為合理。那些被葉適等人看成“奇險”而“不足為信”的材料,反倒被司馬遷悉數吸收,因此我們認為竹簡文獻未必曾經過司馬遷所親見,否則《史記》中的孫武傳記也不會只是寥寥數百字。應該看到,先秦不少典籍都受地域和政治環境等影響,從而在流傳過程中出現書寫差異,有長有短,有繁有簡。《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和《見吳王》之間的差異,可能也是因此而生。當然,這些不同地域流傳的文獻,即便不是一脈相承,卻也可以彼此互證。也就是說,竹簡文獻可以對《史記》中記載的基本史實起到證明作 用。〔31〕不管如何,這批竹簡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比《史記》更早更翔實的有關孫武的史料。人們對于有無孫武其人的懷疑可以暫時擱置起來,必要時重新進行審視。
銀雀山竹簡提供的第二個有利于司馬遷的證據就是,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關《孫子》其書的早期信息,而且不少都能和《孫子吳起列傳》的記載求得互證。這批竹簡文獻中曾兩次提到了“十三扁(篇)”〔32〕,和《孫子吳起列傳》中兩稱“十三篇”形成了呼應之勢。簡文《吳問》篇首(0233簡)“吳王問孫子曰……”的字樣,以及《威王問》篇首(0108 簡)“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等〔33〕,顯然可以和《史記》有關孫武和孫臏的記載形成互證。更為重要的是,銀雀山竹簡為我們提供了比諸如“武經本”或“十一家注本”等宋本《孫子》更為古老的另外一種版本。在銀雀山出土的這個《孫子》古本,其總篇目數也為“十三”。這不僅有一塊尚可識讀部分文字的篇題木牘提供證明,更有十三篇中尚未被時光和塵土磨滅的大量文字作為注腳。傳本現有篇目中,除《地形篇》不見出土之外,其余十二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文字留存,《形篇》甚至還有甲、乙兩種抄本出土。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銀雀山出土的簡本《孫子》篇目數應該是“十三”。簡本《孫子》的版本價值彌足珍貴,其史料價值同樣不可估量。這些出土竹簡除了告訴我們,在歷史上一直有著廣泛影響的杜牧所謂“曹操刪削《孫子》篇目說”不可信之外〔34〕,更告訴我們司馬遷有關《孫子》其書的記載由來有自,宋降學者的懷疑或否定有“疑古過猛”之嫌,應該重新審視和反思。
銀雀山竹簡提供的第三個有利于司馬遷的證據便是《孫臏兵法》的出土。如前所述,當人們對司馬遷的懷疑愈演愈烈之時,孫武和孫臏之間何種關系,是否本為一人,都曾引起過熱烈討論。前述梁啟超和錢穆的學術觀點,都曾迎來不少附和者。〔35〕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主要原因就在于《孫臏兵法》的中道失傳。當竹簡《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同時在銀雀山漢墓出土之后,有關《孫子》的著作權之爭,以及孫武、孫臏是否同為一人等疑問,都很自然地渙然冰釋。在銀雀山竹簡中,《吳問》的篇首0233 簡寫有“吳王問孫子曰……”《威王問》的篇首0108簡寫有“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36〕簡文顯然可以和《史記》中有關孫武和孫臏的記載形成呼應和互證。據此,人們應該更有理由相信,司馬遷為先秦兩位孫氏軍事家所作傳記應該是各有依據,并非胡編亂造。而且,孫武和孫臏本來就是各有兵法傳世,孫武本不應當被錯認為是孫臏,《孫子》十三篇也不應被錯認為是孫臏所著。也就是說,錢穆等人的研究結論并不可信,已被出土文獻駁倒。
三、另一種嘗試:出土兵書及其他考量
有關孫子其人其書的信息,先秦典籍中也可以發現一些,尤其陸續出現的引用文獻。〔37〕雖說只是零星片段,但也多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考察《孫子》成書的基本線索。銀雀山出土竹簡則為我們提供了更多類似信息,而且也可以和傳世典籍形成呼應,自然也會對推斷《孫子》的成書年代有一定幫助。
在銀雀山出土的兵書中,包含有曾被懷疑是偽書的《尉繚子》。這一方面可以證明該書并非偽書,另一方面也為人們提供了更多先秦兵書征引《孫子》的信息。何法周根據竹簡文獻研究認為,《尉繚子》的寫作年代應該在魏惠王時代。〔38〕鄭良樹對該書明引、暗引《孫子》的情況也進行過系統考察,將《孫子》的成書時間推斷為《尉繚子》之前。〔39〕在傳本《尉繚子》中,我們也可看到作者曾盛贊孫子的用兵之術:“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40〕如果《尉繚子》成書時間果真可以前推,那么《孫子》成書時間自然也可以相應地前移。
與《尉繚子》相比,銀雀山出土的另一部兵書《孫臏兵法》,其中征引《孫子》的情況理應引起加倍重視。此書曾長期失傳,1972年意外地重見天日,加之作者孫臏與孫武之間存在著特殊關系,自然會引起格外關注和重視。鄭良樹曾考察《孫臏兵法》明引、暗引及發揮《孫子》的各種情況,將《孫子》成書時間推斷為《孫臏兵法》成書之前。〔41〕如果細究起來,鄭良樹所列舉的暗引例證并不具備什么說服力。因為英雄所見略同的道理,即便是高明的軍事家,其兵學思想難免也會存在某種趨同性。至于明引《孫子》十三篇,其實也可以找到更好的例證,比如《威王問》篇中“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必攻不守”及《勢備》篇“晝多旗,夜多鼓”等。“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出自《孫子·計篇》,“必攻不守”則出自《孫子·虛實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而“晝多旗,夜多鼓”則可在《孫子·軍爭篇》中找到出處。這些例證也許比鄭良樹文中所舉例證更具說服力。鄭氏所舉例證中,有一條出自《十問篇》,但該篇后來被調整出《孫臏兵法》。〔42〕總體來看,《孫子》成書早于《孫臏兵法》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已有《史記》這種權威史書作為依據,另一方面也因為銀雀山出土大量可資互證的重要文獻,尤其是一批兵書文獻。古兵書的大量征引,令我們可以對《史記》的有關記載增添一重信任。這些地下新出土文獻,正好可以“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43〕。 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依靠銀雀山竹簡正可以對《孫子》成書研究起到作用。銀雀山新出兵書,也為考察《孫子》成書提供了新線索。它們不僅和《史記》形成互證,也可和古兵書之間求得互證。《孫子》十三篇和《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兵書一樣,是先秦時期誕生的兵學著作,而且其寫作年代要早于后二者。
在竹簡之外,就“春秋成書說”,學術界也有其他論證和推進。自從宋代學者梅堯臣推測《孫子》為“戰國相傾之說”〔44〕后,歷代都有響應,而且舉證似乎越來越多。當然,細究起來,最有力的證據似乎有這兩條:第一,戰爭規模較大,是明顯的戰國時代特征;第二,五行思想大量滲入,也體現出戰國時代的特點。當然,如果細究起來,這兩條證據也嫌貧弱。
考察十三篇,孫子論戰爭發起兩次言及“十萬”,并將戰爭模式設定為“興師十萬,出征千里”〔45〕這一規格。這在《作戰篇》與《用間篇》都可以看出。孫子還對相應規模戰爭所花費的財政支出和物資消耗等進行了論述,如“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和“內外之費,賓客之用”及“馳車千駟,革車千乘”“膠漆之材,車甲之奉”等。這便令不少學者心生驚愕,認為當為戰國時期的戰爭規模。其實,“十萬”本為虛指,而且有關論述實則為司令部想定作業〔46〕的一種,為了使得推算更加具備可操作性。考察“廟算”的設計和要求,更可看出其中體現了想定作業模式的特點。〔47〕有學者指出,“十萬”也許只是一種估算。〔48〕應當說,這本來就是估算。因此,從“十萬”這種作戰規模并不能推定《孫子》寫作年代為戰國時期。不僅如此,在春秋時期,諸如晉國、楚國這樣的大國,其軍隊已有相當龐大之規模,“十萬”并非遙不可及的數字。比如,吳國伐楚之役,吳國動用軍隊三萬,楚國則達二十萬,故《新序》等書稱“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春秋時期,各國軍隊主要由“國人”編制而成。國人皆有納軍賦的義務,壯丁必須充當甲士,遇到戰爭即由“授甲”或“授兵”而應征入伍。〔49〕“國人”也隨時而成“戰士”或“甲士”。〔50〕這種情況下,軍隊員額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就管仲時期的齊國而言,如果是“率九家一兵”,即可“得甲十萬”。〔51〕春秋早期的齊國既然能達到如此之規模,春秋晚期的晉國和楚國等達到“十萬”的規模,也并非沒有可能。
在《形篇》《勢篇》《虛實篇》等中,孫子大量借用五行方式論兵。如《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勢篇》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虛實篇》曰:“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這一現象的出現被不少學者認定為戰國時期的理由,因為他們認為“五行”思想的流行當為戰國時期。其實,上述駁論也較為貧弱。陰陽五行思想的起源,不少學者推定為西周末期。〔52〕《國語·鄭語》載史伯語曰:“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因為前期積累,到了春秋時期,已經“流行五行方位圖式”〔53〕。 從《國語》《左傳》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五行”模式的語言痕跡。《國語·魯語上》載展禽語曰:“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子產語曰:“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其中,“五聲”“五色”“五味”等詞語也在《左傳》中其他地方數次出現。如《左傳·桓公二年》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左傳·昭公元年》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國語·鄭語》:“五色雜,然后成文。五味合,然后可食。”學者推定,五行不僅在春秋時期出現,而且“已經和干支時日結合,形成了復雜的體系”〔54〕。既然如此,《孫子》出現大量體現五行思想的文字,也非突兀。
兩條戰國成書的證據缺乏說服力,十三篇中不見騎兵也是“春秋成書說”的力證。《孫子》雖提及戰馬,如《行軍篇》曰“粟馬肉食”,《九地篇》曰“方馬埋輪”,卻沒有出現“騎兵”,更不見騎兵與其他兵種的合成戰術。《孫子》較多論及車戰,也符合春秋時期作戰特定。對比《六韜》等兵書,更能明顯看出這一特點。騎兵的出現,一般考證為戰國初期。〔55〕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56〕《墨子·號令》曰:“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由于此處出現“騎卒”,有學者懷疑其時已經出現成建制騎兵。〔57〕對此,顧炎武也有較詳細考訂。《日知錄》曰:“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于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于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58〕總之,“用騎”是戰國時期的作戰特點,而非春秋末期,更符合孫臏生活時期的歷史語境,而非孫武。〔59〕由“用騎”與否,可推定《孫臏兵法》比《孫子》晚出,更證明十三篇成于春秋末期。其他如從“將軍”和“軍將”等個別詞語差別形成的結論,可能是流傳過程中存在抄寫之誤。〔60〕
四、不同解讀:竹簡文獻并非一邊倒地支持《史記》
銀雀山出土文獻中雖說出現了不少支持司馬遷的證據,但也有若干材料對《史記》形成了駁難,包括數篇《孫子》佚文在內,部分竹簡文獻的寫作年代尚難斷定,由新出文獻來判斷《孫子》的成書,也便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
其中最受矚目的一處出現在《用間篇》的異文,傳本寫作:“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簡本寫作:“……□□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師比在陘。燕之興也,蘇秦在齊。”很顯然,簡本多出兩句,又提及蘇秦等另外兩名間諜。雖說和《用間篇》主題非常吻合,但也給《孫子》成書帶來一定的遐想空間。蘇秦至今仍家喻戶曉,是戰國中晚期的風云人物,但是師比鮮有人知且史籍無考。對此,銀雀山竹簡整理小組的專家判定為衍文,指出:“蘇秦時代遠在孫武之后,簡本數語似可證《孫子》書出于孫武后學之手。或以為此數語當為后人所增,待考。”〔61〕學界持類似觀點的較多,占據主流。〔62〕既然蘇秦所處時代為戰國中晚期,簡本此語不能不讓人對《史記》中有關《孫子》成書年代的記載產生懷疑。一直堅持“戰國成書說的”的齊思和在看到簡本此語后,立即將其作為《孫子》晚出的證據,更堅信十三篇兵書是成書于戰國。〔63〕在齊思和看來,簡本中多出的這兩句并非后人所增,因此能對考察《孫子》成書年代有著別樣的意義。李零也堅持“戰國成書說”〔64〕,但他判定上述二句為衍文。從李零行文可以看出,他認定該句為衍文的前提是,《孫子》作者就是孫武。〔65〕
聯系上下文考察,無論是伊尹和呂尚,抑或是蘇秦和師比,作者提及他們都是為了強調用間的重要性,連續舉出四個例證,或許對文氣有所幫助,但過度則會造成傷害。因此,在筆者看來,它們都像是旁記文字衍入。黃樸民指出,傳本中的“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也是衍文,因為這些內容和《孫子》的“舍事而言理”這一整體風格是相悖的。〔66〕不管如何,簡本《用間篇》中多出的上述兩句,為《孫子》的成書研究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為“戰國成書說”提供了證據。
如果對銀雀山竹簡文獻的史料價值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吳問》等簡文實則也有重新考察的必要。雖說它們對于研究《孫子》的成書時代大有助益,但未必是能夠幫助司馬遷的確鑿證據。就簡文《見吳王》的史料價值而言,如果我們不急著將銀雀山出土文獻和司馬遷的《孫子吳起列傳》建立起必然的聯系,那么,簡文的史料價值反而可獲得倍增。〔67〕毫無疑問,這是一篇給《史記》相關記載以足夠支持的簡文,但學界對此并沒有多少關注。相比之下,另一篇簡文《吳問》倒是引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至少學界對其曾有一段較為熱烈的討論,而且一度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
《吳問》是一篇問答體簡文,以考察春秋末期晉國六大家族的興衰為切入點,通過吳王與孫子的一問一答完成。由于田制和稅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民心向背,而民心向背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王室的命運,因此簡文《吳問》從田制和稅制的角度出發來考察王室興衰,在邏輯上自然也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這篇問答體簡文是否真實發生,存在不小的爭議。吳樹平雖將《吳問》寫作時間推定為春秋末期,但也同時認為其只是后人追記而成的。也有學者直接懷疑起《吳問》的真實性,比如李零。〔68〕王暉也指出,《吳問》中反映出儒家思想特征,其中體現出的“王道”思想,只能是戰國中期之后才會出現,《吳問》中的一些術語也體現了鮮明的戰國中晚期的時代特征。經過多方分析,王暉推斷:“《吳問》的成文時代可定在戰國中晚期。”〔69〕此外,郝進軍也認為,《吳問》不是孫武言行的真實記錄,它甚至是戰國末期才產生的贗品。〔70〕既然如此,在不少學者眼中,包括《吳問》在內的銀雀山竹簡文獻,并不能為《孫子》的寫作年代提供直接的證據,至少還不能讓人百分百地信服。因此,有關《吳問》寫作年代和真偽討論等,一定還會繼續深入下去,并對判斷《孫子》的寫作年代等疑難問題產生相應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吳問》的真偽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真偽并不能直接聯系在一起。視《吳問》為真實對話記錄,明顯是過于樂觀,但推斷《吳問》為偽作,也顯得過于保守。在愚見看來,《吳問》實則為一種“問答”體的注解文字,也許是孫子后學模擬先祖事跡而寫成的一段對話,我們大可不必太過追究其真偽。《吳問》很可能和《通典》、何氏注、張預注中的諸多孫、吳問對一樣,是孫子后學學習《孫子》十三篇所留下的注解文字。其寫成年代未必如吳樹平等人所說的那么早,但應該誕生于十三篇著成之后。如果我們根據《吳問》是政治議論而將其與兵家剝離開來,也許欠妥。兵家討論政治問題,寫作政論文字,并不奇怪。孫子會論及“修道保法”,也將“道”視為影響戰爭勝負的第一要素。雖然兵家在主體思想上和儒家、法家等有很大差別,但他們關心政治和參與治國的熱情,絲毫不亞于其他學派。〔71〕孫子在《計篇》《形篇》《火攻篇》中有關“道”和“安國全軍”的討論等,都是很精彩的政論文字。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孫子后學才會有諸如《吳問》這樣的政論作品產生。關桐等人認為《吳問》“決不是兵家者流假托吳王與孫武的問答之辭”〔72〕的判斷,其實也值得商榷。
還應注意的是,銀雀山出土孫子佚文明顯地存在著風格不一的特點,這應該可以證明數篇簡文寫作時經歷時間跨度之長。簡文《黃帝伐赤帝》的寫作時間可能更晚。〔73〕宋會群對此也有討論。〔74〕考察該篇簡文,可以不難看出其中沾染了較為濃重的兵陰陽家色彩,與《孫子》十三篇中強調的“不可取于鬼神”〔75〕的精神背道而馳,似乎也無法對《孫子》成書研究起到直接的參考價值。鄭良樹認為:“《兵家遺簡》的作成時代似乎是頗為參差的:作成時代早的一部分,極有可能就緊跟在《孫子》之后;作成時代晚的,可能要到漢代初年了。”〔76〕這些簡文是不是果如鄭良樹所言,竟有作品遲至漢代才誕生,還需要繼續加以探討,但鄭氏“頗為參差”的判斷還是基本可信的。由于這些竹簡文字的出現,我們顯然不能將《孫子》的寫作年代推斷得過晚。有些學者視《孫子》為戰國中后期作品,甚至秦漢時期才獲定型,不免顯得過于保守。〔77〕總體考察銀雀山出土簡文,其對推斷《孫子》成書年代有相當大之價值,但對于推斷更為準確的寫作年代,仍是無法給予太高的參考價值。
結論:回到《史記》,抑或繼續予以否定
圍繞《孫子》成書所引發的爭議,其實可以集中到一點,就是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信或不信。銀雀山竹簡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得互證。至于《孫臏兵法》的出土,則更對《史記》中兩個孫子各有著述等記載提供了力證。簡文曾兩次提及“十三扁 (篇)”〔78〕,和《孫子吳起列傳》兩稱“十三篇”也形成呼應之勢。傳本十三篇中,除了《地形篇》之外,其余十二篇均有或多或少的文字出土,也可證明司馬遷所記載的有關《孫子》的記載大致可信。這些竹簡被深埋地下兩千多年,得見天日之時,仿佛立即能夠證明司馬遷的著述并非向壁虛構。而且,從司馬遷的著述精神考察,我們也應當對《孫子吳起列傳》更多一重信任。對于那些因時代久遠而無法確定之事,司馬遷都會保持“闕疑”態度,所謂“聞疑傳疑”〔79〕。比如他在為老子和墨子作傳時,都用到“或”和“蓋”這樣表示存疑和推測的詞語。〔80〕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司馬遷用墨固然簡略,卻沒有使用“或”“蓋”這種推測之辭。這一現象或許能夠說明,在太史公眼里,孫子其人其書等是可以確定的。從這一層面考察,探討《孫子》成書問題時,如果沒有更新更全的出土文獻,不妨相信司馬遷的記載,尤其是在銀雀山出土文獻給予相當程度支持之后。
當然,即便如此,《孫子》成書研究也未到蓋棺定論之時,至少學界還有不同的主張。就《孫子》書中所體現的戰國時代特征等問題,宋人掀起的爭論一直延至今天,因為有齊思和、藍永蔚等學者的參與〔81〕,因為有銀雀山竹簡的出土,種種爭論變得更加激烈。就目前情形而言,回到《史記》,固守《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似乎占據了主流意見,但是對于“戰國成書說”似乎也不能立即全盤予以否定。
【注釋】
〔1〕為避免混淆,以下所稱“孫子”皆為孫武。
〔2〕《孫子·用間篇》有云:“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89 頁。
〔3〕歐陽修:《孫子后序》,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四二,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06 頁。
〔4〕歐陽修:《孫子后序》,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四二,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06 頁。
〔5〕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六,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75 頁。
〔6〕[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清]姚鼐:《惜抱軒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黃云眉:《古今偽書考補證》,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6 頁。
〔10〕黃云眉:《古今偽書考補證》,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310 頁。
〔11〕[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九,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
〔1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 頁。
〔13〕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4 頁。
〔14〕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5 頁。
〔15〕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305 頁。
〔16〕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1 頁。
〔17〕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5 頁。
〔18〕相關論著很多,重要論文有:許荻《略談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古代兵書殘簡》(《文物》1974年第2 期)、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第2 期)、詹立波《略談臨沂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 期)、遵信《〈孫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時代——談談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孫子兵法〉的出土》(《文物》1974年第12 期)、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 期)、常弘《讀臨沂漢簡中〈孫武傳〉》(《考古》1975年第4 期)、藍永蔚《〈孫子兵法〉時代特征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 期)、何炳棣《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金景芳《孫子十三篇略說》(《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 期)、曾憲通《試談銀雀山漢墓竹書〈孫子兵法〉》(《中山大學學報》1978年第5 期)、吳如嵩、魏鴻《漢簡兩〈孫子〉與〈孫子兵法〉研究》(《軍事歷史》2002年第1 期)、黃樸民《孫子的著述及其釋疑》(《北京圖書館學刊》1994年第3 期)。
〔19〕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 期。
〔20〕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載《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21〕何炳棣:《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歷史研究》1999年第5 期。
〔22〕關桐:《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的幾點考證》,《孫子學刊》1992年第4 期。
〔23〕陸允昌:《從竹簡〈吳問〉考孫武入吳時間》,《蘇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1、2 期。
〔24〕黃樸民:《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佚文〈吳問〉考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1 期。
〔2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簡釋文》,《文物》1974年第12 期。
〔26〕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27〕常弘:《讀臨沂漢簡中〈孫武傳〉》,《考古》1975年第4 期。
〔28〕于汝波主編:《孫子兵法研究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5 頁。
〔29〕熊劍平、黃樸民:《簡文〈見吳王〉與〈史記·孫子列傳〉關系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6 期。
〔30〕熊劍平、黃樸民:《簡文〈見吳王〉與〈史記·孫子列傳〉關系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6 期。
〔31〕熊劍平、黃樸民:《簡文〈見吳王〉與〈史記·孫子列傳〉關系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6 期。
〔32〕《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 頁。
〔33〕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 頁。
〔34〕更加詳細的討論可以參看熊劍平《曹操與〈孫子〉——基于孫子學史的考察和辨誤》,《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3 期。
〔35〕日本學者武內義雄認為孫武和孫臏為同一人,“臏”是綽號,與錢穆仿佛,可能也是受了梁啟超的影響。參見武內義雄:《孫子十三篇之作者》,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377 頁。
〔36〕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 頁。
〔37〕比如《尉繚子》《鹖冠子》等書曾明引或暗引《孫子》詞句。《尉繚子·將理》篇曰:“兵法曰: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此語實則從《孫子》的《作戰篇》或《用間篇》化出。《作戰篇》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用間篇》云:“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都表達了類似意思。《鹖冠子·天則》篇曰:“故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此語實則出自《孫子·計篇》。
〔38〕何法周:《〈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 期。
〔39〕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40〕《尉繚子·制談》,見《〈武經七書〉鑒賞》,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 頁。
〔41〕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42〕如果細究起來,鄭文中還有一些瑕疵。比如他把《七錄》和《七略別錄》混淆,再如孫武卒年本不可考,他卻將《孫子》成書斷為“孫武卒后的四十余年間”。這些瑕疵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的寫作思路和立論。而且,按照鄭氏的觀點,既然是孫武卒后的四十余年間寫成,它就應該不是孫武的作品,他卻又認定“《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吳國名將孫武的作品”(《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這不免也讓人感覺一頭霧水。
〔43〕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 頁。
〔44〕歐陽修:《孫子后序》,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四二,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06 頁。
〔45〕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89 頁。
〔46〕參謀業務和指揮人才的訓練方式之一,為了強調實戰而注重模擬的真實性。
〔47〕熊劍平、儲道立:《孫子的戰略情報分析理論》,《濱州學院學報》2011年第1 期。
〔48〕江聲皖:《〈作戰〉既非“備戰”也非“野戰”》,《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2 期。
〔49〕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 頁。
〔50〕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9 頁。
〔51〕[宋]陳傅良:《歷代兵制》卷一,中華書局2017年版。
〔52〕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4 頁。
〔53〕金春峰:《先秦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 頁。
〔54〕金春峰:《先秦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 頁。
〔55〕劉全志:《先秦諸子文獻的形成》,中華書局2016年版。
〔56〕《春秋左傳正義·昭公二十四年》。
〔57〕蘇成愛:《〈孫子〉文獻學研究》,2012年安徽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6 頁。
〔58〕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60 頁。
〔59〕劉全志:《先秦諸子文獻的形成》,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73 頁。
〔60〕張涅:《從“將”字解讀〈孫子兵法〉的思想結構》,《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 期。
〔61〕《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 126 頁。
〔62〕詳參吳九龍主編:《孫子校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 頁;楊炳安:《孫子會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 頁;李零:《兵以詐立》,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80 頁。
〔63〕在晚年所編論文集中,齊思和用“燕之興也,蘇秦在齊”這一句,來為他本人早年所提出的“戰國成書說”作證。參見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年版。
〔64〕李零:《關于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文史》1979年第7 輯。
〔65〕李零:《兵以詐立》,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80 頁。
〔66〕黃樸民:《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7 頁。
〔67〕熊劍平、黃樸民:《簡文〈見吳王〉與〈史記·孫子列傳〉關系考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6 期。
〔68〕李零:《關于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文史》1979年第7 輯。
〔69〕王暉:《試論〈吳問〉的成文年代及其有關問題》,《東南文化》1993年第2 期。
〔70〕郝進軍:《銀雀山竹簡〈吳問〉考辨》,《四川文物》2010年第1 期。
〔71〕黃樸民:《中國古代兵家經國治軍思想概論》,《軍事歷史》2010年第4 期。
〔72〕關桐:《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的幾點考證》,《孫子學刊》1992年第4 期。
〔73〕詹立波指出,《黃帝伐赤帝》那一部分,有一些文字是在解釋《孫子·行軍篇》中的“黃帝之所以勝赤帝也”。見詹立波《略談臨沂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 期。
〔74〕宋會群:《論臨沂漢簡〈黃帝伐赤帝〉的著成時代》,《河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 期。
〔75〕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90 頁。
〔76〕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77〕前面說過,齊思和就是將《孫子》的著作年代定為戰國中晚期。此外,楊炳安甚至認為《孫子》晚至秦漢才定型。參楊炳安、陳彭《孫子兵學源流述略》,《文史》1986年第27 輯。
〔78〕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 頁。
〔79〕[漢]司馬遷:《史記》卷五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997 頁。
〔80〕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司馬遷這樣寫道:“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附錄一段有關墨子的記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
〔81〕詳細內容參見齊思和《〈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燕京學報》1939年第26 期)和藍永蔚《〈孫子兵法〉時代特征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