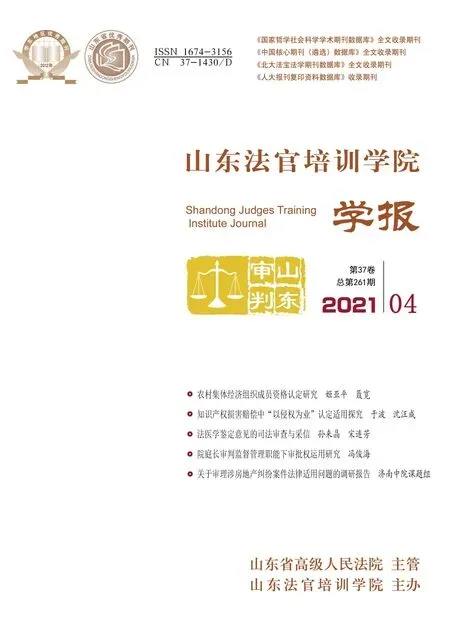后疫情時期野生動物資源刑事司法保護的反思與完善
汪媛媛 吳安榮
野生動物資源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對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2021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吸納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決定》)的相關內容,擴大法律調整范圍,將以食用為目的的非法獵捕、收購等行為納入《刑法》調整對象,對于從源頭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當前立法對野生動物的概念界定不明,刑事司法審判實踐不統一,導致刑法保護功能的發揮受阻。本研究通過梳理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H省法院近7年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相關裁判文書,分析H省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刑事審判現狀,總結審判規律,為預防和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提供參考。
一、現狀掃描: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司法裁判樣態分析
(一)整體概況
1.案件數量集中在近3年。以“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罪,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非法狩獵罪”為案由,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共搜集到H省2014—2020年刑事裁判文書2240份,其中2018—2020年1836份,占總數的81.96%。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近3年國家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打擊力度較大,涉案數量多;二是近3年司法公開力度較大,公開的裁判文書多;三是人們自覺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意識較差,犯罪人數增多。
2.被告人受教育水平低。搜集的文書中,有文化程度記錄的被告人共1073人,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94%,職業多為農民或無業。某一類犯罪的被告人職業具有同一性,比如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其被告98%為漁民。此類被告人平常接觸法律少,對自己行為的違法性預見不足。法律意識的淡薄導致“一增一降”,即增加了被告人違法犯罪的概率,降低了法律對其產生的威懾力。
3.被告人認罪認罰率高。裁判文書中體現“自愿認罪、當庭認罪、如實供述、坦白”等字眼的共2060份,占92%,其中有“認罪認罰”字眼的共1080份。多數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好,對檢察機關起訴的事實和內容均無異議,請求從輕處罰。
4.簡易程序適用率較高。裁判文書中寫明“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共896件,占總數的40%,說明此類刑事案件大多數是事實清楚、爭議不大、處罰較輕的案件。從裁判文書的表述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大部分被告人為當場抓獲,屬于“人贓俱全”、證據確鑿的情形。存在爭議的情形多為主觀上是否系故意或明知(即知道或應當知道犯罪對象是受保護的野生動物)、涉案野生動物數量及犯罪金額的認定等。
5.案件上訴率、發改率低。統計的裁判文書中一審生效文書2083份,占總數的93%,上訴率僅7%,這一點也印證了認罪認罰率和簡易程序適用率高的特點。大多數被告人對案件的審理結果和法律責任的承擔無異議,且當場繳納了罰金。上訴案件中,二審維持原判、改判、發回重審的比例依次為83.3%、13.6%、3.1%,說明人民法院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的質量較高。
6.判處的刑期和罰金偏低。統計的被告人總人數為3040人,其中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340人,占11.2%;免于刑事處罰的274人,占9%;判處罰金、管制、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477人,占81.5%。適用緩刑的1146人,占37.7%。單處罰金的金額中,最高為4萬元,5000元—8000元的比率最高。偏低的刑期和罰金,以及較高的緩刑適用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犯罪分子利用野生動物獲利的僥幸心理。
(二)法律適用重點難點及存在的問題
1.關于野生動物死體的認定結論不一
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的死體屬于珍貴動物還是珍貴動物制品。有法院認為,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死體構成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比如“杜某某非法收購、出售瀕危野生動物罪”一案①參見杜某某非法收購、出售瀕危野生動物罪案,湖南省龍山縣人民法院(2019)湘3130刑初45號刑事判決書。,杜某某以6750元的價格收購穿山甲死體1只,人民法院認為,雖然動物是死體,但被告人的行為侵害了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所保護的法益,應當構成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有的法院則認為構成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也有法院認為雖然構成犯罪,但情節輕微,應免于刑事處罰。
2.關于主觀上是否要求行為人“明知”的處理態度不一
對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需要認識到犯罪對象為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實踐中認識不統一。統計的被告人中,以“不明知”為抗辯理由的有218名,但法院對該理由基本未予采納。比如“彭某非法狩獵案”②參見彭某非法狩獵案,湖南省保靖縣人民法院(2017)湘3125刑初128號刑事判決書。,被告人辯稱其不知道“蚌蚌”系國家保護的“三有”野生動物,主要證據為“蚌蚌”經湖南省野生動植物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后才確定是棘胸蛙而不是蟾蜍,且當地群眾有許多人不知道“蚌蚌”是國家保護的“三有”野生動物。最終法院依然認定彭某構成非法狩獵罪,僅在量刑上予以了從輕處理。
3.關于罪數的認定與罪名的確定存在分歧
被告人同一行為同時觸犯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和其他罪名時如何處理,以及前后實施的相關行為定性為此罪還是彼罪,實踐中均存在爭議。主要表現為以下情形:
(1)非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與非法狩獵罪的罪數認定。被告人在禁獵期、禁獵區,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野生動物,究竟是一行為觸犯數罪,還是行為實質競合,實踐中認識不一。比如“蔣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狩獵罪一案”③參見蔣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狩獵罪案,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9)湘0529刑初175號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屬于一人犯數罪,應當數罪并罰。但“楊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一案”中①參見楊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案,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人民法院(2019)湘1102刑初189號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同時觸犯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和非法狩獵罪,屬想象競合犯,應擇一重罪以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定罪處罰。
(2)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與非法持有槍支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罪數認定。被告人同一行為同時觸犯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和非法持有槍支罪兩個罪名時如何處理,實踐中存在數罪并罰和擇一重罪處罰兩種觀點。H省法院以數罪并罰的觀點占主流。比如,“張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非法持有槍支罪一案”②參見張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非法持有槍支罪案,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湘10刑終17號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非法持有槍支的行為與非法獵捕的行為,具有不同的犯罪故意,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客觀行為,分別滿足不同罪名的犯罪構成,應實行數罪并罰。但其他地方對此兩罪進行數罪并罰的觀點并不占主流,有學者研究認為,實踐中大多是將持槍和獵殺行為視為牽連關系,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和非法持有槍支罪進行數罪并罰的比例較低。
(3)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與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認定。被告人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后,通常會有非法運輸、出售等后續行為,對此,是認定為兩個單獨的犯罪行為,還是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以及定性為何種罪名,實踐中認識不一。比如“被告人顏某某等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一案③參見顏某某等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案,湖南省永州市冷水灘區人民法院(2016)湘1103刑初128號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實施獵捕行為的目的是出售并從中獲利,因而獵捕行為與出售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依法應從一重罪以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處罰。但“汪某某、劉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一案④參見汪某某、劉某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案,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湘06刑終366號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上訴人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小天鵝后出售,情節特別嚴重,構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
4.存在法定刑適用混亂甚至錯誤的情形
(1)錯誤適用法定刑。從裁判文書反映的情況來看,法定刑適用錯誤的情形雖然不多,但依然存在。比如“萬某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一案⑤參見萬某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案,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湘02刑終243號刑事判決書。,一審法院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宣告緩刑1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根據《刑法》第340條之規定,應當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即對被告人應當在主刑和財產刑中擇一判處,一審法院在判處主刑后又并處財產刑,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導致量刑錯誤的情形。
(2)法定刑適用標準不一。由于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情形多樣,涉及的野生動物種類繁多,重量和數量不一,不同地區對“一般情節”“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有差異。比如,同樣是在禁漁期、禁漁區用放置“地籠網”的方式捕撈水產品,捕撈1053斤的被判處罰金4000元,捕撈800斤的被判處管制1年。
二、原因檢視: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司法裁判困境探究
上文的實證研究,揭示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審判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檢視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立法供應不足
目前,關于野生動物保護的國內立法主要為《刑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這兩部法律雖然為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罪名確認以及其他立法提供了指導和參考,但由于兩部法律的概括性和總攬性特征,難以為司法機關提供全面和可操作性強的法律依據,①參見段帷帷、徐小平、朱硯博:《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罪的法律適用問題研究》,載《天中學刊》2020年第1期。且兩部法律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范圍也不盡相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了《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我國《森林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中有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規定,部分省份也制定了有地方特色的保護野生動物的實施辦法和條例,我國還加入了諸多國際條約,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條約》等,但這些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以及國際條約,規定過于原則,行政指導意義大于指導司法審判實踐的意義,難以符合新時代我國野生動物資源保護以及刑事司法審判的實踐需求。
(二)保護范圍受限
首先,野生動物的概念不周延。《現代漢語詞典》對“野生”的解釋為:生物在自然環境里生長而不是由人飼養或栽培的。可見,野生動物應當是與飼養動物或家養動物等相對應的概念。《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條規定了野生動物的范圍,但對于人工繁育、馴養的野生動物是否屬于野生動物并未明確規定。其次,《刑法》中的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與非法狩獵罪雖然針對所有野生動物,但其受限于特定時間、特定區域、特定方式方法,而其余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罪名設置主要針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最后,我國對野生動物采取分類保護的原則,將受保護的野生動物分為三類:一是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實行重點保護;二是地方重點保護動物;三是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這三類動物物種的名單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名錄中的物種保護級別也在發生動態變化,這就會導致許多普通動物物種因經濟利益等原因成為圍獵的對象。
(三)刑罰威懾力不夠
將野生動物保護納入《刑法》保護范圍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用刑罰的威懾性加大對野生動物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但從上文分析情況來看,我國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刑罰力度較為輕緩,判處罰金、管制、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比很大。無論是管制、拘役等輕緩化刑罰種類的大量適用,還是緩刑的大量適用,均反映了我國當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刑罰適用呈現輕緩化態勢。與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獲取的巨額利益相比,輕緩化的刑罰措施不足以形成威懾力。除了主刑輕緩化以外,罰金刑的適用既不廣泛,也與犯罪所獲形成鮮明對比。這就形成了主刑在懲治破壞野生動物犯罪時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罰金刑適用比例低、金額低也難以遏制此類犯罪的發生,從而導致犯罪分子容易鋌而走險不斷實施侵害野生動物的犯罪行為。
三、理論探尋:生態文明視域下野生動物保護的刑法理據
《刑法》對于生態環境領域特別是野生動物保護領域應否介入及如何介入,其依據何在?這是一個重要的論題。從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司法裁判所揭示的問題來看,有必要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對動物的刑法保護理據進行探究。
(一)動物的刑法保護與法益理論
作為破壞生態環境的典型,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侵害的法益,究竟是傳統法益還是新型法益,這尚有爭議。探討動物刑法保護與法益理論的關系,其實就是解釋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犯罪的實質客體問題。依據現行《刑法》,侵害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是侵犯傳統法益的行為。因為該類行為被《刑法》規制后就轉化為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而自然資源具有財產價值,若以《刑法》來保護,在立法技術上完全可實現其目的。然而司法實踐中,該類犯罪的侵害對象被表述為違反環境資源管理制度,其客體被認定為國家秩序。但秩序是不可類型化的法益,而且國家行政創設的管理秩序并不一定需要《刑法》同步保護,只有嚴重違反秩序時才能認定為犯罪。即使被認定為犯罪,對該類行為所侵害的客體仍應進行實質解釋,不能只以秩序為解釋對象。此時,“生態法益”便應運而生。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給生態環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生態法益已經成為急需《刑法》有效保護的重要法益。生態法益分為兩類:一類是包括人身和財產的傳統法益,另一類是傳統法益之外的不可類型化的其他法益。當實施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違反環境資源管理制度時,即使未對傳統法益造成實質損害,但可能損害不可類型化的生態法益,如果滿足實定法規定的構成要件,也可成立犯罪。
(二)動物的刑法保護與風險刑法理論
當下是否屬于風險社會,《刑法》是否應當定位為風險刑法,學界對此尚存在爭論。不過有學者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矛盾日趨多樣化、復雜化,刑法應積極預防風險,保障社會安全。①參見齊文遠:《刑法應對社會風險之有所為與有所不為》,載《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當然,當下的部分立法確實回應了風險刑法理論,②參見于志剛:《風險刑法不可行》,載《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但純為抵御社會風險而任意擴充國家權力的方式亦不可取。第一,若刑事立法過于偏向刑事政策,則公眾的自由恐有被摧毀的可能,所以風險刑法理論也應當接受刑事責任基本原則的規制,以實現原則與例外關系的平衡。③參見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二,風險社會所述的可能風險并不必然轉為現實風險,《刑法》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即使風險客觀存在,《刑法》也應當在具體領域具體情況下作具體的可類型化、可度量化的考量。因此,回歸本文論題,保護野生動物固然重要,但對生態平衡的破壞需要一定量的積累,我國野生動物刑事立法過于依賴一般預防,導致“司法實踐中的環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甚至嚴厲化欠缺合理性”。④參見劉艷紅:《環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對》,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7期。故風險刑法理論運用于野生動物刑法保護領域應當慎重。
(三)動物的刑法保護與社會危害性理論
毋庸置疑,社會危害性理論在學界的地位舉足輕重。一直以來,社會危害性在我國都是認定行為構罪與否的實質標準。因此,破壞生態或污染環境等行為的入罪問題,也要接受該理論的檢驗。步入21世紀后,該理論在學界雖得到相當程度的堅守,但也受到內部的一些反思和批判。筆者認為,運用社會危害性理論解釋如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或財產等傳統的犯罪行為令人信服,因為國家和公民在判斷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上通常不會有本質上的差異。但是,在野生動物的刑法保護上,該理論陷入了解釋的困境。第一,國家出于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對侵害野生動物犯罪行為配置較高的刑罰,法官據法斷案便重判重罰。而公民卻認為該類行為的法益侵害性較弱,社會危害性較低,國家與公民對該類行為的罪感認知不一致。第二,國家出于對生態環境利益的焦慮,其立法理念已轉為生態中心主義,寄望于《刑法》積極規制破壞生態的一切行為,甚至不惜嚴懲重罰。但公民由于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將直接從大自然獲取利益視為正常行為,認為對生態環境無損害或損害不明顯,所以公民對司法的重判重罰持抵觸情緒。⑤參見焦艷鵬:《自然資源的多元價值與國家所有的法律實現——對憲法第6條的體系性解讀》,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1期。這實際上也是公民與國家在利益層面上的認知差異。
從上述理論分析可知,對于以野生動物為載體的新型法益,任何單一刑法理論均難以實現完整的解釋。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加強對動物,特別是野生動物的刑法保護,提升刑事立法的科學性與精細化司法水平,需要科學配置刑法在法益保護、人權保障與秩序維護三者之間的機能,將刑法機制與生態環境領域的相關規律實現有機結合,要對生態法益建立更加科學可測量的價值評價標準。如此,才有利于實現環境刑事司法的個案正義。
四、解決路徑:野生動物刑事司法保護的發展與重構
(一)加大立法進程,確立野生動物全面保護的基本原則
1.完善野生動物刑法保護的前置法律。野生動物刑事司法保護的發展與完善,離不開《野生動物保護法》《漁業法》等前置行政法律、法規的發展完善,要進一步明確相關前置法中所涉及的不法行為與涉野生動物刑事犯罪行為的界限,為準確打擊犯罪奠定基礎。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動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對動物檢疫、食品安全標準、生產加工檢查等環節進行明確,并對監管機構及其職責權限進行法律體系上的協調和統一。①參見田宏杰:《野生動物刑法保護的理念與完善》,載《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此外,還要進一步細化《生物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將野生動物保護提高到維護生物安全的戰略高度,滿足生物多樣性發展的時代需求。
2.確立全面保護的基本原則。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的重點在國家級保護動物,而非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則處于無保護狀態。比如蝙蝠等野生動物,雖不屬于國家重點保護動物,但卻是對人類健康造成重大威脅的病毒的天然宿主。因此,確立全面保護的基本原則,對預防和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具有重要意義。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2月24日出臺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決定》,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并對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的獵捕、交易、運輸陸生野生動物作出了規定,《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以食用為目的的非法獵捕、收購等行為將涉嫌犯罪,這就為今后《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進一步修改指明了方向。基于此,筆者建議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加入禁止生產、經營使用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為食用而非法購買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同時,針對我國已經形成的野生動物繁殖加工等規模相當的產業鏈體系,應制定逐步退出計劃,促進產業轉型。
(二)完善野生動物的內涵與外延
1.明確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種類和范圍。野生動物及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范圍認定是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刑法規制的首要問題。根據《刑法》第341條的規定,該罪懲罰的是非法侵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構成犯罪的行為,因此,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認定是該罪入罪的前提。但我國《刑法》未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范圍和種類作出明確規定,《解釋》第1條亦未予以明確,而是將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認定權力賦予其他法律法規及國際公約,而我國的相關名錄對一些關鍵類群并未完全覆蓋。故筆者認為,應當進一步明確珍貴動物與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范圍,并由相應機構審核公布,避免照搬國際公約規定的物種將其直接納入名錄進行刑法保護,同時做到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分級保護。
2.區別馴養繁殖的物種與相應的純野生動物物種。動物分為野生動物、人工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和家禽家畜。生態意義上的野生動物應當界定為生存在天然自由狀態下或來源于天然自由狀態的雖然已經短期馴養但還未產生進化變異的各種物種。《解釋》認定刑法意義上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馴養繁殖的物種,有違文義解釋規則,超出了一般公眾的認知范圍,易造成法官裁判量刑畸重的后果。如“深圳鸚鵡案”,該案一審法院的裁判未對行為對象作充分考量,未區分侵害純野生鸚鵡與馴養繁殖的鸚鵡的社會危害性的差異,從而導致量刑畸重引發社會爭議,二審法院作出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改判,并得到了最高院的核準。①參見涂俊峰、李磊:《如何認定出售人工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的行為》,載《人民法院報》2018年5月3日,第1版。故應當區別對待野生動物與馴養繁殖的野生物種,對于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的要體現從寬的立場,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確保有關案件裁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三)規范犯罪構成要件及犯罪競合問題
1.主觀上是否“明知”應以一般人的標準認定。由于《刑法》未對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進行明確規定,司法審判實踐中對行為人主觀上“不明知”的辯解極少采納。但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根據,在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時亦不容忽視。如非法狩獵罪,行為人在訴訟中往往辯解自己不知道是禁獵區或者禁獵期,如果確有證據證明其不知這些要素的存在,則很難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在此情形下,對于如何用證據證明行為人應當明知則成為構成此罪的關鍵因素。如果行為人所在地的當地政府公布了禁獵區、禁獵期等文件,或有相關宣傳報道,則根據一般人的認知能力,可以知曉該規定,進而推定行為人的“明知”。②參見史運偉:《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刑法規制實務研究》,載《三峽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對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能夠認識到犯罪對象為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等情形亦可根據一般人的認知標準進行判定。
2.正確處理犯罪競合問題。不同犯罪侵害的具體法益不同,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各罪名之間,以及與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之間,極易構成犯罪競合。從上文的分析可知,審判實踐中,罪數的認定和罪名的確定均存在一定分歧。首先要完善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相關罪名的規定,解決該罪罪名之間區分困難、適用模糊等問題。如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和非法狩獵罪,從現有規定來看,非法狩獵罪包含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犯罪手段和犯罪對象,但又有時間、地點和方式方法的限制,而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更側重對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故兩罪存在一定范圍的重合,應當進一步厘清兩者保護的重點。其次要結合具體案情,準確運用犯罪競合理論進行定罪量刑。如行為人持槍獵殺野生動物的行為,雖然持槍獵殺是破壞野生動物的手段,但持槍行為屬于可分性的犯罪行為,即便行為人不實施獵殺野生動物的行為,亦侵害了非法持有槍支罪的法益,故對于此類競合情形,應予以數罪并罰。對于行為人采用同一獵捕工具或方法,同時造成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和一般野生動物破壞的情形,由于犯罪行為具有不可分性,一行為造成了多結果,故應根據想象競合犯的理論擇一重罪處罰。
(四)提高刑罰威懾力
1.提高有期徒刑的適用比率和罰金刑的金額。刑罰的目的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①參見【意】切薩雷·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8頁。可見,刑罰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懲罰手段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們犯罪的動因,都存在一種經濟利益的衡量,通過對比或計算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和因此而受到的刑罰處罰,再作出一定的決策。當因犯罪行為獲得的收益遠遠高于受到的懲罰時,行為人會鋌而走險選擇收益高的行為。從調研數據來看,破壞野生動物的違法犯罪行為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僅占11.2%,當行為人因販賣野生動物獲得的收益大于受到的懲罰時,便造成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的現狀,刑罰的威懾力不足,導致《刑法》預防破壞野生動物犯罪行為的作用大打折扣。提高有期徒刑的適用比率,應根據破壞野生動物的具體情節,破壞的野生動物是否屬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態度等因素,對性質惡劣的行為,適用有期徒刑并限制緩刑。對于罰金刑的適用,司法實踐中更是適用不規范,標準不統一。對于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在罰金的適用上可以結合違法所得的金額,采取一定倍數的標準來確定,以充分發揮罰金刑的經濟制裁作用。
2.完善生態修復制度。刑罰威懾力既體現在對犯罪分子人身和財產的約束,也體現在對其內心的震懾。打擊破壞野生動物犯罪的行為,根本目的在于保護野生動物,保護生態環境。在刑罰處罰中適用生態環境修復制度,是處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的一種趨勢。雖然目前我國《刑法》沒有相關規定,但相關司法解釋中已有一定體現,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規定:“行為人及時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消除污染,全部賠償損失,積極修復生態環境,且系初犯……應從寬處理。”可見,對于情節輕微的罪犯,如果積極修復生態環境,在量刑時可以作為從輕情節。由于法律并未明確規定生態環境修復制度的具體適用,故該制度應用于刑罰中的情形并不常見。進一步完善生態修復制度,設立動物放生、繳納生態修復基金、義務勞動等補救措施,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修復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的生態效果,同時也可以深入宣傳保護野生動物的生態理念,提升社會公眾的生態觀念。
結 語
加強野生動物資源的刑事司法保護,既是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決策部署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客觀需要。當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刑事司法審判中存在的野生動物范圍認定不同、罪名罪數認定不一、主觀方面認定存在分歧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野生動物資源刑法保護功能的發揮,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需進一步明確珍貴動物和重點保護的珍危野生動物的種類和范圍,完善相關罪名規定,明確犯罪構成要素,提高刑罰威懾力,以充分發揮刑事司法預防和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