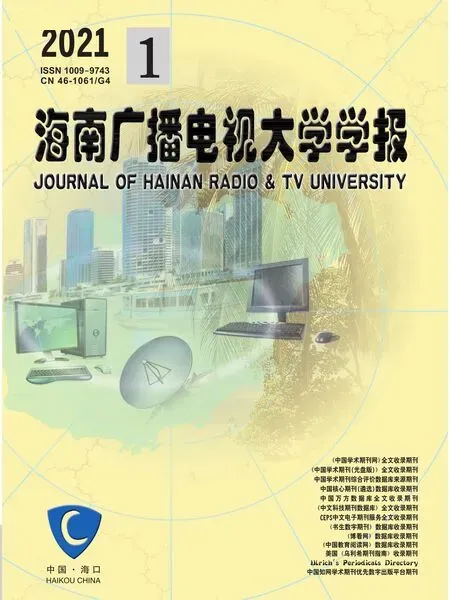論蘇童《妻妾成群》敘事空間與頌蓮悲劇成因
吳俊熹
(福州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小說被巴赫金稱為“藝術時空體”。他認為文學敘事中的時間必須在空間當中匯集、流動才能成為可見之物。20世紀以來的現代、后現代小說因其打破既往小說敘事的時間線性規律從而使得小說的空間特性更加突出。《妻妾成群》故事脈絡簡單、題材古老,但蘇童作為一個以“想象力”著稱的作家,通過對文本敘事空間的巧妙編織與虛構,使得歷史題材煥發出新的生機。
蘇童將《妻妾成群》中人物活動、情節發展主要放在了陳家府內空間中,作者似乎有意將府外空間隱藏起來。但實際上,文本中所呈現的府外空間與府內空間形成了二元對立關系。列斐伏爾認為空間不僅僅是社會關系演變的靜止的“容器”或“平臺”,相反,當今的社會空間往往充滿矛盾性的相互重疊、彼此滲透。而《妻妾成群》中出現的兩個并置空間也并非完全中斷,它們相互滲透、交疊,最后才呈現出沖突對立的尖利姿態。頌蓮也就在兩個空間的相互傾軋當中一步一步走向崩潰。
一、府外空間——精神原鄉與自由想象共同構成的“神圣空間”
應該說,府外空間是《妻妾成群》當中最重要的地理坐標之一。在《妻妾成群》當中,府外空間并非一個簡單的烏托邦世界,其本身也是泥沙俱下的。對于頌蓮而言,府外空間是她出生、成長的地志空間,同時也是給予她生存壓力、迫使她進入陳府的社會場所。但是“記憶所由產生的特定的物理環境,對人類的記憶具有廣泛的影響[1]473-474”,而且記憶并不是大腦對原生事件的儲藏,意識事件才是記憶主要涉及的內容。府外空間的客觀事實在頌蓮大腦一系列的加工、選擇、編碼之后被美化了。也就是說,實際上并不如何美好的府外空間卻是以一種美好精神原鄉的姿態存在于頌蓮的記憶當中。而頌蓮始終是以精神原鄉為參照系來體認陳府之內的生活、事物的。所以頌蓮在府內常常尋找來自精神原鄉的空間意象,從而給予自己慰藉和生存勇氣。而且在府內空間中,頌蓮又不斷給府外空間疊加有關自由的想象,最終,府外空間發酵成精神原鄉和自由想象的共同體——神圣空間。接下來,我們將從精神原鄉和自由想象兩個方面分析頌蓮的神圣空間。
進入陳府是頌蓮經歷了破產、失學、喪父之后做出的選擇,實際上也說明了頌蓮在府外空間曾經得到物質富裕、家人疼愛的美好生活。所以,當頌蓮面臨生活危機時,她難以接受這種巨大的落差:
“頌蓮記得她當時絕望的感覺,她架著父親冰涼的身體,她自己整個比尸體更加冰涼。災難臨頭她一點也哭不出來。那個水池后來好幾天沒人用,頌蓮仍然在水池里洗頭。頌蓮沒有一般女孩莫名的怯懦和恐懼。她很實際。父親一死,她必須自己負責自己了。在那個水池邊,頌蓮一遍遍地梳洗頭發,借此冷靜地預想以后的生活[2]8。”
這種異乎尋常的冷峻,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頌蓮內心深處無法表達的絕望和痛苦,還看到了府外空間并不美好的一面。父親去世、家道中落意味著孤獨、貧窮,而學業無望、繼母冷漠則代表著理想破滅、信任消失。這種物質、精神等多方面的打擊已經威脅到了頌蓮記憶中精神原鄉的美好形象,所以頌蓮才在做工與嫁人之間選擇了嫁給有錢人做小。也就是說,精神原鄉和府外空間并不等同,精神原鄉是嵌套在府外空間當中的。頌蓮逃離府外空間的行為既可以說是迫于生存的無奈,又可以說是為了維護精神原鄉的主動選擇。由此,我們才能明白頌蓮為何要去給他人做妾,否則,不管是儒家詩教人生觀還是新興知識分子人生觀都無法給此行為一個合理解釋。這次逃離退守的選擇,留在頌蓮身心之上最深刻的烙印是信任喪失,以至于她后來在陳府之內也因信任缺失而回絕了自我救贖的可能。
府外空間中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西餐社。西餐社是類似于空間門檻的特殊存在。頌蓮和陳佐千在西餐社初次見面,但陳佐千第一次去找頌蓮是吃了閉門羹的,這種行為極其符合頌蓮知識分子身份。西餐社是頌蓮自己的選擇,這也恰好說明頌蓮是以精神原鄉當中的自我形象——女性知識分子作為參照系來體認這次約會的。西餐社場景中出現了一系列密集的意象:細雨、綢傘、蛋糕、蠟燭、火苗,這些唯美的南方圖像構成了一個詩性空間。王德威曾這樣描述蘇童構造的南方世界:“南方纖美耗弱卻又如此引人入勝,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淵[3]。”西餐社所有唯美的意象,其指向也是墮落與告別——蠟燭熄滅、火苗消失、生日過完。這次見面既是頌蓮和陳佐千的開始典禮,也是頌蓮和府外實體空間的告別儀式。
家宅和西餐社是營造頌蓮府外空間最重要的兩個意象,頌蓮無意識地摘取其中美好、溫暖的圖像構成了自己的精神原鄉,甚至拒絕承認府外空間所具有的藏污納垢性質從而采取了逃跑策略。在這一過程中,精神原鄉漸漸從府外空間中剝離出來,但同時被剝去的還有頌蓮對人的信任和直面生活的勇氣,最終府外空間也就成為了高懸在頌蓮心中烏托邦式的精神原鄉。
當頌蓮進入陳府之后,不被府內空間接納的她只能在精神原鄉中追尋力量與安慰。法國哲學家巴什拉認為“家宅”不但能夠安放回憶,而且能夠安頓夢想:“由于有了家宅,我們的很多回憶都安頓下來,而且如果家宅稍微精致一點,如果它有地窖和閣樓、角落和走廊,我們的回憶所具有的藏身之所就更好地被刻畫出來。我們終生都在夢想中回到那些地方[4]6。”對此,海德格爾也有類似看法,戴維·哈維指出:“海德格爾的反響在這方面很強烈。‘空間包含著被壓縮了的時間。這就是空間的目的之所在。’對記憶來說最重要的空間就是家——‘把人類的思想、記憶和夢想結合起來的最偉大的力量之一。’因為正是在這個空間里,我們才懂得了夢想和想象[5]273。”頌蓮的精神原鄉是以“家宅”為原型的,當她在陳府當中苦苦掙扎的時候,她對于自由的想象不斷疊加在精神原鄉之上,久而久之,精神原鄉又容納了她關于自由的想象。最后精神原鄉與自由想象合為一體,構成了獨屬于頌蓮的神圣空間。
頌蓮初進陳府,經歷了毓如的漠視鄙夷、卓云的笑里藏針、梅珊的橫刀奪愛。她被夾在悵然與悲哀之間,彼時她在紫藤架旁聯想到的是自己在府外空間的學生形象。頌蓮向陳佐千討要項鏈,發現陳佐千眼中的自己和其他姨太太并無差別,她感到自身理想形象的破滅,而后,她看到飛浦時又想起了大學里那個獨坐空室拉琴的男生。頌蓮備受冷眼、孤獨失寵之時,出現在她腦海中的自我形象是母親懷里的小女嬰,她用來為自己慶生的食物是來自府外空間的四川燒酒和鹵菜。總之,精神原鄉和自由想象是頌蓮在府內空間遭受挫敗時的力量源泉。而梅珊與府外醫生的地下戀情、常年在外經商的飛浦與頌蓮的曖昧關系,帶給頌蓮的則是關于戀愛、性的自由想象。這些有關性、戀愛的自由想象都來自于府外空間的滲透,投射在頌蓮的精神原鄉之上,也就成就了頌蓮個人宇宙中的神圣空間。
二、府內空間——肉體監獄與心靈陷阱的異托邦空間
頌蓮在秩序井然的陳府中苦苦掙扎、明爭暗斗,但最終淪陷崩潰的悲慘故事是整本小說的敘事主線。所以在《妻妾成群》中,陳府構成了文本當中的顯性空間。對于頌蓮來說,陳府是一個包含了肉欲、錢欲等多種物質需求的特定場域,也是頌蓮的行動域。但這種物質需求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對于男性的依附之上,顯然,府內空間就如同一個豢養金絲雀的鳥籠,是衣食溫飽之處,更是禁錮的囚籠。
頌蓮是陳家的四太太,府內空間也就是頌蓮的婚姻生活場所,而這種婚姻關系的本質是肉體交易。府內空間的競爭是殘酷的,四個女人爭風吃醋、相互競爭,頌蓮在府內能憑借的只有她令陳佐千迷戀的新奇性體驗、在床上的熱情與機敏。左拉對于西方世界十九世紀的婚姻有過這樣的論斷:“就這樣變成了講究實利的愛情,草草交易,就像交易所里的買賣一樣[6]368-369。”而府中的頌蓮同樣是以肉體為資本進行交易,從而得到府內空間的物質滿足。從陳府角度來看,陳佐千并不在乎女人們的內斗、心理需求、性需求,僅將女人視作自身肉體欲望的發泄場和生殖工具。陳佐千也并不希望女人出現不符合自己要求的行為,而想要掌控肉體就必須從精神、心靈上規訓一個人。所以掌管府內空間的陳佐千建立的是一個以控制肉體為目標的全景敞式結構——肉體監獄,此空間對女性的規則是:一個女人能給予的肉欲體驗、感官刺激越多,她的物質條件、身份地位也就越高。
在作為肉體監獄的府內空間當中,仆人是極為重要的運作機器。仆人主要有三個作用:監視、規訓、懲罰。仆人監視著頌蓮的一切,如雁兒偷窺頌蓮房事、梅珊的女仆打斷頌蓮房事等。初進陳府時,頌蓮被仆人們判斷出的身份是陳家的窮親戚。仆人的反應似乎是府內空間對頌蓮的下馬威,頌蓮用以回擊的寒意并無作用,仆人依舊笑話她。這是府內空間對頌蓮的第一次規訓,頌蓮穿著學生裝,而仆人們卻問頌蓮是誰呀?怎么這么厲害?這種集體無意識行為是府內規則的外化,即女性知識分子在府內空間與其他攀附男權的女人并無差別。當梅珊外出偷情被發現后,仆人又起到了懲罰作用——將梅珊扔進井里。陳佐千本人也曾多次直接對頌蓮的行為表達不滿,如陳佐千一把推開當眾親吻他的頌蓮,他認為頌蓮作為一個女人不應該抽煙和戴帽子。這些都是對于頌蓮肉體的規訓,在府內空間當中,女人除了用肉體爭取陳佐千的寵幸、迎合陳佐千的癖好以外的肉體行為都是不正當的。如此,就構成了一個以陳佐千為中心、以眾多仆人為零件的肉體監獄。
蘇童曾這樣說《妻妾成群》:“痛苦中的四個女人,在痛苦中一齊拴在一個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氣中互相絞殺,為了爭奪她們的泥土和空氣[7]124。”女性在肉體監獄中依照規則競爭,非常規的競爭關系使得女性表現出弗洛伊德所說的“偏執癥”——被迫害妄想、嫉妒妄想和夸大妄想。而后,她們將這些系統化的妄想癥落實為相互廝殺、爭奪物質的手段,同時還總結出一套適用于府內空間的扭曲畸形的心靈法則。毓如的法則是視如無睹、置若罔聞,卓云的法則是毫無原則、諂媚奉承,梅珊的法則是撒潑耍賴、母憑子貴,雁兒的法則是暗送秋波、陰毒詛咒,女人們憑借各自法則獲得了在陳府空間當中生存的物質和地位。這些以心靈異化為代價的法則同樣影響了府內的頌蓮:頌蓮在陳佐千50大壽這天反思自己是什么,頌蓮并不喜歡府內的自己,但她很快就認為這種反思是耍小性子而且對她的生活有害無益;梅珊也曾勸頌蓮以生育換地位,所以頌蓮在發現自己那攤污血時備受打擊;頌蓮還學著卓云放棄底線,對陳佐千說:“今天你想干什么都行,舔也行,摸也行,干什么都依你[8]76”。心靈法則不僅異化心靈,而且異化人際關系。女人為了用肉體爭取更大利益而形成了相互監視、迫害關系。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頌蓮逼雁兒吞草紙一事:在頌蓮受到冷落又懷胎無望時,她恰好看到雁兒用于詛咒她的草紙,頌蓮“渾身顫抖著把那張草紙撈起來,她一點也不嫌臟了,渾身的血液都被雁兒的惡性點得火燒火燎[8]63”,在這樣非人狀態下,她逼迫雁兒吃下那張惡心骯臟的草紙。令人更加驚奇的是,雁兒為留在園內選擇吃下草紙,我們在這對主仆之間的對話、行動中,好像看到了兩個畸形異化的女人——兩個怪物在相互博弈。頌蓮這種喪失理性與人性的狀態,正如尼采所言:“若往一個深淵里張望許久,則深淵亦朝你的內部張望[9]119。”果不其然,受迫害的頌蓮也惡毒地害死了雁兒。這些心靈法則如同欲望陷阱,與肉體監獄相互補充,既鼓勵女性以肉體換取利益,又讓女人忙于內斗而失去反抗的可能。
米歇爾·福柯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中曾提出一個“異托邦”概念,“異托邦”是存在于真實空間又超出這一空間并表現出迥異性質的空間。府內空間使得頌蓮并未遠離故土卻與故鄉遙不可及;讓女人忘掉曾經、放棄未來,只考慮如何以肉體換取當下利益。府內空間超出常規空間,通過肉體監獄和心靈陷阱的嚴密監控,從而使得府內空間與府外空間的連續性中斷,也就構成了一個異托邦世界,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制造出受規訓的個人[10]354”。
三、二元對立的空間沖突與頌蓮悲劇成因
張從皞認為:“異質性和差異性空間的二元并置是蘇童小說空間安排的基本邏輯[11]。”《妻妾成群》同樣存在空間的二元對立,這種二元對立的空間形式反映了現代社會價值文化與傳統封建道德秩序的矛盾,又同頌蓮內心沉迷物質欲望與追求精神理想的糾結心態互為呼應。對頌蓮來說,空間沖突的結局是神圣空間的破碎,而后她發瘋崩潰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具體討論空間沖突與頌蓮悲劇成因之前,我們必須注意到府內空間包含的特殊空間——花園。府內空間通過肉體監獄和心靈陷阱進行嚴密監控,中國傳統建筑又是體現權力、身份的高度秩序化空間,而花園是處在正常倫理秩序邊緣的另類空間。正因為花園具有這樣的邊緣性質,所以在花園中才能容納具有逸出府內空間傾向的行為和想象。首先,頌蓮在園中的住所是后花園的南廂房,這是一個遠離陳府中心(飯廳)的地志場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部分肉體、心靈的規訓。所以在花園當中,頌蓮能與飛浦相遇、相知、相愛、分離,頌蓮能窺見梅珊與醫生的曖昧動作。正是這些不能被府內主流空間容忍的行為帶給了頌蓮關于自由戀愛、自由逐愛等聯系著府外空間的想象。但花園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由空間,花園仍然是府內空間的一部分,頌蓮在花園中也接受了監視、規訓、懲罰。所以花園本身就蘊含著空間沖突性質,而具有復雜性質的花園也同樣是頌蓮復雜性格的空間化象征,花園的邊緣性質也表明了頌蓮在府內空間邊緣性地位。
花園作為性質復雜的空間,既是府內異托邦世界的一部分,又容納了向往神圣空間的頌蓮,那么此處的空間沖突就會表現得格外明顯。頌蓮是穿著白衣黑裙的學生裝被抬進花園的,而后她卻遭到了在場仆人的嘲笑,這實際上就是府內異托邦對頌蓮神圣空間的示威,頌蓮按照府內空間規則換上旗袍后才恢復了氣色,后來雁兒也因不滿朝學生吐唾沫,學生裝與旗袍的對立實則反映了其背后空間的沖突。頌蓮始終是以精神原鄉作為參照系來體認生活的,她對于愛情和婚姻的想象也是如此,她認為自己在陳佐千眼中是和其他女人不一樣的,所以頌蓮在索要項鏈時聽到陳佐千提及其他女人會十分不滿、在陳佐千提出變態要求時會放聲哭泣,但是陳佐千作為府內空間的掌權者只不過將頌蓮看成一個肉體交易工具——婊子,雙方認知上的對立沖突也就反映了文化層面的空間沖突。陳佐千還曾專斷地收走了頌蓮從府外帶來的至親遺物——簫,簫實際上是頌蓮精神原鄉中關涉親情的空間意象,此后頌蓮對雁兒的兇狠、對陳佐千的冷漠實則是對府內異托邦世界踐踏她精神原鄉的報復。但頌蓮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空間沖突后,陷入了府內空間的心靈陷阱,她剪到卓云耳朵、間接害死雁兒。但是受害的不僅僅是卓云和雁兒,頌蓮用以體認生活的參照系——精神原鄉也逐漸崩塌了。頌蓮初進陳府,在井邊聯想到的是女學生形象,而頌蓮精神原鄉中的自我形象正是女性知識分子,但是在府內空間扭曲畸形的心靈法則影響下,現實生活中的頌蓮在追求物質、地位的過程中逐漸異化了。花園中的井就像一面鏡子,頌蓮每一次臨水自照都反映出她異化之后的形象,但是以女性知識分子形象體認自我的頌蓮并不敢承認自己的墮落,反而不斷安慰自己(剪到卓云耳朵之后認為是自己不小心)。井中的自己與精神原鄉是相悖的,而精神原鄉對頌蓮極為重要,所以頌蓮對于井的恐懼才會不斷加深。當雁兒的死訊傳來,頌蓮再也不能自欺欺人,所以她感覺自己“死到一半”,實際上就是頌蓮用以體認生活的精神原鄉正在崩塌。
頌蓮在欣賞菊花時初見常在府外經商的飛浦,在受到冷落時得到飛浦的安慰,后來還借由飛浦聯想到了大學里的男同學。頌蓮與飛浦兩人身上都具有府外空間的某些特質,所以才會相知相愛。飛浦還帶給了頌蓮自由愛情的想象,甚至幫助頌蓮找回了喪失已久的信任和勇氣。但兩人都處于府內空間的肉體監獄當中,受到嚴密的監視和規訓,所以在頌蓮和飛浦相處時,總是被來自府內空間的力量打斷,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空間沖突,而這種空間沖突集中體現在頌蓮向飛浦表白時:頌蓮的心里有一種陌生的欲望,但此時飛浦的激情只能徒勞地在眼里洶涌澎湃,他的身體只能僵硬地維持原狀。飛浦的身體失控是肉體監獄長期規訓所致,飛浦內心涌動的人性已難以突破長期被規訓的肉體。梅珊和府外醫生的地下戀情則是帶給頌蓮自由想象的另一個途徑,但梅珊的命運卻是被投入井中。物傷其類,兔死狐悲,此刻頌蓮的自由想象也已完全破裂。
由此,構成頌蓮神圣空間的精神原鄉和自由想象都在空間沖突中消解。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對于神圣空間有過這樣的解釋:“教堂作為宗教徒的神圣空間,就是他們世界的基點和人生意義的來源[12]398。”神圣空間的崩潰意味著頌蓮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她用以體認世界的過去經驗和想象未來的生活期許。對于《妻妾成群》,蘇童曾說:“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個關于‘痛苦和恐懼’的故事呢[7]125?”頌蓮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神圣空間,為此,她逃離了自幼成長的府外空間而進府做妾。她的“痛苦和恐懼”實際上是對于神圣空間破碎的痛苦和恐懼,當頌蓮神圣空間在空間沖突中消亡時,其悲劇命運也就無可避免了。
《妻妾成群》是蘇童1990年前后完成的中篇小說,女性知識分子頌蓮神圣空間破碎、無處容身的悲劇遭遇似乎折射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無處安放理想的精神迷惘和心靈陣痛。蘇童以舊瓶裝新酒方式,將書中考察人性的敘事空間與現實生活的歷史空間勾連起來,用一夫多妻的古老題材表現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從而賦予這一歷史題材更深刻的時代內涵。同時,蘇童《妻妾成群》遠離歷史敘事的線性思維,在架空歷史的空間中展示了個體生命的憂郁凄涼,也是一次對空間敘事的藝術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