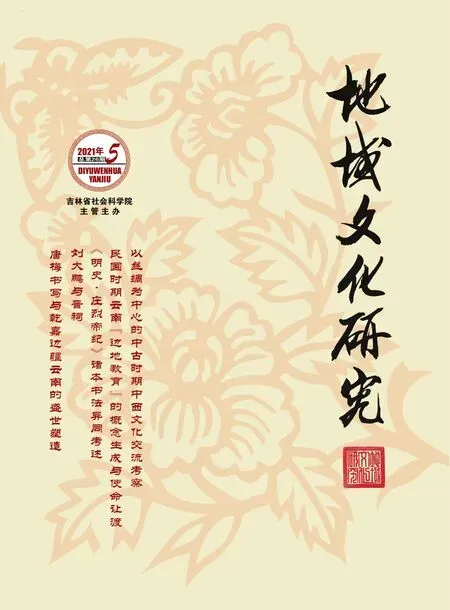江左玄學盛,儒道釋交融
——六朝時期的江蘇儒學
徐勝男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在維護封建統治方面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并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意識形態。承接漢代的魏晉南北朝亂世,則缺少治世儒學發展所必需的政治、經濟及人文條件,但該時期的儒學并非停滯、瓦解,而有著其獨特的發展特點,并取得了相應的成就。在這段歷史中,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皆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在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總的來說,當時南方思想文化水準比北方高,所以江南地區,特別是江蘇地區①江蘇是近現代行政概念,六朝時期江蘇地區的行政區劃經歷了諸多變遷。三國時期,今江蘇北部屬曹魏,南部則屬孫吳,中部的淮南地帶則為曹魏、孫吳對峙之地。魏于彭城(今徐州)置徐州,吳建都建業(今南京),置揚州。西晉統一之后,在今江蘇省境內江北置徐州,江南置揚州。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由于南北紛爭,江蘇省的政權歸屬與政區劃分頗為混亂,綜合來說,是在政治、民族、軍事、地理形勢等因素的影響下,逐步走上了淮北(淮河以北)、淮南(江淮之間)、江南(長江以南)三大地域分途異向的演變歷程。(詳參胡阿祥《魏晉南北朝時期江蘇地域文化之分途異向演變述論》,《學海》2011年第6期),可以說是當時的天下文樞,也是儒學發展的重鎮所在。因此在六朝儒學的整體特點之外,東吳、東晉、南朝分別代表了不同時期江蘇儒學的發展情況,是江蘇文化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魏晉南北朝儒學發展的思想背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發展的思想背景主要有兩個:一是玄學的興起與影響;二是“儒”的內涵變化。玄學興起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思想現象,也是該時期儒學發展的第一背景。①魏晉玄學是在兩漢經學的矛盾下發展起來的,玄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潮,主要盛行于荊州以及江東一帶。湯用彤在《魏晉玄學論稿》中曾將魏晉玄學思想的發展,粗略分四個時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以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詳參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0頁。漢末以來,儒家思想不斷受到沖擊,逐漸失去了鞏固統治、維系人心的作用,儒家名教陷于衰落的危機中。儒學式微的同時,帶有自然無為特點的新的思想形態玄學開始興起。但玄學并非清虛寡欲,而是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魏晉的玄學家,都是屬于世家大族這個大地主階層,他們在行為上,恰恰和老莊的學說相反,過著放蕩縱欲,腐朽糜爛的生活,因此魏晉之際的玄學清談,表面上也主張崇尚自然,而實質上是在替世族大地主的放蕩糜爛生活找理論依據。”②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94頁。從而鞏固世家大族地主經濟的發展與地位。在思想領域,魏晉玄學以其新穎的本體論、方法論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玄學的影響下,該時期的儒學分化出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一是玄學化儒學,即魏晉“新儒學”;二是正統儒學或傳統儒學的延續和發展。③李中華:《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頁。經學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傳統經學之外,受魏晉新儒學影響而產生了玄學化經學,即在儒家經典的解釋中融入道家思想,重義理,不重章句。④玄學化經學,如何晏《論語集解》、王弼《周易注》等,其一改漢代煩瑣注經的舊習,重義理詮釋,以玄學的虛無為所本之道,改造儒家經典,開一代新風。以玄理闡釋儒學思想者,其后還有郭象《莊子注》《論語體略》,韓康伯《易·系辭》,以及南朝梁時皇侃的《論語義疏》等。當然,對玄學思想持反對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如西晉裴頠《崇有論》、東晉孫盛《老子非大賢論》、東晉范寧《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紂論》等,皆對玄學思想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玄學化經學之外,延續傳統儒學的魏晉經學則有范寧《春秋榖梁傳集解》、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干寶《周易注》等。
其次,該時期的“儒”在內涵上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道教、佛教、玄學、儒家思想多元發展的歷史時期。在儒學統治地位松動的背景下,儒學與道教、佛教思想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交融。因此該時期的儒家,其內涵及標準比漢代寬泛得多,尤其是漢末以后,面對玄學與佛教的沖擊,儒家思想對法家思想多有吸納,“因為魏晉以后,很難再有‘純儒’或‘純法’的學者……已經擴大了內涵的儒家思想,進一步世俗化、民間化和政治化,并強調‘軍國得失’‘君臣之義’‘公私之別’‘安上治民’等具有經世意義的原儒精神……從理念形態和價值理念上看,凡不排斥仁義道德,承認六經及孔子的地位并正面征引儒家經典,主張禮法對社會的作用,強調崇教勖學、任賢使能等,基本上均可劃為儒家范疇。”⑤李中華:《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7頁。
二、三國時期的江蘇儒學
漢末儒家思想式微,但承漢末亂世而來的魏、蜀、吳三國政權仍對儒學持支持態度。曹魏政權中,曹操用人不重道德名節,唯尚其才,依靠名法之治統一北方。曹操雖一定程度上毀敗儒家倫常,但對儒學十分倡導,其所任用之人,雖有不仁不孝之徒,但更多的是具有儒士風范的儒吏,如王朗、王肅、劉劭、高堂隆、王粲等。此外,曹操、曹丕等掌權者均曾采取選才任賢、興學著書、尊儒祀孔等一系列舉措。劉備建立蜀漢政權,以漢室后裔自居,以復興漢室為己任,更以儒學維系人心,以儒治蜀,興學業,立博士,任用儒士,推行經術等。又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玄學之風并未影響到巴蜀之地,因此蜀漢有頗多正統的儒學之士,如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姜維等。
江蘇儒學與魏、蜀兩國關系甚疏,僅能從江蘇籍士人身上略窺一斑,如曹魏政權中的陳琳、桓威等。①陳琳,建安七子之一,廣陵射陽(今江蘇揚州寶應)人;桓威乃下邳(今江蘇邳州)人。他們出仕曹魏,雖于儒學方面貢獻較少,但卻是曹魏政權中“江蘇儒士”的代表。相較而言,東吳政權的儒學色彩最為濃郁,代表了該時期江蘇儒學的成就。東吳政權的儒學特色首先與統治集團主要人物的階級出身有關。曹操出身寒族,以名法為治,用人尚才不尚德。劉備雖以漢朝宗室自居,但淵源甚遠,實質上亦是寒族,而重臣諸葛亮則是世代相傳的法家。由此可見,曹魏與蜀漢為政之道本質上大致相同。而東吳統治者則出身于服膺儒教的統治階級,與兩晉統治者的階級性相同,這也是東吳與兩晉尤其是東晉之間的另外一種淵源。孫氏世代在吳地為官,在張、朱、陸、顧等強宗大族及地方豪族的擁戴之下建立政權,這些東吳大族也因擁戴有功而成為操縱東吳政治社會的主要勢力,成為后來門閥世族的前身。世族政治特征使東吳具有了更多儒家色彩,“東吳政權重門第,而維持門第繁榮的最好手段則是文德與武功,故東吳多以經術傳世者。其政權亦顯示了儒學的特色。”②李中華:《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7頁。東吳政權的儒學色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官方興儒的堅持與努力,另一方面是東吳官員深厚的儒學素養。孫氏統治者本身即十分重視對后代的儒學教育,對官方興學也不遺余力,如景帝孫休于永安元年(258)下詔興學。詔曰:
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③(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158頁。
在重儒興儒的大環境之下,東吳政權所任用之人也多具深厚的儒學修養,甚至以儒學晉身,如張昭、顧雍、諸葛謹、闞澤、唐固、謝承、程秉、顧邵、步騭、士燮等。東吳時期已具有了門閥籠絡政治的特征,其弊端無須贅述,但門閥政治長久興盛也絕非門閥士族尸位素餐所能維持,其中世家大族對后代儒學教育的重視便是保證門閥興盛的重要原因。
東吳政權的首都始建于吳郡(今江蘇蘇州),后來孫權筑石頭城而遷都于建業(今江蘇南京),其為江南地區的開發做出了重大貢獻,也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東吳政權時期的儒學發展代表了三國時期江蘇儒學的最高成就。但整體上,政治沖突、軍事斗爭是貫穿東吳政權始末的主要矛盾,其無暇顧及思想文化建設,官方倡導儒學的措施也未有明顯成效。東吳政權所團結的一批儒學人才則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維持東吳統治,使其成為三國中最后一個滅亡的政權。
三、東晉時期的江蘇儒學
東晉江蘇儒學的發展首先要從西晉儒學以及兩晉之際南北文化播遷說起。司馬氏通過“高平陵事變”掌握了曹魏政權,并用十幾年的時間鏟除了曹氏集團及其他異己勢力,最終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雖然西晉政權的建立悖于儒家倫理,但為維護統治,仍對作為封建階層統治思想的儒學十分重視。司馬昭為晉王時便隆禮重樂,命朝廷儒臣撰訂新禮,以服務新政權。晉武帝司馬炎即位之初便確定諸郡中正薦舉賢才的六項標準,以舉賢任能,還實行了建明堂、行鄉飲大射之禮、祀孔子、起國子學、置博士、倡孝道等一系列恢復儒學的措施。此外,西晉君主還親臨指導儒學教育,晉武帝、晉惠帝都曾親臨辟雍,身體力行,親身講學。西晉也出現了一批儒學之士,著名大儒有杜預、傅玄,名儒還有皇甫謐、夏侯湛、摯虞、束皙等。但西晉的統一只是曇花一現,其儒學發展也隨著永嘉之亂以及西晉的滅亡戛然而止。
永嘉之亂后,西晉皇室后裔司馬睿在長江以南建立東晉政權,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司馬睿即為晉元帝。西晉南渡成為東晉,北方士族也隨之南渡,這些北來世家大族一方面成為東晉新政權拉攏依靠的勢力;另一方面,他們依靠軍功與才德維持世族的權力。由此形成了東晉門閥政治的現實,這種門閥勢力是自東吳即存在的,“西晉滅吳之后,吳境強宗大族勢力并未消失。因為未消失,所以能反抗洛陽的統治。洛陽政府采取籠絡吳地統治階級的綏靖政策,然而未收大效而中州已亂。”①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頁。東晉的建立也多賴江東世族之力,由此南渡的中原名門望族與江南的土居氏族成了東晉王朝的統治階層,這些世族大地主掌握著東晉社會政治的命脈,君權則十分羸弱,始終沒有形成中央集權的權威。當然,兩晉之際的南渡并不僅僅只是政治變動,在文化傳播上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河洛地區興起的玄學以及在玄學影響之下產生的新儒學,隨永嘉南渡被帶到了江南地區,從而影響了東晉南朝儒學、經學的發展。②就世傳的《十三經》注而言,漢人與魏晉人幾乎各居其半,其中魏晉時人所注有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周易注》,何晏《論語集解》,范寧《谷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其中大部分由西晉南渡傳入南方。皮錫瑞指出“魏晉人所注經,準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徑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壞于三國志分鼎,再壞于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見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13頁。玄學南渡之后,儒學統一北方,南北思想形態不同,加之雙方的地理隔離,從而形成了經學上的南學、北學之分。南學除《詩》《禮》遵鄭玄外,皆以魏晉注為主,如王弼《易》、孔安國《書》、杜預《左傳》等,北學則仍以漢學為宗,初步奠定了南學約簡、北學深蕪的發展局面。
東晉江蘇儒學的發展是從對玄學的反思開始的。東晉初建總結西晉滅亡教訓時,十分注重對思想意識形態的考察與反思,視玄學為導致中原淪喪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體現在許多政治家及有志之士的只言片語中,更直接體現在從理論形態上對玄學進行的系統化批判中。葛洪是最早著書批評玄學的人,其雖是道教大師,但對儒學十分推崇,他的《抱樸子外篇》便以儒家立場自居,批評玄學背棄禮教的放達之風敗壞倫常。范寧也指出“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的現狀源始于王弼、何晏,故作《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紂論》以崇儒抑俗。此外,戴逵、孫盛、王坦之,袁宏、范宣等人都對魏晉玄學持批評態度。除了思想層面上的批評之外,東晉統治者還致力于恢復儒學。三國至兩晉,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儒學屢立屢廢,但只要政局穩定,統治者都會不遺余力地倡導儒學。東晉一朝,內亂外患不斷,復興儒學也多是有始無終,但是中央和地方復儒興學的努力一直在進行。東晉始建之初便敦崇儒學,明經興學,王導、戴邈、荀崧等人紛紛上疏主張重視禮教,崇儒興學。晉元帝時又置史官,立太學,修禮學,立經學博士九家①《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荀崧上疏請增立《儀禮》《公羊》《谷梁》及鄭《易》四家博士,因王敦之難未得實行。②詳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977-1978頁。太興四年(321),元帝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除了倡立國學之外,東晉君主本身也熟習儒家經典,并多次講經。③“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并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并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權以中堂為太學。”(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99頁。中央倡儒之外,儒學之士在地方的教授活動也未曾停止,范平、杜夷、范宣、范汪、范寧等人,都曾講學一方,傳授弟子。但東晉政局動蕩,先后有王敦叛亂、蘇峻謀反、殷浩西征、桓溫北伐、王恭叛亂、桓玄篡逆、孫恩盧循起義等一系列事件,內憂外患頻仍致使東晉儒學不能真正復興。
整體上,東晉的儒學在官方手中并未有較大的成就,儒者多世家傳習或個人修習,儒士們講學鄉里的個人行為也成為對官學不振的一種補償。盡管如此,儒學在東晉政權中仍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東晉皇權的統治力極為軟弱,“東晉政權所以能夠維持下來,實由儒學的宗法倫理觀念在統治階層中仍然客觀地在起著支配作用。”④劉振東:《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3頁。統治階層權臣觀念里儒家基本的君臣之別、上下之義是維系君權權威的一絲微弱的思想力量,因此王敦、桓溫、桓玄、劉裕等權臣即使有不臣之心,也不敢輕易冒天下之大不韙。可以說,自漢代以來,儒家倫理思想深入人心,即使在君權軟弱的亂世,也依然能夠形成一股強勁的思想的力量,規約著為臣者的基本政治行為。
四、南朝時期的江蘇儒學
晉室南渡之后,形成了南方東晉與北方十六國之間的對峙,南北朝是這種分裂形勢的繼續,其中南朝有劉宋、南齊、南梁、南陳四朝,北朝則包含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朝。南朝皇權微弱,世族強大,故南朝儒學的發展首先需面對門閥政治的歷史現實。世家大族憑借世資,占據高位,并在莊園經濟的保障下,不斷鞏固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他們還以門閥相標榜,強調門第望族的優越感與士庶之別,使六朝成為典型的世家貴族型社會。“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諸方面都有固定的優越地位,因此都只孜孜于保持他們家門富貴。君統的變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與己無關。在禪代廢立之際,世家大族不是不與聞,便是幫忙篡位,均以自己門第利益為轉移。”⑤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7頁。柳詒徵也曾陳述過此觀念:“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旗,帝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當時士大夫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于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搖動,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①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1頁。貴族門閥勢力在南朝政權的更迭過程中,僵化成為可與皇室相抗衡的半獨立政權與壟斷力量。
思想上儒道玄佛相交融是儒學在南朝亂世中面對的另一個歷史現實,“大一統的觀念瓦解,正統思想失去了約束力,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隨之發生變化,從統一的生活規范,到各行其是,各從所好。”②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5頁。該時期王權衰落、儒家思想落潮,玄學極端發展至南朝時也已引起玄學內部及儒家學者的不滿。與此同時,道教逐漸發展壯大,佛教興起并急劇膨脹,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負擔。面對佛教對儒學的沖擊與挑戰,知識分子分成反佛與崇佛兩大陣營。反佛的儒家學者有何承天、周朗、郭祖深、范縝、荀濟等。儒家致力于抑佛時,對玄學的批判力度大為下降,相反還常常孔老并提,援引玄道思想以對抗佛教。故在反佛的大趨勢下,玄學的本體論、道教的自然主義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儒家學者吸收,儒道思想得到進一步融合。而崇佛的知識分子也多倡佛而不反儒,主動援儒入佛或援佛入儒,因此他們雖推崇佛教,但在思想深處仍以儒學為宗。由此南朝儒學一方面吸收了魏晉的名法和兩晉的道玄,顯出儒與玄的融合;另一方面,在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又表現出儒與佛的融合。
在門閥政治及思想多元的亂世現狀下,各朝掌權者對儒學都十分重視。雖然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在軍事、政治、思想、文化等發面都發生急劇變化,但就儒學的發展而言,可以說從未中斷。儒道玄佛等思想雖存在著沖突矛盾,但從當權者的角度而言,儒學仍然是主流的意識形態。因此各政權都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并采取制禮作樂、改定歷法、撰史修文、開館興學等舉措。《南史·儒林傳》對南朝興儒情況做過總結:
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后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帝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③(唐)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730頁。
盡管在南朝的政治斗爭及政權更迭中,儒家綱常倫理被徹底踐踏,但統治者每以違背儒學理念的手段取得政權之后,又總是企圖以儒學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因此南朝的統治者在倡導儒學方面十分用心,更在梁朝形成了儒學大盛的局面。南朝各政權大多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而且統治者們多熟習儒家經典,不僅個人修習儒學,對儒學也十分倡導,因此,南朝帝王與江蘇儒學的關系水乳交融。
雖然有來自官方的努力,但皇權不振,朝代更迭頻繁,往往興儒的努力尚未取得成果,便已改朝換代。因此南朝儒學的發展帶有明顯的亂世特征,其較少以官方的、集體的、全面的、長久的形式出現,更多的是民間的、個人的、局部的、暫時的。大致而言,南朝儒學的成就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代表性儒學人物的出現;二是士人階層較高的儒學素養;三是經學上南學統一北學。
南朝儒學的代表性人物,有劉宋時期的雷次宗、何承天、顏延之、何尚之,南齊的王儉、劉瓛、陸澄、顧歡,梁朝的范縝、皇侃等。劉宋儒學大家雷次宗在儒學的傳授方面貢獻突出,①雷次宗曾兩次被皇帝請到京城講授儒學,第一次是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并設祖道。”見(梁)沈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93-2294頁。第二次是元嘉二十五年(448),又征詣京邑,“為筑室于鐘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見(梁)沈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94頁。他的分科教學思想,對后世專科教育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何承天則是劉宋時期儒佛之爭中反佛陣營的代表,他秉持儒家立場,以儒家的人性論、仁義學說、入世主義等理論反對佛教理論,在形神問題上批判“神不滅”的唯心主義理論,宣揚無神論,維護儒家正統。顏延之、何尚之則屬于崇佛陣營中的代表,顏延之曾與何承天圍繞《達性論》②佛教徒宗炳著《明佛論》,將有生命的事物總稱為“眾生”,并證明有所謂“因果報應”“六道輪回”。《達性論》是何承天反駁《明佛論》的哲學論文,其論證人為貴,乃天地萬物的中心,不能與其他生物并列為“眾生”。《達性論》站在儒家立場、根據儒家經典思想批駁佛教的觀點,收入在《弘明集》卷4。進行爭辯,與著名藝術家宗炳結成同盟,顏延之駁斥《達性論》,宗炳非難《白黑論》③《白黑論》,劉宋高僧慧琳著,載《宋書》第97卷。該文以白學先生喻指儒、道,以黑學先生喻指佛學,通過白、黑兩先生的問答,論述三教異同,指出三教均為圣人之說,各有所長,倡導三教并立、三教融合。并對佛教的緣起性空理論予以駁斥,也因此遭僧眾圍攻。宗炳非難《白黑論》,何承天與宗炳就《白黑論》有過相關論辯,是南朝形神之爭的一部分。,成為支持佛教的中堅力量。何尚之與顏延之一樣,崇儒又不斥佛,他對佛教濟世之功進行了透辟的闡釋,稱揚佛教在維系世道人心、輔助現實政治中的巨大作用,開后世“佛法輔政論”之濫觴。對齊代儒學有促進作用的在朝有王儉,在野則有劉瓛。王儉官職地位較高,大力推行儒學,成為一時儒宗,著述頗豐。④王儉在儒學方面的成就主要在目錄學領域,曾校勘古籍,依劉歆《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同樣出身于瑯琊王氏并有儒名的還有王儉的叔父王僧虔。王僧虔(426-485),字簡穆,好文史,善音律,尤其留意雅樂。曾因“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疏進言。劉瓛學貫當時,為一代大儒,以其學識與品格影響一代學風。著名道教學者顧歡也是儒學的傳承人,他前半生治儒,堪稱老子學大家,其母去世后,隱遁不仕,于天臺山開館聚徒。他晚年信奉道教,著有《夷夏論》,雖站在道教立場上排抑佛教,但是卻是以儒家的尊夏卑夷為出發點,借儒家“夷夏之防”的民族觀否定佛教在中國傳播。梁代儒學貢獻突出的則是無神論斗士范縝以及經學大師皇侃。范縝出身儒學世家,反對佞佛,著有《神滅論》,主張注重現世人生,反對報應思想;主張無神,反對佛教的神不滅和人死為鬼的說法。梁朝儒家學者、經學家皇侃則撰有《論語義疏》,以老莊、玄學釋經,不拘家法,隨意發揮,是南朝玄學化經學的代表作。
南朝儒學的成就,不僅體現在上述幾個重要人物身上,還更多地體現在活躍在各個領域,堅持儒學立身,并積極踐行儒家宗旨的士人身上。這也是南朝儒學成就的第二種體現,在梁陳時期表現最明顯。梁代是南朝儒學發展的高峰,陳朝則是梁朝的余緒,梁陳時期出現了大量以儒學名世的儒學人物。名儒有徐勉、周舍、朱異、賀琛、孔子祛、何佟之、賀玚、嚴植之、明山賓、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縝等。另外還有一批經史兼通的學者,如沈約、阮孝續、蕭子顯、裴子野等。又有文學家、文藝批評家鐘嶸、劉孝標、劉勰等。梁代儒學的繁榮是全方面、整體性的,出身于不同階級,活躍在文學、政治、軍事等不同領域的士人,均以儒學立身,甚至有卓越的儒學成就。如朝臣朱異以儒學知名,將軍羊侃也頗具儒家風度。當然,梁朝儒學之盛尤其鮮明地體現在名儒、碩儒的集中出現上,他們開堂講學、制定禮儀、著書立書,又多以“五經博士”的身份言傳身教。主要有明山賓、孔休源、賀琛、司馬褧、伏曼容、何佟之、范縝、嚴植之、賀玚、崔靈恩、沈峻、孔子祛等。作為當時的大儒,他們均有學術貢獻,禮學方面尤其顯著。如天監初年,梁武帝蕭衍詔求通儒治五禮,開五館并置五經博士,于是有掌治吉禮的明山賓,治嘉禮的司馬褧,治兇禮的嚴植之,治賓禮的賀玚,另有多次擔任五經博士的沈峻。此外,又有致力于講學、治學的伏曼容、何佟之、崔靈恩等人。梁代儒學之盛與梁朝統治者的態度相關,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對于秩序穩定性的迫切需要。南朝動蕩的政局致使其難以為儒學的發展提供長治久安的基本保障,但官學不興,儒學不振的局面,并不代表儒學的徹底衰微。相反,從上述對南朝儒學及儒學人物的梳理來看,儒學在士人心中仍然具有不可動搖且無法取代的重要地位。無論是為了維護“正統”思想,還是因為詩書傳家的意識,儒家經典都是士人階層普遍學習的文化知識。
南朝儒學成就的第三個體現是它對北朝儒學的影響,尤其是經學上的南學北傳。北朝各政權統治者多為塞北鮮卑族,或與鮮卑族有密切關系的漢族,他們建立政權、謀求發展的過程其實是少數民族政權實現并發展封建化的過程,這必須依靠不斷加深漢化程度才能實現。少數民族漢化“實質不過是以傳統的封建制度的上層建筑為模式,不斷地構造和完善自己的上層建筑體系。”①劉振東:《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03頁。封建制度的核心思想便是儒家的社會原則與思想,因此北朝各政權均積極學習、吸收儒家文化,其崇儒興儒的目的與效果更加顯著。加之北朝本身已有雄厚儒學基礎,故儒學在北朝有一定的發展。南朝江蘇儒學對北朝儒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士人的流動與交流上。其中北魏雖南儒寥寥,但卻形成了北朝重儒的傳統,在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持續產生影響,余波綿延至隋唐。北齊曾出現一批知名的儒者,見于《北齊書·儒林傳》《北史·儒林傳》,其中有幾位曾在江蘇為官,如張雕、李廣,也有途徑江蘇之人,如祖鴻勛,亦有江蘇籍儒者,如劉逖、顏之推、袁奭、江盰,其中以顏之推最為有名。北周沈重為南人入北,王褒、庾信等也都是入仕北周的南朝儒生。此外,蕭?、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宗懔、劉璠、柳霞等都是南朝舊臣入仕北周。當然,南朝儒學對北朝儒學的影響最主要還是體現在經學上南學的北傳。《隋書》卷七五《儒林傳》中曾總結南學與北學: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②(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705-1706頁。
北學以漢學為宗,傳鄭玄之學,重章句,故保守細致。而南學受玄學、佛學的影響,以義理解經,不拘家法,兼采眾經,故南學重義理、輕經文,不重傳注而多興“義疏”之學。關于南學與北學的區別,前人多有論述,如范文瀾在《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一文中指出:“南北朝時期,北朝儒生保守漢儒煩瑣經學,南朝儒生采取老莊創造新經學。所謂南學簡約,得其英華(要義);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煩瑣)。就是南北學的區別。”③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238頁。雖然由于地理隔閡,南朝、北朝之間存在文化差異,但二者并非完全隔絕,南北學術之間存在一定的溝通與交叉。如劉宋時期北魏占領了青州、徐州,新學北傳,其進一步結果便是南北朝之后經學統一,北學折于南學。《隋書·經籍志》總結經學統一的情況,《易》則“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①(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13頁。《書》則“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②(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15頁。《春秋》則“《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③(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33頁。即隋朝統一后,繼承漢末儒學傳統的北學漸漸式微,而繼承魏晉新學的南學則成為經學正宗,即經學統一,有南學而無北學,南學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至于北學并入南學的原因,皮錫瑞解釋說:“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是當時北朝稱羨南朝之征。經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里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余,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④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5-136頁。其實,南朝儒學的地位與影響之所以能逐漸回升,是歷史趨勢使之然。“由宋至梁,幾個政權的統治者所以逐步加強對儒學的倡導,內在的原因是世族階層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地位開始由盛轉衰,新起的掌握政權的豪族勢力感到作為世族階層代表性意識形態的玄學思想,對確立和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并沒有什么效用,鑒于魏晉的教訓,他們不得不重新強調儒學這種傳統的思想武器。”⑤劉振東:《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3頁。
結語
自漢代以來,思想學術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即“道統”與“政統”之間的較量暗潮涌動,文士階層以知識、道德為武器與權力對抗,以此獲取生存空間。這種文化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矛盾,在皇權不振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得到了緩和。君權羸弱導致權力下移,各掌權的士族門閥又通過教育的方式掌握了文化話語權,儒學知識成為世家大族教育傳承中的普遍知識。在官學不振的背景下,儒學更是依靠這種家世的傳承而綻放出別樣的風采。即使這一時期的道、玄、佛等思想都十分興盛與活躍,但其都具有儒學底色,秉其思想的文士也都不乏儒家風范。在這一段歷史中,江蘇地區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在儒學的發展傳承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歷史作用。東吳雖于儒學上少建樹,但其保留了儒學傳統以及儒學發展所需的士人基礎,東晉雖亦不能推進儒學發展,但儒學仍以星星之火的態勢維系著封建君臣倫理。南朝時期玄學沉寂,儒釋道多元思想相融合,逐漸形成了重新肯定儒學作為社會統治思想地位的大趨勢,儒學回溫也為新的大一統國家的建立準備了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