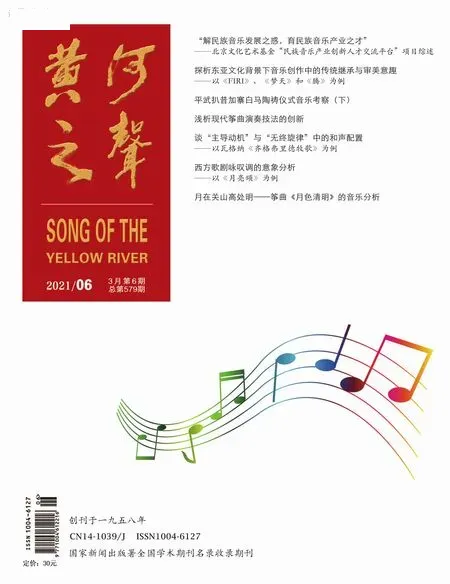西方歌劇詠嘆調的意象分析
——以《月亮頌》為例
高 涵
一、《月亮頌》作品簡介
(一)歌劇《水仙女》簡介
《水仙女》是一部三幕歌劇,作者為德沃夏克,講述了水仙女魯薩卡愛上了人類王子后被王子拋棄,最終王子死去換得她回到水中的愛情故事。
魯薩卡愛上人類王子,想去陸地生活,向森林女巫獻祭聲音換取人類的身份。王子對魯薩卡無法說話感到苦惱,婚禮上愛慕王子的外國公主對魯薩卡出言嘲諷,王子聽后竟然去傾慕熱情的外國公主而厭倦魯薩卡。這時老水仙來婚禮看望自己的女兒,發現王子拋棄了魯薩卡,詛咒王子永遠無法擺脫魯薩卡的愛情,隨即帶著魯薩卡進入了湖水中。王子嚇得跪倒在外國公主面前求救,卻只得到公主的嘲笑。森林女巫告訴魯薩卡變成人類的水仙女被人類拋棄后只能過著痛苦的半人半精靈的生活,而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要破解只能取王子的性命來換回魯薩卡的生命和靈魂。王子聽到后向魯薩卡懺悔,最終用生命換回魯薩卡水仙女的身份。
(二)詠嘆調《月亮頌》簡介
《月亮頌》節選自歌劇第一幕,魯薩卡在人間遇到了傾慕的王子之后,又與他失之交臂,帶著對王子無限的眷戀返回水中。這一唱段前面承接的劇情是:魯薩卡告訴自己的父親自己愛上了人類王子,想要去陸地上生活,魯薩卡的父親再三勸告、警告無果后,悲憤中告訴魯薩卡她應該去找森林女巫求助。老水仙離開后,魯薩卡對月唱出了這曲詠嘆調。
二、歌劇中的審美意象
(一)審美意象
“意象”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原本“意”與“象”是分開的,意是審美主體的心意狀態,象是審美對象的感性形象,二者經過歷代哲學家、美學家的研究和歸納,逐漸融合、總結成為一個詞語。即對象的感性形象與自己的心意狀態融合而成的蘊于胸中的具體形象。
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藝術家通過藝術表現手段將自己的意象訴諸于作品,以此向欣賞者敞開這一意象世界。但藝術創作不能將藝術家的意象世界完全轉化,因此藝術作品總是對欣賞者保留一定的自由,同時藝術作品也在欣賞者的不斷欣賞和闡釋中不斷地被發掘和揭示出新的方面和更深的層次。藝術的本體就是審美意象。因此,我認為這一中國古典美學概念也可以運用在西方藝術作品的美學分析中。
(二)歌劇中的審美意象
在中國古典美學看來,意象是藝術的本體,意象也是美的本體。歌劇作為一種藝術,其本體也應當是意象。意象是情與景的內在統一,是一個完整的有意蘊的感性世界,歌劇的本體也是一個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
歌劇的本體是審美意象,歌劇的創作就是意象的生成。但歌劇藝術的創造過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從作曲者到表演者再到欣賞者,經歷了兩次創造。在歌劇藝術中,第一次藝術創造是作曲家由創作素材生成審美意象,以曲譜的形式表達出來。第二次藝術創造是表演者以作曲家創作的曲譜融合自己的心意狀態,生成了復合作曲家和表演者二者審美意象的意象世界,再以表演的形式呈現給欣賞者。在第二次創造過程中,表演者既是意象的欣賞者--在表演者的欣賞中曲譜的意象世界才得以呈現;表演者同時也是意象的創造者--將自己胸中的意象呈現給觀眾。
葉朗在《美學原理》中將藝術作品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材料層、形式層和意蘊層。歌劇藝術作品也可按照這種層次結構加以分析。
材料層是藝術作品的物質載體,承載了“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飛躍。歌劇作品作為一種音樂作品,其物質材料是聲響。歌劇作品的物質材料層對歌劇的美感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它會影響意象世界的生成。西方歌劇中的西洋樂器和美聲唱腔都是構筑其意象世界的基礎。另一方面,物質材料會給予觀賞者一種質料感,例如花腔女高音常給人一種歡快的、靈巧的質感,男中音則給人一種渾厚的、有力的質感。質料感帶有情感色彩,能夠給作品營造一種氣氛,使歌劇的意象中充滿一種韻味,從而成為歌劇作品美感的一部分。
形式層是藝術形象的物化,可分為內形式和外形式。內形式是藝術家創作時已形成但未能傳達出來的藝術語言;外形式是作品呈現給欣賞者的形式符號。外形式本身也具有形式美。這種形式美相對獨立于歌劇的意象世界本身,可以體現在表演者的炫技上(如唱高音、長音或出音律高、音高變化幅度大的裝飾音等)。這種技巧美可以孤立的被觀眾欣賞,引起人的驚奇感和快感,同時也能融入整個歌劇的意象世界,從而具有審美價值。
藝術作品的意蘊是直觀欣賞作品的感受和領悟,很難用邏輯判斷和語言“說”出來。意蘊還帶有多義性、寬泛性、不確定性和無限性。多義性、寬泛性和不確定性意味著不同的欣賞者對同一藝術品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和領悟,而作品經過不同的欣賞者不斷地體驗和闡釋,就有不斷的新的方面被揭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歌劇作品不斷被演出、被觀看的過程,也是它的美感和意蘊不斷顯現和生成的過程。
藝術的形式層和意蘊層都具有復合性。從形式層來說,歌劇的曲譜、文本是它的第一形式,演唱、演奏是它的第二形式。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都含著歌劇藝術的意蘊,但作為一種音樂表演藝術,歌劇的意蘊對于欣賞者而言主要在于第二形式的演唱、演奏。
三、詠嘆調《月亮頌》的審美意象分析
(一)材料層分析
《月亮頌》是一首女高音詠嘆調,在劇情中是由魯薩卡——水仙女,水中精靈這樣一個角色來演唱的,所以其音色除了女高音本身所具有的清晰、明亮以外,還帶有一種空靈、柔美的色彩。在歌劇中,先由豎琴演奏一段引子,引出交響樂的前奏。豎琴的音色高雅、純凈,前奏中豎琴演奏的琶音像是月下泛著波紋的湖水,營造出靜謐、優美的氛圍。管弦樂的伴奏在前奏和間奏中保持了靜謐的氛圍,但在尾聲中演奏了高出音率的低音,然后不斷向上推動,將樂曲推向高潮,管弦樂的變化象征著魯薩卡心情的變化。作曲家通過豎琴及其它管弦樂器的配合,營造出了樂曲的氛圍。
(二)形式層分析
《月亮頌》全曲共127小節,其結構是“引子+A+B+連接部+A1+B1+尾聲”。
引子共22小節,在歌劇中引子開始前有4小節的豎琴音階演奏鋪墊,銜接了引子部分前3小節的屬七和弦上行琶音。后接5小節的下行和弦,引入管弦樂隊,前3小節力度為ff,從豎琴的下行和弦開始漸弱,至管弦樂隊合奏部分轉為pp。前奏表現出魯薩卡內心渴望到陸地上與王子一起生活,對水妖的身份感到掙扎的情緒。平緩、柔和的管弦合奏為后面A段的演唱鋪墊,營造了神秘而幽靜的氛圍。
A段為23小節到46小節,是魯薩卡對月亮傾訴。音區偏低,曲調比較平緩柔和,像是較為平靜的娓娓道來、緩緩訴說。第31小節到第37小節和第39小節到第45小節的詞一樣,但是音高上移了,體現出情緒的遞進,表現了魯薩卡愈發激動的情緒同時為B段作鋪墊。
B段為47小節到62小節,開頭就是一個八度的大跳,整段旋律中跳進較多,節奏律動感加強,伴奏織體更加豐滿,音響效果更加明亮。這一段魯薩卡對王子的思念從婉轉、溫柔變為激動、無法抑制的吶喊,對月亮的傾訴也從平緩的訴說逐漸變成激動的祈求。
63小節到67小節是樂曲的連接部,63、64小節節奏快、力度變化大、出音律高,延續了B段強烈、激動的情緒,65小節開始音高下降、力度漸弱,到66小節結束時最弱,表現出魯薩卡情緒的平復,以承接A1段。
A1段(68小節到93小節)、B1段(94小節到109小節)是A段和B段的變化再現。A1段B1段和A段B段在情緒上是遞進的,所以這個部分是更激動的、更急切的,尤其是B1段,即將連接情緒最緊張的尾聲,這里相對于B段的變化就是要讓魯薩卡的情緒更推進、更激動,表現出魯薩卡對王子的向往、對去陸地上與人類王子共同生活的想法變得堅定,決意去陸地上追求愛情。
尾聲為110小節到127小節,110小節到116小節是一段間奏,和連接部的旋律、節奏基本相似,但是在114小節從pp做了漸強,116小節漸弱,到117小節人聲進入處最弱,間奏部分的器樂演奏保持了樂曲整體的情緒和完整性。117小節到120小節,演唱的力度為p,音高全部在較低的d1,節奏快,此時表現的是水仙女對月喃喃自語的場景。121小節開始,旋律層層推進,力度漸強,歌詞均為“月亮啊,留下吧”,124小節是全曲的高潮,125小節的降b2是全曲的最高音,力度最強,也是情緒爆發的頂點,之后全曲結束于調性主音的八度大跳,收在了魯薩卡澎湃的情緒上。這種戲劇性很強的高音和大跳在表演上本身也帶有一種技巧美。
曲式作為歌劇的外形式,它的形式符號與生活具有較為直接的對應性。例如引子部分的豎琴演奏就對應著靜謐的自然環境中的水波,平緩進行的A段對應著演唱開始時魯薩卡較為平靜的情緒,B段、尾聲的音高上移和八度大跳都對應魯薩卡激動、急切的心情。這些形式符號構筑出一個完整的意象世界,引導欣賞者從外形式進入內形式。外形式本身也具有其形式美,《月亮頌》工整的曲式、優美的旋律與和諧的配器本身都具有形式美。而內形式更接近作品的意蘊,下面就內形式和意蘊展開分析。
(三)《月亮頌》中的移情作用
《月亮頌》全曲的內容都是魯薩卡對月亮訴說自己對王子的眷戀和思念,其實是將王子的生命移置到了月亮上,將魯薩卡的情感與遙遠的月亮同一化。月亮本身是無生命的,但在詠嘆調中,魯薩卡的情感賦予了月亮生命和力量,此時歌曲中的“月亮”不是物理的、客觀的天體,而是意象世界中的月亮,是作為一種審美對象的存在。
歌劇中的形象是藝術家借助形象手段將自己的藝術發現和審美經驗揭示出來的產物。這種藝術發現雖來源于生活經驗,但其創作的形象化手段往往需要將藝術形象與純粹的生活形象拉開距離。這種距離是對生活經驗、生活形象的一種取舍,以此去把握更深刻、準確的生活本質和情感內涵。在《月亮頌》中,移情作用將人的情感移置到月亮上,這種愛情的形象與生活中愛情的形象拉開了距離,摒棄了功利性和過度的熱情,從而凝練出更令人共情的藝術形象。
移情作用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意象世界是一個情景相融的感性世界,《月亮頌》以魯薩卡對王子的情與寂靜的月夜湖邊的景相交融,使觀眾能夠身臨其境,與情境“物我同一”,以達到對作品意蘊的領悟和感受。
(四)意境與飄逸
意境是超越具體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從而對整個人生、場景、歷史、宇宙獲得一種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飄逸是中國文化史上,以道家文化為內涵的一種審美的大風格。飄逸有三個特點,一是超越時空的闊大,二是逸興遄飛的美感,三是人與大自然融而為一的境界。飄逸的文化內涵是精神的超脫和人與自然生命的融合為一。意境與飄逸都具有超越時空的特點。
《月亮頌》以月為象,“月”是一個相對遠的意象,它能把人的思緒從有限的歌劇舞臺延伸到無限的時空中,引發觀眾的思念、眷戀、惆悵。這種感興超越了“情景交融”,在與藝術家的情感達到同一性的基礎上得到了自我確診,在藝術形象的啟發下產生了自己的情感。觀眾在欣賞《月亮頌》時,也化身為魯薩卡展開審美活動。這時產生的審美感情和自我確證超越了與魯薩卡的共情,是欣賞者自己的情感,更加親切和自由。
《月亮頌》中,魯薩卡移情于月,向月亮傾訴對此刻不知身在何處遙遠戀人的思戀,本身就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無限感,使角色的情感不再局限于一隅舞臺,而是擴散到了整個“月光漫游的世界”;而月作為一種思念的象征,能過引發欣賞者更遠的思想和情感,體現出一種闊大的效果。魯薩卡是湖中的水仙女,詠嘆調的配器上多用豎琴演奏琶音以制造月下湖面水波的效果,營造林中湖邊的靜謐美感。人的情感與月的形象融合為一,塑造出清新自然的藝術形象。
魯薩卡追求超越物種、超越時空限制的愛情,其精神是自由超脫的;《月亮頌》的藝術形象是人與大自然的生命融為一體的。這都體現出飄逸的審美特征。
(五)魯薩卡的悲劇性
真正的悲劇是由個人不能支配的力量所引起的災難卻要由某個人承擔責任,是以個體生命毀滅的形式來肯定人類生命中正面價值的美學范疇。
在《水仙女》中,魯薩卡追求的愛情是純潔的、甘愿為其奉獻一切的;但魯薩卡獻出聲音、改換身份以得到與王子結合之后,卻遭到了王子的拋棄,她的愛情被毀滅了。魯薩卡對愛情的追求,其實也是一種對超越物種、身份的自由的追求。魯薩卡被王子拋棄和王子最終為魯薩卡獻出生命,都體現出一種宿命感,一種無力抗爭命運的感覺。《水仙女》第一幕,魯薩卡告訴老水仙自己向往成為人類同王子在一起時,老水仙告訴她這樣勢必付出巨大的代價;王子拋棄魯薩卡時,老水仙警告他永遠無法擺脫水仙女的愛情。而最終,魯薩卡失去了愛情,王子失去了生命,魯薩卡的抗爭失敗了。劇作中不可調和的矛盾,以情感和生命的毀滅作為終結。但這種毀滅引發了欣賞者內心的震撼,它帶給欣賞者對命運的恐懼感,但也令人對魯薩卡產生憐憫。魯薩卡為了自由愛情的抗爭在悲劇中顯得渺小,情感也被命運所吞噬,但卻給人們心中留下了純潔、勇敢的藝術形象。
而在詠嘆調《月亮頌》中,預示了魯薩卡的悲劇。水面與月亮的距離,象征著作為誰仙女的魯薩卡和作為人類的王子在身份和物種上的差距。魯薩卡在詠嘆調中不住的請求月亮留下來,其實是盼望王子留在她身邊;但月亮的移動不會因魯薩卡的請求而改變,不專情的王子也不會因為魯薩卡的心意而專注于魯薩卡。魯薩卡向月亮請求,希望王子能在睡夢中想起她,“哪怕只有一剎那”;而魯薩卡獻祭聲音和水仙女身份求得的王子的愛,連二人的婚禮都沒能維持過去。《月亮頌》出現在整場歌劇的第一幕,這種與后續劇情所對應的預示感與《紅樓夢》中的十二判詞有些相似,都在后續情節中一一應驗,在“命運”的力量下,魯薩卡自由愛情的理想被毀滅了,她愛情的悲劇實際上是命運的悲劇。
結 語
《水仙女》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悲劇,魯薩卡追求超越身份、物種的自由的愛情,卻又被命運打敗,失去了自己的愛情。而《月亮頌》這一唱段,集中表現了魯薩卡對自由愛情的向往與期盼。《月亮頌》旋律優美、情感充沛,從審美上來說,也以音樂的手段構筑了一個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并且超越了具體的場景和物象,讓人能感受到包含了人生感的惆悵與美感。對《月亮頌》進行意象分析,一方面是幫助表演者從第一形式上理解從而更好的表演,另一方面是有助于欣賞者從第二形式中領會、體悟作品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