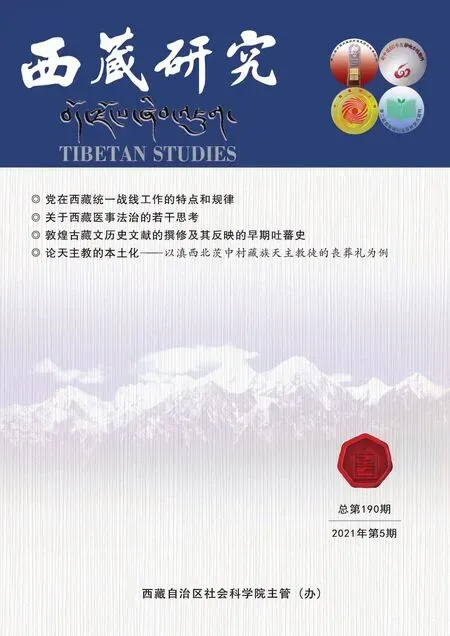和平解放70年來西藏城市的發展
李馨妤
(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2)
西藏地處中國西南邊疆,毗鄰四川、云南、新疆及青海等省區,并與尼泊爾、印度、不丹、緬甸等國接壤,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中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和生態安全屏障。西藏城市作為各民族相互交往的空間載體,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發展體系,對維護邊疆安全、民族團結以及推進中華民族發揮著重要作用。和平解放70年來,在中央大力支持、全國人民支援和西藏各族干部群眾艱苦奮斗下,西藏城市迎來全新發展機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為新時代的城市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隨著國家邊疆安全戰略上升到新高度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西藏城鎮化建設日益受到學界關注,對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城市發展特征與原因進行回望、研究和探討,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和平解放70年來西藏城市發展軌跡
和平解放以前,受制于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西藏城市發展動力、結構功能、空間布局以及類型體系等發展十分緩慢。和平解放后,西藏城市逐漸實現從局部到整體、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型,具體而言,以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與改革開放為重大時間節點,可劃分為四大歷史時段。
(一)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1951—1959):革新與束縛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民主改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社會發展的措施,推動了西藏城市的發展。首先,中央多項財政優惠政策為西藏城市建設奠定了經濟基礎。這一時期,中央政府大力推動西藏國營商業建設和邊境貿易發展,于1952年成立了西藏國營貿易總公司,隨后將商業網點擴展至日喀則、昌都等地。其次,投入大量財力、人力與物力,修通了川藏、青藏、新藏等公路,大大改善了西藏的交通條件。再次,在中央政府與人民解放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西藏建成了一批包括機關住房、郵電所、電站、交通運輸站、氣象站、醫院、學校、銀行、影劇院等公共設施。
這一時期的西藏城市建設雖開始起步,但受制于封建農奴制度,西藏城市生機和活力受到嚴重束縛,仍不具備進行大規模城市建設的基礎。“從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8年間,各地只建成一些必要的供電、醫療、文教衛生等公共設施”[2],這期間西藏的城建進程十分緩慢。直到1955年,拉薩“仍然保留著過去封建社會時期的面貌”[3],與中國內陸城市發展存在較大差距。
(二)西藏民主改革至自治區成立(1959—1965):穩定與發展
從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開始至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西藏經歷了一個貫徹穩定發展方針,鞏固民主改革成果的階段。這五年多時間,實際上是西藏徹底完成民主改革和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的時期。”[4]這一時期,西藏城市處于較為穩定的發展時期。
一方面,西藏經濟得到持續而穩定的發展。全面武裝叛亂平息后,為促進經濟發展和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中央政府在西藏開展了有計劃有步驟的“四反雙減”運動(1)“四反雙減”指反叛亂、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剝削、反封建特權和減租減息。,有效清除了西藏殘余的叛亂分子,穩定了生產秩序,安置了大量貧民、游民,推動了西藏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伴隨經濟的發展,學校、醫院與救濟機構等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也相繼出現。在民主改革中,“西藏建立起第一個供銷社、第一個農村信用社、第一所民辦小學、第一所夜校、第一個識字班、第一個電影放映隊、第一個醫療衛生機構”[1]29。1959年底,“拉薩市區建立居民委員會28個,先后安置8700多名貧苦游民和乞丐就業,救濟8500多名生活困難的貧民,收容了一批孤、老、病、殘者”[5]162,拉薩市區修建了勞動人民文化宮、革命展覽館、新華書店、劇院、銀行、郵電、招待所等設施,建筑面積達15萬平方米。1960年,納金水電站正式建成發電,拉薩市居民首次用上了電燈,這是民主改革和黨的穩定發展方針帶來的成果,也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結出的碩果。
(三)西藏自治區成立至改革開放(1965—1980):徘徊與前進
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至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這一時期,西藏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逐步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社會制度的偉大跨越,西藏城市發展既開啟了偉大歷史轉折,又歷經了一些頓挫,但最終在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下走上持續健康發展之路,整體呈穩步發展之勢。
1965年西藏自治區的正式成立標志著西藏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西藏人民廢除農奴制、實現民主改革以后的又一偉大勝利”[6]285,西藏城市發展由此走上了全新發展道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開啟了有計劃的現代化城市建設。一是西藏各級城市建設與發展逐步進入社會主義軌道,并“形成了72個數百人至萬人的規模不等的城鎮”[7]。二是隨行政區劃調整與基層政權漸趨穩定,西藏地區以各級政府所在地為基礎,開展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初步形成以拉薩為中心,7個行政專區行署所在地為副中心,縣城為區域次中心,包括各行政建制鎮在內的城市發展體系,奠定了西藏現代城市體系基本格局。
西藏自治區成立不久,全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鑒于西藏特殊區情,在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特殊關懷下,中共中央與西藏各級黨委、革委會仍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規定和措施,使西藏“并未像內地一樣具有相當破壞力,從而保證了西藏城市秩序相對穩定”[5]250。1971年3月,根據《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的報告精神[8],西藏自治區黨政領導進行新一輪調整,有效糾正了“文革”前期西藏受到的沖擊和破壞,穩定了西藏局勢和城市秩序。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會議形成《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開啟了西藏建設和發展的新時期。
(四)改革開放至今(1980—至今):創新與跨越
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立了“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邊防,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強起來”[6]301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的穩定與發展,先后召開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并根據現實情況做出重大決策部署。在歷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指導下,西藏城市各項事業取得全方位進步和歷史性成就,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顯著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脫貧攻堅全面勝利,新型城鎮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40余年,西藏城市發展水平呈穩步提高和跨越式發展之勢。據統計,1978年至2019年,西藏城鎮常住人口從20.2萬人增長至110.6萬人,城鎮化率則從11.3%提升到31.5%[9]13,城鎮數量增長至142個,增長了近4倍。與此同時,西藏城市經濟總量持續增加,產業結構持續優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持續加大對西藏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制定了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涉及財稅、金融、產業發展等各個領域。1978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為6.65億元,及至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900億元[9]21,城市經濟實力明顯提升,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并建立了包含清潔能源、天然飲用水、農畜產品加工業、民族手工業、藏醫藥、建材等在內的富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10]。涉及城市市政、旅游、文化教育、體育、醫療衛生、能源等領域的援藏項目,惠及西藏七地市,輻射范圍廣,直接推動了西藏城市自身造血功能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隨著城市經濟、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西藏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根本改善。
2015年,西藏自治區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部署新型城鎮化推進工作,并出臺了《西藏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同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為各族群眾走出農牧區到城鎮和企業就業、經商創業提供更多幫助”,李克強總理強調“要將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為推動西藏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黨的十九大以來,立足于國際國內新的形勢,黨中央在深刻總結治藏、穩藏、興藏成功經驗基礎上,形成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西藏城市進入全新戰略發展機遇期。2020年西藏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長10%[10],西藏城鎮人民生活已全面邁入小康時代。
二、西藏城市發展演變特征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因特殊高原地理環境、邊疆戰略地位及政策優勢,西藏城市發展演變既有全國城市發展的一般共性,又呈現出獨有的個性。
(一)西藏城市發展呈現出空間上的失衡
總覽和平解放70年來西藏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可見西藏城市演變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存在“歷時性”的轉折與頓挫。同時因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條件,西藏城市發展也存在“共時性”的失衡,即城市地域空間分布上的不均衡。
青藏高原群山糾互,地勢或起或伏,或環抱或舒展,區域內部自然環境差異巨大,加之西藏區內外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優先向拉薩市等政治中心、次中心城市配置,導致小城市發展動力不足,因而西藏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西藏城市分布“區域間呈現巨大的不平衡性”[13],即城市主要集中于西藏南部和東部地區,而西藏西北部則分布較少。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隨著行政區劃的調整與重構,西藏建置城市分布漸趨穩定且在交通要道、邊貿重鎮之地興起一批城市,藏北“無人區”也因開發需要興起了一部分縣級城市,西藏城市空間分布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因高原內部地域自然環境與人文條件的差異性,西藏城市空間分布仍呈現出“東南多于西北”的不均衡特點且城市之間相距甚遠。20世紀70年代,西藏縣級及以上建制城鎮合計71個,其中以拉薩市、日喀則(2)現為日喀則市。和山南專區(3)現為山南市。為主的“一江兩河”地區,以昌都專區(4)現為昌都市。為主的藏東地區,共有56個[14]221,占全區城市數量的79%,而以阿里、那曲專區(5)現為那曲市。為中心的地區,僅分布著15個城鎮,占全區城鎮總量的21%。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西藏相繼建成了一批特色小城鎮,并初步形成了全區范圍內小城鎮群,有效推進了西藏特色小鎮之間、縣域之間、市(地)之間的聯系與合作,較大程度上解決了區域內城市布局不合理與發展失衡的問題。但因自然、區位、歷史等因素的制約,西藏城市空間分布格局的不平衡狀態依然存在,截至2019年,西藏共有142個城鎮,其中110個分布于西藏東部、南部及“一江兩河”地區,而廣袤的西藏西部、西藏北部地區僅分布有32個城鎮[9]3。
(二)西藏城市發展具有政策比較優勢
和平解放以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西藏城市建設,相較于全國其他大部分地區,西藏城市發展具有政策上的比較優勢。
和平解放至改革開放前夕,是西藏社會主義建設與城市化起步的重要階段,尤其是“文革”時期,在全國大部分城市發展都停滯不前的局勢下,西藏城市整體呈不斷發展態勢,甚至出現了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發展“黃金時期”。
這一時期,西藏城市規劃的編制工作隨著西藏自治區及各級政府的建立而逐漸展開并不斷調整和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相較于全國其他地區,政策機制成為西藏城市發展的助推手與加速器,尤其是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后啟動的全國性的援藏工程成為推動西藏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伴隨著各類援藏人才和外來務工人員不斷入藏,西藏各級城市規模呈持續擴大之勢,城市發展速度領先全國大部分城市。
(三)西藏城市發展具有相對滯后性
和平解放70年來,西藏地區雖因政策上的比較優勢而開啟了早期城鎮化進程并呈持續發展趨勢,但從區域對比視角分析,相對于中國內地及其他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西藏城市現代化起步較晚,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城市發展水平整體偏低。
從城市經濟發展來看,全國大部分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僅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而且開啟了早期工業化、現代化與城鎮化進程。而同一時期的西藏則依然處于封建農奴制社會,僅能開展有限的城市建設。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開始后,因西藏社會發育程度相對較低,為保持穩定發展,不同于內地土地改革完成后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西藏從1959年開始民主改革至1965年自治區成立的這幾年一直秉承“穩定發展”和“五年不辦合作社”的方針。及至1965年,隨著五年期限已過,中央同意在西藏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試辦人民公社,本著“應當把步子放得穩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實一些”[19]的原則,西藏于1975年基本完成了農牧區的社會主義改造,繼而對城鎮私營商業、民族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76年5月,西藏全區私營商業全部被納入國營商業軌道,基本實現對城鎮手工業、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相比內地西藏整整晚了20年。
受制于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我國其他城市和少數民族地區相比,西藏仍處于物質積累的階段,其城市公用設施建設明顯落后于我國大部分城市。尤其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逐漸掀開了國家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西藏地區城市與其他地區的廣大城市間的發展差距始終存在,甚至呈不斷加大的趨勢。
三、西藏現代化城市發展經驗簡析
城市發展原因來自多方面,“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經濟的、文化的、社會心理的等多方面的因素”[20]。西藏因自然、政治、經濟及宗教的特殊性,城市內生動力孱弱,推動城市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區外,外力成為首位驅動力。和平解放70年來,西藏城市建設雖曾歷經徘徊頓挫,但整體呈不斷發展之勢,取得了較大成就。究其原因,中央支持是西藏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逐步建立為城市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及全國人民的大力援建為西藏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而區內外交通的改善則為城市創造了良好發展條件。
(一)中央支持是西藏城市發展的關鍵因素
和平解放以來,西藏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中央政策的引導和支持。70年來,中央在西藏均采取了一系列有別于其他地區的措施,以穩固邊防和維護國家統一。中央對西藏采取了優惠財政措施,從1952年到1979年,“中央給予西藏財政補貼、定額補貼、專項補助、基本建設投資累計達60.94億人民幣”[21],1994年至202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機關及中央企業分9批共支援西藏經濟社會建設項目6330個,總投資527億元[10]。國家財政的大力扶持,不僅緩解了西藏財政困難,為西藏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還極大地支持了西藏城市教育、醫療衛生及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西藏城市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1965年西藏自治區的正式成立,標志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使西藏人民以新時代主人翁的姿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為西藏社會發展和進步獻力獻策,極大地解放了被封建農奴制度束縛千年的社會生產力和創造力,從根本上推動了西藏城市現代化建設與發展。同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了西藏自治機關充分行使各項自治權,有利于西藏地方據其區情制定發展策略,有益于西藏地區因地制宜進行城市建設。其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相繼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西藏確立,西藏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從而為城市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三)全國大力援建助推了西藏城市發展
為促進西藏與其他各省市的共享式發展,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采取特殊扶持政策的同時,動員全國力量大力援助西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和平解放以來,全國各地對西藏的教育、醫療、科技及交通等進行支援,為西藏城市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體現了“中央人民政府致力于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與進步的民族政策”[22]。
具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援藏工作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大力布局和實施以城市基礎設施為主的援建工程。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前后,中央各部委和北京、江蘇、上海等省市為西藏無償援建了10項工程,修建了以拉薩市人民路為中心的包括百貨商店、新華書店、中國人民銀行拉薩市中心支行、市郵政局、民航站、勞動人民文化宮、西藏革命展覽館、自治區第一招待所、拉薩影劇院等在內的25項主要建筑工程,并在城區各主要街道“鋪設了10萬平方米的柏油路面,開辟了5條市縣間的公路”[14]77,大大改善了拉薩市的基礎設施。二是在國家政策的動員和支持下,一批又一批來自五湖四海的大學生、文化工作者及工程技術人員等援藏人員,以“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為口號,大量涌入西藏各級城市,既給西藏城市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動力,又為西藏封閉、質樸的城市生活方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四)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的無私貢獻是西藏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
西藏的解放、改革與建設,都離不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的默默付出和無私奉獻。70年來,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堅持“長期建藏、邊疆為家”,在艱苦的高原條件下,不畏艱難,默默堅守工作崗位,集守衛與建設于一身,是新西藏歷史不可取代的見證者與奉獻者。一句“哈達不要太多,有一條潔白的就行;朋友不要太多,結識解放軍就行”,充分肯定了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的重要歷史地位,也直接表達了藏族同胞對其深厚而濃烈的感激之情。
(五)交通條件的改善為西藏城市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交通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大動脈,對內決定了城市規劃布局和整體發展,對外則直接關系著城市與區域內外城市之間的物資轉運、人員流動及經濟文化交流。對西藏而言,交通運輸條件對城市發展尤顯重要。西藏雖然在古代就已經有驛道、貢道、茶馬古道及車牛道與周邊地區互通有無,但受制于自然、經濟、制度及技術等因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西藏交通發展極其緩慢,與鄰接諸地及西藏地區各地之間的交通,“惟倚馱獸之背負而已”[23],西藏與外界聯系十分困難,“言商業則貨物運轉維艱,言軍事則糧秣輸送困難”[24]。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隨著青藏、川藏兩條公路的通車,西藏“羊腸小道猴子路,云梯溜索獨木橋”的交通面貌開始改變。就城市內部交通而言,從首府拉薩到各地市所在地及縣級城市,通行狀況都因城市規劃工作開展及道路橋梁本身的修建或擴建而日趨便利和合理化。就區內外交通來看,繼青藏、川藏公路通車之后,新藏、滇藏公路以及青藏、拉日鐵路也相繼通車,成為西藏與我國其他省市的交通主干線,“進藏難”成為歷史。與之同時,橋梁與航運取得新的突破與發展,西藏初步形成了貫通區內外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對于促進區際商貿、文化交流,加強西藏城鎮體系建設及城鄉互動產生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西藏已形成以拉薩市為中心、各市地為次中心,通達大部分縣鄉鎮的公路網,從中國其他省市運來大量物資,基本解決了西藏經濟生產和人民生活物資的需要。而民航事業的迅速發展則“更縮短了西藏與內地的距離,加強了各兄弟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增強了民族團結”[25],大大推動了西藏城鎮化進程。
西藏作為國家重要安全屏障與生態安全屏障[26],在西部大開發戰略部署與國家“一帶一路”總體布局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經過和平解放70年來的建設與發展,西藏城市成功按下了現代化啟動鍵,而西藏城市要實現新時代美麗宜居城市建設目標,必須以強化自身造血功能、重視區域協調發展、促進城鄉一體化、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等為著力點,以促進西藏新型城鎮化的建設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