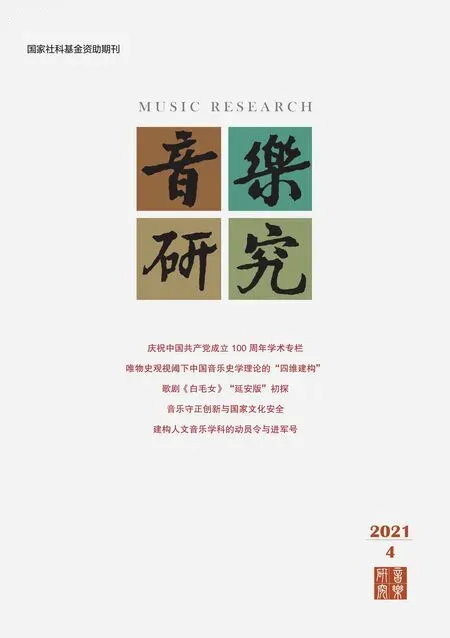“指尺”制律實乃荒唐至極
——有感于《魏漢津“以君指節為尺”真的荒唐至極嗎?》一文
文◎王 旭
《音樂研究》2020 年第2 期刊載了學友潘江《魏漢津“以君指節為尺”真的荒唐至極嗎?》一文(下文簡稱“潘文”),文章討論了北宋方士魏漢津以宋徽宗手指長度為尺制律這個音樂史上的著名事件,不同意楊蔭瀏、遲乃鵬等學者對魏漢津“荒謬、無恥”“為歷史唾棄”的批評,①楊蔭瀏:“一位無恥地取媚于統治者的音樂政客魏漢津……建議用……宋徽宗的三指的長度連接起來,作為黃鐘律管的長度。這樣荒謬、無恥的主張,果然最能投合愛受吹捧的皇帝的口味!”(《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9 頁)遲乃鵬:“魏漢津……把唯心主義的樂律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理所當然地應當受到批判,為歷史所唾棄。”(《魏漢津及其雅樂樂律理論》,《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1 期,第15 頁)認為“魏漢津‘以君指節為尺’并非荒唐至極”。②潘江《魏漢津“以君指節為尺”真的荒唐至極嗎?》,《音樂研究》2020 年第2 期,第80、81、83 頁。文章得出“魏漢津‘指尺’‘大晟律’的提出,結束了徽宗朝混亂的宮廷音樂局面”、“‘指尺’彌補了先儒提倡以黍定律尺的不足,將大晟律推上歷史舞臺”;“看似荒唐的‘指尺’背后,實際上蘊含著魏漢津并不荒唐的樂律學理念”;“‘指尺’‘大晟律’上承北周、隋、唐,下啟宋、金,不僅在北宋末年的宮廷音樂中產生著引領作用,且被金代宮廷樂官肯定,并依照其樂律理論所制造的鐘磬亦奏響于金朝宮廷。這使不同朝代、不同民族間的宮廷音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相繼承襲”;“與其說他荒唐,不如說是在封建制度逼迫下,懷著宣揚學說志向的樂官們,面對自己悲慘命運而被迫‘不擇手段’做出的無奈之舉”等結論。③同注②,第84、85 頁。
筆者拜讀此文后,認為“潘文”作者有著敏銳的學術視角——魏漢津“指尺”一事,由于與大晟律的密切關系和“指尺”本身的神秘,在歷史上備受關注,宋代以后的文獻常提到此人此事。對這一事件進行剖析,于音樂史研究有著重要意義。在史料的處理上,作者沒有“盡信書”,而是有志于“秉持客觀態度”“深挖其根源”“深入討論現象背后的緣由”“分析細節背后的含義”“做出全面評價”。④同注②,第78 頁。作者認真思考楊先生等音樂史家的評價,提出不同見解,為這一“背負‘荒唐至極’歷史罵名”的人物正名,其學術勇氣可嘉。筆者欽佩之余,也對這一學術議題產生濃厚興趣,故也在文獻中尋求線索,對“指尺”之說是否“荒唐至極”提出自己的意見。
一、從《宋史》看“指尺”制律事件始末
《文獻通考》《宋史》《金史》皆載“指尺”事件,⑤“指尺”事件載《文獻通考》卷130“樂考”,中華書局2011 年版,第3991 頁。所述大體一致。而《宋史·樂志》最為全面,現將其中關于“指尺”的內容進行摘引,并予以說明。
從北宋初年至崇寧三年(960——1104),黃鐘律的標準音高一直是朝廷雅樂改制的爭議中心。在魏漢津提出以“指尺”制律前,北宋已歷經五次雅樂改制:“建隆和峴樂”“景祐李照樂”“皇祐阮逸、胡瑗樂”“元豐楊杰、劉幾樂”和“元祐范鎮樂”。⑥“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樸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樸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后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知禮院楊杰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幾與杰參議。幾、杰請遵祖訓……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幾、杰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杰、劉幾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杰復議其失,謂出于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鼐、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宋史》卷126“樂志”,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2937——2938 頁。從《宋史》記載可見,五次改制,或以古尺為據,如和峴;或以累黍為法,如李照⑦“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宋史》卷126“樂志”,第2949 頁。、阮逸、胡瑗⑧“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宋史》卷127“樂志”,第2960 頁。、范鎮;或主張依人聲定律,如楊杰、劉幾⑨“杰言……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詔鎮與幾等定樂……幾之議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宋史》卷128“樂志”,第2981、2986 頁。。崇寧三年,宋徽宗立志對雅樂“銳意制作,以文太平”,就在這時,魏漢津提出了以徽宗指節長度為尺制律的辦法:
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余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后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⑩《宋史》卷128“樂志”,第2998 頁。
魏漢津托古黃帝、夏禹之事,提出將宋徽宗的三、四、五指的第三節長度相加,合為九寸,制成黃鐘律管,即著名的大晟律,并據此鑄成鐘鼎,最終成就當朝之樂,即大晟樂:
崇寧四年……以鼎樂成,帝……乃下詔曰:“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宋史》卷129“樂志”,第3001 頁。
可時過多年,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嘆,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宋史》卷128“樂志”,第2998、2999 頁。
原來,因徽宗忌憚“帝指不可示外人”之諱,崇寧三年的“以指為尺”一事并未付諸實施,僅“略比度之”,沒有實際測量。徽宗趕忙令時任大司樂的劉昺彌補,卻也僅出“中指寸”,而無四、五指寸。可“漢津初說”的方法是:
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宋史》卷129“樂志”,第3025 頁。
只有帝中指長度,又不得“徑圍為容盛”,如何制定度量衡?劉昺只好“匿漢津初說”,以“前議為度”,以徽宗中指長度為據制作一管長笛,卻由于中指較原來“略比度之”所得要“長”,恐引起別人的懷疑,只能“遂止”了!
這件事的最終結局是:
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宋史》卷129“樂志”,第3025、3026 頁。
《宋史》所載,事實清楚,魏漢津并未得到徽宗手指的確切長度,大晟律由樂工“隨律調之”而已,“指尺”制律一事純屬子虛烏有,大晟律、大晟樂與“指尺”之間并無實質上的關系。
二、從“身為度”析“指尺”制律是否可行
魏漢津托古于夏禹“以身為度”的史說,以示其“指尺”有據可循。“身為度”的方法真的能制尺,進而再制律嗎?
“以身為度”出于《史記·夏本紀》,原文為:“禹,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索隱按:“聲與身為律度,權衡亦出于其身。”?《史記·夏本紀》,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51 頁。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用自己的身體部位作為參照進行計量,是最簡單、自然、易得的辦法。文獻里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孔子家語》:“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孔子家語》,《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9 年版,第14 頁。《說文解字》:“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尺。”?《說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40 頁。《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小爾雅》,中華書局2008 年版,第357 頁。;等等。從以人體為法,過渡到其他物體(如樹枝、木棒等),再漸漸發展為以形態穩定的物質為度量衡標準(如以黍為度等),都是尺度發展的必經階段。
其實,關于夏代度量衡情況,除“身為度”外,還有“夏十寸為尺”?《通志》,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2 冊,第956 頁。“夏尺去二寸為周尺”?[明]朱載堉撰,馮文慈點注《律呂精義》,人民音樂出版社2006 年版,第791 頁。等記載,這說明夏代已有尺度標準器,非停留在以人身體為法的原始階段。
關于如何制定尺度,文獻里也有很多依據。《尚書》的“同律度量衡”,就是描述律、度、量、權衡四者之間的關系,即以律為首,由黃鐘律的長度標準決定度量衡的標準。《漢書·律歷志》的解釋較為具體:“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21]《漢書·律歷志》,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966 頁。度、量、權衡,都由黃鐘律的長度衍生而成。每逢改朝換代、政權更迭之時,統治者首先要確定黃鐘律標準,繼而規范度量衡。黃鐘律標準明確后,再通過累黍得出黃鐘律的長度,是為律尺,度尺則與律尺等長。經考古人員對出土文物的考校,已明確從戰國至東漢,度尺皆為23 厘米左右,[22]參見國家計量總局《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2 頁。這度尺的來源便是等長之律尺。[23]關于律尺與度尺的關系,參見鄭榮達《西漢黃鐘標稱律長與度尺考》(《黃鐘》2017 年第1 期)一文。
律、黍、尺的關系,大抵如上所述。文人士大夫們尋古法累黍不成,原因是未能正確理解累黍與律之間的關系。南宋蔡元定說:“若秬黍,則歲有兇豐,地有肥瘦,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谷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后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余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24]《律呂新書》卷2“造律”,載注?第212 冊,第22a 頁。即先明確黃鐘律高,繼而“度之以黍”。士大夫們的弊病在于無視黍的自然屬性,又不解樂律之理,“專恃累黍”,教條地遵循“九十黍”“千二百黍”等數量規定,以為找到大小合適的黍,再通過累黍就可以求得理想的黃鐘律。明代樂律學家朱載堉的說法與蔡氏大體相同:“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他認為蔡元定的制律方法是正確的:“多截竹管,權擬黃鐘,復用人聲與管相較。聲是而黍非,則易以大黍,大之而益大,至于大不得,斯則黍理已盡,若管內猶不滿,乃管之非真而當從黍也。若非證之以人聲,則黍未免失之小。若非忖之以黍數,則管未免過乎大。人聲、管黍,互相校正,于理極精。”[25]馮文慈點注《律學新說》卷2,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1、112 頁。先擬黃鐘律管,確定了管的長度,再累之以黍,管與黍相互參校,這才是定律“古法”。
魏漢津效仿“身為度”,提出“指為度”,所謂“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云云,從樂律學的角度看,十分荒謬。《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的記述,本為說明五音在治國中有重要作用,與人倫、綱紀等也緊密相關。水、火、木、金、土;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東、南、西、北、中……古人將各種各樣的事物納入五行敘述系統,目的是構建“一個宏大的、秩序井然的宇宙自然和哲學精神的統一體”[26]李玫《淮南律數新解》,載《傳統音樂軌范探索》,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 年版,第31 頁。,并非討論音樂內部規律。“指尺”說規定中指、名指和小指分別為“君——宮聲”“臣——商聲”“物——羽聲”,實無任何依據,況人的五個手指的長度不同,怎可能長短不一的三指都是“三節三寸”?這是連最基本的常識都罔顧了!這充分暴露出魏漢津對聲律的數理規律一無所知。律管制作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需要計算管的長、周、徑、冪、積,還涉及管口校正、開口閉口所導致氣柱長度變化等變量,制作材料對發音也有著制約效果,人們的吹律方法、辨別音高等經驗也起到重要作用。從科學制律的角度來看,“指尺”制律完全行不通。
魏漢津“指尺”制律,與文人士大夫們累黍制律的本質并無不同,皆無視樂律的自身規律,違背制律的基本原理。魏漢津棄黍而用“指”,只是換了一個更加極端的說法,于制律而言毫無可取。這個說法在當時起到取信于君的效果,一度掩蓋了真相,對于人們認知大晟律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制造了阻礙。
三、“指尺”是什么尺?
“指尺”制律不可行,“指尺”也并未付諸大晟律的制定,但它曾被正式命名為“大晟樂尺”:
翰學張閣請頒指尺于天下,政和元年五月六日,頒大晟樂尺。[27]《玉海》卷8,載注?第943 冊,第209d 頁。
“指尺”畢竟作為實物存在過,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尺呢?
文獻和傳世、出土實物可證,歷代都有明確的尺度標準。[28]《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載由商至清歷代尺度數據。尺度標準的制定,或沿用前代,或據前代尺改作,某一個時期的尺度,總是能通過其與前后代的聯系進行考校。后周,制律之尺稱“鐵尺”,隋、唐皆沿用此鐵尺制律。唐、宋有太府寺,專掌度量衡,其尺稱“太府尺”。后周至宋,尺度標準是相繼承襲的。[29]參見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第八章第一節“唐宋元明度量衡制度總考”,上海書店1984 年版,第217、218 頁;吳慧《新編簡明中國度量衡通史》,中國計量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5、106、121、123 頁。宋代景祐年間,李照為了降低黃鐘標準音高,放棄累黍方法,始用太府尺制律;元祐間,范鎮也用該尺又造新律。《金史》記載了金章宗明昌五年時一位樂官對此事的講述:
后周……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宋初亦用王樸所制樂……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30]《金史》卷39“樂志”,第882、883 頁。
該樂官清楚地講述了后周、隋、唐、宋的制律之尺的沿革情況,范鎮用尺,仍是李照所用太府尺,這在《玉海》里也有明確記載:
鎮用太府尺以為樂尺,下今樂一律有奇,以為得其理。[31]《玉海》卷8,第209a 頁。
遺憾的是,范鎮所造律“未用”,沒有得到皇帝的青睞,于是乎:
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鐘磐即今所用樂是也。[32]《金史》卷39“樂志”,第883 頁。
魏漢津在提出“指尺”說之前,是范鎮的屬下:“舊嘗執役于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33]《宋史》卷128“樂志”,第2997 頁。對于范鎮使用太府尺的事兒,他是比較清楚的。既然范鎮“無法以下之”,干脆給太府尺換個“指尺”的名字,也就是后來的“大晟樂尺”了。從太府尺、指尺到大晟尺,這三者間的關系,史料記載脈絡清晰。吳承洛先生梳理了宋代二十一等尺的情況后,很明確地說“大晟樂尺”出于哲宗元祐中,即范鎮尺。[34]《中國度量衡史》,第241 頁。
金代樂官毫不隱瞞地揭示了魏漢津提出“指尺”的目的:
然以王樸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于太重。其后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謂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眾人不敢輕議。[35]《金史》卷39“樂志”,第882、883 頁。
所謂“指尺”,并不是真的根據皇帝指頭長度制成,而是與李照、范鎮所用相同。李照、范鎮的尺,也并非從天而降,憑空而出,而是從前代繼承而來。李、范二人以太府尺制律,雖未能產生重要影響,至少實事求是;魏漢津為不與他人“同之”,為達到“眾人不敢輕議”的目的,將原有之事以“指尺”名之,其媚上欺下之心昭然若揭。
這位金代樂官對“指尺”的評價是:
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于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制,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36]《金史》卷39“樂志”,第882、883 頁。
這就是說,“清濁高下皆適中”的音高標準本就存在,它由“古制”而定(或早已存在于音樂實踐中),依據是傳下來的“北周、隋、唐所用之尺”,而不是“出于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不是出于突然冒出來的“指尺”。朱載堉進一步指出李照、范鎮、魏漢津之律“聲比古無射倍律之聲”,魏漢津只是“以無射倍律命曰黃鐘矣”,“指尺”說乃憑空“杜撰”。[37]《律呂精義》,第842、844、849 頁。
四、關于“指尺”制律的歷史評價
魏漢津以“指尺”在身前收獲了功名利祿,卻于后世留有罵名。
朱熹的批評甚為激烈:“崇宣之季,奸諛之會,黥涅之余,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38]蔡元定《律呂新書》“序”引述,載注?第212冊,第3d 頁。
馬端臨云:“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39]《文獻通考》卷130“樂考”,第3994 頁。一語道破魏漢津之流非知樂之士,樂工違其志,其渾然不覺。
脫脫評價魏漢津“尤為荒唐”[40]《宋史》卷126“樂志”,第2938 頁。,“上以取君之信,下以遏人之議,能行之于一日,豈能使一世而用之乎?”[41]《宋史》卷81“律歷志”,第1916 頁。
楊蔭瀏先生對“指尺”制律的本質揭示為:“大晟律……并不真如魏漢津所建議的用皇帝幾個指頭的長度連接起來所成的律……實際是劉昺……將當時的教坊律黃鐘作為夾鐘,從而推得的民間的黃鐘音高標準。”[42]《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390 頁。也就是說,人們在長期的音樂實踐中已經形成了合適的音高標準,這個標準是自然和文化雙重選擇的結果,這個結果不會因某種說法的提出而輕易改變。先有實踐后有理論,是音樂發展的一般規律,大晟律的出現,就是由于契合了當時的音樂實踐,才得以沿用百數年。
時隔楊先生做此結論的四十年后,李幼平教授在其博士論文中繼續討論了這個問題,主張要對大晟律進行“名實之辯”:“大晟新律,魏漢津只有其名,是劉昺主其事,而工人們施其實。”[43]李幼平《大晟鐘與宋代黃鐘標準音高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0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5 頁。對比宋初的多次樂議,他認為“一手遮天”的指律,“使某種在社會實踐中客觀存在的事實,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如果說和峴之議,使尺度考證與以黍累尺之法有名有實的話,那么,其后百余年的諸種相類似的方法,則多少呈現出有名而無實的狀態,而物極必反的大晟指律,就科學的定律方法而言,更應該是無名無實。”[44]同注[43],第70 頁。
對魏漢津“指尺”制律的評價,古今學者眾口一詞。筆者經過上述分析后認為:“指尺”事件事實清楚,“指尺”制律沒有科學依據,不可行。魏漢津以太府尺假托“指尺”,對于制律毫無積極意義,其掩蓋事實的做法有礙于人們理解、揭示歷史文化的真相。魏漢津為個人之利取悅封建君主的做法,是真正的封建糟粕。歷代學者對魏漢津的批評是客觀的,說其“荒唐”“荒謬”“無恥”并不為過。
以上是筆者通過爬梳史料、學習諸位學者的著述后得出的結論。另,“潘文”言大晟律的產生,“逐步結束了徽宗朝混亂的宮廷音樂局面,對北宋宮廷雅樂、宴樂,教坊,太學、辟雍等教育機構,甚至對金代宮廷音樂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上承北周、隋、唐,下啟宋、金,在北宋末年的宮廷音樂中產生著引領作用……使不同朝代、不同民族間的宮廷音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相繼承襲”,[45]同注②,第84 頁。給予大晟律至高評價。對此,筆者想表達一點兒不同意見。
大晟律的確定使宋代雅樂黃鐘音高得以長期穩定,且由于它的來源是早已存在于民間的燕樂,就相當于從官方角度肯定了燕樂,這對于宋、金、元時期的雅、燕樂的交融,具有重要意義;大晟律的物質載體大晟鐘,是我們今天了解宋代音樂成就的重要實物文獻,其學術價值不可估量;大晟律的制定,是古代樂律理論建設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我們樂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即便如此,大晟律也不能擔負上述如“潘文”所言的宏大任務。作為黃鐘音高,大晟律是單一的,固定的,不流動的,只有將其置于一系列樂音之中,以一定的邏輯關系組織起來,它才有音樂上的意義。作為一個標準音高,它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樂音運動的規律,說它對雅樂、燕樂有“深遠影響”“引領作用”,過于夸大其功用。
在大晟律確定之前,音樂實踐一直存在,各種表現形式按照它自身的規律慢慢發展著,音樂的古今傳承也一直在發生著,正如黃翔鵬先生所言:“傳統是一條河流。”無論是“北周、隋、唐”,還是“宋、金”,朝代更迭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當然也不依靠大晟律來“承上”“啟下”。
筆者才疏學淺,謹以上述文字表一己之言,敬請方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