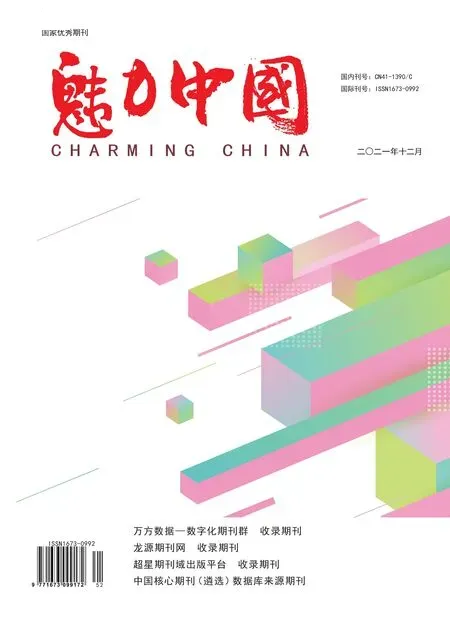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發(fā)展史回顧
盧江
(貴州省從江縣第二民族高級中學,貴州 從江 557400)
一部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的發(fā)展史,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事業(yè)的縮影。[1]從尋找“夏墟”的田野調(diào)查和發(fā)掘,到不斷加強國際合作,引進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典型之一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斷向前。本文將圍繞二里頭文化的研究史展開敘述和總結,并討論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研究方法上的諸多思考。
一、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史
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是在中國考古田野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發(fā)展的。其發(fā)展歷程可分為大致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起步階段(1958-1976 年)
對于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是伴隨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的進行而不斷深入的。此階段主要為二里頭遺址被發(fā)現(xiàn)至夏鼐先生提出“二里頭文化”命名前。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中豫西晉南地區(qū)的考古學調(diào)查,本身就有尋找商代更早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的形狀,所以一開始的研究就籠罩在探討所發(fā)現(xiàn)的二里頭文化遺存與夏商關系的氣氛中。
此階段有學者指出,在鄭州洛達廟和南關外發(fā)現(xiàn)的介乎于二里崗下層文化層和龍山文化層之間的“洛達廟期”或“南關外期”文化層最后可能是夏代的。[2]也有學者指出“洛達廟層”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線索或對象。[3]1959 年徐旭生先生調(diào)查“夏墟”的報告公布,推測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不小。[4]盡管有學者指出“二里頭西亳說”提出商榷[5],但主流認識任然是“西亳說”。
1960 年許順湛首次提出了“二里頭文化”,[6]但當時并未引起較大影響,仍然以“洛達廟類型”為主流提法。隨著二里頭遺址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的推進,人們逐漸認識到其比洛達廟遺址規(guī)模更大,文化內(nèi)涵更加豐富,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提出了“二里頭類型”命名。
此時期以夏文化的探索為主要議題,文獻與考古學調(diào)查和發(fā)掘材料結合為主要研究方法。對于發(fā)掘出土的玉器制作工藝的研究討論也是特色之一。
(二)第二階段:初步發(fā)展階段(1977-1978 年)
此階段以二里頭文化古史性質討論和夏鼐先生提出“二里頭文化”命名為標志。
1977 年國家文物局召開的“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會”是二里頭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會議。在會議上關于二里頭文化的古史性質展開討論。一種認為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屬于夏文化,三四期文化屬于早商文化;另一種觀點認為二里頭一至四期均為夏文化。[7]
1977 年夏鼐先生提出“二里頭文化”的命名。[8]有學者將其解釋為“是指在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地發(fā)現(xiàn)的介于龍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間的古文化”。由于二里頭文化遺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特征,隨后被學術界廣泛接受。
同時伴隨田野考古發(fā)掘的深入,關于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銅器等異物研究也是此階段的特色。年代學出現(xiàn),碳十四測年技術等自然科學技術開始運用于研究中。而此階段古史復原仍然是重點研究議題,關于二里頭與夏商關系的討論未能取得共識;遺物研究有較大發(fā)展;年代學研究相對較少,但已經(jīng)出現(xiàn),為今后研究開拓了領域;自然科學技術的加入是此期一個重要變化。
(三)第三階段:繼續(xù)發(fā)展階段(1985-1995 年)
此階段為夏商周研究的一個高峰期,諸多相關談論的論著出自此階段的談論成果。
由于前一階段關于二里頭遺址與夏商關系的討論并未達成共識,在1983 年偃師商城發(fā)現(xiàn)之后,對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年代和性質問題成為討論的重大議題。關于此議題的討論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出版的學術論著也較多。關于二里頭古史復原研究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此外,年代學、遺址建筑研究、遺存器物研究、宏觀態(tài)勢研究在此階段有了深入的發(fā)展,尤其以器物研究為最。考古學文化研究、墓葬研究受到了較多關注。考古學文化研究涉及到二里頭文化源流、分期、與其他文化交流互動關系等方面;墓葬研究涉及到二里頭文化墓葬的葬式、隨葬品等方面。
(四)第四階段:深入發(fā)展階段(1996 年至今)
此階段伴隨田野考古發(fā)掘的新方法、新技術、新理念的引進和轉變,田野發(fā)掘取得豐碩成果,相關研究也取得較多成果。此階段“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相關專項課題設置,使得此階段表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1996 年5 月開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中專門設置了“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課題。此課題包括了“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等專題。“二里頭全為或主體為夏都說”逐漸成為學界主流,但仍然有堅持“二里頭前夏后商說”[9]和“二里頭主體商都說”[10]。許宏強調(diào)“在作為目前主流觀點的假說之外,還存在著另外的假說,且其所提示的可能性似不容忽視”。[11]
1999 年秋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的田野工作思路轉變,工作重心放在看遺址聚落形態(tài)的廓清上。在此工作思路的指導下,二里頭遺址的勘探和發(fā)掘工作發(fā)生轉變,極大地推動了二里頭文化聚落形態(tài)的研究。
2002 年6 月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得二里頭遺址研究中結合諸多學科結合的方法,如碳十四測年、植物考古、環(huán)境考古、動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古DNA 研究、同位素分析等,對器物如陶器、玉器的制作工藝研究等。
此階段關于理論方法的反思也在不斷深入,涉及二里頭遺址的都邑歸屬與二里頭文化的族屬、傳世文獻及其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夏文化的內(nèi)涵、考古學文化變遷與王朝更替之間的關系、歷史發(fā)展階段劃分、考古學的特征等方面。
二、二里頭文化研究與中國古史研究的思考
二里頭文化的研究與中國古史研究有著密切關系,作為中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史記》記載的最早的朝代——夏代,證實它的存在對我國古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12]記載,紀年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 年,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在西漢晚期的劉歆及其以后一直到清代中葉,都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但囿于傳統(tǒng)文獻學與考據(jù)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這些問題均未能得到較好的研究和探索,這也一直成為困擾中國史學界的難題。
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擔負了構建中國“信史”的歷史責任。五四運動后,中國史學界“疑古學派”對中國古史進行研究,對黃帝以來到西周前的中國歷史提出了重新挑戰(zhàn)。中國傳統(tǒng)歷史研究的局限性也使得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時至今日,國際上仍然有學者對夏朝的可行度有所懷疑。史學大家顧頡剛先生提出了“上泉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13]研究方法,通過考古發(fā)掘來尋找夏文明實證,通過考古學研究來重新構建中國古史的“信史”地位。
正因為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了考查組,以1959 年徐旭生先生為首的調(diào)查隊伍,對豫中豫西晉南地區(qū)進行了調(diào)查。由于深厚的史學學習背景,徐旭生先生沿著古史記載的夏王朝活動地區(qū)展開系統(tǒng)調(diào)查,試圖能找到像“殷墟”一樣的“夏墟”。而二里頭遺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發(fā)現(xiàn)的。二里頭遺址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立刻在考古學界和史學界引起的重要反響。關于二里頭遺址性質的歸屬問題,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隨時二里頭遺址考古發(fā)掘材料的逐漸豐富,其文化內(nèi)涵和面貌也越來越明晰,相關爭論也逐漸趨同。在這其中,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相關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在問題談論逐漸趨同中起到了主導作用。這也正是張忠培先生所說的“考古,要讓材料前者鼻子走”。[14]正如鄒衡先生所指出的傳統(tǒng)文獻對于夏文化研究的癥結在于哪一條文獻更可信,然而文獻材料是無法自證的。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恰恰能夠反映出考古學方法在古史研究問題中的優(yōu)勢。
國內(nèi)學者關于二里頭文化的闡釋做過諸多嘗試,如孫慶偉先生結合歷史文獻對夏文化的年代學與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遺存和二里頭文化的對應關系做出了闡釋。[15]而陳淳先生對從孫先生的方法提出了諸多質疑。[16]而許宏關于相關考古學文化研究闡釋的方法思考上,也堅持從考古學本體出發(fā)的較為客觀的態(tài)度。[17]
目前由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研究的帶給我們關于考古學調(diào)查、發(fā)掘、研究、保護和傳承方面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對于研究理論的思考也是全方位的。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作為新中國考古事業(yè)長足發(fā)展的縮影,始終為我們學習中國考古學史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