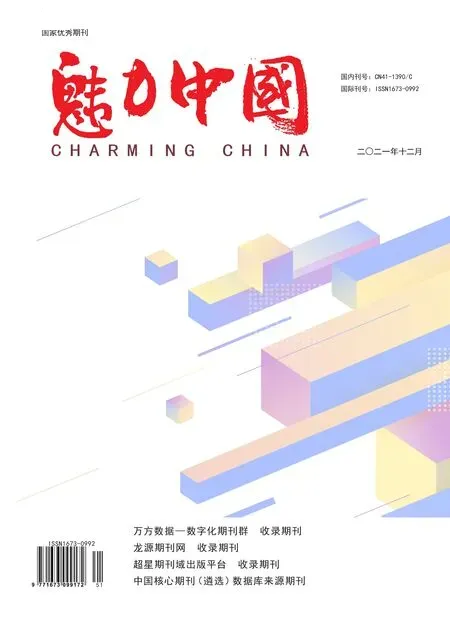當代“自傳性”油畫風格特征
孫思萌
(河北師范大學,河北 石家莊 050000)
一、油畫:當代性與風格形式
中國油畫自九十年代開始已經不僅限于對歷史的敘述,藝術家已逐漸向主題性繪畫及其精神上的壓力告別,進行具有“個性”油畫語言的尋求。全然是在記錄自我感受、經歷,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第一人稱“我”為主的油畫語言。實現了主體對自我真實存在的精神態度的判斷和“自我”認知。
外部環境的壓力迫使藝術家轉向屬于個體的私人空間。當代油畫作品中的自足性促成的這種演變正符合藝術的自律性原則。筆者認為當代油畫存在自律性是藝術家創作“自傳性”油畫的驅動力,黑格爾關于藝術史的遺產與當代個體油畫不謀而合,在繪畫自律性的形式規則演變含有精神的動力。作為一項實踐型藝術學科,創作材料的摸索與應用、表現畫面藝術手法的多元化、其中不難含有畫家的個人經歷以及情感經驗的投入,時代心理是上述形式模式的背后歷史產生的類別。在藝術史上沃爾夫林將時代心理與形式模式的連接看作為風格演變。而同樣屬于這一類觀點的認同者貢布里希更加傾向于用藝術家對形式的認識論,來說明油畫創作形式(形式模式)和藝術家本體(人文歷史)的呈現關系,當代油畫存在“自傳性”不是突如其來,史學家在討論觀念史變化中正式印證了“當代美術”以及眾多油畫藝術家的創作精神。當代油畫語言的轉向并非偶然,身處其中的藝術家將社會進步與個人經歷的觀念深入繪畫創作中,由此“自傳性”油畫風格的突出是必然的,更是主觀的選擇。藝術家將及其隱匿性的個人意識以油畫形式在觀者眼中展開,是“背后”的人與“現存”的人緊密結合的過程。經過分析當代油畫與油畫家的創作兩者之間的關聯,油畫家在創作中產生的現象所形成的風格,使得之后的油畫學習者對當代油畫歸類具有明確的認知。
二、畫—人:油畫本體與主體意識
“我在作品中力圖做的是,以物理的詞匯揭示我自己。——或者說,以自己的感受去解釋事物,”當代油畫創作是一種社會的代替物,融于社會現實之中,卻更是獨立現實之中的,它具有“我性”,是一種將“本體性”的經歷賦予一種“自主意識”之間的關系,兩者合二為一達到“我性”。
閆平是當代油畫藝術家也是女性藝術家的代表之一,繪畫主題就是扎根于自己的生活而來,更像是記錄生活與工作的影像,一件小事、一種情緒都是她拿起畫筆的原因,就是大眾能想象到最平凡不過的一些事實了,用獨特的色彩符號抒發她的情緒。她曾在記者的采訪時說,現代主義繪畫初期的具有自傳性畫家,例如馬蒂斯、畢加索等對她的影響深刻,在他們的油畫作品中呈現的都是他們熟知的事物,無論以怎樣的形式出現都是感染人的。她日常生活非常簡潔,常常獨自在畫室中,望著油畫布敘述出她所想所感,在作品中觀眾可以純粹直接地感受她在創作中生命力的沖擊性。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復興,著重強調的是“人”的覺醒,到近現代的藝術創作上逐步由“人”轉到了“我”。出現了大量的以“我”為主題的藝術作品,來凸顯“我”自身的價值。藝術家的自傳性風格的創作主題是結合那時的社會語境下發出的具有強烈自我感受的作品。是將“自我”主題直接呈現在畫布上,與上述的閆平的藝術作品有自傳性相比起來,劉曉東的繪畫并非是直抒胸臆,但是他們是另一種含有自傳因素的油畫作品。
劉曉東作為當代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代表,是“新生代”的主力人物,尹吉男曾說:“新生代藝術家或近距離藝術傾向往往不喜歡明確表態,把各自的人生態度藏在生活表象的背后,從作品中緩緩滲透出。新生代多不喜歡發表正式宣言是容易理解的。往往對大觀念的藝術理論缺乏興趣,而是以創作實踐去代替宏大的理論體系的自我構筑”劉曉東采用敘述方式,映襯出藝術家內心深處的個人意識,也是他自身的藝術體驗與生活態度的另類呈現方式。自傳性”繪畫風格是具有當代性的,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本質精神的關注,是藝術創作對藝術家在當下語境以及現實生活的個性展現與深刻表達,逐漸地轉變為了一種新的繪畫理念。就像是一位文學工作者用語言敘述完成自傳的編寫,劉小東把畫筆、畫布作為媒介輸出的油畫“語言”是油畫“自傳”的表現。
三、時代特征造成“自傳性”反觀
觀念與歷史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油畫這一藝術始終與自傳性油畫將人(藝術家)與人(觀眾),人與油畫創作間的關系以直觀的手法呈現在當下語境中。藝術家完善自身油畫創作審美屬性,賦予作品時代意義。提到時代,率先回歸到人文內涵的油畫風格,當之無愧為現實主義油畫。它從創作主體到風格形式有了極大的轉變,生發出大規模具有時代特征的油畫藝術作品。當藝術家身處在當代的中國,社會責任感油然而生,關注時代,主體地位凸現出來,在真實、自主、審美的當代文化語境下,藝術家被動回歸本我,正是由于時代的強烈感召,藝術家從自我審視去消解油畫對理想的呼吁。在多元化的藝術格局下,時代審美價值與社會文化心理促成了一種新興的、既非傳統又非激進的現實主義油畫創作手法。這種創作樣式它從內容到表現上都呈現出了一種對現實或自我的玩世不恭的意味。從側面交代了新一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態,與外部世界疏遠、獨自活在自己編織的精神世界里。
“自傳性”是指以自我為引領者,通過關于“我”的一系列事物為創作出發點,時代特征引起當代油畫表現出主體意識形態,一般將其歸為藝術家審美經驗的產物,具有時效性的概念。觀眾作為藝術家對面的人,藝術家為了博取受眾者的審美意識認可,畫面背后主體經歷的痕跡凸顯,觀者與藝術家二者間在主體精神上產生共鳴的必要性。如此一來油畫審美特征中優化了時代審美特征。巫鴻通過“當代美術”與“中國美術”進行了詳述,在文章中說明了中國當代美術與世界美術相互聯系但又存在差異,不做單一的解釋,宏觀的講述中國當代美術已經是具有成熟的藝術理論支撐,其中進行油畫創作的藝術家在當代這個空間對于國內外來說都是非常特殊,在油畫創作風格形成的歷史角度來看,在西方18 世紀中葉當代性已初露端倪,到了20 世紀的當代藝術的活動都是之前的藝術自律性確定產出的結果。當代藝術如何當代,這一種經驗是屬于藝術家的價值判斷,當代與當代審美關心的是有異于之前的一種全新的經驗。在前期審美經驗的生成更多的是來自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當代空間的審美經驗是從社會中生發,是具有痛感的、疏離感的經驗,兩個視角分析當代性具有的特征,不只是時間性具有的意義,在空間產生的價值已然不容忽視。西方印象主義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關鍵并不是他們自然地描繪外部生活,是他們懂得抓住在那個審美時代具有的特征。國內當代“自傳性”意識是從藝術自律觀中來的,之前的時空中詩意與生氣充斥了生活,恰恰是時代深刻感化藝術家,顛覆了油畫超越生活的精神形態的預設。最早開始顛覆這種片面認知的是杜尚,他就是要摒棄精英藝術觀,藝術也更加不是高于日常生活,他否認藝術是高高在上的,20 世紀藝術不再注重畫什么而是怎么畫的問題,他甚至直接將生活用品當作是藝術品展出。自從杜尚作為極有影響力的先鋒藝術家出現,許多藝術家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理想消除藝術與生活的邊界,但也沒有藝術消匿與生活。當代性既有時代特征又不囿于時間長度,更多地為價值性理念。巫鴻《論中國當代藝術家》中解釋到的當代如何當代的問題正是對前面現代性的延續,更多的是從中國當下語境進行分析,也是與現代性交織相融,但是當代藝術家在創作時加深了杜尚對藝術的見解。當然不是為了讓藝術消失在生活之中,只是消除藝術與大眾的隔閡,油畫創作中具有“自傳性”藝術家做到了這一點。由此形成了一條脈絡,其實也對“自傳性”油畫風格形成作了背景與形式的解釋,架上繪畫中的油畫創作急速成為主流,再看油畫家的背景經歷,走向現實主義是必然的。
“自然的人化”與審美當代化觀點相似。再從美學的視角看劉小東的油畫藝術創作也更加是表達了藝術家本我的含有的觀念。關注自我,是一種直覺性的發生,由此在其中感受到的美是不受約束自然而然流露,提高了自己的精神。他知道如何生活,更加能品味生活,從繪畫創作語言的運用到精神情感的表達緊緊貼近生活,都是能觸及到他本身的人與事情,觀眾直接感受到藝術美感。在國內研究的文獻中將劉小東深入研究的文章眾多,大部分只是作為案例,在史春娟的論文中深度探討到的他出生生活成長的外部世界是對他影響及其深刻的,情感的“日常化”,人物的“普通化”,創作的“寫實化”,他在進行藝術創作時采用的寫實手法被評論家成為新現實主義,這個“新”也就是與傳統寫實大相庭徑,受到了照相機的影響,采用不拘一格的構圖格式,隨意變換的構圖也是拉近觀者的一種方法,定格在某一瞬間的生活,強調了人物的真實感,觀眾有一種身處其中的感覺,充滿了趣味。這種輕松的日常生活的存在的悲喜都是生動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擁有特殊的張力,雖然出自藝術家之手,但是觀眾在這樣的視角下具有強烈的帶入感,是人們的生存狀態的揭露。“新生代藝術家或近距離藝術傾向往往不喜歡明確表態,把各自的人生態度藏在生活表象的背后,從作品中緩緩滲透出來”,尹吉男作為批評家率先提出“新生代”,這個概念讀者可以窺探到他講述的藝術家們都進行或多或少地充滿“自傳性”風格的創作。他在編寫這些文章時將“新生代”概念賦予到這一時期的藝術家身上。這些畫家所處的時代相同使得他們放棄虛無縹緲的現代都市生活轉而關注到鄉村文化。其所講述的這一批藝術家創作的出發點與成果是清晰的表達了當代藝術中的“自傳性”中要求的一部分。
四、時代性:走向新風格
在繪畫與精神之間油畫與藝術家之間有什么關系?在不可見的當代油畫精神以直接的方式呈現本體時,引起的是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共同的思考,藝術家通過這樣的方式解蔽觀者雙眼,藝術家實際是占有主導性的地位。在具有“自傳性”觀念的油畫中“自我意識”轉換到“油畫語言”,精神實際上是對眼睛的遮蔽,藝術家作為連接了觀念與客體的一種介質,理論與繪畫不在當作兩種模式去理解,當代油畫作為新時期藝術家精神呈現,這里是不存在一個表面的優化油畫語言。模仿西方是剛進入20 世紀的一大浪潮,浪潮退去藝術家需要面對本民族文化展開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