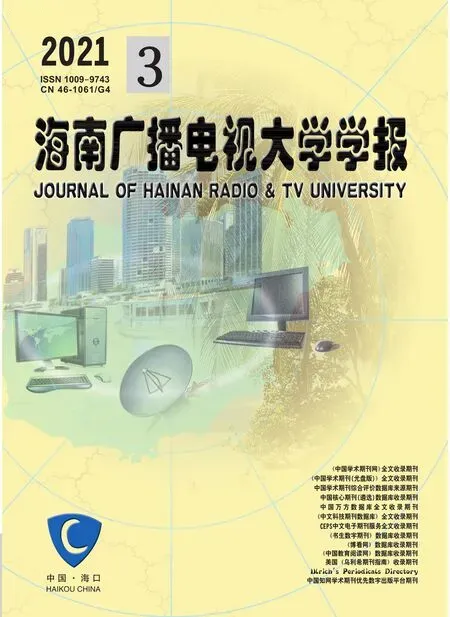“精準扶貧”背景下中國鄉土文學中的“官民”形象書寫
盧春苗
(南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初等教育學院,江蘇 南通 226001)
“當前農村,似乎仍然靜悄悄地連蟋蟀都不語,卻在發生著驚心動魄的變革。農村是孕育中國悠久而燦爛文化的搖籃,也是培育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的地方。”(1)王宏甲:《塘約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精準扶貧文學以“農村”為敘事時空背景,以農民與扶貧干部為人物核心,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精準扶貧文學”大敘事。在中國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有大量農民形象與干部形象,他們在精準扶貧景象下以不同的面貌體現在不同的扶貧文本中,官與民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迥異的形態。對他們形象與關系的書寫體現了作家們對人生的百態與社會現象的深刻體察,是對新時代“官民關系”的新觀照。農民形象的書寫體現了中國土地上農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內生力,也體現了他們精神與人性上的復雜性,而精準扶貧干部形象的書寫則折射了官場政治生態、紅軍精神的傳承、國家扶貧的情懷。本文以《高腔》《塘約道路》《山盟》《大國扶貧》《通江水暖》為研究文本,透視不同類型作品中體現出來的官民復雜動態關系。
一、扶貧文學視域下中國農民形象分類
隨著政治學與社會學學者對貧困農民主體性的審視與對“精神貧困”的關注與理論建構,精準扶貧對象以“精神性”為標準分化為“精神貧困型”與“內生力型”兩類。審視精準扶貧對象的精神主體性成為研究精準扶貧文學的基礎理論性問題。本文以此依據對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農民形象進行分類:內生力型貧困農民指的是物質上貧困匱乏但是靜默沉穩又充滿活力的作為精準扶貧對象的農民,他們具有強烈脫貧的主體性意識,成為精準扶貧內源動力;精神貧困型農民指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習慣與風尚等不能滿足現實需要,思想觀念保守、脫貧意志匱乏、生活目標游離的貧苦農民,他們脫貧主體性缺失,成為脫貧攻堅中的阻力。在《高腔》《塘約道路》與《山盟》三部“精準扶貧史詩級”作品與《通江水暖》《大國扶貧》等扶貧主題文學群象中,作家們恰恰塑造了內生力型、精神貧困型兩種不同中國農民形象群,體現了中國精準扶貧背景下的農民的社會生活與人的精神境象。
(一)內生力型農民形象
生命自身釋放內生力才是最高價值的成長。在中國的精準扶貧文學作品視野中出現了一批充滿內生力的農民,他們充滿干勁,對自己的家園有共同的系念與牽掛。他們或是有民間文化情懷的貧苦農民,或是自尊自立的樸素百姓,或是心系故土、回歸農村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撐起了中國農村經濟文化的脊梁,用行動詮釋著大寫的中國農民精神。
1.“本土者”——內源力型農民
“戲臺和唱詞串聯起一個家庭甚至一個村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賦予小說起承轉合的戲劇化節奏感,而高腔本身提精神壯聲勢,既有悲壯激烈的高亢,又有千回百轉的蘊藉。”(2)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高腔》中的官民關系借“高腔”這一四川戲劇元素呈現出起伏的詩意,在“唱”與“幫”的戲劇節奏中,使得具有中國文化情懷的精準扶貧干部與具有民間文化內生力的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詩意的互動關系。《高腔》中出現了以米蘭香、柴云寬為代表的有文化內生力的農民,他們順應了生態、弘揚民間文化等社會熱點,演奏了起承轉合的精準扶貧“高腔”。
米蘭香是《高腔》中出現的農村青年女性,如一首律詩,平平仄仄鏗鏗鏘鏘中呈現出中國農村女性的柔韌與剛強。她出生于一個原生態的農村藝術家庭,從小浸潤在民間藝術氣息濃郁的環境中,她熱情善良、堅韌,如曲般優雅,對中國民間藝術愛的深沉,對“高腔”這一四川戲劇文化有著先天的青睞,雖然身處物質的窘境中仍然對高腔這一民間藝術有著執著,而扶貧干部滕娜正是以藝術為突破口,打開兩人精神困頓的桎梏,最終將生活與藝術融合在一起,抱元守一,回歸初心,實現了藝術與生存的合一,人生的“黑暗”反而更磨練了米蘭香的意志,讓她有更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對黨忠誠的信仰,最終她將民間文化融入生活、融入經濟、融入政治中,為精準扶貧涂上詩意藝術的底色。
冬哥是有理想有情懷的老派農民的代表,他身上有一股樸實、肯干、上進的精氣神,他從小多才多藝,是出名的打工詩人、農民吉他手,用他嘶啞蒼涼的歌聲傳遞著對命運的不屈服。他窮得有骨氣,有老式農民的不服輸、內向、要面子的特點,當在扶貧干部石承的幫助下湊足了做手術的費用,能夠有希望站起來時,他那院子里頌揚共產黨的歌聲由蒼涼轉為喜悅,成為精準扶貧文學中最美的歌聲之一。
“夏蓮如同跌宕而來的山泉,哪怕摔成八瓣也叮當有聲,一雙杏眼,飽含質樸。”(3)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頁。《山盟》中的夏荷自立自強,如荷花般清幽淡雅,蓮般潔凈,如一首絕句,質樸真淳,藍天無云,是中國農村中堅韌自愛、自強忠貞、遵從孝道的年輕女性。《塘約道路》中也有一群“窮則思變”的具有內生資源的農民,他們謹守著中國農民最樸素的智慧,勤奮肯干,把脫貧致富作為全村人的最高追求。從踏實肯干的村長左文學,到愛讀《老子》的曹書記,從一群奉獻自己的老志愿者到勤勞樸實的先進農民,無一不展示著中國農民的內生力量。《大興之道》中“內外因素的疊加共振,村民們我要脫貧的口號叫得山響,內生動力被激活。”(4)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頁。更是中國農民內生力被激發的典范。
米蘭香、冬哥和夏荷他們都是中國最普通的奮斗在土地上的農民,他們自尊自愛,熱愛生活熱愛勞動,愿意付出,辛勤勞動,骨子里有一種不屈服的品質,他們是普通平凡的,但是中國“農民”兩個大字正是由一個個小小的平凡的普通的“米蘭香”“冬哥”和“夏荷”們組成。盡管他們身上也有一種過度的自尊導致的“要強”“不肯承認貧困”的心理,但他們憑借自己勤勞的雙手創造未來,自愛自尊,加入脫貧攻堅的時代主題中,成為精準扶貧的內源力。
在內生力型農民的書寫中,中國作家寄托了對中國千百年來傳統農業文化的敬畏與傳承、創新,對深耕于農業文明中靜默沉穩又多變創新的中國農民品質的頌揚,呈現了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精準扶貧”戰略下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變遷以及農村文化生態、社會習俗、人性心理的演變,寓意對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的美好愿景。
2.“返鄉者”——回歸的農民企業家
他們是腳踏實地為家鄉奉獻自己的農民或農民企業家,用拼搏、創新主動為家鄉人民謀福利,創建一個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通江水暖》中內生力十足的民營小企業家是“內生力型農民”的一種代表。
作為返鄉農民的代表,通江愛心社社長賈芝華回到自己的故鄉成立公司,帶領更多的通江人奉獻愛心:“我先是自己打工,然后帶出一支隊伍,再后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5)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頁。為家鄉的慈善事業做出貢獻;閆仁安是先富帶動后富的先進農民形象,他的初心是“一個人富裕,不是真正的富,只有帶動大家都富起來,過上好日子,那才是真的好。”(6)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頁。他普及自己的技術,帶動一方葡萄種植業的發展;返鄉投資的民營小企業家們扎根通江,為通江經濟發展注入活力,開辟生態經濟之路;《山盟》中的企業家梅琪關愛農村父老鄉村,幫助他們度過危難……這些返鄉者對故鄉對自然的熱愛敬畏之情可謂真摯,他們以一己之力支持國家扶貧事業,有精準的經濟學眼光和敢于創新拓取的精神,擁有強烈的家鄉情懷和帶領農村共同富裕的情懷與可貴的生態意識,成為中國精準扶貧事業中令人敬佩的一群人。他們彰顯了中國小型農民企業家的創業精神與民族尊嚴、崇高的情懷與價值追求,創造了與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一脈相承的“中國精神”。
(二)精神貧困型農民
杭承政、胡鞍鋼從行為科學的視角提出“精神貧困現象的實質是個體失靈”,從“個體失靈”“行為失靈”“志向失靈”等概念切入,分析了“精神貧困”的內涵。所謂“精神貧困”是指“貧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極和行為決策不理性,從而影響其脫貧的行為現象。”(7)杭承政,胡鞍鋼:《“精神貧困”現象的實質是個體失靈——來自行為科學的視角》,《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 年第8期,第97頁。精準扶貧文學作家以犀利敏銳的文學視角在扶貧作品中也刻畫出這樣的“精神貧困者”群像。比如《山盟》中好吃懶做的“閑散分子”凱子、貪小便宜哭窮喊窮的郝婆,又如《大國扶貧》中“等靠要”農民代表、《通江水暖》中安于貧困、悲觀惰性的方山村人等,他們從不同的層面揭示了中國農民中在行為或志向上固守貧苦、個體失靈的現象,也能體現出來新時代風貌下部分中國農民的精神狹隘與局限性。
《山盟》中凱子是懶散型精神貧困農民。凱子是新生代“精神貧困”農民的代表,他褪去了對農村土地的執著,在精神上歸依了城市,努力想要活出與農民的不同,想要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身份,他夢想過,掙扎過,卻唯獨沒有奮斗過,他沒有冬哥熱愛生活的勇氣,也沒有改變生活的行動,他是一個標準的個體失靈的精神貧困者。他秉持“叫花子理論”,好吃好閑,窮不哭窮,苦不言苦,在這貧困中纏繞著的是過度的自尊、虛榮、懶散與所謂的骨氣。
《山盟》中的郝婆是“哭窮”型精神貧困農民,她的兒子是大老板,但不贍養老人,郝婆藏起自己的私房錢,天天哭窮喊窮要精準扶貧的指標,《通江水暖》中的方山村人是“等靠要”型精神貧苦農民,他們安于貧困、不思進取,以向政府等、靠、要為主要的謀生手段,缺少人生目標的規劃,更沒有為之奮斗的意念與行動。
“精神貧困型”貧苦農民的形象書寫反映了部分中國農民固守思維,安于貧困、懶惰閑散的不良品質。這些形象的出現,合乎人情人性,是作家追求客觀寫實風格的體現。但是這些人擺脫精神貧困后釋放出的思變、創新的思維體現了他們最終能反思自我、力求上進、改變命運的品質。而激發他們的內生力,從文化、教育等方面對其進行“精準扶貧”則是精準扶貧文學農民形象書寫的深度與理性思考所在。
二、精準扶貧“官員”干部形象書寫分類
精準扶貧文學視域下作家勾畫了一個官員干部形象圖譜,他們或是政府派駐農村的年輕扶貧干部,或是老而彌堅、忠貞不渝的老黨員,或是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的省委領導,或是原住基層村鎮干部。本文主要從駐村干部、基層鄉鎮干部、省市領導三種在精準扶貧中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干部形象解讀精準扶貧文學官員眾生相。
(一)年輕駐村扶貧干部“第一書記”
“做人,做大寫的人,清清白白,勤勤懇懇,不求光環,不求繽紛,只愿做棵禾苗深深扎根。”這是電影《第一書記》的主題歌,真的是唱到了駐村扶貧干部的靈魂深處,勾起多少駐村第一書記的酸甜苦辣、悲喜之情,唱出了他們的精神與價值追求指向。駐村干部(第一書記)是精準扶貧中的一個承上啟下的角色,他們是脫貧攻堅的先鋒,俯仰之間,勾連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政治生態,他們是政策的執行者,亦是百姓的貼心人,是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特有的一類文學形象。《高腔》中的丁從杰、《山盟》中的石承、藍喆、《大國扶貧》中的吳杰、丁強、楊雪梅都是年輕扶貧駐村干部的典范。
以《高腔》中丁從杰為代表的是中國新生代敢為愿為有為的一群年輕干部。丁從杰是一個有文化情懷、人文關懷、生態視野的扶貧干部,他有著較高的政治覺悟、精準的經濟眼光、生態意識與對農民的殷殷熱愛情懷,年輕有為,殺伐果敢,平易近人,注意扶貧的藝術性,與農民形成一種和諧的互動關系。他自愿投入到精準扶貧工作中,積極主動與被扶貧者溝通交流,了解他們的精神世界與生存現狀,主動化解農村中幾大家族之間的矛盾,從生態的角度為農民謀出路。他沉潛到農村的底層,多觀察、善思考、勤總結,他代表了中國新生代敢為愿為有為的一群年輕干部,他們是迅速成長起來的第一代駐村扶貧干部。《大國扶貧》中的四川省“優秀第一書記”丁強、李林蔚、楊雪梅也都是敢為愿為有為的駐村干部典范,他們扎根基層,將精準扶貧的政策落實到細節中,用良心丈量扶貧工作,與農民風雨同舟,在政治情懷與能力方面迅速成長,是中國基層政治新生態的代表。
而石承與藍喆屬于成長蛻變型年輕扶貧干部,他們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熱情,懂得官場的藝術,但是最初對做精準扶貧駐村書記比較抵觸,他們不像丁從杰一樣從一開始就敢為愿為有為,他們對鄉土的熱愛與扶貧的思想覺悟是在扶貧的過程中慢慢形成的,他們的扶貧熱情是伴隨著中國大地上精準扶貧大事業慢慢而成長起來的。他們的內心對做駐村干部有一定的抵觸,把扶貧簡單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在遇到扶貧對象的刁難后,恨其不幸,怒其不爭,對扶貧工作產生了懷疑。但是,扎根于農村的經歷讓他們找到了黨員的初心,他們開始真正走進扶貧對象的世界,了解他們的困難與內心世界,真心實意幫助他們脫貧,并重拾鄉土情懷。他們內心對黨的忠貞與崇高精神的覺醒則象征了中國扶貧事業的偉大成功。
(二)基層鄉村干部形象
“脫貧攻堅,基層干部使命如山,他們除了沖鋒陷陣,真的別無選擇”(8)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頁。,基層的鄉村干部是精準扶貧的“潤滑劑”,上承駐村干部、市委領導干部,下接村民大眾,面對的政治生態比較復雜多元。對下,他們要處理鄉村人際關系與人文生態,宣傳精準扶貧的政策,與群眾進行深度的交流;對上層領導,要針對本村的實際情況進行規劃,讓上級領導深入了解農村的實際狀狀況,以便規劃大局。如《山盟》中的范鎮長、黃主任,《通江水暖》中的劉群才、劉清誼、陳幫洪、周紅梅、朱麗珍,《塘約道路》中的左文學、曹友明,《高腔》中的牛春棗都是出色的鄉村基層干部代表。
“當干部的,只有沉下身子,與群眾面對面,心交心,才能讓大家知曉政策”“用情,是一種誠意,更是一種責任。”(9)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頁。《通江水暖》中的劉群才、劉清誼、陳幫洪、周紅梅、朱麗珍扎根農村,為民生謀福,“通江新巾幗修通開了人心之間的通途,讓干部和群眾之間,不再有隔閡與誤會,心與心一起跳動,并肩作戰,脫貧致富。”(10)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頁。《塘約道路》中具有樸素的農民智慧的左文學、曹友明則體現了新一代鄉村基本干部的銳意進取的精神,他們吸收中國農民的傳統智慧與哲學智慧,用知識與新思維帶領村人致富,他們敢于創新,為農村規劃未來的藍圖,奔波于上層領導與村民之間,力求變革,創造了聞名全國的“塘約道路”。范鎮長、黃主任是《山盟》中的兩個鄉村基層干部形象。精準扶貧作品中鄉村基層干部與第一書記的關系呈現兩種情況。
以范鎮長、牛春棗、左文學為代表的鄉鎮干部將第一書記看作同路人,是責任共擔者。兩者的關系是水乳交融。基于為天地立命,為民生謀福利的情懷,他們在工作中合作和諧,在接觸中產生感情,政治經濟目標追求趨一,可謂“道同相為謀”,共同繪就中國扶貧的壯舉;而以黃主任、米萬山為代表的鄉村干部將第一書記作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競爭者、權利的競爭者看待,他們不愿意配合第一書記進行農村的改革與創新,固守著自己的既得利益,與駐村干部干部就扶貧指標、落實情況、實際操作、返貧現象、占用扶貧指標等問題產生矛盾沖突,體現了其政治意識的狹隘性,但是最終他們難以擋住精準扶貧的大勢,只能服從人民的整體利益,在被迫轉變中慢慢認識到自己的自私狹隘,與駐村干部的關系也從不和諧走向和諧。
(三)省市領導大官形象
相比基層的鄉村干部與第一書記的形象,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的大官形象則相對比較單薄,沒有戰斗在一線上的扶貧干部形象豐滿,作者對其人物描寫的方法也比較單一,限于精準扶貧作家的觀察視角和采訪的視角,省級以上的領導干部形象在整個精準扶貧文學作品群呈現的比重偏少。“運籌帷幄”、“大局意識”是捕捉他們形象的關鍵詞。《山盟》、《春江水暖》、《塘約道路》的筆墨都集中在駐村書記、基層干部與農民身上,省級以上的干部領導隱在敘事的幕后,《春暖烏蒙》《大國扶貧》中則運用了采訪、第一人稱敘事、夾敘夾議等敘述技巧將“大官形象”融入敘事層面。
如《大國扶貧》中的敘事視角比較多元,通過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敘述視角的切換以及采訪實錄的敘事文體,特別以對領導訪談的文學形式將省委書記形象直接呈現在敘事層面中。親切的第一人稱敘事讓我們零距離感受省委領導的扶貧情懷,對他們的政治調控能力與領導藝術有所了解,感受到他們運籌帷幄、掌控全景的氣場與風度,也感慨于他們謀劃布局整個省市扶貧工作的艱辛與勞苦,而他們的黨性也在扶貧工作中得以淬煉升華。
還有一類人,他們不是在編的干部,但是活躍在中國的精準扶貧戰場上,用他們對黨的忠誠回報政府與人民。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這批老黨員形象是紅色文化、老紅軍精神在新時代的崛起的體現。老黨員們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見證著新舊社會面貌的變化,對時代與世道有自己的思考,對黨的事業有著絕對的忠誠和奉獻,他們就像山上那些紅軍石刻,歷經風吹日曬仍不忘初心,堅守山盟海誓。《山盟》中的韓老山夫婦、石現夫婦,《塘約道路》中的老黨員志愿者,《通江水暖》中的老支書,都是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的老黨員形象。
《山盟》中的韓老山有著山一般厚重沉穩、堅貞不移的品質,他知足常樂、安于清貧、堅守信念,以“火塘山”為對黨對祖國忠誠的精神坐標,他把這個戰場遺址作為共產黨堅固的陣地,和妻子堅守55年,以絕對信仰的能量與共產黨的精神共振,為火塘山鍍上忠誠、信仰的精神品質。“塘里的火是不能熄滅的,許多人家幾輩子只生一次火,由祖宗那里燃到子孫,當地習俗,熄了火塘,如同斷了香火”。(11)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頁。李明春借“千年火塘”于深邃中孕育新的輪回來象征革命精神的生生不息。《山盟》中的“老黨員”石現夫婦則沉潛到在鄉村基層工作中去淬煉自己的黨性。作為紅二代,在前一任村支書(石現的父親石新)去世后,石現放棄了在城市政治發展的前途,回到山村當村支書,幾十年如一日堅守在基層崗位上,他是中國扎根基層的老黨員干部的縮影。
人間終有一些品質可以穿越時空,直接抵達靈魂深處,我想對黨的忠誠就是其中一種。無論第一書記還是鄉村基層干部,無論是省市領導亦或老黨員,區分他們的只能是官職的高低,在靈魂與黨性上,他們一樣純粹一樣高貴。
三、傳承與創新——“精準”背景下官民書寫的意義
“精準扶貧”文學拓展了新時期以來鄉土小說的內涵與外延。從其敘事主題與模式來看,精準扶貧文學有對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的繼承與創新,鄉村題材、農民與干部的人物形象、社會結構與人性、思想觀念轉變是精準扶貧文學從體裁、題材、人物形象、主題、敘事結構等方面對傳統鄉土文學的繼承。但由于精準扶貧文學“精準”的專有視角,這批文學作品出現了一些新的主題與新的語言風格,特別作品中駐村干部與鄉村干部關系的書寫是精準扶貧政策下特有的現象。而且精準扶貧文學作品注重強調了“黨性”“紅色血脈”代際傳承的現象,這些都是傳統鄉土小說中不具備的特質。所以,對“精準扶貧”背景下鄉土文學中官民形象豐富了傳統鄉土作品的視域和維度,讓“鄉土”概念更加契合習近平主席實施精準扶貧政策以來的農村社會。
(一)紅軍精神的傳承與變遷——鄉土新境象
精準扶貧文學群像中官員形象書寫意義之一,在于揭示了紅軍精神的傳承與變遷,體現了時代變遷中中國人尋求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遠大愿景。這是精準扶貧文學對傳統鄉土主題的拓展與升華。
李明春在《山盟》中通過石家四代祖孫的名字呈現了中國文化中“紅軍精神”的傳承現象。祖父石新寓意“以斧頭,砸碎舊世界,鐮刀開辟新乾坤”,他們這一代人見證了新舊時代的變革,充滿革新世界、另辟乾坤的激情,是與共產黨新時代共生共存的一代人;父親石現意為“遠大理想,任重道遠”,他們肩負著建設國家富強的遠大愿景,是祖國農村建設的中流砥柱;兒子石承寓意傳承中國紅軍精神,不停奮斗,繼往開來,為祖國繁榮共富開拓新格局;孫子石盟寓意謹守黨盟,“世風日下,生怕后人忘本,取名石盟,希望他像山上的紅軍石刻,山盟海誓,風吹雨打不變心”(12)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頁。。扶貧的主題與共產黨的信仰奮斗聯系,作者在精準扶貧視野中彰顯中國共產黨為民的情懷與對紅軍精神的傳承與堅守,體現了新時代變遷中中國農民向往美好的愿景與共產黨尋求的政治理想高度一致。精準扶貧文學作家借山盟石刻、火塘、王坪25048紅軍烈士群、無名烈士群、空山會戰紀念地、塘約“鄉村殿堂”等地理坐標將紅軍革命精神賦形化,將無形的紅軍精神物化到有形的地理載體中,讓今天的中國人更形象地去體察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核心,這也是中國作家政治情懷的一種體現。
我們可以在精準扶貧文學作品中隨時尋覓并凝視到紅軍精神的傳承:《通江水暖》里鸚哥嘴村專門設立紅軍紀念室,村子里的老輩子有不少是紅軍出身,如閆仕安的爺爺是紅軍,父親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他們家庭一直秉持著無私奉獻的紅軍精神;唱歌鄉的“通州女紅軍”的傳人們用不同的方式奉獻大愛,演繹人生傳奇,如“紅三代”周紅梅,靈魂里流動著紅軍勇于拼搏、積極進取的血液;朱麗珍以女紅軍的干勁拼勁,以女性的強大韌性,迎難而上,投身精準扶貧事業中。他們在新時代新景象下闡釋著新的紅軍精神。
但是,有些作家還用犀利的筆觸揭示了承諾的分量在一代又一代的傳遞中逐漸減弱的事實。例如《山盟》中“紅三代”石承把扶貧當作一份竭力想擺脫的工作,他身上缺少了一份黨員為民的無私精神,這也是當代復雜的社會環境下一部分黨員的真實寫照,盡管讀者品味到了不完美,但這正體現了精準扶貧作家們的清醒的理性意識和民間立場。
(二)折射官場的政治生態
精準扶貧文學中對官民形象書寫的意義還在于它折射了精準扶貧視域下中國官場的政治生態,反映了鄉村基層的政治文化生態,映射精準扶貧文學官與民之間尋求共同政治、經濟追求中建立起來的和諧自然的關系。
精準扶貧文學反映的政治生態的底色和主流是中國政治生態中的良性因素,“上下同欲者勝,風雨同舟者興。”無論是遍布農村的鄉村基層干部,還是市級省級干部,都投身精準扶貧的時代課題中,呈現中國精準扶貧的現狀、主題與工作細節,中國的男性與女性干部成為精準扶貧中“陽剛”與“陰柔”并濟的能量,以共同的精神追求與信仰力,以個人為基本點,用他們的痛與樂、苦與甜、夢想與拼搏、靈魂與肉體成就精準扶貧事業,將小我完全融入到大我中,彰顯愛國愛民心,體現黨性的純粹與無間的信仰力。
但是,在精準扶貧的視域中,也存在著政治生態的非良性因子,而作家們也在盡量客觀地呈現這些問題。如在《山盟》中李明春沒有刻意回避中國官場政治生態中的一些問題,力圖“讓讀者從中獲取切中時弊的思想啟示”,也力求尋找中國政治生態中的良性元素,尋求政治與民生的最佳平衡點。在精準扶貧視域中,整個官場不同層次的官員對于精準扶貧事業的態度比較復雜。比如《山盟》中的有些城市官員不想扎根基層,找理由推脫不肯回到農村,有些官員圓滑世故,李明春沒有刻意美化遮掩,而是以盡量客觀寫實的筆法刻畫出官場的一種不完美的鏡像。
“有人提醒石承,這事兒還得把賈主席挽緊,他肚子里的花花腸子多,別說出個主意,或許生個兒子都行”(13)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頁。
“自掏腰包請客,股長們去,賈主席說搞個工會活動,訪苦問貧,幾個股長馬上放下杯子,嚷嚷工作忙,話完,大家把杯子一碰干,石承可還不敢嫌少,堆著笑臉陪大家唱夠。”(14)李明春:《山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頁。
石承為了湊足扶貧款項,不得不向老領導“取經”,在籌款的宴會上,李明春用幽默詼諧的筆墨刻畫了一副惟妙惟肖的官場“變形記”,官員的世故圓滑,基層干部的為難心酸一目了然。
在刻畫范鎮長這個人物上,李明春較為原生態地描摹了一個普通平凡又有著自私圓滑的鄉鎮干部形象。范鎮長無疑是有政治才干,也愿意為民做事的一個鄉鎮干部,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兢兢業業,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的狹隘不足也體現出來。他的兒子在學校欺負貧困戶冬哥的孩子山仔,范鎮長及其妻子縱容兒子的霸道,公權私用促使山仔被迫轉學,在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后,又千恩萬求地帶錢去冬哥家里希望擺平,最后也只是怕兒子再惹麻煩,把他送到城里的學校去了。在這一事上,范鎮長的以權謀私、在親子關系中縱容不作為、世故圓滑的方面被放在文學的視鏡下特寫,體現了政治生態中的少部分不良因子,也體現了文學家直面現實的勇氣與魄力。
精準扶貧文學中還反映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很多方面,如駐村扶貧干部(第一書記)與老派村干部就扶貧指標、落實情況、實際操作、返貧現象、占用扶貧指標等問題產生的矛盾沖突,折射出官場的復雜曲折與權力的更迭變化;如基層鄉村干部為民謀發展中與鎮、市級干部之間的磨合沖突,以及基層工作的心酸挫折等等。
(三)農民文化與大國文化書寫的彰顯
精準扶貧文學譜寫建構中,文學既是個人的聲音,也是人民的聲音、國家的聲音,個人敘事與國家敘事交織,兩者的融合在于價值、理想上個人與國家的同一性,個人以人類的理想為圓點,基于對家國命運的關注展開對政治、文化的書寫,而這種個人追求恰恰與國家主流價值觀、文化理想、政治構想相一致。此種一致性構成了精準扶貧文學的最高價值與精神追求。
1.農民文化與品質的彰顯
農民形象的書寫有著深刻的意義,它頌揚了中國農民身上具有的民間文化情懷,呈現了中國文化的永恒魅力以及政府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習近平主席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講過:“中國人民的特質、稟賦不僅鑄就了綿延幾千年發展至今的中華文明,而且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15)習近平眼中的中華文化精髓,http:∥news.cnr.cn/native/gd/20160930/t20160930_523172816.shtml,2016-9-30.中國人浸潤于儒釋道文化中,傳承了中國文化靜默奉獻、堅韌執著又靈動如水,思辨進取的精神品質,形成了有著東方智慧文化品質的人群。中國人民弘揚和傳承中國民間文化,讓文化說話,是新時代中國人民的使命,激發中國農民身上的民間文化特質和藝術情懷是中國文化發展在新時代的一道使命。
《通江水暖》中質樸進取的通江好兒女身上沉淀著通江多元文化底色。通江深厚的紅軍文化、佛教文化、生態文化、民間文化滲入通江人的身體與靈魂里,形成了誠樸堅韌、開拓進取的通江人民。如《通江水暖》中巴山人的奉獻、堅定無畏、創新、誠信樸實、豪放、熱愛家鄉的精神品質,他們以智慧與魄力踐行生態理念,以紅軍革命的精神開創新生活,以樸實純善滌蕩著城市人的心靈,讓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實現了深度的交流;“懂得感恩的通江人,樸實無華的山里人,他們接受了人間多少愛,就用心回饋社會多少愛,在脫貧攻堅的道路上,通江人富了起來,但這富裕,不只是體現在物質方面,還有精神上的富裕和崇高。他們富起來了,擁有了最為寶貴的情操,將仁愛灑向多情的大地。”(16)何建明:《時代大決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頁。知足常樂、感恩回饋也是通江人精神品質的一部分。
《高腔》中的幾代農民身上的四川民間戲劇文化元素,《塘約道路》中鄉村書記體現的老子的樸素辯證思想和農民特有的智慧,《大國扶貧》中民營企業家顯現的佛教、仁愛思想,《時代大決戰》里貴州山民的有苦不言,以苦作樂,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山巖般的血脈精神,《大國扶貧》中紅軍的故鄉巴中人寧愿苦干、不愿苦熬,敢為天下先的開拓創新的“巴中精神”,都是人民所傳承的中國傳統與民間文化的體現。人民智慧、大國形象,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最深的底氣。
2.大國文化的具象呈現
精準扶貧文學官民主題書寫在文本敘述中對國家意識形態給與明確回應,通過“生態” “生命共同體”“社會和諧”等符號,弘揚大國生態扶貧的意識成為所有作品背后的共同旨趣。同時,作品在塑造駐村干部與農民形象時,為了呈現小說敘事的詩意性或文學化,有意或無意地攫取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精華,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傳統文化哲學品質映射到住村干部或農民身上,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畏之情。精準扶貧過程體現了中國政府對生態文化、生態美學建構在頂層設計與實踐落實層面的高度重視,而不同省份的農民形象的書寫又體現了中國地方文化的多元性與豐富性。中國文化的縱深性、多元性與地域性在官民形象書寫中以具象化形式呈現出來。
精準扶貧敘事方興未艾,精準扶貧文學視域下的官民關系還在呈動態發展中,需要更多的作家去沉潛到民間,用審美的視野與理性的思考與農民、扶貧干部、基層干部一起見證時代偉大課題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