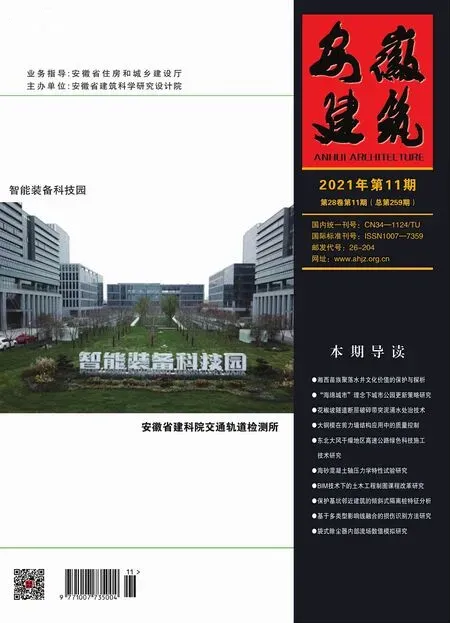湘西苗族聚落水井文化價值的保護與探析——以懷化市麻陽縣夸里村為例
李輝,羅明金 (重慶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重慶 401331)
1 引言
苗族的聚落的選址和布局都和水系、水源有關,水井作為湘西苗寨景觀之一,在村民心目中有著神圣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生活生產都離不開水井的滋潤,并且對村寨的位置及周邊的環境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研究水井,就是探究物背后的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互動的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當地主要的水井文化和鄉村禮制文化,即苗族歷史文化。但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環境,同樣也改變了傳統的鄉村生存方式和生活環境,居民對水井的依賴性也逐漸降低,并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與遺棄。作為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結合體的載體之一,維護和保護水井的功能性、文化性和象征性,是對保護苗族文化最好的傳承與保護。
2 湘西苗寨中水井的空間布局及文化解讀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記載:“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于人者”,糧食和水源一直都是作為人類日常生活生產之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在原始時代,受到當時生產力的限制,苗族先民都是擇水而居、沿水而行,臨近河流不僅土地肥沃、便于灌溉,而且能夠網魚捕獵,滿足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然而,湘西地區氣候多變、旱澇分明,很容易導致河、湖水的不穩定。時而干涸,時而洪澇,時而渾濁,時而內澇,對沿岸居民的基本生活構成了威脅。于是部分苗族先民們逐漸地遷移到半山坡上定居,由于一個住在山上,—個住在江河湖邊,所以分別冠以“高坡苗”和“河邊苗”的名稱。苗族先民從原始的沿河而居轉變沿井而居,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吃糧靠天,喝水靠井,不僅是苗族居民繁衍生息的重要水源之一,更是成為孕育生命、灌溉五谷及滋養大地的井。
2.1 夸里村水井的基本空間布局及造型結構
夸里村是以單姓苗族組成少數民族傳統村落,屬于高坡苗類,既有代表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全村寨共有300多戶,村莊四面環山,房屋呈階梯狀依山而建,村前有良田數頃,水井五口,能滿足全寨村民的日常基本生活用水。村寨的修建是基于水井的建成,換句話說,就是先有井、后有村,五口水井井然有序的開鑿在通往村寨的兩旁,規劃建設完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周邊自然環境相協調。其中以營造規模最大的井最有代表性,當地村民稱為“澎水龍”,泉眼冒出的水猶如巨龍在水下翻滾,很形象地描述了水流量之大,井口流出的水冬暖夏涼,一年四季源源不斷,如圖1所示。

圖1 呈空間階梯劃分的“澎水龍”井
“澎水龍”井水的選址、開鑿、使用及維護上處處體現著當地村民智慧和文化,是技術美學和自然美學的互融;是生態觀與宗教觀的互滲。在選址擇地上,在村寨前三座大山交接的砂石之處修建水井,即使逢極端干旱天氣,也能保證井水不枯竭及清潔衛生。“澎水龍”水井是按地勢高低呈梯級分布的三級井,各級井各擔其責、分工明確。一級井是飲用水井;二級井是供村民洗菜洗肉;三級井用于洗衣服、農藥用水,最后流入排水溝灌溉農田,水井的空間布局體現了一水多用、立體用水、科學用水。地面鋪裝都是使用當地產的花崗巖石板,花崗巖結實耐用,除了方便在水井周圍洗菜、洗衣之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方便清理打掃,往石板面上潑水就能沖洗殘留污垢。苗族居民信奉萬物有靈,常常在村寨的橋、祠堂、井等重要空間節點旁種植各種不同的樹種,他們稱為“神樹”,景觀學上稱為“風景樹”。“澎水龍”井旁屹立著一棵百年柏樹,選擇在井旁種植柏樹,是當地居民長期實踐摸索的結果,柏樹是一種常綠高大喬木,一年四季不落葉,完全不用考慮掉落的樹葉造成井底沉積,發達的根系能凈化水源,茂盛的枝葉也能為村民日常洗衣、打水遮風避雨,高聳入云的柏樹是水井存在的一種信息符號,傳遞給過路人或其他村寨人,樹下有一口水井的信息,可以前往柏樹下的井旁解渴納涼。與“澎水龍”水井類似的空間布局是當地水井文化的一大特色,如圖2所示。它們是滋養當地村民世代繁衍生息的生命源泉,這不僅反映的是苗族居民對于生命的敬仰,更是他們的生態觀、美學觀和人文觀的集中展現,是把自然資源的利用發揮到了最大化,同時也將對水資源的浪費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使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有機融合,無不彰顯著苗族人民在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得出的大智慧。

圖2 村內其它呈相同空間布局的井
2.2 苗族水井蘊含豐富的文化價值
對于文化的解釋,英國學者泰勒認為:“文化是個復合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風俗習慣和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一些其他的能力和習慣。”是源自于獨特的地域環境和人文環境,水井作為當地村民的公共空間之一,不僅為道德禮制和鄉土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客觀環境,而且空間的范圍和結構可以規定并維系特定社會的禮制文化。
2.2.1 彰顯鄉村美德、重視個人教化
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人口的流動性很小、活動面積也僅限于村落經濟圈內。水井作為當地村民主要活動空間之一,除了滿足全體村民日常基本的生活飲水、洗漱用水及農田灌溉之外,還圍繞水井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鄉土文化,這種文化包括了很多不成文的約定俗成的相關規章制度、鄉村美德及鄉村倫理,即鄉村禮制,目的就是能夠滿足生活需要和利益。這體現在“澎水龍”井的“一井三格”的造型中,每格水井的使用功能和用途都各有不同,各村民不能夠“越界”使用,洗菜不能在飲水井,洗衣服不能在洗菜井,雖然沒有白紙黑字的文字記載,但是這種村規民約通過耳濡目染早已根植于每個村民心中。正所謂“子不教、父之過”,一旦做出“越格”的違反規矩的不良行為,不僅當事人會受到相關的懲罰,而且家里人也會受同村人的輿論譴責,這種譴責會影響整個家庭成員在村寨中的聲譽,這是一種內化的道德威懾,有時比成文的法律更具有約束性。相反,要想在村寨中享有美譽,和其他民族一樣,都提倡樂施好善、積善成德。吃水不忘打井人,水井不僅源自于空間的共享,更源自于對于事物的共享。在“澎水龍”的井旁的柏樹上掛著一把木瓢,這是全體村民用來舀水、喝水公共使用,個人不能私自帶回,凡瓢有損壞或老舊,當地某個村民就會自覺地重新制作新瓢懸掛在柏樹上供大家使用,這種雙手稱贊行為往往會獲得其他村民的褒獎,從而在心理上獲得認同感和榮譽感,就是提倡更多的村民樂施好善,積善成德,這是村民對傳統道理禮制的重視,是自我立德修身的體現。
2.2.2 寄托精神信仰、追憶生命起源
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中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由于當地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比較落后,就廣泛的充斥著泛神論者的特征,“凡百神靈,盡續敬禮”,信仰萬物有靈,村寨中的古樹、石頭、山、橋、井等都能夠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都附會上了風水、鬼神之說,水井便在苗族居民觀念中就形成了“水井神”的觀念。每逢春節臨近,就有絡繹不絕的村民前來祭拜,“水井神”和井旁的“神樹”都是祭拜的對象,熙熙攘攘排著隊,各自的背簍里裝著豬頭肉、米酒、香、紙、蠟燭和鞭炮等祭祀用品,見圖3所示。在大年三十晚上吃過團圓飯之后,村寨里的長者就會組織村里人清理井底沉積的淤泥,以及井旁香紙焚燒殘留的灰燼,當地居民稱之為“清井”,從井底挖掘出來的淤泥是一種上等的有機肥料,全部都傾倒在井旁的農田中,把資源利用到了最大化,同時也是在勞作過程中,產生交集、交流和互相幫助,間接地鞏固了村集體的凝聚力、團結性,維系了村民之間超出家族范圍的集體觀念,見圖4所示。

圖3 年關在井旁祭祀祈福

圖4 村民自發組織清理水井
新年初一,許多人家要早起到井中挑水,而且越早越吉利,當地人稱為“搶頭水”,即新的一年中的第一桶水,祈禱水神帶來福佑,除了有納福趨吉寓意外,也鼓勵村民要勤勞,爭做第頭名。夸里村還有著“舞龍燈”的民間習俗,這種民俗活動已經延續了好幾百年,每逢冬月二十六都要使用竹子、稻草、草紙扎一公一母兩條龍,苗族的龍和龍文化源自于盤瓠崇拜,是黃帝族的“龍”文化在民族的交融中與九黎族的“犬”文化結合,形成了盤瓠文化,成為現在苗族龍文化的源頭。夸里村的龍不僅在本村表演,還受外村邀請進行巡回表演,每次龍燈表演之前都必須在“澎水龍”井旁舉行祭拜“水井神”的儀式。當地苗民認為,龍住在水里,習水性,是掌管水勢和降水的一種瑞獸,井水貫通四海,進行祭拜儀式,除了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井水滔滔不絕永不枯竭之外,也是對于水井饋贈給族人源源不斷的甘泉的一種感恩儀式。當地村民有著樸素的生死觀,認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上天冥冥安排,每逢村寨有人去世,在入土之前要舉行相關的殯葬儀式。在“澎水龍”井中“取水”儀式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水都是和人們生死與共的神圣之物“取水”是由死者的直系后代或兄妹用竹筒在井水中舀滿水并密封,擺放在死者的身邊,隨棺材一起埋入墓地,那不僅是一筒井水,更是一種對家鄉的眷念,一抹念念不忘的鄉愁。不管是水井本身還是周圍種植的風景樹,苗族人都附上了神學之說,其背后的目的均在于保護這些大樹不被破壞、水井不被污染、水源不被破壞。這些主觀的神無疑對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穩定地表徑流,保持水井水量起到了積極作用。
3 新農村建設中湘西苗族水井面臨的問題現狀
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等相關政策的不斷落實,農村的經濟、面貌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傳統農耕環境下創造的鄉村建筑、鄉村禮制和鄉村民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水井作為鄉村必存的鄉村建筑節點之一,在使用、管理和維護上都面臨很多的問題。
3.1 工業文明沖擊、水井逐漸遺棄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打工熱便逐漸地流行起來,許多以傳統務農為生的村民都選擇外出打工,加上新一代的青少年受到現代工業文化的影響,價值觀、世界觀和思想觀都發生了改變,錯誤地認為居住在農村是貧苦、窘迫的表現,不少搬遷至各類服務齊全的城鎮中定居,昔日熱鬧非凡村寨現在也略顯冷清,留守在村寨中的也僅剩老人、孩童和婦女,因為自身的原因,他們前往水井中洗衣挑水的頻率減少,導致一些水井使用率很低,水質變差。加上村寨中的每家每戶都安裝了自來水,既方便又衛生,逐漸地擺脫了對于水井的依賴。
3.2 鄉村禮制滑坡、管理意識薄弱
在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關注的重點都是在改善村寨的經濟和村容村貌上,而忽視了鄉規民約維持,村民逐漸丟失了他們祖輩恪守的鄉村禮制。水井是公共的資源,一口水井供應著很多的居民,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在“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錯誤價值觀的沖擊下,原本淳樸的鄉村道德不斷丟失,水井常年無人打理,人畜用水、打藥用水和洗衣用水等嚴重的交叉使用,導致惡性循環。新一代的年輕人打工歸來,頭等大事就是修建西洋水泥房來顯示自己的富有,缺乏科學的統一規劃,許多村民擅自把新房子修建在自家的耕地上、山林中或池塘旁,生活垃圾、廚衛垃圾等其他垃圾亂排亂放、污水橫流,缺乏集中回收管理,地下水水質遭受了巨大的污染、滲透和破壞,井里的水也發臭變色,逐漸被遺棄。
4 水井的科學管理及鄉土文化的重塑
一口水井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之源,在上百年或者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誕生了一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或者喜聞樂見的鄉土文化,包括了各種傳統文化集合的群體活動,是鄉村倫理、民間習俗、民間信仰的集合體,這種文化集合是溝通和維持群體活動的途徑之一,加強對村寨內的水井的維護和管理,就是對鄉村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繼承與發揚。
4.1 構建管理制度、政府介入幫扶
水井是一個村莊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所以加強對水井的保護勢在必行。提高村民的環境保護意識,讓生態文明深入人心,使水井免受人為破壞,要求健全村內的衛生管理制度,做好垃圾分類、污染排放、藥物用水等措施,通過水井治理來強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可,達到生態宣傳的效果。充分實施村內責任制,做到“一井一管”,按照地緣位置劃分管轄范圍,在范圍內選取管理的人員,實行輪流管理或者選定人員管理,實現管理有序化、公開化、人性化及常態化,改變以往那種水井無人管理,臟亂差,亂排放,污染嚴重等癥。還要加強對苗寨水井保護資金的投入,沒有政府資金的注入,管理也不能持續進行,要做“量化”,有多少口井就投入多少資金,合理地分配資金到水井的開發利用、管理、文化的塑造和傳承。
4.2 重塑鄉土文化、形成村民自管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區別不同在于法律具有客觀強制性,而道德是個體的自我遵守實現,具有主觀自覺性。現在工業文明背景下,在農耕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倫理道德逐漸土崩瓦解,道德的譴責略顯力不從心,除了挖掘和重塑鄉村禮制之外,加強村民的自我約束的能力,還需要制定強硬的懲罰措施,阻止不良行為的發生,如井旁刻字立碑,詳細地說明違禁行為和處罰的方式,并直接處以經濟處罰等。
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水井是村民在合理利用自然資源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具體體現,也是鄉土文化繁育和生長的一片沃土,保護水井不僅是保護村民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也是對鄉村禮制、鄉俗文化的繼承。
5 結語
文化是人思想的內化,只有附著在某個客觀存在的物體實現傳承,才能達到教導或者影響人的思考方式、行為規范及生活狀態等目的。水井作為“高坡苗”苗寨中公共空間之一,除了承擔著滿足當地村民日常浣洗、集聚、灌溉等物質功能之外,還充當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重要表達的載體,是構成苗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現代工業文明的背景之下,由于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變,水井的功能性逐漸地被削減,水井文化也不斷面臨式微,急需采用對應的拯救措施和方法策略來保留水井和水井所蘊含的苗族歷史文化,調用民間或政府的力量,讓水井文化內化成為一種文化自覺,這是對水井最好的保護,也是對苗族鄉土歷史文化最好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