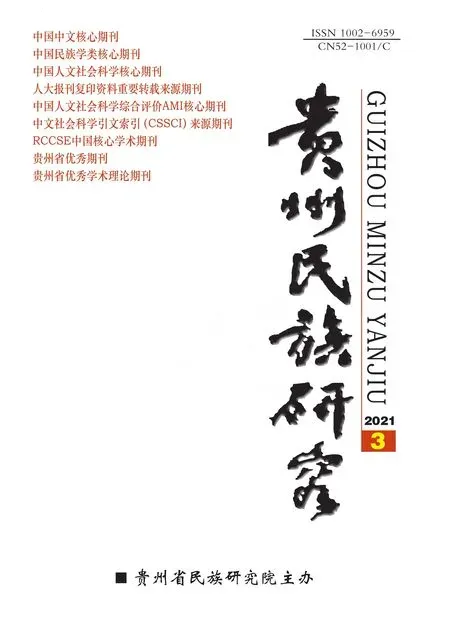文化選言中的愛情體驗:以吳娜電影為例
普天行
(貴州民族大學 傳媒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吳娜導演成長于貴州黔東南,畢業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教育專業,生活背景、文化體悟奠定了其電影的雙面底色——一面是對民族文化的眷戀,一面是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行歌坐月》(2011)和《最美的時候遇見你》(2014)均從女性視角講述了初戀體驗的青澀、美好和遺憾。前者克制、細膩地再現了貴州黔東南侗族村寨的生活情趣及自然風貌,用輕緩的視聽呈現了侗族大歌、吃新等民俗,少女情愫埋藏并氤氳在這片濃綠的大山之中,又充滿了對外界的向往;后者則將愛情放置于現代化城際間距的背景之中。
一、故鄉
《行歌坐月》作為一部“獻給家鄉的情書”,少女心思顯得含蓄而令人著迷。這封情書屬于未來和過去,但不存在于現下,她深藏于一個少女的暗戀潛流中,隨著姑姑的歸來,戀情的挫折已然若揭——故鄉也回不去了。這位中學畢業便留守侗鄉的女孩,因少年時的返鄉情愫而涌動。醋意伴隨著對外界的好奇,曖昧交織。風雨橋中裸露的女性大腿,野泳的紅色泳衣,漸次去往城市的伙伴,木質吊腳樓與磚房,文琴與吉他,鏡頭始終深深埋在綠色的大山中,直至火焰將之心緒波動。外部世界的樣貌囿于離鄉少年們的玩笑、姑姑的故事和父輩的“不準去”里。城市在電影中不作為一個具體的形象被呈現,它被廓除了,觀眾始終停留在一個孤獨的少數民族村寨中。盡管杏還是追隨飛(是追隨愛情的對象還是追隨著想象的時髦都市?)離開侗寨,她遇著什么,亦無明示。歸來的杏懷孕了,又做了一場夢:她背著一個戴了民族帽的嬰兒。拉鏡頭離開她,失焦。這個她屬于過去。因為爺爺去世了,時間的流動性意味著逝去,影片最終言明了創作者對故鄉的眷戀。這與該片開頭第一個夢呼應,那個源自醋意(一面關于飛,一面關于其他出走的伙伴)的夢暗示了杏對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對未來的期許。
顯然,城市或鄉土作為一種非此即彼的選言命題,在時間的流動中,在一個少女不甚明朗、謹小慎微的暗戀姿態下緩緩推進。結尾隱喻出一個往復洄游的文化認同,不甚明了。孕育代表了愛之永恒的延續性,它是戀人間的,也是文化間的——融合始終伴隨著彼此間或多或少的拉鋸式淘汰與失落。于是,民族身份尤為顯眼地成為這部影片的視覺識別系統,間或出現的他者以及“叛離”,使其文化的徘徊變得遲鈍又脆生生地撕扯陣痛起來。
有些時候,文化身份會在敘事中作為一個不相容選言——譬如這樣的句式:“文明客不是同‘蠻荒’之人相殺,就是同‘蠻荒’之人相愛”。在庫珀和舍德薩克的《金剛》(1933)、吉勒明的《金剛:傳奇重生》(1975)以及杰克遜的《金剛》(2005)中,不同語境產生出“相同故事”的不同選言。1933年的金剛還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異域奇觀,來自現代文明的金發麗人則作為一個誘人的符號;四十多年后,金剛和金發麗人之間的關系就顯得曖昧多了;到2005年,他們似乎墜入愛河,盡管文化身份依然作為一道鴻溝[1]。不相容選言中的愛情故事,往往“顧此失彼”,建立在“主客體”視域中的本體論規則之上。又如復雜社會格局和國家想象中孕育的《瑤山艷史》(1933)講述了漢族青年黃云煥深入瑤疆,與瑤族少女孟麗、李慕仙之間產生的三角戀情故事,“是3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產物,在聯合境內各民族打造‘中華民族’的年代,蠻荒被視為摩登,走入邊疆是流行的壯舉。”[2]這部現實中“有跡可循”的電影在宣傳上描摹了邊民的異族情調,用一種不著邊際的招搖將瑤族形象為文明客傾心的情色待開化者。“瑤女裸浴曲線畢露,瑤民就談教育普及”[3],這部影片的宣傳語從某種程度上再現了西方世界“想象的東方”。闖入者的“他者之眼”是文化想象中影響力最強的表達范式,《云上太陽》(2012)誠摯地表達了丑丑作為一名少數民族導演對異鄉人的熱情好客,對法國女畫家的奇妙治愈則顯現出這部電影某種虛無縹緲的詩意。相比《瑤山艷史》呈現出的對于異質文化的情色欲望,《云上太陽》的友好姿態是善良而積極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后者健康地傳遞出落落大方的包容和人情味。通過不相容選題,我們最終選擇一個正確答案,為之感動或興嘆。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在深度上顯示出文化交流的裨益?文化想象將他者文化降格為淫靡的狂女,或者我們僅僅停留在“一廂情愿”的美好期許下,那么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壑與摩擦在疏忽大意的小心呵護中消隱了。不得不說,潤滑劑并不能使得那個最為本真的存在彼此靠近,我們依然需要正視并珍惜那些在文化的長談中不經意流露的真心話。文化的交往,與兩個他者的相遇一樣,不可能是沒有體積碰撞的。
另一方面,“還要經歷多久時間,個體身份才能不再與民族同情的律令死死地綁定在一起?”[4]從《瑤山艷史》到十七年電影創作,愛情首先作為一種服從于主流話語的意識形態表達——如《秦娘美》(1960)及《劉三姐》(1960)。政治教化作為這些電影最重要的任務,“黨的文藝方針是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為大眾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一切文學創作都要圍繞著這個方向,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組成部分的電影也不例外。在這樣的語境下,電影為‘政治服務’成為首要的‘政治任務’,特別是作為與國家政權穩固息息相關的文化宣傳工具,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拍攝,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必須為‘鞏固邊疆,加強民族團結’的政治形勢服務。”[5]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腳步,國家戰略不斷發生調整,個人生活體驗急劇改變。少數民族或地方創作主體對于民族、地域及自我的思考亦在發生改變。當兩個不得不同處一室的陌生人在短暫地相互客套和試探性地彬彬有禮之后,很可能進入到一個認識論的緊張階段。這與“尋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從而導致我們的經驗視野日漸狹窄”[6]不同,我們可能對他者產生敵意,也可能產生敬畏,我們意識到一個特異于我們的另一個主體,有助于了解自己。
在吳娜的電影中,少數民族身份并未淪為媚態的刻奇,作為一位暗戀狀態無法邁出的少女,作為一個封閉的孤獨個體,其戀情無法與人訴說,只能克制而隱忍。初戀的青澀,家庭的善良以及自我的省思,對于那個未來的世界,已到的現代化,亦非采取強烈的批判姿態,這種意識流的直接感受正誠實而可貴地嘗試著將概念世界廓除。
杏的爺爺在“看電視”時,電視內容總是本民族的(影片最開始,爺爺面前的電視正在播放一個侗族少女彈唱民歌的內容;杏離家出走后,爺爺生病臥床,電視上播放的是侗族大歌的場景);而年輕人面前的電視則播放流行音樂和偶像劇。前者的觀看如同顧影自憐,是等待或守望的,甚而是那喀索斯式的;后者是向外拓展的,表明了一種想象和渴望。爺爺的離世告知了這種等待的無望和茫然,杏重復了姑姑的命運又告知了渴望的無期和困惑。電視作為現代媒介兀然放置于這個孤獨的村落中,投射出兩種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卻無法給出那個選言的確切答案。這個現下處于等待中的少女并未被動地遭到一種民族關系或文化表征的裹挾,而是先在最一般人類情感的肇始下觸碰到了異質的他者和文化。民族、文化、政治、性別或者簡單的媒介關系,反過來使得愛情作為受到抑制的情感沖動顯現——在“保守”的村寨里,杏渴望著出尋;而后,時間又使這個村寨變成了回不去的故鄉。正如加繆在《局外人》里說,“故鄉安置不了肉身,從此有了漂泊,有了遠方。異鄉安置不了靈魂,從此有了歸鄉,有了故鄉。”在故鄉與異鄉的回環中,總有一個是不在場的,在加繆的句式中,文化身份是飄忽的,它同樣是一個優柔寡斷的選言命題。如同鄉愁的發生一樣,愛情的發生亦伴隨失去或空缺。《行歌坐月》敞開了一個更為復雜和本真的文化狀態和愛情存在——一個相容的選言。
二、他鄉
與第一部影片相比,即便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這個愛情故事的重要“發生地”,《最美的時候遇見你》似乎除了鎮遠的徽派古城及凱里的現代民族體育館,已無更多可供辨識的地域特征(甚至方言的使用也并不“地道”)——這個故事僅保留了一段促成愛情生發的簡化的時空距離。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愛情敘事,最終導向的是那種巧妙對仗(置換)在時空關系中的話語、倫理及概念。愛情由一個動詞轉換為名詞,即一個結果。促成這個結果或相反,取決于橫亙在一對戀人間的阻礙(矛盾)是否得以解決。當這個矛盾作為一種宗教、政治、倫理或種種其他因素出現時,所有使之不能結果的,均會引起人們的同情或厭惡之感。
無論是斯萬的嫉妒、歐律狄刻的消失還是波德萊爾的驚魂一瞥,無論是莎翁的毒藥、法海的雷峰塔還是珠郎娘美的款約,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愛情敘事都作為一個不永恒的存在顯現,它們(愛情)存在于信息不對等的時空流動中,伴隨著某種猜測、誘惑和妒意。在這部電影中,楊芳芳和郭陽的每一次“遇見”都伴隨著疾風驟雨的快樂和隨之而來的痛苦。不同地域不再表征城市與鄉村的緊張,也并未出現一個其他的矛盾阻礙他們的愛情關系,這個相對立體的行為,只存在于時間和空間的拉扯中。在吳娜的電影中,電視、電腦、書信、火車、手機的介入完成了一層媒介的隱喻——人們的經驗世界及關系受到媒介的左右,另一方面,這些影響了人們如何使用感知的媒介反過來道出了“觀者之意”。
從書信、火車再到手機,技術似乎使得分隔兩地之人愈發便捷地取得聯系,但這些依賴于位置和時間衡量的技術“創造了聞所未聞的機遇,但又立即以相同的方式破壞這些機遇。”[7]楊芳芳在浮光掠影的城市中踽踽而行時,過去戀人的電話讓她回憶往昔——與愛情一樣,回憶是抓不住的。她最終沒有走入那個咖啡館,如同穆罕默德二世所做的,一旦感受到自己的強烈情感,他就用匕首刺死那個妃子。
楊芳芳不愿意重蹈哥哥缺乏勇氣的覆轍,希望避免自己像他那樣在站臺上錯過邂逅,面對“無聊”的“大海”。命運的火車注定她將失去“美好”,因為她同樣沒有在站臺(凱里)“停下”,而是去了海邊(廣東)。最后,吳娜將結果置換成如果。回到過去,郭陽擁抱了離別時回頭的楊芳芳。時空距離的不可克服在這部影片中被媒介賦形,媒介一方面解決了人際交往的間距,一方面又將這種間距顯現出來。手機不是直接聯通的,它必須有雙方的授權,對于撥出者和接話者而言都是需要等待的。在這段時空的間距中,與手機的被動性一樣,火車的終點亦被決定。火車的運行不可逆轉,此種意義上,它與時間保持一致(這部電影的副導演畢贛在其作品中完成了另一種詩化的表達)。解決空間問題的火車意味著離開,解決時間問題的手機意味著等待。
電影中的現在時是楊芳芳置身于城市中,接到了郭陽的電話,約她在咖啡館見面。火車駛向“大海”,將永遠無法回到時間原點;手機接通思念,將伴隨著空間距離而持續膨脹,在持續的未達成中,愛情于此得以顯現。“一個人既然愛,就是還沒有那樣東西;他盼望它。就是盼望他現在擁有它,或者將來擁有它。即鐘愛者還沒有得到所愛的對象。”[8](P46,58)在語境中,鄉土成為了城市的“后花園”和附屬品。一方面,它在一些由于城市“從來不用心……鬼頭鬼腦……神經極度衰弱……心腸太硬而骨頭太軟……(城市中的)一幢幢高樓在黑暗中跪了下來,一個個美人兒在謊言中毀容,一座座展覽館,只展出不三不四的東西”(《把城市拉回鄉下喂狗》俞心樵)而回望的文化邏輯下被定義。在這種因果關系中,鄉土喪失了首先作為生活場所的本然。另一方面,鄉土又作為一個與城市“分庭抗禮”的被復制的文化消費品導致了一些傳統村落的破壞性“保護”和開發。主體性喪失使鄉土不再作為一個文化的他者,選言變成了“城市或‘非城市’”(或者反過來,“鄉土或‘非鄉土’”),而非“城市或鄉土”。本文并非要用批判的方法研究這些現象,而是時間決定了“相對于”的邏輯是很難解決的,簡單來說,我們總會先局限于一個城市或鄉村——如同那位塞浦路斯國王一樣,不愛所有現下的美人,卻愛一個“沒有生命”的雕塑(完美的相)。與敘事中的雕塑終于獲得生命不同,現下的我們不具備完整性。
另一則神話中的俄爾浦斯因為回頭,永遠失去了妻子(于是擁有愛),他的悲痛(愛)被酒神(麻痹記憶)的狂女(匱乏愛的)撕碎并吃進腹中。于是,《最美的時候遇見你》是以回憶的方式展開的,愛并不以具體的存在者化身,它始終作為匱乏之物的某種假定性存在——一個“如果”。當然,這不是一部在形式上頗值得玩味的電影,其獨特在于,如何能展現一個絕大多數私有的愛情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它廓除的不是敘事,而是觀眾。通過“拋卻族群訴求的羈絆,當代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女性導演在處理非本民族題材影片時,個體化的女性視角卻表現得更為自由和深入。”[9]某種意義上,那些膩歪的對白,只有忘我的情侶才能親昵出來。
三、愛情
兩部影片對于愛情狀態的描寫截然不同。前者中的愛情是神秘的,其愛的滋味源于一種不甚明了的暗戀;后者抽象出一個空蕩的舞臺,猜忌和熱烈的重逢輪番上演。前者房門半掩的村落中有人離去,有人歸來,原有的少數民族生存樣態,潛移默化地讓人嗅到異質文明的氣息——含蓄而低調。對于他者的好奇和外界的期待,暗合了少女暗戀的心意,涌動卻沒有聲張,“達成”作為一種渴望而非現實。這種人與人、人與物或文化與文化的曖昧關系生成了一種誘惑。后者轉變為一種更為直接而淺層的情感體驗,相應地,一旦其失去了同類“青春片”的“漂亮臉蛋”或錯綜復雜的敘事策略就更顯乏力了。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腳步,原本封閉的社群在諸多因素下與外界發生聯系,這種愈發密切的聯系帶來更為曖昧含混的文化交融。其予之個人的直接體驗、身份不再作為一個首要克服的矛盾,愛情體驗簡化為時空關系;時間的前后腳中,亦不再有一個如此不同的鄉土等我回去。
盧曼在談論愛情時指出,當“愛情作為媒介本身(時)不是情感,而是一種交流符碼,人們根據這一符碼的規則表達構成、模仿情感,假定他人擁有或否認他人擁有某種情感,如果相應交流得以實現,還能讓自身去承擔所有的后果。”[10]當我們試圖找到那個愛情本身時,語義層面的愛情并不作為愛情本身存在,非但因為有了愛情的“相”愛情才存在,“相”或語義還作為可替換之物,是被愛情的敘事傳喚的。愛情本身作為那個不被擁有的“東西”,在最難以捉摸的距離中顯現。愛情本身“不可見”。但在藝術創作中,我們始終“鄙夷”那些最直接給予我們情感的沖動之物,反以修辭賦予其形而上的“美感”和“韻律”——愛情作為名詞被歌頌。愛情的感知并不首先是語義,即我們予之的任何定義或先驗的概念,而是距離的偶然與不可控性,是時空不對等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錯位。換言之,愛情并不簡單顯現為語義,而是語義因之傳喚的距離。其神秘與誘惑正源于語義的可替換和不確定性,距離之感是第一性的。
前面我們說吳娜第二部作品中的兩位青年男女在初戀時的膩歪對白是忽略了觀眾的。當愛情作為一種語義操縱的媒介時,其矯情伴隨著以往愛情敘事的模式,人們揣測其擁有的小小幸福是否與符合著最一般規則的愛情期待視野相匹配。當其作為一個“他的”而非“本我”的方式和嵌套了的存在者出現時,投其所好的敘事學用符合觀眾期待的方式供其“扮演”,于是作為我的觀眾看見我想看見的。換言之,只有當這個作品再現的是一個知覺現象時,我們才看見另一個作為主體的他者。由此,鐘愛者才無法得到所愛的對象——愛情得以存在。此種意義上,文化亦是如此。迄今為止,吳娜只拍攝了兩部影片。這位細膩直接的電影導演,在其愛情故事中潛移默化地投影出別樣文化體驗。從城鄉關系的對立到地域與地域之間對文化符號的消隱,他者的存在從文化的沖突搖擺轉變為面對直接時空的錯過,其愛情圖式又最終化身為都市男女的一般情感。
“愛并不是以美的東西為目的的……其目的在于在美的東西里面生育繁衍。”[8]假如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所說的“愛的生育”是“愛的不朽”,這種不朽之永恒不是某種“確定性”,而是“美的東西”的持續變化之生滅。杏在離開后,她的爺爺問了村里的先生,他們能不能找到杏;先生答,不能,只有當杏遇到了問題,想念家人才會回家。杏懷孕后回家,顯然在北方的城市中遇到了麻煩,此刻爺爺已經離世,她可能重新陷入對于過去(文化身份)的追索里去,這意味著除此以外的世界重新處于未達成的狀態之中。也就是說,那個還未誕生的新生命孕育著不確定性,當它來到這個永遠在未來存在著可能性的世界時,它的身后留下一條線性的足跡,它的下一步則可能踏在不確定(未達成)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