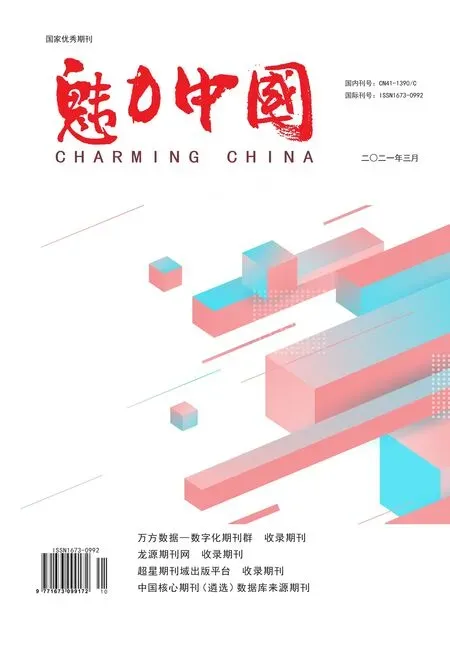戲曲導演的專業手段
楊小紅
(濮陽市戲劇藝術傳承保護中心,河南 濮陽 457000)
自由、靈活、虛實結合的美學原則構成戲曲時空觀念及舞臺空間結構的獨特性。本文對戲曲導演的專業手段進行分析。
一、以實為本,以虛為用,虛由實來,實仗虛行的獨特戲劇美學思想
中國戲曲藝術對戲和生活之間兩者關系的認識是有其獨特性的,即戲是生活的虛擬。“因夢成戲”,“用之貴虛”正是戲曲這一戲劇藝術在戲劇美學思想上的獨特性的表現。
虛擬是產生戲曲程式的理論根據,程式是虛擬在藝術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在戲曲藝術的時空觀念和舞臺空間結構上,虛擬手法是戲曲時空自由的所有表現手法中最重要的手法。
戲曲藝術表現生活的辦法不是照抄生活的原狀,承認舞臺假定性是中國戲曲藝術的傳統。這種假定性的美學思想基礎即出于戲是生活的虛擬這一獨特認識的。戲曲中時空的虛擬、自然環境的虛擬、地理環境的虛擬、物體的虛擬、人物動作的虛擬等,都是基于舞臺假定性這一戲曲的基本特性的。虛擬是戲曲假定性的核心,是戲曲時空觀的主要體現。
這種手段直接導致了戲曲時空觀念的獨特性和舞臺時空結構的多樣性、靈活性。虛擬的表現是戲曲時空風格的主調。戲曲的虛擬動作不但是戲曲表演區別于其他戲劇流派的主要標志,而且也是戲曲體系區別于其他戲劇表演體系的主要標志。因此,以假定性為前提的戲曲虛擬說是直接關系到民族戲劇美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弄清虛擬的概念,并尋求其產生的原因,不但是探討戲曲時空自由問題的重要一環,同時對中國戲曲的表演體系,及美學理論的研究也不無好處。
“虛擬”一詞,由于對其概念內涵理解的不同,其外延也就不同。“虛擬”一詞,實際是后人對戲曲表演特征的總結。它適應的范圍主要在戲曲表演中。虛擬中“虛”的意思是要虛掉戲中與角色發生關系的環境和實物對象;“擬”的意思是環境和對象雖然虛掉了,卻要通過舞蹈身段的模擬顯現其存在。“虛”并非純而又純的徹底虛無,有時不排除小道具的借代、指示、暗示作用,既刻畫了人物,同時也顯現了角色活動的環境和對象才能稱“虛擬”。它不同于西方的芭蕾舞、啞劇、民族民間舞蹈,西方藝術的舞蹈動作只是用以說明解釋劇情,其動作雖虛但它不表現劇中環境和對象以及其他變化。阿甲先生說,虛擬表演的主要目的,在于處理環境和對象。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處理戲曲中那沒有辦法上臺的時空自由敘事體的環境和對象,當初的虛擬表演也不會形成。這就要追究一下戲曲虛擬的產生原因了。
二、以舞蹈的形式表達敘事體內容的特殊歷史道路決定了戲曲時空觀念及表現形式的獨特性
如前所述,既然一般性舞蹈表演中沒有虛擬表演,那它來自何處?我們說虛擬產生于以舞蹈的形式表現敘事體的內容。從本質上講,戲劇乃是一種再現性藝術,這種再現性質要求其情節應該是一種適合于在舞臺上再現的“再現體”,而不是“敘事體”。再現體要符合舞臺再現的原則,而敘事體與再現體相比則是時空自由的。一個是封閉式結構;一個是開放式結構。如果在舞臺上表現“敘事體”的情節,就會發生兩方面的矛盾:一是敘事體的時空環境變化頻繁,而舞臺的時空是固定不變的,二是敘事體的時空環境廣度大,而舞臺的時空是有限的。
中國戲曲的劇本情節是一種時空自由的敘事體,而并非嚴格受舞臺制約的再現體。戲曲形成之初以既成之歌舞搬演“敘事體”的故事,而不是像古希臘戲劇那樣以舞臺再現原則創作劇本。從戲曲藝術因素的構成看,戲曲的發展來源主要有:歌舞、滑稽戲、說唱三個主要成分。從問世的第一個戲曲作品《張協狀元》開始,直至現在其間無論是宋元南戲,明清傳奇,北雜劇或清代地方戲以及今天上演的傳統戲,其情節都是“可以將天涯海角連在一起的敘事體,這種獨特歷史道路形成了戲曲藝術的獨特風格”。假如當初戲曲也走古希臘戲劇之路(歐洲古典主義戲劇的劇本創作規則:“三一律”要求劇本情節、地點、時間三者完整一致,一個事件,一個整天,一個地點,情節結構簡練、集中),恐怕中國戲曲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獨特的歷史使戲曲沒有自己的再現體劇本,而是采用了敘事體的故事。這就使戲曲劇本有了時空自由的特性。時空自由的敘事體是不可能再現的。如果完全襲用敘事體內容原來所采用的敘述手法,那會使一切都失去視覺形象,而使戲曲變為一種單純的聽覺藝術。怎么辦?中國戲曲憑著它的巨大包容、消化和創造能力,既不想再現又非要表現這種時空自由的敘事體,于是一種新的表演方法——虛擬表演誕生了。它虛掉了那沒辦法上臺廣闊博大,復雜多變的環境及各種實物的對象,再以舞蹈身段模擬其存在這種虛擬表演只用舞蹈身段,就可以把廣闊多變的環境和巨大的實物對象表現出來,因而就突破了客觀舞臺的“有限”和“固定”的限制,贏得了戲劇舞臺上的時空自由。可見,戲曲的虛擬表演是為適應特定內容的特殊需要才出現的。也就是說,當用舞蹈的形式表現時空自由的敘事體內容時,就需要虛擬來克服這個困難。
由此可知,虛擬表演是戲曲發展到一定階段,以舞蹈形式來表現敘事體的內容,為解決時空環境和對象在舞臺上的轉化問題而逐步創造出來的一種絕妙的表現手法。它成為了戲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生活是無限的,任何藝術要表現生活都是有局限的,用有限的藝術手法去表現無限的生活,如果不在藝術中變換生活的原來形式,完全照生活原樣去反映是辦不到的。因此,所有藝術都不能不做變形。戲曲的變形和生活原形距離較大,其變形的方法與程度較之其他藝術也有所不同。這種變形手法之一就是虛擬,它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即通過程式手段。
虛擬表演本來是一種限制下的產物,但長期的藝術實踐卻使它形成了風格。這種風格一經定型,就成了藝術特性。而這種特性竟至成為中國戲曲表演體系的核心。當它一旦形成了統一的風格,它的一切表現手法、表現形式就必然要體現著它的美學思想。它對那些雖然從再現角度來說并不困難的時空環境和對象也決不去再現,而一定要以那閃爍著自己美學體系光輝的獨特風格去表現,從而體現出戲曲對舞臺時空處理的靈活、自由的特性。
三、中國戲曲藝術的“虛擬程式動作”和話劇的“無實物動作”的本質區別
寫實派戲劇藝術的所謂“無實物動作”是一種訓練演員的方法,(一種假設的訓練,在空空無物的手里,假設有某種實體的東西存在,并表演出真實性給人看。)在舞臺正式演出時是基本上不用的。而中國戲曲藝術在演出中卻經常離不開無實物的虛擬動作。如京劇《拾玉鐲》中孫玉姣之喂雞、轟雞、數雞、做針線……再如戲曲舞臺上的開門、上下樓等等,臺上并無實物的門、樓,而完全由演員做表意的程式動作來體現,這當然就是虛擬了。但如果說戲曲藝術的開門、上下樓、喂雞等等諸如此類的大量的程式動作就是話劇藝術的“無實物動作”,實在是似是而非。它們是有著質的區別的。“無實物動作”雖沒有實物,但它要求演員心中有實物的物質感。既要明確實物的體積、質地、位置、重量、結構等等,又要求通過動作如實地表現出來,要有嚴格的分寸感、量感、質感。比如話劇演員表現自己拿一張紙,他就要明確表現出紙的厚度、輕飄、脆弱等等特點,如同有實物在手一樣。而戲曲的“虛擬動作”雖也注意及此,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強調把沒有實物的“實物”意象化。要求并非生活原型的模仿,而是在“虛擬”原則下進行的一種想象的形象創造。它不要求演員如有實物一樣的一般無二。正因如此,在戲曲表演藝術中,即使把實物和無實物程式動作同時并用,也不會使人感到別扭。如京劇《柜中緣》一戲中劉玉蓮做鞋,鞋底是實物,而針、繩卻是無實物;《秋江》一戲中船槳(或篙)是實物,而船卻是無實物;《挑滑車》一戲中馬鞭是實物,而馬卻是無實物……表演起來情調、風格非常統一。這是因為無論有無實物,都是統一在戲曲虛擬的程式化表現方法中的緣故。是對生活真實進行意化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使戲曲的虛擬動作夸張了、美化了、舞蹈化了所以在戲曲演員的表演中,只要求演員交待清楚要表現的東西,意思明白、點到為止,做到能夠使觀眾看懂就夠了。對其瑣碎細節并不苛求,也不必去斤斤計較。例如京劇《秦英征西》中秦英被鎖在太湖石上,秦英行走只好提石而行;《拿高登》后邊開打用的石鎖;《十三妹》中何玉鳳所舉的大石頭…都不著意表現其重量感及分寸,而是輕松自如,因為戲曲藝術的“虛擬動作”著重寫意而不拘泥于形似。戲曲藝術認為從虛擬想象到有景物不是目的,只有在虛擬中看到人物的神情才有意義。
總之導演要觀察生活、熟悉生活才能組織好舞調度。舞臺調度的巧妙性和表現力是直接以導演的個人經歷、生活基礎、文化修養、特有的藝術鑒別力為轉移的。這些是舞臺調度的基本藝術要求。因此,可以說舞臺調度即是一系列合乎邏輯的有明確目的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