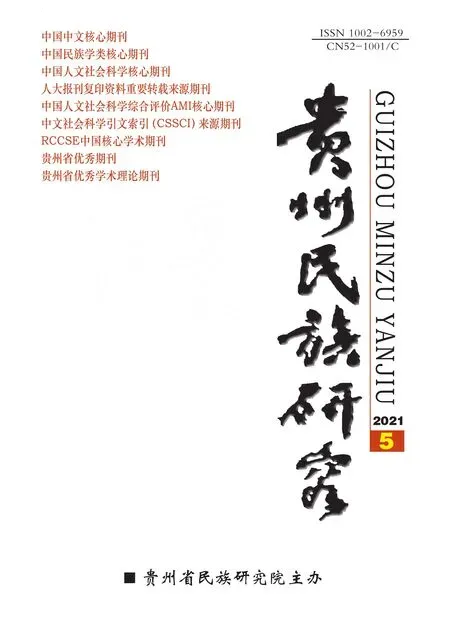方南苗族服飾日月星辰紋樣的視覺符號交融互動研究
胡瑞波 董建輝 果 霖
(1. 廈門大學 人類學與民族學系,福建·廈門 361005;2. 貴州師范大學 國際旅游文化學院,貴州·貴陽 550001;3. 云南農業大學 機械工程學院,云南·昆明 650201)
引言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農民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對文明的一種詮釋》中提出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概念,雷德菲爾德強調:“大傳統由為數不多且善于思考的人群構成,小傳統則由數量很大且不善于思考的人群構成”。雷氏提出大小傳統后學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并逐漸演化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對其進行修正。大傳統存在于學校和教堂等會讀書寫字的人群中,小傳統則存在于不擅長讀書寫字的鄉村社區的人群中,他認為“大傳統”和“小傳統”并不是絕對分離的,而是存在交流交融和互動的關系。上層社會的精英文化,也可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社會人員的流動和變化逐漸地流入民間文化。例如古代的宮廷音樂二胡從精英階層經過不斷地發展和演變而流入民間。苗族服飾中的圖案也即如此。例如“卐字紋”在中國佛教和中國古代社會中是最為常見的圖案,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和變遷逐漸流入民間,被民間所開發和利用。小傳統的大眾文化也可以隨著個人的、群體的擁護及統治者的利用升級成為大傳統的精英文化。比如說苗族中的張秀眉和務茂喜等歷史人物為反對階級壓迫而進行的農民起義和反抗清王朝統治的事跡,逐漸地被清水江流域的方南苗族視為民族英雄而被逐漸地升級為這個支系的民族精神和象征性符號。基于此,本文引入雷德菲爾德的“大小傳統理論”,探討苗族服飾中的太陽紋、月亮紋、“卐字紋”和八角星紋等圖案,在大傳統中如何轉變為小傳統,而小傳統又如何被當地人所識別應用和賦予新的文化內涵的過程。與此同時,對當地人是如何辨別“卐字紋”“壽字紋”和“拐棗紋”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也加以辨析。關于這些符號的運用,在《苗族古歌》中的“射日射月”中闡述了苗族先民對其鑄日造月和天地萬物生成的狀態。在苗族先民看來,宇宙生成之前,天地萬物都是云霧彌漫,白茫茫黑沉沉的狀態,于是就有了“云逛”“霧抱”的宇宙生成觀。在這樣的狀態下,通過“云逛”“霧抱”逐漸開天辟地[1]。天地分開以后,天地間的距離太近,于是大象來踩踏,實現了天地分成兩半的狀態。此時,天黑沉沉的,于是就有了苗族先民鑄日造月的神話故事。在鑄日造月的過程當中,鑄造了十二個太陽和十二個月亮,導致了天地萬物災難性的后果,于是又產生了苗族古歌射日射月的故事。完成射日射月的任務以后,剩下一個太陽一個月亮。此時萬物舒展,天地恢復正常,于是有了楓香樹產生妹榜妹留的故事,展開了人類對大自然改造和優化升級的過程[1]。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們對當地的萬物生成,在小傳統當中有了獨特的認識,對小傳統的宇宙生成觀,對苗族當中的“卐字紋”、太陽紋給予地方性的解釋。對于這個解釋是如何變成地方性解釋在苗族歷史中少有文字的記載。加之,苗族不善于文字記載,其歷史通過口耳相傳和苗族服飾載體傳遞下來,苗族婦女將符號和文字繡在白布上,作為母題代代相傳。由于長期的遷徙歷史和世代不斷地給予新的嘗試,這種大傳統的文化符號逐步與當地的生活化場景的符號聯系起來。例如苗族服飾圖案“卐字紋”由精英階層當中的太陽、光明、希望的寓意逐漸地賦予了地方性的解釋。而“拐棗紋”正是逐步由“卐字紋”引申而來,從“拐棗紋”的造型上來看,彎彎曲曲的造型將其平面化,很像“壽字紋”的形態,但是從拐棗的實用上看,它又具有中藥的價值成分,因此對人的身體健康有益。由此,從實用的層面上來看也與“壽字紋”有聯系,且“壽字紋”與“光明”“太陽”“希望”有著廣泛的聯系。因此,施洞苗族服飾中的“卐字紋”被賦予了地域性的解釋,且從精英階層的大傳統走向平民化的小傳統的一種全新詮釋。本文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針對苗族服飾當中的太陽紋、月亮紋、八角星紋、“卐字紋”進行田野調查和訪談,其目的是探索苗族服飾圖案的生成并對其傳承和發展探索新的途徑。
一、日月星辰圖案在苗族服飾中的符號與象征的關系
雷德菲爾德指出“大傳統”依賴“小傳統”,“小傳統”通過凝聚轉化而上升為“大傳統”[3]。進一步指出“大傳統”具有“高雅的”“上流的”和“神圣的”的特征,“小傳統”具有“低等”“世俗”“鄉土”“民間”的特征,兩者之間相互借鑒和吸收,共同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變遷。苗族服飾中常見的圖案有太陽紋、月亮紋、八角星紋、“卐字紋”等,這些圖案在漢族及其他民族中也非常普遍,其圖案在創作的過程中存在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的流動關系和彼此間交流交融互動的關系。
從《苗族古歌》 中的“鑄日造月”中講述“天地和萬物生成以后,白天無太陽,夜晚無月亮,大地黑漆漆,自然界萬事萬物死氣沉沉,從而誕生了寶公、雄公、且公和當公主持鑄日造月的故事。當時由于沒有圓簸箕和圓水缸做參照,日月也不知其形,后造水圈描繪出日月的形狀。金子造太陽,銀子造月亮,舉錘打金銀過程中脫離的金銀微粒造星星和長銀河,最終造了十二個太陽、十二個月亮、滿天星和長銀河。制作完成后請理工和雄天將其送上天均以失敗告終。此后,請冷王將其運送上天,途中艱難險阻后由固勞舉斧一砍,烏云散開,冷王沖破層層艱難險阻終于成功地將其運送上天。臨走前交代‘從今日起,你們留在天上,子天子出來,丑天丑再上,輪流出現不要亂闖’。日月由于沒有記牢冷王說的話,同時出曬得水田冒泡,石頭像黏膏,草木枯焦,小孩出來割草死在坡上,姑娘撈湖瓢死在田里,造成自然界和宇宙萬物不得安寧。激怒了當地的民眾,決心要射下太陽和月亮的故事,后請桑扎射掉了十一個太陽和十一個月亮,剩余的一個太陽和一個月亮躲了起來,天地又回到了黑茫茫的狀態。基于此,讓蜜蜂和黃牛去叫日月重新出現未果,后讓公雞去請日月才出現,太陽白天東起西落,月亮晚上出現。此后,牯牛打架、姑娘出嫁、田間溫水、莊稼生長,自然界萬物才散發生機勃勃狀態。”[1]從這個故事題材來看,是典型的小傳統通過族群內部的相互傳唱和優化而逐步升級為大傳統的故事題材。
《苗族古歌》的內容表達了苗族共享的集體記憶,是以大傳統的話題出現的,后經過無數婦女的再創作,創造題材又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在小傳統中,創作圖案的話語權,與苗族婦女對刺繡、剪紙、織錦和講故事等方面集體對其評價有關,通過口耳相傳逐步升級為大傳統的文化。同時,從“鑄日造月”可以看出,苗族高度擬人化的色彩,堅持人定勝天的觀點。在認識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彰顯了樸素的苗族先民為創建美好家園,能夠就地取材,化萬物為我所用的精神為該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鑄日造月的過程中,彰顯了寶公、雄公、且公和當公在選擇日月鑄造材料、工藝、造型、工具等方面經歷了艱辛萬苦。鑄造日月由于溫度過高需要尋找無人區進行鑄造以減少對人和大自然的破壞,彰顯了苗族較為樸素的生態觀念。鑄造日月的材料和工藝的使用體現了苗族先民就地取材和萬物為我所用的觀念。從“鑄日造月”整個故事中,不難發現,苗族先民能夠根據自己的生計方式就地取材來為我所用,為改造惡劣的生存環境譜寫了一曲優美的歌謠。這些動人旋律被無數的苗族先民傳唱和苗族婦女用刺繡的方式將其繡在服飾上,采用夸張、變形和抽象的創作手法代代傳承。
二、卐字紋在苗族服飾中的符號與象征關系
縱觀卐字紋的發展演化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小傳統發展變化的過程。在李亦園先生看來,大傳統代表精英文化或上層文化,“小傳統”代表民間文化或下層鄉民文化,它們之間在表現形式上各有差異,集中表現為“大傳統重義理與儀式,小傳統重功利甚至迷信”,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機整體。由此,大小傳統之間的流動和傳播交融交匯是研究的核心問題。在苗族社會中,苗族先民樸實的宇宙生產觀是通過當地人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逐步演化而形成的。他們對自然界通過主觀臆測和原始宗教高度擬人化,且能夠用直接和樸實的方法將其表現以祈求吉祥和安康等寓意。卐字紋在古今中外表現極為豐富,在古代中國、印度、古巴比倫、波斯等古老的國家都有卐字紋的痕跡。相對于大傳統的中國而言,新石器時代晚期馬家窯文化(前3300—前2050 年) 中的半山型和馬廠型的陶瓷上,都發現了卐字紋的形態。此后,在內蒙古小河沿文化發現大口深腹罐和廣東石峽文化中層陶器均有卐字紋的出現[11]。相對苗族小傳統而言,卐字紋在方南苗族服飾中表現也極為豐富。兩者之間的文化內涵是否存在一致性和差異性的問題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方南苗族服飾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款式的服飾中,在衣襟后部上方的疊布繡和服飾前胸靠下外側的疊布繡上的圖案是永恒不變的。苗族婦女使用疊布繡的工藝,將漿好的布料裁剪成一定的大小,折成三角形一層層疊在一起而形成的紋樣。中間為兩個卐字紋,兩側各一個卐字紋,卐字紋外側為菱形紋,菱形外側為八角星紋,中間用兩道橫杠隔斷成三個部分,并在橫杠上下飾以山形紋。根據傳播論的觀點,傳播論被喻為“文化的水波論”,認為文化傳播的漣漪縱橫交錯地遍布于各文化之湖,從中心到往四周逐漸地減弱。傳播論表現的特征為越靠近中心的文化越容易發生文化變遷,越靠近邊緣的文化越容易完整地保留文化產生時的形態。結合傳播論的觀點來看,對于苗族服飾中的卐字紋和八角星紋而言,與古老的中華文化中的卐字紋和八角星紋的內涵有關。那么,卐字紋到底是怎么來的呢?有專家認為卐字紋為八角星紋的簡寫,代表著東南、西南、西北和東北四個方位,后逐步演化為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寓意著太陽循環和四季更迭等含義。佛教中的卐字紋則象征太陽和火的崇拜。不難看出,八角星紋源于卐字紋,卐字紋是八角星紋的簡略版,都是吉祥圖案為太陽崇拜演化而來。而苗族服飾前后兩片疊布繡中的卐字紋和八角星紋寓意著太陽崇拜,寓意著子孫延續并健康長壽等。同時隱含了苗族民間十二對日月崇拜的故事和苗族長期的遷徙歷史,其中,疊布繡上的山形紋、菱形紋和橫杠寓意苗族在長期的遷徙歷史中所遇到的山水和大江大河,并將其刺繡在服飾上以警示后人銘記遷徙的歷程。
在清水江流域方南苗族那里認為“卐字紋”也即“荄里芥”,包含了施洞為中心上至平寨下到五河區域中的最為常見的一個紋樣。在方南苗族地區“荄里芥”也稱“荄氣”或“拐棗”是指生長在山中的果實的紋樣。有的地方也稱“木珊瑚”“雞爪”“龍爪”“蜜爪爪”“萬壽果”等,地方不同稱呼也不同。從圖案的產生上看,其圖案的生成經歷了大傳統流向小傳統的過程,通過不斷發展演化逐步形成了更接地氣的解釋。在五河調查過程中,潘玉真把卐字紋稱為水車紋,那么是否卐字紋與水車相似,水車又是如何在大小傳統中流動的問題值得研究。水車紋從圖像上來看確實很像水車運水的形狀,這是當地卐字紋的一個說法。水車紋放置在服飾的最中間,在五河地區更多用于圍腰、衣袖、胸襟、衣襟等位置。五河地區的服飾中通常由四個卐字紋組成一個圓形的圖案,中間用其他顏色點綴,組成一個大的卐字紋,四周有馬蹄紋、山水紋等紋樣。潘玉真介紹,圍裙上記錄著苗族遷徙歷史的過程,紋樣顯示著整個民族在遷徙之前家鄉的建筑、窗花上的紋樣,窗花上一格一格地還原當時的生活場景。卐字紋在苗族服飾中應用得相當廣泛,五河地區在圍腰上用得最多,認為卐字紋是太陽花或水生花,平兆的石柳莎則認為是拐爪紋、刺梨花等。在苗族服飾當中最為普遍的就是在前胸口用疊布繡疊起來的繡片,有兩到三個卐字紋,圍繞卐字紋往四周進行疊布,形成疊布繡的狀態。通常是胸襟和衣襟各放一塊,服飾多為左衽。訪談中詢問當地人為何放疊布繡,當地人回答放置疊布繡的主要目的是定型、方便勞作和強化裝飾美感。五河地區穿的服飾恰恰與施洞的穿著相反,通常為右衽,若是左衽則是施洞嫁過去的女子。為何五河服飾穿著為右衽呢?當地人普遍認為他們是從東方遷徙過來的,衣著右衽則表示遷徙的方位的記憶。在服飾包裹內側部分不會繡得太滿,這寓意著做事不能做得太滿,要有殘缺美。外側的衣襟則使用卐字紋的疊布繡來裝飾。由此,可以看出,服飾制作的目的是實用性、功能性、審美性與當地風俗共同構成的有機整體。
三、日月星辰紋樣中的美學形式法則與美學價值
關于十二個太陽和十二個月亮主題創作的服飾,也同樣存在大小傳統的流動關系。從服飾創作的色彩上來看,分為紅色盛裝和藍色盛裝兩種。兩套服飾創作的母題是一樣的,在創作的過程中,不同的制作者,采取不同的繡法,使得服飾呈現的風格不一,其中不同的色彩的運用,所表達的含義不同,穿著的場合也不一樣。日月紋樣的創作設計,最為常見的組合就是“鑄日造月”的故事題材。整套服飾母題由日月紋構成,內部裝飾著人娛龍、龍紋、蝴蝶紋等適合紋樣的圖案。從圖案的造型上來看,服飾圖案最多的是擬定日月紋的母題,內部填充不同的適合紋樣的題材,圖案造型夸張、變形且復雜的文化內涵。從服飾的背面來看,背后由七個基本圖形圍繞一個主圖。從構圖上來看,中間大日月母題和環繞的子母題大小形成鮮明的對比,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視覺都是平衡和完整的。從日月輪廓內部的裝飾圖案來看,每個日月母題內的裝飾圖案都不一樣,內部都有其表達的主題,減少了對其觀看視覺疲憊。從服飾的正前方來看,重裝飾看得見外側,輕裝飾看不見內側,內側和外側形成了虛實的對比。這種對比關系,與其說是當地人制作不能太滿要留有余地的制作理念,倒不如說是當地人對服飾審美功能和避免人力、物力和財力浪費的優良傳統。
卐字紋中的形式美、形式法則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這些形式發展同樣存在大小傳統的流動關系和相互影響與借鑒的關系。在五河苗族服飾中的圍腰上菱形紋樣不同的變形與組合,與九宮格的美學法則十分地相似。卐字紋不同的造型構成不同的服飾圖案,且相互之間隨機的組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據潘玉真介紹,這些苗族圍腰上的織錦圖案,反映了苗族遷徙以前家園窗花圖案的歷史記憶。因為遷徙時建筑無法搬走,為了表達對故土家園的記憶,于是就有了將窗花織在圍腰上的表現手法。而苗族認為的故土家園是中原地帶,是華夏文化的發源地,是標準的大傳統的文化,后來由于代代相傳且不斷賦予新的地域色彩。例如在疊布繡中,服飾通常由卐字紋構成的疊布繡在衣襟和胸襟前后各一塊,用以表達對故土家園中的兩扇門的歷史記憶。而服飾中間的織錦帶不僅具有豐厚的美學價值,而且也表達了特殊的歷史記憶。織帶上的一道道痕跡,表達了當地人對遷徙時橫渡黃河和長江,跨過清水江,來到方南地區的遷徙歷史的記錄。而卷邊繡中的刺繡一條條白灰色的記憶則表達了他們對故土家園中屋頂上的瓦片的特殊歷史記憶。總體而言,卐字紋所構成的疊布繡,既具有九宮格的審美特征,也有獨特圖案的造型,還有神秘色彩的元素在里面。方南苗族服飾圖案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對服飾背后文化內涵的解讀和提取其時尚元素且與現代設計有機結合,來解讀“卐字紋”背后豐厚的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價值。
小結
本文通過對苗族服飾中的太陽紋、月亮紋、八角星紋和卐字紋的研究,表明了苗族服飾中的圖案與苗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節慶禮儀、生活實踐等有關。苗族服飾中的卐字紋蘊含了“大小傳統理論”,明顯地表明大傳統流向小傳統,精英文化流向民間文化的歷史印記,并被當地人賦予了地域化的闡釋和新的文化創造。當地的社會生活、禮儀節慶和宗教信仰是相輔相成和不可分割的整體,通過對方南苗族中的卐字紋的調查研究,發現當地普遍認為卐字紋與拐棗紋之間有聯系。通過對卐字紋和拐棗紋造型的對比,發現卐字紋平面化的造型與拐棗紋的形態相似,從實用價值上來看,卐字紋與壽字紋的聯系也非常普遍。通過深入的研究,發現“卐字紋”與當地自然生長的植物聯系非常緊密,當地人通過對生產生活環境的植物與其符號象征相結合,創造性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并給予新的解釋,具有濃厚的生活化色彩。同時在其織錦的卐字紋形態當中,反織正看和數紗技藝相結合的織錦反映了苗族婦女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