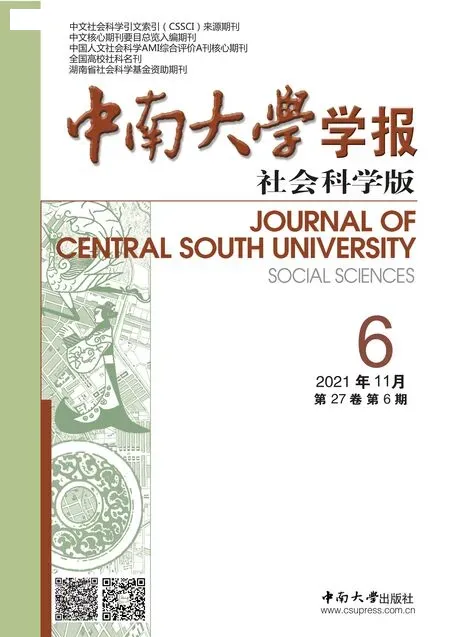晚清中國思想文化的意義重構與新文學的發生
黃健,盧姍
(浙江大學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58)
晚清以降,由中西文化沖突引發的意義危機及隨之而來的意義重構問題,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現象,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一種內源性動力。如果說在以現代化為內核的全球化浪潮中古老中國所遭遇的沖擊是空前的,那么這種沖擊不僅表現在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及經濟方式等顯性層面,也表現在價值觀念、思想意識、文化心理和精神結構等隱性層面。陳萬雄在考察“五四”新文化源流時就指出:“近代中國的改良和革命運動,在求救亡圖存的同時,其更廣的目標是在國家民族的改造,以臻中國于近代化。”[1]在傳統文化、傳統意義系統出現劇烈震蕩時,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界既批判傳統思想,又結合“國家民族的改造”目標,提出意義重構的問題。這不僅呼應了時代變革的訴求,而且成為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發生的邏輯基點。
一、意義重構的關鍵:喚醒人的“倫理覺悟”
一般來說,中國傳統的意義系統是建立在由家庭血緣倫理向社會道德倫理不斷演化的層面之上的,特別是在儒家道德倫理獲得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之后,就形成了一整套以“仁”為核心理念,以“忠、孝、禮、義、廉、恥”等為人生綱常的意義系統。這種基于家庭和社會互動的血緣親情和道德倫理層面而建構的意義系統,在相對封閉的古代社會,有效地支撐起了生活在農耕文明、農業社會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維護了人的心靈秩序和社會秩序,使人們在世俗生活中就可以獲得相關聯的道德倫理意義的充分支持。這既滿足了人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滿足了人的精神信仰的價值建構,如余英時所說:“儒學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從一個人自生至死的整個歷程,到家、國、天下的構成,都在儒學的范圍之內。”[2]在這里,他所提到的“秩序”,指的就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以儒學為主干的傳統文化在意義系統建構中,都強調要用家庭血緣倫理和社會道德倫理來維護中國人的心靈秩序和社會秩序。在余英時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價值關懷,便是要在這種秩序體系中突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天下“有道”和人生、社會“有序”的價值理念,彰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實現“天下大同”的社會目標。張德勝在《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中則進一步對“秩序”進行了詳盡的闡釋,指出形成所謂的“秩序”尤其是“社會秩序”,就是儒家道德倫理意義系統中的重要目標。他認為,“社會秩序”其實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主線,“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的文化發展,線索雖多,大抵上還是沿著‘秩序’這條主脈而鋪開。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中國文化存在著一個‘秩序情結’,……它之所以能于傳統時代脫穎而出,長時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相信這是最主要的原因”[3]。
在傳統的意義系統中,“仁”既是人的一種精神信仰,也是人在世俗生活中所遵循的血緣親情和社會道德價值的倫理法則。儒家大力宣揚“仁”的核心價值,所要求的就是“仁者愛人”,突出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親情理想。同時,賦予“仁”價值功能,包含“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和“不成功便成仁”等內涵,即要在天、地、人三者關聯的層面上,打通世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隔膜和界限,形成意義系統的“仁學”價值關懷,彰顯“不成功便成仁”的生命(人生)理想。也就是說,傳統的意義系統所建構的是以“仁”為核心理念,以“忠、孝、禮、義、廉、恥”等為人生綱常的價值體系,旨在為生活在世俗社會的人提供超驗的價值證明和意義支持。具體地說,儒家是要通過道德去教化、感化、引導人,用倫理去約束人,規范人的言行舉止,由此培育所宣揚的“浩然正氣”,獲取道德人格的確立,獲得精神的滿足和生命信仰的支持。歷史證明,在農耕文明和農業社會中,儒家建構的以“仁”為核心的意義系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運轉良好,行之有效,使人的精神世界有所寄托,日常生活有所規范,人與人交往有序,也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有效的、和諧的、穩定的秩序和管理方式,確立了相應的管理機制和制度規范。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這種建立在單一的道德倫理本體領域的意義系統,也存在著致命的弱點。換言之,單純地靠道德律令來約束和規范人的行為舉止、思想觀念和精神意識,并由此構筑意義系統,只能是在特定的、相對靜態和封閉的社會環境中才能發揮它的效應。一旦內外部的環境改變,如社會急劇的變遷演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人的內部訴求的日益增多等,這種性質的意義系統就難以再滿足人的思想多元化和精神多樣性的需求,難以給予現代人以持續性的支持,更解決不了由人性的復雜性而引發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其對于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權利、尊嚴、地位的忽視,使人無法拉開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消除不了由血緣親情倫理所帶來的復雜的人際糾葛,加上專制制度對人的壓迫,對個性的壓制,使人極容易產生奴性的性格心理,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停滯不前。研究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美籍華裔學者孫隆基對此指出,“中國文化不讓‘個體’有合法性與精神性,而只把它當作是一個‘身’,于是,由個體自己決定而不是由他人制約的‘心’就很容易變成‘私心’,而這個‘私心’仍然必須在人情的磁力場中以‘借力打力’的方式發揮作用”[4],進而嚴重影響社會機理、機體的發育與演化,影響文化的創造力和創新性發展。故晚清之后,中西文化的大碰撞、大沖突、大交匯,就使得以儒家道德倫理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意義系統受到猛烈的沖擊,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被李鴻章稱之為“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反映在思想文化層面上,便是意義系統的劇烈震蕩給現代人帶來了空前的茫然感和虛無感,如同杜亞泉所描述的那樣,它使“吾人精神界破產之情狀,蓋亦猶是。破產而后,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無所憑依,僅余此塊然之軀體,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資的生活,故除競爭權利,尋求奢侈以外,無復有生活的意義。大多數之人,其精神全埋沒于物質的生活中,不遑他顧,本無主義主張之可言”[5]。
意義的危機為現代中國重構新的意義系統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同時也為新的文化生成奠定了堅實的邏輯基礎,找到了明確的邏輯基點,確立了相應的發展理路。如同陳獨秀所指出的那樣:“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像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6]在這里,陳獨秀所說的“倫理問題”,指的就是與意義系統相關的問題,如存在境況、價值觀念、精神信仰等問題。他認為,相較“學術”與“政治”等問題而言,“倫理問題”更為重要。在他看來,只有解決了“倫理問題”,才能解決相關聯的政治、經濟及學術等其他領域的一系列問題。為此,陳獨秀致力于“批判舊道德,建立新倫理”,大力倡導新文化,主張文學革命。他指出,“舊道德”,即儒家的倫理道德,其中最匱乏的是現代人的“獨立自由意志”,結果是“使今猶在閉關時代,而無西洋獨立平等之人權說以相較”[7],嚴重地妨礙了人的發展,尤其是個人的發展,從而阻礙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在批判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當中,陳獨秀也同時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新倫理的建立,認為這是“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他描述道:“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于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從現代文明發展的角度,陳獨秀列舉了意義重構過程中將要遇到的三大矛盾沖突:一是現代文明強調要發展個人獨立人格,與傳統的要求絕對服從及其等級制度相矛盾;二是現代社會要求的男女平等,提倡婦女解放,與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之大防相矛盾;三是現代生活主張以經濟為命脈,與傳統的打擊個人擁有財產相矛盾。為此,他批評傳統的意義系統,“其所心營目注,范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于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8]。顯然,陳獨秀看到了傳統意義系統的致命缺陷,而將“倫理問題”“倫理覺悟”看作意義重構的關鍵性問題。他抓住了中國新文化發生、發展中的核心問題,為中國新文化建設和發展指出了方向。
二、意義重構的中心指向:關注人的存在價值
因為意義問題與人的存在和發展緊密關聯,特別是與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生存與發展緊密關聯,所以中國新文化對意義的重構,就勢必要以關注人的存在價值與意義作為中心指向,同時在策略上也勢必要將批判矛頭直接指向傳統倫理道德對人的壓迫,尤其對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壓迫。魯迅就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以及整個中國歷史也都只不過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9]的兩個時代間交替循環。面對這種狀況,新文化先驅者們認為,要推動中國新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就必須要開啟一條新的“人學”意義重構之路,即把“人的問題”,如人的現代化特別是人的思想現代化、觀念現代化,人和對象世界的新型關系,作為人的存在與發展,個體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個性解放,人的精神自由等,統統都要納入新的意義系統。換言之,中國新文化對意義的重構,必須要始終聚焦在“人”尤其是個體的“人”這個邏輯基點上。其主旨是要最終擺脫奴役,消除“奴性”,凸顯現代意義層面上的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如同卡西爾所闡明的那樣,人只有在創造自身的文化當中獲得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的證明,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卡西爾預言:“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可以被稱作人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語言、藝術、宗教、科學,是這一歷程中的不同階段。在所有這些階段中,人都發現并且證實了一種新的力量——建設一個人自己的世界、一個‘理想’世界的力量。”[10]
基于現代文明的價值理念,中國新文化的發起者們在這方面形成共識,都強調要把“人的問題”置于意義重構的中心。胡適就指出:“真正的哲學必須拋棄從前種種玩意兒的‘哲學家的問題’,必須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方法。”[11]他宣稱:“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們現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國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建造‘人的樂園’。我們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們要在這世界上做個活潑健全的人。我們不妄想什么四禪定六神通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有聰明智慧可以勘天縮地的人。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人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我們也許不信靈魂的不滅了,我們卻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權是神圣的。”[12]他大力倡導人的人格獨立、個性解放,推崇平等、自由的人生觀。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除了介紹易卜生的寫實主義之外,他還重點向國人介紹以發展個性和個人才能為宗旨的“易卜生主義”,并認為這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他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13]他認為,現代人權的要義首先是“自由”,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心靈的自由。他指出,現代的國民應具備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人人都有追求平等、獨立和自由的權利。他還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自由的精神價值。譬如,他就稱老子為“爭取思想自由的第一人”[14]。在另一篇文章里,他還從紛繁的歷史中梳理出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指出“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學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有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統”[15]。顯然,胡適把自由作為人的存在的首要條件,所突出的就是人的存在價值,尤其是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存在價值。陳獨秀在這方面則比胡適表現得更為激進。在談到近世文明時,他指出,“人權”和“獨立自由人格”是作為人的首要存在特點,是“人類之得以為人,不至永淪奴籍者”的重要因素[16]。他主張全面批判傳統文化,批判儒家倫理道德,否認傳統的意義系統能與現代生活相融,認為其“帶來的壞風俗有害于世道人心”,會阻礙中國社會繼續向前發展,“吾人所不滿意者,以其為不適于現代社會之倫理學說……以為文明改進之大阻力耳”[17]。他認為:“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6]他大力推崇人權,主張個性解放,注重個人的價值,認為個人的生存目的便是努力追求自身的幸福,指出:“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會上,后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18]陳獨秀將意義重構的價值主旨聚焦在“人”尤其是個人的層面上,是抓住了中國新文化生成中的核心問題的。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較胡適、陳獨秀來說,魯迅對意義重構的價值立場,則鮮明地體現了他對于現代文明、文化認識和把握的高度。他既不主張簡單的中西文化調和,也不主張全盤西化,而是以更為激進的態度,以全面批判性的“破”,來尋求全面建設性的“立”。魯迅深刻地認識到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性,指出在“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中國就再也難以見到“振拔改進”的文化發展態勢。在他看來,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的意義系統中的那一整套有關人的信仰、信念、價值觀、意義取向、終極關懷,以及文化發展機理和機制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危機。因此,他大力鼓吹“與舊習對立,更張破壞”的精神,甚至憤激地呼吁,“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他指出:“然則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于將來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質,即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者耳。”[19]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張,“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19]。通過比較中西文化,他發現西方之強“根柢在人”,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人”的意識嚴重不足,是形成循環的“奴隸時代”、奴性性格和“吃人”歷史的總根源。為此,他主張以“人”的觀念改造國民性,讓人擺脫精神的禁錮,獲得精神的解放,個性的解放,最終達到“群之大覺”,使整個“中國亦以立”[20]。從“立人”到 “人國”的建立,在魯迅的意識和觀念中,都是把意義重構的價值聚焦在解決“人的問題”上。正如他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類間應有的愛情;知道了從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惡;于是起了苦悶,張口發出這叫聲”[21]。
將意義重構聚焦在“人”的價值層面,反映在文學方面,就是直接促使了“為人生”創作觀念的確立和創作思潮的興起,而這也是中國新文學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五四”時期,周作人明確提出了“人的文學”的主張,他指出:“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22]這種直接受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的新文學觀念,針對的就是傳統的“非人”文學,矛頭對準的也是傳統的倫理道德,批判的是傳統的“三綱五常”觀念,并大力為個體的人、平民、婦女及兒童發聲。如朱自強所指出的那樣,“周作人倡導新文學,最大的動力是源自對于婦女和兒童被壓迫的深切同情,源自解放婦女和兒童的強烈愿望”[23]。周作人要求新文學能夠充分地表現“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人的地位,由此推動整個社會和文化的轉型與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新文化的發起者們的價值聚焦,首先是“人”,是個人的“人”,是個體存在的“人”。在他們看來,確立人的價值和意義,既不是彼岸高高在上的“上帝”,也不是此岸道德倫理的“仁”,而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一個個獲得生命(人生)覺悟、有著獨立自主的現代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個體存在的“人”,而這恰恰也就是意義重構的主旨所在。每一個人都應充分認識到:只有當有限的個體生命在獲得更為廣闊和無限的生命(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觀照、滿足和支持時,才會真正地獲得人自身的獨立、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如神學家麥奎利所描述的那樣:“對生存意義的探求如此普遍,以致它已成為生存本身的構成因素。”[24]可以說,中國新文化對意義的重構,就是要為現代人的有限生命提供新的價值生成的精神動力,提供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超驗證明。從哲學的維度來說,意義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觀和人生價值觀等方面的精神內容,涉及一整套有關生命理想、存在價值、人生信仰和終極關懷等相關的思想文化命題。狄爾泰指出:“人們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人們如何領悟這個世界,以及人們為了什么而努力,這些問題都應歸于一個精神結構(mental structure)。”[25]正是因為意義的價值主旨所指向的是人,隨著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它也就要在不斷的發展中“對人類所碰到的困境做出回應”[26]。如同胡塞爾所說:“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環境世界,有它的傳統,它的神和神人,它的種種神話力量,這些便構成了由每一個民族來自我驗證的實在世界。”[27]他指出,對于人的存在而言,“唯有精神是永生的”,只要“按照這樣的態度,就成功地建立起一種具有始終一貫地自身一致,并與作為精神成就的世界一致形式的絕對獨立的精神科學”[27]。
中國新文化以聚焦“人”的方式對意義進行重構,其形態則是一種全新的現代文明形態。如果說文化是一個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是每一個個體生命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它對于人,對于社會的發展,都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從意義重構的維度來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新文化的發起者們就不再是追求社會、文化的局部性改良,而是要求從意義重構的高度對傳統文化進行整體性的反省、批判和革新,謀求對傳統觀念、制度、機理、譜系、范式等進行整體性更新,以推動中國文化由傳統向現代的整體轉型和發展。
三、意義重構的重要途徑:革“死文學”為“活文學”
中國新文化運動將“人的問題”置于意義重構的中心,并以文學作為重要的傳播形式和表現方式,謀求的是最廣泛意義上推動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深入發展,以促使整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陳獨秀宣稱:“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28]從意義重構的維度來看,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受傳統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總體特點是在文學對于世界、社會和人生的反映與表現等方面,多側重于特定的道德倫理及審美領域,那么古代文學對于意義的認識和把握,也多是側重于將文學的審美功能與其他的功能(諸如政治、倫理、社會等功能)融為一體,強調的是“文以載道”,恪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古訓,以維護傳統意義系統的運作。針對古代文學的這種性質及特點,中國新文學首先就是要求打破這種“文以載道”的局面,提出要在意義重構這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思想意識層面,使文學能夠更加體現出對于人,對于個體,對于歷史、社會、現實人生所肩負的使命、責任和擔當,要求能夠更充分地展示現代中國人對建構新的生命(人生)意義的高度關注之情。
陳獨秀指出,古典文學“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而“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此等文學,作者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仿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系”[28]。基于意義重構的需要,從批判“文以載道”開始,他認為,中國新文學的生成與發展首先應以“破”字當先,即從批判舊文學開始,使新文學充當社會變革、文化轉型的“急先鋒”,進而推動新文學在觀念、范式、話語、文體和藝術表現、審美理想等各個方面完成轉換。胡適雖然較為溫和地提出“文學改良”,但他的改革理念、決心和行動則與陳獨秀一致。在致陳獨秀的信中,他指出:“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彎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矣。稍進,如南社諸人,夸而無實,濫而不精,浮夸淫瑣,幾無足稱者。”[29]他主張以“歷史的文學觀念”,創造每一個時代的新文學,要求在時代的開闊領域中,用歷史進化的發展觀念,譜寫中國文學的新篇章,展示更具活力的現代性審美價值。
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胡適首提“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主張從文學語言(即話語權)入手,將新文學語言從文言轉變為白話進行藝術表達。在他看來,這不只是文學的純技術性問題,而是要通過新文學賦予、表現和傳達新的生命(人生)意義的問題。他指出,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30]。他認為,新舊文學最大的區別,并不只是表現在形式上,而在于其焦點是否對準的是人,是不是將新的意義賦予現代人的生命內涵之中,如同海登·懷特所指出的那樣,文學盡管是一種“語言形式”,具有“敘事性”,但其真正的特點是“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對意識形態問題的‘想象的’解決”[31]。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實際上也就是指意義重構所需要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如果說古代文學不具備現代性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無法承擔新意義的賦予功能,那么中國新文學以意義重構的方式,尋求現代性的價值建構,這既是歷史必然性所驅使,也是生成新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因此,胡適主張將文言和白話置換,就不僅僅是純粹的語言置換問題,而是鮮明地蘊含著新的文化意識形態、新的價值和意義內涵的問題。因此,陳獨秀在胡適提出的“文學改良”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激烈的“文學革命”的主張,宣稱在“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28]。胡適則進一步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發問:“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32]
不難看出,陳獨秀、胡適等人大力倡導“文學改良”“文學革命”,重點是關注新文學在價值層面、意義層面上的整體轉換,期待新文學能夠在這兩個方面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一是超越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意義約束,表現現代中國人對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及精神自由的向往;二是通過文化反省與批判,賦予新文學現代性價值的意義內涵。
中國新文學在發生之際就表現出給予現代中國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等諸多領域高度關注的創作特點,展現出向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結構深處開掘的創作走向,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價值創作理念,如同嚴家炎在評價魯迅小說創作時所說的那樣,他的《吶喊》《彷徨》既是“開端”,也是“成熟”的標志。從新文學創作實踐來看,魯迅正是在洞察了傳統文化禁錮人,特別是在精神上異化人,造成國民劣根性的嚴峻事實之后,借“狂人”之口發出“從來如此,便對么?”的質疑之聲,呼吁新文學要“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33]。新文學的這種創作態勢,在“五四”時期就是創作的主流。如郁達夫的創作,就善于通過對心靈創傷的揭示,展現出國民被扭曲的性格和病態心理,反映出歷史行進中的艱難性和曲折性的特點。他的小說《沉淪》,就以“自敘傳”的方式,通過剖析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抑郁癥患者的心理,寫出了國民心理變異、性格扭曲和精神壓抑的全部過程,表現出現代中國人對個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渴望。同時,在尋求現代性價值建構中,中國新文學也非常注重現代性意義的賦予,如“五四”時期的新詩創作,就注重將追求新的人生信仰、爭取個性解放及確立新的人生價值,置于創作的中心。如郭沫若的《鳳凰涅槃》,通過鳳凰五百年集香木而自焚的寓言,抒發出覺醒的一代中國人對自由的精神向往;在《天狗》一詩中,以“我便是我呀!”的呼喊,張揚著個性解放的精神。徐志摩則以另一種浪漫抒情方式,盡情地抒發性靈,體悟人生,展示個性,追求自由,肯定自我的價值。從這個維度上來說,作為中國新文化的一種先鋒形式,中國新文學在發生之初就注重在意義重構中,展示現代中國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創作精神,體現出“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34]的發展特點。不論其內部的創作主張、創作流派、美學理想有何種區別,中國新文學整體上突破了傳統的“文以載道”的創作束縛,突破了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創作局限,始終洋溢著中國新文化的那種蓬勃朝氣及自由創造、創新的精神,充滿著轉型時期的文化反省、批判和價值探尋、意義重構的思想張力,從而拉開了與傳統文學的距離,推動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