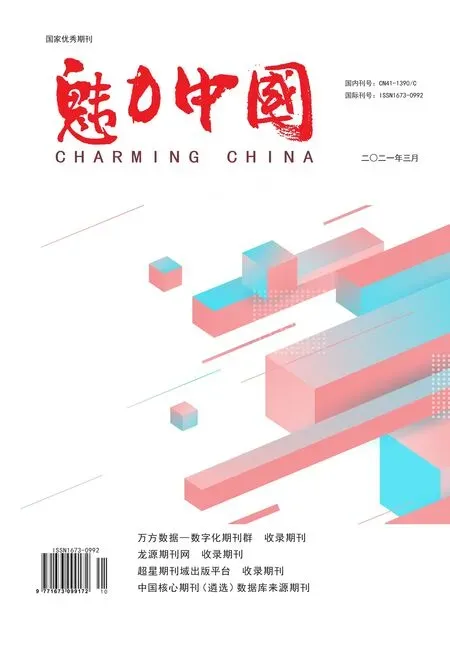探究新媒體環境下微記錄片的拍攝傳播
劉璐
(四川電影電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36)
一、微記錄片的拍攝制作
(一)微觀的個體視角
新媒體賦予每個普通人話語權。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人們已經習慣了自我表達而不愿意讓別人代言,全知視角常會讓觀眾感到疏離。因此,微紀錄片通常使用微觀的個體視角,以小窺大,并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體驗色彩。微紀錄片常以第一人稱講述,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主流媒體記者進入疫區采訪報道困難重重,因此多家媒體攜手邀請全民參與,以PGC+UGC的制作模式,制作出一批抗疫題材“日記體”微紀錄片。這些微紀錄片以第一人稱視角,集聚眾多抗疫期間中國人日常生活、工作的真實經歷,以“史詩微積分”的形式塑造出大寫的中國人群像。大部分作品關注重點不在于哪一個人,甚至哪一群人,而是平凡而偉大的普通人群體。此外文博題材微紀錄片常采用擬人化的方式,賦予文物以生命,以它們的口吻進行講述。如《故宮100》的《威猛銅獅》一集采用擬人敘事手法:“我是百獸之王,也曾叫狻猊。我是龍的兒子,也是佛的坐騎……”冰冷的銅獅被賦予生命和性格。
(二)以點敘述
經過百年發展歷史的紀錄片在時間和空間的延展上創造出無數種可能,在表現歷史與現實的不同題材中可以實現多種形式的時空組合。長紀錄片足夠的容量令其可以從容地在縱向時間軸上講故事,通過跟蹤拍攝、歷史回溯等方式在歷史變遷中完成人物塑造。而微紀錄片篇幅短小,采取的是一種與長紀錄片完全不同的敘事策略,這就是單點敘事。與長紀錄片的縱向時間軸不同,微紀錄片截取的是歷史橫斷面,講述在時間線上的某個時刻、某個個體的故事,然后在系列化的串聯中,由點成面、由點成線地形成群像,完成對歷史與現實的宏觀講述。短小靈活的單點敘事能夠拓寬紀錄片的題材領域。長紀錄片需要較大篇幅集中講述有限的內容,因此要估計到大眾的喜好,選擇的都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題材。而微紀錄片篇幅短小,每一集都自成體系,可以將觸角伸向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一些被認為是冷門的領域也可以成為微紀錄片的題材,如《傳家本事》中的“折紙藝術”。
(三)符合新媒體風格
紀錄片向新媒體風格的靠攏,不僅體現在作品時長的縮短,同時體現在剪輯和包裝風格的轉變上。在網絡綜藝剛出現的時候,其憑借新奇的包裝風格、明快的剪輯風格和花樣較多的字幕收獲了大量用戶的關注。如今,一些微紀錄片也在嘗試向網絡綜藝的風格靠近。這其中最具特色的微紀錄片作品是《早餐中國》,該作品在每集5分鐘時間里介紹一家早餐店。作品敘事簡潔,直奔主題,俏皮的花字、早餐店老板淳樸的笑容、每集片尾出現的老歌等都成為作品中鮮明的標簽。以百姓日常生活為記錄視角的《早餐中國》通過別有風格的包裝和剪輯制作,讓觀眾看到了別樣的美食紀錄片。視頻技術的迅速更迭帶來的不僅僅是影像品質的提高,而伴隨著的,還有視頻內容包裝風格的變化,在內容生產上,不僅要適應時代變化、迎合受眾審美,更要從作品的實際需要出發,找到合適的創新點,同時還應兼顧年輕用戶作為新媒體用戶的主要群體的收視喜好和習慣。因此,《早餐中國》的成功絕不僅僅是視頻制作技術的更迭,同時也是制作理念的創新,尤其在美食紀錄片創作已趨近完善、優質作品繁多的當下,這種創新和突破更顯寶貴和難得。
二、微記錄片的傳播優勢
(一)網絡平臺優勢
網絡視頻的迅速發展催生了大量視頻內容平臺,而經過一輪發展和行業洗牌,央視影音、愛奇藝、騰訊、優酷、嗶哩嗶哩等平臺成功突圍,在成功突圍之后,各個平臺都依托強大的用戶資源開始了自制內容,試圖樹立起產品壁壘,使其產品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不可替代性是視頻平臺擁有“獨播內容”的前提和條件。推廣獨播內容本意是為了鎖定用戶,然而這并不妨礙任何一個受眾個體同時成為多家視頻平臺的用戶。隨著競爭日趨激烈,多平臺給受眾帶來的是更為豐富和優質的內容。此外,新媒體視頻平臺用戶普遍使用的手機客戶端,非常方便客戶隨時隨地地收看內容,可以說,伴隨著手機等移動客戶端的不斷完善,新媒體視頻內容正在逐步占領用戶的碎片化時間。
(二)作品形態優勢
在作品形態上,微紀錄片與傳統紀錄片有所不同,最顯著的區別在于作品的時長。傳統的紀錄片每集40分鐘左右,而新媒體平臺上的微紀錄片單集普遍時長在15分鐘上下,甚至更短。微紀錄片這樣的時長設計出自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把握和對網絡用戶的收視習慣的適應;第二,如果微紀錄片的時長向新媒體短視頻貼近,則顯得時間過短,從而失去紀錄片最基本的特點和優勢。微紀錄片既能充分展現紀實影像的優勢,在時間上又符合受眾的收視預期。由此,紀錄片在新媒體平臺上重新找到了與年輕受眾之間的平衡。新媒體平臺上的一眾微紀錄片作品正以其新的形態煥發魅力,吸引著越來越多網絡用戶的關注。
三、結語
在短視頻內容競爭激烈的大背景下,作為新媒體微紀錄片的創作者,在注重內容質量的同時,還應適應時代變化,選擇用戶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創作,創作出高質量的紀錄片,并借用新媒體的傳播優勢傳播給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