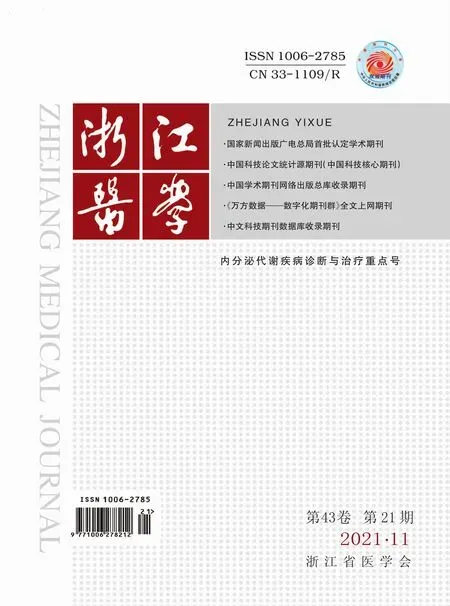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的規范化診治
鄭芬萍 李紅
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primary aldosteronism,PA)為腎上腺皮質自主分泌過量醛固酮所引發的疾病,可導致水鈉潴留,血容量增加,同時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活性受到抑制。PA患者臨床主要表現為高血壓伴/不伴低血鉀。PA從1955年首例報道至今已有66年,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醛固酮和腎素活性測定的開展以及血漿醛固酮和腎素活性比值(ARR)的推廣,PA的診斷率比1990年時提高了5~10倍。目前已認識到PA系繼發性高血壓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在高血壓患者中,PA的患病率為5%~10%,而在難治性高血壓患者中PA的患病率更高達17%~23%。近年來國內學者發現,在新發高血壓患者中PA的比例為4%~7%[1],其中72%PA患者血鉀正常。由此可見,在難治性高血壓和新診斷高血壓患者中進行PA的篩查對臨床工作有著現實指導意義。PA患者與年齡、性別、高血壓病程和血壓程度相匹配的原發高血壓患者相比,其心、腦、腎不良事件的發生率和致死率增高2~3倍。PA患者心血管風險的增加歸因于高血壓以及高醛固酮促進心臟和血管纖維化及其對靶組織的損傷作用。PA患者確診后可通過手術以及特異性的藥物治療而獲得治愈或良好控制,故PA的早期識別和規范化診治是降低PA心血管風險的根本措施,也是內分泌科、心血管科、全科和泌尿外科醫生的職責。
1 PA的病因和臨床表現
PA的診斷年齡主要在20~60歲,男女患病率相近。腎上腺醛固酮腺瘤(Coon瘤,APA)和雙側腎上腺增生(特發性醛固酮增多癥,IHA)是PA最主要的亞型,其他少見類型包括原發性腎上腺皮質增生(UAH)、家族性醛固酮增多癥(FH)、分泌醛固酮的腎上腺皮質癌和異位醛固酮分泌瘤,其中APA主要和體細胞突變有關,而FH則為胚系突變所致,見表1。高血壓是PA患者最主要的臨床表現,可表現為中到重度高血壓,且對常規降壓治療表現出“抵抗性”,而僅28%的PA患者合并低血鉀。偶爾存在血鉀低但血壓正常的PA,主要見于年輕女性(基礎血壓較低)。與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相比,PA患者心臟、腎臟等高血壓靶臟器損害更重。2018年發表的一項薈萃分析比較了來自31項研究的3 838例PA患者和9 284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的心腦血管疾病風險,結果發現PA患者與性別、年齡、高血壓病程和高血壓程度相匹配的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相比,腦卒中風險增加1.58倍、冠狀動脈疾病增加0.77倍、心房顫動增加2.52倍、心力衰竭增加1.05倍,左心室肥厚增加1.29倍;同時,PA患者的代謝異常風險也較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增高,其中新發糖尿病比例增加0.33倍、代謝綜合征增加0.53倍[2]。而針對PA腎臟損害的薈萃分析顯示,在高血壓診斷后8.5年,PA患者較原發性高血壓患者腎小球濾過率(eGFR)增加3.37 ml/min(中位數),微量白蛋白尿風險增加1.09倍,蛋白尿風險增加1.68倍[3]。一項研究系統評估了PA對患者的生活質量(QoL)和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結果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未經治療的PA(APA和IHA)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表現出身心QoL受損;與原發性高血壓患者相比,PA患者焦慮、抑郁、低落等癥狀發生的頻率更高,而腎上腺切除術可改善其生活質量和精神癥狀[4]。

表1 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病因分類、構成比和基因突變
2 PA的篩查對象和方法
2016年美國PA臨床實踐指南[5]和我國PA診斷治療的共識2020版[6]均推薦對以下PA高危人群進行篩查:(1)持續性高血壓(>150/100 mmHg)患者,使用3種常規降壓藥物治療(包括利尿劑)無法控制血壓(>140/90 mmHg)的患者,≥4種降壓藥才能控制血壓(<140/90 mmHg)的患者及新診斷的高血壓患者;(2)高血壓合并自發性或利尿劑所致的低鉀血癥患者;(3)高血壓合并腎上腺意外瘤患者;(4)早發性高血壓家族史或早發(<40歲)腦血管意外家族史的高血壓患者;(5)PA的一級親屬;(6)高血壓伴睡眠暫停綜合征患者。然而,PA的篩查和診治率卻不盡人意,一項對意大利和德國全科醫生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3 135例高血壓患者中僅7%~8%得到了篩查,甚至部分患者在發展為不可逆的慢性腎病Ⅳ~Ⅴ期后才進行PA的檢測[7]。美國內分泌學會PA臨床實踐指南制定者梅奧診所Young教授[8]指出,臨床實踐指南未能促使更多臨床醫生進行PA篩查的原因與醫生對該病的重視不夠以及過于繁瑣的篩查停藥流程有關,他強調應簡化指南的診斷流程,特別是簡化針對藥物使用的要求,并指出PA的篩查不應局限于指南重點推薦的患者類型;PA并不像其他腎上腺疾病(如庫欣綜合征)有特殊的臨床表現,低血鉀也并非診斷PA的可靠生化指標(僅9%~37%合并低鉀血癥),故建議所有高血壓患者均應進行1次關于PA的檢查;而對于初次檢查陰性的患者,在出現血壓惡化時應再次進行PA檢查。
目前國內外指南建議ARR作為PA的篩查指標。檢測方法為清晨起床后保持非臥位(坐位、站立或行走)至少2 h,靜坐5~15 min后采血測定血漿醛固酮濃度(plasma aldosterone concentration,PAC)、血漿腎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PRA,放射免疫法)或直接腎素濃度(direct renin concentration,DRC,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ARR篩查包括PAC/PRA及PAC/DRC,由于PAC、PRA和DRC檢測單位各不相同,在計算ARR時需注意不同單位間的換算見表2。以PAC(ng/dl)和PRA(ng·ml-1·h-1)為單位,最常用的 ARR 截斷值是30;以 PAC(ng/dl)和 DRC(mU/L)為單位,ARR 最常用的截斷值為3.7。近年來國內許多醫院開展了全自動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測定DRC,較之放射免疫法測定PRA,前者具有樣品處理簡單、檢測快速、穩定性和重復性好、易于標準化且不受血管緊張素原濃度的影響。國內研究顯示,以化學發光法測定的立位PAC(ng/dl)/DRC(mU/L)比值篩查 PA 的受試者 AUC為0.980,以4.3為截斷值,診斷PA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90%[9]。

表2 不同單位PAC、PRA、DRC計算的ARR常用截斷值
ARR篩查前應盡量將患者血鉀糾正至正常范圍,維持正常鈉鹽攝入。目前國內外指南仍建議停用對ARR影響較大的藥物2~4周,包括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antagonist,MRA,螺內酯、依普利酮)、保鉀利尿劑(氨苯蝶啶、阿米洛利)、排鉀利尿劑(呋塞米、氫氯噻嗪)和甘草提煉物4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和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RB)至少停用2周再檢測ARR。但如服用ACEI或ARB或MRA,其PRA仍被抑制<1.0 ng·ml-1·h-1(或DRC<參考值下限)則高度提示PA,可維持原治療方案繼續后續檢查;但如服用ACEI或ARB或MRA,PRA(或DRC)不被抑制,則應停用 2周(ACEI或 ARB)或 4~6周(MRA)再次測定。如血壓控制不佳,建議使用α-受體阻滯劑及非二氫吡啶類鈣離子拮抗劑。
ARR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醛固酮水平不高(甚至低)但腎素水平極低時,ARR有時會明顯升高,這種情況通常不符合PA診斷。故部分學者提出增加PAC>10 ng/dl或15 ng/dl作為PA的篩查界值。
3 PA的確診試驗
雖然大多數ARR篩查陽性的患者并不能診斷PA,須通過確診試驗證實有自主的醛固酮分泌才可確診,但對于合并自發性低血鉀、血漿腎素水平低于可檢測水平且PAC>20 ng/dl的患者可直接診斷為PA。確診試驗可根據情況選擇下述任一種:生理鹽水抑制試驗、卡托普利激發試驗、氟氫可的松抑制試驗和口服高鈉抑制試驗。在國內0.9%氯化鈉溶液(生理鹽水)抑制試驗和卡托普利激發試驗最常選用,而在梅奧診所則通常選擇口服高鈉抑制試驗,日本則以氟氫可的松抑制試驗為主。國內氟氫可的松藥物不易獲得,而口服高鈉抑制試驗過程繁瑣,且在我國居民普遍鹽攝入量較高的情況下是否適合以及確立何種診斷標準都是未知數,故國內極少開展這兩項試驗。
生理鹽水抑制試驗和卡托普利激發試驗對于PA的診斷價值相當。生理鹽水抑制試驗診斷PA的PAC截斷值一般采用10 ng/dl。華西醫院的回顧性研究顯示生理鹽水抑制后PAC 11.45 ng/dl診斷PA的靈敏度為88.2%,特異度為95.4%,高于國外的研究[10]。而重慶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研究則顯示生理鹽水抑制后PAC 8.0 ng/dl診斷PA的靈敏度為85%,特異度為92%[11]。而對于老年、嚴重低鉀血癥、心功能不全、血壓未控制患者則不應行該項試驗。卡托普利激發試驗相比生理鹽水抑制試驗安全性更高,操作更方便,特別適用于嚴重高血壓患者,且可在門診開展(門診取坐位)。卡托普利激發試驗確診PA的標準是服藥(25或50 mg)后PAC的抑制率<30%。近年多項研究均提出卡托普利激發試驗后具體的PAC截斷值診斷PA的價值優于PAC抑制率:日本指南推薦卡托普利試驗PAC的最佳截斷值為12 ng/dl[1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研究團隊以氟氫可的松抑制試驗為對照,提出卡托普利激發試驗后(50 mg,服藥2 h后)PAC絕對值11 ng/dl診斷PA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90%,顯著優于PAC抑制率[11]。北京協和醫院針對674例高血壓患者的研究則顯示,服用卡托普利(25 mg)后ARR>40,診斷PA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8.7%和84.8%,優于PAC抑制率[13]。目前指南中仍將卡托普利激發試驗后PAC抑制率≤30%或ARR>20作為PA診斷標準。卡托普利激發試驗中尚可關注服藥后PRA(或DRC)的上升率(PA患者 PRA或DRC上升率顯著低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
4 PA的分型診斷
PA確診后,進行亞型分類即確認病因為單側還是雙側腎上腺病變是目前臨床上的難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療方案的選擇。在PA的分型診斷中,最主要的檢查是腎上腺CT和雙側腎上腺靜脈采血(AVS)檢查。腎上腺CT檢查對于分型診斷的準確率僅為60%~70%,靈敏度為78%,特異度為75%。MRI在PA的分型診斷上并不優于CT,且價格更貴,空間分辨率低于CT。AVS的靈敏度為95%,特異度為100%,因此被認為是PA分型最可靠、最準確的方法。一項針對腎上腺CT/MRI和AVS用于PA分型診斷的薈萃分析顯示,CT與AVS的一致性為62.2%,而基于腎上腺CT/MRI結果制定的治療方案,使14.6%雙側腎上腺病變PA患者接受了單側腎上腺切除或腫瘤切除術,19.1%單側PA患者接受了MRA治療,甚至3.9%PA患者接受了非病變側腎上腺切除[14]。國內外指南均推薦PA的分型診斷首選腎上腺CT檢查,其易于操作,可排除腎上腺皮質癌;而對于診斷為PA且有手術意愿者應行AVS檢查以區分系單側或雙側病變。2014年美國發表的《雙側腎上腺靜脈采血專家共識》建議以下情況可不進行AVS檢查:(1)年齡<40歲,腎上腺CT檢查顯示單側腺瘤且對側腎上腺正常患者;(2)腎上腺手術高風險患者;(3)懷疑腎上腺皮質癌患者;(4)已證實為家族性醛固酮增多癥Ⅰ型 [即糖皮質激素可抑制醛固酮增多癥(GRA)]或Ⅲ型[15]。美國內分泌學會臨床實踐指南提出,對于年輕(年齡<35歲)PA患者合并自發性低血鉀、醛固酮大量自主分泌且腎上腺CT檢查符合單側腺瘤影像(對側正常)無需進行AVS檢測[5]。AVS系有創操作,技術要求高,費用高且有一定的輻射暴露,現階段主要在大型三甲醫院由有經驗的放射科醫師操作。
5 PA的治療和臨床轉歸
PA的治療方法取決于PA的病因和對藥物的反應,如為單側病變(單側醛固酮瘤或單側腎上腺增生),則行腹腔鏡下單側腎上腺切除術;如患者不能手術或為雙側病變(雙側腎上腺增生或腺瘤)則推薦使用MRA,建議螺內酯作為首選藥物,依普利酮作為選擇用藥;對于GRA則推薦用最小劑量的糖皮質激素終身治療。PA的治療目標不僅需要血壓、血鉀達到正常,PRA也應恢復正常。大型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單側PA術后心血管風險顯著低于原發性高血壓,而MRA治療的PA患者治療后如PRA仍被抑制,其房顫和心血管風險較原發性高血壓增加3倍,死亡風險增加63%;但MRA治療后如PRA上升則心血管風險與原發性高血壓相當[16-17]。故近年有學者提出,經MRA治療的PA患者治療目標:血壓≤140/90 mmHg,血鉀≥4.0 mmol/L,PRA或DRC正常(不被抑制),ARR<40。
PA患者術后低鉀血癥能被糾正,90%高血壓有改善,40%高血壓被治愈,其臨床結局與多種因素有關。最近,來自國際28個中心的31位專家(回顧分析了9個國家12個中心的前瞻性PA隊列)共同制定了單側PA術后隨訪及臨床、生化結局評估的國際標準(PASO標準),這為后續探討PA術后臨床結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提供了統一標準(表3)[18]。按照PASO標準,目前國際上單側PA術后生化完全緩解率達94%,但臨床完全緩解率僅為37%。年輕、女性和KCNJ5突變與PA單側術后臨床完全緩解相關,而術前服用更多的降壓藥物、合并左心室肥厚以及eGFR下降者臨床完全緩解率更低[19]。術前依靠腎上腺CT定位的PA患者術后臨床完全緩解率與AVS定位者相近(39%比37%),但生化緩解率較AVS定位者低(80%比93%)[20]。

表3 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手術結果研究的評價標準
總之,PA是最常見的內分泌性高血壓,其心血管風險遠高于原發性高血壓,是一項公共健康問題。對其患病率和危害性的再認識、早期發現、統一標準提高規范化診治水平和多學科協作能力是PA診治的關鍵所在。我國對PA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有亟需解決的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PA的篩查率且在不同人群(不同年齡、性別、使用不同高血壓藥物、不同程度高血壓靶器官累及等)中制定ARR分層截斷值;AVS系有創操作且難度大不易開展,應進一步探尋能夠替代AVS用于PA分型診斷的無創方法;MRA治療后部分PA患者無法耐受其不良反應(如男性乳房發育),且仍有較高的心血管風險,尋找特異性阻斷醛固酮合成和分泌的藥物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PA病理診斷尚無統一標準,驅動醛固酮合成和分泌的基因體系和胚系突變的發現僅僅揭示了部分PA患者的發病機制,亟待更多更深入的基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