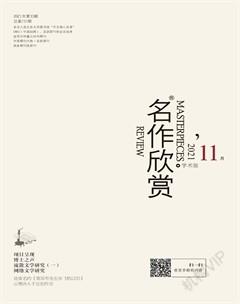跨文化劇目的創作與再現
摘 要:黃哲倫的《蝴蝶君》對所謂的“東方主義”文化的解構與詮釋,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世界”。復排版誕生后,黃哲倫做出了“世界幸運地向前推進了對性別認同和身份流動性的更廣闊的理解”的闡釋。文化間的跨越必定帶有誤讀的色彩,但跨文化本身的經驗可能是共通的。它能夠讓西方從文化層面秉持著全新的時空觀與歷史觀重新審視東方。黃哲倫的華裔身份與獨特的東方視角也通過該劇的創作與二次改編體現出來。
關鍵詞:跨文化戲劇 《蝴蝶君》 黃哲倫 東方視角
戲劇與民族語言和民族意識密切相關。在關注20世紀西方探索劇場理論的中國學者看來,跨文化戲劇是現當代西方實驗戲劇的代名詞。“從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格羅托夫斯基的‘貧困戲劇、巴爾巴的戲劇人類學實驗,到布魯克的‘普世戲劇等都統一在這桿大旗下。在此語境下,跨文化戲劇被認為是一種跨越民族文化語言的界限、超越戲劇文本束縛的戲劇,是全球化語境下的‘一種指向未來的戲劇理論。” a 1988年,美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蝴蝶君》在百老匯公演,這不僅是第一部榮獲美國托尼最佳戲劇獎、劇評人最佳新劇獎的華裔劇作家的作品,并且在當時也收獲了可觀的票房。《蝴蝶君》憑借黃哲倫作為華裔的獨特身份與創作傾向呈現出東方文化視角,也因此讓這個故事能夠在跨文化的語境與全球化的背景中更加易于傳播與被接受,更具有普遍性與永恒性。本文將從四個方面對《蝴蝶君》中體現的東方視角加以分析。
一、與《蝴蝶夫人》的互文性
《蝴蝶君》劇本的創作原型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于1905年創作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在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東方作為一個所謂的“他者”是被異化的。好像只有西方人才具有正常的人性,而東方包括它的習俗以及社會建制都是“古怪、奇異”的。如第一幕描寫喬喬桑的家人,就交代他們有著古怪的習慣,此時的音樂也追求怪異性,追求一些西方所認為的東方色彩。在描述西方人時,音樂都是正常的音調且氣魄強大。劇中反復出現的《蝴蝶夫人》的旋律與臺詞是貫穿全劇的伏筆和懸念,在演出中也呈現出神秘的東方元素,正中百老匯的軟肋。
基于此種情況創作而成的《蝴蝶君》,以伽里瑪作為敘述者,通過他的回憶和幻想展開情節。伽里瑪扮演《蝴蝶夫人》中的平克爾頓,宋麗玲扮演蝴蝶夫人,突出了人物身份與性別的錯置。在其中運用蒙太奇手法轉換時空,場景來回切換之間人物已經有了新的身份,但中間的過程并沒有被架空。登上百老匯的舞臺演出時,還運用了布萊希特的“間離”手法,讓伽里瑪與觀眾直接對話,打破了“第四堵墻”,讓兩部不同時空的劇作形成了全球化這一大環境下“附近的消失”的具象呈現。美國現代戲劇家阿瑟·米勒曾對戲劇做出如下描述:“我們之所以需要戲劇,首先是由于劇院能夠將人置放于世界的中心。我們需要一個探索的平靜點、一個大風暴的‘風眼,從風眼去認識那古老的、人類在創造自己命運的時候對上帝的挑戰。”b黃哲倫用精巧的設計打造了一出成功的百老匯戲劇,他深諳百老匯的喜好,并能夠營造出一個美輪美奐,極具東方美感的戲劇舞臺。
藝術家的創作需不需要考慮異質文化的存在,兩個具有互文性的文本是否存在理念的沖突與雜糅的嫌疑?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在對比中相對虛弱的個體才會擔心他者的入侵。”英國學者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當大多數社會經驗都只是環繞例行作息,而運轉時民族國家的認同也就退隱至意識之后成為背景,這個時候,人們對于外來文化產品的例行接觸,也就與他們消費任何其他文化商品一樣,持有相同的態度,而且也受制于相同的需要。” c
《蝴蝶君》這部劇作巧妙地與普契尼的經典歌劇《蝴蝶夫人》構成互文關系,劇中人物的角色、個性、結局全部反轉。它的英文譯名M. Butterfly的M.與中文“蝴蝶君”的“君”均暗藏玄機。創作最有力的地方還是黃哲倫希望扭轉西方人一直以來俯視東方,甚至是亞洲人的傲慢、偏見的態度。他有意識地顛覆了《蝴蝶夫人》,塑造了一個用西方傳統思維和觀念看待東方的主人公,揭示了歷史上西方早已形成的對東方已經固定的模式化的想象和認知錯位。在這種對照性與M. Butterfly的外殼之下,劇作家通過喬喬桑的故事對西方對東方社會的刻板印象進行了諷刺——伽里瑪成為這只“蝴蝶”,宋麗玲則調轉成平克爾頓,與喬喬桑和平克爾頓在不同的時空中琴瑟和鳴。
二、東西方文化的認知錯位
“從賽義德理論推演出來的后殖民戲劇理論認為,‘戲劇再現的過程本身就很可能有意無意地把一個族群的文化價值強加到另一個族群的成員頭上:一邊說要表現他們的不同特色,一邊卻在把他們漫畫化;一邊說要承認他們存在的價值,一邊卻在抹殺他們的存在。”d這個理論可以安置到許多西方劇作家創作的跨文化的文學作品或電影作品上,但它總體上過于籠統。美國有不少評論家根據這一理論而批評《蝴蝶夫人》說:“這個趨近于‘病態的亞洲女性形象完全是失真的,她是長久以來,白人為了讓處于弱勢的民族永遠逆來順受,而特意建構出來麻醉他們自己的‘政治敘事。”國內也有許多學者和作家對中國的藝術家做出批評。如張藝謀憑借他的諸多影片在國際上獲獎,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文化,正因如此,不少評論家說他自我東方化中國,刻意迎合西方評委的趣味,向他們展示了中國落后的一面。
將早期西方的一些跨文化作品并置到一起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出現的“東方面孔”始終是非理性的:東方女性被刻畫成嫵媚、放蕩、順從且頗具不同于西方文化環境的異域風情,這其中常見的元素有后宮、深閨、面紗、藝妓這一類,她們大多是具有典型的“蝴蝶夫人”式的悲情形象。西方的“東方主義”式的帶有臆想色彩的文藝作品還有很多,正是在這種文藝氛圍中,黃哲倫在《蝴蝶君》中展開了對白人男子形象的反諷:伽里瑪在法國就是徹頭徹尾的底層人,可以說是被懷疑和審視的。但是到了北京后,他的地位就瞬時被提高,形象被放大成了“人上人”。而宋麗玲的出現,適時地滿足了他潛意識中對東方神秘風情的向往,也從而激發了他在白人群體中所欠缺的陽剛之氣。
文學畫廊中有的作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被人們質疑甚至詬病,失去在彼時代的光彩;而也有一部分作品則像時代的“移民”,始終具有文化與審美的普適性,兼容于任何一個時代,甚至歷久彌新。
“一部優秀的戲劇作品應該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吸引力,而不是匆匆而過的淺薄之作。人類歷史上那些閃爍著光輝的作品都有著強大的‘穿透力,完全不受國界、語言,乃至時間的束縛。”e在全球化背景下,2017年的復排版《蝴蝶君》展現出黃哲倫對“性別和文化身份問題的全新思考”。他將大量的中國戲曲元素融入英語戲劇創作中,在解構“東方主義”的同時也構建了“中國蝴蝶”的意象——幫助宋麗玲撕下女性、陰性的標簽,完成生理與心理層面的雙重反轉。
三、戲劇主題
可以發現,在劇作設定的特殊或私人語境下的宋麗玲的行為方式,包含有愛恨交織的復雜情緒,在進入到公共語境達成普遍認知后就具有了更加廣泛的意義,表達的情感也單一化、趨同化。對于伽里瑪來說,他的自我認同感體現在對蝴蝶夫人的態度上,一旦作為“蝴蝶”的宋麗玲的真實面目被揭開,他的價值觀就被徹底顛覆了。“愛情”蒙蔽了伽里瑪所有的判斷,讓他成為一個背負著多重恥辱的罪人。“死于忠貞比活著,帶著恥辱活著要好”,伽里瑪選擇忠實于自己的愛情和價值觀念,作為“蝴蝶夫人”而死去。
“你們希望東方國家向你們的槍炮屈服,希望東方的女人屈從于你們的男人,——在你們看來,東方女性的神秘特質就是因為她們軟弱、精致、貧窮又精于藝術,具有不可思議的智慧。”“作為一個東方人,我從來不可能完全是一個男人。”f 《蝴蝶君》的靈感的確來自于《蝴蝶夫人》,但是他所傳遞的價值觀念與情感傾向與原作截然不同,也因此顛覆了原型的結局:《蝴蝶夫人》中是作為“蝴蝶”的喬喬桑自殺,而《蝴蝶君》則是美國白人伽里瑪因絕望自殺,2017年的復排版更是以更加包容的態度對待性別與身份。這些改變與他自己的身份認同感與所處的文化環境有著不可忽略的內在聯系。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象征,《蝴蝶君》中的中國戲曲元素在百老匯的舞臺上與異質文化碰撞、交流、磨合,成為華裔劇作家構建新文化身份的重要基礎。文化作為一個集合體,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是因為它脫不開經濟,脫不開政治,脫不開地理和天然環境,更脫不開跨文化的舞臺。亨廷頓在《文化的重要性》中寫道:“到了80年代,對文化這一變數的興趣開始回升。社會科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釋各國的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軍事戰略、種族和民族群體的行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和對抗。”g從古希臘到伊麗莎白時期,從啟蒙運動到“二戰”勝利以后,所有這些案例既展現了東西文化之間深刻的差異和沖突,又證明相關的各種文化一直處在不斷的發展和交流之中。
兩版《蝴蝶君》的差異正是在時代主題變化下傳達這樣一種觀念:切穿層層的文化和性別的錯誤感受,拋棄原有的刻板印象,各異的文化之間才能由對立、對抗轉為對話、交流。雖然劇作家并非有意為東方文化正名,但精準地關注到跨文化語境下的全球性問題,即個體刻板印象中對自我觀念的綁架。這不僅僅關乎同性的虐戀、東西方文化的隔閡與溝通,也體現出在美的華人對于中國的發展是持肯定態度的。
四、人物形象
“一部成功的作品必須有與某種條件和情景相融合的生動而鮮明的人物。不論這些人物屬于哪個國度、哪個民族、使用什么語言,他們一旦出現在舞臺上就無比生動。他們會引起觀眾的共鳴,使觀眾與之一同哭泣,一同歡笑,一同受熬煎。”h 《蝴蝶君》的故事原型是一個日本藝伎喬喬桑愛上了一個美國白人平克頓,出于被平克頓拋棄的痛苦與對愛情的絕望,喬喬桑最終選擇揮刀自盡。這是一個無怨無悔的東方女子和殘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的故事。
而黃哲倫解構了西方人心目中東方女子作為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顛倒了原有的東西方權力關系,調轉了原有的角色關系:伽里瑪是一名法國外交官,宋麗玲是一名來自中國的京劇演員,她與伽里瑪的相識正是源于《蝴蝶夫人》。聽完宋麗玲演唱的伽里瑪認為,宋就是他鐘情的“蝴蝶”。他們相愛,一同生活了二十余年且育有一個男孩。然而一切都是預謀。多年后,在法國的軍事法庭上,伽里瑪以叛國罪接受審判,這時的他才發現自己被欺騙:宋是一個中方間諜且是男兒身,為獲取情報才以女人的身份臥底在他身邊。伽里瑪心中的幻影破滅,最終選擇在獄中扮成蝴蝶夫人的樣子自盡。
宋麗玲充分知悉伽里瑪對東方女性的幻想:美麗、順從、樂于為愛情自我犧牲。但宋麗玲也是沉浸在這段關系之中的。因此即便在四下無人時,她也仍然身著女裝、拿著外國雜志,扮演著伽里瑪的“蝴蝶夫人”。他已然分不清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國家和情報,為了演戲,還是為了伽里瑪。在二十多年里,自命血液里流淌著高貴的、高高在上的伽里瑪,也未必一直不清醒。他始終沉溺在自己的幻覺中,深陷這個東方女性為他量身打造的夢境里無法自拔。如伽里瑪自己所言,他“愛上了一個被男人創造出來的女人”,成為法蘭西的笑話。
將兩人置于象征意向中,伽里瑪代表了西方的傲慢僵化的外交官,宋麗玲與當時的中國屬于同構關系:宋麗玲是伽里瑪想象中的“蝴蝶夫人”,中國則象征著西方想象中的“蝴蝶君”。黃哲倫嫻熟地拿捏著他已在《舞蹈與鐵路》《剛下船的人》中所展露的東方視角,打破了西方白人男子腦海中對于東方女子等同于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即使有的觀眾看不懂中國戲曲,或者聽不懂意大利歌劇,也仍然會在語意之外的心理方面獲得情感上的共鳴。這些可能帶有猜測、誤讀的共鳴,往往最能表現出跨文化戲劇的魅力:不同時空背景、不同語境下解讀的個性化。
結語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每當中國的文化發生了某種更新,基本是在與外界的交流之下產生的。黃哲倫的兩版《蝴蝶君》作為一部跨文化的戲劇作品,不僅在內容與形式上跨文化,否定了所謂強勢文化對于其他文化的態度,《蝴蝶君》的戲劇內核也體現出其獨到的東方視角,從中我們可以學到很多經驗和教訓。站在21世紀的今天,創作者擁有了比前人絕對豐富的跨文化交流的條件。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戲劇本土化過程,中國無論是在話劇、電影,還是舞劇、交響樂等諸多現代表演藝術領域,業已建立起自己的傳統,人們很少再認為它們是在迎合西方文化。因此,吸收了各種文化形式的跨文化戲劇的接受在中國已經不是太大的問題。在全球化這一新的時代環境下,我們應該秉持一個更加包容和開放的視角和態度,更加尊重他人、理解其他文化,從世界性的角度看世界,積攢足夠的藝術力量。作為美國當代戲劇舞臺上中國元素的探索者,黃哲倫把京劇元素作為文化符號,傳遞時代的精神。這種文化的交融實現了東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為跨越東西方文化界限、進行多元文化交流、文化之間的互釋與融合開辟了一條具有東方視角的道路。
a 梁燕麗: 《全球化語境下的跨文化戲劇》,《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beh張耘: 《現代西方戲劇名家名著選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第3頁,第5頁。
c 〔英〕 湯林森: 《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頁。
d 孫惠柱:《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結》,《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
f 〔美〕黃哲倫:《蝴蝶君》,張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頁。
g 亨廷頓、哈里森:《文化的重要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參考文獻
[1]孫惠柱.誰的蝴蝶夫人[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 梁燕麗.全球化語境下的跨文化戲劇[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8 (3).
[3] 亨廷頓,哈里森.文化的重要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4] 孫惠柱.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結[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6).
作 者:?王彥斐,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2018級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國文學。
編 輯: 曹曉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