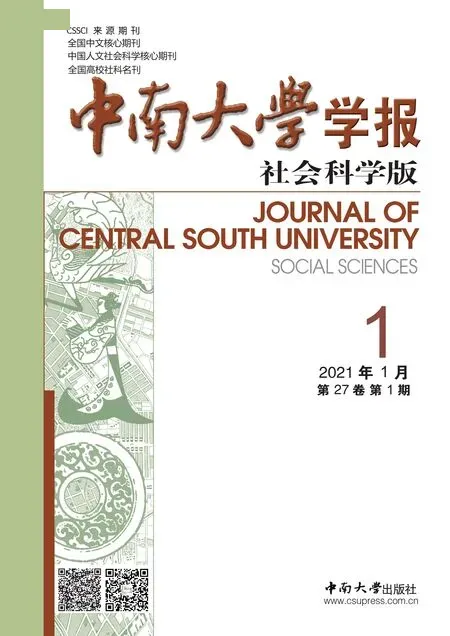“后革命”時代的社會主義想象
——韓少功的創作思想與實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58)
一、“后革命”轉型與社會主義文化重組
眾所周知,中國當代文學曾長期受到“工具論”的影響。洪子誠將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視為這一傳統的起源,并以“一體化”理論加以概括。盡管這一論斷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當代文學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理論的發明者在此后也作了重要補充,但是“一體化”理論作為一種文學史知識得到了學界認同。由此前溯,則有五四新文學的“啟蒙”主題以及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文學功利色彩。基于上述背景,改革開放奏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號角,此后第四次文代會將文學與政治關系解綁,這些對當代文學來說顯然是極為關鍵的轉折點。在反封建和現代化的時代潮流下,知識分子和民間力量形成“合力”,有效推動了觀念更新和社會轉型。
懷舊敘述往往把“新時期”描述為文學的黃金時代,激情的理想、活躍的觀念是“新時期”的思想標簽和文化記憶。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出現及其轟動效果,證明了這一時期社會蘊藏的巨大能量。但是,不少學者也注意到“新時期”內部的“革命”基因。李陀指出,新啟蒙陷入了為歷史尋找本質性原因的化約主義思維和單一因果律陷阱[1](254);陳曉明則直言20世紀80年代的“精神實質與五六十年代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2](368)。從對“傷痕”的嚴厲控訴到對“改革”的熱情召喚,我們不難看出文學界和思想界跟隨社會主流步伐,以敏銳的洞察力引發社會共鳴并構造新的時代想象的意圖。因此,“撥亂反正”主要是把“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重獲合法性的“十七年”文學傳統,以及新啟蒙提出的“回到五四”,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內涵,它內在地規約了思想解放的方向和限度。
“新時期”表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它以新的現代化想象讓革命時代的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告一段落。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尤其是1992年以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新的問題再次出現。一方面,貧富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使基于現代化想象的啟蒙共同體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趨于分裂甚至崩潰。韓少功描述道,“個人從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投入金錢的懷抱”,并批評“消費主義毒化民心,渙散民氣,使民眾成為一盤散沙,追求正義的任何群體行為都不可能”[3](19),繼而質疑當時的“世俗化”將公平正義等“社會的基本精神尺度”視為大敵,成為少數人“擴張權勢和剝奪財富的心理通行證”[4](118)。這成為啟蒙知識界立場分化的歷史見證。另一方面,新啟蒙固然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規定性和針對性,但其賴以言說的人道主義資源也為拆解自身內部的思想整體性提供了可能。“人道主義”“異化”“主體論”等命題的提出,以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入,使“去政治化”和“審美性”重回中心。文學界出現了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潮流“各領風騷三五天”的現象。毋庸諱言,文學在告別本質主義和宏大敘事、退回“文學自身”和“日常生活”的同時,未能進行有效的自我規約。如韓少功所說,“自我”成為“漠視他人、蔑視公眾的假爵位”[3](337),“表面上的自由并不意味著沒有一種隱形的控制甚至壓抑,甚至給我們一種很不自由的結果”[5](244)。在“后革命”氛圍下,文學逐漸失去了革命時代對集體和社會的關注,越發顯露出消費化、個人化可能導向的封閉、偏執和自戀。
消費社會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消解,以及個人化時代多元話語的共時爭鳴,使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美國學者德里克的“后革命”時代的意味。“后革命”本有“之后”與“反對”兩層意思[6](83),本文所指,即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語境。“后革命”以其多元化語境掙脫了“新時期”那種二元對立式的“撥亂反正”軌道,這使“革命”和“去革命”兩種話語歸為多元話語的一元,“重新理解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契機”似乎已經到來[7]。或者正如陳曉明所言,革命文化從未退出“后革命”時代,“它只是以更加辯證的方式在發生作用”[8]。“后革命”在“繼續去革命”的同時啟動了對新啟蒙的反思,某種意義上暗含了對革命的“回望”甚至“重評”傾向。
立場觀念的分化是“后革命”時代的特征之一,對社會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評價是其中的重要話題。較早表現出這一癥候的是始自1993年的關于“人文精神”的論爭。也許是因為身處改革前沿,更早感受到消費主義的泛濫和人文精神的消退,上海文化界率先拋出了“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命題,并迅速引發全國廣泛關注。此后,民族文化、“儒家資本主義”等相繼成為話題。在此類思潮的推動下,汪暉提出的“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開啟了“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一度沉寂的退到幕后的革命資源”被重新用于“對當下的批判和鞭撻”[8]。思想界的交鋒很快波及文學界。張煒、張承志積極為道德和精神張目,“現實主義沖擊波”和“底層寫作”相繼興起,證明文學直面現實的“介入”姿態與“戰斗精神”并未消亡。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韓少功逐漸形成文學“向下看”的主張。他說:“崇拜成功和成功人士,已成為當今社會主流意識。但我倒是愿意看看所謂最不成功的人,看看社會金字塔結構的最底層的人,他們的生存境遇與內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樣的。”[5](216)在發表思想性隨筆之余,韓少功所主持的《海南紀實》和《天涯》雜志都曾引發關注,后者至今仍是極具影響力的思想文化平臺。學術界的研究趨向和重要成果也表現出與上述背景的明顯關聯性。例如聲勢較大的“重返八十年代”和“再解讀”,分別對新時期文學和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的文學史敘述展開“重評”或“重讀”。它們將意識形態還原為“歷史復雜多元性”的一種存在方式[9](15),帶有清理“新啟蒙”話語并重構文學史的企圖。近年來頗受矚目的“社會主義文藝”“重估社會主義文學‘遺產’”等話題,以及興起的“詩性正義”“文學倫理”話語等,皆展現了文學領域中關于道德、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價值的歸來。這并不純粹是基于文學的內部邏輯推演,它也是全球化、現代化進程中思維觀念轉型的必然結果。
在此背景下,重返“前三十年”和重估社會主義革命“遺產”(或曰“債務”),成為面向當下的一種反饋機制。在搭建歷史與現實的“長時段”參照系,認識現實作為“漂浮的土地”的變動性和反思主體有限性的基礎上,這一反思或可超越因距離近而造成的歷史性短視和情感性遮蔽,進入更為開放和“及物”的狀態。因此,不必將共識的破裂、話語的爭鋒化約為新與舊、進步與落后的對峙,“簡單地站在某一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知識立場上,已經很難對當今世界發生的許多事情作出準確的判斷”[11](351)。面對個人化寫作盛行的當下文學生態環境,應為其他風格留有余地,避免造成新的壟斷。葛蘭西所言“非國家機構”的“文化領導權”及其對社會大眾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熏陶作用,即資本包裝下的個人化、多元化可能生成的話語霸權,仍然值得警惕。由此,社會主義革命“遺產”在娛樂消費化的“后革命”時代不失為一種補償資源。
“50 后”作家在革命年代所形成的歷史哲學以及其獨特豐富的代際經驗,是其不可忽視的文化印記。這種文化印記或隱或顯地存在于這一代的思想資源和思維方式中,是當下多元話語中的重要一元。作為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家,韓少功的創作思想和藝術實踐尤其具有代表性。發表于新時期初期的《西望茅草地》等一系列作品對知青運動的評價頗顯躊躇;《爸爸爸》對民族本土性的挖掘和《歸去來》對知青記憶的不斷重返,在1985年“現代派”備受矚目的文學場域中令人側目;20世紀90年代的思想性隨筆和《馬橋詞典》更引起了極大關注,展現出文學與思想的深層互動。近年來,其理論隨筆《革命后記》直接聚焦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困境,其小說《日夜書》和《修改過程》著眼于對知青一代進行整體性反思,尤其是革命時代與“后革命”時代的敘事對比,這些都不難使讀者看出作者重溫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道德理想,以填補市場經濟時代的人情冷漠之意圖。作為對個人化話語的補充,韓少功對人民性和文學正義等社會主義資源的接受和想象,在當下無疑具有思想整合的意義。
二、社會主義資源的接受及其藝術實踐
當下文壇,韓少功的觀察視角和價值傾向具有明顯的異質性。不談他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中的獨特態度,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對社會公正和道德理想的執著關注,但說他對“尋根文學”的倡議,便在沉浸于西方化和現代化想象中的20世紀80年代獨樹一幟。在置身時代主流思潮之余,韓少功自覺保留獨立的思想和言說空間,有人將其視為“當代保持先鋒姿態最為持久的作家”[12]。在肯定韓少功的文體探索之余,筆者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韓少功創新原動力背后的廣闊視野。
(一)回望傳統:對接現實的整體性視角
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市場主義現代化的審視,是韓少功一貫的思想立足點。作為革命時代和市場時代的親歷者,轉型前后的對比為韓少功提供了思維方式的整體性和開放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對某些歷史問題和現實認識的極端化傾向。
對歷史和未來的責任感是“50 后”作家群體的某種代際特征,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長在紅旗下的這代人所接受的“人民史觀”的旺盛生命力。韓少功曾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參與主流話語的生產[5](22),也曾加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時代主潮宣泄“不平之鳴”,隨之卻轉向民族文化深處尋找“改革由治標到治本”所需的文化啟蒙資源。他說:“對淺薄的政治疏遠,正是從更深層關心現實的一種成熟。”[5](73)從政治反思深入文化反思,固然基于藝術審美和思想深度的追求,但也證明了全球化時代韓少功對本土文化問題的敏銳。韓少功憶及“尋根”倡議之初的污名化,一面被指責為“回到封建主義”,一面被認為是“對抗全球現代化的螳臂當車”[13]。如今看來,“尋根”較早敏銳地感覺到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失衡,以及中國應以何種文化姿態進入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問題。這一論題在不久后出現的文化熱、國學熱中得到了接續。體現在文學創作中,《爸爸爸》被認為繼承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主題,未老先衰、愚昧麻木卻極具生命力的侏儒丙崽,是韓少功“尋根”的代表性成果。研究者一早便察覺到丙崽在韓少功思想譜系中出現的必然性,“尋根”既是對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深化,也是作為知青的韓少功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反思。但是《爸爸爸》還有另一個重要主題,即反思現代性。小說以大團圓的和諧結局,預示對人的原生態的生命狀態而言,“任何希望改變和改造并且強行使之符合某種主觀意識的企圖,最后都將歸于失敗”[14](362)。韓少功的現代性反思與其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是一體兩面的。《戰俘》《西望茅草地》《飛過藍天》等發表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已顯示了對簡單否定歷史而實質上規避反思這一做法的質疑。上述作品塑造了國民黨軍官趙漢笙、農場場長張種田和知青麻雀等復雜形象,在當時遍布政治控訴和情緒宣泄的文學場域中,這些早產兒雖沒有獲得如謝惠敏、王曉華等時代代言人一樣的身份,但保留了主旋律之外的現場聲音。對悲劇英雄和革命理想的同情,對知青群體人性陰暗面的體認,或許僅僅源于歷史現場的不成體系的直觀感受,但無疑表露出韓少功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所建構的簡單化、道德化的歷史敘事的潛在質疑。
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和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情,加之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警惕,使韓少功與“新左派”達成了某種共識,甚至被“派定一頂有點別扭的帽子”[5](158)。然而,與其說這是基于觀點立場的共識,不如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共通。標簽化的認識與解讀所造成的“虛假的對立”往往“遮蔽現實的復雜性,并且讓參與者在對立的情緒中流失對復雜現實本應具有的探索能力”[15]。對“后革命”時代的觀察促使韓少功重新回顧革命時代的合理性因素。1981年的《風吹嗩吶聲》已經察覺金錢主義與政治專制在導致人性異化方面的異質同構性。幾乎與此同時的《飛過藍天》和《遠方的樹》也顯示了他對改革時代道德問題的隱隱擔憂和重審人性的意圖。事實上,韓少功對現代化的凝視始終沒有離開知青記憶的標尺,而這一標尺的內涵又緊緊地與農村(或曰本土道德體系)、社會主義集體道德和理想情懷相結合。《歸去來》《余燼》《山上的聲音》等不斷講述“知青返鄉”的故事,《暗示》的魯少爺、《日夜書》的郭又軍、《修改過程》的毛小武等改革時代失落者的悲劇命運,是韓少功對主流知青敘事和改革敘事的一種“修改”。知青田家駒逃離了農村,但“即便他以后能跑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他的魂魄還可能在這里遺失,在這里沉睡”[16](304)。或許韓少功的隨筆更能表明其立場,“金錢也能生成一種專制主義,決不會比政治專制主義寬厚和溫柔”[3](308-309)。在這一意義上,他認為知識界至今未能完成清理社會主義革命“遺產”的任務,這使當前社會仍延續著其反思對象的內在邏輯,留下“一筆巨額欠賬”[17]。
韓少功觀點與立場的傾向性,實質上也是其思維方式和觀察視角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的表現。他對“主義”和“立場”框限的越位,使不少學者從中發現了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跡象。吳亮曾述及閱讀韓少功時感到的“背反的價值猶疑”和“深刻而紊亂”的理性[18](336);南帆同樣得出韓少功“缺少一種正面的強烈之感”,他所肯定的“遠不如他的否定對象明晰”[19]。這一傾向性也體現在對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話語的質疑。對抗主導話語時的“中立”往往表現為對弱勢方的同情。薩義德關于知識分子邊緣性、獨立性和批判性的論述在此仍具解釋力。整體而言,韓少功的立場與觀點呈現變動性,但對象的分析應置于時代語境的參照系中。時代語境的變遷造成價值標準的挪移,對作家的定位隨之發生改變。《西望茅草地》因涉及老干部的形象問題,幾經周折才得以發表[20](482);“尋根”也曾遭遇“左右夾擊”;而在“人文精神”論爭中,韓少功同張煒、張承志一并被稱為“文壇三劍客”。作家的事后追述澄清了固化思維所造成的“誤讀”,贊成“人文精神”并不意味坐視其成為可能“帶來某種串通糾合和黨同伐異”[3](102)的標語口號。韓少功對絕對價值和神圣理念的懷疑,恐怕與“文革”結束后“懷疑一切”的虛無主義思潮和知青的被拋棄感不無關聯。這種生命痛感使作家在觀察、探索歷史規律時不忘投以向內的人性觀照,也讓他的“理想”“崇高”多了幾分對人性的理解和寬容。
韓少功的思維方式表現出鮮明的縱深感與開放性。他試圖“將‘過去’作為‘潛能’來閱讀”,“使之向新的歷史經驗與歷史條件開放”[21](430),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就現實言現實、就歷史論歷史的狹隘與封閉,獲得了一種整體的多維視角。他在全球化時代強調本土特殊性,在個人化時代重提集體理想和公正理想。中國五千年的“大傳統”和社會主義“新傳統”,共同構成了觀照當下的重要資源。
(二)重提人民性:主體反思與觀念調適
作為一劑現代化良方,“啟蒙”曾點燃了“新時期”的極大熱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它所許諾的“好社會”并未伴隨市場化降臨。新矛盾的積聚很快導致知識界的分化和重組。新世紀初,“人民性”話語再次“升溫”。在紛繁復雜的思想場域中,我們既能看見話語間的碰撞和沖突,也能捕捉到某種奇異的交織與合力。韓少功似乎站在人民性與啟蒙的話語交匯處,他既質疑全球化和市場化這一“他者”,又對本土“自我”持有清醒的批判意識。這種富有意味的“越位”顯示其兼具保守性和超越性的背反特征。
下鄉插隊和返城的經歷,以及2000年后往返城鄉之間的生活方式,使韓少功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韓少功對農村生活的描寫雖不諱言鄙陋,卻往往給人親切適意之感;城市生活雖物質豐裕卻難掩人情涼薄,反倒是底層的道德情義常常令人感動。韓少功的寫作姿態呈現階段性:其傷痕文學代表作《月蘭》同情極左時期民眾的苦難生活,當屬“為民請命”的激憤之作;而《爸爸爸》的丙崽形象、《北門口預言》中縣官王文彬的冤死,則接續國民性批判傳統,展開對文化根性的溯源和反思。上述階段可簡略歸入知識分子書寫的范疇。但是,我們仍可從中窺見其對民間力量的敬畏,例如《爸爸爸》中仲裁縫等人義無反顧的赴死和雞頭寨人的集體遠行,這種強烈的儀式感顯然蘊含了某種來自遠古的悲壯難言的生命力。《馬橋詞典》通過清理抽象語言背后的豐富歷史和生命具象,幾乎是韓少功對理想鄉村生態和健康人性的重建。以村民萬玉、志煌為例,他們對現代知識一竅不通,透著一股現代人難以理解的“寶氣”,但恰恰是“寶氣”中流露的倔強信念令人感動。萬玉玩世不恭,卻對“覺覺歌”有一種“藝術殉道者的勁頭”,情愿放棄逛縣城、放棄工分遭受處罰也不愿接受“關于鋤頭的藝術”[22](56);志煌與一頭叫作“三毛”的牛之間有著驚人的默契,小說中志煌和“三毛”犁地的場景幾乎把勞動演繹成了藝術。在這種民風民俗背后,韓少功發現了一種“直接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原生智慧”[4](27)。中國人擁有一套自足的知識結構、認識范式和價值體系,“法治”“效率”等“現代”“普世價值”與植根于傳統的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某種天然的隔閡,由地域和歷史所塑造的獨特空間對觀念、價值的橫移提出了質疑。韓少功對鄉土生態及其價值體系的探索興趣,在此后的《山南水北》《趕馬的老三》《怒目金剛》等作品中得到持續演繹,出現了一批像何大萬、吳玉和這樣秉持獨特價值信仰和處事方式的人物形象。而《報告政府》中的囚犯黎國強等人和獄警車管教、馮管教組成的城市底層生態,尤其是黎國強那種既狠辣又因不曾體會過關懷而對善意缺乏抵抗力的形象,不免讓人重新打量道德和人性。韓少功的人民性表現為對鄉村生態、城市底層及其價值體系的理解、接納、包容和同情。面對缺乏批判性的質疑,他回應道:“只是在談到這些缺點時盡量避免某些都市人的一種缺點。”即“冷漠與無知,還有建立在這種冷漠與無知基礎上的歧視”[5](202)。
人民性與啟蒙兩種話語在其創作中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但總體上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任何單維概括都可能遮蔽韓少功思想的復雜性。“新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要的轉型節點,韓少功在轉型前后通過分享人民性和啟蒙兩種時代話語,接受了二者對這一代人思想資源的調整。“人民性”固然沾染了階級色彩,而“啟蒙”在話語轉型之際也未必完全擺脫了上述邏輯。作為兩種帶有某種專制意味的剛性話語,其內化為作家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必然會經歷一番磨合與創化。一方面,韓少功的特殊性在于,出身于城市的他在某種意義上是在鄉村找到了心靈的棲居地。帶有自傳色彩的《鞋癖》講述了父親自殺、因出身成分而遭受歧視的精神創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尋根”“返鄉”敘事的反復以及對鄉村和人民性的歸屬和追尋。另一方面,偏離現代化許諾的荒誕現實激化了時代話語與個人記憶之間的矛盾,潛藏于“茅草地”的困惑趨于明晰①,社會主義教育和“再教育”所塑造的價值觀日漸復蘇。當韓少功在1986年說“一個民族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的質量”“中國知識分子質量上有毛病”[23]時,這種啟蒙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已經表征了立場的位移。上述感慨也與韓少功同年所批評的“不負任何責任的自由”[3](5)有關。韓少功主張文學應正視本土經驗和周邊現實,把對自我的理解納入個體與群體的相互關系中,避免封閉的知識繁殖和冷漠的理論復制,從而“喚醒消費社會、權力社會中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喚醒他們內心中的人道主義同情,喚醒他們作為社會的精英所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24]。在這里,人民性成為對趨于偏至的啟蒙精英的補正。韓少功對社會主義資源的重審與發言,可被視作基于“前三十年”革命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市場化轉型,再到20世紀90年代深化改革這一歷史鏈條上的個性化整合,也是這一眾聲喧嘩的轉型期必然出現的一種聲音。
由此可以理解,韓少功并不把人民性推向“神化人民”的極端,正如他對“啟蒙”和啟蒙主體的反思是建立在人民性和啟蒙兩者構成的互動參照系中一樣。在他那里,“崇拜”是對主體獨立性及其批判精神的貶抑機制,它與生俱來的非理性特質往往導致獨裁和集權。因此,同情與共情意義上的尊重和接受在用來表述韓少功的“人民性”概念時顯得更加貼切,啟蒙因此而不失溫情與敬意。基于對上述兩種思想的共同指向及其可融通的探尋,韓少功為個人化時代出現的種種問題提供了可能的解決方案和實踐路徑。
(三)文學正義:道德堅守及其限度
人民性成為韓少功調整啟蒙立場的重要資源。如果說二者的交織互動,是其思維方式和立場觀點呈現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內在原因,那么對“文學正義”的信仰以及對道德有限性的認知,則是看似對峙的兩種思想資源得以互補并存的深層底蘊。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向內轉”“回到文學自身”等口號支持著“跟著感覺”越走越遠的文學異化為“自戀游戲”,也助推了文學的技術主義傾向。與此同時,文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的邊緣化成為學界的關注點。有人認為:“文學影響力式微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源于文學主體精神的退卻和失落。”[25]確實,僅從時代轉型角度解釋文學的邊緣化未免過于簡單,它應是文學與社會雙向疏離的結果。“躲避崇高”引發的“人文精神”論爭,從道德層面對正在發生的變化做出了及時回應。在此期間,韓少功的隨筆掀起了“庸常年代的思想風暴”。這一立場并未因“人文精神”論爭的平息而轉向。讀者不難在《馬橋詞典》《暗示》《山南水北》《日夜書》等作品中發現文體實驗背后強烈的言說訴求,其中對公正與效率、群體與個體、道德與欲望、城鄉差距與階層分化等話題的反復探討,表明韓少功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狀況的持續關注及其所持觀點的延續性。
但問題在于,“正義”不會真正退場,而“道德”的作用也有其限度,否則就難以解釋何以烏托邦往往在“落地”后迅速幻滅。早在1995年,“人文精神”的討論者就意識到糾纏于道德爭論無益于問題的解決[26](274)。本質上,文學正義是“社會正義的轉喻性代償物”[25],并不產生直接效用。有鑒于此,韓少功對“道德”及其限度的警醒就格外值得關注。正如拒絕將人民性推向“民眾崇拜”一樣,韓少功也警惕道德可能導向的專制。《日夜書》中的馬濤就是滿口“崇高”卻逼得妹妹馬楠為其傾家蕩產、出賣尊嚴來攫取更多利益的人。《馬橋詞典》也早已出現了鹽午對鹽早關于“孝道”的指導和指責,可笑的是,“讀書人說完就走了。他每次回來都是這樣,吃一頓飯,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當然,他盡可能留下一點錢。他有錢”[22](144)。因此,相比于觀念之爭,更讓韓少功入迷的是“人性指紋”[5](264)。豐富的人生經歷為韓少功提供了測量人性的多重視點②。在韓少功的作品中,諸如張種田般以人性“軟化”階級性的嘗試,知青老木的精神逆變,何大萬等集狡慧刁蠻和樸實善良于一身的形象,皆為例證。面對現實人性,非但人民性及啟蒙立場顯得單薄,道德同樣形跡可疑。基于此,韓少功認同道德無法挑戰“世俗利益的硬道理”,并揭露了“道德進化論”的盲目,主張退回人性視角重審被視為偶然事件的歷史災難。他贊同道德“分級制”,即在強調堅守道德的同時,反對“把少數人的責任強加給大眾”,因為后者無異于新一輪的“造神運動”。在他看來,“革命的第二天”中的“亦圣亦魔”的復雜人性和利益理性,早已宣告了“六億神州盡舜堯”僅是一廂情愿的烏托邦想象,而這一教訓至今仍未得到足夠清醒的認識[16]。
韓少功的人性探索之所以既鮮活又帶有相當的異質性和沖擊力,與他的實踐體悟因果相承。《回聲》描寫的隱匿于革命背后的宗族斗爭陰霾、《飛過藍天》中知青返城暴露的利益傾軋,或是最初的痛點。《暗示》中的老木對紅歌樂此不疲、《馬橋詞典》中的鹽午非要在馬橋建個“天安門”,這批改革時代的“成功人士”曾深受“成分”之累,但其意識深處已銘刻了集體道德和紅色信仰的印記,時而抵抗著市場時代的冷漠和虛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時半刻,也往往是記憶中最柔軟的一角”[17]。在如此精微的觀察下,韓少功觸摸了觀念和理論背后具體的生命體驗,更深刻地揣摩了人性。
與此相對應,其文學的理想主義立場也有所回撤。韓少功以“改造社會”的嚴肅態度邁入文學之門,而后承認了文學功能的有限性,即文學“不一定能改造社會,至少不可能把社會改造成文學所指向的完美”[4](293)。“真正現實主義者對理想的態度,是既不夸張也不放棄”[27]。韓少功既反對擱置利益的理想化敘事,也不認同利益決定論的認識基點和行為模式。當“經濟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啟蒙主義假設帶來心靈的無依,面對個體與群體的割裂和責任與使命的棄置,文學可以并且應當提供神性的滋養,個人化的信奉者也置身于現實的群體社會中。這使韓少功在反思道德有限性時,能自始至終地堅持對文學正義的信仰。
三、“元話語”的個性闡釋與轉換路徑
出于特殊的情感記憶和獨特的思維方式,韓少功在“新時期”啟蒙主潮中較早表現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異質性反思。“后革命”時代的語境置換提供了歷史重評的契機,在多元話語并置共存的當下,社會主義“元話語”再度成為闡釋對象。通過對革命時代與市場經濟時代的整體性書寫,韓少功試圖剝離情緒化和對立化,對這一“元話語”進行個性闡釋與接受,重新發掘人民性、集體性和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道德價值,成為韓少功創作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對“元話語”作出個性闡釋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有效的文學轉換。理性思考賦予韓少功強大的思想穿透力和明確的態度。但是,文學有與理性對話的獨特表達方式。黑格爾將人的認識能力劃分為感性、知性、理性三個階段。作家的天然優勢可能在于對外部世界的敏銳感知。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于文學對接生活,拓寬對社會的觀照面。盡管對感性經驗的理性認識是凝練、提升作品內涵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更合理的呈現方式仍是將思想內化于形象。馬克思的“抽象—具體”認識理論富于啟發性。在此意義上,形象既是創作的出發點,也是思想的著陸點。
被稱為“思想型作家”的韓少功從來不缺獨特的見解,甚至“困擾韓少功的并不是想法太少而是太多,敘事法則所能容許的范圍能否容納得下它們,甚至如何接納它們都是個問題”[28]。理性觀念的形象轉換問題,不但讓圍繞韓少功的評價出現了巨大的分歧,也長期困擾著他本人。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韓少功便意識到“思想性往往破壞藝術性,文學形象有時也不足以表達這些思想性”,然而“關心理論已成嗜好,抽象剖析已成習慣”[29](267)。文學是人學,形象的塑造是評價作品的一個重要維度。思想性作為韓少功的優勢和樂趣固然賦予其作品深度,但也一定程度上帶來觀念化、符號化的問題。有批評說:“《爸爸爸》《女女女》的概念化傾向非常嚴重,簡直與‘十七年’的某些小說無異。”[5](279)丙崽的寓言化和象征手法預示了作家平衡形象與觀念的乏力。而《日夜書》將“二流子”、發明家和愛國者三重身份置于賀亦民一身,這一針對讀者閱讀習慣和思維慣性設置的大膽調試,因強烈的理性沖動不免損傷了形象的圓融性,似乎缺乏融合三種身份的支點。另一個問題便在于“典型”與“群像”的矛盾。從《馬橋詞典》中的村民到《日夜書》《修改過程》中的知青,韓少功一如既往地表現出對群像塑造的興趣。這種注重宏觀性的文學創作范式,可能與作家對歷史進行整體性的還原、反思的企圖有關。以前者為例,“馬橋”形成了圓整的鄉土生態和風俗人情;見多識廣、頗具威望的村支部書記馬本義因“暈街”不惜舍棄前程也要返鄉,“成分”不佳、寡言少語的鹽早默默承受不公,竟熬成了啞巴并練就了一身百毒不侵的本事。在這里,馬橋人的固執倔強反倒凸顯了生命的韌性硬度,成為他們的共同根性和文化印記。很難說上述形象缺乏深度或是不夠鮮活,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對群體共性的呈示削弱了個體塑造的力度。這當然不是說塑造“典型”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充分條件,畢竟《馬橋詞典》就開始了打破“主線霸權”的文體探索。但缺乏足夠分量的人物形象,應該說是韓少功長篇小說的一個缺憾。有評論認為,韓少功試圖突破“某種知識觀念的控制下而漸漸形成的‘固體’狀態”,以恢復個體與其存在語境的“充滿活力的自然的聯系”[30]。新觀點的提出和論證勢必對作品的豐富性和開放性提出要求,也解釋了“打碎與重組”成為韓少功文體創新顯著特征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韓少功曾說:“想得清楚的寫散文,想不清楚的寫小說。”[31](149)但總體而言,其散文和小說的互文性較為明晰。歷史重評和當下發言仍是韓少功小說的基本內涵。韓少功的文體實驗固然有其形式探索的意圖,同時也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不懈嘗試。引入現代派的寓言、象征手法接通觀念和形象,時常成為擱置問題的捷徑。散文化通過挑戰“主線霸權”,開拓了文本的思想空間,卻也容易引發小說文體邊界的爭議。聚焦人性書寫不失為有效途徑,但韓少功的言說欲望常常使作家超出敘述者身份。散文化的松散結構或是觀念化“硬塊”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了針對個性化思想如何進行有效的文學轉換這一命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問題的存在固然對文學審美造成一定損害,但遠離思想并沒有帶來感覺的鮮活豐富,反而使文學趨于麻木、貧乏和淺薄[4](289)。隨著個人化寫作的極端化發展,文學沉浸于自我空間的獨語和賞玩,漸漸遺失了介入社會的勇氣。在思想貧瘠愈加凸顯的當下,韓少功的思想探索和藝術實踐別具價值。一方面,思想探索及其某種超前性,本身便給作家尋找現實原型提出挑戰;另一方面,生活雖然提供對象和靈感,但作家必須超越對感性直觀的模仿、調動概括和想象能力對素材進行打碎重組。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是文學不同于紀實報道的重要特征。外界信息的提取以及由此而生的主觀想象是作家轉換視角、開拓思維的一把鑰匙,文學由此指向過去、現實和未來,承擔對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多維探尋,擁有獨特視角和新的發現。在文學生產過程中,作家又勢必對其思想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這使其創作思想某種程度上“大于”思想資源。因此,某種意義上文史哲合一的“雜文學觀”“大文學觀”相較于“純文學”,更契合文學的本質。文學無須也無法保持純粹或明晰,并自然生成新的含混性和多義性。或許這正是韓少功所謂“想不清楚的寫小說”的文學意味。韓少功以其豐富的生命體悟,為社會主義“元話語”提供了諸如新啟蒙的人道主義、人性等豐富意蘊。這些“加減乘除”使文學富有“彈性”,也構成其獨特的魅力。
文學如何容納思想這一命題,是以韓少功為代表的作家群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問題的存在不應成為文學放棄思考、懸置思想的理由。畢竟,是否思考與如何容納思想是不同層面的問題。進入新時代,我國文化供給的主要矛盾從“缺不缺、夠不夠”轉向“好不好、精不精”。韓少功的意義,即在為泛物質化、泛娛樂化的“小時代”提供一種追求思想深度和堅守理想溫情的文學流脈。也正是在思想貧弱、價值失據的當下,對社會主義“元話語”的想象與召喚,重新被賦予一種新的前沿性。這或許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注釋:
①韓少功在《西望茅草地》末尾寫道:“過去的一切都該笑嗎?茅草地只配用幾聲輕薄的哄笑來埋葬?”參見韓少功:《同志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頁。
②例如六年的知青實踐、《海南紀實》的利益糾紛、《天涯》的左右之爭、新世紀二次下鄉,都成為韓少功的豐富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