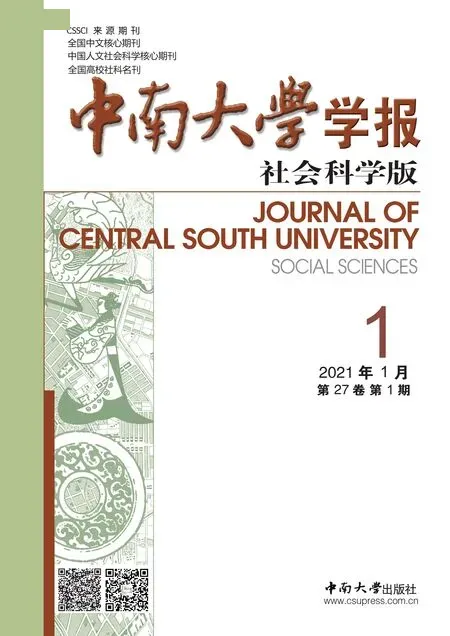《全明詞》所收明太祖、建文帝詞辨偽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28)
明清時的詞選、詞話、方志與筆記中所載的明初君臣所作的詞作,往往出自偽托。如清人徐釚《詞苑叢談》卷八所收劉基《沁園春》(生天地間)、《明詞綜》卷一所收鐵鉉《浣溪沙》(晚出閑庭看海棠),均已有人作過辨偽①。而《全明詞》第一冊所收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的詞作各一首,分別出自方志及詞話,也是疑點重重。現試作辨偽。
一、明太祖《折桂令》辨偽
《全明詞》第一冊收錄明太祖朱元璋“闕調名”詞一首:“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煙寺迂迂,云林郁郁,風竹姍姍。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偷閑,花鳥娛情,山水相看。”[1](112-113)經查《詞譜》,此首實為《折桂令》。
此首《折桂令》,編者輯自《金壇縣志》卷二,但未附上相應的版本信息。查閱《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等可知[2](342-343),現存《金壇縣志》共四種,分別修于康熙、乾隆、光緒和民國時期。經核查,此詞在上述幾種縣志中均有記載,現錄《(康熙)金壇縣志》卷一“山川”:
顧龍山,在縣治南五里。前望白龍蕩,故名。一名烏龍山,俗呼為土山。平湖澄碧,遠山環秀,上有敕建圓通庵、大圣塔、五顯靈官廟、季子廟、關帝廟、修真觀。左有茅山書院舊基,山地周回一百四十畝。歲丁酉十一月,明太祖東征,嘗駐蹕于此,題樂府一闋于寺壁,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煙寺迂迂,云林郁郁,風竹珊珊。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偷閑,花鳥娛情,山水相看。”今勒碑建御亭于其上(知縣劉美書)。洪武中有傅敬者,初授金壇尹,陛辭,上諭之曰:“金壇有橫山一座,朕曾臨幸。”即此山也。御書、僧舍在今圓通庵。[3](99-100)
后續修的幾種縣志所記與此大致相同。除以上四種縣志外,據《(康熙)金壇縣志》卷首所收錄的分別由王守仁、劉美撰寫的《金壇縣志序》可知[3](31-37),明代正德、萬歷年間金壇縣均修纂有縣志,惜兩種書今已不見。《全明詞》第一冊從《金壇縣志》卷二收錄此詞,經核對卷次,編者應是輯自民國十五年修撰的《金壇縣志》。又從《(乾隆)鎮江府志》卷首所收錄的前志序文內容可知[4](19-20),明代曾在永樂、成化、正德、萬歷年間分別修纂了府志,惜前三種已佚,僅存《(萬歷)鎮江府志》。清代則有康熙、乾隆所修的兩種。現存的三種府志中均有明太祖題樂府于顧龍山寺壁的記載,所記文字俱同,可知后兩種是沿襲了《(萬歷)鎮江府志》而來。今錄《(萬歷)鎮江府志》卷三“山川下”的文字如下:
顧龍山,在縣南五里。前望白龍蕩,故名。一名烏龍山,俗呼土山。山上有圓通庵、大圣塔、五顯靈官廟、季子廟、漢壽亭侯祠、修真觀。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東征,嘗駐蹕焉,題樂府于寺壁,云:“望西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命詞臣續之,曰:“煙寺迂迂,云林郁郁,風竹珊珊。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偷閑,花鳥娛情,山水相看。”今勒碑亭中(知縣劉美書)。有傅敬者,初授金壇令,陛辭太祖,諭之曰:“金壇有橫山一座,朕曾臨幸。”即此山也。[5](539)
將《(康熙)金壇縣志》與《(萬歷)鎮江府志》的相關記載相對照,有同有異。所同者,兩種方志皆謂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東征時曾登臨金壇縣治南五里之顧龍山,并題樂府于寺壁;所異者,《(康熙)金壇縣志》謂整首詞為明太祖所作,而《(萬歷)鎮江府志》則謂明太祖僅作了開頭數句,后面大部分為詞臣所續。所錄詞作也有個別異文,首句《金壇縣志》作“望東南”,《鎮江府志》作“望西南”。
又明人鄧伯羔《藝彀》卷中有“顧龍山樂府”詞條,其文云:
邑有顧龍山,山有御制樂府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此下《縣志》直謂高皇帝自為之,《府志》《南畿志》謂詞臣續之。此以詞臣續之為是,“他日偷閑,花鳥娛情,山水相看”,大哉皇言,曷宜有此。[6](26)
鄧伯羔,《(康熙)金壇縣志》卷十二有傳,“鄧伯羔,字孺孝,少即謝去諸生,隱天湖之銅馬池,博學洽聞,撰著甚富。郡守王公應麟聘修《鎮江府志》,捃摭獨詳。柯御史督學南中,召為記室,不就,巡撫某以行修學博聞于朝,亦不赴。日徜徉釣雪亭,綜述文史,乘興往來兩浙,與諸名流唱和。上下古今,筆無停涉,有《臥游集》四卷藏于家,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已行世”[7](312-313)。小傳中所提及的郡守王應麟,字仁卿,福建龍溪人,萬歷二十一年(1593)知鎮江府,任間聘諸名士修府志,府志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付梓,即我們現在所見的《(萬歷)鎮江府志》。又湯賓尹有詩《寄壽鄧山人》追懷鄧氏,詩曰:“每恨生較晚,不及與同朝。……崛起嘉隆間,身存道獨韜。”[8](444-445)據以上材料可知,鄧伯羔主要生活于嘉靖至萬歷年間。其在《藝彀》言“《縣志》直謂髙皇帝自為之”,此縣志當指現已失傳的《(正德)金壇縣志》或《(萬歷)金壇縣志》。則至遲在正德至萬歷年間,已有明太祖登顧龍山并御作樂府的記載;《府志》或指鄧伯羔所參與纂修的《(萬歷)鎮江府志》,或指萬歷以前所作的府志,而《南畿志》當指聞人銓、陳沂所纂,刻于嘉靖十三年的《(嘉靖)南畿志》。
《(嘉靖)南畿志》卷二十四:“顧龍山,在縣南五里。前望白龍蕩,故名。又名烏龍山。高皇東征,嘗駐蹕,題樂府于寺壁,命詞臣續之,今建御亭于上。”[9](413)此志已經認為現在所見的《折桂令》樂府之開頭為明太祖御制,而后面部分為詞臣所續。而鄧伯羔贊成這一說法,并且進一步從詞作內容上進行論證,認為“他日偷閑,花鳥娛情,山水相看”這樣的表述,不是皇帝所說的話。看來,在明代嘉靖至萬歷年間,認為朱元璋曾經登臨顧龍山,并作樂府開頭,詞臣續成的觀點,已經成為主流觀點。
《折桂令》一詞,除以上幾種記載外,由于早期的幾種明代所修纂的《金壇縣志》《鎮江府志》的亡佚,我們已經無法更詳細地考知是否還有更早的文獻來源,但從現在我們所掌握的這些材料來看,此詞很可能是假托之作,與朱元璋及詞臣并無關系。
首先,幾種方志中所記載的明太祖登臨顧龍山及題寫樂府的時間與史實不合。無論是記明太祖獨創的《金壇縣志》還是記君臣合作的《鎮江府志》,一致認為此詞作于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東征駐蹕于金壇顧龍山時。丁酉十一年即元至正十七年(1357),該年十一月朱元璋未嘗東征,亦未取道金壇。據《明太祖實錄》卷四記載,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占集慶(今江蘇南京),改應天府,同年四月“乙丑克金壇縣”,至此,金壇縣納入朱元璋轄內。《明太祖實錄》也未記錄至正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朱元璋集團的軍事活動,但記載有同年十月的戰事:
冬十月辛未朔。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已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禽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眾敗走,得糧九千余石。薄暮,敵復以戰,船百余艘來,逆戰,復大敗之。甲申,上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鑒以其眾降。……至是,大亨攻之,明鑒等不支,乃出降,得其眾數萬,戰馬二千余匹,報至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余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10](57-58)
上文中的“壬申”即十月初二,“甲申”即十月十四日,“大通江”在銅陵縣境內。十月十四日朱元璋于銅陵大通江閱兵,從地理方位看,銅陵、池州在應天府西北方位,并不需要經過遠在東南面的金壇。從“上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可知,朱元璋并未親臨揚州戰役現場,況且自池州出發進軍揚州,也無須經過金壇。
方志記載的東征戰事,在翌年即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之間實有發生。據《明太祖實錄》卷六:
十一月乙未朔……甲子,上以樞密院判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
十二月乙丑朔,命籍戶口。庚午,遣主簿蔡元剛往東陽招長槍元帥謝國璽,不從。其部將何同僉陰遣其屬龔敬赍書,以所部兵來降。庚辰,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引兵道蘭溪,壬午至婺。……甲申,上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10](70-72)
以上引文中的甲子即十一月三十日,庚辰即十二月十六日,壬午即十二月十八日,甲申即十二月二十日。那么是否方志混淆了年份,將1358年11月朱元璋親征誤記成1357年11月呢?根據朱元璋南下進軍的線路,也排除了這個可能。朱元璋率軍十萬親征婺州,自應天經宣城南下,經徽州、德興、蘭溪,依此行軍路線,根本無須經過東面的金壇。何況戰事危急,朱元璋率領十萬大軍,更不可能行南轅北轍之事。為防疏漏,筆者一并查閱了《昭代典則》《國榷》《明史紀事本末》等各類史書和今人所撰《朱元璋系年要錄》《朱元璋傳》《洪武大帝朱元璋傳》諸書,但均未能找到與方志記載內容相合的事件,故方志記載丁酉年十一月朱元璋東征駐蹕金壇顧龍山并題詞之事很可能是虛構的,歷史上并無此事。
相關縣志、府志“顧龍山”詞條下記洪武中傅敬授金壇知縣,陛辭時明太祖謂“金壇有橫山一座,朕曾臨幸”。明太祖是否到過金壇,是何時及什么情況下去的,囿于文獻失征,現在已經無法考知了。即使明太祖到過金壇,他所說的“有橫山一座”,這座橫山是否就是顧龍山,也大有疑問。而且“臨幸”與“駐蹕”也不完全相同,“臨幸”即曾經到過,“駐蹕”則是暫住下來的意思。目前所見的《鎮江府志》《金壇縣志》也沒有說明明太祖所說的“有橫山一座”,為何就是顧龍山。又考傅敬其人,史料記載甚少,方志中有寥寥數語,《(康熙)金壇縣志》卷七《職官志》“明知縣”:“傅敬,江西新喻人,洪武中任。”[3](568)《(萬歷)鎮江府志》卷十六記載相同[5](694)。明太祖是否對傅敬說過那番話,其史料來源及其真偽也已無從考究。
另有《大明一統志》《廣輿記》二書認為朱元璋駐蹕顧龍山的時間為洪武初。《大明一統志》卷十一云:“御亭:在顧龍山。洪武初,車駕駐蹕于此,有寶床及御題樂府碑、萬歲碑焉。”[11](269)陸應陽《廣輿記》卷三云:“御亭:顧龍山。洪武初,車駕駐蹕于此,有御題樂府碑。”[12](111)二書的材料來源已無從考知,筆者查閱《明實錄》在內的上述諸書,沒有記載入明后朱元璋到過金壇,該說亦不可靠。我們現在所見的《大明一統志》系萬歷年間所刻,已增入隆慶、嘉靖至萬歷年間的內容,而陸應陽也是嘉靖至萬歷年間的人,這兩部書中所記顧龍山有御題樂府碑,可知成書于御碑興建之后。
其次,御碑當為明太祖作樂府的傳說出現并流傳之后,萬歷年間金壇知縣劉美所建。《(康熙)金壇縣志》卷一“山川志”謂“御書、僧舍在今圓通庵”,該志卷十“寺觀”謂:
敕賜圓通庵,在顧龍山,舊名新興院。梁大同間僧妙高創造。元延祐間重修,有四佛殿、大悲殿,宋元間畫筆尚存彌勒殿塔。明太祖東征,嘗駐蹕于此,賜名圓通庵,其御亭三間,正統十四年二月僧道穎奉旨重修。僧道穎疏稱:“切思本庵原系太祖高皇帝駐蹕處,所有御床、御亭見在供奉。臣先于正統十二年二月內奉請本庵名額,已蒙敕賜圓通庵外,今臣又思得本庵御亭三間,年深朽壞,欲將自己衣缽收買木料,重新修蓋。緣系御亭,未敢擅便,伏望圣恩憐憫,敕部允臣修蓋完固,朝夕焚修,祝延圣壽,永圖補報。便益謹具奏聞。”奉圣旨:“準他修蓋,工部知道。”[7](148-149)
據上文所述,以太祖駐蹕為由,新興院于正統十二年(1447)得賜圓通庵名,因庵中御亭年久失修,僧道穎上疏重修,疏中提太祖駐蹕而未言題詞之事,述庵中情況時,列御床、御亭,但并沒有提到題詞寺壁和御碑。由是觀之,在正統年間,顧龍山有御亭但無御碑,太祖顧龍山駐蹕的故事雛形已經出現,但似乎還沒有衍生為太祖駐蹕并題詞的完整傳說。
刻有傳為明太祖所作的《折桂令》詞的御碑當為萬歷年間所建。從《(萬歷)鎮江府志》卷三“顧龍山”詞條“今勒碑亭中(知縣劉美書)”、《(康熙)金壇縣志》卷一“顧龍山”詞條“今勒碑建御亭于其上(知縣劉美書)”等記載可知,御碑為金壇知縣劉美所建。《(康熙)金壇縣志》卷七“明知縣”條目下有言:“劉美,萬歷四年由洋縣任。”[3](570)可知御碑修建于萬歷四年(1576)后。除建置御碑外,為自圓其說,劉美在顧龍山一帶建造了相關的建筑,并以“龍”“蛟”這些象征帝王的文字命名,與高祖駐蹕題詞傳說桴鼓相應。《(康熙)金壇縣志》卷二“津梁”:“見龍橋,在顧龍山南,俗名九里橋,明萬歷八年知縣劉美建,自為記,今圮。”“騰蛟橋,在見龍橋西,明萬歷八年知縣劉美建,有記,今圮。”[3](188)
依上文《(嘉靖)南畿志》《藝彀》二書所敘,至遲在正德至嘉靖年間,已有明太祖駐蹕顧龍山并題樂府的記載。相較而言,御碑修建時間很晚,御碑的建造應該與知縣劉美好大喜功的個性相關。劉美喜立碑撰文,據《(光緒)金壇縣志》卷十五“碑碣”記載,劉美在任期內俢撰了縣志碑、題名碑和義成廣澤二閘碑[13](1248)。另據《(康熙)金壇縣志》卷十記載,劉美還重修了縣東的龍興庵并撰碑[3](151)。
最后,從詞作內容本身分析,《折桂令》作偽嫌疑很大。從整首詞中可以看出,詞作者歆羨僧舍生活明凈無染,山水之間悠閑淡然,萌生隱居消遣之意,希冀棲身于廟宇山林。觀照朱元璋的生平經歷,他是不大可能創作出這首詞的。朱元璋出生于貧困農民家庭,幼時為地主放牛,十七歲入皇覺寺為僧,是年僧舍乏食,只得托缽流浪,乞食四方,后又返寺。朱元璋出家是為求生計溫飽,絕非追尋詞中所述“塵不染”“花鳥娛情,山水相看”的超然境界。況且丁酉年十一月東征期間,朱元璋秉鉞于身,統率萬軍,不大可能去懷念過去的苦難生活,更遑論題壁示眾。與此同時,當時朱元璋周遭強敵如林,出征途中亦不應有隱退閑居的心境與表述。倘若如《府志》和《南畿志》所言,該部分為詞臣所續,作為朱元璋屬下,不應不知道其有多年出家經歷,續作部分兩處提及“煙寺”“僧舍”,下闋有功成身退,回歸山中廟宇之意,文字僭越,也不合情理。
除以上的方志等記載外,明代有關朱元璋駐蹕金壇顧龍山并創作樂府的故事,另有一個版本。據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言:“金壇城外顧龍山,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于此,今有御制詞刻石碑。”[14](4)
李詡,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卒于萬歷二十三年(1593),字厚德,自號戒庵老人,南直隸江陰人(今江蘇屬縣)。一生坎坷不遇,七試均落第,后淡于仕進,居家讀書著述自娛。《戒庵老人漫筆》是李詡晚年的筆記,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由李詡孫李如一初刻。該書記錄相關的典章制度、遺聞軼事,兼及學術辨析,內容蕪雜,可信度低。《四庫全書總目》謂該書“其間多志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敘次煩猥,短于持擇,于凡諧謔鄙俗之事,兼收并載,乃流于小說家言”[15](1105)。《戒庵老人漫筆》今有魏連科的點校整理本,魏氏在篇前《點校說明》直言“有些荒誕不經的異聞,也必一一載入,這些糟粕成為本書之累”[14]。盡管《戒庵老人漫筆》內容真假混雜,難補史書之未備,但該書是唯一記載明太祖征伐對象的文獻,我們仍然需要進行覆按。
《戒庵老人漫筆》記載甚為簡略,片言只語中唯一有用的信息是“于高五郎作亂”。從稱謂上看,“于高五郎”應是其別稱而非真名,僅憑《戒庵老人漫筆》的寥寥數語,筆者在各類史書中按圖索驥,皆未能找到相對應的人物,所幸最終還是在《(康熙)金壇縣志》中發現了線索。《(康熙)金壇縣志》卷一“兵事”:“丁酉年,太祖東征,駐蹕顧龍山時,縣南有余皋五者,拳勇好斗。太祖率□親征至顧龍山,勒兵□□掩至林中燒殺之。”[3](88)比對《戒庵老人漫筆》《(康熙)金壇縣志》二書,“于高五”與“余皋五”音同,可以判定《戒庵老人漫筆》中的“于高五郎”即是《(康熙)金壇縣志》中的“余皋五”。時間與方志記載吻合,俱是丁酉年東征,太祖東征事件在前文已證偽。同時,二書在敘事的邏輯關系上相抵牾,依《戒庵老人漫筆》所敘,于高五郎作亂是太祖東征的原因;而在《縣志》中,剿滅余皋五只是太祖東征途中為民除害的小插曲。在史書和其他文獻中,筆者依舊未能找到“余皋五”的蹤跡。退一步講,若確如《戒庵老人漫筆》所言,明太祖東征“余皋五”或“于高五”,史書中怎會沒有任何記載?且太祖為金壇縣內一個“拳勇好斗”的地痞流氓而親自東征,顯然不合常理,故《戒庵老人漫筆》乃偽說無疑。
通過對上述材料的梳理辨析,我們可以推測,在李詡生活的嘉靖、隆慶、萬歷年間,朱元璋駐蹕題詞的傳說可能已經衍生為多個版本。李詡為南直隸常州府江陰人,常州府與鎮江府相鄰,金壇、江陰兩縣雖未接壤,但相距不遠。李如一在《戒庵老人漫筆》的序中稱李詡“晚乃紀歲月陰晴、里闬人事”“上搜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14],明太祖顧龍山題詞事應屬于“里闬人事”“鄉邑之闕聞”之類。書中的“于高五”與縣志中“余皋五”音同,應是口耳相傳所致。《戒庵老人漫筆》所收的明太祖事,是由東征于高五郎與顧龍山題詞兩個故事雜糅而成,屬于民間流傳的故事版本之一。
另,將故事發生地設在顧龍山,可能與“顧龍”之名有關。其實,“顧龍山”的名稱并不是依據明太祖駐蹕的傳說而來的,早在南宋就有顧龍山的記載。《(嘉定)鎮江志》卷六《地理志》記載:“顧龍山,在金壇縣五里,俗呼土山。下瞰思湖、龍蕩,高不能五六丈,而巨石盤亙,瞰平湖數千頃,湖之旁山者,居民占植芙蕖,界以菰蒲,如錯錦繡。暑風至則荷香,與偕若非凡境。”[16](418)又《(萬歷)鎮江府志》《(康熙)金壇縣志》等書謂顧龍山取名來自“前望白龍蕩,故名”,此山因“下瞰思湖、龍蕩”“前望白龍蕩”而得名,而后人可能望文生義,引申為見龍之意,附會出明太祖曾駐蹕于此的傳說。
綜上所述,《全明詞》所收的《折桂令》詞乃假托朱元璋所作。太祖因東征而駐蹕顧龍山并題詞是層累地造成的民間傳說:先是明太祖可能對即將赴任金壇知縣的傅敬說過自己曾經臨幸過金壇一橫山,后來好事者因為“顧龍山”的山名附會出太祖所臨幸的橫山即是此山,并有了駐蹕于此的傳說。到了正統年間,和尚據此重修寺院并建御亭。在這之后又附會出太祖駐蹕于此并題樂府于寺壁的傳說。到了萬歷年間金壇知縣又建造了御碑亭,而當地的志書不僅將太祖駐蹕于顧龍山當作信史載入志書,而且將該樂府收錄其中,或謂太祖御制或謂君臣合作。而后世修撰的志書則陳陳相因,明人筆記也以訛傳訛,而《全明詞》未加辨析,導致錯收。
二、建文帝《滿江紅》辨偽
《全明詞》第一冊收錄建文帝朱允炆《滿江紅》一首[1](231),詞曰:“三過吳江,又添得、一亭清絕。□占斷、水光多處,巧依林樾。漠漠云煙春晝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壺、玉鑒暑宜風,寒宜雪。曜庵右,山嵐缺。虹橋左,波濤截。正三高堂畔,舊規今別。何□漁翁垂釣好,漫將柳子新吟揭。信登臨、佳興屬彭宣,能揮發。”并注輯自《蓮子居詞話》。此詞本為宋代無名氏所作,而歸入建文帝名下,當肇始于清人褚人獲纂輯的筆記小說《堅瓠集》。該書補集卷二首篇《建文帝詩詞》云:
建文帝首至吳江史仲彬家,題詩《清遠軒》云:“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破曉風。詩就云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畫鹢高飛江水漲,老漁亟唱夕陽斜。秋來客子興歸思,船到吳江即是家。”又三至吳江,題《滿江紅》詞云:“三過吳江,又添得、一亭清絕。剛占斷、水光多處,巧依林樾。漠漠云煙春晝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壺、玉鑒暑宜風,寒宜雪。臞庵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濤截。正三高堂畔,舊規今別。何但漁翁垂釣好,謾將柳子新吟揭。信登臨、佳興屬彭宣,能揮發。”又《觀競渡》詞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初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斗巧盡輸年少,玉腕彩紗雙結。艤彩舫,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望水中天日暮,猶是珠簾高揭。歸棹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17](24-25)
《堅瓠集》多取歷代逸聞軼事,兼及詩詞文章,失實處甚多。記建文故事者,有《半邊月》《建文云游》《水月觀》《遜國詩紀》等,內容怪誕不經,取材自明以來的各種野言稗史。如《堅瓠集》丙集卷一《半邊月》篇載:“建文帝初生,頂顱頗偏高,高皇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每慮其不克終,或以詩對試之。一夕,與懿文同侍高皇側,命詠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云頭。雖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云:‘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龍不敢吞。’高皇覽之不悅。未幾,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應其語。”[17](589)此事亦見于明人黃瑜《雙槐歲鈔》卷二[18](35-36)、陳師《禪寄筆談》卷二[19](603)、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卷十九[20](380-381)、呂毖《明朝小史》卷三等處[21](499)。《詠新月詩》實為元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所作,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一》引葉子奇《草木子》為之辨偽[22](370)。胡丹在《“神奇其說”:建文傳說的神秘性探析》一文中也對偏顱之說和《詠新月詩》進行了證偽[23]。
《建文帝詩詞》所載建文帝出亡諸事始見于《致身錄》。此書于萬歷后期流傳于吳中,托名史仲彬所著,在承襲先前建文傳奇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講述自身得建文帝慧眼賞識,靖難時助其水關出亡,后建文帝三過吳江等事。現引《致身錄》建文帝首至吳江片段于下:
彬曰:“大家勢盛,耳目眾多,況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筆者注:師即建文帝)于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將何所之,眾議浦江。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載者,有一艇來焉,聞聲為吾鄉,急叩之,則彬家所遺以偵彬吉兇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為程、為葉、為楊、為牛、為馮、為宋,余俱走散,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之西偏,曰“清遠軒”,眾出拜,師亦大適。[24](5)
后兩至吳江部分,筆者憚煩不引。《建文帝詩詞》載詩、詞各二首,其中《清遠軒》一詩,取名應源自上文《致身錄》中的居所名“清遠軒”。《致身錄》來歷可疑,情節怪誕,問世以來屢遭辨偽,諸多學者進行了文獻翔實的考證,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云:
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 又賡和篇什,徜徉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為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期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25](9)
對此書考辨最有力者當屬錢謙益。錢氏作《〈致身錄〉考》,分析吳寬為史仲彬所作墓表等材料,列十條“必無”證據,判定《致身錄》為后人偽造[26](755-758)。錢氏十論,理據皎然,《致身錄》之偽庶幾定讞,其后潘檉章、潘耒等學者在此基礎上繼續考證,筆者不再一一詳說。《致身錄》既偽,《堅瓠集》中的《建文帝詩詞》以《致身錄》為背景,亦應是偽造而成。
現從《(弘治)吳江志》卷十九、卷二十二“集詩”中發現了《建文帝詩詞》所載二詩、二詞,俱標為無名氏所作。經核對,《(弘治)吳江志》卷十九收錄的七言絕句《適吳江》(二首)即為《建文帝詩詞》中的《清遠軒》(二首)[27](443),卷二十二收錄的失調名二詞《釣雪亭》《吳江觀競渡》則為《建文帝詩詞》中的《滿江紅》《觀競渡》[27](597-598)。比對二書,除題目不同外,內容亦稍有刪改。《(弘治)吳江志》中《釣雪亭》詞上片首句為“三過松江”,下片第六句為“舊觀新別”,而《建文帝詩詞》則是“三過吳江”“舊規新別”。又如《適吳江》(其二)末句為“船到松陵即是家”,《建文帝詩詞》改為“船到吳興即是家”,顯系迎合建文出亡故事背景而有意篡改。現經查證,《適吳江》(玉蟾飛入水晶宮)為南宋蘇庠所作,《全宋詩》卷一二八八據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十四收錄[28](14605)。另一首《適吳江》(畫鹢高飛江水漲)未見于其他文獻。在《(弘治)吳江志》卷十九中,二首《適吳江》系于同一無名氏名下,前者為蘇庠所作,《適吳江》(畫鹢高飛江水漲)也當判為蘇庠佚作。《吳江觀競渡》一詞即為北宋黃裳詞作《喜遷鶯·端午泛湖》,見于黃裳《演山集》卷三十一[29](209),《全宋詞》第一冊收錄[30](378)。而《釣雪亭》,即《全明詞》收錄的建文帝《滿江紅》詞,現無法找到其他文獻來源,《(弘治)吳江志》卷二十二該詞之前有言“此后俱宋人”,故僅知此詞為宋代無名氏所作。綜上所論,《堅瓢集》補集卷二首篇《建文帝詩詞》所載建文帝詩詞四首均為宋人所作,《建文帝詩詞》或摘錄自《(弘治)吳江志》,或出自同一來源。
《堅瓢集》誤收在先,后人詞集相繼因襲。清人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十六選建文帝《滿江紅》詞,于詞末標注《堅瓠集》[31](2089)。清人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八摘錄此詞,詞后疑其真偽,作者注云:“余謂老還大內,死葬西山之說,斷不足信。若《致身》《從亡》等錄,與《堅瓠》所載詩詞,咸具不忍死其君之心,疑以存疑可耳。”[32](2675-2676)而清人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三著錄此詞[33](2642),未標明出處,《全明詞》據此收錄,未考鏡源流,以致錯收。
三、結語
《全明詞》收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詞各一首,經過對文獻材料的發掘、稽考、釋證,二詞皆系偽作的事實彰明較著,因此筆者在重編《全明詞》時,將二詞剔除不錄。
據《全明詞》記載,這兩首詞分別輯錄自清代以后的《金壇縣志》與《蓮子居詞話》。推而廣之,在從事文獻輯佚和采錄工作時,當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與追本溯源的方法。就明代而言,對于湯顯祖、李贄這類著名文學家和朱元璋、朱允炆這類帶有傳奇色彩的帝王,被后人偽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②,因此,在文獻整理出版如火如荼、古籍數字化蔚為大觀的今日,采錄佚作時更要謹慎。
注釋:
①劉基詞辨偽見周明初《劉基佚詞四首小考》,原載《劉基文化論叢》第2 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今已收入《明清文學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61—364頁;吳留營《有關劉伯溫的詩詞考述二則》,載《文獻》2018年第5 期;而鐵鉉之詞實為五代李珣所作,清人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九已經指出,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734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頁;王兆鵬進一步指出此詞已見于《花間集》卷十,見王兆鵬點校《明詞綜》,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
②關于明清文獻輯佚與整理時材料采錄的可靠性問題,筆者在《〈湯顯祖集全編·詩文續補遺〉辨偽》一文中已指出。(《文獻》2017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