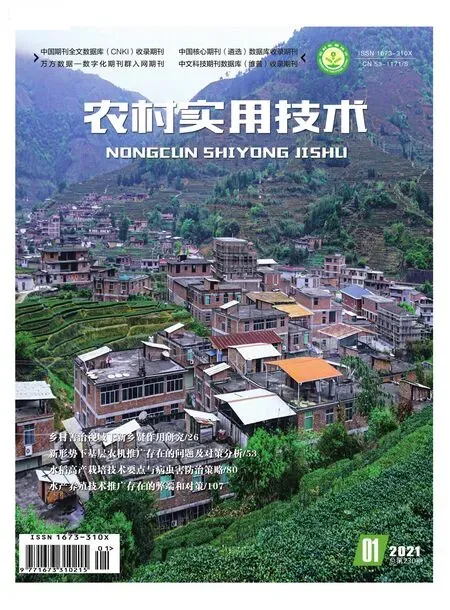中國古代鄉村自治的弱化趨勢及其邏輯
周志遠,周志華
(1.江西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市 330022;2.青海師范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8)
鄉村自治自古以來就是統治者無法漠視的用以鞏固政權的重要一環。幾千年以來,鄉村自治的模式經歷了多次變遷,但大可分為三個階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鄉村自治有著不同的特點。筆者認為,隨著中央集權不斷強化,其在總體上呈現出逐漸弱化的趨勢,并最終喪失了應有的自治功能。分析中國古代鄉村自治的弱化趨勢及其邏輯,正確地認識鄉村共同體,對進一步探索我國當下村民自治具有重要意義。
1 中國古代鄉村自治的主要模式及其自治性
1.1 第一階段:鄉官制模式
鄉官制作為鄉里制度最早的形態萌生于先秦時期,初有鄉、遂之分。直至西周時期,族群不斷發展,出現了“國”“野”之分,鄉里社會也自此有所界定。到了春秋時期,什伍制趨向成熟,鄉野之間的元老權威逐漸凸顯。秦漢時期則是封建君主專制下鄉官制建立和發展的鼎盛時期,出現了“縣——鄉——里”三級行政系統。
這一階段的鄉村自治,雖形式有所不同,但組織原則相似。特別是在后期,鄉和里的作用比較突出,鄉村社會基本處于半自治狀態。
1.2 第二階段
鄉里制度到保甲制、鄉官制到職役制的模式轉變。隋代鄉官制向職役制轉變,鄉官轉為強制性差役,鄉的功能弱化,里和村的地位上升。鄉制在唐代名存實亡,而作為鄉的下一級管理組織的負責人——里正,則成為了鄉里組織的真正領導者。同時期,“村”正式以國家法令的形式成為了鄉里組織的一級單位。北宋前期仍實行鄉里制,鄉、里的規模較前代更大。
該階段是鄉里制度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鄉和里的地位逐漸淪落,官方的控制與統治逐漸增強,相應地,鄉、里的自治功能逐漸弱化,鄉村權力上調州縣。
1.3 第三階段:職役制
北宋中期,階級矛盾尖銳,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王安石推行變法,實行保甲制度,嚴格甄選職官并劃定責任,自此,鄉里制真正轉變為職役制,國家公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元代在改進鄉里自治的同時,設置了村社組織,此舉增加了自漢以后減弱的自治色彩。明朝南北方鄉里自治各有特色,從里甲制再到保甲制,鄉約與保甲制結合,民眾受社會控制程度更高。清代鄉里制度并無實質性創新,鄉里組織受民眾重視的程度一落千丈。統治者雖在清末民初尋求鄉村自治的新突破,但終因失敗收場。
此階段的鄉村自治夾雜著公權力的滲透和民間的自我發展,但鄉村自我發展的力量難抵不斷強化的封建專制,地方鄉里的色彩仍呈現出弱化趨勢。
2 自治功能弱化的趨勢
2.1 自治組織的獨立性喪失
發展數千年的鄉村自治,以鄉里制度和保甲制為主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國家公權力不斷向基層社會滲透,使得鄉村自治組織逐漸變為國家政權的工具。作為自治地方的管理組織,應對自治地方的財權、事權有所掌握,但伴隨著鄉官制完成了向職役制的轉變,再加上鄉、里權力的上移,自治組織的獨立性逐漸喪失。國家公權而不是民眾掌握了自治過程,這使地方自治呈現出政治化色彩。
清末以來的鄉村自治亦然。“蓋所謂地方自治之機關,本為民眾集合之所,以謀本身之福利,而結果乃純變為下級行政機關,負傳達公文及征發之任,于其本身應負之責任,反覺渺不相涉”。便是時人對南京國民政府有關鄉村自治的評價。原本地方自治的權威,因被法律賦予法人的資格而高高架起,可實際上并無任何處理地方財、權問題的權力。可見,自治組織的獨立性喪失,使得地方自治完全被公權控制或主導。
2.2 自治領袖的變化
我國自古便是一個十分強調宗法的國家,推選地方有德望的長者作為自治組織的領袖成為一種傳統。作為自治組織領袖的代表——鄉紳的存在,在維持鄉村基本秩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鄉里組織領袖的本質仍是農民,二者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即便鄉紳自治不是鄉民自治,在家族色彩和血緣意識的影響下,鄉村自治也難免逃不脫宗族勢力和傳統倫理的范疇,影響鄉村政治的運作方向。
隨著鄉村自治模式的轉變,地方自治組織自治功能的弱化,原本在鄉村社會處于相對超脫和較為優勢地位的鄉村士紳,淪為公權的附庸,其影響范圍也大大縮小。從擁有家長式的權力和權威到淪為國家的代理人,鄉紳作為自治領袖在鄉村自治的發展過程中遭受著權力控制與利益劃分上的沖突。
我們可以通過鄉村自治領袖利益和地位的變化上看出,在公權力的影響下,鄉村熟人、半熟人社會雖未完全消解,但作為鄉村自治組織領袖的“鄉村文化人”受到壓制。由此,鄉村自治不再是權利的制度載體,民眾對于鄉村自治的參與也大大降低。
3 自治弱化功能的邏輯
3.1 公權擴張
無限的公權擴張是我國古代鄉村自治呈現出弱化趨勢的根本原因。清末交通通訊的改善,為公權擴張提供了可能。用現在的視角看,當一個帶有濃厚自治色彩的家族社區,受到公權力滲透的影響時,則會變為一個具有正式權力的社區。通過這種在地方鄉村社會具有直接授權的自治組織,國家政權的影響力得到了更好的延伸,當然,這不得不犧牲自治組織的自治性。
公權力總是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滲透到鄉村社會,但最明顯的還是國家寄希望于將權力介入鄉村社會,實現對地方的有效控制。與此同時,自治地方并沒有顯現出與公權力的對抗。因此,無限擴張的公權力打破傳統的“不下縣”的傳統顯得相對容易。
公權力的擴張使自治組織的自治性弱化,具體表現為鄉村自治的空間縮小、自治團體的獨立性喪失、自治的民眾基礎被摧毀等。這一過程也表現出了中央集權與地方權力的沖突,但是公權介入的尺度以及是否應該保留鄉村自治組織的自治功能確實值得思考。
3.2 鄉村共同體自身的封閉性和隨意性
鄉村共同體的封閉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在自治領袖的帶領下,以宗族為構成基礎的鄉村共同體可以實現“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應對社會風險。自治功能強大的宗族形成一種社區,并發展成為可以與中央對抗的地方勢力。
與此同時,鄉村共同體所具有的這種自給自足的特點又因為它的隨意性逐漸被打破。鄉村共同體的隨意性體現在它在應對鄉村自治模式的轉變時,并沒有體現出絲毫的抵抗。當傳統的自治領袖被迫與職役制掛鉤,變為一種差役性義務,成為國家公權力的附庸時,鄉村自治也就失去了它的自治特色。
因此,如果鄉村共同體能夠從一而終地固守其封閉性,又能夠甩掉它的隨意性的話,鄉村自治組織的自治性便不會那么容易地被國家公權力吞噬。
3.3 民眾權利與民主意識的缺失
民眾的權利與民主意識向來都是維持鄉村自治功能的關鍵,不論是在古代,還是近現代。鄉村自治好似是地方民眾權利與民主的保障,但筆者認為,將其看作是團體利益的維護會更好,一榮俱榮、一恥俱恥。
處于自治狀態中的民眾,其權利和民主意識的缺失與自治組織的領袖脫不開干系。但隨著國家公權力的沖擊以及自古以來“權利本位”、“官本位”的影響,無論是自治領袖還是普通民眾,都沒能認識到地方鄉村自治的權利意義。于是乎,權力的擴張失去了制約。“用民政治之構造,鄙人亦有一語足以概括之,則行政網是已。大凡世界各國,其行政網愈密者,其政治愈良好愈進步···鄙人現在亟亟于編村制,意欲由行政網不漏一村入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做到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網能密到此處,方有政治可言”。正如閻錫山所言,在公權力的干預下,中國鄉村自治組織變為行政工具,織起了基層社會的密網,而民眾缺失權利與民主的意識這件事實正是織線。
4 啟示
綜合考慮國家治理體系下鄉村自治的角色,充分考慮農村未來的改革。村民自治是實現村民當家作主的最好途徑,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步。對此,筆者有以下幾點意見:
4.1 完善制度建設,保障基層民主的發展,避免過度干涉,防止權力越位
上級政府對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既要有所控制,又要適當放權。要讓中央政府、地方基層、人民群眾三股力量并駕齊驅,休戚與共,成為基層治理體系不斷推進和革新的中流砥柱。
4.2 合理利用宗族觀念,提升鄉村自治的質量
發展好村民關系,繼承“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良好村風,構建氛圍融洽的鄉村共同體。
4.3 復位村民個體的全面自治
提高民眾參與度,增強民眾的權利和民主觀念。吸納優秀的村小組長進入黨員隊伍,以前自治靠鄉紳,現在當家跟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