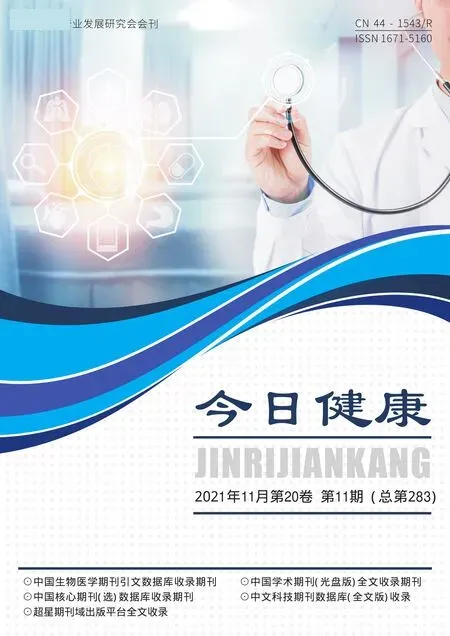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病因及診治的臨床研究進展
韋振克
(河池市第四人民醫院,廣西 河池,547000)
酒精所致精神障礙,顧名思義是由長期飲酒多引發的精神障礙疾病,該疾病既往在歐美國家具有較高的發病率,甚至因此而首次住院的群體更占比1.3%~17.4%,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癥患者[1]。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飲酒人數的不斷增加,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人數也在持續增長。經任季冬[2]調查研究發現,在2005年1月~2014年12月的10年間,攀枝花市第三人民醫院共收治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986例,住院構成比10年增長約1.5倍;而其中男女發病人數比約為38:1,初飲平均年齡約25歲,飲酒年限超過10年者更占比72.8%,由此可見,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率呈持續增長的趨勢,且男性患者遠高于女性患者,飲酒年限越長者發病率越高。除此以外,有研究發現[3],該類疾病患者心理癥狀嚴重,軀體化程度和焦慮程度較高,敵對情緒明顯,存在嚴重的精神病性癥狀。不僅如此,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多合并糖尿病、高血壓或脂肪肝等全身性的慢性疾病,對其生命安全也構成一定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更增加患者的病死率[4]。基于此點,筆者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從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發病原因、發病機制以及臨床診斷和治療措施等方面對該疾病展開綜述,為該疾病的臨床診斷和治療提高參考。
1 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原因
目前,臨床對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原因尚未給出明確的定論,但普遍認為與遺傳和家庭環境因素、工作或生活壓力增大以致長期精神緊張、社會習俗及風氣等因素有關[5]。 經賈宏學調查分析發現[6],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終生患病率加權后為5.93%,其中存在家族遺傳病史更是導致患者發病的危險因素(OR=1.574,95%CI:1.181~2.098)。與此同時,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是一種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精神心理疾病,該疾病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要遠高于普通飲酒人群,而經周晴晴的研究發現[7],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焦慮和抑郁程度與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關(r=0.471、0.599,均P<0.05)由此可見,酗酒與焦慮、抑郁情緒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當飲酒者存在負性情緒時可能需要依靠酒精來抒發內心的苦悶,但大量飲酒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繼續加重人體的身心負擔,從而引發更為更嚴重的后果,并逐漸形成惡性循環,使得陷入負性情緒者對酒精的渴求更甚,繼而增加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率。另外,受人情社會和部分地區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無酒非宴”的風氣,隨著飲酒量的增加,因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發病率也在逐年遞增。
2 酒精所致精神障礙診治進展
2.1 臨床診斷 既往臨床對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礙的診斷主要依據患者的是否存在明顯的飲酒史,以及有充分理由斷定患者的神經癥狀是直接由飲酒所致;而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臨床醫師對于該疾病的診斷在原有的診斷方式上增加影像學檢查技術進行輔助診斷[8]。在馬文國[9]的研究中,通過對于健康體檢人員和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頭顱CT檢查發現,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在側腦室前角寬度、第三腦室寬度、第四腦室寬度、側裂池寬度以及腦溝寬度方面均大于健康體檢人員,而其腦白質密度卻低于健康體檢人員,而導致此情況的原因可能與腦萎縮和腦白質變性有關。在樸香淑[10]的研究中,68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經腦電圖檢查后發現,腦電圖異常者占比61.8%,而其異常的主要表現為α波慢化,β波增多,中至高波幅的θ波和δ波短、長程出現或彌漫分布于各導聯,主要集中在額、顳區;推測其原因可能與長期飲酒致使患者的腦細胞發生脫水、變性或壞死,神經傳導速度因此減慢,繼而引起腦生物電的變化。在林紅[11]的研究中,通過對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和健康體檢者超聲心動圖檢查結果發現,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相較于健康體檢者而言存在明顯的心肌損害癥狀,具體表現為的左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室舒張末期容積和左室收縮末期容積升高,E峰A峰流速比值、心輸出量和左室射血分數降低。經黃靜[12]研究發現,對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和健康體檢者分別采用事件相關電位和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結果顯示酒精所致精神障礙者兩項檢查均存在明顯異常,并且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測定的血流速度與事件相關電位檢測測定的潛伏期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故而可將二者聯合檢測結果作為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重要診斷依據。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酒精所致精神障礙受長期大量飲酒的影響會存在不同的腦組織和心肌組織病變,故而可借助頭顱CT、腦電圖、超聲心動圖、事件相關電位和經顱多普勒超聲檢查等檢查判定患者是否存在腦組織和心肌組織病變,從而為疾病的確診和病情嚴重程度提高可靠的依據。
2.2 治療措施 戒酒:對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而言,其首要的治療措施是戒酒,戒酒能否成功是患者疾病能否康復的關鍵所在,其中癥狀較輕者可采用一次性戒斷的方式;而對重度依賴酒精的患者需采用遞減法進行戒酒。在患者戒酒期間,尤其是戒酒的第一周需嚴密監測其體溫、脈搏、血壓、意識和定向能力,嚴防戒斷反應的發生,從而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13]。對癥治療: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在疾病癥狀的表現上存在的明顯的不同, 但大部分患者會伴有幻覺、妄想、精神運動性興奮或抑制的表現,對此臨床對于與該疾病的治療可采用抗神經疾病藥物進行干預。在姜堯[14]的研究中發現,對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采用非典型抗神經疾病藥物氨磺必利治療12周后患者的精神癥狀和生活質量得到顯著的改善,并且患者治療期間不良反應較少,治療的安全性更高。而在王丹[15]等研究中也發現,對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采用利培酮治療6周后患者的精神癥狀評分、焦慮和抑郁評分以及運動和協調能力評分均得到顯著的改善,且改善程度遠勝于采用氯丙嗪治療的患者,但二者均易引起錐體外系反應,故而在藥物治療期間需加強患者的用藥監護,及時處理能力發生的不良反應,保障患者用藥治療的安全性。行為療法: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不僅會存在生理功能損傷、營養代謝紊亂,甚至會隨著病程的延長逐漸損傷患者的中樞神經,造成認知障礙,而常規的抗精神疾病藥物雖然可以改善患者的精神癥狀,但對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卻為明顯助益[16]。對此郭隆潤[17]對31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在常規藥物治療基礎上輔以計算機認知矯正治療,結果顯示患者治療8周后的記憶力和認知功能均得到顯著改善,分析其原因可以發現,計算機認知治療是一種基于行為訓練的新型認知訓練技術,作用于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時可以有效減少于威斯康星卡片分類試驗的持續錯誤數量,提高患者的糾錯能力,從而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而經楊靈靈[18]研究也證實,在喹硫平治療基礎上聯合行為療法可以有效改善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精神癥狀,提高其生活質量,進一步凸顯行為療法在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中的應用優勢。心理治療: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受家庭、經濟及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都曾通過飲酒的方式來緩解內心的焦慮和抑郁,并且不斷強化飲酒行為;而且該疾病患者自我意識強烈,性格內向且敏感多疑,因此患者想要完全戒酒的關鍵在于預防復飲[19]。森田療法又稱為根治的自然療法,屬于一種常見的心理療法,該方式始終將“順其自然”作為理論原則,通過幫助患者消除思想矛盾,使患者擺脫疾病觀念的影響,而經徐淼[20]研究發現,對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開展改良森田療法可以緩解其緊張心理狀態,疏導其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引發失望無助感;并且在治療中引入心理疏導和知識講解,還可以不斷增強患者的自信心,使其更積極地配合醫生治療方案,為促進患者康復奠定良好的基礎。
3 總結
綜上所述,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患者的發病基礎是長期過量飲酒,而造成患者長期飲酒的原因與心理、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有關。對于該疾病的診斷更是依據患者是否具有飲酒史,以及其精神癥狀是否由飲酒所致等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并鑒于長期飲酒對患者腦組織和心肌組織的損傷可輔以相應的影像學檢查為疾病的確診提高依據;而在治療方面戒酒是必行措施,為了保障戒酒的成功可以輔助相應的心理和行為療法,針對患者的精神癥狀可采用相應的抗精神疾病藥物進行干預,但需加強患者用藥監護,以保障患者的用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