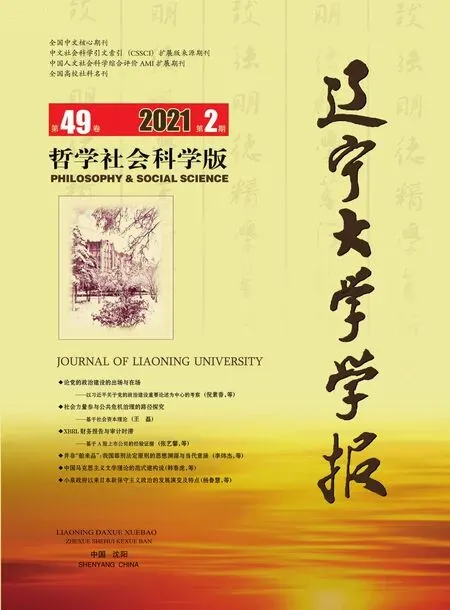語言政策與摩洛哥現代國家的建構
張婧姝
(大連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學院/突尼斯研究中心,遼寧大連116044)
語言既是身份和地位的標志,也是文化和思想的載體。語言政策是國家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政治權力、文化傳統、社會狀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自殖民時期以來,摩洛哥的語言政策經歷了一系列的調整與變化,語言生態也隨之變動。隨著各種語言地位的升降變換,不同社會群體獲得的地位也隨之有所改變,社會群體的層級從而區分開來。
摩洛哥社會一直是多種語言并存的,語言和文化多樣性體現出悠久的歷史傳承。當今,摩洛哥語言以阿拉伯語及其變體、阿馬齊格語及其變體、法語和西班牙語等為主,日常生活中最通用的是摩洛哥阿拉伯語方言與阿馬齊格語。2011年摩洛哥的《憲法》(以下簡稱《憲法》)頒布后,官方語言由阿拉伯語單語轉為阿拉伯語與阿馬齊格語雙語,這也是阿拉伯國家的首例。語言生態在語言和文化互動與融合的背景下,呈現出多樣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因此,在多語化國家的語言政策的相關研究中,摩洛哥語言政策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義。
一、語言政策與國家權力的雙向作用
語言社會學理論認為,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符號系統,與其所處社會的政治權勢和經濟利益密切相關,故有時被稱作語言政治學(linguistic politics)。國際學術界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受到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后現代思想家批判思想的影響,形成了一種通行的研究范式,即對語言政策進行政治解讀。①馮佳、王克非:《近十年國際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研究的CiteSpace分析》,《中國外語》2014年第1期,第71、73頁。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研究語言與權力、政治的關系后提出,語言不僅是交際和溝通的手段,也是權力關系的一種工具或媒介,是一種象征性暴力符號。社會生活中的語言行為,均是說話者通過對話和語言交流而進行的權力較量,語言實踐就變成使用者背后的整個社會勢力和社會關系的力量對比和權力競爭的過程。①參見高宣揚:《布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頁;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tra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p.77-91.與語言行為相比,語言政策顯示出更深層次的權力關系,從社會哲學層面對國家政策和語言狀況進行關聯性的思考與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語言政策背后的政治意圖和意識形態傾向,分析語言政策與權力之間關系。比利時的社會語言學家簡·布洛馬特(Jan Blommaert)通過批判性研究發現,每一種語言政策都與意識形態相關聯,語言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選擇,是政策制定者認為有利于社會和人民、有益于國家進步的假設。②Jan Blommaert,“Language planning as a discourse on language and society:The linguistic ideology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vol.20,No.3,1996,p.215.加拿大語言學家諾曼·拉布里(Normand Labrie)關注語言政策與政治的關系,認為語言政策是個人、社會群體、國家各職能部門和國家體系在有組織的活動中所行使的政治權力。③Normand Labrie“,Les conf lits linguist iques au Québec et au Canada:vers une grille d’analyse”,Normand Labrie.ed.,études récentes en linguistique de contact,Bonn:Dümmler,1997,pp.199-220.經過研究發現,國家權力機構通過在媒體以及教育界、科學界等領域宣傳和實施語言政策,即通過多領域的話語實踐建構國家認同。④參見Normand Labrie“,Politique linguistique ou action politique?Questions de méthodologie”,Peter Hans Nelde,ed.,Minorities and Language Policy/Minderheiten und Sprachpolitik/Minorités etl"aménagement linguistique,Asgard Verlag:St.Augustin,2001,pp.61-75.加拿大學者托馬斯·里森托(Thomas Ricento)采用批判社會語言學理論進行研究指出,意識形態是影響語言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執政者的意識形態傾向是研究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一個關鍵視角。⑤參見Thomas Ricento,“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vol.2,2000,pp.196-213;Thomas Ricento,ed,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Theory and method,Oxf 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7.以色列語言學家博納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認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研究是一個復雜的話題,需要同時研究語言學和非語言學元素,他提出“研究語言政策的,必然是要聚焦在政治單位(political units)上,因為語言政策與權力和權威密切相關。在當今世界,國家是權力彰顯的地方,政府機構是依靠憲法建立起來的,擁有公民管理權。原則上,任何政府都能夠依照憲法、法律或規章來制定語言政策,并且有辦法實施或執行這些語言政策。事實上,各個國家的確都是這樣做的。”⑥〔以〕博納德·斯波斯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張治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9頁。根據斯波斯基的觀點,新加坡語言學家萊昂內爾·威(Lionel Wee)提出“通過研究社區的語言實踐、語言信仰或意識形態,以及各種影響政策的話語行為,可以更好地研究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復雜性。”⑦Lionel Wee,“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ames Simpson.ed.,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23 November 2012,p.68.
語言政策與權力的關系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美國學者詹姆斯·托勒夫森(James Tollefson)認為,“語言既反映了權力關系,又影響權力關系”。一方面,語言政策的實施離不開權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語言政策的目的,是要在權力博弈中獲利。博納德·斯波斯基提出,“在民族國家內部,各種民族、宗教和少數民族團體都試圖修改本國的語言政策,因為這些團體都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實踐和語言信仰。他們通過這三種方式:要么呼吁政治獨立,要么要求更多的人口或者領土的有限自治權,要么發起爭取特定語言權的運動(該運動也許是獨立進行的,但往往是與其他文化權、社會權或政治權一同進行),爭取實現自我管理,并試圖影響團體中其他人的語言實踐或語言信仰,甚至試圖影響到本國更大的政治單位(如民族國家)的語言選擇。”①〔以〕博納德·斯波斯基:《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第209頁。所以,語言政策的作用不是只局限在語言、教育等社會層面,也同樣影響政治權力的爭奪和再分配。
那么,就摩洛哥國家而言,其語言政策也受到政治群體博弈的影響,體現了執政主體的意識形態傾向,是其語言選擇和治理目的的呈現,與國家權力分配密切聯動。摩洛哥政府通過實施語言政策,從語言與文化層面規范國民語言行為,影響各種權力群體間的抗衡,架構起社會關系網。并通過研究語言政策文本和教育界、科學界、媒體等領域有關語言政策的實施與評價,可以理解語言政策背后的政治意圖和國家發展目標。通過研究政策的影響因子與實施效果,總結各群體的權力范圍與訴求,可以理解和體現出摩洛哥政府通過語言政策維護執政的合法性,強化國家認同感,并最終建構現代社會的國家。
二、不同時期語言政策對執政合法性的維護
合法性是指執政者在政治層面獲得了社會成員給予的內心資源的認同、支持與服從,反映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互動和公認理念。②孫建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論辨析》,《求實》2004年第2期,第59頁。摩洛哥在被殖民時期、獨立建國后與穆罕默德六世國王繼位后語言政策經歷兩次變化。實際上,在1912-1956年期間,即保護國時期,法國成為摩洛哥的宗主國起,摩洛哥才有對語言地位有具體要求的語言政策,法國當局明確要求摩洛哥的官方語言是法語。通過普及法語和激勵阿馬齊格語的復興,壓制阿拉伯語,實現文化殖民。其語言政策主要是在對教育和公共管理領域的語言規劃。摩洛哥獨立之后,“官方語言”一詞開始出現在國家憲法中,如1962年摩洛哥第一部憲法的前言中明確規定“國家的官方語言是阿拉伯語”。③摩洛哥政府:《1962年摩洛哥憲法》(阿拉伯文),拉巴特:摩洛哥官方印刷局,1962年,第14頁。而在2011年,摩洛哥頒布的新憲法又明確規定官方語言政策:“阿拉伯語仍然是摩洛哥的官方用語,作為全體摩洛哥人的共同財富的阿馬齊格語也是官方語言,同時還要保護哈桑尼亞語,承認其是摩洛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摩洛哥政府:《2011年摩洛哥憲法》(阿拉伯文),拉巴特:摩洛哥官方印刷局,2011年,第5頁。在保護國時期,法國與西班牙政府均制定了“推廣宗主國語言(法語、西班牙語)、壓制阿拉伯語、扶持阿馬齊格語”的語言政策,力圖通過普及宗主國語言,維護精英利益,推廣法國文化與西班牙文化,實現文化植入和文化殖民。通過語言與文化的普及,不僅增強摩洛哥人對宗主國的好感,也對摩洛哥人的心理和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以期實現殖民化與同化的目的,消除他們對殖民統治的反感,從而維護宗主國政府的執政合法性。
在摩洛哥獨立后,執政主體的首要目的是重構王室統治和君主體制的合法性。首先,國王的執政合法性有歷史根基,公元8世紀,穆斯林陸續抵達摩洛哥,穆萊·伊德里斯一世(Moulay Idriss I)在8世紀末建立了第一個伊斯蘭國家,此后,阿拉伯語開始成為歷史、宗教、傳統和文化的象征,是摩洛哥歷史、摩洛哥人身份和伊斯蘭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元素;其次,國王的執政合法性有宗教根基,其統治的宗教合法性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國王是信士的長官(全體穆斯林的首領),是宗教領袖,是所有穆斯林的首領,掌握著摩洛哥人的精神權力;二是阿拉維家族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其血統純正、身份高貴,所以,穆罕默德五世、哈桑二世、穆罕默德六世三位國王,分別是圣人穆罕默德的第34、35、36代傳人,因而阿拉維家族的國王具有天然的執政合法性。在歷史和宗教基礎上,阿拉伯語成為國王執政合法性的第三大依據來源,因為它既是民族象征,又是宗教象征,還是阿拉維王朝王室血統純正性的代表,所以成為合法性的最佳體現。
摩洛哥政府一直通過實施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振興阿拉伯語,強化阿拉伯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國受“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影響,均推行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即規定阿拉伯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或者國語,政府自上而下地復興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在這一背景下,摩洛哥在獨立后的30年,一直積極推行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普及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政府制定上層政策,人民在社會生活中推動語言阿拉伯化、教育阿拉伯化,從而形成自上而下的去法語化和去殖民化的民主化浪潮,也得到了民眾的擁護。穆罕默德五世從保護國時期到國家獨立初期都在維護阿拉伯文化,積極投身于民族解放和反殖民斗爭中,因此確立了其在民眾心中的執政合法性。而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歷任國王一直采用拉攏的策略,吸納社會中各種反對勢力,如政黨反對派、伊斯蘭復興運動派、公民組織等,在政治多元化的理念指導下,將反對派勢力納入以國王為領導核心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政府通過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化解政治危機,緩解社會矛盾,該政策被視為是促進阿拉伯國家團結和摩洛哥獨立的重要舉措。獨立后的不同語言的地位差別體現出了社會層級的差別,已然成了族群斗爭的一個重要領域。語言之間的緊張關系即是族群間的緊張關系,如果關系惡化會刺激身份認同的分化,會對國家建設有消極的影響。所以要實現長治久安,就必須就語言問題達成全國共識,才能加強國家和民族凝聚力,為政權穩定和國家發展奠定良好的群眾基礎。阿拉伯化語言政策有效地團結了摩洛哥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維護了族群和諧和社會穩定。
摩洛哥前任國王哈桑二世和現任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大學期間,都學習的是法律和政治專業,所以深諳法律權威對君主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意義。《憲法》實際上體現的是國王的最高意志,如《憲法》第19條規定,“國王是信士的長官、國家的最高代表、國家統一的象征、國家永世長存的保證。國王是公民和社會團體自由和權利的保護者。他在真實疆界內保衛國家的獨立和王國的領土完整”。此外,兩位國王都意識到重視和普及阿拉伯語是維護國王的權威性和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措施。
但是對于摩洛哥國王來說,國家治理始終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做好維持王權、實現民主與維護國家穩定三者之間的平衡。穆罕默德六世繼位以后,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選擇延續哈桑二世國王時期的政治多元化政策,①張玉友:《當前摩洛哥國內政黨形勢:分裂與崛起》,《當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64頁。但是與哈桑二世對反對黨實施強硬打擊政策不同,穆罕默德六世更加注重用較為溫和懷柔的政策影響反對黨,并包容各種不同意見。在這一背景下,語言政策也開始向多元化發展,這也是2011年憲法會增加阿馬齊格語為官方語言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背景。
在建設現代國家的同時,執政主體需要不斷緩解各種社會矛盾和消除執政危機,在這一過程中,執政主體的包容性和多元意識不斷增強,并逐漸意識到必須尋求一種長期有效的多元化策略。也正因為此,摩洛哥才能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引發了如“2.20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之后做出快速反應,盡量降低社會動蕩的風險。實際上,摩洛哥的政治體系在阿拉伯之春前已經開始政治轉型,并將包括伊斯蘭主義者在內的大多數政治力量納入國家轉型計劃之中。這使得摩洛哥能夠和平解決國內沖突和推動漸進性變革。②Ashraf Nabih El Sherif,“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PJD):The Question of Democratic Islamismin Morocc”,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6,No.4,2012,pp.660-682.當前的語言政策就是改革舉措中的重要一環,從文本上看,是將阿馬齊格語列為官方語言,重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及其多樣的文化傳統,對外語和外國文化持開放態度;而通過分析執政主體的治理需求,可以明確這一語言政策是執政主體對包容性和多元主義的實踐,其實際目的是維護政權穩定和社會和諧,符合當時突出的社會訴求,在解決語言問題的同時,安撫了少數族群的情緒,解決了社會矛盾,化解了政治危機。
三、多元化語言政策與國家認同的建構
身份認同源自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緊密互動,包括歷史記憶、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和民族關系等。身份認同具有一種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的功能,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隨著社會制度、文化狀況和環境的改變而被不斷地建構、塑造出來,即溫特所說的“身份習得”(Learning Identities)。①汪長明:《馬格里布地區一體化:進程與前景——地區認同的視角》,《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第19頁。
從語言學的視角看,語言是一種思想的驅動,是一種重要的思考和感知方式。阿拉伯語既是阿拉伯民族語言,又是伊斯蘭教的宗教語言。在阿拉伯語成為母語后,摩洛哥人思維方式開始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從此,摩洛哥人一致認可阿拉伯伊斯蘭的身份認同。自公元8世紀伊德里斯一世建立阿拉伯伊斯蘭帝國起,摩洛哥就一直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并延續至今,各代國王都宣稱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以及“信士們的長官”。②Marvine Howe,Morocco:The Islamist Awakening and Other Challenges,New York:Oxf 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5-126.所以,伊斯蘭身份通過宗教信仰根植于每一個摩洛哥穆斯林心中。因此,從歷史發展來看,阿拉伯伊斯蘭身份具備自然性和合理性。
在保護國時期,摩洛哥國家以宗主國語言為官方語言,即實施殖民化的語言政策,而獨立后則采取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隨著語言政策的轉變,國家認同由法國和西班牙屬地認同向現代阿拉伯伊斯蘭國家認同轉變。摩洛哥政府通過采取阿拉伯化語言政策,實現了文化同質化、強化了阿拉伯認同,加強了共同歷史情感;通過推廣阿拉伯語,弘揚了歷史傳統和宗教文化,重新強化了摩洛哥人的阿拉伯伊斯蘭身份。由此可見,摩洛哥的語言政策,尤其是教育領域的語言政策一直是建構和強化國家認同的有效途徑。
在國家獨立后,阿拉伯化語言政策的確強化了國家認同和阿拉伯民族認同,“將確保摩洛哥的文化統一,增強阿拉伯和伊斯蘭的身份認同。”③Aomar Bourn,“The Political Coherence of Educational Incoherence:The Consequences of Educational Specialization in a Southern Moroccan Community”,Anthropology&Education Quarterly,vol.39,2008,p.9.民族國家的構建既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結合的過程,也是在民族的基礎上形成的“想象的共同體”。④想象的共同體,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創造以分析民族主義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不同于現實共同體,現實共同體是建立在成員之間每日面對面的互動。他提出一個解釋關于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新的理論典范。安德森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他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安德森相信民族是社會建構的共同體,是由認知他們自己是團體一分子的人們之想象所建構而成。參見許紀霖:《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6期,第92-94頁。但是進入21世紀后,泛阿拉伯思潮的影響幾乎消失,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強度和持久性都有所弱化,“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07年的調查顯示,在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僅有34.1%的民眾認為自己是“摩洛哥人”。⑤張楚楚、肖超偉:《地緣政治視角下的馬格里布地區現代國家構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76頁。在母語建構身份認同的層面,因為日常生活廣泛使用的是摩洛哥阿拉伯語方言,其與阿拉伯語普通話差別很大,其他國家阿拉伯人很難理解,這也影響了摩洛哥人在阿拉伯世界的融入和同化,語言層面的地區認同不斷弱化。
2011年,摩洛哥語言政策再一次轉變,《憲法》明確規定了雙官方語,隨后教育語言政策也向多語化轉變,既重視普及雙官方語,也積極發展多種語言。多元化的語言政策有三個主要目的:首先是管理多樣性的語言,如弗朗西斯·格林(Fran?ois Grin)指出,“語言政策的根本使命是多樣性的管理,因為在多語社會,語言問題都圍繞多樣性和生存空間展開。”①Jamses Tollef son,Planning language,planning inequality:Language policy in t he community,London:Longman,1991,p.77.目前的語言政策穩固了阿拉伯語的第一地位,強調了阿馬齊格語的官方地位,還鼓勵學習外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有助于保護摩洛哥古已有之的語言生態多樣性。第二個目的是解決語言問題,處理語言之間的矛盾。約書亞·亞倫·費什曼(Joshua Aaron Fishman)提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是有組織的尋求解決語言問題的方法,一般是國家層面的行為。”②Howard Giles,ed.,Language,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Academic Press,1977,pp.16-53.理查德·D·蘭博特(Richard D.Lambert)認為,“在兩種或三種語言處于積極競爭狀態的國家,語言政策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好這些語言的矛盾,許多民族國家在它們的憲法或語言法中認可兩種官方語言或國語,以便從形式上和法律上劃分國家的社會語言空間。”③Richard D.Lambert“,Ascaff olding f or language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vol.137,1999,pp.23-24.從這點分析,摩洛哥政府增加阿馬齊格語為官方語言,即增加阿馬齊格語的社會空間,有助于解決語言矛盾。第三個目的是維護語言生態的良性互動。有學者指出,“如果一個民族的語言僅局限和封閉在本民族狹隘的生活空間里,就會喪失與時俱進的發展力和創造力,從而逐漸趨于衰落和消亡。”④李寧:《摩洛哥官方語言政策變遷背景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第83頁。目前的語言政策,是探索摩洛哥多語共存的有效途徑,盡量避免雙官方語的政策可能引起的摩擦。
《憲法》在序言部分規定:“摩洛哥是一個伊斯蘭國家,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團結和民族多樣性,國家屬性由阿拉伯伊斯蘭、阿馬齊格、撒哈拉哈桑尼共同構成,富有非洲、安達盧西亞、希伯來和地中海特性。摩洛哥身份具有伊斯蘭教神圣性,并將宗教屬性置于首位。摩洛哥人民的價值觀是開放的、溫和的、寬容的,愿意與世界所有文化和全人類文明之間展開對話、相互理解。”《憲法》正文規定:“阿拉伯語仍是國家的官方語言。國家致力于保護和發展阿語并開發阿拉伯語的用途。同樣,阿馬齊格語也是國家官方語言,堅定認為阿馬齊格語是所有摩洛哥人的共同財富。制定實施細則,建立監管機制,奠定阿馬齊格語的官方地位,并將其納入教育領域和公共生活領域,使其履行官方語言的職能。”還要求“要保護代表摩洛哥文化的各種語言和表達的權利。國家重視語言政策和國家文化的和諧共處,重視學習和使用國際最通用的外語,并將其作為與知識社會交流、影響和互動的工具,對不同文化和時代文明持開放態度”。文化是群體內部成員彼此認同的核心,建設共同文化即是建構一致的身份認同。由于部落制度的歷史淵源,摩洛哥人對血統和譜系的認同超過領土,對語言和習俗等本土文化的重視超過法律。⑤參見張楚楚、肖超偉:《地緣政治視角下的馬格里布地區現代國家構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86頁。在歷史上,家族認同、部落認同乃至地域歸屬感普遍高于國家認同。摩洛哥執政者一直在努力地通過實施語言政策,借助語言在認同建構層面的重要作用,建構有利于國家團結統一的國家認同。當前的多元化語言政策,受到民主平等和多元化思想的影響,依托文化多元的歷史根基,挖掘包容性強、多文化共存的國家特性,強化寬容和多元的國家認同,是摩洛哥政府又一次努力和嘗試。
四、語言政策變遷與少數民族認同的轉變
國家是民族的顯性的政治組織形式,民族是國家隱性的文化實體內容。⑥張踐:《國家認同下的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中國民族報》2010年2月23日,第6版。在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語言使用者逐漸認識到,語言權利與其經濟、社會、政治利益息息相關。少數族群會選擇一種語言作為民族象征和身份建構的工具,呼吁提升語言權利,強化語言與文化意識,從而強化民族地位和爭取權力空間。
摩洛哥最大的少數民族是阿馬齊格族,其民族認同以部落認同為根本,后又受到阿拉伯伊斯蘭帝國認同與法國身份認同更新的影響,最終形成與阿拉伯民族融合的信仰伊斯蘭教的阿馬齊格民族認同。在被殖民之前,阿馬齊格人學習《古蘭經》和阿拉伯語,阿拉伯的風尚習俗開始在他們中間傳播,大部分阿馬齊格人在與阿拉伯人的融合中逐漸完成伊斯蘭教化。皈依伊斯蘭教后,阿馬齊格人不再是最初的被征服者,而成為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承者的一部分。
在保護國時期,宗主國的語言政策弱化了摩洛哥人的阿拉伯屬性、伊斯蘭教屬性,同時,又強化了阿馬齊格的民族認同。1930年保護國政府頒布《柏柏爾詔令》卻破壞了摩洛哥社會中已經形成的阿拉伯語與阿馬齊格人的緊密聯系。復興阿馬齊格語的政策,使得阿馬齊格民族意識覺醒,阿馬齊格人對阿拉伯民族屬性的認同弱化,隨著殖民者對兩種語言差異的宣傳和利用,阿馬齊格民族認同不斷強化。
摩洛哥現代國家建立初期,政府一邊恢復伊斯蘭教的核心價值地位,一邊推廣阿拉伯化的語言政策。即使是不同的群體和文化背景,但是為了現代國家建構的目標和共同的利益訴求,認同也可能交叉或重疊。這一時期的語言政策和國家政策限制了阿馬齊格人使用自己的語言,抑制了阿馬齊格人的民族身份,強化了伊斯蘭宗教認同和泛阿拉伯民族身份,這使得阿馬齊格人的身份認同再一次出現大的變化。阿拉伯化語言政策沒有提及阿馬齊格語和阿馬齊格文化,公立學校的歷史課程故意跳過伊斯蘭教到來之前馬格里布原住民的重要歷史,①Adil Moustaoui,“Conf licto lingüístico y política lingüística en Marruecos:una propuesta de análisis”,Documentos del Congreso,Diversidad Lingüística,sostenibilidad y paz,Barcelona:Linguapax,2004,p.41.進一步削弱摩洛哥的阿馬齊格身份,阿馬齊格語的空間受到擠壓。但是因為國家的首要目標是團結一致建設現代國家,阿馬齊格人也融入了擺脫殖民統治的喜悅大潮和國家建設的大軍中,其認同在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中博弈,阿拉伯文化與阿馬齊格文化再一次共同影響著阿馬齊格族群。②參見,pp.11-23.因為阿馬齊格語使用者在經濟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就業也受到限制,所以大量的阿馬齊格人積極學習阿拉伯語,承認自身與阿拉伯民族有著深厚的關系和相同的情感。此外,伊斯蘭教信仰也加強了他們的阿拉伯語言屬性。這一時期,阿馬齊格人在阿拉伯民族身份和阿馬齊格民族身份之間徘徊,最終,一部分阿馬齊格人因為通婚和融合轉向了阿拉伯民族認同;而對另一部分阿馬齊格人來說,“語言忠誠構成了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價值”,③Moha Ennaji,Multilingualism,Cultural Identity,and Education in Morocco,New York:Springer US,2005,p.1.其民族認同從而持續強化。
近幾年,隨著語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樣性凸顯,阿馬齊格人逐漸意識到自己從未完全阿拉伯化或伊斯蘭化,這導致語言生態發生了細微而復雜的變化。復興阿馬齊格語,必須要消除語言隔離,并且強化民族身份的凈化意識。④Fatima Sadiqi“,Women,Gender and Language in Morocco,Leiden and Boston”,Journal of Pragmatics,MA:Brill,2003,p.17.新的語言政策與獨立后的語言政策相比,更重視摩洛哥語言生態情況,也更多強調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與發展。這說明在憲法出臺之前,摩洛哥政府做了足夠的調研和論證,從而全面地照顧到各種語言及其代表的文化。《憲法》強調“國家重視語言政策和國家文化的和諧共處”。明確規定要照顧到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和文化權利,承認了阿馬齊格語和阿馬齊格文化的重要性,并且充分體現出語言政策要從國家多語言多文化的實際出發這一要求,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和諧和促進文化共存,有助于積極的、溫和的阿馬齊格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形成,為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復興和認同建構樹立了典范。但不可忽視的是,當前的語言政策可能為國家建構提出各種復雜和多元的挑戰,身份認同的交叉和互動更加頻繁,也會對摩洛哥人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認同產生深遠影響。
結語
摩洛哥的語言生態自古以來就是多元的,無論其語言政策如何變化,政策文本都涉及多種語言,每種語言都擁有其象征性資本。從殖民者占領摩洛哥以來,該國語言政策隨掌權者的更替經歷過兩次重大改變。從社會治理目標來看,各時期的官方語言政策目的明確,即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推動國家的語言文字事業與文化發展。雖然隨著語言政策變遷,不同語言的地位有所置換,但是每一種語言一直有其獨特的使用場域,也因此劃定了明確的權力范圍,而語言的互動和競爭,實際上是使用不同語言的群體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的博弈,在這一博弈過程中,現代摩洛哥的國家認同建構而成,各民族認同也在其中建構和角力。2011年的摩洛哥《憲法》明確規定了官方語言地位,強調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鼓勵學習外語,發展國家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通過官方語言政策影響民眾的語言選擇,實現國家權力主體的治理目標,強化國家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加強意識形態建設。
當前,摩洛哥政府重視多元文化發展,鼓勵社會各階層和各領域的交流與融合,積極推動民主實踐,2011年《憲法》及修憲以后的各項語言政策也體現出這樣的治理目的;從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看,摩洛哥語言政策均實現了執政者的權力意圖,即在語言層面,穩固執政合法性,完成政策制定時的預想,建構和協調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推動實現現代國家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