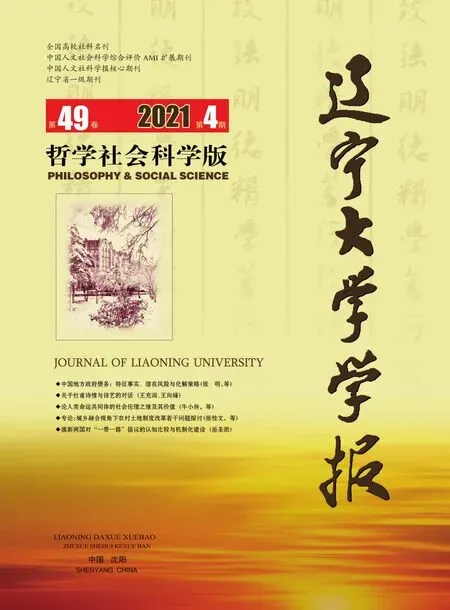海德格爾如何轉化康德哲學
尚 杰
(四川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研究中心藝術與科學研究所,重慶 400053)
一、我與時間:切己性與不可置換性
現在,“我”而不是“我們”研究時間——“現在”已經在時間之中了,生命的真諦,就是永遠從現在開始。現在,我撇開“現在”這個還要反復分析的時間之謎,專門談談“我”。“我”有薩特的談法與海德格爾的談法,薩特直接說“我”與“人”,海德格爾反對,他說形而上學不是“人道主義”,“我”和“人”都是已經定義了的、可重復的概念,不可作為思想的出發點。海德格爾不說“我在這兒”,而說“此在”①德文:da-sein,法文être-le-la,英文being then and there。——它被整個哲學史遺忘了。如果being被重復,就成為beings,beings可以被理解為存在,相應的時間,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時間概念(時間就像是一條河,過去、現在、將來,是相互交融理解的),但如果逼真地說,其實事情就是此時此刻,爾后同樣的情形永不再來(有生活閱歷的人都知道這是事實),那么這此在(瞬間)才是唯一真實的,即不可重復性。舉個例子,張三聽到朋友的死訊,他悲痛但事實上與他無關,因為那是別人時間的終結,只有他自己的時間才是真正的時間,這里所謂“真正”就是無法替代性,他死后盡管時間仍舊存在,但是對他而言,已經毫無意義。因此,雖然時間就像是一條河,但他自己才是真正的這條河,這種切己性或親自性,被哲學史遺忘了。
以上的不可替換性,就是海德格爾哲學中的核心問題,這個“此在”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形式上它是此時此刻(瞬間),內容上它是此情此景(在場),但是兩者不分彼此(一切真實的在場都是瞬間在場),而且都具有不可替換的本質特征。海德格爾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一書中,認為康德從來沒有明確指明這種不可替換性,但海德格爾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處處在其中捕捉“此在”的影子,這就是對經典著作的“哲學家式”的閱讀方法。
時間的切己性就是瞬間,人的切己性就是我自己。根據上述哲理,我自己就是一切,因此叔本華認為,“要么孤獨,要么平庸”,這話與別人是天才而自己是普通人的事實無關,它其實是說:我是以對話的方式與別人、與世界發生關系的,比如海德格爾讀康德的書的切己方式,是寫出《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他以較勁的方式,與康德對話。
理解,就是去對話。對話就超越了我自己,這是荒謬的,因為它犯規了。它將原本只是自己的事情,比如獨白,變成了兩個人或者多個人之間的事情。說穿了,這是一種假對話,因為我與你之間無法替換。但是,對話假定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假定是必要的,實際上是根本做不到的。也就是說,事情從出發點上就已經含有虛假。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有一句名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荒謬現象:“愛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愛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所以,我愛你,與你無關。”但是,每個人都有一種自尋煩惱的天性,就是極力使愛與你有關,因此,愛與傳統哲學一樣,從一開始就蘊含著悲劇命運,因為試圖去建立關系的愿望,就是想合二為一,也就是設定了置換的可能性。
切己性與建立關系之間,是不可分的關系。換句話說,思想是從自相矛盾開始的,事實上我們時刻在替換著原本不可替換的東西,這已經很荒謬,就像黑格爾說的,在哲學出發點上,存在與虛無完全是一回事——海德格爾認為,肯定自相矛盾,就是康德思想中最值錢的寶貝。
這里有一條極其隱蔽的思想線索,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具有看不見的相似性,彼此之間是相互解釋的。胡塞爾曾經說,笛卡爾哲學是現代哲學的神秘渴望,他用現象學改造笛卡爾的思想。同樣的話也適合海德格爾與康德的關系,他認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根本不是一部認識論的著作,而是為形而上學本體論尋找新的基礎。簡單說,這個基礎就是時間,或者說,是此在與時間,存在就是此在,而“此在”就是此刻的時間。海德格爾并沒有強行解釋,他用康德的著作說話。
傳統上,形而上學就是關于本體論的。“本體”是基礎,是根本原因,它形成某種獨斷。如果我們強說康德和海德格爾的哲學都有各自的本體論思想,這個說法隱含嚴重誤導。也就是說,即使他們在字面上尋求某種新的本體論,也絕不意味著“基礎”或者“根本原因”之類的獨斷論,它不是一個清晰明白的具有整體論性質的判斷,而意味著某種破碎,也就是自相矛盾。它緣起于認為存在問題的根源在于時間問題,這是海德格爾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讀出來的。
康德要解決的問題是:1,我能知道什么?2,我應該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由對于三個問題的回答,最終歸結為4,人是什么?先從表層上,在康德的語境中,我是人,反之亦然。在康德那里,有一種人類學,但區別于與盧梭同時代的思想家布豐①布豐(G. L. L. de Buffon,1707-1788),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論人》(Del’homme)中,詳盡描述了人的自然形態,使人類學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雛形。創立的現代人類學,在康德那里是“哲學人類學”。雖然海德格爾不同意把哲學做成任何意義上的“人類學”,但他特別看重康德從先驗的眼光描述人,康德對以上四個問題做了先驗回答。在康德那里,“先驗”與“超驗”有嚴格的區分,他的哲學是一種先驗哲學。至于“超驗”,他批判形而上學獨斷論,就是指責傳統本體論的“本體”概念是“超驗”的,他認為這種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一書中,康德的“先驗”與“超驗”被移植到海德格爾的理解平臺上,他不再采用康德的區分,而是消解了“先驗”與“超驗”之間的界限,他認為時間與空間這樣先驗的直觀形式,就是居于“基礎”或“本體”的地位,就是“超驗”的。海德格爾事實上認為,康德思想的發源地,既是先驗的也是超驗的,先驗與超驗,可以合起來說。在“形而上學的出發點”的意義上,“先驗”與“超驗”是一回事兒!他沒有明明白白地這么說,但我明明白白地讀出了他的這個意思。這就是以下我要著重說明的,他把康德扔掉的東西當成思想寶貝又撿了回來。
海德格爾在書的導言開篇就有以上的意思:“基礎本體論不過就是關于人的Dasein 的形而上學,因此形而上學才是可能的。”①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Gallimard,1953.p.57.雖然海氏文本中的Dasein 具有不可譯性,但就像以上茨威格所謂“我愛你,與你無關”的這種自相矛盾,我還是不得不用漢語把Dasein 顯示出來,我選定“此在”。 海氏緊接著說“此在”遠離一切人類學,他此處沒提胡塞爾,但顯然這種遠離只有借助于現象學還原方法才有可能——人仍舊存在著,但描述人的方式徹底改變了,如此而已。
形而上學(métaphysique),顧名思義,是“超越物理學”的無形的學問,目光不要耽擱在邏輯學、倫理學、美學這樣的形而上學分支。不為這些分支而分神,只留下純粹的思想。純粹思想是無界限的,這里返回源頭,還談不上什么學科。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但在海德格爾看來,由于這個傳統本體論是有前提的,并沒有徹底返回基礎。這個前提,他歸結為思考存在本身,而存在已經是現成的存在了,就是復數的beings。這個“存在”本體論還暗含了這樣的設定:它是整體性的、它把確定性或者同一性看成第一原則,它已經蘊含著認識論和體系化哲學傾向,其中的思考方法是定義與證明,它們就是邏各斯展開的含義,盡管“邏各斯”的表面含義是語言與說理。
思考存在,就是思考“什么”,認識論以傳統本體論作為基礎,它們都在以“什么”的方式問答,康德以上四大問題,都保留著傳統形而上學的嚴重痕跡。馬克思說從來的哲學家都是在解釋世界,他所謂“解釋”就是試圖定義世界和人,定義的方法首先就是抽象出事物的本質。這個過程,簡單說就是創造一個概念,給事物(包括人)起一個實質性的名字——所有這些判斷都被視為發現了具有永恒價值的真理,都忽視了它們的出場過程,都遺忘了時間,忘記了它們不過是一次瞬間思想沖動的判斷,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都遺忘了“此在”。
“第一哲學”或純粹思想原本是從“創造”(在海德格爾看來,它和康德的“先驗想象力”與“藝術”是等值的)或者“原創”起步的,它并非“第一原因”,而寧可說,它是“自因”,但“自因”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實際上處于因果鏈條之外了。亞里士多德從來就沒說清楚“第一原因”,它等于被擱置了、沒被思考。他直接從“存在”出發,但這等于從被創造物出發了,從此就只能說出重復的話。
海德格爾不贊成超越感性的形而上學,他認為感性本身也可以是形而上學的,關鍵是目光,而非人為的形而上學界限。在他看來,康德這個著名提問的性質不是認識論的,而是本體論的:“先驗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把本體論的可能性引向這樣的問題:‘先驗綜合判斷是如何可能的?’闡明了這個問題,也就會理解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形式下,所實施的建立形而上學的基礎工作。”②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73.“判斷”表面是要解決認識論問題,其實是解決認識來源即本體論問題。作為概念,“先驗”與“綜合”單獨拿出來,其含義都是已知的,但兩者嫁接在一起,“先驗綜合”形成一種被創造出來的新意思,作為判斷,它的性質是“自因的”、創造性的,因此也是本體論的。在被創造出來的第一瞬間,它不是一個“已經”,從前沒有,因此起個名字叫它“先驗”。這個“先驗”在尚未被重復的情況下,就不是一個復數的beings,因此作為“自因”的“本體”,“先驗”不是存在而是此在,這就是海德格爾閱讀康德的方式。“此在”是不可置換的,它抗拒分類,所以“此在”是先驗的,這兩個詞語都不意味著“已經”,也就是說,不是經驗的。
海德格爾說:“本體論的認識,也就是說,先驗的‘綜合’就是康德全部批判的真實的理性。”③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75.這就區分了兩個理性,一個是康德批判的獨斷論的所謂純粹理性,就是被海德格爾稱為“存在”的概念,另一個是“先驗綜合判斷”,如上所述,這實際上被海德格爾理解為“此在”,這是一種新的理性,它被哲學史遺忘了。
“此在”的“自因性”其實就是原創性,它顯示為如此這般或者那般地建立一種嶄新的精神連線,例如“先驗綜合”,或者“直觀與概念”,或者胡塞爾的“理性直觀”,“此在”專門指其中的“第一次”,它是涌現的、突如其來的,一旦被重復、可置換,就具有了可譯性,也就化為了形形色色的存在,這樣“此在”就失蹤了。“此在”是自相矛盾的,“此”含有“彼”,就像作為判斷,“先驗”一出生就與“綜合”建立起關系,就像圓形與方形嫁接為“圓方”,就像孤單的愛沒有意義,得說“我愛你。”但是,只有第一次建立聯系的思考行為,具有原創性,只要重復就意味著平庸或者不真實,因為重復首先假定了置換是可能的,理解或者解釋是可能的,但從“此在”的目光來看,置換或者可譯性實質上都不徹底可能,就像dasein 這個德文詞一樣。
海德格爾強行把“先驗綜合判斷”讀成“此在”,康德肯定不同意,但從以上看出,海氏不是在毫無根據地胡說,他在一個新思想平臺上說話。康德的判斷平臺屬于亞里士多德傳統,即主詞+謂詞=知識。無論分析判斷還是綜合判斷,都是如此。這里的精神連線,以形式邏輯作為基礎。但是,一旦把康德的“先驗綜合判斷”讀成“此在”,就不再屬于“主詞+謂詞=知識”的模式。這種轉換或者新的思想平臺,通俗地說,它相當于在顯示而不是在表達,比如“下雨了”——表面看是判斷,其實是顯示或者描述,它只有降臨而無須判斷從哪里降臨,因為人們絕少說:“天下雨了”。“天”莫須有,加上“天”,乃多此一舉。“下雨了”與“主詞+謂詞=知識”的模式,沒有關系,它以降臨的方式發生,這就是“此在”。這里不需要主詞和人稱代詞,不是人類學。這種無我之境等于把思想之路堵死后,殘留的思想感情。因此,海德格爾把形而上學的思和詩同等看待。王維的詩句中有“月出驚山鳥”和“春去花還在”,和人無關,并因此有點恐怖。“此在”不排除沒有人情味的殘酷,不同于人道主義。
在海德格爾看來,“先驗綜合判斷”的要害,在于它顯示出不可置換性,這與分析判斷(例如可以用“單身漢”置換“未婚男人”)的比較中特別明顯,“先驗綜合判斷”的句子加進了某種絕對陌生的、推不出來的含義,因此是在創造。所謂綜合,就是建立關系。所謂先驗綜合,就是說這種關系是以先驗方式突然建立起來的,與曾經的經驗無關。康德說:“不是研究對象的知識,而是研究認識對象的方式,后一種情形就是我所謂先驗,這種先驗的方式是可能的。”①轉引自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75-76.很難說這種先驗與胡塞爾現象學無關,就像薩特說的,我們不是看一所房子而是以某種方式看這所房子。我們不是意識到這所房子,而是意識到關于這所房子的意識,因此才有厭惡的問題。也就是說,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的哲學都與康德的“先驗”概念有關,在這個意義上這確實是一場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它以降臨的方式涌現出與外部經驗沒有直接關系的某些新鮮感受,它不是存在論而是先驗論。海德格爾和康德在“先驗”問題上的差別,在于他認為可以用“此在”取代“先驗”,但“此在”本身不是康德所謂認識事物的先驗前提,海德格爾否定任何在遭遇或者奇遇之前的理解,否定前理解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e la compréhension préalable de l’être②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76.)。但這只是改造了康德而沒有徹底否定康德的“先驗”。也就是說,我們確實是以某種方式去意識事物,但是康德用某種固定的或者僵化的說法界定這種方式(“先驗綜合判斷”),而海德格爾不說“先驗綜合判斷”,甚至也不說“意向性”,而是使用了不可譯的、自相矛盾的“此在”。
前面說過“先驗”與“超驗”的統一問題,海德格爾就是這樣理解康德哲學的關鍵詞。他寫道:“提出本體論的可能性問題,就等于在詢問可能性本身,即詢問理解此在①此處,法文譯本使用的是與“l’étant”有本質區別的“l’être”,國內學界之前的譯法,把前者譯成“存在者”,后者譯成“存在”,但在漢語理解的語感中,很難將“存在”與“存在者”區別開,“存在”自然就已經是“存在者”,要費很多口舌才能勉強區分。實際上,海德格爾做這種區別,即所謂“本體論的差異”的重點,就是將所謂“本體論”理解為“差異”本身,而這種差異就在于將“l’être”理解為“être-le-la”,即“此在”,它絕非指黑格爾“對立統一”框架內的“差異”。的這種超驗(transcendance)本質問題,它等于從先驗的(transcendantal)目光去思考。”②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76.也就是說,對“超驗”做“先驗”的理解,是可能的,反之亦然。海德格爾認為康德找到了重建本體論的一條新途徑,他將這個新途徑,理解為“此在”。
二、把康德的“先驗”轉換到“此在”的思想平臺
叔本華認為康德最大功績在于區別了“現象”與“自在之物”,他要更新康德的“自在之物”,從中得出“唯意志論”,而海德格爾認為康德的最大功績,在于區別了“先驗”與“經驗”,他想根本扭轉康德的“先驗”方向,從中得出“此在”現象學。③在此,海德格爾與叔本華的近似之處,是值得探討的,但由于轉移了這里的問題視域,暫不做專門討論。“先驗”的要害,在于一個“先”字,這里又遭遇自相矛盾,“先”就是不以經驗作為思考的前提,乃至思考之時可以擱置一切前提,這種徹底性就是胡塞爾現象學還原的真諦。但在康德那里,雖然“先驗”不以經驗作為自身成立的前提,但“先驗”卻在事實上成了經驗對象的前提。這種事先性成為胡塞爾-海德格爾現象學不贊同的“理論的態度”,他倆覺得康德陷入了一種壞的或消極的自相矛盾。
康德認為,先驗的真理先于一切經驗的真理,先驗使經驗得以可能。對康德的這種態度做一種微妙的改造,就變成胡塞爾-海德格爾的態度:經驗屬于自然態度,先驗屬于現象學或哲學態度。
海德格爾的“此在”現象學與康德的先驗哲學另一個根本沖突,在于對智力的理解。康德認為智力就是對概念的理解能力,哲學就是思考廣義上的概念的能力,甚至“直觀”和“趣味”都是變相的概念。但是,海德格爾把形而上學問題還原為思想,認為思想早于形而上學。思就是詩,他這樣說的要害并非去歌頌詩歌多么偉大,而是肯定一種積極的自相矛盾,也就是非概念思維,類似“非感性的感性”或“具象的概念”這些說法,而康德極力擺脫“二律背反”,他認為自相矛盾是消極的,是理性的丑聞。
與上述區別相對應,康德把哲學理解為以思考和理解概念為基礎的判斷力,不僅“先驗綜合判斷”,即使在趣味-美的領域,他所謂“判斷力批判”本身,仍舊止于實質是智力的判斷力。但是,海德格爾把“判斷力”置于上述新的理解平臺,他把“判斷力”消解為一種現象學描述,把思想之“思”與詩歌之“詩”聯系起來,還描述“操心”“焦慮”“無聊”“死亡”,這些都是廣義上的“此在”情景,是具有哲學意義的在場的時間與空間。這種區別,在語感上就體會得到,康德給“先驗綜合判斷”列舉的典型例子,是“5+7=12”—— 這個表達式之所以是判斷,它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它可重復或再現,無論多少次重復都自身同一,無關時空,它的真理性永遠成立。但是,海德格爾以上類似“焦慮”的描述,發生在當下時空之中,是在場的情景。所謂“此在”就是近,它既可以“近”而遠,比如恐懼死亡,也可以遠而近,例如深度無聊感。這些場景還連接著例外或偶然性,它們是突然降臨的,也就是創造性。以上,從“判斷力”到“描述”,其中有德里達的“解構”,解構了哲學與藝術之間的界限。
與以上區別相對應,在康德那里,思想(及其概念)與直觀(及其感官內容)以先驗的方式綜合為認識對象(即作為現象的存在),而在海德格爾這里,所謂“綜合”絕不僅僅限于概念與直觀之間的結合,而是思想的自由連接形式,就是“和”、去建立關系。
與以上區別相對應,在康德那里,“現象”概念,無論狹義的還是廣義的,都指“對象”①海德格爾在這里引用了康德的原話,康德寫道:“物自身并非指另一個對象,而是指以另一種再現關系,去關注同一個對象。”轉引自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93.語境下的事物自身,與康德的理解不同,在海德格爾所理解的現象學語境下,現象就是“此在”的純粹顯現,這已經是事物的本質,不存在現象背后的本質。
與以上區別相對應,在康德那里,感性和理解力(所謂“知性”)是分開講的,似乎它們在時間上是兩個不同的階段,通過感性直觀,我們獲得了認識對象,通過概念,去理解對象。而在海德格爾這里,感性和理解是同時發生的,它們顯示為此時此刻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以上描述過的那些貌似感性的非感性,其中也包括情緒化的因素,并不完全屬于智力。簡潔說,在康德那里不同時發生的事情,海德格爾認為是同時發生的,而“同時”就意味著自相矛盾。
康德的自相矛盾還在于,一方面,他重新發現了時間,發現了創造思想與時間之間的緣起關系。另一方面,他構造起來的哲學體系,卻是一切都從“現成的”出發,他訴諸一種事先性,其中的因果關系,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思想的可能性,在他以“批判”的姿態出現之前,實際上他已經知道了,這就像法國新小說家西蒙對《紅與黑》作者司湯達的批評,于連得死這一事實,作者在寫小說的第一句話時,就已經想好了,或者黑格爾對康德的批評,在河岸上練習游泳是不行的,想要真會游泳得下水。我這里補充黑格爾的話,下水后才有時間問題,否則無論提到多少次時間,也沒有時間,因為一切都是對于已經構造好了的思想的重復。就像海德格爾對康德形而上學的總結:“對存在的認識,只有在對于存在本體論結構的某種預先認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②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98.這里的“預先”(préalable)其實就是先驗,它暴露出在“先驗”概念上,他與康德沖突的關鍵,在于“先驗”究竟是某種預先,還是即刻正在發生的情景(“此在”)。
既然康德有如上的自相矛盾,那么海德格爾有責任從中找到寶貝,以便服務于他自己的思想。他要發掘康德的心理起源,它是未知的、不確定的,不屬于“已知”的康德認識論。從“已知”追溯到“未知”,從有意識追溯到無意識的意味。但是,海德格爾不說“無意識”,而說“先驗的心理學”(psychologie transcendantal③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101.)——這里揭去認識或知識的面紗,返回思想的真諦即“起源”問題,那么可以說它涉及傳統哲學所謂“本體論”,它是“自因的”,但這等于說它是無因的,是陌生的而且莫名其妙地涌現出來。當然,康德哲學從來沒有朝這個方向走得如此之遠,這個“此在”已經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有關。
在這里,哲學批判能力體現為從看似不一樣的概念中,發現相似性。例如,康德說“先驗綜合判斷”,海德格爾從中發現“先驗心理學”,并說它“使本體論的綜合成為可能,這就是康德認為‘批判’就是‘研究我們內在本性’的緣由,揭示人類的此在‘是哲學家的義務’。”④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101.海德格爾繼續寫道:“我們在這塊土壤上重新發現形而上學,在此形而上學扎根于人性中的熱情。”⑤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101.熱情是“自因的”,而“此在”也是熱情——這是他真正想說的話。
康德不直接陳述“熱情”。對于熱情,可區分為“經驗”與“先驗”兩種說法。經驗的說法,認為熱情來自外界的誘因。先驗說法,熱情是自己產生自己的,并非來自外部世界的某種誘因。后一種說法雖然有點晦澀,但它也屬于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的一部分。
海德格爾先把“先驗綜合判斷”改造成“本體論的綜合”,然后寫道:“這個問題,就是人的此在及其有限性有能力在存在之前并超出存在……”①Martin Heidegger, Kant et le problème de la métaphysique,p.102.他十分重視人的限度或界限,康德的說法是人的可能性,但海德格爾真正想描述的,其實是人的孤獨或不可交流性,之后現象學所謂“他者”問題,也初露端倪,康德并沒有朝這個方向設想,即沒有設想本體論的“本體”不指向“存在自身”(或者變相的說法“起源”“事物本身”“人本身”等),而是指“差異”或者德里達所謂“延異”,它意味著去建立非同一性的關系,它先于“存在”的概念。延伸這種區別,本體論的表達心思,也不再是“主詞+謂詞=知識”,因為這樣的表達式把系詞“是”理解為“存在”,在如此的理解形式中,思想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了,或者說思想是從“結束”開始的,也就是同義反復。替換這種傳統本體論的表達式,就是海德格爾和德里達的“差異”思維,其中有非感性的感性,或非理性的理性,它用“描述”置換“證明”,用“詩”置換“思”。
孤獨就是自身顯現,它與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并行不悖,但海德格爾、勒維納斯、德里達揭示了其中的“差異”思維。自身顯現與他者之間形成陌生的、不同于存在的關系,也顯露了人的界限。
三、現象是再現,而再現是差異的再現
海德格爾更看重《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驗感性論”,而不是“先驗邏輯”。先驗感性論——全部思想都要重新奠基在對于對象的直覺之上,思想的作用只是闡明,確定直覺可以通達的路徑。如果廣義上的認識主要是直覺的,如果其他與對象關聯的方式都要服從于直覺,這就意味著先驗綜合認識,甚至本體論認識,主要是直覺認識。“在某種意義上,直覺是《批判》的中心問題,是決定性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胡塞爾作為現象學研究的奠基人,完全不依賴康德,重新發現了認識,尤其是哲學認識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直覺作為現象學的基礎,正是這一點惹起了時下哲學的抵制。”②Martin Heidegger, Interprétation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de Kant》, Gallimard,1982,p.95.
特別重要的是,在海德格爾看來正是直覺使得本體論認識成為可能,而直覺已經意味著時間,或者說時間是一種直覺,這種看法令人激動,卻又十分困難。時間現象的根源要追溯到直覺。
如果直覺具有人格,會說話,直覺說:“我要說……”。直覺要說什么呢?直覺要找自己的家族,與直覺相似的,還有知覺(perception)、感受(sensation)、再現(repré-sentation)或者認識。它們意味著與直覺關聯的舉止行為,不僅是純粹觀念性的,也包括生理因素。針對某某的直覺,某種活靈活現的、有血有肉的東西給予我們——被給予,直接相遇——誕生、緣起。康德寫道:“直觀與概念構成了全部認識元素,以至于沒有某種方式的直觀相應的概念,和沒有某種方式的概念相應的直觀,都不可能形成認識……沒有感受性,對象就不能給予我們;沒有理解力,就無法形成思想。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的。”③轉引自Martin Heidegger,Interprétation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de Kant》,p.99.這也就是說,由于有了理解能力,就使得直覺被給予的東西具有智性,而智性不僅在于給雜多的現象命名,即用所發明的概念使感性雜多統一起來,還在于概念只能顯現在感性事物之中,它是世界的某種特定場景。它們總是可以情節化甚至小說化的,例如薩特在《惡心》中這樣描寫:“半小時以來,我就一直避而不看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④〔法〕讓-保羅-薩特:《薩特精選集》,沈志明編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4頁。這里的它就是啤酒杯本身或事物本身,由于缺少對于事物本身的理解,只是從不同側面直觀到感性雜多,從而缺少智性或無法解釋,此刻涌上來的就只是某種情緒,例如恐懼。當我們用概念給事物定性時,會感到心安理得,因為事物獲得了解釋,情緒就趨于平穩了。在這里,概念是具象化了的,概念與具象并非在時間上分開的兩個過程,它們是同時發生的,是感性與理解的融合(union)。如果沒有理解,事件就顯得古怪陌生,而當事人就成為局外人。比如,如果不懂得足球游戲規則,就只能感到一只皮球在不停地接觸不同人的下體,從而會覺得索然無味。這種理解甚至不僅僅是康德所謂“認識”,它同時還是趣味,可以寫成小說,成為創造出來的藝術生活。
如果沒有直觀,思考就是純粹形式化的概念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內容。直觀是思考的基礎,思考的作用僅在于確立直觀的性質。感性是元素,理解是科學,是邏輯。
海德格爾指出,感性和理解是人類認識的兩個“基礎”,兩者有共同的起源——再現(représentation)。“康德說直觀與思想都是再現某一事物。”①Martin Heidegger, Interprétation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de Kant》,p.100.再現,就是說又一次。沒有所謂絕對起點,任何“起源”其實都已經是再現。進一步說,再現意味著重復,重復意味著距離與間隔,那么絕對的直接性是不可能的。距離與間隔已經意味著以迂回的方式進入,也就是間接性,它永遠推遲了初衷或“原始”意向對象的“如實”實現,它們實現了別的,而這些別的,是無法事先預判的,偶然性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按照上述海德格爾式的解釋,康德創造了理解哲學的一個拐點:傳統形而上學都是“直接性的哲學”,因為它們都忽視了“再現”過程中所誕生的差異,將這些差異抹平了,視差異為永恒的同一性,即巴門尼德首次提出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所謂“直接性的哲學”,例如萊布尼茨的唯理論簡單地將感性歸結為理性,洛克和休謨簡單地將理性歸結為感覺印象,或者唯心論認為精神是第一性的,而唯物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
直覺與思維(思想、概念),或者感性與理性、外感官(五官)的被動性與內感官(心靈)的自發性——它們都只是再現的不同方式、途徑、渠道,它們彼此有著程度上的差異,又融合在一起,只是為了方便分析,我們才將它們羅列起來,但是,將它們分門別類是十分重要的,這可以使我們保持清晰的頭腦,深入人類思維的本性。
以上,關于直覺與思維的共同起源即“再現”的問題,是海德格爾根據康德著作分析出來的,“顯然康德并沒有明確提出要從這一共同起源出發,處理這兩個基礎的起源問題……”,②Martin Heidegger, Interprétation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de Kant》,p.102.質言之,康德哲學還不是一種關于差異的哲學,就此而言,康德不屬于后現代哲學家。那么,康德就沒有自覺意識到時間問題的再思考,可以顛覆整個傳統哲學。海德格爾將《純粹理性批判》中的時間問題,視為這部著作的中心,因為沒有時間因素的介入,差異問題就無從談起。因此,《存在與時間》更精準的理解,應該是“差異與時間”,它超越了,或者說置換了康德的思想平臺。
康德意識到,不能只是從思想出發,從概念到概念,這樣的認識是沒有新意的,要有多出概念的直覺,這得使“先驗綜合判斷”成為可能。但是,在這個判斷中,究竟是先驗為主還是直覺為主呢?康德說融合,不可分割。他要用先驗抵制休謨的徹底經驗論立場,又得用直覺抵制理性的獨斷論。從消極方面說,康德陷入某種兩難境地,甚至是自相矛盾,也就是不徹底、不直接,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立場。從積極方面說,這種悖謬的判斷本身意味著康德的創新。所謂悖謬,在這里意味著“起源”構成的復雜性,其結構諸因素是沖突的,因為先驗意味著不依賴一切外來經驗,而直覺卻離不開經驗,現在將先驗與經驗撮合在一起,分析與綜合的融合形成一種新型判斷形式,這不再是笛卡爾式的清楚明白的觀念。“起源”問題上的折中,意味著起源的復雜。一方面,康德的哲學是先驗哲學,不是經驗論;另一方面,康德如何能夠說服我們直覺只能止步于形式而不包含經驗內容呢?沒有經驗內容的“直覺”,相當于把“直覺”取消了,康德并沒有發明“理性直覺”這樣的說法,盡管“先驗綜合判斷”已經蘊含了這樣的苗頭。
在康德那里,直覺究竟偏向于形式還是偏向于經驗內容?他時而向形式偏轉,這時他批評經驗論。時而向經驗內容偏轉,這時他批評獨斷論(“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的”,離開經驗說“內容”是不可能的),具體如何偏轉,取決于臨時需要。但是“臨時”,這思想情景連同純粹偶然性一道,都是康德極力回避的。他所忽視的這些,恰恰是海德格爾想重新拾起來的,就像德勒茲這樣說尼采:哲學家就是從地上拾起一支箭,然后把它射向別的方向。
經驗的邊緣域(horizon,這是海德格爾從胡塞爾現象學中借用的概念),或者說綜合判斷,已經趨向于離開“沒有內容”的思想(概念),但康德馬上說需要一種理解的模式約束雜多經驗的肆意狂野,需要先驗綜合判斷。經驗的直觀需要先驗的直觀加以統籌,這種統籌使得綜合判斷得以可能。這使得先驗綜合判斷已經不是“純粹理性”了,因為純粹理性中的“純粹”意味著完全先驗,脫離經驗——這種情形,在“先驗綜合判斷”中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環節在于,作為先驗哲學的決策機制,“先驗綜合判斷”的要害是超越純粹概念,超越純粹概念思維。關鍵在于,這樣的超越是如何可能的。這需要在“先驗感性輪”中解釋,從而實現為形而上學重新奠基。
經驗直覺止步于感性材料,比如粉筆,受制于外感官,它是有對象的感覺(sensation),可以產生認識。但是,“感覺”寬泛不清,有時還作為主觀感受,也就是感情——快樂與痛苦等,與其說它連接某個具體對象,不如說是純粹主觀感受,并沒有實現認識,不屬于認識論范疇。
康德寫道:“經驗直覺的不確定對象,叫作現象。”①轉 引 自Martin Heidegger, Interprétation phénoménologique de la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de Kant》,p.102.現象顯現出來,直接被給予我們。古代本體論直接在現象與物本身之間建立統一關系,認為現象世界是本體世界的顯現,而在康德看來,這種統一無法建立,現象不同于物本身。叔本華曾說,康德哲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區分了現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物本身就是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還沒有被思考,例如上帝存在。如果懷疑上帝存在,則相當于無神論的思考。思想是以假說的方式存在的,例如提出上帝不存在。
于是,理解康德的一個關鍵之處在于,他認為古代哲學沒有區分現象和物自身,其所認為屬于“物自身”的,其實也只是現象,由此陷入無休止的爭吵。為了澄清與糾正誤解,本體論問題要通過先驗哲學的認識論途徑得以解決,而先驗認識論只能解決古代本體論中屬于現象世界的問題,不能解決古代本體論中關于“上帝存在”“自由意志”等屬于自在之物或物自身的問題。在這里,海德格爾發現康德對無限、抽象、普遍性觀念,持有某種十分謹慎的態度。“先驗綜合判斷”中的直觀,是有限直觀,不是自在之物的觀念,不是附屬于這類觀念之上的普遍必然性。
但是,海德格爾指出,康德有時也把事物本身稱為現象,這種含混為日后理解康德哲學制造了混亂。它是不確定的嗎?在康德哲學中那些被邊緣化了的術語,反而成為超越康德思想的突破口,例如上述的“有限”和這里的“不確定性”。有限已經意味著界限,它回答認識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不僅被康德用來抵抗獨斷論,甚至指向“批判哲學”自身也含有某種獨斷,就像叔本華批評康德哲學的12個先驗范疇圖式就是一種獨斷。為什么一定是12 個呢?原來康德有將概念一一對稱起來的癖好。而德里達在《繪畫中的真相》中則批評康德對于12 范疇的安排順序,并沒有嚴格按照先驗邏輯進行。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量的范疇被放置在質的范疇之前,而在《判斷力批判》中,則顛倒過來,質在前,量在后了。那么,這種邏輯安排本身就沒有遵守一定如此的邏輯,它取決于康德在討論審美趣味時的臨時需要。但康德思想主流,輕視臨時性和當下時刻的重要性,即使它們在構造康德哲學體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體來看,康德排斥“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只屬于經驗的直觀,它意味著還沒有發生思想,思想不能以不確定的、亦此亦彼的悖謬方式發生,康德正是如此劃定了認識的邊界或可能知道的界限,而他所處時代的物理學-數學只相信確定性才是科學標志,這和同時代的啟蒙理想是一致的。康德相信不確定的現象世界是確定的,如此才有科學。當然他使用的不是物理學與數學公式,而是先驗綜合判斷,使看起來如此混雜的世界井然有序,人類就安心自得了。
經驗直觀是有限直觀。比如一支粉筆,有顏色,有長寬高。但是,即使在這樣的經驗直觀中,“這里”“之下”“現在”這樣的字眼,也不是從外感官中自發產生的,它們屬于對事物自身的規定,是感覺中多出感覺的思想。止步于感性雜多,是沒有思想的。前與后,位置關系,這些抽象思維,不可能從外感官直接獲得。但是,即使原始人,也從來不是毫無秩序地觀察世界,其中的秩序來自給感性材料建立“關系”。關系本身不是感覺而是某種抽象能力,康德認為這種精神能力是自發的,是人類原本就有的卓越天性,哲學術語叫作“先驗”——某種不依賴外部經驗而獲得抽象感覺的能力。當這些詞語抽象程度足夠高時,就是哲學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