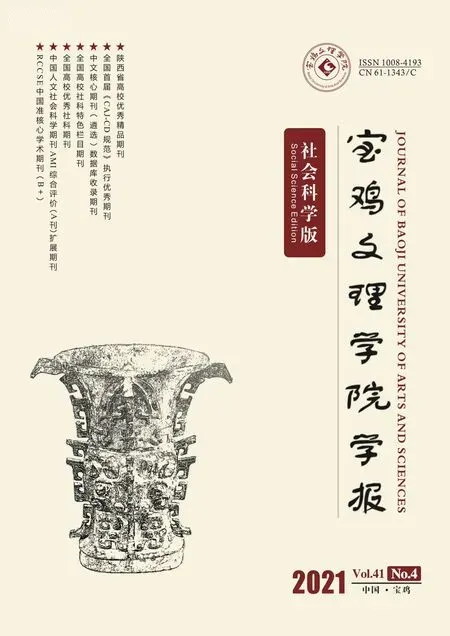嵇康對“君子”的解構與建設*
張盈盈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 哲學與文化所,安徽 合肥 230053)
嵇康生長在魏晉時期的大環境中,他的思想與傳統儒家差異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異端”。他激烈地抨擊“名教”,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魯迅稱嵇康表面抨擊禮教,實際上是把禮教當“寶貝”。在嵇康詩文中,提到“君子”大約三十余處,體現出其對儒家倫理道德真諦的堅持以及對“君子”的重視。在《與呂長悌絕交書》中,他與呂長悌絕交時說“君子絕交不出丑言,從此別矣”[1](P230),這里的“君子”是指代他自己;他在《家誡》中以“君子”期許子女,可見他是用生命力行君子之道。魏晉時期的學風雖然崇尚道家,但是嵇康與“儒家”有著無法割舍的關系。《晉書·嵇康傳》稱其“家世儒學,少有儁才”,《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嵇紹《趙至敘》載,趙至在四十歲那年“入太學,時先君(即嵇康)在學寫石經古文”。此外,在嵇康入獄期間,“太學生三千”曾上書為嵇康求情。在嵇康成學的過程中,他并不是“守一經”“專一家”,而是不墨守成規,不拘泥于儒家與道家。因此,嵇康的君子人格的內涵也呈現出儒道融合型態,但萬變不離其“儒”。
一、以“真”駁“偽”
“君子”一詞由來已久,君子人格一直是儒者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模式發展到魏晉時期,受魏晉崇尚自然風氣的影響,在人格型態上有變化,但其核心內涵并沒有因此而發生改變。這一點突出的表現在嵇康的君子觀中。《晉書·嵇康傳》載嵇康“家世儒學”,但是他對君子詮釋的路徑很特別。嵇康說:“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1](P402)在這句話中,嵇康對“君子”的內涵做了兩個規定:一是“心無措乎是非”,二是“行不違乎道”。在《釋私論》中他將“君子”與“小人”對比:“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而對于“小人”則以“匿情為非”。所謂“匿”,就是隱藏、隱瞞,也就是偽匿、不真。君子高貴的品質則是“貴乎亮達”,所謂“亮達”就是光明磊落,率真而為。可見,在嵇康的視野中,“君子”最突出的本質內涵是“真”。這個本質體現在他對“公”與“私”之辨的討論中。
公和私則是指人對待自己思想感情的態度是公開還是隱匿。嵇康為了說明這種復雜的關系,舉了一個“第五倫”的例子。第五倫是東漢士人,其身居高位,以清正廉潔著稱,敢于公開自己內心深處的思想雜念。《后漢書·第五倫傳》載,有人問第五倫是否有私心?第五倫回答說,他兄弟的孩子生病,他一夜“十往”,但是“退而安寢”。自己的孩子生病了,“雖不省視而競夕不眠”,雖然沒有去看,但是徹夜未眠。第五倫說也許這就是私心,但嵇康認為,“私”是指隱匿,第五倫毫不避諱地講出來,是屬于“無私”。對自己兄弟孩子探視而不關心是“是非”問題,公私與是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說:“故論公私者,雖云志道存善,(心)無兇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1](P403)心中雖然懷有善念,但是隱而不宣,這也叫作“私”。情欲雖有不善,但能無所隱匿,這也叫作“公”。所謂“公”就是指公開內心的真實感情,坦坦蕩蕩,光明磊落。“私”是指隱匿內心真實的情感和想法,即陰奉陽違之徒。不管一個人的思想、念頭如何,只要不隱瞞自己的真實思想和情感,這都叫作“無私”。有私無私、有措無措是從本質上區分人善惡的標準。
“公私之辨”在先秦時期就被廣泛討論。“公”與“私”的關系涉及政治、社會、倫理等領域。自古以來“崇公抑私”是主流觀點,在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崇“公”的思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戰國之前,“公”代表統治者,“私”代表被統治者或者人民。如“天子”“封建君主”為“公”。“公”是古代圣王、君主遵循的準則。“國家”的概念出現后,“公”與“國家”“天下”聯系起來,這使得“公”的概念變得更為復雜。從倫理上講,“公”與“私”涉及道德領域的區分。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立公滅私”的觀點,“私”帶有負面的色彩。《禮記·孔子閑居》記載,子夏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致謂三無私。”[2](P1277)同時,孔子以《詩經》中的描述進一步頌揚了禹、湯、文王奉行“三無私”的德行,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作為圣王君主的追求。《呂氏春秋·貴公》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3](P20)若要社會安定與百姓安居樂業,只有公私的界限分明,“天下為公”、秉持為公是必走之路,這樣會達到理想的治理狀態。可以看出,傳統“公私之辨”關系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公私的討論,其主流的價值必然以公為準,一般我們所謂的“公”,都被賦予了正當性,與之相對的“私”是要被抑制的,因其關乎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核心問題。
然而,嵇康的公私觀,顯然沒有按照傳統的路子來。在嵇康的倫理序列當中,“公私”比“是非”更為重要。他說:“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1](P403)事理也有好像錯了卻并不錯,仿佛正確卻并不正確的現象,故應仔細加以考察。其實,公私之辨即是真偽之辨。所謂君子“無措”為真,為公。“匿情”為“偽”,為私。可以說,在嵇康看來,君子最核心的本質是“真”。
那么嵇康為什么提“真”呢?因為他所處時代充斥著虛偽。這種虛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當權者的虛偽。司馬氏集團利用原本引導人們向善的道德名目,鏟除異己,欺壓百姓。陰奉陽違、口是心非之士太多。司馬懿以服膺儒家名教著稱,大倡“以孝治天下”。“高平陵政變”大批名士被誅三族,司馬氏集團為了能夠把權力牢牢握在手中,以名教的借口戕害異己,即便手上沾滿鮮血,還要振振有詞。司馬氏廢掉魏帝曹芳的罪名為“恭孝日虧,悖慢滋甚”,曹髦被殺的罪名為“不能事母,悖逆不道”。司馬氏集團所標榜的“名教”顯然是虛偽至極的,許多有識之士十分痛恨和厭惡。嵇康身為曹魏宗室的女婿,更是猛烈抨擊司馬氏集團的虛偽嘴臉。另一方面,嵇康所針對的“偽”是名教本身異化之偽。名教所倡導的倫理綱常與君子人格內涵是重合的。名教作為道德倫理規范的代名詞,其內涵學界已廣泛討論。陳寅恪認為,“名教即以名為教,即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4](P182)余英時認為“名教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其中君臣、父子兩倫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礎”[5](P358)。龐樸認為,“以名為教”是把符合封建統治階層利益的政治觀念、道德規范等,立為名分、名目、名節并以此進行教化。[6](P391)名教的內涵由漢武帝時期的“三綱五常”發展到東漢章帝時的“三綱六紀”。所謂“三綱”,即君臣、父子、夫婦的倫理關系,“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白虎通》曰:“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舊目張也。”[7](P375)很顯然,“三綱六紀”在“心性”的角度上更進一步豐富了“名”的內涵。以家族血緣關系為核心的“三綱六紀”,將人倫關系規范得一清二楚。諸父、兄弟、族人、諸舅是以有血緣關系的為主軸,“朋友”這一倫的加入,使得名教的內涵更為廣泛。因為白虎觀會議,把名教綱常用國家法典形式予以欽定,至此,“名教”就無處不在,無處不用。尤其是在漢末察舉清議制施行以來,“名”所產生巨大的號召力,讓人們對其趨之若鶩,紛紛追求其“名”。因為擁有“名”的人可以飛黃騰達、名利雙收,可升官、可發財。社會上產生了一批所謂的“名士”,這一類名士并不是按照名教的道德修養獲得的,而是通過欺世盜名。例如趙宣,“葬其親而不閉遂,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鄉邑稱孝”,于是成了“名士”,但是他這二十余年的服孝當中,卻生了五個兒子。這些沽名釣譽之徒并不在少數,究其本質,是因為名教是獲得功名利祿的工具,名教變成了仕途的敲門磚。
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君子不是“真”君子,而是“偽”君子,以君子為標桿的名士由原本的“經明修義”到“刻情修容”,總之就是一字:“偽”!名教大廈隨著東漢政權的崩潰倒塌了。因此,漢魏之際選拔人才的標準變得多元化。儒家以名教標準、道德準繩的名聲名節在此時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曹操“唯才是舉”,即一個人不仁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會被委以重用。這說明此時用人時在乎人的才智,不注重德行。漢魏之際的動蕩不安,確實需要“有事尚功能”的準則,然而這對人們追求的人格模式也會造成影響。通常,我們會把嵇康所說的“真”與儒家所說的“誠”聯系起來,二者有重合的內涵,但是嵇康所說的“真”,與道家所倡導的“自然”更為密切。從人格的角度上講,“真”意味著回歸人的“天性”,就像莊子說的“法天貴真”一樣,這對儒家的君子人格的發展來說是一種補充。
二、以“自然”解構“克己”
“偽君子”、偽名士的產生是時代造成的產物,當然,這也要歸因于儒家君子人格自身的一些機制問題。儒家之君子講“克己”“慎獨”,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雍也》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只要是不合于“禮”的行為,就要“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遵循“禮”的規范從而達到仁與禮的統一是邁向君子的必經之路。這也“意味著禮成了人為的非出于自愿的強制性的命令”[8](P17)。強調道德自律,其關注點在于道德行為是出于自覺的,但并非是自愿的,因此,人們會為了好名聲而造假,從而成為“偽君子”。由此,嵇康視野中的“君子”著重強調了“自然”這一特性。嵇康說:“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鈴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1](P402)“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倫理思想總綱。他對所謂“名教”妄圖把自然人性束縛于偽善的仁義禮教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名教“非養真之要術”,因為要遵守其禮樂教化的規范,就要“克己”。
“克己”是“違其愿”,是反自然的。只有尊重人的內在意愿,才能體現自然原則。在《難自然好學論》中,嵇康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愿,從欲則得自然。”[1](P447)張叔遼作“自然好學論”,嵇康以《難自然好學論》對其進行了反駁。討論“好學”與“不好學”和“克己”有直接的聯系。儒家所講的“君子之學”實際上就是“為己之學”。《論語》中有句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做了進一步發揮,如《荀子·勸學》說:“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對“君子之學”與“小人之學”作出了具體的分野與闡釋。“為學”的傳統,一是古代儒生學以修身、為官的必經之路,也是統治階層因教化、統治所需而倡導的,因此,由先秦到兩漢,“以學為本”已然成傳統,一方面提倡教化,另一方面如從賈誼的《新書·勸學》到徐幹的《中論·治學》,大多站在肯定的立場上肯定“學”。官方提倡“學”主要是為了推崇“教化”作用,這是漢代創立太學制度的宗旨,無論是曹魏、還是司馬氏集團,這一點都沒有改變過。但是嵇康的《難自然好學論》對于“學”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嵇康認為,人類的本性好逸惡勞,世人所謂的“好學”是因為學可“以代稼穡”“學以致榮”,于是才“好而成習”,但是,這其實違反了人的自然本性。世人以“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1](P407),但是嵇康卻認為“六經為蕪穢”“仁義為腐臭”。六經、仁義泛指名教,它的本質是“以抑引為主”,是壓抑人類的工具。如果不對“六經”進行反思而盲目的尊崇,執書摘句、服膺其言并以此為修身法典,必然會造成上文所述之“偽君子”。嵇康所向往的文明時代是“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1](P447),在這種狀態下的社會是“物理全順”,人和社會等萬事萬物處于和諧自如之中。在原始的蒙昧時期,即使統治者未頒布禮儀法治,人們也自得其樂。然而,有了仁義與野蠻之分、有了人的階層和等級之分、有了名分之分后,人類產生了有意為之的一些行為。諸如“始作文墨”“造仁立義”“制為名分”“勸學講文,以神其教”,這對人類的文明以及社會的穩定起到積極的作用,但也是人類給自己造的緊箍咒。嵇康說:“仁義澆淳樸,前識喪道華。留弱喪自然,天真難可和。”[1](P137)“前識”意為“先見”,比別人認識的早,即制禮作樂之人有的“先見之明”。《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王弼解釋為“前識者,前人而識也”。禮樂教化以及倫理道德規范的另一面即是對人的自然性的束縛和異化。嵇康反對束縛人性的名教,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外化于人的存在,過度的強調必然會導致人的自然性情被壓抑。所以他提倡任自然。康中乾認為嵇康的“自然”是其所要追求的“本體”。他說:“自然有兩重含義:一是人自己的自然之性;二是天地的自然本質。”[9](P144)這是嵇康哲學的目標和原則。任自然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它的另一種表達是“越名任心”。此“心”是“心不措乎是非”之“心”。它不以外界的是非毀譽等為念,而是根據自己的“心”的要求“自然而然”地開展其生命活動。這個君子形象的設置,汲取了道家思想資源。所謂“居九夷、游八蠻,浮滄海、踐河源”“泊然純素”“與天道為一指”,就是道家理想人格的形象。當然,所謂“任自然”之“自然”,并不是要追求人的自然屬性或動物性,而是說追求人作為社會性存在之自然性。嵇康說:“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1](P403)在社會生活中常常出現許多是非不辨、善惡不分的情況,是人喪失了自己的自然本質。
嵇康反對“好學”并不是“不學”,而是主張君子要“適性而學”。所謂“適性”就是尊重人的自然之性。在嵇康看來,“好安惡危”“好逸惡勞”是人類的自然性情,為學不是站在人類自然性情的對立面去壓制它,而是要認識到人類的自然本性后再去“為學”。首先,嵇康肯定人的基本生理之“欲”,這是自然之性的一種表現。饑而求食,困而求寢,這是維系人類生命的基本條件,這些皆“生于自然”[1](P296)。人類“循性而動”,沒有摻雜任何智慮的雜念,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人不斷滿足自己欲望的動物性存在,會導致“役身以物,喪智于欲”。可見,嵇康并不同意沒有節制的欲望。“循性”是對“嗜欲”的超越,即是循自然之性,具體的說是稟之自然、“歸之自然”和“任自然以托身”。同時,人不為外物所役,理想的狀態是“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耳、目、口、鼻等感官,依天性有“欲”的要求。心外物為活動對象的分別之“知”,會產生是非、好惡之價值判斷,這種心“知”積存于心,久之形成主觀成見。心有成見,從而有與人對立、競逐之心。嵇康主張“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所以嵇康反駁張叔遼說:“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后學耶,茍計而后動,非自然之應也。”[1](P407)即將“學”所能產生的各種影響和各種好處都考慮進去后再學,這不是“自然本性”的表現,因為這種行為充斥著名利與欲望。為了達到名與利而學,一方面是“克己”,另一方面其心也不“淑亮”。
三、君子以“志”抗“命”
儒家認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命是養成君子人格的必要條件。“知命”指的是什么,簡單地說,“命”就是人力達不到的極限之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人無法超越的客觀限制。對于“命”的追問源于古代人對周圍發生的事件希望知道根本原因。人們不斷在探索,或把這個原因歸之于天,或者歸之于神秘的力量,或是認為是宇宙運動的規律等等,種種解釋就形成了一種命運觀。[10](P147)從命運觀來看,儒家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家認為“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二者對于命運的理解都可以稱之為命定論。君子知命,就是孔子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認為天命決定人事,知命的窮通、極限,但卻不放棄主觀的努力。所謂的“知命”更應該理解為人對命運的感知、體悟后所形成的人生態度。這對嵇康的命運觀影響很大。
嵇康關于“命”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他與阮德如關于宅有無吉兇攝生的二論兩答四篇文章中。阮德如作《宅無吉兇攝生論》,其觀點是“宅無吉兇,惟重攝生”[1](P459),這是他繼承漢代王充自然命定論思想。如王充說:“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11](P124)阮德如認為“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1](P460)。嵇康將阮的觀點歸結為“命有定數,壽有定期,不可改變”[1](P474)的宿命論。嵇康還駁斥阮德如說,既然認為命有定數,壽有限期,那么如何解釋“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1](P473)但是,阮氏并沒有回答出“命何同言”“命何同短”的問題。孔子“慎神怪而不言”,不隨便輕易地認為自己是“知變化之道也”,普通人更不能隨便斷言自己知神而言宅之吉兇。這是一種“妄求”的現象,應該窺探現象背后的深奧之理,對于未知的事物要勇于探索。嵇康的命運觀由兩個基本要素構成:一是時命,一是性命。嵇康曾在《幽憤詩》中說: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即窮困達通是注定的,我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幽憤詩》是嵇康在被長期關押時所作,單從嵇康命運的窮與達的態度來看,似乎很坦然。
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在孔子身上充分顯現。他一生都懷才不遇,帶著學生到處奔波。《荀子·宥坐》記載:“孔子曰: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可見孔子對于逆境有著清醒的認識,賢與不賢是自身決定的,君子注重“求在我者”,即更加注重自身的修為與道德實踐。 嵇康視野中的君子“知命”,體現出一種淡然與從容的風度。在《琴賦》中說“委性命兮任去留”,嵇康似乎并不在意生死壽夭,即“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自得”。他認為人能不能“盡性命”還要看人的主觀努力,也就是說在力命關系上,注重人力。他在《養生論》中說:“似特受異氣,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余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1](P253)嵇康認為,人稟氣而來,是“稟命有限”的,必須“導養以盡其壽”。這是說人的壽命是有限的,既不能長生不死,但也不會只有百年,只要導養得理,就可以達到“自身壽年的最大值”。即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1](P252)人稟受元氣而生,厚度不一,可以通過后天養身以養壽命。嵇康所說的養生,是采取一種無心無意、順其自然的態度。清虛靜泰、養神的各種技術做到了,自然而然就長生了,不需要為了成仙而孜孜追求。
嵇康在命運面前強調人力,并以“志”肯定人力的作用。在《說文解字》中,“志”乃“從心從聲,心之所之也”;《詩序》有“在心為志”。也就是說,“志”是個人自身對自己發展的意向。孔子肯定了“志”的作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同時也規定了“志”的方向:志于道、志于仁。此后千百年,儒家都不曾將“志”拋離。嵇康吸收并改造了儒家之志。嵇康說:“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后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1](P544)“有志”乃是人之為人的基本條件,嵇康對“志”有著強烈的自覺。他說:“志在守樸,素養全真。”[1](P543)可知“守樸”、全真乃是嵇康固守的核心價值。《莊子·性繕》說:“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按照莊子所說,古代所謂得志是指達到快樂自由,今之得志只是貪求逸樂,自我被物欲所蔽。嵇康融合了儒家與道家的思想,認為最高的守志,乃是人生在世,“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1](P297)。這不是簡單的如儒家所說的“立志”“行志”,而是“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裝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1](P544),這是發自于內,不需要外力的規范與強制而有的“志”。在嵇康看來,作為人要有一定的志向才行。嵇康認為行仁義行義要進行思考與斟酌,以不傷害自身的生命為原則。無論個體處于何種境地,是窮還是達,都要守住自己的志向,保持節操,這就是“遂志”的表現。
四、“行不違道”的修養工夫
嵇康追求“游心太玄”的自然境界,但卻掩蓋不住他內心對仁義道德的堅持,因此,他所講的“君子”既有儒家的君子人格以道德實踐為基點的內涵,從內向外而擴充之強調生命的道德內涵和道德意義,又有“行不違道”的“弘道”理想。嵇康說:“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任心無窮,不識于善而后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后為也。”[1](P403)這一切都凝練在他的君子“行不違道”的修養功夫中。從“行不違乎道”可見嵇康的關注點在于君子之“行為”。
君子一生的志向便是以全部的生活活動實現道德價值。“君子”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有仁義之性。道德原是出于人源發于內心善意,且表露于自身行為的道德實踐,它既是自覺的,也是自愿的。袁濟喜稱嵇康是“從本體論上力主人性以澄明為本”[12](P209),他的人生論也是“將人性中最高的道德境界作為人的普遍性加以規定”[12](P209)。他宣揚“非湯武而薄周孔”,號稱以“老莊為師”,在他的詩文中,多次出現對道家“游心太玄”的生命境界的向往。如“逍遙游太清”“飲露食瓊枝”“遠托昆侖墟”“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等等,以詩意的玄化意境將自己對道家境界的追求展現出來。在他的倫理思維中,道家“自然”的境界,是君子行道的出發點。在德行倫理學中,人的行為、情感、道德習慣都是被關注的重點,相對來說,“道德規則”的分量要弱一些。嵇康對君子行道做了細化的闡釋。比如《卜疑》中的“宏達先生”有這樣的特質:“恢廓其度”“常以忠信、篤敬、直道而行”[1](P235),即氣度恢宏,忠誠、憨厚,任何行為都出于真誠,沒有半點虛假。所以他可以“居九夷,游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立足于天地之間。這其中,“忠和佞”“義和利”“誠和偽”“正和邪”之間的對立,選擇前者或后者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嵇康在獄中寫了《家誡》,叮囑其兒子所有的行為都要據“志”而行、與人交往要謹慎,諸如宏行寡言,立身清遠。《家誡》的寫作背景是嵇康入獄,自知不免才作此以誡子,想必句句肺腑,透露出殷殷親子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他對自己一生言行的反思,這便是他心中真實的儒家仁義道德。魯迅據此判斷嵇康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可以看出嵇康對名教和社會禮法的重視。
儒家君子把孝作為實行“仁”的根本,這一點也體現在嵇康的“孝悌觀”中。嵇康的孝悌觀念體現在他對母兄的思念中。他說:“奈何愁兮愁無聊? 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郁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 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 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詠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1](P87)這首詩是嵇康對母兄去世后思念之情的描述,情真意切,聲淚俱呈,深沉地表達了嵇康的悲痛心理。嵇康按照道德規范孝敬母親,尊敬兄長。如他說:“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切。女今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1](P544)在《家誡》中,嵇康的語重心長,體現出他注重教養子孫。在“悌”的問題上,嵇康對呂氏兄弟用心良苦,力勸二者,希望呂氏兄弟不要反目,這就是儒家所倡導的兄弟之間“悌”的表現。當被反咬一口后,嵇康寫了《與呂長悌絕交書》中,表達了對呂巽的氣憤與失望,其結尾說:“古之君子,絕交不出丑言。”[1](P231)他的這些行為真切地體現出傳統儒家思想中注重孝悌人倫的倫理道德觀念, 與其所謂的與自然為親的竹林之游和逍遙物外的行為大相徑庭。此外, 君子“行不違道”的特征還體現在嵇康的音樂修養中。在《聲無哀樂論》中,嵇康雖然以“和聲”的特質否定了儒家傳統樂教的“聲有哀樂”,但是嵇康的樂論卻以儒家音樂的移風易俗為歸結點,認為樂教之本在于“心”,倡導在音樂審美中形成一種倫理人格,這也是他對君子人格的一種詮釋方式。
結語
嵇康的君子論,不是建立起新的道德規范而取代儒家道德標準,而是關注道德動機以及如何行道,這提供了與德行倫理學對話的契點。如亞里士多德視野中的“德行”是來自生活中好的行為習慣,這個“德行”來自靈魂中的“理性”部分,但“行為”必須是出于自愿,而并非強迫。之所以經過“理性”的考量,是因為行為不是“盲從的”,這種道德行為,更加契合人的內心所在。如嵇康說的“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錯,而事與是俱也”[1](P235)。任心即是任自然,這種道德行為的發出,不是在心中思考后去踐行,而是順著內心去行動,其行為剛好與外在的道德規范相符合。這說明君子的道德行為是“隨心”的結果,達到了行為動機與行為理由的統一。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打破了名教的束縛而又不失名教,并且賦予儒家“君子”新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