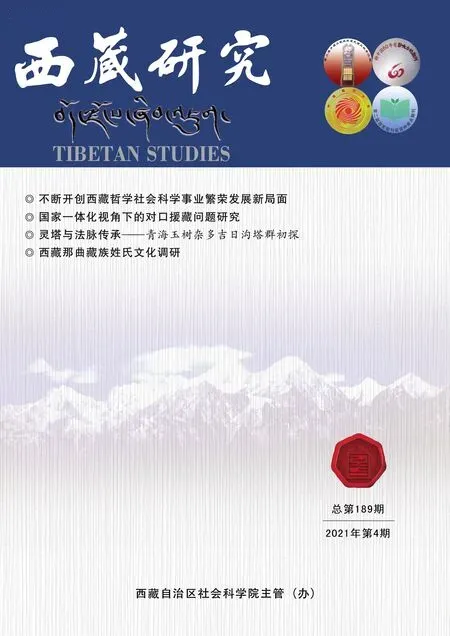日本杏雨書屋藏737號吐蕃天下都僧統愿文研究
——兼談吐蕃僧官制度
陸 離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江蘇 南京 210097)
日本杏雨書屋藏737號文書是一件佛教發愿文,首尾殘缺,收于《敦煌秘笈》第九冊。發愿文題名為“擬吐蕃圣神贊普千僧齋”,原題名為“吐魯番道場文”。上蓋朱印一顆,字為“木齋真賞”,并附有錄文,末尾朱印為“李盛鐸印”[1]。對于該件文書目前尚未見有專文論及,筆者對照文書圖版照片和錄文重新對之加以錄文,并就其中出現的吐蕃贊普和天下都僧統進行一些考辨。
一、文書錄文
1.調御稱尊,獨擅無上,法王利見,厥號能人,由是廣運慈舟,濟苦海之沉溺,高懸仁日,
2.朗法鏡于昏衢,天中之天,豈明言之可測,今此橫敷大廈,廣開真場,供設千僧,珍羞
3.百味者,其誰施之,則我當今圣神贊普,啟愿崇福之所建也。伏惟贊普,圣歷自天,
4.皇圖作鎮,居九五而稱最,首萬國而咸尊,威雄八方,恩加四海,霞施沛澤,廣布慈
5.靈,加以情殷至道,深挽法門。以佛乘為國正之端,將法門為治道之本,考(?)得聲高往帝,威蓋前王,啟弘愿于四時,諷金言于八部,將冀國休謐,圣壽遐進處百姓之欲,
6.當一人之慶,雖復年長懇愿,建福未足,盡三業之懇誠。閱八藏之金言,弘化更堅今又重增四時之勝會,欲使經聲
7.合響,六時無間隙之音,福慶相資,八節有康災之益。將成欹(?)愿,必籍賢良,僉曰有
8.誰,則我天下都僧統和上之謂矣,伏惟資岳瀆之靈,稟星神象,橫才杰出,氣悉
9.騰芳,七眾仰其清規,萬乘委之法印,既承綸音,無倦畏途,重光小邑,于聚名德,揖高僧,六時無替于宣揚正駕西行,遠屆邊城,躬親
10.勸導,今者能事既就,勝愿咸享,若不廣建禮耶,何以慶揚斯美,于是
11.開寶帳,閱真儀,緇徒儼雅而臨進,冠冕詵然而入會,想此
12.遐福,夫何以加[1]

圖1:日本杏雨書屋藏737號文書
二、文書中的吐蕃贊普與天下都僧統
該件文書記載吐蕃贊普崇奉釋教,并由天下都僧統和上(尚)西行來到邊城敦煌做法會齋僧千人,禮佛祈愿,應該是對當時敦煌地區的所有僧人進行供施。吐蕃崇奉佛教始于唐成宗大歷十四年(779),即本土第一所佛法僧三寶俱全之寺院桑耶寺落成之際。當時的贊普赤松德贊正式在吐蕃境內全面弘佛,供養寺院和僧人[2],該愿文撰于779年之后,文中出現的贊普應該是赤松德贊或其后的某位崇佛贊普。
愿文中出現的天下都僧統和上(尚),使人自然將之與P.3699《祈愿文》中出現的天下僧統聯系在一起。敦煌文書P.3699《祈愿文》中出現有吐蕃重要僧俗官員,其中有如下記載:
贊普永垂闡化。宰相尚起(乞)心兒,鹽梅邦國。宰相尚結羅、論屈林熱、論顯勃藏弩悉荼位顯南官。節兒監軍福祚潛運,安詳大乘,榮貴日新……都督代天理物,助圣安人……康大郎天祿彌厚,寵寄日增……三部落二判官繁祉斯集……國大德的盈律和上,愿蓮花世界。天下僧統觸堅,愿敷揚政術,鎮遏玄門,色力……本州都教授,駕三車而誘物,嚴六度以……惟我釋門二教授大德之□□故法律藏積……[3]





P.t.999文書的年代已是吐蕃政權末期,當時末代贊普達瑪被僧人刺殺,沃松與云丹二子爭立,沃松占據約如(今山南地區),云丹占據伍如(今拉薩及周邊地區),各自稱贊普擁兵割據,相互展開混戰,政權分裂為二部。敦煌地區支持沃松一方,故為沃松母子抄經做法會,佛法住持當是沃松一方所任命的吐蕃佛教僧官,在沃松所管轄的瓜沙地區發號施令,管理這一地區佛事僧務,身份是瓜州節度使轄區最高僧官。由于贊普達瑪在位末期滅佛,故而可能原來的吐蕃佛教宗師已經被廢,到沃松與云丹二子爭立時已經沒有這一職務,所以沃松又重新任命了相關僧官,教法住持仍然是瓜州節度使轄區最高僧官,來管理其所管轄的瓜沙等地之佛教。而占據吐蕃都城邏些(拉薩)一帶地區的云丹可能也任命了相應僧官來管理自己所控制區域的佛教事務。
此時在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僧官制度仍然存在,寺院有基層僧官上座、都維那、寺主等,吐蕃沙州都教授總管沙州僧務,下面設管理機構都僧統司,有法律、判官等協助其處理僧團各類事務。唐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義,推翻吐蕃在沙州、瓜州的統治,遣使歸唐,建立歸義軍政權,當時的吐蕃沙州都教授洪辯也率領當地佛教僧團給予大力支持。在歸義軍政權建立后,洪辯仍然擔任敦煌等地佛教僧團最高領袖河西都僧統,隨后又派遣其弟子悟真前往長安覲見唐朝宣宗皇帝,師徒二人都得到宣宗皇帝的封授賞賜[26]。而吐蕃在河隴地區的僧官制度也最終消亡,由歸義軍僧官制度取代。
杏雨書屋藏737號文書記載吐蕃贊普派天下僧統在敦煌齋僧千人。吐蕃在敦煌齋僧,在其他文書中也有記載,如吐蕃時期文書P.2162背《寅年沙州左三將納丑年突田歷》記載:“趙卿納一千人齋蒸作麥一馱”“氾弁……一千人齋一馱”“張家珍……四百人齋油四升三合”[18]405-406,可知吐蕃在敦煌曾分別舉辦一千人齋和四百人齋的齋僧活動。這一做法也影響到歸義軍時期,P.3781《度僧尼文范》記載尚書府主“每載春秋,弘施兩會”,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團春秋齋會得到歸義軍節度使的資助,各寺可以從官府得到布及糧食,同吐蕃時期一脈相承[27]。杏雨書屋藏737號敦煌文書是研究吐蕃僧官制度和齋僧制度的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