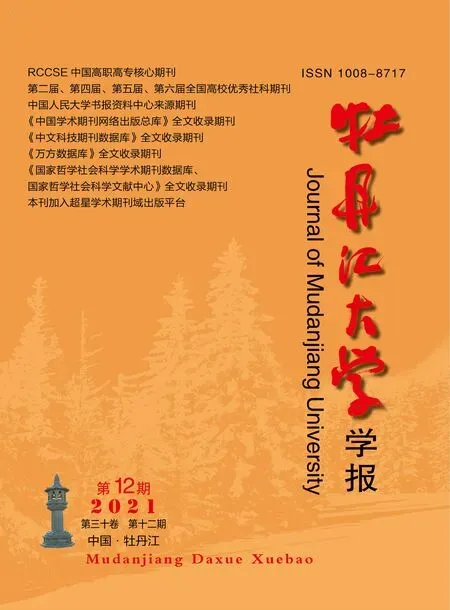從范式的視角探究批評性話語分析與福柯話語分析之研究定位
張永霞
(沈陽師范大學 大學外語教學部,遼寧 沈陽 110034)
一、引言
批評性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作為一個學術思潮最早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體現在兩本標志性著作的問世——諾曼·菲爾克勞(Norman Fairclough)的Language and Power (1989)和魯斯·沃達克(Ruth Wodak)的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1989)。在1992年 阿 姆斯特丹學術會議上,這兩位語言學者連同特恩·范迪克(Teun van Dijk)和萬·魯文(van Leeuwen)等研討了有關CDA的理論建構等問題。隨后,有關CDA的大規模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和相關學術刊物的出現,如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批評話語研究》)、Discoures & Society(《話語和社會》)和Th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語言與政治學報》)標志著CDA進入快速的蓬勃發展時期。
CDA作為一個廣為流行的社會話語理論,其重要哲學依據來源于福柯話語觀但又有別于后者。以往學者認為CDA與福柯話語 分 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FDA)的一個重要區別性特征是CDA在話語分析中對語言學分析工具的依賴和對文本分析的重視,即CDA側重從語料庫或系統功能語法視角進行文本分析,以揭示語言結構所表達的社會意義和語言所維系的權力關系。相比之下,FDA則注重抽象的理論研究,沒有涉及過多的文本分析。[1]它從社會學的視角闡釋了話語在知識形成和社會現實中的建構作用及話語與權力緊密交織的關系。這種區分試圖從學科領域的角度闡述兩者的區別與聯系,但未能深入探索兩種方法所折射出的存在于研究者頭腦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原則,而正是這些關于研究者所秉承的對知識及其與研究對象的關系決定了他(她)的方法論立場和對某一具體的語言運用所采取的分析方法。美國著名教育研究者J.Amos Hatch認為,“衡量不同的范式問題……理解不同的世界觀及其對研究的影響是研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2]鑒于此,本文嘗試從范式的視角出發探索CDA與FDA的關聯與區別,對隱藏于兩種話語分析思想背后的信念系統和價值觀進行深入挖掘與比較。范式的視角有助于啟發研究者清楚地意識到本體論與認識論立場對話語分析方法的影響,促使研究者對所選擇的具體分析方法進行世界觀層次上的內省并樹立自覺的范式意識或方法論意識,以保證話語研究過程的嚴格性、邏輯連貫性和科學規范性。
二、什么是CDA和FDA?
CDA作為語言學領域一個新興的研究社會語言的學術派別,體現了一套具有共同哲學立場和認識論取向的批判主義模式。它采用語言學的話語研究方法,包括系統功能語言學、會話分析、語料庫語言學等對社會生活中的話語實踐形式進行分析,揭示話語所承載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可以說,CDA在批判語言學基礎上史無前例地將語言學為主的話語分析和社會科學研究的話語轉向緊密結合,致力于改變現存的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話語實踐,并以此重建和改變社會組織,從而為消除壓迫和促進社會公平指明方向。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理解CDA的理論內涵:1.CDA的話語觀。CDA中的話語是“再現世界的方式和參與社會實踐的手段”并以“書面和口語的形式出現”。[3]這種社會學轉向的話語觀拓展了語言學意義上的話語分析視角,使得CDA不再是傳統結構主義意義上對語言結構特征的靜態描述,而是通過分析社會生活中使用的具體語言形式(書面和口語)的產生過程考察話語背后的社會結構、價值體系、權勢關系和意識形態是如何得以構建或延續的。2.CDA的權力觀。受福柯話語權力理論的影響,CDA的權力指“由話語體現的,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關系”[4],話語實踐中的個人通過使用機構話語或依托社會關系施展或維護其話語權力,也可以憑借一定的話語策略挑戰對方的話語權力。進行話語批判就是要揭示話語實踐如何和權力運作交織在一起,以及自然化的話語策略如何控制意識形態,進而變革權力不均的社會結構,以實現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秩序。3.反身性。CDA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對身為研究者的自身經歷、角色、立場、價值觀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關注這些因素在研究過程和文本制造中產生的影響和作用。
與CDA相比,FDA更多的是從后結構主義方法論視角,運用福柯的系譜學方法深入探索話語和權力如何建構社會文化構架和多元復雜的主體性,解構二元對立的等級思維和宏大敘事。FDA的代表性人物大部分是女性后結構主義者,如Micheal Foucault[5], Dona Haraway[6],Patti Lather[7], Judith Butler[8],Maggie MacLure[9],Ian Stronach & Margaret MacLure[10],Glenda MacNaughton[11]等的作品中都體現了FDA思想。福柯作為話語分析的領軍性人物,其系譜學拓展了他早期的考古學方法,將權力和話語納入到獨特的分析機制中,目的在于突出兩者復雜和不穩定的相互作用如何生產出“真理”、價值、社會制度和“馴服的身體”[12]。系譜學下的FDA避免對事物本質性或規律性的探討,而是在局部細節和日常生活話語等細微之處尋找斷裂和不連續性。正如德賴弗斯和拉比諾所言:“系譜學的武器外殼也許標明著:反對深度,反對終結,反對內在性……事物沒有本質,或者它們的本質是用事物的異化形式零碎地拼湊起來的。”[13]這種方法論取向使得其它話語分析學派所極力追求的確定性、本質性和一致性變得岌岌可危。FDA聚焦于話語、權力和主體三個關聯性維度。福柯認為話語“是一種決定某些談話,思考,行為的可能性而抑制其它可能性的開放的知識體系。”[14]話語既構成了我們談話的話題和知識客體,影響和支配著我們進行某種思考、談論和行為的方式,同時還生產、承載和強化了權力,而權力的實現又會強化原有話語或創造出新的話語以鞏固權力的施展。這里的權力并不是被某個集團所把握或可控制的占有,而是指社會各種力量并存的一種不平衡的動態復雜關系和行為模式。這些力量間相互競爭角逐造就了流動不穩定的權力關系和矛盾多重的話語實踐。[15]個人正是在主流話語與其它話語形式策略性的斗爭中成為話語的主體,其主體性被多元而流動的話語實踐所塑造和構建。因此,FDA的主體性是不穩定的,多重而矛盾的,總是處于構建的開放過程中。FDA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不以尋求事物內在的本質屬性或批判“誰擁有權力”為目的,而是運用權力的生產性、流動性等特點和話語權力的轉換關系仔細審視真理話語是如何上升到二元等級中的主導位置并加以固定化和自然化的;那些非主流話語(如倒置話語)如何通過策略性的對抗挑戰或顛覆主流話語以及主體性如何在真理游戲中得以建構、再建構、塑造,再塑造的……。
三、什么是范式?
“范式”一詞最早由托馬思·庫恩(Thomas Kuhn)在1962年《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指在科學探究中指導科研行動的信念體系。[16]古巴和林肯認為在學術研究中,范式“是一套具有哲學原則的基本信念體系,它代表了范式持有者的一種世界觀,界定了世界的本源,個人在世界中的定位,及與世界的關系。”[17]我們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上理解范式的含義。首先,本體論指對世界是如何構成或世界本源是什么的信念。這種信念反過來影響到我們能夠合理地提出哪些問題和對知識本質的認識,即認識論。認識論通常指什么是可知的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我們所堅持的認識論立場繼而會影響到我們會尋求什么技術手段來尋求答案,即方法論。可以說,范式代表了科學的哲學框架,每一項研究都被范式這種更高的信念系統所指引,只是有時研究者并沒有意識到這種隱藏在他們思想背后的高階理論。然而作為一名能夠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研究者,他(她)應具備的一個基本學術素養是在選擇具體研究問題或方法時能夠認識到自己受哪種信念體系或哲學框架所影響。[18]話語研究者無論選擇CDA或FDA,都應首先深入思考兩者所折射出的不同的范式是如何在研究者的觀念體系中指導著不同的話語分析問題、方法和解釋的。
四、社會科學的四種主要范式
西方20世紀50年代在社科領域展開的范式大戰門類繁多,為了便于討論,本文采用科瑞恩·格萊斯(Corrine Glesne)提出的四種范式:實證主義(positivism)、解釋主義(interpretivism)、批判主義(critical theory)和后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19]實證主義由19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強調自然科學主義的哲學觀。實證主義的本體論認為,存在一個獨立客觀且能被嚴格的科學程序檢測的客觀存在。這種現實主義的本體論決定了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即只注重定量統計分析的科學嚴謹性,而沒有必要研究認知者和認知對象的互動。方法論層面上,實證主義者強調操作手段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堅持系統科學的實驗手段,收集可觀察的數據和資料,驗證假設,構建理論,以達到發現真理的終極目標。實證主義者認為研究的目的在于精確全面地描述把握世界的運行規律,從而做出有效的預測與控制。
解釋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等人。在本體論上,解釋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是被人為建構的,是多元、復雜而多變的。認識論上,解釋主義認為研究結果是研究者和參與者的互動產生的,研究目的在于從研究者的視角解釋社會;方法論上,解釋主義采用質性研究,利用觀察、訪談等方法在社會情境里長期深入地與參與者互動以達到視域融合。
批判主義堅持歷史現實主義的本體論:社會現實受種族、性別、階級、經濟、智力等價值體系制約形成,而這些思想觀念會扭曲現實,批判主義的目的是揭露那些扭曲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認識論上,批判理論采取交互性和主觀主義立場,認為研究結果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在互動中產生。知識是主觀的、政治的、有價值介入的,即研究者的價值體系和政治立場不可避免地滲透到知識創造中。方法論上批判主義提倡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對話性研究,以喚起并增強被壓迫者的覺醒意識,通過賦權被壓迫者和支持社會變革來實現社會公平。因此,批判主義通常研究權力問題,聚焦于主導話語規則如何“規定著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誰能說權威性的語言、誰必須聽從,誰的社會建構是合法的、誰的社會建構是錯誤的和不必要的”[20]。對于批判主義研究者來說,研究是一種政治活動,用來揭示社會生活中的語言如何支持和維系不平等或壓迫的權力關系,挑戰人們習以為常的規則、強制和習慣,并指明改變現存社會組織或結構的方法。同時,批判主義強調由于研究者通過自身的理論構架呈現知識,所以研究者應對自身的政治立場、價值觀和研究視角進行自我反思。
后結構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有雅客·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后”這個術語不僅是時間的印記,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對過去的抨擊和與傳統的決裂。西方主流語言學所倡導的結構主義認為語言是一個靜止、孤立于社會現象之外的中立的抽象系統,能指與所指是一一對應的映照關系,存在著一個明確的實在等待研究者去發現。后結構主義則反對這一思想。體現在本體論上,后結構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是多元、流動、復雜的,是話語權力建構的產物。話語不僅包括書面文字,還包括人們的口頭表述和行為等。認識論上,不存在有待發現的真理,因為真理總是地方性的和變化的,是話語權力的游戲。研究者只是“站在某個角落”,從事情境化、局部化和關系化的知識生產。[21]方法論上,后結構主義文本分析的核心目標在于解構,即探明這些文本是如何系統地以合法化的方式去包括和排斥某些思想與行為。話語建構了我們所熟悉的事物和觀念,但這種建構并非是自然的、毋庸質疑的,而是可以解構的。福柯的系譜學方法就是解構主義的有力武器。
五、CDA與FDA在研究范式上區別
CDA與FDA都摒棄了針對語言本體的研究,轉向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社會生活中話語的產生和運用,都主張話語實踐者通過借助話語策略維護或挑戰他人的話語權力,權力具有生產性和變化性特征等,都通過分析話語與權力之間的內嵌關系揭示權力如何通過話語策略使權力合法化和社會秩序自然化,且都強調文本的反思性研究。但兩者遵循的研究范式和哲學立場截然不同。CDA體現的是批判主義路線,走的是歷史現實主義的本體論立場,即世界因種族、階層、性別、性取向等不同而存在權力過剩或壓迫欺詐的非正義的現實。研究者通過CDA產生的知識話語是“主觀的、解放性的、能導致基本的社會變革”[22]。認識論上的主觀主義要求研究者對自身所處的立場和利益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承認研究結果是有價值介入的,是由研究者與參與者對話性的共同努力協商的結果。研究者通常將自己定位成社會變革的實踐主義者和推動者,熱衷于利用自己知者的優勢消除壓迫與控制,并力圖與參與者建立一種非等級的和睦關系。研究目的是要通過文本分析揭示語言表現出的支配關系、歧視、社會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喚醒民眾的平等意識,從而解決不公平的社會問題(如種族/性別歧視)和推動社會政策的變化。因此,CDA的終極目標是要通過研究的干預促進社會變革,這種研究具有解放的性質。
而FDA體現的是后結構主義路線,走的是反現實主義的本體論立場,強調社會現實是話語權力的結果。由于話語是多重的、開放的、矛盾的,所以存在多元并存的現實,沒有哪一種優于另一種。FDA否認了研究者或個人在創造知識中的主體地位,而是權力與話語/知識的內在關系決定了知識的生產。正如福柯所言,“決定知識形式和知識的可能范圍的不是生產出對權力有用或反抗權力的知識主體活動,而是權力/知識,是模貫并構成知識主體活動的過程和斗爭。”[23]知識作為話語權力的產物,具有多重、不確定的特點。研究者多重變化的主體性在文本生產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24]對FDA研究者來說,CDA所倡導的研究者與參與者間的和睦關系(rapport)是不可能的,因為研究這一社會實踐本身就已構建起了研究者話語和參與者話語的二元對立關系,[25]所謂的非等級的合作關系在FDA看來只不過是權力和語言的游戲。研究者在表征時要時刻徹底反思“我們自己是否正在維持社會的不公平”[26],并常以第一人稱敘述以試圖解構研究者在文本生產中的各種專制主義形式。[27]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CDA和FDA在范式上的根本區別在于兩者持有截然相反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知識觀和研究目的。前者所堅持的歷史現實主義本體論立場認為存在一個剝削壓迫的不公平世界,通過創新的方法論——探尋參與性研究和建立和睦關系所生產的知識能夠改變現存的社會結構,并能通過賦權消滅不公正的事實。這種范式立場在FDA處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FDA解構了所有中心化思想和穩定性思維,包括批判主義,同時“拒斥解放的理念”[28],這使CDA的研究結果成了很大的問題。因為雖然CDA出于反抗壓抑和解放社會之目的,但在FDA看來,壓抑的文化機制生成了壓抑的對象,這無形地助長了霸權話語的隱蔽性運作,維護了其主導地位。因此,以受壓迫者之名所從事的解放事業陷入了另一種形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為打破權力過剩而掙脫出來的受壓迫者反而成為霸權話語自我強化的工具,從而禁錮了CDA試圖解決的難題。同樣,CDA研究者在自我定位為賦權者和強調主客和睦的研究關系的同時,也相應地建構了研究者在知識生產中的權威地位和研究者/被研究者的二元對立的主體位置,這些主體位置賦予研究者/被研究者一整套話語權力和義務,迫使雙方在研究過程中根據自身的主體位置選擇相應的詞匯、句式、言說方式來傳遞信息、理解世界和參與活動。[29]而這種研究者的權威和研究者/被研究者的二元對立話語正是FDA在研究中時刻省察和解構的對象。對FDA來說,研究目的不在于解放,而是放棄前話語存在的本體論幻想,探尋話語權力關系如何構成意義的生成方式,在去自然化的過程中否認壓迫性的中心和二分法,置換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并通過尋求意義的多樣、流動和開放的可能性創造更加包容的平等社會。
六、結束語
本文從研究范式的視角探討CDA與FDA的區別,不是為了突顯哪種范式能更“準確”地進行話語分析,而是為了對兩種分析方法與其背后所依賴的研究范式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探察,因為正是這些信念系統決定了具體分析方法的選擇和實施。與其爭論某一種路徑的優劣,不如研究如何在范式引導下設計與范式框架相一致的研究問題和分析方法,從而更全面綜合地體現出研究過程所應遵循的科學素養。例如,如果你是一位對批判主義感興趣的女性主義者,你會選擇CDA作為研究方法,你的一個基本假設可能是女性飽受父權制的社會壓迫,你熱衷于發現并推翻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以此改變女性地位低下的社會狀況。你會自我定位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實踐者和行動研究者。方法論上你會尋求建立與被研究者的非等級的和睦關系并關注對文本分析的自我反思。如果你是一位后結構女性主義者,你會選擇FDA作為研究方法,你會從本體論上重新思考女性的身份問題,你會傾向于認為女性“不應被設想為一個名詞或靜止的文化標記”[30],而是由話語不斷生成、建構、再生成、再建構……開放的意指過程。你的認識論關注點會由追尋和批判性別等級的源頭轉向探索和質疑生產這些話語的權力運作機制的系譜學方法上來。總之,不管使用哪種分析方法,本文倡議話語分析的研究者應首先憑借自身的立場、經歷、價值觀自覺選擇和樹立相應的范式意識,然后以與范式相一致的視角看待世界,確定研究目的,在此基礎上提出符合理論立場的研究假設、研究設計和相應的分析方法,從而保證話語研究過程的嚴格性、邏輯連貫性和科學規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