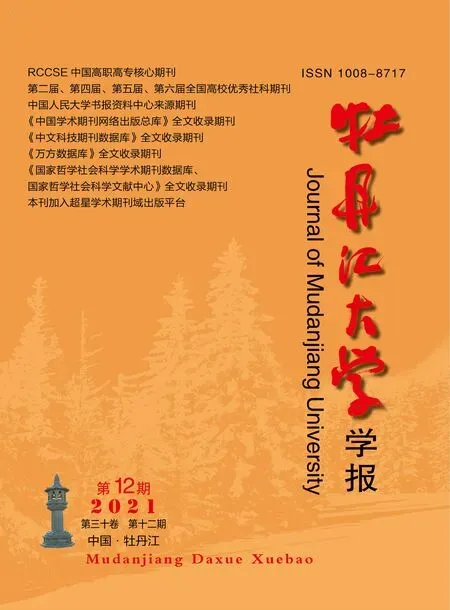淺論漢代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于 萍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文心雕龍》一書,是產生于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一部有關文學理論批評的偉大作品,此書著作有著系統的理論、嚴密的結構、細致的論述。古往今來,影響著后人的文學創作,同時也對文章學和修辭學有著重要的影響。此書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劉勰,于南朝齊和帝年間著成。《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或者說是“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宗經”為論著文章的基本思想, 《文心雕龍》的創作建立在吸納漢代經學的精神思想上,漢代經學給予《文心雕龍》的創作很多的精神養料。《文心雕龍》理論系統的建構,從古往今來的學者研究成果來看,受到漢代經學多方面的影響:關于文學本體論,經學典籍《禮記》影響著《文心雕龍》的文學本體觀。關于創作論,《周易》《樂記》的一些精神內涵對劉勰所揭示出的文學創作論(感物——情動——文見)有明顯影響,劉勰提出的“質文相附”學說和“情經辭緯”學說,都逃不開經學的思想范疇。[1]對于文學發展論,《通變》篇則是對于《周易》中的論述文學的繼承與發展的哲學思想的繼承,《時序》一篇就是受到《樂記》《毛詩序》中關于詩樂發展與社會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理論的影響,進而闡釋了文學內在發展和外在發展的基本規律。關于文學功用論,以《文心雕龍》中篇章來看,“明道”“政化”“事績”“修身”等功能,這些都明顯地受到經學的影響,都逃不出經學的范疇。
一、經學之起源
什么是經學,首先就應該探討一下。經學,是中國千年傳統學術文化主題,自漢代年間形成以來,存在中國的歷史足足有著差不多兩千多年之久,經學的影響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代的儒家仕子以及經學的研究者對其所作的闡釋也貫穿著中華文脈的始終。而何謂之經,又何謂之經學?許慎在《說文解字》里面說過,我們從他的語源學角度來看,“經”,常與作為織物的“緯”相對,后來引申出的意思與“天”有關,“經”就具有了和天一樣的統攝地位和非凡的力量。古文中有“經緯天地曰文”等之語,從古漢語的語境中,可以看出經緯常常和天地相對比,經就和天有了一定的聯系,故而在使用“經”這一術語的時候,就往往帶有一種征服的意識。在漢武帝時期,由于經常與天相聯系,就具有一種統攝萬物征服世間的力量,經就具有了很高的地位,而有道德規勸功能的儒家詩學逐漸地與國家大一統社稷安穩的政治倫理相聯系。于是結合天時地利人和,經就與儒家詩學相聯系,就成為了所謂的經學。
因為儒家詩學固有的倡導建立功業,齊家治國的思想,和封建時期統治者需要的政治需求相吻合,儒家詩學其中的一些精神內涵就有助于社會的進步和滿足現實的需求,于是儒家詩學就與國家的政治倫理相結合。而經學本身就具有的社會道德規勸的功能,這一種社會道德規勸的功能需要政治權力的加持,社會大眾的認可,在漢代和皇權主流的結合就是一條比較方便達到其互相目的的路徑。所以,加上正處于漢代君王有作為想尋求大一統局面的環境下,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抓住歷史機遇,和政治倫理結合,然后經學不斷發展,汲取有利于君王統治、社稷安穩以及國家大一統的思想,在漢代成為一種學術宗教而被確定下來,儒家經典于是就成為了統治者規定后代仕子學習的書籍。
又有說,經學產生于西漢,秦亡后,項羽火燒咸陽加上秦皇之時的焚書坑儒,導致六經除《易經》外皆無可幸免,漢朝從文帝景帝時期始,開始古籍的收集工作。到漢武帝即位后,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五經等篇章書籍就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形成了崇高的法定經典。漢代以后儒生因為各種原因,逐漸就以傳習、解釋五經經典為主業,自此經學開始形成。漢代經學,繼承了先秦原初儒家學說的思想,同時又有結合時代的創新和發展。由于漢代經學的崇高地位,這對中國古典文學、文論的影響都是非常深遠的,這也自然就包括《文心雕龍》,所以經學不可避免地對《文心雕龍》的創作產生影響。
二、從《宗經》論淺析漢代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總論五篇,是全書理論的基礎,為“文之樞紐”。第一篇為《原道》,開篇即是“文之為德也大矣”,進而論述“自然之道”,從世間的天地萬物皆有文采說起,在論述人必然有“文”,所有的萬物文采,又都不是人為的,外加的,而是客觀事物自然形成的。然后《原道》的第二部分,開篇就是闡釋人類之“文”的起源是起始于混沌之氣。《原道》第三部分論“自然之道”和“圣”之間的關系。劉勰認為,古代圣人是根據“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來著寫文章,通過古代圣人的文章來闡明“自然之道”。《原道》最后一段中說,自伏羲到孔夫子,遠古的圣王伏羲創立章典,有王德而沒有王位的孔夫子進行闡述和發揮,他們都推崇自然之道。劉勰通過論述例子,進而闡述自然之道是由圣人體現而為文章,圣人又是通過文章來解釋自然之道。就像《易傳》之中說的,章辭之所以能夠寫得優秀有感染力量,就是因為它符合自然之道。劉勰從《原道》出發,繼續闡釋他的思想,在《征圣》篇和《宗經》等篇都明顯顯現出受到經學思想的影響。
從劉勰《為文心雕龍·宗經》篇來看,就明確提出了文必宗于經的思想。在《宗經》中, 劉勰首先是高度論述了經書的崇高地位和非凡的價值: “經也者,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鴻教也。…… 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義既極乎性情, 辭亦匠于文理; 故能開學養正, 照明有融”。《宗經》篇直接宣言“文必宗于經”,全文為三部分,第一是為概述諸子經學的基本情況,以及諸子經學對人的感化教育作用的內容,第二部分則是專門介紹“五經”寫作的不同的特點以及“五經”的成就;第三部分,是闡明文章為什么要宗于經,宗于經有什么意義。劉勰通過研讀古今儒家經學典著,綜其所究,認為經對各種文體都有一定的影響,文章要宗于經,好處有六種,能夠文質皆美。能夠宗經,就不會出現楚漢以后魏晉以來,文章都矯揉造作顯現出一種浮夸文風的文學思潮,文學朝著追求絢爛的文字華麗的文采而忽略掉文章所要表達內在思想的方向發展的弊端。《宗經》開篇就向我們說明了什么是經學,即:闡明天、地、人三才者尋常道理的,這類書就叫做經書。所謂的“經”,也就是歷經歲月不改的根本道理,不可改變的圣人教導。由此可見劉勰在這就把經書推崇到了一個高度,自然他的著作就離不開經學對他的影響。
《宗經》篇中認為儒家的經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義既極乎性情, 辭亦匠于文理”,就是說,不論思想內容,還是語言技巧,經典都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所以文章必須要宗經。 所以也可以從另一角度看出,《文心雕龍》的著作離不開漢代經學的影響。
《文心雕龍》中,除了文之樞紐之一的《宗經》一篇開頭的直接宣言外,后文也繼續說明了論、說、辭、序、詔、策等各種文體的類型,都來源于五經。五經作為“文章奧府”“群言之祖”,表明后世文體的創作就得學習經學,效仿經學的創作,以五經為文體創作的范文,足見經學對后世文體的影響。就本體論而言,劉勰在論述文學創作和作品產出的問題的時候,涉及到文學理論核心這一基本問題,而《文心雕龍》的文學本體論的理論根源就在于經學。受經學元典中的《樂記》的影響,劉勰就提出了以“人心”為本的文學本體論。如:《樂記·樂本》篇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也就是說,只有人心生,才有作品出。劉勰對“樂由心生”這一命題的把握,不光是樂由心生,文自然也由心生,文學與藝術沒有情由心生,是不會產出優秀打動人心的作品。以樂論來移植文論,文學理論從《樂記》中汲取營養,可見經學之一的《樂記》思想對其理論觀念的影響。
三、從創作論淺析漢代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從劉勰《文心雕龍》的《神思》《情采》《體性》等篇來看,可以發現劉勰對文學創作論的基本原理的揭示,這個原理即是:感物——情動——文見。一說是世界萬物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本源,先感物方能更好抒情,情才更好的由心而生。才可以“言形”來“吟志”,這就是劉勰“感物吟志”說。這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主流就是抒情文學。劉勰的這種“感物吟志”說的觀點自然源于經學,明顯地受到漢代經學的影響。經學元典《周易·咸掛·彖辭》中有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不從思想來看,《文心雕龍》中也有很多地方受《易經》的影響,從字面上看多處出現“兩儀”“三才”“玄黃”“太極”,這些術語皆出于《易經》。而從思想高度來說,劉勰的“感物吟志”一說就受漢代經學《易經》的影響,受“感而化生”提出“感物斯惑”,之后其很多的篇章和理論也受這個影響。
《文心雕龍》也闡釋了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文學作品的構成因素,文學作品的審美理想等等。《文心雕龍·情采》中:“夫水性虛而淪漪結,……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劉勰認為作品的文質關系應是“文附質”和“質待文”,文質二者之間互相依賴,此論和經學中倡導的文質彬彬相切合。在劉勰之前,漢代經學大師董仲舒也曾論述過“文質”的問題,曾提出:“文質兩備,然后禮成”。漢代辭賦家揚子云,認為文章之“事”重于“辭”,質重于文。劉勰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繼承和發展前人的思想,就形成了《文心雕龍》的“文質論”。經學家的基本觀點是以質為先,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情經辭緯”論和“以質為先”的觀點有相似之處。
以劉勰的《風骨》一篇來論述,《風骨》篇總結了前人對“風骨”的研究和看法,也論述了劉勰自己對文學作品的看法和基本要求。黃侃先生對劉勰的“風骨”說進行闡釋,風即文意,骨為文辭。 二者在作品之間又都是作為獨立的審美因素。在文中,劉勰也相應舉出不同的例子。就“風”而言,劉勰以司馬相如的《大人賦》為例,而以“骨”來說,就是說,潘勖寫就《冊魏公九錫文》,企圖學習經典的文辭,使別人都不敢下筆。同時,“風骨”論的宗經傾向還體現在“風骨”作為一種詩學范疇,“風骨論”和儒家倡導的思想相契合。劉勰反對晉朝至南北朝以來的浮夸文風,所以《文心雕龍》就是針對晉朝以來社會猶重清談的現象,文學作品中過分追求華而不實的文采,從而忽略文章真摯的思想內容的傾向而提出的,這種對社會沒有裨益的文章不為所喜,于是劉勰倡導文章需要有風骨,“情與氣偕,辭共體并”,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劉勰強調的“風骨”和儒家思想中所奉行的“剛而無虐”的精神內涵相符合,同時,也可以說劉勰的“風骨”也被經學所儒化了。
四、從發展論淺析漢代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文心雕龍》中的《通變》和《時序》兩篇,較為集中體現了劉勰的文學發展史觀的思想,以及對于文學創作與時代關系的認識。通,即是繼承傳統,也就是說古代現代文學有相通相承的一面。變,就是發展變化,也是古今文學之間有存在差異的一面。“通變”一詞出自《周易·系辭上》,《周易》中有云:“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和“變”,一個是繼承,一個是發展,是一對對立統一的辯證范疇。劉勰受《周易》一書的影響,吸納“通變”觀念的精神內涵,在文學創作中,文學發展中,用通變來闡述文學批評的繼承與革新之間的關系。 《文心雕龍·通變》中“通變”一詞,就足足出現有七次。文中的一些原文,如:“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通過原文和經學典籍的對照,可以看出,劉勰所論的通變與《易傳》的淵源關系不淺。《周易》一書,其中蘊含的事物發展規律就是一個字“變”,變,才會有生機有新的方向。正所謂世間萬事萬物時刻都在變化,于是也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地位和永恒的標準,因此就有“唯變所適”,即是說要積極地適應,順從事物的變化。《周易》中的“通變”思想,通過劉勰學習前人思想吸納前人觀念,繼而又結合時代進行創新,富有創造性地將二者對舉成文,進而就形成了一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的文論范疇,用于闡述文學發展過程中繼承與創新的關系。通變觀念與時序觀念,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是關于文學的發展,文學與時代的兩個主要概念。二者各有各的理論指向,同時又互相關聯,但是就邏輯而言,通變所處的層面高于時序。
“時序”的觀念源于經學典籍《樂記》,“時序”是闡述文學的外部發展規律,是論述文學的創作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總結了文學發展離不開時代的變遷,與時代息息相關。但由于古代的時候,詩樂一家,將《樂記》中論述“時序”和“樂”之間關系的思想移植至文學的創作。漢代《毛詩序》中就有此例,《毛詩序》中是將樂論用于詩論,而劉勰則是進一步吸納《樂記》和《毛詩序》中的觀點,聯系當下社會的變遷來論述文學的發展,分析文學的變化。同時,無論是《樂記》還是《毛詩序》中有關詩樂與時序的探討,都離不開經學的范疇。所以說,是劉勰運用漢代經學來闡釋文學理論的實例,又是劉勰《文心雕龍》中受漢代經學影響的實例。
總體而言,《文心雕龍》在建構其理論系統上受到經學影響,而且在字詞的運用,句法的表達,術語的引用上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見經學對其也有影響。《文心雕龍》中常用的范疇術語,從《原道》到《序志》來看,每一篇都有明顯的出自經學的范疇術語,如:兩儀,三才,文質,言,意,象,養心,通變,這些范疇術語皆出自于經學。《文心雕龍》中的這些范疇術語,對劉勰的思想理論建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文心雕龍》中有著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地位。同樣,漢代經學對《文心雕龍》的創作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顯著的影響,從漢代經學來研究《文心雕龍》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探析了解龍學的學術特色和理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