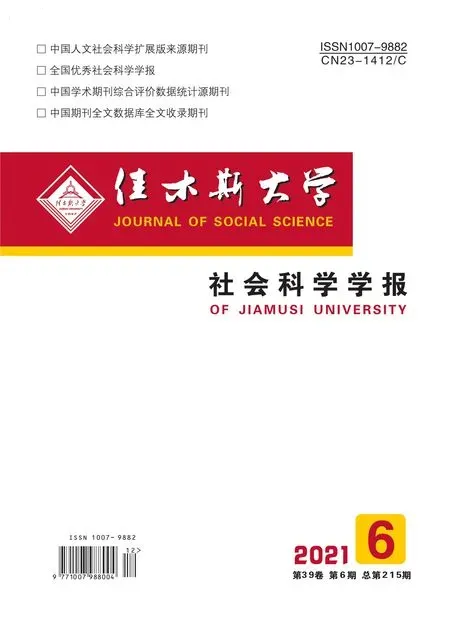從“呼語法”視角重審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生態意識建構*
張曉平,王 磊
(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2021年6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實地察看青海湖環境綜合治理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成效時說:“生態是資源和財富,是我們的寶藏”[1]隨著全球生態脆弱化問題日益凸顯,保護生物多樣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建立無物種歧視的多元文化主義觀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同時為文學的社會價值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在反思的迫切性和責任意識的合力催動下,生態批評家不斷探索生態視閾下的文學研究方法:從早期集中關注文學中的自然世界,轉向文化研究和跨學科理論視野,再到考掘多元文化語境中的生態思想資源,生態批評的視域和內容得以持續地拓延和豐富。在歐洲文學史上,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是一片具有持久強勁生命力的瑰麗奇景,構成英國生態批評的源流。以《西風頌》《秋頌》《古舟子詠》《威斯敏斯特橋上》為例,從“呼語法”視角,以“生態共同體”理念為思想根基,重審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生態意識建構,有助于豐富生態審美維度,利于建構與生態文明建設相協應的更具創新性和創造力的生態審美修辭。
一、生態批評的勃興推力及學理辨析
生態批評生發于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對現實中全球生態危機的思慮和憂患,對生態災難近在咫尺、逼迫人類警醒、反思、用有力舉措消除危機的介入沖動。這正是文學批評的擔當與責任。2000年,被譽為“新生態詩學”(new eco-poetics)典范的著作《大地之歌》問世,它既是有關環境意識發展的重要歷史,同時也是關于“科技一統天下、生態惡化愈加嚴重的時代里,詩歌的社會功用能否存續”的激昂論據[2]1。文學必須對社會問題負責,必須對當代的危機、困境和壓力做出反應。文學批評探索的領域應當涉及人、社會及自然。然而,縱觀其發展,不難發現,文學批評對自然的關注明顯匱乏。人類進入所謂“工業文明”之后,因為科技的騰躍、人自身力量的強大,自然之于人類生存的作用日漸式微,文學和文學批評的重心偏向人和社會。如此“以人類為中心”的傾向,加之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觸發了文學批評的內部調節功能,終于使其重歸對自然領域的關注。
關于生態批評的學理辨析很必要:1. 生態批評并非意味著和局限于研究和評論所有自然文學。首先,其發展的起始階段,生態批評呼吁人們關注文學中展現的自然世界。然而,傳統文學中不乏一些自然詩篇,其本質是以人類為中心的;自然只是充當作者“抒情”或“言志”的“假托”,并不具有主體性,其地位無法與人類相提并論,這是真正的生態批評所摒棄的。其次,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不局限于描寫自然的作品,而是以整個文學為媒介展開,發掘其中的生態意蘊。2. 生態批評絕非文學批評與生態學或生物科學的簡單疊加。隨著生態批評的迅速發展,它的研究視域已延伸至多領域,如挖掘導致地球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的文化根源。“寬泛地講,生態批評是關于人類和非人類關系的研究,遍及人類文化的歷史,同時也包含對‘人類’這個術語的審視。”[3]1373.“生態批評”不等同于“環境批評”。“環境”environment一詞并未在18世紀約翰遜博士的詞典中出現,而是誕生于19世紀的社會分析語境中。經過詞源學的考察,“環境”被證實意味著“環繞”,是指環繞在人類周圍的物質,究其根本,它是一個“人類中心的和二元論的術語”[4]20。而“生態”ecology的詞源可追溯至古希臘語 “oikos”,意為自然和人類整體家園。二者是互賴共存的共同體。因此,盡管“環境批評”與“生態批評”都研究和關注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但二者的價值尺度和批評旨歸不同:前者將“環境”與“人”分離,將“自然”視為他者,以人的利益作為評判萬物的根本標準;后者則視“人”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部分而非“中心”,把萬物眾生的和諧共生、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多樣作為評判尺度。
基于以上學理辨析,不妨以英國生態批評濫觴——浪漫主義詩歌開啟生態批評實踐的新視野,運用生態審美的原則理論,探察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呼語法”使用背后的生態審美效應。
二、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呼語法”蘊藏的生態審美
“呼語法”apostrophe一詞源自拉丁文“apostopha”。前綴“apo-”意為“離開,轉向”。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呼語法”用于說話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時把自己的敘說對象轉向在場或不在場的某人或某物身上,對之呼名說話這樣的情形。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呼語”可分為三類:1.與人對話。如《倫敦,1802》 (“Milton! thou should’st be living at this hour”);《給英格蘭人民的歌》(“Men of England, wherefore plough for the lords who lay ye low?”) 2.與動物或物體對話。如《杜鵑頌》(“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希臘古甕頌》(“Thou still unravish’d bride of quietness,/ Thou foster-child of silence and slow time”) 3.與大自然對話。如《西風頌》(“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秋頌》(“Who hath not seen thee oft amid thy store?”) 說話人與呼語對象進行對話或發出呼語,情感強烈,效果直接。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垂青使用“呼語”這一修辭,除了出于對文體效果的考慮之外,也是其生態意識和美學訴求的表達。生態文學具有與傳統的描寫自然或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全然不同的藝術特性和審美原則。生態審美有四大原則:
就審美目的而言,其第一原則是“自然主體性原則”。先看兩例:《西風頌》的創作緣起大自然的壯麗景觀——詩人漫步林中,突然西風驟起、枯葉飛旋、烏云翻滾、電閃雷鳴,好似吹響了暴風雨的號角。壯美的景象令青年詩人雪萊熱血沸騰,遂寫就輝煌詩篇。全詩五個部分,始終沒有脫離西風這一主導意象。它滌蕩腐舊、摧枯拉朽,又保存新生,在詩人心靈喚起豐富的想象和聯想:“不羈的精靈,你啊,你到處運行;你破壞,你也保存;”[5]211詩人敞開胸懷與西風對話:“但愿你勇猛的精神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為剽悍的你!”[5]217呼語將中心意象“西風”與“我”緊密相連,渾然一體,共奏雄壯激昂的革命交響曲。然而,詩歌是否遵循自然主體性原則?自然主體性原則旨在感受和表現自然本身的美,而不是將自然當作“客觀對應物”來表達、抒發、暗示、象征人的主觀情感。自然審美不等同于生態審美,界限在于是將自然工具化、載體化,還是全身心地去真切感受和聆聽自然。顯然,《西風頌》屬于前者——西風是詩人革命激情的象征,承托著他追求自由、建立新秩序的宏愿——被突出者并非自然審美對象。詩中的真正主體是詩人、是革命者。與之相較,《秋頌》是一首嚴格恪守生態審美自然性原則的詩歌。詩中的主體是自然,且只是自然。濟慈創作的靈感和沖動來源于他對秋日自然純粹的欣賞及對生態和諧的欣喜頌贊。他在給友人雷諾茲的信中,這樣追述三天前自己的創作緣起。“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喜歡殘梗散碎的田野……殘梗的田野給人以溫暖感……這一點在星期天早晨我散步時給我強烈印象。于是我寫了一首詩。”[6]216濟慈患有肺結核,因而對生態環境異常關注、對生態變遷非常敏感,能“見出常人之所不能見”。第一詩節“霧靄的季節,果實圓熟的時令,/你跟催熟萬類的太陽是密友;/同他合謀著怎樣使藤蔓有幸/掛住累累果實繞茅檐攀走;”[7]45原文雖未出現 “thou”這樣的人稱呼語詞,但其效果——說話人強烈真摯的情感溢滿字里行間,他與秋之間的親昵緊密不言自明。說話人列舉了14種意象——薄霧靄靄、瓜果成熟、太陽、藤蔓、蘋果、苔蘚斑駁的老樹、葫蘆、榛子、遍地的鮮花、辛勤的蜜蜂等等。原詩未出現顏色的字眼,讀者卻早已飽覽了秋天的色彩紛呈,遍嘗了果實的馨香甜美,進而感恩于自然的慷慨豐饒——它是一個龐大的充滿智慧的生命共同體,動植物各司其職,靈動和諧。第二詩節,出現了 “thee” “thy” “thou”呼語詞共六次:“你”坐在打谷場上,發絲在簸谷的風中飛揚;無需匆忙,小睡一會兒也無妨;“你”頭頂谷袋,走向谷倉;耐心地看著徐徐滴落的酒漿。這里,與其說詩人將“秋”人格化,倒不如說詩人將人的形象融入這秋日豐收圖中。它反映了生態審美的第二個原則——“交融性原則”——人不是居高臨下,俯視自然萬物,而是與自然的忘我交融。“其他生命形態與人相遇會改變人們的認知、價值和審美……讓人在詫異、驚喜中重獲看到未顯之物的視能,從而重構人們的價值觀念。”[8]113收割、揚谷、拾穗、榨漿的人是“秋”的化身,姿態各異,或悠然閑適或慵懶恬淡。詩人將人的形象、心靈納入自然生態圈,并將人文景觀打麥場、谷倉、榨果架與自然景觀田壟、花畦、小溪并置,使其相得益彰,體現了人類樸素的農業活動與自然的美妙融合。自然中的每一個個體都以自身的方式參與整個宇宙的運行,共同展現出和諧共生之美。
就審美視域而言,“整體性原則”是生態審美的第三原則。它強調從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以生態整體利益為標尺,對整個生態系統的運行秩序懷有敬畏之情。這種審美欣賞的對象不拘囿于條理化的、對人類有益的、施予者身份的自然,而是神秘、不可駕馭甚至殘酷暴戾的自然。除了正面贊譽,生態審美評價亦可包含負面、批判的。前者從正面反映人對自然的沉浸依賴和自然對人的哺育撫慰,而后者則逆筆昭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體性。這就是生態審美的“否定性價值”(negative value),在柯爾律治的《古舟子詠》中可找到闡發。老水手在航行途中蔑視自然仁慈的法則,射殺了一只信天翁,招來災禍。船只遭到形形色色的懲罰,船員們相繼死去,只留下老水手這個罪魁禍首在人間煉獄苦苦掙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歷經孤獨與恐懼之后,他真心懺悔,厄運才得以解除。詩歌尾章: “Farewell, farewell! But this I tell/ To thee, thou Wedding- Guest!” 老水手急于講述自己駭人的經歷,硬生生地攔下匆忙赴宴的賓客。他對賓客發出呼語:“我來告訴你啊,只有兼愛人類和鳥獸的人,他的祈禱才能有效;對大小生靈、所謂高貴的和低賤的生命都一樣看待;因為上帝愛我們大家,一切都由他創造。”(筆者譯)老水手的呼吁帶有強烈的宗教訓誡色彩。不止如此,還需注意:婚禮,老水手本人,以及他發出呼語的對象——賓客,構成了敘事的核心框架。老水手“罪與罰”的經歷形成了一個生態倫理場域,婚禮作為吸引賓客的外部背景象征歡樂、世俗的物質場域,而處于“場域二項”中間的賓客被賦予深刻含義。老水手呼語的對象,本質上不只是一位賓客,而是整個人類。詩歌并沒有停步于警世箴言,而是以 “A sadder and wiser man,/ He rose the morrow morn.” 作為結尾,意味深長。賓客晨起后的變化——更憂郁也更智慧——暗示他/人類獲得了認知上的跨越和精神上的提升:一方面聽過老水手對“血紅的太陽”“銅黃色的天空”“腐爛的大海”“粘滑的海面”等夢魘般的描繪,他似乎預見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滾滾車輪對生態系統的碾壓和人類無可回避的生態災難,因而更加憂郁(sadder);另一方面,也許他會轉變最初熱衷奔赴喧囂俗世、對勸誡漠然的態度,而與了然開悟的老水手一道,投入喚起人類生態整體意識的宣講——任何領域的發展不應以破壞“生態圈的核心民主”為代價;在生態共同體中,人類并不是征服者的身份,而應該滿懷感激地與自然當中的所有成員共享自然的神圣和博愛——頓悟使他更加智慧(wiser)。因其作品奇異詭譎,柯爾律治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長期遭到低估。生態批評的興起使這一狀況得到改變。《古舟子詠》因負載豐厚的生態思想資源而被生態評論家譽為“英國最偉大的生態寓言”。柯爾律治的生態倫理意識具有明顯的前瞻性。
作為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自然涵容了紛繁復雜、形態各異的個體。每個個體之間都存在直接或微妙的聯系,都應進行平等的主體性溝通,在交互溝通中建立親和關系,共同體驗自然之廣博。這就是生態審美的第四原則——“主體間性原則”。同樣看一個使用呼語的例子。 “Dear God! the very houses seem asleep;/ And all that mighty heart is lying still!” 在盛贊并具體詳盡地描繪倫敦清晨的靜謐祥和過后,華茲華斯發出感嘆:“上帝呵!千門萬戶都沉睡未醒,這整個宏大心臟仍然在歇息!”[9]219從認識論的角度探究和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顯著特點之一,而華茲華斯更加見長于對泛神論進行詩意的潤色。反對將上帝視為凌駕于萬物的觀點,泛神論者認為世間萬物都是上帝的外在表現。“將上帝引入到所有存在物,將超出經驗世界之外的絕對價值引入世俗世界中。”[10]66把個人信仰擴展、投射至自然世界——冰川、河流、花鳥、魚獸等都體現出上帝多樣性的神圣統一。上文十四行詩《威斯敏斯特橋上》的結尾就是華氏泛神論的注解。在他筆下,自然被賦予神性的輝暈,而已不僅僅是客觀的自然。其中的萬物擁有同一個生命、同一個靈魂。這是其一。其二,眾所周知,華氏的詩歌創作以吟頌原始質樸的鄉間田園為主,城市經常被拒斥在他的自然詩作研究之外。《威斯敏斯特橋上》是他為數不多的以城市為題材的詩作。從傳統眼光看,城市文明與自然生態似乎從來都是二元對立的關系。布萊克詩歌中充斥著孩童哭喊、士兵哀嘆、被煙霧熏黑的教堂的城市(“London”);狄更斯小說里污水橫流、詐騙偷竊泛濫、偽善殘暴并行的城市(Oliver Twist);胡德筆下黑煙繚繞、血淚四溢的城市(“Song of the Shirt”)……無一不是對工業文明扼殺環境、蠶食人性的控訴。正因如此,浪漫主義詩人要逃離罪惡之城對心靈的禁錮,去鄉間自然尋找精神樂土。然而,《威斯敏斯特橋上》一詩中的城市圖景卻是罕見的澄澈:這座城市“披上了明艷晨光”“船舶、尖塔、教堂、劇院、華屋”[9]219,敞開胸懷,對著綠野,向著藍天,在纖塵未染的空氣里,一切都光彩熠熠。代表典型城市景觀的尖塔、劇院、教堂等意象與代表自然的田野、蒼穹、朝霞等意象,彼此交融輝映,主客二元對立被消弭,城市、自然、上帝、人相互聯系,產生對話和交互主體性溝通。詩人特別提到,對如此深沉的靜謐壯美無動于衷、缺乏感知共情的人一定是一個愚鈍的生靈。此時,狹隘的“人的屬性”被抹除,人不再有“社會人”或“自然人”的區分,他就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員,而生態系統包括了(神性)自然和城市(社會)。他們之間有相互支撐和承載的價值作用。以呼語法為切入點,在生態審美的主體間性視角下,我們探察到華氏的神性自然觀和他筆下城市與自然的辯證關系。華氏自然文學創作的社會功能不只在于呼吁以鄉野自然療愈人們為“工業文明”、物質至上戕害的精神和心理。同時,他以哲學家的敏銳洞察城市與自然彼此抗拒、拉扯又有所調和的博弈關系,在《威斯敏斯特橋上》一詩中,表達了對未來城市文明與生態和諧的可持續共生發展的展望與期盼。
三、結語
作為一種修辭技法,“呼語”一方面便于直抒胸臆、增強真情實感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它可以跨越時空和形態的界限,拉近作者、讀者、呼喚對象之間的距離,激發共情。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呼語法,不僅讓讀者注意到詩人與自然世界之間的互動與聯系,而且非常直觀地展現出生態個體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相互感知的過程。而認識生態圈中人類之外的其他主體形式和生物學意義上的不同主體間的生態互聯性恰是生態批評關涉的主要問題。因而,研究“呼語法”的使用背后蘊藏的生態意識和審美為生態批評打開了一個新視角,使讀者對兩個世紀以前浪漫主義詩歌對當代生態問題的預見和關照以及對人類與萬物、自然與城市互構互生、和諧共存的寄寓和展望多一層更加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