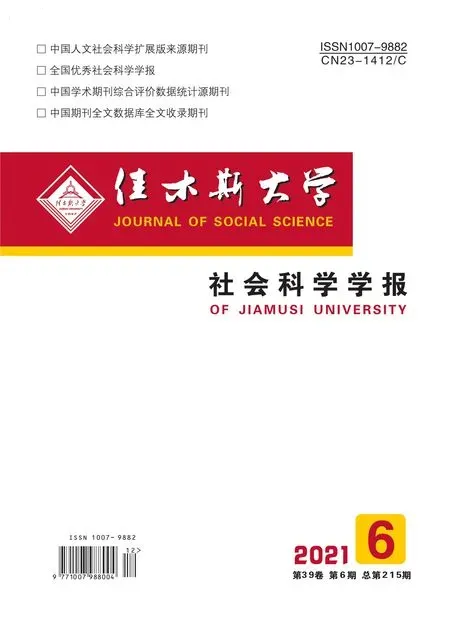汲海煎雪:明代臺州鹽業與私鹽問題研究*
管志怡,王智汪
(淮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鹽是中國人民食用幾千年的調味品,有百味之祖的美譽。“八政以食貨為先,鹽居食貨之一。”[1]1539歷代政府都施以鹽政、征收課稅加以控制。宋廷視東南鹽利為天下最厚。元朝時鹽課全靠江南之賦。明代禁榷之利數海鹽最資國用,浙江依靠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自吳王濞始便世代煮海熬波,產鹽歷史悠久。
一、明代臺州海鹽的生產
臺州地處浙東,鹽業資源豐富,海岸線綿長,潮汐涌蕩,斥鹵盡為膏腴,為浙鹽主要產區。從產鹽條件看,灘涂面積六百余平方里,曬鹽場所寬廣。鹽土深厚,含鹽量高,利于凝結鹽花、提取濃鹵。海水平均鹽度達25‰~31‰,近海潮差大于四米,便于鹽場吸納海潮;從氣候條件看,臺州四季溫暖濕潤,無雨日占全年三分之二以上,鹽區年蒸發量大于降雨量,煎曬兩便。
明代海鹽以煎為主。在海邊開辟攤場,分區劃片,統一規格與面積,再用牛翻耕,于攤場內開挖數條溝渠,以便海水納入浸泥,培養優質咸土。做完準備工作便可正式產鹽。因物質條件、生產技術差異,成品鹽顏色或黑或黃,味道或苦或淡,上等海鹽顆粒細致,色白如雪,味道咸而不澀。
鹵水是煎成優質白鹽的關鍵。鹵的淋取各地不同,兩浙因灘土細潤鹽分充沛,直接刮取即可。“取塗泥曬干以潮水潑之,如是者數四,聚土成堆,候鹽汁入溜,取汁煎之。”[2]922海邊培養的塗泥雖已有一定鹽分,但距離濃鹵還遠遠不夠,因此以海水數次潑灑,利用日曬使鹽分增加,待上結浮白,再用鐵刀將咸土刮取。同時期日本的“鹽田引濱作業法”與這種方法很像:在光照下,毛細血管現象使附于地表上的水分蒸發,最終使鹽分凝結在鹽土上。[3]29
取鹵之后是入溜淋鹵。將含有鹽分的咸泥挑到一處堆積,其下修筑池子,形狀如槽坑,槽坑旁挖一口窄井,用海水在上頭澆灌,將土壤中的濃鹵逼出,并通過事先挖通的管子流積于井。如此淋鹵,夏只兩日,冬則四日。
鮮鹵用蓮子試濃度。挑選重量大的五枚蓮子投入鹵水,蓮子浮起越多表明鹵水越濃。萬歷年間臺州“或用雞子試之亦以浮沉為鹵厚薄。”[4]18原理與前者相同。
鹵水濃度達標便可起鍋燒煎。浙東多用竹編而成的鍋,謂之“篾盤”。煮鹽之前用石灰涂抹篾盤縫隙,每灶放盤四口,鹵液注入,經高溫煎煮凝結成鹽。四盤中以中間兩盤燒煎效果最好,第一鍋因溫度最高常有焦黃鹽粒,最后一鍋因火候不夠仍浮有鹵水。古時因技術水平限制多用生鐵鍋,表面粗糙,鐵元素容易進入鹵水中,竹篾用竹制,比鐵鍋潔凈。
二、明代臺州鹽務管理
(一)明代臺州鹽務機構設置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辟臺州灣兩岸為鹽場并置新亭鹽監,位列全國十大鹽監之四。北宋新亭監廢,真宗時又設黃巖監(又稱迂浦監),是為兩浙五監之一,延袤一百四十里。元代改為黃巖場監,屬兩浙都轉鹽運使司,聚團公煎,歲辦額鹽九千五百九十引。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臨海縣桃渚北澗設置杜瀆鹽場,延袤八十五里。長亭鹽場在寧海縣東一百里,元代屬浙東鹽司管轄,延袤四十里。以上便是臺州三大鹽場在宋元時期設立與變革情況。
明代鹽政大體沿用宋元,鹽場穩定,地方機構組織稍有變革。一級機構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設于朱元璋吳政權時,承擔的鹽課額重大,統管兩浙鹽業經濟,以轉運使領之,從三品。溫臺分司是二級機構,設于洪武元年(1368年),以同知(從四品)、副使(從五品)領之,受鹽運司管理,監督鹽場的生產安排。基層機構是分布于各府州縣的鹽場。明代改場為鹽場鹽課司,負責鹽的生產和購銷。溫臺分司下設八場,臺州有杜瀆、黃巖、長亭三場鹽課司,各場鹽課司設有正副使、辦事小吏、工腳等人員。與之同屬基層的還有鹽倉,放置成品鹽。中央以戶部為鹽業經濟的最高統制,管理鹽引制作與份額頒發。
(二)明代臺州鹽務機構的職責
管理灶戶和生產資料:明代實行“戶貼制”,鹽場管理灶戶,將之編入灶籍,永為世業,子孫后代不得脫籍。煎辦所需的鍋盤、草蕩、灘場等生產資料均由鹽場提供,明廷以之為收買灶丁食鹽的經濟基礎和法律依據。草蕩提供柴薪煮鹽,離海遠者為上蕩(也是一蕩),其次中蕩(二蕩),下蕩(三蕩)最受海波,黃巖場有遠蕩三至四、五者。除了官撥蕩地,政府也鼓勵灶丁新開蕩地,截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長亭場各灶開墾荒灘一千五百八十二畝七分九厘,杜瀆場“新墾田地蕩山三千九百四十二畝八分七厘,各灶自墾升科荒蕩一千五百八十九畝五分。”[5]480灘場斥鹵不能“勘耕”,專用于刮泥。鍋盤是灶丁煎鹽的生產工具,只許在鹽場內使用,不得私自借出或挪為他用。
組織食鹽生產與運銷:為管理食鹽的生產,鹽場內專門聚團公煎,團既是鹽場下的分場,又是灶戶煎鹽的組織形式,各團設總催編審催灶,各蕩場催役根據人丁田產數目多少選派,多由殷實灶戶充任。杜瀆場團額有五,分別是:東洋團、連盤團、輕盈團、塗下團、大芬團,總催四十八名。黃巖場不設團而設倉,有:高浦倉、青林倉、第四倉、平溪倉、鮑浦倉、沙南倉、沙北倉、赤山倉、正監監,黃太二邑各領四倉,赤山倉歸臨海,場設總催九十名。長亭場設十一團,有:楓林團、塗下團、義岙團、衷嶼團、靈嶼團、東團、西團、東井團、青嶼團、東浦團、東岙團,共總催四十八名。團內蓋灶舍,給灶戶提供住宿和工作的場所,其四周建有柵欄,成鹽經報數、過秤、登記、捆包、驗收等程序入倉堆存,等候轉輸運銷。
開中法下,商人應戶部榜示,向邊防糧倉納米后,持軍隊出具的憑證向政府換取鹽引。商人持鹽引到場領鹽后,過鹽倉批驗所鹽引截角,行鹽須根據水程驗單上的路線進行發賣,至終點,無論是否售空,鹽商都須將鹽引上交注銷。明中后期,開中法漸廢,臺州引鹽不行。為使臺州鹽業恢復正常,浙江巡鹽御史李遂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上疏建議臺州黃巖、長亭、杜瀆三鹽場實行“票鹽”制度,只要交稅,沿海居民就可憑票取鹽。票鹽制度下的稽查程序變革較大“每場設置內外號簿一扇,每扇編票一千張。內號簿編寫運司字號,外號簿編寫察院字號……內號簿發場,外號簿每一扇編寫天地元黃字號。每收票官一員發與一扇各收掌。”[6]471其票數及行鹽總額仍受舊有引制的限制,不能自由銷售。當然,票鹽也不能越境販賣。票鹽制度因官鹽滯銷私鹽盛行而起,實際在實行后期助長了臺州私鹽的猖獗,個中細節這里先按下不表。
巡緝私鹽:緝私向來是鹽政管理的重點,由于私鹽有破壞交易秩序、逃漏課稅等弊端,明廷對販售私鹽者處以杖一百、徒三年的重罪。中央每五年特派巡鹽御史到地方巡視鹽政,巡鹽火甲常在核心地段巡邏,各關津要隘、交通要道又設巡檢司對過路船只盤詰檢查。各地巡鹽官有嚴格的考核標準,萬歷十三年(1585年),針對軍衛捕兵中央出三等限獲條令。臺州府被要求為上等“上則臺州衛并松門衛捕軍各二十名,年各限鹽七千二百斤。松門衛屬隘頑、楚門二千戶所各捕軍二十名,年各限鹽二千四百斤。海門衛捕軍二十六名,年限鹽九千六百斤。海門衛屬前所桃渚、新河、踺跳四千戶所捕軍各一十名,各限鹽二千四百斤。”[7]543捕軍巡查有輪班制度,臺州府各衛所分為兩班,每半年一換,上班專門緝查私鹽,每名捕軍可得月糧八斗。換到下班時不再擔任巡緝之責,而在城中操練,維持日常治安,每月得糧六斗。“如獲不足,每百斤扣銀二錢二分解送。”[7]543礙于績效壓力,很多官吏會與捕軍相勾結,捏造指標,冤枉清白商人,管控環境的惡化間接導致商人更加不愿來臺州支鹽貿易。
三、明代臺州私鹽問題
“臺為海郡,僻需海隅,□□擾費,水陸之產,益□具境內之需,蓋亦樂土也。獨鹽政與他州異,民其病之。”[8]明中葉,兩浙私鹽尤其猛烈,浙江又數臺鹽私販最盛。明人蔡潮擔憂的臺州鹽政之弊即私鹽問題,私鹽泛濫給臺州鹽政造成巨大損害,產生一系列惡劣影響。
(一)明代臺州私鹽盛行的原因
私鹽分為私煎、私販。民間得以私煮食鹽主要有食鹽制作無技術壁壘和官鹽價高質低兩方面因素。臺州灘涂廣闊,鹽資源豐富、獲取方便,制鹽不難,只是國家利用強權將其收歸官辦,并規定民間只能向官府或官商買鹽。作為煎鹽的重要生產資料“鍋盤”雖收歸官辦,實際管控并不如條例宣稱那般嚴格。臺州三鹽場使用竹制篾盤,制作時取材方便,更不好稽查。因政府生產工具管控不到位,民間私煮食鹽現象層出不窮。
煎鹽與天氣密切相關,每逢夏秋多雨,則鹵土被傷,鹽分被稀釋。產鹽不足時,市場上官鹽價格飛升,同時期低廉的私鹽顯得更具吸引力。且場官考核常只注重是否完成官定鹽課數,鹽的質量并不在首要。有時為完成課額,灶戶中煎辦隨意者竟然混入灰土以期達到斤數。負責管理的官員也曾因急于交付而用質量粗劣的土鹽充數。元末明初一則史料可看出端倪,陳龍“升兩淛都轉運鹽使司,長亭場鹽司管勾先是鹽額恒虧,君察知其弊,躬歷諸團廣積土鹽增辦如額,且補煎前數暨別場所虧鹽數。”[9]陳公雖解決了鹽課額缺之弊,及時完成任務,但從其解決辦法可以看出官鹽的質量其實無法保證,上頭隨意,下邊承辦者怎會盡心?相比之下,私鹽無官方生產背景,買食私鹽者總有“來路不明”的顧慮,鹽販要保證收入,自己煎煮或向灶戶收鹽時會更加用心,嚴格要求品質以維護口碑。如此,官鹽在市場上反而不如私鹽受歡迎。
私鹽因販運方式不同分為商私、船私、灶私、武裝走私諸多類型。因臺州地處偏僻,商人畏涉波濤多不愿來臺提鹽,所以商人走私在臺不多,與之關系緊密、常相伴相生的船私也不多見,最多的是灶私和武裝走私。
灶私出現,根本原因是灶戶待遇下降,灶戶難辦,只得冒險變賣余鹽。太祖吸取元亡教訓,優待灶戶,兩浙鹽場辦鹽一引發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換取米一石。之后寶鈔貶值,宣宗時二貫五百文只能買到五升米,世宗時工食已無,灶戶生存條件惡化。貧灶煎辦無資,官撥灘蕩不堪耕種,若有逋課,總催就要問責,貧灶被迫典當蕩地或賣兒鬻女,逃逸鹽場。情況稍好者便鋌而走險,將原來賣給官府的余鹽盜出,賣與私鹽販,交代課額。一小部分灶戶由罪徒僉派,這類人多作奸犯科記錄在案,非安分守己之輩,盜賣官鹽毫不驚訝。大部分灶戶屬忠厚淳樸之輩,難于生計,只能沖破鹽禁,大量余鹽就變成私鹽在市場流通。
武裝走私的鹽徒勢力龐大,常百十成群“往來大江,張打旗號……貪利之徒,公然替伊轉販”[10]532-533,可見這類鹽徒社會影響力之廣。官府為之忌憚的不止是他們走私食鹽逃避賦稅,更重要的是他們持有武器。武裝勢力和民間普通人群發生廣泛聯絡是封建專制政府最為忌憚之事,極有可能危害社會穩定和統治秩序穩固。
后期“票鹽”制度實行后,灶戶、軍民等個人也可以販賣食鹽“沿海灶戶、軍民人等但于三場煎販鹽斤……不分船裝肩挑,每百斤稅銀二分,給票照往白水溪、清溪鎮、寧海委官處盤驗。”[6]471體現了明朝從中央到地方對私鹽認識的深入,并意圖通過政策的修訂達到在近場社會中嚴禁私販與體恤瀕海貧民的雙重目的[11]。這種小范圍的社會救助確實使沿海民生得到改善。但鹽利豐厚,明廷從嚴禁私鹽到合法馳禁的轉變,給了私鹽販更多機會。私鹽販運的渠道被拓寬,售鹽主體自此更加廣泛,原來灶戶不準接觸其他人群的禁令也被正式打破,軍民一體現象普遍,私鹽防范機制失靈。后續暴露出的問題都表明明代鹽政的衰敗。
(二)明代臺州私鹽產生的影響
私鹽是臺州鹽政的毒瘤,歷來難以拔除。明中后期私鹽的泛濫嚴重影響臺州的社會經濟。
第一,官鹽銷量減少,影響政府財政收入。私鹽價格低、質量優,比官鹽更具競爭力,由于私鹽不納任何餉課,避開所有掣查,游離于政府控制的任何環節之外,市場充斥的私鹽斤數雖然沒有留下文書記錄,但毫無疑問,私鹽泛濫擠占了官鹽的市場份額。鹽課是國之重利,官鹽臃滯直接導致臺州鹽課收入減少,國家稅收也將受到影響。
第二,走私形式多樣,損害綱紀商人利益。鹽販走私有多種,灶戶走私、商人走私、船夫走私和武裝走私等。鹽商之所以鹽利豐厚成為古時商人之首,得益于他們對食鹽的專賣特權。其他人員走私食鹽破壞了鹽商的專賣特權,后期明政府放開近場私鹽的限制,更是從法律上認可了鹽商不再具有食鹽獨占性的現實。鹽商獲取鹽引后,不僅久支不成,即使領到食鹽也無法與市場上大量私鹽競爭。奸商為求利益加入走私行列,剩下的綱紀鹽商只能連年虧損,遵守規則的清白官商越來越少,鹽政難以為繼。
第三,武裝鹽徒走私,破壞臺州社會穩定。“濱江群盜糾集流亡,初止販鹽射利,浸至奪貨殺人,或連艘數十,鉦鼓相聞,馳突風濤,如履平地,甚至一舟之眾敵殺官兵數千人。”[12]225可見至明中期鹽徒武裝走私已經非常成熟,他們行動有序形成規模,裝備先進的火器,甚至配備行軍樂器鉦鼓,用以指揮船隊的前進和后退,井然有序,戰斗力足以媲美官軍。對這類暴徒,巡檢不能苛、地方不能詰,其活動造成社會心理緊張,嚴重危害正常的社會運轉。
第四,鹽徒勾結倭寇,動搖國家統治秩序。臺州地處浙東沿海,對外聯系頻繁。明代臺州經常受到海上倭寇騷擾,鹽務也受到破壞。鹽徒中有好事者與倭寇勾結,為之鄉導。“漳、泉、溫、臺與土著亡命之徒往往逃遁還到,勾引倭奴深入為患。”[13]正統四年(1439年),倭寇駕四十余艘戰船進攻臺州臨海,桃渚城破,位于城內的杜瀆場受到沖擊,設施大壞。由于倭寇行動迅速,登岸后常分眾四掠,殺傷軍民,社會生產遭到重創,農人釋耒、鹽丁罷灶,加重了政府財政危機。倭寇的數次進攻也嚴重威脅東部海防,危害國家安全。
民無一日無鹽,鹽無一人不食。灶私和武裝走私使臺州民間私鹽盛行,官鹽無人問津,以致浙江巡鹽御史李遂發出“臺州私鹽之多,難與他府同日語也”[6]469-470的感慨。臺州官鹽在明中后期開始沒落,家家戶戶吃私鹽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四、結語
臺州鹽務隨朱元璋設立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而展開,一直是明代兩浙海鹽的重要產地,為國家財政稅收作出重大貢獻。但到后期鹽業生產官有制在臺州開始衰敗,臺州豐富的鹽資源給民間私煎提供便利條件。鹽販除了逃避賦稅,常尋滋鬧事,兇猛彪悍,官兵也無可奈何,這股不安定勢力給地方治安造成重大威脅。雖然鹽徒與政府之間不是單一對抗關系,如鹽徒曾為戚繼光所用,助其打退倭寇,但鹽徒與官兵的矛盾并未消失。特別是明中后期的票鹽制度下,政府對近場私鹽實行馳禁,這表明官方已經失去對食鹽的絕對獨占性,不得已而作出退讓。
中國古代的食鹽專賣制度有其合理性,它是社會控制能力和市場秩序沒有現代有力有序時專制政府作出的普遍選擇。鹽業生產官有制的內核是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對重要資源進行管理,有利于資金調配,維護社會穩定。然而善法必須有善行,當國家缺乏監督、官方權力過于膨脹時,制度執行就會走樣。開中法被破壞后,無論是嘉靖時在臺州率先實行的票鹽制度還是萬歷時實行的綱法,都只是對明代鹽業官有制的修修補補,最終都是得一利而數弊生。官僚隊伍的墮化、經營者的無能、技術的限制等問題與私鹽形成惡循環,明代鹽業官有制從原來財政本位和維穩的目標寄托轉變成統治者用來獲取更多白銀以滿足其奢靡生活的工具。臺州的私鹽盛行已經昭示明代中后葉鹽業生產私有制的趨勢。清代鹽業生產及供銷環節均由場商負責,鹽業官有制徹底被私有制取代。
[注 釋]
①此處原文為“十八萬五千一百弓”。兩浙各場灘蕩面積有畝計和弓計兩種計算方式。弓計只計算與海岸平行的灘蕩長度,五尺等于一弓。明制“五尺為步,步百二十四為畝”。為統一單位,將弓換算成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