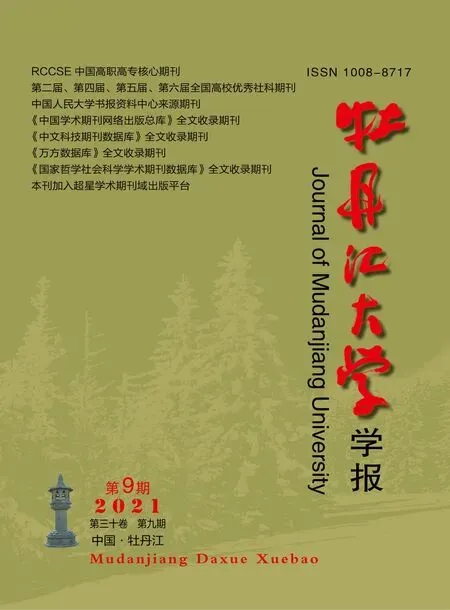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域下的露易絲·格麗克詩歌自然意象與生態意蘊
——以詩集《野鳶尾》為例
孫 嵐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美國當代詩人露易絲·格麗克(1943-)獲得了20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在格麗克的頒獎詞中寫道:“她那無可辯駁的詩意般的聲音,用樸素的美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①此后,格麗克的詩歌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格麗克的詩歌創作始于20世紀60年代,其先后創作并出版詩集12部,榮膺美國國家圖書獎、普利策詩歌獎等獎項以及“桂冠詩人”的稱號,成為了美國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在格麗克眾多的詩集中,獲得普利策詩歌獎的《野鳶尾》別具風格,詩集以野鳶尾這種植物的名字命名,共收錄詩歌五十四首,詩集中的詩歌大部分都以自然景物來直接命名,詩中也包含著對具體的自然景物的描寫,體現格麗克對存在、死亡、生命等永恒而深刻話題的思考。
21世紀初,中國學界開始譯介格麗克詩歌。學者們或結合格麗克的生平經歷,選擇單一角度對其詩歌進行總述,如柳向陽《露易絲·格麗克的疼痛之詩》[1]、沈玉慧《創傷理論下露易絲·格麗克詩歌解讀》[2]等;或對格麗克具體詩歌作品進行評論、分析,如方婷《孤獨、重生和死亡:評露易絲·格麗克<幻想>》[3]、 黃冰瑩《露易絲·格麗克<阿弗爾諾>中的愛、靈魂與死亡》[4]等;或關注格麗克詩歌所傳遞出的關于生命的哲學意識,如吉曼青《露易絲·格呂克詩歌中的孤獨意識》[5]、劉文《露易絲·格麗克:生命的短暫與永恒》[6]、胡鐵生的《格麗克詩學的生命哲學美學價值論》[7]等。總體來看,國內研究格麗克詩歌的論文數量不多且角度有所局限,亟待突破。
生態女性主義處于女性主義運動發展的第三階段。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最早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弗朗索瓦·德奧博納提出,在這一階段,該理論將婦女運動與生態環境運動相結合,從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雙重視角反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壓迫,主張婦女和自然的解放,促進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人與人之間更加和諧穩定的發展。[8]1生態女性主義與詩集《野鳶尾》有著諸多契合之處。從《野鳶尾》中具體的自然景物描寫,以及格麗克作為一名女性詩人而在詩歌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識,能夠察覺到《野鳶尾》蘊含著鮮明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詩集《野鳶尾》既有對自然意象的描寫,又有從哲學、倫理、文化、審美的維度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男性與女性性別身份的差異作出的具有生態意蘊的思考,為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理論和文本實踐。本文擬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對詩集《野鳶尾》中的自然意象和生態意蘊進行分析。
一、《野鳶尾》中的自然意象
自然意象是詩歌意象中最普遍的類型,每一自然意象都是詩人主觀情思的體現。生態女性主義將自然意象與女性主體相聯系,其理論的形成借助于符號和意象的使用。[8]56《野鳶尾》中的自然意象是詩人女性身份的表征,其中滲透了詩人的主觀情感以及社會文化內涵。《野鳶尾》的自然意象有多種類型,人與自然意象構成了“女性-自然-文化”的關系,這對于建構生態女性主義理論有著積極的文本與實踐意義。
(一)自然意象的類型
《野鳶尾》中的自然意象類型較為豐富,可簡單概括為三種類型,即“花、樹”系列,“天空、月亮、太陽、大地”系列以及“鳥和其他動物意象”系列。
第一類是關于樹和花的描寫。《野鳶尾》中描寫了各類自然植物意象,其中以花和樹居多。如嬌弱的玫瑰、頑強的雛菊、雨中搖蕩的百合花、枝椏晃動的松樹、燃燒的楓樹等。花和樹在形態和寓意上都和女性相聯系,詩人對這一系列自然植物的生存狀態的特殊限定(如玫瑰是“嬌弱”的、雛菊是“頑強”的)是詩人對自然、女性生存體驗的主觀感受與描繪。
第二類是關于天空、月亮、太陽、大地意象的描寫。天空、大地、太陽、月亮也是詩集中反復出現的自然意象,如月亮“升起在潮濕的大地之間”[9]34(《冬天結束》),“天堂的空虛/映在大地上/田野再度空虛/死氣沉沉”[9]90(《夏天結束》),以及像天空一樣的花朵,火紅的不升不落的太陽等。天空、大地、太陽、月亮在開闊的視野中被置于人類/自然/文化的場域,自然意象不再是單純的物象,而是人類建構出的社會文化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文化意蘊。
第三類是有關鳥以及其他一些動物意象的描寫。動物意象也是《野鳶尾》中的自然意象組成部分,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鳥”這一意象。“深色的鳥表演宵禁的音樂”[9]59(《晨禱》)以及反復出現的鳥鳴,給詩中寂靜的自然環境增添了生機。其他自然生靈如螢火蟲、羔羊、蚜蟲等,在格麗克的《野鳶尾》中,它們與人類的關系是和諧共生的,不存在等級上的高低貴賤或壓迫。現實話語中,人類中心主義導致自然萬物為人所控制與奴役,父權制的中心主導又導致女性群體被壓迫,不能表達與發出自己的聲音,屬于自然、屬于女性的聲音和經驗被遮蔽,這與詩歌中描寫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形成了鮮明反差。
(二)女性主體與自然意象的情感聯結
格麗克在詩集《野鳶尾》自然意象的選擇方面,多以個人主觀感受為主要依據,這種主觀感受之中蘊含著女性群體普遍存在的心靈疼痛感以及女性的生存體驗。這種微妙的女性生存體驗在與外在自然物疊合時,形成了“女性-自然-文化”的結構特征,即女性主體與自然意象形成一個情感的聯結。如《天堂與大地》中“生活將再不會結束/我怎能留下我丈夫/站在花園里”[9]73,格麗克童年時期敏感孤獨,成年后又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因而她詩歌中的自然意象一貫呈現出傷感、悲涼的特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大自然和女性都充當著孕育培養的角色,自然與女性形成了一種天然的聯系。由于人類文化觀念的偏差,大自然受到人類剝削,女性也受到男權社會的壓迫,致使女性與自然有著相同的情感價值屬性,女性的形象與自然的形象相聯結,背后遵循著自然與社會文化的邏輯:自然和女性同屬于被壓迫的一方,“女性-自然-文化”結構背后正是對男權、父權社會壓迫的反抗。格麗克結合個體自身的經驗,將一種生態女性主義的思想融入《野鳶尾》中,使得原本物質性的自然意象具有了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屬性。
(三)非個性化的自然表達
詩集《野鳶尾》除自然意象種類多元、詩人與自然意象構成情感聯結符號等的特點以外,在自然意象的情感表達方式方面也呈現出“非個性化”的表達特性。象征派理論家艾略特提出詩歌的“非個性化”理論:“詩歌不是放縱情感,而是逃避情感”[10],認為詩歌不應該直接宣泄情感,而是要找到“客觀對應物”,間接表現情感。格麗克借鑒了艾略特的“非個性化”理論,在詩集《野鳶尾》中不對自我情感進行大肆渲染,而是將自我情感投射在自然意象中,并對自我情感加以控制和收斂,從而使原本極端的自我情感(如悲傷、壓抑、絕望)透過自然意象的緩沖變得輕描淡寫,從而實現自我情感的隱晦呈現。如《白玫瑰》中的“你是誰?在亮燈的窗子里/此刻掩映在那棵綿毛莢蒾樹/枝葉搖曳的陰影里/你能存活嗎?在我活不過第一個夏天的地方”[9]100,格麗克以白玫瑰的口吻發出疑問,詩人予以自然物以思想,讓它們成為主體而對于生死進行思考和發問,雖然格麗克對個人情感并未直觀表露,但通過詩歌中白玫瑰的疑問和情感的間接表露,能體會到作者對死亡持一種絕望與悲觀的態度。又如在《牽牛花》中,“我在另一生里有什么罪/就像我此生的罪是悲傷/不允許我向上攀登/永永遠遠/無論什么意義上/都不允許重復我的生命/在山楂樹中受到傷害/所有的世間的美我的懲罰/正如它是你的——我的磨難的源頭”[9]102,以牽牛花的口吻,敘說生命存本相中的壓抑與磨難。以擬人化的形式,表現牽牛花對生命的悲傷感嘆,實則是表達詩人對生命的悲觀感受和痛苦之感,自然意象的運用使詩人沉痛的情感得以節制和收束,自然意象成為與詩人情感相印證的“客觀對應物”,更能啟發人們去思考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增強了詩歌的深意。“格麗克的詩歌雖然描寫外部世界但意在精神內在,人們可以感覺到內在與外在之間的聯系,但詩歌表現的目標是精神、神話與宗教的層次,而不再是日常生活本身”[6]38,正是這種“非個性化”的情感表達方式而使得格麗克《野鳶尾》的內在精神和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得到彰顯,構成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的具有鮮明個性的情感表達方法。
二、《野鳶尾》中自然意象的生態意蘊
生態意蘊是文學作品中的生態環境描寫所傳達的深層思想,生態女性主義者善于從作家的作品中發掘出生態意識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詩集《野鳶尾》的生態意蘊集中體現于哲學、倫理、審美、文化四個維度。
(一)自然哲思
詩集《野鳶尾》的生態意蘊在哲學層面上主要體現為對自然生命的哲思、從上帝視角來反思人類中心主義這兩個方面。
生態女性主義將生存和死亡描述成線性生命周期上的自然階段,[8]256格麗克在《野鳶尾》中反復表達了對生死的思考,生死的意象構成其詩歌的一個基本母題。例如這首《野鳶尾》“在我苦難的盡頭/有一扇門/聽我說完:那被你稱為死亡的/我還記得。頭頂上/喧鬧/松樹的枝杈晃動不定/然后空無。微弱的陽光/在干燥的地面上搖曳”[9]21,世間萬物都將經歷從美好的盛放,到苦難的摧殘,就像柔弱的松樹枝杈,在風里搖曳,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最終必然經歷衰敗,走向凋零。《野鳶尾》對生與死的哲思,將人類與自然緊密相連,它們有著同樣的生命結構與規律,在自然生命的哲學意義上,宣揚了人與自然生命的相似性。
生態思想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認為,人類對待自然采取竭澤而漁的手段,背后原因在于支配人類意識長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全球生態危機凸顯,美國興起環境保護運動,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病所在,要拯救人類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就應該摒棄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家們也順應了環境運動的潮流,因此,格麗克的詩集《野鳶尾》的創作背景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環境運動的影響,其中不少詩篇體現出格麗克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并以上帝的口吻對人類不加約束掠奪自然的行為予以委婉警示:“當你尋找著田野之上明亮的天空/你們倉促的靈魂/像望遠鏡集中在/你們某種放大的自我上”[9]78(《仲夏》),人類憑借自己的力量,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大自然加以掠奪,上帝發出控訴,批判人類盲目自大。“是我先在這里/在你到這里之前/在你建起一個花園之前/我還將在這里/當只剩下太陽和月亮/和大海/和遼闊的曠野/我將掌握這曠野”[9]56(《女巫草》),客觀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終將歸屬自然本身。格麗克在詩集《野鳶尾》中描摹的“神蘋之聲”,借造物主之口,感慨人類的輕浮以及他們對永生的徒然渴望,[11]提醒人們摒棄自以為是的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自然平等的實現,實質上也意示著男女平等的實現,生態女性主義者一直以此為目標而斗爭著,《野鳶尾》是生態女性主義文本的一次偉大實踐,有著相當積極的意義。
(二)生態倫理
生態倫理思想是對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思考,它將整個自然都納入人類的倫理關系當中,提倡人與自然平等共生。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向我們昭示了這樣一種“土地倫理觀”:“土地道德是要把人類從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平等的一員和公民。”[12]環境倫理是生態女性主義關注的重點,格麗克的詩歌創作是對生態女性主義倫理觀的一次探索與實踐,將人類與自然視為生命共同體。“土地”是《野鳶尾》中反復出現的一個意象,其表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在關系:“我種下一棵無花果樹/在這兒,維蒙特/沒有夏天的國度/這是一個試驗:如果這棵樹活下來/那就表示你存在”[9]45(《花園》),以惡劣生存環境下的播種來驗證大地與生命的關系,格麗克以自然物的存在來確證人類自身的存在,將自然與人相連接、溝通,體現了人與自然平等共生的生態倫理思想。“如果另外的某個世界上存在正義/那些像我這樣的人/因大自然強迫而過節制生活的人/就應該得到/所有事物中最好的份額/所有渴望、貪婪的目標/作為對你的頌揚”[9]80(《晚禱》)。格麗克體會到大地、自然萬物與人的深刻關聯,受限于自然條件,人類應當節制生活。這種生態正義觀正是生態
女性主義的環境倫理思想之流露。
(三)間性美學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的審美價值也相當關注,格麗克的詩集《野鳶尾》的詩歌語言是優美且雅致的,并且體現出人與自然交融以及主體間性的美學特點,這是格麗克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創作原則的發展。格麗克對自然景觀有著敏銳、細膩的感受,能夠捕捉到獨特的自然畫面,并運用恰切的感情對自然畫面進行表達,這源于格麗克對大自然的細致敏銳的觀察以及整個身心融入自然時的真切感受。“我的憤怒結束/當冬天結束/我的柔弱對你應該是顯而易見/在夏日的微風里/在成為你自己的應答的詞語里”[9]115(《日落》),詩中的“我”和“你”,是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主體的自然之間的對話,詩人有意將兩者模糊,讓人分辨不清是以自然的口吻還是詩人的口吻在敘說,呈現出人與自然相融合的狀態。格麗克的詩集《野鳶尾》“將自然還給自然,全神貫注地感知自然的一切,接收自然的能量和智慧”[13],體現出人與自然交融的特征。
生態審美的主體間性是指在生態審美的過程中,除了將欣賞者視為主體以外,視自然景物為另一主體,并在兩個主體之間進行交互主體性的聯通,在平等的溝通中尋找、體驗自然景物的美。“我已經把自己和那些花相比/它們的感受范圍要小那么多/而且沒有反應/和白色的綿羊/實際上是灰色的/相比:我是獨一無二地適合稱頌你”[9]84(《晚禱》),詩人創設出自我主體與自然意象平等的情景,將“我”與花朵、綿羊等同,實際上傳達了人與自然和諧、友好、平等的思想,人與自然都是主體,兩主體進行平等的對話和溝通。格麗克企圖通過詩歌創作實踐,讓自然由“他者”回歸主體,就如同讓女性從“他者”回到和男性擁有平等身份的主體一樣。詩歌表達了人與自然的平衡、和諧與共生的美好愿望,體現出生態審美主體間性的積極意義。格麗克詩歌中運用的交融性和主體間性原則為生態女性主義的批評實踐提供了很好的文本示范,為生態女性主義提供了美學實踐經驗。
(四)文化批判
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學者認為,生態女性主義的文化批評通過重讀和發掘文本,幫助讀者理解文本的潛在意義,從而樹立“生態觀念”[14]。與此同時,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比較于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屬于一種“框架觀念的壓迫”的邏輯,這種邏輯根源于“西方占統治地位的等級思維、價值二元論和統治邏輯”[15],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對此,生態女性主義者從性別、種族等文化維度對其進行批判。格麗克在詩集《野鳶尾》的某些詩篇中體現出“女性在男權社會和男女關系中感受到的個性壓抑、性別歧視及心理沖突,以及女性與男性、女性與家庭,責任、義務、女性本能等錯綜復雜的關系”[16],流露出女性從自身出發,對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關系的深入思考。如詩歌《花園》借自然環境的“淺山淡綠,花團錦簇”[9]45映襯詩中男性和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想停下來/他想繼續做這件事/直到結束”[9]46(《花園》),女性的話語力量被男性話語所遮蔽,格麗克深感男女地位不平等,從而對男權社會制度進行控訴。在《月光下的愛》中,“有時一個男人或女人把自己的絕望/強加給另一個/這被稱作裸露心/或稱作,裸露靈魂——意思是此刻他們獲得了靈魂……外面,夏夜/一個完整的世界被拋在月亮上……”[9]49,男女雙方情感的交互,并置于自然畫面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男女間對立、沖突的關系得以緩和,勾勒出男女平等、相處和睦的幻象,格麗克幻想自然環境的和諧景象以及男女關系的平等地位,對自然和諧、男女平等進行了構想,反襯出現實世界存在著的人與自然、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真相。文化意義上,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中自然、性別、宗教等文化互相交織,女性身份的建構以及自然環境以及宗教典故都與文化有著密切聯系。《花蔥》一詩內置了《圣經·創世紀》中“雅各的梯子”的故事和宗教的主題,“但正如男人女人似乎欲望彼此/我也欲望天堂的知識——而如今你的悲傷/一根赤裸的莖/正伸到門廊的窗口/而最終,什么/一朵藍色的小花/像一顆星”[9]57(《花蔥》),在《圣經》中,雅各夢里的梯子連接大地與天堂,是人與神之間的橋梁。在宗教世界里,人們相信上帝與人類同在,將永遠保佑人類。格麗克化用這一典故,借助藍色小花、星星等寧靜的自然意象點綴與反襯,表達對現實世界中男女關系的不平衡與失和狀態的不滿和控訴,對人間悲傷的同情以及對幸福降臨的追尋,將詩歌中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和宗教文化相聯系,顯示出神圣的宗教文化意味。格麗克從性別和宗教維度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生態文化意蘊作出了反思與實踐,推動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實踐的進步。
三、結語
格麗克在詩集《野鳶尾》中表現出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對男權中心與人類中心進行“對抗”。從格麗克詩歌創作的譜系上看,除詩集《野鳶尾》之外,格麗克的其他詩集如《草場》《新生》《七個時期》當中,也有一些體現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詩篇,如詩集《草場》中的《無月之夜》《下雨的早晨》《蝴蝶》等,詩集《新生》中的《廢墟》《鳥巢》等,詩集《七個時期》中的《月光》《星》《紗窗門廊》等,這些詩篇與詩集《野鳶尾》共同構成了格麗克生態女性主義詩歌創作的整體風貌。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在格麗克詩歌創作中占極大的比例,成為其詩歌創作的顯著特點。美國其他的生態女性主義詩人的詩歌創作,如洛里·安德森的詩集《培育失度》、諾拉·霍蘭德-莫爾斯的詩集《泥姑:黏土中的詩篇》、達琳·霍根的《美洲獅》《命名動物》《皮膚幻想》《偉大的度量》、奧克塔維婭·巴特勒《野生種子》等,與格麗克的生態女性主義詩歌在思想內核上一脈相承,都表現出對自然和女性的權利的尊重,以及對一切生命平等的呼吁。這一群詩人的作品共同構成了美國生態女性主義詩歌創作的譜系和網絡,很能代表美國生態女性主義詩歌創作的顯著成就。
格麗克的生態女性主義詩歌寫作,拓寬了自然意象的類型,形成了其獨特的“女性-自然-文化”意象結構關系,其獨特的以女性個體的經歷與體驗來寫詩,既體現出文化意義上的自然與女性群體與整個人類社會的聯結,又對社會意義上男性和女性身份的不平等現象作出反映與思考,為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完善做出了貢獻,也為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提供了生態意義、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思考,以及哲學、倫理學、美學等多個角度的經驗。格麗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一個契機,使西方傳統中偏狹的男權、父權制在一個更為國際化的視野中被人們再度關注,同時促使人們對生態女性主義有了一個更深入的認識。生態女性主義并不局限于關注生態、性別、種族等,較之于西方人類中心論和男權中心論,生態女性主義者的關注視野是更加開闊與包容的,其思想核心在于打破種種等級框架,為一切被壓迫者發聲。通過研究格麗克等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能更好地為全球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轉變提供新的視野、經驗與方法。
注釋:
①參考自Nobel prize.org,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0:Louise Glück https://www.Nobel 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0/summ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