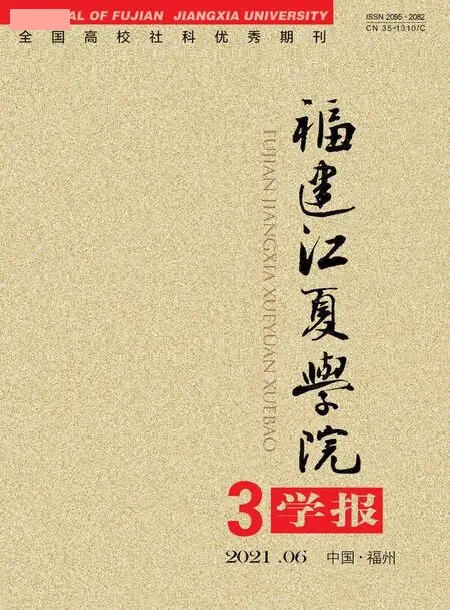馮夢龍文學思想探源
潘旭君
(福建江夏學院設計與創意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作為通俗文學的積極研究者和倡導者,馮夢龍一生致力于戲曲、民歌、笑話,尤其是白話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與編纂等工作。其通俗作品成就之大、作品之多是文學史上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而這些突出成就皆源自于他進步的文學思想。馮夢龍成長于封建時代,但與同時代的其他文人相比,他的社會觀和文學觀具有明顯的先進性。他長期處于社會底層,對平民文學情有獨鐘。他切身感受到平民百姓對文學的真實需求,深刻地認識到通俗文學作品快捷而深刻的教化作用。他率先塑造了市民階層的小人物形象,著力反映市民觀念;宣揚濟困扶危、誠信不欺、懲惡扶善,追求個性解放,重視市民友情和市民意識;著重描寫市民階層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表現他們的道德觀念與理想追求,這些較為客觀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充分顯示馮夢龍文學思想的時代性、進步性與人民性。
研究作家的文學主張與作品,應該客觀、歷史、全面地了解作家的文學思想來源。馮夢龍的思想相當復雜,主要以儒家為基礎,兼有釋道,以及明代中期以降的哲學思潮和沿海一帶的開放觀念,其中,李贄、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文學主張對馮夢龍文學思想的影響較為深刻。李贄是一位主張“真情”的激進思想家,王陽明則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二者雖然屬于兩個不同的哲學體系,但在思想理論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維系的紐帶就是儒家的忠孝節義。可以說,馮夢龍文學思想是多種思想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儒家“仁義”思想對馮夢龍的影響
馮夢龍從小就接觸并學習儒家思想,儒家經典爛熟于心。他不僅編著了大量的“治經”著作,如《麟經指月》《春秋衡庫》《四書指月》《中興偉略》等,還編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學作品,塑造了大量具有傳統儒家思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強調儒學的價值觀,如“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情史》《古今譚概》等。此外他年屆六十還不遠千里來到福建山區為官,實現“大濟蒼生”的夢想,體現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積極入世思想。
書院林立是明代儒家思想發展的一大特點。諸多知識分子通過講學來表達政見和傳播思想,其中就有東林黨和馮夢龍參與的復社。他們以儒家思想為基準,倡導和傳播儒家“經世致用”的積極入世思想,大力宣揚主張“興復古學”。晚明沿海經濟發達,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城市新興市民階層和農村富裕人群開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訴求,他們在擁護儒家思想時也為自己爭取利益。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馮夢龍敏感而又深刻地感受到這一思想變化,并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之滲透在自己的文藝作品中。“三言”中諸多商人身上所體現的“誠信觀”“義利觀”就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寫照。如《警世通言》卷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醒世恒言》卷三《賣油郎獨占花魁》、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卷二《陳御史巧勘金釵鈿》等作品中刻畫的重仁義、講道德、守誠信、以德報怨、平等互利的商人形象,他們秉承傳統儒家道德,在社會劇烈變動的經濟轉型時期獲得成功并提高了自身社會地位。
儒家的仁義思想成為馮夢龍思想的底色。但是明代社會思潮發生較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宋代理學和元代的沉悶之后,明代文藝思潮蓬勃且復雜,各種思想匯聚爭鳴,晚明出現了“儒釋道”合流的傾向,這些思想傾向自然影響了當時的文學創作。在“儒釋道”合流中對馮夢龍的影響除仁義思想外,還有釋道的“尚真”和釋家的因果報應等。從根本上說,這種釋道思想在思想合流中并不違和,也可視為仁義的延展。
馮夢龍常將釋道與儒并提,“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1]馮夢龍崇尚道家“虛無”“尚真”思想,并將之貫通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如他所倡導的“真情說”,其主要哲學來源就是道家的“尚真”。在“三言”中,道家識心見性,蔑視功名富貴,追求逍遙自在等思想得以充分體現,如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謫仙醉草嚇蠻書》、《醒世恒言》卷四十《馬當神風送滕王閣》等作品中,馮夢龍用極富浪漫色彩的筆法寫出失意文人(李白、王勃)恣意灑脫的生活,以慰藉現實苦悶的自我。同時他還將自己率真的個性,真切自然地融入到文學創作之中。《墨憨齋定本傳奇》文尾的題詩“誰將情詠傳情人?情到真時事亦真”[2]就是這種思想的直接反映。《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錄事魚服證仙》中薛錄事的入夢化魚、《警世通言》卷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中莊子的假死試妻,以及搜集民間歌詩發出的“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3]等,皆可看到道家之“真”。這種“真”與文藝創作中“藝術真實”普適性相對應,對馮夢龍文學思想的生成與傳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馮夢龍編纂的“三言”120篇作品中,有20多篇內容涉及佛教的“因果報應”及關于“酒色誤人”的佛家戒律等思想。如《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結語:“恩愛夫妻雖到頭,妻還作妾亦堪羞。殃祥果報無虛謬,咫尺青天莫遠求 ”[4]36,對王三巧兒的命運作了相應的評價;《警世通言》卷五《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的老大呂玉、老三呂珍無意中做了善事,最終一家骨肉團圓,而老二呂寶心懷鬼胎,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結語處點明了“本意還金兼得子,立心賣嫂反輸妻。世間唯有天工巧,善惡分明不可欺”[5]62的“善惡果報”思想;《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李源與僧人圓澤的因果故事,卷三十七《梁武帝累修歸極樂》宣揚“有等善人,安樂從容,優游自在,仙境天堂,并無掛礙;有等惡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拔舌油鍋,蛇傷虎咬,諸般罪孽 ”[4]555的佛教思想,等等。這些雖然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蘊含封建宿命的因子,但是對于那個時代的受眾而言,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懾和勸誡的作用。
晚明時期的自由風氣,追求個性開放、人性的解放等思潮也影響了馮夢龍對佛教清規戒律、禁欲色空等思想的認知。在《三教偶拈·濟顛羅漢凈慈寺顯圣記》中,他將“喝佛罵祖”“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濟顛和尚,立為“僧家之首”[6],體現馮夢龍對“襲其跡”的厭惡與“得其意”的認同[7]2。
二、王陽明“心學”對馮夢龍的影響
馮夢龍的后期作品更多偏向于王陽明的“致良知”,不僅講求“真情”,還注重“知行合一”,可見王陽明“心學”對馮夢龍的影響。
第一,“心即理”影響了馮夢龍的文學觀。王陽明作為儒家思想哲學化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8]13-14等重要命題,對世界本源、社會道德、人性等進行了考量,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文學界。王陽明思想不僅影響了馮夢龍的人生道路,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馮夢龍的文學思想體系。馮夢龍極力推崇王陽明的軍事才能、辦案才能與治國之道等,在《古今譚概》《智囊》等中輯錄了15個王陽明故事,他還在晚年創作了《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生靖亂錄》,書中寫到“國朝道學公論,必以陽明先生為第一”[7]3,歌頌了王陽明的豐功偉績,極力推崇王陽明的“心學”,馮夢龍的文學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8]13的唯心主義觀點。如在《警世通言》卷二《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開篇入詩即寫到:“莫把金枷套頸,休將玉鎖纏身。清心寡欲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5]14馮夢龍向往修心養性達到成己成圣境界的超脫由此可見一斑。莊子妻子死后,莊子鼓盆而歌則表達了其獨特的生死觀和“心即理”的哲學思想。
第二,馮夢龍的醒世思想與王陽明的救世思想具有同質性。“致良知”被世人認為是王陽明救世醒世的一劑良藥。王陽明在不同的情境中,從不同的角度對“良知”進行不同的闡釋,所謂“良知”,可以說是一種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先天賦予的、不假外求的、人人具備的主觀存在。具體指是非善惡之心、孝悌惻隱之心、真誠辭讓之心、忠君愛國之心等。“致良知”即在實際行動中保持良知不為私欲所遮蔽、自覺自愿踐行知行合一的道德規范。馮夢龍的醒世思想是認為自己可以通過通俗小說的勸誡,從而達到教人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效果。二者所宣揚的基本思想原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馮夢龍的文學思想里,更強調文學的情感作用,“致良知”表現為對“情真”的崇尚。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賣油郎秦重樸實忠厚,又有一種異于常人的向往和追求,無疑是古代文學世界中難得一見的一個人物形象。作品不僅正面表現了秦重的“良知”,而且通過邢權、老鴇的猥瑣卑鄙反襯出秦重那光芒耀眼的“良知”。《醒世恒言》卷十二《佛印師四調琴娘》中佛印更是“致良知”量身定制的藝術形象,體現了馮夢龍教化勸善的思想。馮夢龍的“致良知”還體現在一些“小人物”,如商人、小手工業者的身上。他們有情有義、濟困扶危、誠信不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的特征。《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的養蠶人施復和朱恩,一個拾金不昧、分毫不取,一個知恩圖報、濟人之危,兩人友愛互助,結下了兄弟般情誼。由此可見王陽明“致良知”思想和馮夢龍“以文教化”理念之間的同質性。
第三,王陽明強調個體價值,主張用獨立的批判意識認識世界,促進了馮夢龍文學主體意識的初步覺醒。明代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商品經濟活躍,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出現了王陽明、李贄、徐渭為代表的追求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英雄式人物,引領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備受時人的推崇。馮夢龍通俗小說的情教思想正是王陽明“心學”影響下的產物,強調個體價值。在《情史》中,馮夢龍大膽宣揚“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化。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9]1,強調“情”的重要作用,認為“情”是可以脫離個人而獨立存在,這些思想在馮夢龍的文學作品中均得到充分的體現。“三言”不但肯定了男女之情,也頌揚手足之情、朋友之情。《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等,表現情真實意的作品比比皆是,極力倡導情真,強調以真情感人、以真情教人。作品還首次反映了明代市井百姓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如《喻世明言》卷一《蔣興歌重會珍珠衫》中的蔣興哥與王三巧新婚燕爾,十分恩愛,但迫于生計,婚后不久,蔣興哥便外出經商,在家無聊的王三巧卻耐不住寂寞而紅杏出墻。蔣興哥獲悉之后,忍痛將王三巧遣回娘家,“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4]28。改嫁后的王三巧碰巧得知蔣興哥遭遇了官司,念及舊日夫妻之情,她想方設法搭救,幾經波折,夫妻二人最終重歸于好。普通百姓情感的自然流露、封建貞節觀念的弱化等各種復雜思想意識,在這篇作品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醒世恒言》卷三《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生動表現了賣油小販秦重和名妓莘瑤琴之間的愛情故事。在這里普通小商販可以用真情感動花魁,而花魁娘子也并非只為從良而嫁人。為了追求自主愛情,他們敢于沖破傳統婚姻門第觀念的禁錮,關注自我生活,注重自我表現,說明了明代末年婚姻問題已經突破了封建門第等級觀念的束縛,一種全新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正在萌芽等等,也顯示了馮夢龍創作主體意識的覺醒。當然,馮夢龍的這種主體意識還處于朦朧狀態,因此,他的文學作品處處充滿著矛盾與糾結,《蔣興歌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痛恨妻子王三巧出軌而休妻,卻又因舊情難忘而重歸于好;《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斷家私》中的滕大尹有清明斷案的能力和智慧,暗地里卻設計私吞苦主的千兩黃金。《喻世明言》卷十一《趙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主人公趙旭赴京趕考,科名因故被廢而流落街頭;卻又因宋仁宗的偶然一夢而衣錦還鄉,等等。
三、李贄“童心說”對馮夢龍的影響
李贄對馮夢龍影響深刻且多方面。李贄的思想主要體現為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批判觀、倡導男女平等觀、尊重女性的進步婦女觀,以及在文學作品中要表露真情實感的“童心說”等。馮夢龍不僅廣泛閱讀李贄的著作,而且虔誠地接受李贄的思想。在所編撰、評改的“三言”和《古今譚概》《情史》《智囊》等諸多著作中,馮夢龍大量引用李贄的言論,肯定李贄的多元化觀點。
首先,在馮夢龍的著作中,不乏對孔子及其“六經”的嘲諷與質疑。如《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謝知音》中,以“二親不允”否定了孔子“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5]7-8的觀點;而在《廣笑府序 》中則強調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大膽提出了孔子道學殺人的觀點,“又笑那孔子這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么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10]其激進程度并不亞于李贄。當然,馮夢龍并未像李贄那樣,對孔孟經書進行系統的研究與批判,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李贄的觀點,并將李贄的觀點運用到他的文學作創作之中。
其次,受李贄進步婦女觀的影響,馮夢龍認同、肯定、稱贊女性的才智。在他的《智囊》專輯《閨智部》一卷中,刻意贊頌了古今才女。馮夢龍認為,“婦智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11]。這與李贄的男女見識無長短之別的進步觀點不謀而合。他同情、理解和贊美女性,在“三言”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抗爭、追求婚姻自主、個性鮮明、才智卓越的智慧女性形象,閃爍著人性的光芒。她們地位卑微,卻敢于反抗封建禮教、大膽追求自由婚姻,如歌姬杜十娘、花魁娘子莘瑤琴、團頭女金玉奴、青樓歌姬嚴蕊等;她們的美貌與智慧并存,敢于追求并堅定捍衛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如蘇小妹、喜順娘、張淑兒、周勝仙等。這些熠熠生輝的女性形象體現馮夢龍的歷史進步性和現實針對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李贄和馮夢龍不但對歷史上有作為的女性給予極高的評價,而且對寡婦再醮也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們都贊美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的婚姻自主行為,李贄在《藏書》卷37中評價了漢代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一事,反映了他對卓文君私奔再嫁之事的贊揚。無獨有偶,馮夢龍在《情史》也談及此事,“相如不遇文君,則綠綺之弦可廢;文君不遇相如,兩頰芙蓉,后世亦誰復有傳者。是婦是夫,千秋為偶,風流放誕,豈足病乎!”[9]86而且在《喻世明言》卷五《窮馬周遭際賣媼》中,不但讓寡婦王媼再嫁,而且嫁得很好。
第三,李贄的“童心說”影響了馮夢龍的文學價值取向。李贄“童心說”是從王陽明“心學”發展而來,兩者之間一脈相承,但又有內涵上的質的差異。“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12]146-147李贄在提出“童心說”之前的思想皆是在此理論上建構的,這是“童心說”成熟前的思想準備與積淀,李贄后期的思想均圍繞“童心說”而展開。李贄認為世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實感的表露。針對明代詩文創作的復古傾向,“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12]149-150從文學發展的角度對復古派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12]145的理論提出了驚人的批評。明代之前,通俗小說始終被看作是粗野俗物,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李贄不但肯定了通俗文學的藝術價值,還極力推崇那些出自“童心”的優秀通俗文藝作品,認為它們是“古今至文”,至于“六經”和《論語 》《孟子 》等儒家經典則與“童心”無關;他還評點了《水滸傳》《幽閨記》《紅拂記 》等小說戲曲,并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些思想直接影響了馮夢龍的文學價值取向。馮夢龍在繼承李贄文學思想的基礎上,大力倡導通俗文學,創作了大量通俗白話短篇小說,如“三言”等;搜集整理了民歌笑話集,如《掛枝兒》《山歌》《笑府》等;改編創作了戲曲文本,如《牡丹亭》《雙雄記》《萬事足》等,推動了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發展。
四、結語
綜觀馮夢龍的文學作品,不難看出,“情教說”是馮夢龍文藝思想的核心,其主要來源于儒家“仁義”、王陽明“心學”及李贄“童心說”等思想,李贄對馮夢龍的影響尤為深刻。李贄是一位激進的思想家,他嘲諷和否定孔孟著作及其思想,抨擊明代的假道學,但他又受到王陽明的影響,很多的精辟思想里都有王陽明“心學”的痕跡。王陽明的思想基調是儒家的,其中孟子和陸九淵的痕跡尤為明顯。馮夢龍的總體思想是進步的,堪稱文化雜家,他有著非凡的洞察力和辨識力,又有兼收并蓄、運用自如的智慧;他總是能圍繞“以情教化世人”這一目的,在不同的情境中恰如其分地表現不同的思想。比如,他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為愛私奔,另一方面又在《壽寧待志》中為節婦立碑著傳;一方面肯定女性、贊美女性的才智,有著進步的婦女觀,另一方面又在《萬事足》中嚴責高妻悍妒,不容丈夫納妾,贊美心靈已被嚴重扭曲的不妒之婦梅氏;一方面嘲諷孔孟思想,另一方面卻又埋頭編撰《麟經指月》《春秋衡庫》等經書。這種矛盾現象正是王陽明“心學”與李贄“童心說”思想碰撞的結果,而將二者統一起來的則是儒家之以真情、自覺自愿地行忠孝節義之道的思想,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教化世人”“用情化人”。
此外,馮夢龍的文學思想還受到了釋家和道家的影響。“三言”中的有些作品具有突出釋道思想的傾向,但其大部分文學作品還是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馮夢龍有時將釋道與儒并提,但在編撰“三言”時,則不忘“喻世”“警世”“醒世”的教化功能,欲“以二教為儒之輔”,而且他還努力踐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理想,可見儒家思想早已深入馮夢龍骨髓并構成了其思想體系的基礎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