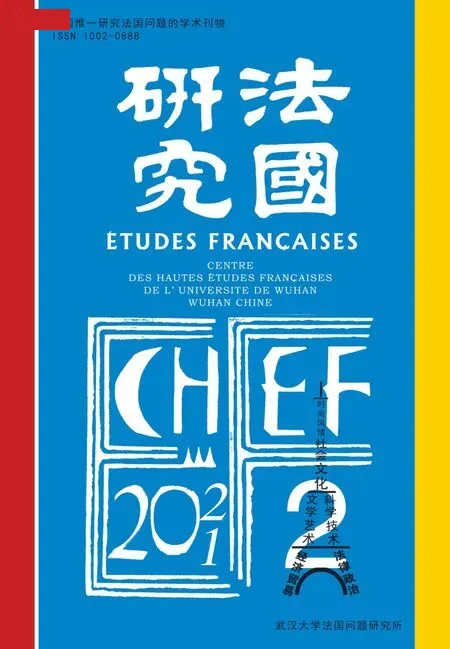爭議中的環境風險預防原則:法國的經驗及啟示
王建學
引言
現代社會已經毫無疑問地步入風險社會,①德國學者貝克建立了風險世界觀即第二現代性的理論基礎,提出風險在當代社會處于核心地位,參見[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張文杰、何博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3-5 頁。特別是在以環境為代表的各種生活領域中,個人權利、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都面臨越來越多的潛在威脅,現代國家在不確定的風險中日益左支右絀。在此背景下,風險預防原則因應而生。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該原則不僅在各國環境法中得到日益廣泛的承認,①比如1990 年德國聯邦污染控制法第5 條第1 款第2 項、1995 年法國環境保護法第1 條都予以明確規定。而且寫入1992 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②該宣言在第十五項原則中規定:“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根據它們的能力廣泛采取預防性措施(precautionary approach)。凡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或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地方,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不得被作為推遲采取防止環境退化的成本有效措施的理由。”等國際法律文件。隨著風險擴展到環保以外的幾乎所有社會領域,風險預防原則也由環境法進入其他法律部門并開始上升為憲法原則。作為最典型的代表,法國2004 年《環境憲章》第5 條首次在憲法層面明確宣告風險預防原則。
與此實踐發展相對應,學界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日益增多,并逐漸由環境法步入憲法層次。比如在我國,環境法學界和國際法學界最早關注該原則,③參見胡斌:《試論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載《環境保護》2002 年第6 期,17-20 頁;陳維春:《國際法上的風險預防原則》,載《現代法學》2007 年第5 期,113-121 頁;徐以祥:《風險預防原則和環境行政許可》,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 年第4 期,105-110 頁;高秦偉:《論歐盟行政法上的風險預防原則》,載《比較法研究》2010 年第3 期,54-63 頁。晚近以來學者基于風險社會的普遍背景,在憲法層面更一般地討論國家的風險預防義務。④參見王旭:《論國家在憲法上的風險預防義務》,載《法商研究》2019 年第5 期,112-125 頁;陳海嵩:《環境風險預防的國家任務及其司法控制》,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3 期,15-25頁。在這種研究趨勢中,風險預防原則逐漸得到拔高和泛化。然而,風險預防的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爭議,憲法化必然會放大固有爭議,但它是否有助于解決風險社會的實際問題?中法兩國在編纂環境法典等領域具有獨特的合作關系,⑤參見陳曉徑:《中國與法國的氣候環境合作》,載《法國研究》2019 年第2 期,2 頁。其環境法律問題亦在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旨在考察風險預防原則在法國入憲及適用過程中的各種爭議,從而在我國學術界的討論中提出一種更為審慎地解讀該原則的思路。
一、風險預防原則在法國的規范發展
1995 年巴尼耶法首次在法國引入了風險預防原則,此后該原則不僅編入2000 年《環境法典》并成為其總則原則,而且通過2004 年《環境憲章》第5 條最終實現了憲法化。從形式上看,風險預防原則不僅不斷強化,更因憲法確認而得到提升和普及。
(一)風險預防原則作為環境單行法原則
風險預防原則之所以能夠進入法國法,在形式上借助了環境立法不斷體系化的契機,在內容上則主要是受到1992 年里約宣言的影響。法國環境法自20 世紀70 年代出現以來一直表現為單行法律和法規,內容散亂且龐雜,缺乏基本價值和原則的系統指導。為扭轉這一狀況,法國議會制定了1995 年第95-101 號關于加強環境保護的法律,由于是在環境部長巴尼耶(Michel Barnier)的推動下制定,因此又簡稱為“巴尼耶法”。該法律不僅補充和強化了既有各類環境單行法中的環保制度,而且首次明確提出了環境保護法的一般原則。其第1 條第1 款依次宣告并定義了風險預防原則、損害預防行動與糾正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和公眾參與原則等。
作為該條所列舉的首個原則,風險預防原則的規范表述經過了一系列斟酌。環境部提出的草案版本原規定,“在具有擔憂環境狀態的嚴重事由時,必須采取風險預防措施”,①Rapport n° 4 (1994-1995) déposé le 5 octobre 1994 par M. Jean-Fran?ois Le Grand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p.42.但該表述在議會審議過程中受到普遍批評,認為其不僅過于模糊而且回避了風險預防的定義,因此議會最終在主要吸收1992 年里約宣言表述的基礎上,正式采納了一個更接近里約宣言表述的規定:“即使在考慮到當時科學技術知識仍然缺乏確定性的條件下,也不得推遲以可接受的經濟成本采取有效和成比例的措施來防止對環境的嚴重和不可逆轉的損害的風險”。②Art. 1er de la loi n° 95-101 du 2 février 1995 relative au renforcement d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該條是對《鄉村法典》第L200-1 條的修改和補充,因此,風險預防原則主要作為《鄉村法典》項下的環境保護制度而發揮作用。
(二)風險預防原則作為環境法典總則原則
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者,法國一向將法典編纂視為特定法律部門走向成熟的標志,環境法亦不例外。而總則中的原則性條款是典型法典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2000 年9 月法國政府根據議會授權通過并頒布《環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的法律部分。③《環境法典》由法律部分(Partie législative)和行政法規部分(Partie réglementaire)組成,后者遲至2007 年才編纂完成。關于《環境法典》的具體編纂過程,可參見彭峰:《法典化的迷思——法國環境法之考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112-120 頁。《環境法典》的編纂完成標志著法國環境法的內容體系趨于成熟,這種成熟性特別體現在《環境法典》總則的原則性條款的設計上。
《環境法典》在第一卷共同規定的第一編總則部分首先宣告和定義環境法的諸多基本原則,其中第L110-1 條(首條)第2 款第1 項明確規定了風險預防原則,其定義表述與1995 年巴尼耶法完全相同。④Art. L110-1 du Code de l'environnement.因此,寫入《環境法典》總則的作用主要是將該原則上升為環境保護法的一般性原則從而拓展其適用范圍。后來《環境法典》第L110-1 條經歷了多次修改,但風險預防原則的地位、內容和效力等卻一直保持至今,沒有發生變化。
(三)風險預防原則的憲法化
風險預防原則入憲是法國憲法整體生態化的組成部分。如希拉克總統在2001 年所說,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要求憲法在最高規范層次的回應,有必要“將生態人道主義銘刻在我們共和契約的心臟”。①? Discours de Jacques Chirac, le 3 mai 2001 à Orléans ?.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n° spécial, 2003, p.78.作為這種回應的結果,法國議會于2004 年按照立法程序通過了《環境憲章》(Charte de l'environnement)。后經總統提議修憲,議會兩院聯席會議以修憲程序通過2005 年3 月1 日第2005-205 號憲法性法律,將《環境憲章》寫入現行1958 年憲法序言,即法蘭西人民莊嚴宣告恪遵“2004 年《環境憲章》中所明定的權利和義務”。《環境憲章》是人類憲法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個關于環境的專門文本。
《環境憲章》在第5 條明確規定:“當損害的發生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和不可逆轉的影響時,盡管根據科學知識這種損害的發生是不確定的,公權機關仍應通過適用風險預防原則(principe de précaution),②該原則不同于傳統的損害預防(prévention)原則,二者雖都強調預防性和積極性,但前者適用于具有科學不確定性的風險,后者則通常適用于對已知風險和損害的預防。在其職權領域內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和采取臨時的和成比例的措施來防止損害的發生。”該條是整個憲章中篇幅最長的條文。第5 條風險預防原則與憲章整體一起成為憲法規范體系(bloc de constitutionnalité)③憲法規范體系指那些充當審查其他規范合憲性的依據但其自身的合憲性不被審查的憲法規范,它是制憲權的行使結果,具體包括現行1958 年憲法及其序言所確認的1789 年《人權宣言》、1946 年憲法序言和2004 年《環境憲章》。李曉兵教授將其譯為“憲法團”,參見李曉兵:《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與憲法委員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88 頁。的組成部分。這是現代憲法史上首次在憲法條文中正式列舉并定義風險預防原則,對于憲法生態化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但風險預防原則入憲的過程也集中反映了憲法生態化的爭議,此問題后文詳述。
(四)風險預防原則的規范進階
在風險預防原則的規范發展歷程中,可以明確看到其規范層級的不斷提升和適用范圍的不斷擴大。1995 年巴尼耶法和2000 年《環境法典》將風險預防原則作為法律(loi)層面的基本原則,但前者作為《鄉村法典》的一部分,僅附屬于《鄉村法典》對動植物的保護和傳統農業生產中的環境保護,而后者作為環境法典總則原則卻普遍適用于所有環境保護領域,包括前者所未涵蓋的核能利用等領域。2004 年《環境憲章》不僅在形式上將風險預防原則提高到憲法這一最高規范層級,而且明確預防風險是對公權機關的一般性要求。這不僅符合憲法主要約束公權機關的立憲主義意旨,而且將風險預防原則由環境普及到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事實上,憲法化也使風險預防原則不再僅僅適用于環境法的領域,而且拓展至所有的法領域。”④Rapport n° 547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3-2014, p.20.因此隨著公權力所展開的觸角,憲法化的風險預防原則成為拘束所有法律部門的一般性原則。
二、風險預防原則入憲的紛爭及化解
從形式上看,由環境法原則到憲法原則是風險預防原則的規范進階。但從實質內容上看,其憲法化過程伴隨著各種分歧,特別是關于2004 年《環境憲章》應當如何規定風險預防原則存在巨大爭議。
(一)風險預防原則入憲與否的分歧
在《環境憲章》的具體擬定過程中,科龐委員會(Commission Coppens)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該委員會由希拉克總統在2002 年6 月部長會議上任命,由古生物學家科龐(Yves Coppens)教授擔任主席,包括18 名在環境、法律等領域素有貢獻的專家委員。科龐委員會在擬定憲章草案的過程中通過聽證會、互聯網等途徑廣泛征求社會意見,于2003年4 月8 日提出了環境憲章專家草案。
科龐委員會對憲章應否宣告風險預防原則存在高度分歧。盡管該原則不僅在1992 年里約宣言和一系列歐盟條約和指令中得到肯定,而且在法國《環境法典》的實踐中也得到應用,但將其寫入憲法則需要格外謹慎。“委員會的多數成員認為風險預防原則入憲會導致法律上的大量不確定性。”①Yves Jégouzo, ? Le R?le Constituant de la Commission Coppens ?.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n° spécial, 2005, p.85-86.由此,憲法委員會和最高行政法院可能得到過度的審查權和裁量權,科學活動特別是科技創新會面臨遭到扼殺的風險。由于在科龐委員會的大會辯論中,以及在科龐委員會的法律分委員會和科學分委員會的討論中,贊否雙方始終無法達成一致,科龐主席只好將此問題提交希拉克總統。
希拉克總統對此問題最終作出了肯定選擇。關于選擇的理由,尚未找到文獻予以說明。從制定背景來看,《環境憲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希拉克的個人政治影響和環境保護理念,總統個人希望通過憲章奠定法國在世界上的領導性地位。②參見王建學:《法國的環境保護憲法化及其啟示——以環境公益與環境人權的關系為主線》,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5 期,64 頁。考慮到風險預防原則已經在1992 年里約宣言等中得到宣告,將其明確寫入《環境憲章》無疑更能彰顯法國在環保理念方面的進步和希拉克的個人貢獻。在此意義上,風險預防原則入憲在法國幾乎是必然的。
(二)風險預防原則憲法表述的分歧
隨著寫不寫的問題得到肯定解決,分歧轉向如何以適宜的表述來規定風險預防。由于最低限度的共識都無法達成,科龐委員會只好對風險預防提出兩種不同的表述版本。
第一個版本的表述是:“在已經識別環境受到嚴重的和無法逆轉的損害的威脅,但科學知識卻不能以確定性來證實風險時,公權機關應通過風險預防來執行評估程序并采取適當措施。本條的適用條件由法律予以詳細規定。”③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Coppens de Préparation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Ministère de l‘écologi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2003, p.38.
第二個版本是將風險預防與損害預防、污染者付費等原則規定在一起,其表述是:“環境的維護和改善基于下列原則:??風險預防原則,據此,在已經識別環境或健康受到嚴重的或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威脅,但科學知識卻不能以確定性來證實風險時,公權機關應執行研究規劃并采取臨時和成比例的措施來避免風險。??”①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Coppens de Préparation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Ministère de l‘écologi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2003, p.42.
兩個版本既有共識,也存在高度分歧。共識在于,作為憲法規范都明確風險預防是對公權機關的要求。就此,各方所取得的最廣泛共識是,國家以及國家所設立的公法人必須受到風險預防的拘束,至于國家以外的地方團體以及由地方團體所設立的公法人,則存在輕微分歧。少數意見認為地方團體不具有風險評估的能力,但多數意見認為,隨著未來地方分權和權力下放的發展,地方團體及其設立的公法人不應在風險預防方面得到豁免。
兩個版本的最重大差別在于是否將風險預防提升到憲法原則的高度。第一個版本沒有采用“原則”的表述,并且考慮到風險預防的特殊性而將其與損害預防等內容分開。可見,第一個版本刻意避免了將風險預防作為實體性原則,其支持者認為“原則”的表述過于模糊因此并不適當,而且公權機關在履行風險預防義務的過程中,必須首先在研究的基礎上隨時進行風險評估,由于科學認知的不確定性,關于風險的認定必然充滿主觀分歧。所以與其將風險預防作為一個實體性原則,不如將其作為一個程序性要求,并且由法律來進行更為細致的程序設定。而第二個版本則明確使用“原則”的措辭,從而與1995 年巴尼耶法和2000 年《環境法典》的原則定位相一致,與1992 年里約宣言等國際宣言和條約②1992 年2 月7 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第130r 條等在環境部分將風險預防規定為基本原則。的原則表述和定位相一致。同時通過與1789 年宣言、1946 年憲法序言和1958 年憲法中的原則表述相一致,借以表明將風險預防放在最高的憲法價值序列中,從而將其有效關聯于一個更崇高的原則,即人人有權在平衡和健康的環境里生活(《環境憲章》第1 條)。第二個版本的支持者認為,將風險預防作為憲法原則當然會有版本一的支持者所說的不便,但第一個版本的更嚴重缺陷是對風險預防重要性的認識不足,導致人們對特定環境風險的應對乏力。“如果環境憲章沒有將風險預防明確確立為憲法原則,就會不可避免地喪失其政治影響和折損其法律效力范圍。同時也會被作為人權進步過程中的倒退,無法加入第三代人權運動的歷史進程。”③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Coppens de Préparation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Ministère de l‘écologi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2003, p.43.
(三)政府和議會審議過程中的折衷選擇
在風險預防的兩個草案版本提出之后,憲章草案經過了生態與可持續發展部、司法部、部長委員會等不同階段的政府審議,并被提交議會兩院審議。從關于風險預防的審議和討論過程來看,科龐委員會的分歧幾乎完整地延續下來。但正式提交審議的憲章草案必須是唯一版本,因此政府方面在折衷的基礎上主要偏向了第二個版本。通過對比不同版本可以發現,最終通過的憲章第5 條將“風險預防原則”這一表述穿插在第5 條的正文中間,這既實現了將風險預防確立為憲法原則的目標,同時也避免了第二個版本那樣略顯張揚的表述。此外,公權機關的風險預防義務增加了“在其職權領域內”的限定,從而變得更加明確,此外還刪除了第一版本中的“本條的適用條件由法律予以詳細規定”的授權性規定。
在更寬泛的意義上進行比較可以發現,2004 年《環境憲章》關于風險預防的規定與1992年里約宣言和法國《環境法典》有所不同。《環境憲章》的規定更為積極,即采用了“公權機關應當”這樣的課以義務的正面表述,而非“不得推遲采取措施”那樣的反面表述。此外,《環境憲章》(也包括科龐委員會的兩個草案版本)均將評估程序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上,強調執行評估程序在實際采取預防措施之前,這是為了通過評估來降低不確定性,從而使預防措施具有更強的科學和客觀基礎。由此可見,法國《環境憲章》關于風險預防的表述盡管存在較大爭議,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身的特點和獨特貢獻。
三、風險預防原則的司法適用及效果
憲法化的風險預防原則在文本意義上是唯一的,但其文字表述卻具有模糊性。入憲過程中的種種分歧會否延續至后繼司法適用環節?由此,需要進一步考察最高行政法院和憲法委員會分別在行政訴訟和憲法審查過程中適用《環境憲章》第5 條的情況。
(一)最高行政法院與風險預防原則
自1995 年巴尼耶法生效以來,風險預防原則一直在有關環境的行政訴訟中充當司法審查的依據。在1998 年法國綠色和平協會案中,最高行政法院較早適用了風險預防原則,宣告暫緩執行農業和漁業部的一項允許海洋轉基因技術商業化的命令。①Arrêt Association Greenpeace France du 25 septembre 1998, n° 194348, Conseil d'état.在《環境憲章》生效后,最高行政法院在2008 年的一項判決中確認了《環境憲章》在行政訴訟中的效力和適用。②Arrêt Commune d‘Annecy du 3 octobre 2008, n° 297931, Conseil d'état.從后繼判例來看,最高行政法院基于該原則的法律定義已經在行政訴訟中承認風險預防原則的效力范圍,并主要將風險預防原則發展為一套程序性的審查標準,即行政機關在其對環境產生影響的決定中必須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因此,風險預防原則作為環境行政法的范疇主要是對行政機關的程序性限制。
《環境憲章》第5 條主要是對公權機關的要求,因此,其在普通訴訟層面的適用主要涉及到行政法官對行政機關的行為進行審查。從內容來看,行政法官主要采用明顯判斷錯誤(erreur manifeste d‘appréciation)③明顯判斷錯誤誕生于最高行政法院1961 年的Lagrange 案判決,主要用于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要求行政機關在判斷事實和法律要件之間的關系時,不得違反嚴重的和顯著的錯誤。法文介紹可參見Dominique Lagasse, l’Erreur Manifeste d’Appréciation en Droit Administratif - essai sur les limites du pouvoir discrétionnaire de l’Administration. Bruxelles: Bruylant, 1986.中文介紹可參見王必芳:《法國行政法上的公益概念》,載《中原財經法學》2013 年第30 期,45 頁。的審查標準,即關于潛在風險的科學認知的不確定性并不足以使風險預防措施的使用正當化,為限制風險預防措施的使用,行政法官基于明顯判斷錯誤的標準實施審查,確保行政機關所采取的措施必須能夠避免風險,且必須以適當方式來避免風險,在裁量過程中不出現嚴重或顯著的錯誤。
在2010 年7 月19 日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行政機關在批準興建移動通訊基站的決定中必須考慮風險預防原則,但根據關于暴露于基站磁場信號中的風險的科學認知狀態,市長批準興建基站并不存在明顯判斷錯誤,因此并沒有違反《環境憲章》第5 條。①Arrêt Association du quartier des Hauts de Choiseul du 19 juillet 2010, n° 328687, Conseil d'état.在2013年4月12日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擴張了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范圍,將其運用到征收程序,“只有遵守風險預防原則的要求才能在法律上作出公共利用宣告”,在此基礎上,法院一方面明確了“相關公權機關應負責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另一方面也明確了“行政機關在風險預防原則項下的職責應受到行政法官的審查,確保在此過程中不出現明顯判斷錯誤”。②Arrêt Association Coordination interrégionale Stop THT du 12 avril 2013, n° 342409, Conseil d'état.在2013 年8 月1 日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繼續適用風險預防原則,以存在明顯判斷錯誤為由撤銷了一項禁止商業化種植轉基因玉米的部長決定。在歐盟層面,轉基因玉米的種植是得到批準且不違反風險預防原則的。此判決認為法國憲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與歐盟法的風險預防原則“具有平等且平行的效力”。③Arrêt 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Producteurs de Ma?s du 1 ao?t 2013, n° 358103, Conseil d'état.
(二)憲法委員會與風險預防原則
《環境憲章》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憲法規范,因此是憲法審查的當然依據。據筆者統計,截至2019 年12 月31 日憲法委員會共援引《環境憲章》作出40 項判決,其中僅8 項援引第5 條的風險預防原則,其適用頻率相對較低。此8 項憲法判決在總體上具有以下三方面特點。第一,在時間分布上零零散散,2005 年、2008 年、2013 年、2014 年、2016 年、2017年、2018 年和2019 年各1 項。第二,從審查程序上看,2013 年的判決適用事后審查程序(QPC)即由普通訴訟的當事人提請,2005 年的判決適用提交全民公決的法律案的審查程序,與環境無直接關系,其他6 項判決均適用事前審查程序(DC)即由特定國家機關提請。第三,從判決結果來看,3 項判決結果為合憲,4 項是部分違憲,④必須說明的是,含有違憲認定的4 項判決分布于2008 年、2016 年、2018 年和2019 年,其中被違反的均是風險預防原則以外的其他憲法條文。這些案件中不乏申請人主張風險預防原則遭到違反,但未得到憲法委員會的支持。2005 年判決為駁回提請。
憲法委員會直到2008 年審查轉基因作物法時才首次運用風險預防原則。該案申請人認為受指摘法律因允許種植轉基因作物而違反風險預防原則。憲法委員會首先確認自身“必須確保立法機關不忽視風險預防原則,且它已經采取措施同樣確保其他公權機關也尊重該原則”,“確保違法行為與其所招致的處罰不能明顯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 manifeste)”,但并不能說本案中立法者違反風險預防原則,因為受指摘法律建立了“由行政機關對健康狀況和植物檢疫情況以及相關農業實踐對環境的可能影響進行持續監督的條件”,這使得行政機關“在發現環境風險時能夠采取適當措施包括中止授權,并且立法者通過這些法律規定已經采取措施確保行政機關在轉基因作物管制方面遵守風險預防原則”。⑤Décision n° 2008-564 DC du 19 juin 2008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在2013 年判決中,憲法委員會承認QPC 程序①關于該程序機制及其效果,可參見王建學:《法國事后憲法審查機制的十年:總結與啟示》,載《財經法學》2019 年第6 期,121-133 頁。中可以援引風險預防原則。該判決審查了關于禁止以大型水力壓裂法來探測和開采液氣態碳氫化合物并廢止包含該項目的排他性研究許可的第2011-835 號法律。憲法委員會認為,“立法機關所采取的禁令是為了追求保護環境這一公益目標,而從科學認知狀態來看,對相關研究活動的限制在性質上亦未與其所追求的目標不成比例”,因此,議會在該法律中所設置的措施并未違反風險預防原則。②Décision n° 2013-346 QPC du 11 octobre 2013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三)乏善可陳的司法審查實踐
總體而言,憲法委員會和最高行政法院采取了高度謙抑③有學者提出憲法委員會在前述2008 年判決中的審查“是相當徹底的”,或者認為憲法委員會成為“強有力的環境權保障機構”,此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夸大審查強度的嫌疑,參見李琴:《論法國憲法委員會對〈環境憲章〉的進階應用》,載《交大法學》2020 年第1 期,158 頁;田芳:《對法國〈環境憲章〉及其合憲性裁決的解讀》,載《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20 年第2 期,49 頁。的司法立場來進行風險預防原則的審查,只有在“明顯不成比例”或“明顯判斷錯誤”時才會作出違憲宣告。憲法委員會幾乎不對該原則進行解釋,也從未援引該原則宣告法律違憲。相比之下,《環境憲章》第7 條的公眾參與條款得到憲法委員會援引的判例數為20 項,其中14 項含有違憲認定。④參見王建學:《論環境公眾參與原則的憲法化及憲法審查——以法國〈環境憲章〉和〈環境法典〉為中心》,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0 年第4 期,45-53 頁。最高行政法院的審查作用雖然略強于憲法委員會,但也幾乎尊重行政機關基于風險預防原則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司法審查立場如此謙抑,以至于司法部長坦誠,“無論是憲法委員會還是最高行政法院,都從未在司法適用過程中濫用或擴張風險預防原則。”⑤Rapport n° 547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3-2014, p.22.
在涉及到風險預防原則的實體性理解時,憲法委員會和最高行政法院都傾向于將風險預防視為一種程序規則。通過梳理憲法委員會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可以發現,“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更多涉及到一種程序規則(une règle de procédure),而不是一種實體規則(une règle de fond),即它僅要求公權機關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并采取或調整相應措施。”⑥Rapport n° 547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3-2014, p.22.其實從風險預防原則的原旨來看,其中既有實體要求也有程序要求,而且是以前者為主的。憲法委員會和最高行政法院傾向僅從程序出發,也是其司法立場高度謙抑的表現。
《環境憲章》已經生效15 年,其諸多條款都通過判例發揮作用,特別是前文作為對比的第7 條公眾參與原則。但第5 條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實踐卻幾乎乏善可陳。如學者所說,“如果說《環境憲章》作為整體的法律可訴性已經不再構成問題,那么風險預防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被理解的。”①Michel Prieur, ? Promesses et Réalisations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 Les Cahier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 43, avril 2014, p.13.從司法哲學的角度來講,這種狀況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最高行政法院阿吉拉(Yann Aguila)法官在一次發言中透漏了玄機:“在面對抽象的憲法表述時,法官通常要表現得較為謙卑(modeste),必須小心翼翼。”②這是阿吉拉法官在“中法憲法上的環境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7 月3 日至4 日)上的發言。
四、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修憲案風波
除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適用《環境憲章》第5 條進行審查外,議會也一直在更寬泛的法律政治意義上關注其整體實施情況。通過多次效果評估,風險預防原則的問題逐漸顯現,甚至在2014 年醞釀出一場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修憲風波。
(一)風險預防原則憲法實施的效果評估
自2005 年入憲以來,議會多次對風險預防原則的實施狀況進行效果評估,并通過公開報告和辯論來深化關于該原則的認識。第一次評估是在2009 年《環境憲章》實施五周年之際,議會兩院專門就風險預防原則的實施情況進行了審議。研究報告認為,第5 條在適用中遇到諸多困難,最主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公眾而言日益導致情緒化和非理性至上,社會公眾往往將潛在的風險和確證的風險相混淆,而且只是源于想象的危險逐漸成為公眾所感到的危險;另一方面是對科研和經濟活動形成了阻礙作用,比如,科研工作和經濟活動由于風險舉證責任的倒置而淪為內在不正當,它必須一直負責證明自身的正當性。因此,“有必要更好地限定(encadrer)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條件”。③Rapport sur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Bilan 4 Ans après sa Constitutionnalisation, Office parlementaire d'évaluation des choix scientifiques et technologiques, Audition publique du 1er octobre 2009, p.3.
在2010 年,議會再次以公開聽證和辯論的形式調查風險預防原則在實施中的問題。在本次調查中,風險預防原則繼續引發各方面爭議。研究報告認為,盡管第5 條的實施存在諸多問題和爭議,但其修改甚至廢除涉及到非常多的現實因素,需要基于更深入的研究和在更廣泛的政治框架下作進一步考慮。該報告同時對第5 條的表述提出若干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諸如:是否有必要“通過限定風險預防原則的概念”從而減輕條文模糊性也消除該原則對創新的阻礙作用?是否應將“嚴重的和不可逆轉”中的“和”改為“或”從而與里約宣言相一致?是否有必要為“采取臨時的和成比例的措施”增加“以可接受的經濟成本”作為限定性狀語?④Rapport d‘étape sur l‘évaluation de la mise en ?uvre de l‘article 5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relatif à l‘application du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enregistré à la Présidenc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8 juillet 2010 pp.128-129.
在2012 年,議會專門就風險背景下的創新問題進行公開聽證和辯論。相關研究報告認為,“應當承認,風險預防原則在機制上或在本質上會導致阻礙創新的極端安全性規定(dispositif ultrasécuritaire)。問題主要在于該原則的輪廓缺乏明確性,從而經常導致情緒化或政治性的適用。”①Rapport n° 286 (2011-2012) sur L'innovation à l'épreuve des peurs et des risques de MM. Claude BIRRAUX, député et Jean-Yves LE DEAUT, député, fait au nom de l'Office parlementaire d'évaluation des choix scientifiques et technologiques, déposé le 24 janvier 2012, p.175.因此,該報告圍繞如何更明確地界定風險預防原則提出了若干建議,以便為化解風險預防和創新的沖突提供可行方案。這次公開聽證和辯論間接導致了《環境憲章》第5 條修憲案的提出,為后繼的相關修憲進程奠定了基礎。
(二)風險預防原則的修憲案
通過前幾次效果評估以及相關的公開報告、審議和辯論,風險預防原則的問題逐漸清晰。2014 年5 月21 日,參議員熱拉爾(Patrice Gél ard)針對風險預防原則正式向參議院提出修憲案。其在理由報告中直陳,風險預防原則除因內容難于理解且性質充滿爭議而在司法適用中幾乎沒有發揮作用外,主要問題是在寬泛的法律政治意義上,引發了社會公眾和公共政策決定者的一定誤解,“風險預防原則經常被誤解,完全理解為科學存疑條件下的棄絕原則(principe d‘abstention),而不是作為一種作為原則(principe d‘action),因此,逐漸導致科學研究和經濟創新的停頓”。②Rapport n° 547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3-2014, p.22.公權機關和私人部門在面臨批評、傳媒風險和基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多種訴訟救濟威脅時往往進行自我審查,盡管這些司法救濟并不發達,在面對潛在風險時,人們甚至不肯為更好認識風險而進行科學評估。
據此,熱拉爾在所提修憲案中確定的基本思路是,在更明確表述風險預防原則的同時增加與其并列的創新原則(principe d‘innovation)。③該提案內容及理由說明可參見Rapport n° 547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Sénat Session Ordinaire de 2013-2014, p.39.這一思路在參議院委員會審議過程中基本得到采納。但參議院沒有將創新規定為原則,而是公權機關在風險預防原則項下所應承擔的與預防風險同等的義務。具體而言,參議院最終采納的修憲方案是,將《環境憲章》原第5 條增加兩處限定,同時新增一款作為第二款(下劃線部分為新增內容):
當損害的發生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和不可逆轉的影響時,盡管根據科學知識這種損害的發生是不確定的,公權機關仍應通過適用風險預防原則,在其職權領域內并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條件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和以可接受的經濟成本采取臨時的和成比例的措施來防止損害的發生。
通過鼓勵創新和技術進步,公權機關同樣(également)應確保科學知識的發展,從而實現對風險的最優的評估和對預防原則的最匹配的適用。
為配合新的風險預防定義,第7 條和第8 條進行附帶修改。第7 條的公眾參與原則④該條原只有一款,內容為:“在法律規定的條件和限制下,每一個人都有權獲得由政府當局掌握的與環境相關的信息,并參加會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公共決定的制定。”增加兩款,具體內容為:“公共信息和公共決定的制定尤其應依賴研究結果的傳播,并訴諸于獨立和多學科的科學專家鑒定。”“科學專家鑒定的獨立性和研究結果的公布,其條件由法律予以規定。”第8 條的環境教育和培訓修改為:“環境教育和培訓以及科學文化的促進應該為實施本憲章規定的權利和義務作出貢獻。”①Proposition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 Adoptée par le Sénat, visant à modifier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pour préciser la portée du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N° 63 Assemblée Nationale, Enregistré à la Présidenc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6 juillet 2017.
(三)修憲案的政治不確定性
前述修憲案于同年5 月27 日以參議院第183 號法案得到一讀通過。目前,前述修憲案的最新狀態是于2017 年7 月6 日提交國民議會議長,編號為國民議會第63 號法案。按照法國的修憲程序,議會議員提出的修憲案,必須以內容一致之文字由議會兩院表決通過,之后須經全民公決批準后始告確定,但如果總統將修憲案提交兩院聯席會議審議,且以聯席會議五分之三多數通過,則無須交付全民公決。面對未來復雜的修憲程序,《環境憲章》第5 條的修正能否最終完成還取決很多政治因素,有待于結合未來發展作進一步觀察。現任總統馬克龍秉持“在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尋求平衡的原則不會變”,②陳曉徑、張海濱:《馬克龍當選與法國未來環境氣候政策走向》,載《法國研究》2017 年第3 期,27 頁。但似乎無意在憲法層面采取措施。
五、風險預防:中國問題與法國經驗
在我國,整個實在法體系尚未明確承認風險預防原則,③2013 年修正的《傳染病防治法》第19 條規定國家建立傳染病預警制度,其中的預警與風險預防具有一定相似性。法學界嘗試通過規范釋義從既有法條的零星表述中推導風險預防原則。這種研究思路不僅失之主觀,而且從法國經驗來看,可能引發重大缺陷。
(一)風險預防的實定法空白
從環境法學到憲法學,風險預防原則進入我國法學話語體系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也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然而必須承認,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一直都停留在學理層面,并沒有明確進入實定法。在新《環境保護法》修訂初期,彭峰教授曾提出,“風險預防原則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而言,還只是一個空中樓閣,在環境保護法對其作出規定,時機尚不成熟,即使宣誓性的作出規定,也僅僅是停留在口號層面,離現實還是如此遙遠。”④彭峰:《環境法中“風險預防”原則之再探討》,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2 期,129 頁。
2012 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初次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國家環境保護規劃應當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突出重點、全面推進的原則”。2014 年修訂通過的《環境保護法》第5 條規定:“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其中的“保護優先、預防為主”似乎可以在寬泛意義上包括風險預防,但應當指出的是,相關立法背景資料從未明確提及風險預防的內容。
在我國現行憲法中,也從未出現“風險”以及“風險預防”的概念,唯一在字面上與風險預防存在關聯的是憲法第26 條第1 款,“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其中的“防治”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可以包括風險預防,但從原旨解釋的角度出發,這種理解并不能得到相關制憲或修憲背景資料的支持。
(二)風險預防的學理解釋及其不足
法學界嘗試基于規范釋義來填補前述實定法空白。對于新《環境保護法》第5 條,竺效教授認為“該條的‘保護優先’原則的學理表述應為風險防范原則”。①竺效:《論中國環境法基本原則的立法發展與再發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 年第3 期,12 頁。 該條規定:“國家為將來之世世代代,負有責任以立法,及根據法律與法之規定經由行政與司法,于合憲秩序范圍內保障自然之生活環境及動物。”關于該條的學理分析,可參見張翔、段沁:《環境保護作為‘國家目標’——〈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0a 條的學理及其啟示》,載《政治與法律》2019 年第10 期,2-16 頁。在憲法層面,王旭教授嘗試借助“保護”“保障”“提倡”“改善”“發展”等措辭實現風險概念的憲法教義學建構并發展出國家的風險預防義務,認為“從規范語句出發,我們可以從中國憲法文本中提煉出7 個風險領域”。(王旭:116)
前述兩種代表性釋義方案盡管分布在環境法和憲法兩個領域,卻具有一個共同點,即都默認風險預防原則應當得到褒義的評價,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都從法條中“無中生有”地解讀出風險預防原則,并認為風險預防主要是國家的義務。在筆者看來,這種促進法治進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方法卻并不可取。之所以說其“無中生有”,是因為此種解釋方案過于脫離法律文本及其立法原意,其解釋方法也得不到法學方法和方法論的有效支持。
(三)對既有研究的反思與批判
前述研究取向更為重大的隱患在于“好心辦壞事”。因為基于法國的經驗和教訓,風險預防原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助于在風險實際到來以前將不確定的風險化解于無形(至少是降低其損害的程度),同時也可能對科技和經濟創新產生強烈的阻礙作用。因此,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認知必須全面,不能只看到其優點。法國《環境憲章》實施過程中的各類評估一直建議給予風險預防原則一個清晰的輪廓,在對國家課以風險預防義務的同時為公權機關提供一個明確的操作指南,從而減少其弊端。但如果按照前述的規范釋義方案,風險預防的規范表述恰恰是極度模糊的。如此確立的風險預防原則或義務本身恰恰隱藏著極大的缺陷,更何況根本不可能期待通過司法審查來予以糾正。因此,風險預防的討論特別是憲法學討論應當務實,尋求以精確的措辭審慎建構國家的風險預防義務。
在現代各國憲法中,僅法國明文宣告并定義風險預防原則。1988 年巴西憲法第225 條第1 款第5 項隱含了國家的風險預防義務,②第5 項所規定的政府的義務是“控制對生命、生活質量和環境帶有風險的技術、手段和物質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德國基本法第20a 條①竺效:《論中國環境法基本原則的立法發展與再發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 年第3 期,12 頁。 該條規定:“國家為將來之世世代代,負有責任以立法,及根據法律與法之規定經由行政與司法,于合憲秩序范圍內保障自然之生活環境及動物。”關于該條的學理分析,可參見張翔、段沁:《環境保護作為‘國家目標’——〈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0a 條的學理及其啟示》,載《政治與法律》2019 年第10 期,2-16 頁。為風險預防提供了基礎和依據。除此以外,尚未有其他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風險預防義務甚至將其上升為憲法原則。相比之下,在環境立法包括環境法典中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完整、詳盡、細致的規定,在世界范圍內似乎是一種更為可取的辦法。法國憲法特立獨行的環境理想主義通過其風險預防原則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特殊的警示作用。
本文認同風險預防原則據以存在的風險社會前提,對該原則本身也不持有任何異議,更不反對國家以適當方式來積極預防各種風險。但在承認、肯定并支持該原則的前提之下,本文旨在從憲法層面強調一種審慎的必要性,即風險預防原則本身具有模糊性和爭議性,其不當適用所產生的弊端可能更甚于沒有該原則,因此應當對該原則進行更為深入、周全和審慎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為該原則尋找適當的定位。相比于模糊地入憲,似乎更為可行的方案是將風險預防原則明確寫入未來的環境法典,②王小鋼教授主張在我國未來環境法典的法律原則條款中規定具有包容性的風險預防原則,參見王小鋼:《環境法典風險預防原則條款研究》,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 年第6 期,42 頁。并賦予其明確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