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變的“無能為力”
乒乓臺
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趴在長毛絨毯上,慢慢抬起的頭遮住遠景里的臀,蓬松的金發(fā)下露出一張無憂無喜的臉,倔強的厚唇抵制笑意。這是性感女神的第三十一個銀幕角色,第一次出現(xiàn)在法國新浪潮電影里。有八卦說片頭的裸體是導演找裸替完成的,確實,加上標志性的紅藍濾鏡、標志性的身體局部問答題,如此突顯的并非芭鐸的美,而是導演的任性—還有挑釁。
這是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第六部劇情長片:一九六三年的《蔑視》,也是他第一次擁有大成本的跨國制作,換句話說,也是他第一次慘遭資方束縛手腳。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戈達爾的反抗由內到外,后勁強大,時隔五十三年,這部名叫《蔑視》的電影重回大眾視野,經(jīng)典大全景出現(xiàn)在二○一六年戛納電影節(jié)的官方海報上。

《蔑視》中的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
戈達爾既是導演,又是編劇,這部影片改編自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第四部長篇小說《鄙視》。莫拉維亞晚年曾說這是他最好的小說之一,既有深刻的感受,又有完全的創(chuàng)造。從二十二歲出版處女作《冷漠的人》開始,莫拉維亞始終精于塑造具有現(xiàn)代性特質的中產階級男性,他們大都自我意識過剩,經(jīng)濟條件尚可,或者說有不錯的賺錢能力,但他們并不能夠得到幸福。這些中產階級及其以上階層的人物都顯示出一種很適宜被歸納到“現(xiàn)代性”的無能為力。然而,那終究是半個世紀前的創(chuàng)作,在無意識呈現(xiàn)的男性視角下,即便是莫拉維亞這樣洞悉人性的大作家也難免在刻畫女性形象時落入大男子主義的窠臼,因而在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當代讀者看來,這個故事并不只是男性因為女性的不可捉摸而苦惱,倒有點像“普信男”自命清高、自毀幸福的反面教材。好在婚姻、兩性關系的本質并沒有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得到根本性的改良,所以這個有關忠誠、背叛的故事依然能讓人深思:相愛的人為何互相鄙視?妙就妙在戈達爾對莫拉維亞的改編恰恰弱化了這一點,無論是資本的介入還是戈達爾骨子里的新浪潮意識,都讓他避開了這個雷區(qū)。在莫拉維亞的書中,鄙視的起源被描述成一個緩慢的、背情棄義的過程,小說的某些段落不乏挖苦,甚至憤怒和暴力,影片中,這些負面情緒都不存在了,愛情轉變成鄙視的過程既是轉瞬即逝的、又是整體性的,沒有漸變,也沒有層次,而且不可逆轉,極富隱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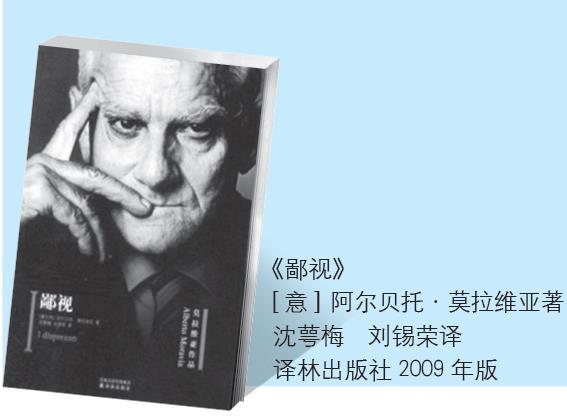
吸引戈達爾的是籠罩在夫妻關系之上的另一層關系:電影和創(chuàng)作。小說的男主角是意大利編劇里卡爾多·莫爾泰尼,理想是創(chuàng)作舞臺劇,但為了還房貸,給新婚兩年的愛妻埃米麗亞一個家,不得不靠寫電影劇本賺錢。制片人巴蒂斯塔請來德國導演賴因戈爾德,要拍一部以奧德賽為主題的大片,還邀請他們一起去卡普里島寫劇本。莫爾泰尼夫婦的感情本來就處于動蕩之中,美麗但憤懣的埃米麗亞最終棄他而去,跟巴蒂斯塔一起驅車回羅馬,途中因車禍喪生,里卡爾多哀傷不已。這是一個溝通無效的主人公,意大利文壇把里卡爾多視為第一個文學作品中面臨危機的知識分子形象,類似的人物將會充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小說和電影,尤其是安東尼奧尼的《奇遇》(1960)和《蝕》(1962),這類人物創(chuàng)作靈感的枯竭總是通過情感破滅來展現(xiàn)的。莫拉維亞也不是無中生有寫電影界故事的,他擔任過很多部意大利電影的編劇,當過記者,還創(chuàng)辦了文學刊物《新主題》,因此和名導皮耶爾·保羅·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成了至交。莫拉維亞是在跟進馬里奧·卡梅里尼(Mario Camerini)的電影《奧德修斯》的拍攝準備工作之后寫出了《鄙視》。
戈達爾當導演前寫過影評和劇本,對這個人物想必很能感同身受,對史詩電影要不要拍成好萊塢式的聲光電大片這類問題也一定有自己的思考,和安娜·卡麗娜的關系也走上了下坡路……詭異的是,書中的里卡爾多和真實世界里的一位編劇高度相似,他叫維達里亞諾·龐加蒂,是個西西里的小說家,后來為一九五四年羅貝托·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導演的電影《游覽意大利》擔任編劇。據(jù)說,龐加蒂親口對莫拉維亞說他在《鄙視》中看到了自己的故事:他也想做戲劇,開始寫劇本就是因為妻子想要一所屬于自己的房子;但就在他能成功地為她買房的那一天,她把他甩了。莫拉維亞開始寫作《鄙視》的時候,正值羅西里尼的這部電影在意大利上映。兩個故事的情節(jié)也很雷同,講的都是一對處在情感危機中的夫婦去意大利南部,但羅西里尼的電影里的夫婦最終達成了和解。更詭異的是,《游覽意大利》這部電影的海報就出現(xiàn)在戈達爾的《蔑視》中,在那座即將荒廢的意大利電影廠的墻上。還有影評家指出,戈達爾這次拍攝奧德賽主題的神話人物時所采用的手法儼如在向羅西里尼致敬:羅西里尼用長時間的全景拍攝那不勒斯美術館中的古希臘雕像,戈達爾也讓雕像長時間地出現(xiàn)在藍天白云的背景中。
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是“電影”這個主題把戈達爾和莫拉維亞乃至羅西里尼聯(lián)系在了一起,而非“感情”—無論是鄙視、忠誠、背叛還是深陷在任何歷史時期的窠臼中的任何人性元素。莫拉維亞以筆力刺穿了現(xiàn)代男性知識分子的痛處,窺到了細微的深處;而戈達爾從那刺穿的洞口往外看,跨在兩性間永恒的裂縫上,將現(xiàn)代化的弊端加以拆解和跳接,將更宏大的矛頭指向電影界和文化界。莫拉維亞的文本封閉在里卡爾多的內心,是內向的剖析和傾訴;戈達爾的電影從頭到尾充滿指涉,滿屏隱喻,話不多說,都是言外之意,全留給觀眾去解讀。為此,戈達爾搬出了新浪潮歷史上最強大的明星陣容—
最厲害的明星:弗里茨·朗
戈達爾徹底取消了敘事者的視點和內心獨白,轉而側重對電影藝術的表態(tài),擔綱這個重任的是電影里看似配角的老導演,由弗里茨·朗(Fritz Lang)飾演的弗里茨·朗—但也不能說這位鼎鼎大名的老導演飾演的就是自己,確切地說是化身為理想、經(jīng)由戈達爾認證的符號化形象,他詮釋了電影藝術的精神內核、坦誠而堅忍的創(chuàng)作實踐,他是這部電影里唯一得到戈達爾袒護的人物,除了他之外的另外四個人物都是被觀察、被評判的對象。
那一年,朗已有三年沒拍電影了,一只眼睛已近失明。這位德國著名導演、編劇、制片人和演員曾在一九二七年導演《大都會》,一九三一年執(zhí)導《M就是殺手》,堪稱影史上的絕對經(jīng)典。朗在一九三三年逃離了納粹主義下的德國,因而要在好萊塢找到折中的辦法。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好萊塢電影工業(yè)興起,和歐洲電影之間產生了鴻溝,像朗、羅西里尼這樣的老導演被好萊塢資本壓制著,被逼到無片可拍的困境。
戈達爾是朗的崇拜者。他曾說過,新浪潮導演的前幾部作品都是“影迷”拍出來的,所以,他一直很喜歡讓他心目中的哲學、政治、詩歌和電影界的杰出人物客串他的電影。比如在處女作《筋疲力盡》中,他讓著名的黑幫片導演讓-皮埃爾·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演了一位時髦的小說家,在《狂人皮埃羅》中,男主人公在碼頭堤壩上遇到了戲劇表演藝術家雷蒙德·德沃斯(Raymond Devos);但這次不一樣,朗不是單純的客串,而是被強烈賦予了精神內蘊,甚至和原著小說中的人物截然不同,毋寧說這是戈達爾在電影中創(chuàng)造的人物。就在拍攝《蔑視》的這一年,呂克·穆萊(Luc Moullet)在《今日導演》系列中論述了朗的成就。碧姬·芭鐸飾演的卡米耶穿著浴袍讀的就是這本書。這種明顯的指涉是戈達爾的標志性手法之一,但時過境遷,當代觀眾需要注腳才能領悟個中深意。
在莫拉維亞的小說里,德國導演賴因戈爾德是個年輕人,對于二戰(zhàn)后的歐洲思想有著自己的反思(諸如“文明對于所有不開化的人來說,常常意味著貪污腐化”等),還善用弗洛伊德理論分析史詩中的人物,正是在他解釋奧德賽拖延了十年才回到妻子身邊的緣由時,害得里卡爾多自行代入,擺脫不了自己被妻子鄙視的困惑和恥辱。在小說中,這個人物的重要性在于:他承擔了“史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精神世界”和“戰(zhàn)后意大利中產知識分子的日常世界”之間的紐帶。

電影《蔑視》劇照,左二為弗里茨·朗(Fritz Lang)
戈達爾改變了這一點,完全顛覆了導演和精神世界的關系:朗不僅忠于荷馬史詩,更要以尊重古典文本的方式來拍這部電影,他的言談間會引用但丁、高乃依、荷爾德林和布萊希特。朗不要拍好萊塢大場面的《奧德賽》,也不想拍被精神分析理論修訂過的版本。電影開始時,一行人在放映廳里,朗在畫面的中央,被身后的放映機的光束照亮,他伸出手,眾神的畫面就出現(xiàn)了。這種鏡頭語言宛如在暗示:朗,這位導演,是《奧德賽》的創(chuàng)造者,儼如造物主。眾神和凡人的關系就是命運,鄙視的故事也由此上升為悲劇。
電影中的導演和編劇不再是對立關系,小說中的人物關系就要做出適當調整,戈達爾就將小說中的意大利制片人改成了美國制片人,通過改變國籍,戈達爾把小說中的兩層矛盾(文化的和情感的)擴大到整個電影史,直面新好萊塢與歐洲作者電影間的沖突關系。為此,戈達爾又選了一位恰到好處的明星—
最可憐的明星:杰克·帕蘭斯
杰克·帕蘭斯(Jack Palance)一九一九年出生于賓夕法尼亞,是煤礦工人之子,前職業(yè)拳擊手,二戰(zhàn)期間是飛行員,因在一場飛機火災中毀容,做了整容術,因而有一張很獨特的面孔,似乎總帶著笑意,還有點土氣。這張臉,加上魁梧的身材,讓他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電影中的招牌壞人,或是野蠻人。到了九十年代,他憑借《城市鄉(xiāng)巴佬》中的表演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但吸引戈達爾選用他的并非演技,純粹是形象—在此之前,帕蘭斯演出的多半是惡徒、殺手。據(jù)說,帕蘭斯剛到劇組時曾真心實意地和導演交流,但提出的各種建議都被否決了,后來他只能和布景師閑聊,可憐那個法國人只會十幾個英語單詞。
在《蔑視》中,他是好萊塢電影的面具化人物,直指戈達爾鐵了心要批判的那種壞蛋:來自好萊塢的制片人,還有了不同于小說人物的新名字—普羅科施。他開一輛紅色的阿爾法-羅密歐,他的電影品位可謂粗野,在觀看半裸女演員在水中撲騰的鏡頭時露出粗俗的大笑,生氣時又像擲鐵餅那樣粗暴地扔出碟盤,聽到“文化”一詞就會掏出支票本,簽支票時讓女助手俯下腰,就像古羅馬暴君在奴隸的背上用蠟板寫字。他送給編劇一本關于古羅馬繪畫的書,說是要幫助他的改編工作,但編劇的回應是:“《奧德賽》是用希臘文寫的。”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個極端漫畫化的人物,只用英語,不尊重翻譯,喜歡用專橫的“Yes or no?”來結束句子,沒有文化,還是個暴發(fā)戶式的自大狂。帕蘭斯的指涉太過明顯,簡直沒資格被稱為“隱喻”,而是明明白白的明喻—儼如一切鄙視的根源和對象—戈達爾這樣做實在很任性,簡直有點孩子氣。
他也沒有照搬書里的結尾,索性毫不留情地讓美國制片人和女主角一起死于車禍。既然如此改編了,留著他何用?既然他指涉的是獨霸強權的美國文化,那么在車禍之后出現(xiàn)的場景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了?弗里茨·朗面對純凈的藍色地中海、開闊的天空,泰然自若地要把《奧德賽》拍完,一切宛如回到電影的原點,不再有干擾。
最容易被忽視的明星:皮科利,以及戈達爾
近似透明的演技讓一位好演員在片中顯得有點暗淡,他不像艷星那樣吸睛,不像老導演那樣讓人仰望,也不像美國暴發(fā)戶那樣招搖又可笑。但戈達爾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才選擇了他,在這部電影里的五個人物里,他必須是最穩(wěn)妥、最靠譜的。他是男主角啊!
一九六三年,米歇爾·皮科利(Michel Piccoli)飾演保羅這個難度很高的角色時已經(jīng)出演過三十部長片了。戈達爾是在皮埃爾·謝納爾(Pierre Chenal)的影片《城市大搜捕》(1958)中注意到他的,拍完《蔑視》后,戈達爾還說過:“我選皮科利是因為我需要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演員。他的角色很難,但他演得很好。沒有人注意到他很出色,因為他的角色重在細節(jié)。”
改編后的里卡爾多成了保羅,里卡爾多的內心戲只能從保羅的神態(tài)、動作、言談中盡量地滲透出來,但這依然是個無法理解妻子的不安的丈夫,保羅不用太癡情,笨拙些更好。這份笨拙就是皮科利精心塑造的結果,他不斷改變說話和姿態(tài)的節(jié)奏,和芭鐸、帕蘭斯形成對比,讓彼此都有施展空間。這個男主角一點兒也不搶戲。
這和戈達爾的改編是分不開的。制片和導演被改寫后,編劇也得到了新的對位:他首先不再是糾纏于夫妻關系的苦惱的丈夫,其次,他對應了史詩中的奧德賽,猶如導演對應了造物主(荷馬),制片對應了惡魔(獨眼巨人)。對現(xiàn)代的奧德賽來說,家是要還貸,還需要犧牲理想的商品,愛人的忠貞是可疑的,他完全不知道該不該或怎樣回到珀涅羅珀的身邊;他不僅意志薄弱,缺乏奧德賽的巧舌如簧(甚至里卡爾多的憤怒反駁)和其他生存能力,還總有種歪戴帽子、手指勾著外套的浪蕩兒的氣質。書中的里卡爾多聽賴因戈爾德解釋了奧德賽的心理動因后是很不悅的,但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和被現(xiàn)代理論解構、重釋的史詩英雄一樣,都已在現(xiàn)代生活中淪落不堪。電影中的保羅卻是有這種意識的,舉止的猶疑、拖沓似乎都在暗示這一點,當他在卡普里島別墅的客廳里成為眾人略帶嘲笑、冷眼關注的對象時,就連彼此的站位都在暗示他有這份自知之明。
一九六三年對戈達爾來說是個大起大落的年份。前一年拍攝的《卡賓槍手》和《蔑視》的劇組幾乎是同一班人馬,也都由法國電影人喬治·德·博勒加爾(Georges de Beauregard)和意大利電影人卡洛·龐蒂(Carlo Ponti)聯(lián)合制片,但前者是戈達爾的第一次巨大失敗,也是新浪潮中引人注目的一次滑鐵盧:在巴黎首輪放映的兩星期里只有兩千八百人次觀影;后者卻有了美國制片人兼發(fā)行商約瑟夫·E.萊文(Joseph E. Levine)加盟—他純粹是被碧姬·芭鐸吸引來的。龐蒂是意大利電影界的老牌制片人,擁有莫拉維亞小說的電影改編權。莫拉維亞的小說里的意大利制片人巴蒂斯塔的職業(yè)生涯和龐蒂有不少相似之處。龐蒂一九五七年開始在派拉蒙公司的美國制片人生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和博勒加爾聯(lián)手,致力于革新意大利和法國電影,制作了戈達爾、梅爾維爾、費雷里和羅西里尼的影片,包括戈達爾的《女人就是女人》和《卡賓槍手》。《蔑視》是三國制片人聯(lián)手,投資金額達到五億法郎(《筋疲力盡》的成本僅為四千多萬)。意大利制片人與美國制片人都想牢牢把控改編和剪輯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部由法美兩國明星聯(lián)袂出演的“國際大片”。戈達爾按照小說的敘事主線寫了幾個不同版本、內容詳盡的劇本—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他與制片人的沖突主要在于“性愛場景”,資方堅持認為這是大眾商業(yè)電影必備的條件。結果,影片為此推遲了數(shù)月才完工,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戈達爾才同意加拍幾個鏡頭。
不難理解,戈達爾對這部電影的評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關于莫拉維亞和龐蒂,IMDB的八卦一欄只提到戈達爾說莫拉維亞的小說是“火車小說”,這句話的出處應該是《電影手冊》(1963年8月刊),“莫拉維亞的小說是庸俗、漂亮的車站小說,充斥著古典的過時的感情,盡管場景帶著現(xiàn)代性。但是人們就是經(jīng)常用這樣的小說來拍出美好的影片”。IMDB的資訊提供者們也沒有引用戈達爾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說的一段話:“我讀過這本書很久了。我非常喜歡它的主題。既然我要為卡洛·龐蒂拍一部影片,我就向他建議改編《鄙視》,一個章節(jié)接一個章節(jié)地遵照著拍。他先是答應了,然后又因為害怕而反悔了。我建議他啟用金·諾瓦克(Kim Novak)和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但他們拒絕了;他更想用索菲亞·羅蘭和馬切洛·馬斯特羅亞尼,但我不想。我們一直僵持在那里,直到我得知碧姬·芭鐸對這件事感興趣,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多虧了她,突然之間一切都變得簡單了,所有人都很高興,包括那些美國人,或更確切地說喬·萊文,他為這樁事投資了一部分,龐蒂向他保證影片會‘很商業(yè)化。接下去,我們就在意大利自由地拍攝了六周。”
他曾說過自己有個夢想:在好萊塢式的片場里,導演一部美國式的大制作。但在拍完《蔑視》的十五年后,他在蒙特利爾的講演會上是這樣說的:“這是一部我感興趣的定制影片。這是唯一一次,我能夠用大預算拍攝一部偉大的影片。事實上,對影片來說預算很小,因為所有的錢都給了芭鐸、弗里茨·朗和杰克·帕蘭斯。然后還剩下我一般拍電影要用到的錢的兩倍多一點。還剩下二十萬美元,這對當時的我來說已經(jīng)很多了,但對一部偉大的影片來說并不算巨額。”

戈達爾(Jean-Luc Godard)
里卡爾多/保羅是創(chuàng)作者,也是現(xiàn)代文明世界里一個普通的計件工人:完成訂單并收取酬勞。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電影/文化生產鏈中發(fā)揮的功能恰恰是《電影手冊》學派猛烈攻擊的對象。這一次,戈達爾自己也難逃此運,附身于保羅之身:他也是不得不出賣天賦的一個合同工。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保羅和戈達爾的相似之處—戈達爾的自我指涉—相當明顯:穿著打扮,兩人幾乎一模一樣,尤其是帽子,片中的助理導演也戴了差不多的一頂;再說品位,兩人引用的文學、電影片段如出一轍,也都對弗里茨·朗崇敬有加。
戈達爾不僅在角色身上進行自我指涉,還索性客串了一把。他飾演了朗的副手。小說講述的是寫劇本階段的故事,而電影講述的是拍攝接近尾聲,制片人強令創(chuàng)作團隊修改補拍部分鏡頭時的故事,所以,電影中就需要出現(xiàn)拍攝現(xiàn)場,戈達爾就創(chuàng)造了“朗的第一助理導演”這個角色,親自出演。一開始他只有聲音出現(xiàn),很快,他的身影就活躍起來,在船上忙碌,還時不時地遮住朗的鏡頭,繼而在拍攝獨眼巨人的片段中變得更清晰,最后,他出現(xiàn)在最后一幕中,儼如老導演的代言人,擔負著把電影創(chuàng)作進行到底的重任。
賺得最多的明星:碧姬·芭鐸
巨額投資的一半,都花在了她身上。我們的文章也將一半篇幅獻給她吧。
一九六三年是碧姬·芭鐸的翻身之年,甚至可以說是這位性感女星演員生涯的至高點。雖然在她之前,戈達爾至少看中了兩位女明星,但最終愿意冒這個風險—在新浪潮名導的影片中飾演女主角—并且沒有淪為花瓶的人是她。甚至不是被譽為“新浪潮的標簽”的安娜·卡麗娜,那時候,她和戈達爾的婚姻已岌岌可危。
換個角度想,安娜·卡麗娜可能并不適合這個角色,對卡米耶而言,她看上去好像太聰明、太鎮(zhèn)定了。根據(jù)莫拉維亞的里卡爾多的描述:“她真的并不出眾,但不知為什么,她總顯得那么美,也許是她那婀娜多姿的、柔軟的腰部襯托出了她胯部和胸部的線條;也許是因為她腰直胸挺,儀態(tài)莊重;也許是因為她的自信和氣度,以及那兩條挺直結實的長腿所顯示的青春活力。總之,她身上有那種無意流露的、天生的秀美莊重的氣質,所以才本能地顯得更為神秘和難以捉摸。”更重要的是,埃米麗亞應該是缺乏知性美的,“我沒有能跟一個與我志同道合、興趣愛好相同又能理解我的女人結婚,卻娶了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素養(yǎng)的普通打字員,她身上有著她所屬階層的一切偏見和奢望,只是因為她貌美我才娶了她。若是跟前一類女人結婚,我就可以應付貧困潦倒的拮據(jù)生活,在一間書房或一間配有家具的房間里湊合,豪情滿懷地期盼著能在戲劇創(chuàng)作上獲得成就;可是跟后一類女人結了婚,我就不得不設法弄到她夢寐以求的房子。我絕望地想道,也許我必須以永遠放棄文學創(chuàng)作這一遠大的抱負作為代價。”細究起來,在埃米麗亞鄙視里卡爾多之前—更早之前乃至之后—他始終都在鄙視她粗鄙的出身。她只有“美”是值得投資的,比如房子和婚姻。這種男性態(tài)度在當今語境下無異于一只大靶子,但凡有點女性意識的讀者都能批判男主角在物化女性。更糟糕的是,這是一個男性知識分子的自我剖白,過于清醒,過于坦白,因而更讓人深思。他徹頭徹尾地相信自己真誠地愛著妻子,對此深信不疑,甚而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如何傷害了妻子。他無法相信妻子不再愛自己的原因僅僅是因為自己讓她坐制片人的跑車、答應制片人的邀請,但事實上,鄙視的肇端并不需要他的批準、解釋或配合,只需妻子本人的感知即可成立。鄙視鏈永遠存在,不僅在兩性間,還在資本與創(chuàng)作之間。

電影《蔑視》海報,1963
戈達爾用電影主題置換了情感主題后,完全放棄了男女關系的這一條線,根本沒有興趣去討論莫拉維亞在小說中細密描摹的那種心理狀態(tài)。埃米麗亞就搖身一變,變成了卡米耶。卡米耶會讓人想到他電影中的別的女主嗎?那是當然—《筋疲力盡》的女主角帕特里夏有一段經(jīng)典的臺詞,闡釋她和通緝犯相處、幫他逃亡又向警方告發(fā)他的邏輯: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因為愛你,而是要做出判斷,既然我對你不好,說明最終是不愛你的。這個過程充滿矛盾,但顛覆了女性被動處于男性追獵、凝視下的刻板形象。在戈達爾的電影里充斥了這種現(xiàn)代男女關系,充滿了動蕩、不可靠。我們應該承認,戈達爾在大部分時間里是反羅曼蒂克的,他的電影里的性不是兩情相悅,不是情色交易,也不是性解放……說起來,帕特里夏還有一段黑色幽默的對話諷刺了電影界、時尚文化界的潛規(guī)則。當男主問她是不是一直在做電影?她回答:“哦,沒有,這得和太多人睡覺。”男主又建議她去當攝影模特,她又回答:“哦,這不行!這得和所有人睡覺。”從帕特里夏到埃米麗亞/卡米耶,她們都分明意識到了這個男權世界里司空見慣的性剝削,鄙視正是來自于這種本能的警惕。雖然埃米麗亞沒什么文化,但她非常清楚,丈夫把事業(yè)不得志歸咎于自己,潛意識里確實有可能放任制片人貪慕自己,假如因為她不喜歡這樣而拒絕這份劇本的差事,他早晚會怪罪她。這種認知不需要“文化”,不過是現(xiàn)代男女之間很基礎的博弈本能。
戈達爾在劇本中是這樣描繪卡米耶的—
卡米耶非常漂亮。她有點像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繪畫中的夏娃。她的頭發(fā)必須是褐色的,或者深棕色,像卡門那樣。她總體上是嚴肅、認真、矜持的,有時候謙遜,帶點孩子氣的天真的沖動。電影并不應該滿足于隱喻,但它知道卡米耶應該被再現(xiàn)為一朵簡單的巨大花朵,長著合在一起的陰郁的花瓣,在它們中間,在這寧靜而清晰的總體之中,一片淺色而鮮活的小花瓣以其攻擊性而發(fā)起反抗。……大部分時間如風平浪靜的海,甚至心不在焉,卡米耶會突然發(fā)怒,緊張而又無法解釋地一陣陣訴說著。我們在影片中不斷思考卡米耶在想什么,當她放棄被動麻木的境地時,她主動出擊,這種行動也總是無法預期和無法解釋的,就像一輛沿著直線行駛的汽車,突然離開路面撞毀在一棵樹上。這是激起影片中三四次真正高潮的原因,同時也構成了首要動力元素。和她的丈夫相反,后者總是在一系列復雜的理性思考之后才采取行動;卡米耶憑沖動行事,一種生命沖動,就像是一棵需要水才能存活的植物,而不是依靠心理。卡米耶和保羅之間的沖突,是由于她是純粹植物性的存在,而保羅是動物性的存在。
碧姬·芭鐸剛好可以展現(xiàn)卡米耶的這種反羅曼蒂克的存在、主動的出擊。
她一出場就是主動發(fā)問。問題非常戈達爾,因為類似的問題在《筋疲力盡》中就有過了。在紅色、藍色的濾鏡下,卡米耶趴在床上,第一時間就用美臀鎖定了觀眾—這部電影的觀眾遠遠、遠遠不止兩千八百人次了。她把自己拆分成很多個局部,一個一個地問丈夫是否喜歡:“你在鏡子中能看到我的腳嗎?你喜歡嗎?腳踝呢?膝蓋?屁股?胸部?乳房和乳頭?肩膀?手臂?臉?全部嗎?嘴?眼睛?鼻子?耳朵?”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她用越來越嚴肅的語氣說道:“那么,你愛我的全部!”而保羅的語調更加強烈、更加低沉:“是的,我全部地、溫柔地、悲劇性地愛著你。”眾所周知,這段開頭是后來應資方要求補的,戈達爾一不做二不休,不僅貢獻了本片中最近距離的寫真照,還盡可能地貼上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標簽。
戈達爾仔細研究了莫拉維亞的文本,原著共有二十三個章節(jié),時間軸長及數(shù)月,由兩段同樣長度的部分構成:第一部分在羅馬,持續(xù)了九個月,包括新婚兩年的回憶,充滿了主人公的推論、揣測和心理剖白。第二部分在卡普里島,持續(xù)三天兩夜,多了一些幻想色彩,以及富有精神性的對白。戈達爾根據(jù)電影拍攝的需求,首先濃縮了人物,僅保留了五人,但顛覆了兩人的國籍和文化屬性;其次精選了地點:意大利電影城里的走道、普羅科施的古羅馬別墅、卡普里島的別墅、加油站、事故發(fā)生時的高速公路,幾乎全是貌似廢墟的處所;還壓縮了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就在兩天內,第一天在羅馬,第二天在卡普里島。但是,在拍攝保羅和卡米耶在家里對峙時,現(xiàn)場發(fā)生了美妙的化學反應,出來了一段日后被奉為經(jīng)典的將近半小時的室內戲。因而,電影的最終形態(tài)有三個部分:經(jīng)典電影之死(約29分鐘),夫妻關系之死(約34分鐘),在神的凝視下的悲劇命運(約26分鐘)。
雖然碧姬·芭鐸在三個部分中都有引人注目的存在感,但讓觀眾(或至少是影評家們)看到她從性感女星轉變?yōu)檠輪T的段落主要就是那段室內戲。劇情大致符合原著中夫妻吵架的段落,演員的動線覆蓋了客廳、臥室和浴室,大家都注意到了芭鐸懶洋洋的、不疾不徐的說話節(jié)奏,她不需要丈夫的注視就能對鏡更換形象,形成自足的存在感。比如,點著煙的她坐在馬桶蓋上,反問追問她的保羅:“也許是我在思考一些事情,這讓你吃驚了嗎?”又比如,她躺在浴缸里讀一段弗里茨·朗對電影的觀點。諸如此類的表現(xiàn)讓卡米耶脫胎于埃米麗亞,又生發(fā)自戈達爾的電影觀念,最終穩(wěn)固地駐扎在碧姬·芭鐸的肉身上。
為什么說這生發(fā)于戈達爾呢?戈達爾已在《筋疲力盡》《狂人皮埃羅》中拍過類似的長時間的室內戲,男女主人公在極狹小的臥室、浴室里不斷交換位置、動作、事件、對白。這是最能體現(xiàn)戈達爾場面調度的空間,也是芭鐸能夠自如演繹自我的時段。他讓她在金發(fā)上戴上黑色假發(fā),穿藍色海軍上衣,穿有淡綠色花朵的連衣裙,穿黃色浴袍,用紅色的浴巾……這是一種讓性感女星的身體變得更引人注目的策略,也是戈達爾輸出海量隱喻的戰(zhàn)術。但戈達爾發(fā)現(xiàn)了這個卡米耶的自我存在感,她沒有笑容、自然而然噘起的飽滿雙唇似乎特別適宜傳達鄙視、漠視、冷眼和嘲諷的情緒。不需要五官賣力地表演,她就可以演好卡米耶。當保羅說她和粗話不搭時,她用低沉沙啞的嗓音、沒有起伏地念出一連串粗話,能指和所指產生劇烈的分裂,粗話好像突然變成了悲劇里的臺詞。相比而言,小說里的埃米麗亞似乎自始至終都是里卡爾多眼里的局部式的女人,晦暗不明,而芭鐸的卡米耶格外鮮明、立體,徹底脫離了原著的男性心理分析敘述局限。
戈達爾還用蒙太奇的手法讓卡米耶的主動性更明顯。書中,里卡爾多在卡普里島上目睹了制片人對妻子求好,吻了她的手臂,還把衣裙從她肩頭撕扯下來,但里卡爾多只是在黑暗的陽臺上站著看,全程無所作為。后來,埃米麗亞告訴他,她知道他在看。電影中,保羅在長長的別墅臺階上往上走,走到了平臺,從那個角度往下看,看到制片人和卡米耶雙雙側坐在窗沿上,她好像先往上看了看,再回過頭去刻意地親吻了美國制片人。這兩種“看”,順序不同,意義大不一樣:卡米耶顯然比埃米麗亞更敢挑釁丈夫—那個她已因鄙視而不再愛的男人。
更進一步說,戈達爾的卡米耶是被設定為神一樣的女人,對位珀涅羅珀,是被欲望爭奪的對象,是“被愛”的原型人物,是悲劇命運的主人公,也是女性主義者重述經(jīng)典時繞不過去的一個形象—我們不妨回想一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珀涅羅珀記》中是如何顛覆這個形象的!所以,在半小時的室內戲中,保羅和卡米耶輪流泡澡后,包裹浴巾的方式儼如古希臘、古羅馬人,讓浴袍垂下自然的褶皺,這讓他們在現(xiàn)代風格的小公寓里對位了戈達爾用以象征純粹電影理念的古典精神—在這個譜系里,卡米耶和朗是同一陣營的,都安然從屬自然的秩序,不受現(xiàn)代文明的惡劣影響。
讓我們退回到《蔑視》的開場鏡頭:大全景,畫面當中的路上鋪著軌道,軌道車上坐著攝影師,持著一臺笨重的攝影機,他的身邊站著錄音師,舉著高高的收音桿,對準女演員,然后鏡頭移動,軌道車慢慢地朝觀眾推進。畫外音開始念誦主創(chuàng)人員名單。戈達爾通過這樣的方式,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我在把整個影片的生產機制呈現(xiàn)給你們看。等到攝影機走到鏡頭前面,大約切到中景的時候,攝影師突然把那臺攝影機的鏡頭調轉九十度,對準了觀眾,也就是另一個鏡頭所代表的觀眾的視角。第四面墻被打破了,影片這才算正式開始。慣常的電影,或者說好萊塢的主流電影總是在強調電影的幻覺性,讓觀眾沉浸在電影里,最好什么都相信。和小說《鄙視》沉浸式的獨白小說截然不同的是,《蔑視》從一開始就強調了電影本身的存在,這些明星的出演并不是要模擬逼真的現(xiàn)實故事,而是一起投身于電影的魅力,拍出一部讓人有所思考、有所批判、有所感受的藝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