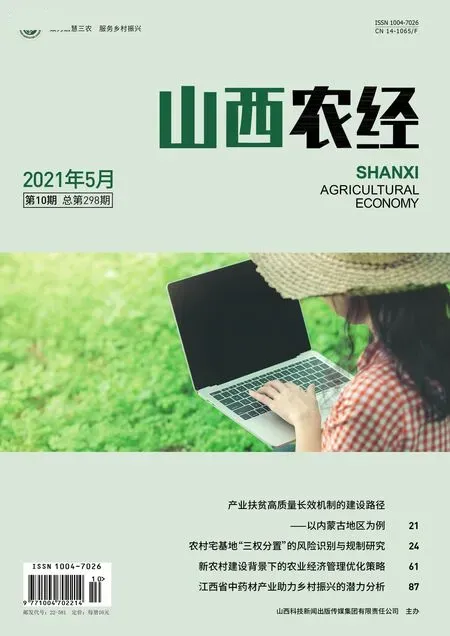“三社聯動”視野下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困境
□任曉彤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 山東 淄博 255000)
1 問題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建設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不可少的一環。長期以來,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農村地區治理模式形成了單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制。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市場化驅動,農村社區社會結構開始變化,傳統農村的基層社會管理體系已經逐步退出治理舞臺,多元治理占據主導地位。社區應運而生,彌補了農村基層社會管理的空缺,成為了農村地區新的生活共同體。在重構農村治理體系的過程中,社會組織作為社區與居民溝通的紐帶,成為提升農村社區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對農村社區治理帶來了重要影響。王思斌(2016)[1]提出,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和社會工作者在社區服務建設和社區治理等方面聯合行動、相互監督,共同進步、共同發展并實現各自職能的過程就是“三社聯動”。
目前,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學者多在探討社會自治組織、社會工作者對社區治理的影響,以及社會組織對城市社區治理的影響。
相關研究文獻表明,學者大多以城市社區作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研究重點,很少針對農村社區開展研究。分析“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對農村社區治理的影響,探尋社會組織發展困境及未來發展走向,希望能夠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2 “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對農村社區治理的影響
2.1 社會組織對農村社區治理的管理和公共服務幫助
根據村民需求建立的社會組織,充分發揮了村民的主體性作用,將農村社區資源有效整合起來,調動社區內部對政策有一定了解的人,通過社區營造和實際效果,感染其他村民,促成一致性的集體行動[2]。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利己行為驅使人們在接觸到社會組織的諸多益處后,積極響應社會組織提出的措施,自發參與到社區中來。社區居民眾多,總會有人作出利他行為,從而有利于社區健康發展。在這一過程中,需求創造收益,有效激發了多樣化管理的轉變,提高了農村社區的集體認同感。
2.2 社會組織對農村社區治理的經濟幫助
社會組織作為“三社聯動”的重要部分,在社區治理之中發揮著重要的載體作用。農村社區中,社會組織帶動著更多社會工作者加入進來,脫離了農村社區治理濃厚的行政色彩,著力為村民考慮,營造了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3]。
近年來,在政府相關政策的引導下,許多社會組織滿懷社會責任來到農村社區,在經濟上給予農村社區幫助,例如援建公共基礎設施、捐贈可用物資等,用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農村社區治理中來。除直接援助方式外,一些社會組織深入農村社區,依據自身優勢建立解決經濟問題的相關社會組織,幫助農村社區提高經濟收益。
3 “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面臨的困境
3.1 社會組織自身面臨的困境
一是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種類發展不平衡。就目前來看,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社會組織大多為組織娛樂活動的組織,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較少。
二是資金及能力不足。社會組織本身存在缺乏資金及運行困難等問題,社會組織仍需依賴政府在資金、人員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由基層黨政機關設置的各種社會組織,大多過度依賴政府扶持。
三是社會組織定位不清。志愿者等公益社會組織的機制不夠完善,其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更像是“輸血式”的幫助,具有極強的偶然性和短期性[4]。社會組織的參與有時會對社區產生負面影響,使社區從依賴政府轉變成同時依賴政府和社會組織,造成了一些新的困境。
3.2 社會組織面臨的制度困境
一是缺乏制度保障,使社會組織的工作得不到配合和實現。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應由政府引導,帶動社區居民參與。缺乏完善的體系和制度,讓社會組織難以在良好制度的基礎上發揮其作用和功能。許多社會組織力量弱小,反映居民訴求和維護合法權益的能力有限,無法滿足居民的訴求和期望[5]。
二是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定義,使得參與社區治理的社會組織單一、狹隘,不能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政府支持和倡導具有法定意義的社會組織,提倡社會工作者以法定社會組織為載體為社區提供服務。單一的法定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村社區多元化的需要。應當吸納不具備法人資質的社會組織,使其有效嵌入社區,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6-7]。
3.3 農村社區治理中社會組織的現實困境
社區是一定空間的人的社會共同體。社區的研究重點并不在于其地域涵義,而在于其社會涵義。因此,詳細的社區規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著眼于人。在農村社區中,居民更在意物質生活,利己主義較為強烈。
在農村社區落實政府的治理政策時,推行難度大,配合度低,社會組織在農村社區治理中舉步維艱。大多數人對社會組織不了解,他們認為社會組織更像是政府的“民間管理員”。社會組織雖然有專業的社工知識,更貼近群眾,但在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很難發揮出作用[8-9]。
“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在農村社區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農村社區治理的道路遠沒有城市社區治理的道路好走。許多農村缺乏專門的公共服務機構,很多公共服務職能落到村委會上。村委會作為自治組織,條件有限,導致公共服務缺失,使原本民主自治的美好期望難以實現。
4 “三社聯動”中社會組織的未來發展
社會組織作為中堅力量,積極參與到農村社區治理中,改變了農村社區治理“一言堂”的問題。雖然各地都對鄉村治理轉型進行了道路探索,但是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要在“完善自治、以人為本、黨政主導、科學謀劃、改革創新、分類施策、依法治理、社會協同”的原則之上,實施更具針對性的措施。
4.1 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社會組織作為政府和村民的橋梁,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背景。應明確社會組織的定位,建立完善的民間組織發展體系,形成科學的運作體系。政府可以嘗試民辦公助、委托服務,加大力度推進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和社會組織轉移職能,深入研究政府購買的事項和范圍,將服務性事項委托社會組織承接。
4.2 依托當地鄉風民俗建立社會組織
農村社區治理離不開當地的文化習俗。“中國鄉土社會是一個有著歷史維度,儲存著文化傳統、人文情懷、社會記憶和群體意識的復雜場域,更是一個物理空間”,鄉村振興既要“塑性”,也要“鑄魂”。在嵌入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社會組織要結合當地鄉風民俗與文化資源,因地制宜地開展建設。
4.3 加強社會組織與社區村民之間的了解與溝通
目前,農村社區的村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程度不夠,對社會組織的信任程度有待加強。“沒有堅定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會顯得沒有厚度和深度,就不會牢固和持久”。只有讓村民全面了解相關情況,了解社會組織是什么、干什么和怎么干,多元主體治理模式才能贏得信賴和支持[10]。這就需要設立公共信息資源平臺,讓社會政策、政府舉措更加透明和公開。發揮社會組織與社區村民之間的協調作用,使社會組織嵌入到農村社區治理中去,代替“碎片化”的權力體系。
4.4 加強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
社會組織在有條件和機會參與到農村社區治理時,要抓住機遇,因地制宜提出解決辦法和舉措。通過文獻閱讀和實地調查發現,雖然大多數社會組織有專業社工,但很少有社會組織能夠對社區現狀進行系統分析。
社會組織要善于運用各種社會調查方法,獲取反映實際情況的材料,并通過統計方法將收集到的材料量化,以便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只有切實依托專業優勢,促進社會組織的成長和發育,才能為改善鄉村治理低效的困境帶來活力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