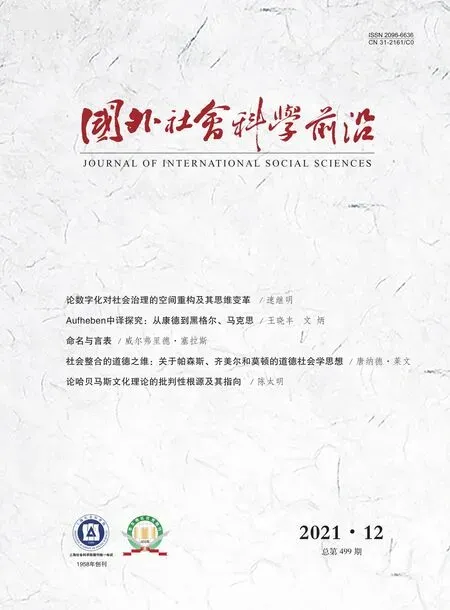命名與言表*
威爾弗里德·塞拉斯/文 馬芳芳 王 瑋/譯
一
我即將論述的諸話題根源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我的出發點將是歐文·柯匹(Irving Copi)教授的論文《<邏輯哲學論>中的對象、特性與關系》。1Irving M. Copi, Objects,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in the Tractatus, Mind, vol. 67, no. 266, 1958, pp. 145-165.其中,在果斷批判了對維特根斯坦所謂的(尤其有關關系陳述的)意指圖畫論的某些錯誤解釋之后,他繼續(根據對某些文本的一種絕非看似不合理的解釋)歸給維特根斯坦一個令人困惑的構想,即維特根斯坦的對象是“裸殊相”(bare particulars)。1Irving M. Copi, Objects,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in the Tractatus, Mind, vol. 67, no. 266, 1958, p. 163.
我不會浪費時間去表述相關的錯誤解釋和總結柯匹令人敬佩的清晰批判。因為我關心的是(在我看來)他正確歸于維特根斯坦的關于作為圖畫的關系陳述的理論,確切地說,是這個理論闡明一般來講關于述謂的傳統哲學困惑的能力。
關鍵的碼段當然是3.1432,“我們絕不能說:復雜指號‘aRb’言表‘a和b處于關系R’;但我們必須說:‘a’和‘b’處于某一關系言表‘aRb’。”維特根斯坦的部分觀點是,雖然名稱和陳述作為指號設計的例證它們的經驗特征都是復雜的,從而(從他的視角看)同樣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即一個名稱由相關系的部分(以各個方式)組成,與它是名稱相關,不同于(圖式來講)
aRb
這樣一個陳述就分為部分“a”“R”“b”與它作出它所作出的陳述相關。后面這些部分本身在(盡管不以相同的方式)發揮指號的功能,而名稱沒有任何部分在發揮指號的功能。不過,當我們問,“相關陳述的部分(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對于它是陳述必不可少)是什么?”,維特根斯坦在闡明的關鍵就出現了。因為,盡管明顯的回答似乎會是“‘a’‘R’‘b’這三個表達式”,但這個回答卻不正確。確切地講,雖然“R”正在廣義上發揮指號的功能,而且肯定參與這個陳述言表其所言表的,但是,根據維特根斯坦,它以一種完全不同于指號“a”和“b”的方式參與。說“R”在發揮謂詞的功能,而“a”和“b”在發揮名稱的功能,雖是定位不同之處,但依然面臨困惑。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的是,雖然表面上看該陳述是三個部分“a”“R”“b”的串聯,但是更深入看它是一個二項事實,“R”進入該陳述來使得表達式“a”和“b”以某一方式二元關系,即,使得表達式“a”和“b”以其間有一個“R”的方式關系。他在闡明,對于任何會言表aRb的陳述必不可少的,不是名稱“a”和“b”有一個關系語詞在它們之間(或在它們之前,或與它們處于任何其他關系),而是這些名稱以某個方式(二元)關系(不管這其中有沒有使用第三個指號設計)。確切地講,他是在告訴我們,承認我們可以通過書寫與“b”處于某一關系的“a”(只用這些指號)而非在“a”和“b”之間書寫“is next to”來表達命題a is next to b,是在做哲學闡明。我們會用一種清晰語言來這樣做。假定混沌人(Jumblies)有這樣一種語言。它不包含關系語詞,但有和我們整齊的英語一樣的名稱表達式。然后我們可以通過作出
“”(在混沌語中)意指a is next to b
這樣的陳述來將混沌語翻譯為英語,準備做哲學闡明。在這方面尤其有趣的會是把《顯象與實在》翻譯為混沌語。
注意,我將這個事實,即在“aRb”中“R”扮演謂詞的角色,和這個事實,即在混沌語中“aRb”所表達的命題會通過不使用謂詞表達式關系兩個名稱來表達,關聯了起來。現在,在弗雷格的系統中,會說“R”代表(bedeuten)一個概念,而“a”和“b”代表對象。因此,維特根斯坦通過說對象的配置由名稱的配置來表示(3.21)——從而混沌語 “”和PM語“aRb”同樣是兩個名稱的配置,盡管后者不清晰——所表述的也可以這樣說來表述,即我們使它們的名稱符合一個n元概念來表示某些對象符合一個n元概念。1使名稱符合哪個n元概念當然(就像哲學家的使用一樣)是約定問題。大致地講,維特根斯坦的配置對應弗雷格概念的一個子集,而且維特根斯坦在向弗雷格提出異議,堅稱一種清晰語言不會包含發揮謂述功能(那就是說,當我們說aRb時“R”發揮的功能)的概念語詞。一種清晰語言怎么會起到非謂述使用的概念語詞起到的作用,維特根斯坦沒有怎么說明,不過他對并行問題,即一種清晰語言會怎么處理信念陳述(其中,根據弗雷格,從句的Bedeutung是通常會是的它的意義),的簡略處理對回答給出了提示。
現在,上述評論概述了很多對存在論和邏輯哲學來說重要的話題。其中一些我將在論證后期繼續。不過眼下我將聚焦問題“維特根斯坦的對象是什么樣的東西?”首先我要說的是,在我看來,柯匹堅持維特根斯坦的對象是殊相,這毫無疑問是對的。用一種略微不同的方式來表述這一點,維特根斯坦的名稱是殊相的名稱。當然,這不是說,在含糊語言中以一種表面類似名稱的方式發揮功能卻不命名殊相的表達式沒有意指。而只是說,它們不會翻譯為清晰語言的名稱。大致地講,含糊的類似名稱的表達式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分屬兩個范疇:(1)會翻譯為清晰語言的,就像(根據羅素的描述語理論)含有描述短語的陳述翻譯為獨特的實存句(existentials)(比較維特根斯坦在3.24中對復雜項的處理);(2)(更有趣的是)根本不會翻譯為清晰語言的那個部分:其用來作關于在世界中什么是這樣或不是這樣的陳述。就是后者在一個特殊意義上沒有意指,但不是在任何日常意義上沒有意指。它們提及的“對象”或“個體”或“邏輯主詞”是偽對象,因為“提及它們”就是指出關于在世界中什么是這樣或不是這樣的話語的那些特征:其 “顯示自身”,即在清晰語言中不是作為語詞而是以語詞結合的方式顯現。2我們想起(根據弗雷格)當我們試著談論概念時我們談論的奇特對象。因此完全可以說存在不是殊相的“對象”,并作出關于它們的陳述。不過,這些對象(先不談復雜項)不在世界中,關于它們的陳述也不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的。用維特根斯坦的術語來講,沒有關于這樣的對象的陳述是“圖畫”,因此在“圖畫”有意義的意義上它們沒有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設想一位哲學家,他贊同維特根斯坦在清晰語言中這個事實,即兩個對象處于一個二元關系,會通過使它們的名稱處于一個二元關系來表示,但他拒絕認為在世界中的對象或個體只是殊相。這樣一位哲學家可能會(例如)在這個事實,即某一感覺材料(假定存在這樣的實體)是綠的,內區分兩個對象,一個其名稱可能會是“a”的殊相和一個(盡管同樣是對象或個體)不是殊相的項。我們來假定這對象的名稱是“green”。3我隨后會論述使用顏色例子涉及的危險,尤其有關將顏色語詞解釋為名稱。我們來說green是一個共相而非一個殊相,它在共相中是一個性質而非一個關系。根據這位哲學家,4我在考慮的這位哲學家是古斯塔夫·貝格曼(Gustav Bergmann)教授,我在論述的看法(我相信)會在他有趣的論文“不可說、存在論與方法”(它發表在《哲學評論》1960年1月號)的某些段落中找到。言表ais green(抽離關乎提及時間的問題)的清晰方式是將兩個名稱“a”和“green”置于某個關系,即如果我們想要說b is red我們會將“b”和“red”置于的關系。我們來假定我們書寫“Green a”。
我們之前的論述讓人想到這個問題:言表“Green a”所言表的含糊方式會是什么,即什么會之于“Green a”就像(根據維特根斯坦的看法)“aRb”之于(比如) “”?我在考慮的這位哲學家提議以下回答:
a exemplifies green(譯作:a例示green)。
這并不出乎意料,因為當(就像在這個情況中)牽涉兩個對象,要含糊就要一個二位謂詞恰當串聯(一邊)一個殊相的名稱和(另一邊)一個共相的名稱,這是我們哲學家雇傭“exemplifies”做的工作之一。因此,這位哲學家會說,就像根據維特根斯坦的看法言表ais next tob的清晰方式是通過書寫與“b”處于某個關系的“a”,同樣言表aexemplifies green的清晰方式是通過書寫與“green”處于某個關系的“a”。在這樣利用了維特根斯坦的梯子之后,他會登上他自己的頂峰。因為,他得斷言維特根斯坦以錯的例子闡明了一個深刻的觀點。簡言之,他得否認言表ais next tob的清晰方式是通過書寫與“b”處于某個關系的“a”。從以下考慮中容易看到確實如此。
例示(exemplification)不是哲學家們通常會稱之為經驗關系。這個稱呼通常留給空間并列和時間相繼這樣的關系。然而例示很可能會是在一種比通常認為的更深刻的意義上的一個(an)——或者也許是那個(the)——經驗關系,1參見貝格曼, 同上,第23頁,注釋2。如果世界中最簡單的原子事實是由“Green a”來清晰表示和由“a exemplifies green”來含糊表示的那種,那么確實如此。
因為,我們來看,如果關系陳述以一個與上述對“ais green”的處理相一致的方式來處理,那么我們通常稱之為的經驗關系會怎樣。根據上述處理,事實a is green由兩個名稱“a”和“green”并列來清晰表示,由一個語句(它包含三個表達式,其中兩個是名稱,而第三個(沒有洞察力的哲學家可能會認為它是第三個名稱)實際上是來使得名稱之間實存一個獨特的二元關系)來含糊表示。那么,顯然,對“a is below b”的并行處理會斷言它是由三個名稱“a”“b”“below”適當并列來清晰表示,比如
Below a b,
由一個使用四個表達式的語句來含糊表示,比如,或許
Exempl2我使用這個表述方式來適度地闡明觀點。不過,值得反思的是,與“a exemplifies green”語法并行的會是“a exemplifies being below b”或者“a and b jointly exemplify below-ness(一物在另一物之下的關系)”。a b below。
我隨后會評論這個解釋(即“below”是一個名稱)和這個事實(即它初步看來不如同樣之于“green”的步驟合理)。不過,我應該說我和貝格曼教授都持有可能會這樣說來表達的觀點,即日常語法是智慧之人的紙幣愚蠢之人的黃金,來作為下述評論的開場白。因為,我眼下想對比《邏輯哲學論》的述謂理論和貝格曼教授的述謂理論,盡管他顯然更喜歡掃羅(Saul)而非保羅(Paul),但絕非一個正統的《舊約》倡導者;我認為這點具有重大的哲學意謂。
然后,根據《邏輯哲學論》,事實ais belowb由一個有兩個二元關系的名稱組成的表達式來清晰表示,由一個除了這兩個名稱還有一個二位謂詞表達式組成的表達式來含糊表示。根據貝格曼教授,如果我對他的理解正確,那么ais belowb這樣的事實就是由有三個三元關系的名稱組成的表達式來清晰表示,由一個除了這三個(被適當斷開的)名稱還有一個具有“exemplifies”效力的表達式組成的表達式來含糊表示。這個不同究竟相當于什么?哪個看法更接近真相?
首先處理第一個問題,這個不同可以重新表述來揭示它與實在論者和唯名論者之間的老問題的密切關系。維特根斯坦在告訴我們世界中的對象只是殊相,貝格曼在告訴我們世界中的對象既包括殊相也包括共相。當然,貝格曼用他自己的剃刀以他自己的方式將世界剃干凈,但不像維特根斯坦那樣干凈。表述這個不同的另一個方式是說,在維特根斯坦(掃羅)看來,通過關系其關系項(relata)的名稱來清晰表達的是世界中的經驗關系,而在貝格曼看來,經驗關系作為名謂項(nominata)在關于世界的話語中出現,通過關系其關系項的名稱來清晰表達的是例示且只有例示。
為了闡明后一表述方式,有一些術語評論。如果我們這樣使用詞項“relation”(譯作:關系),即說什么它是一個關系就是說它在話語中由一個表達式配置(而非通過使用一個單獨表達式)來清晰表示,那么在貝格曼看來(先不談改進)就只存在一個關系,即例示,1嚴格地講,每個事實次序都會有一個例示關系,(根據非要素論的觀點)每個類型都會有一個家族的這樣的關系。而且通常所說的關系(例如below)會作為關系項在世界中出現。因此,如果我們要以這樣一個方式(即below會是一個關系)來繼續使用詞項“relation”,那么貝格曼理解的例示就不是一個關系。因為,雖然(他認為)below和例示都在世界中,但是前者作為一個名謂項在話語中出現,而例示不是,確切地講,不能。
為了保持清楚,以這樣一個方式,即說什么它是一個聯結就是說它在話語中由一個表達式配置(而非由一個單獨表達式)來清晰表示,來引入詞項“nexus”(譯作:聯結)是有益的。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能如下對比貝格曼和維特根斯坦:
維特根斯坦:世界中存在很多聯結。事實的簡單關系是聯結。所有生成聯結的對象或個體是殊相, 即0類型的個體。世界中不存在例示的關系或聯結。
貝格曼:只存在一個2參見上一腳注。聯結,即例示。每一個原子事態包含至少一個(如果要素論的論點為真,那么至多一個)不是殊相的個體。
如果我們這樣使用詞項“ineffable”(譯作:不可說的),即說什么(to eff something)就是使用一個名稱意謂它(to signify it),那么維特根斯坦的看法就是,通常稱為的關系是不可說的,因為它們都是聯結,都由名稱的配置來(不管是清晰地還是含糊地)表達。另一方面,在貝格曼看來,通常稱為的關系被說出;不可說的是例示。
在試著評判這些對比立場之前,我們來繞繞圈子。首先,我們來注意,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原子事實是對象的配置,比如
2.0272諸對象的配置生成原子事實。
我想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要多么嚴格地解釋這個語境中的語詞“對象”的復數。確切地說,可以有一個對象的配置嗎?必須承認,肯定的回答會聽起來很怪。但說從空類前提得出結論聽起來也很怪。“重構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們常常認為將一個視為另一個的“極限情況”是在做闡明;如果羅素(就是其中一位)愿意說一個性質是一個一元關系,那么最初還是有可能認為維特根斯坦可能會愿意說一元配置。
他會愿意這樣做嗎?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細心考察文本。我不認為2.0272單獨對理解這個問題有太大幫助。然而,當它和
2.031 在原子事實中,諸對象以明確的方式組合
2.03 在原子事實中,諸對象相互之間像鏈條一樣環環相扣
(它們沒有暗示可能會有一元“組合”或者,可以說,單環鏈條)這樣的碼段一起時,累積效果是支持這個論點,即在《邏輯哲學論》中沒有為一元原子事實準備什么。
但(至少乍一看)似乎并非必然如此。畢竟,說事實ais belowb會由一個表達式[其中名稱“a”(與“b”)處于一個二元關系]來清晰表示的人,有可能會說事實ais green會由一個表達式[其中名稱“a”處于一個一元關系,即(用一種更通常的方式來講)具有某一性質]來清晰表示。因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位哲學家,其說在清晰語言中,一元原子事實會通過以各種顏色或各式字體書寫其中單個對象的名稱來表示。這是一個常見想法。有任何理由認為這對維特根斯坦不可行嗎?
一條思路可能會是,在這樣一種符號論中我們不能區分名稱和陳述。畢竟,一個名稱得以某個樣式來書寫,要是這樣,一個名稱的每一次出現(在這假設的符號論中)不就憑借它的樣式具有一個陳述的效力,并因此根本不是一個名稱嗎?然而,這個異議高估了表達式間的經驗相似蘊涵語言角色的相似的程度。顯然,將“a”寫在“b”旁邊可能會在言表a在時間上先于b,而在“b”下方的“a”可能會根本沒有意指。因此,以黑體書寫“a”可能會是言表ais green,而普通字體的“a”可能會只發揮一個名稱的功能。隨后會論述怎么會是這樣。我現在的觀點僅僅是,理解表達式就是知道在關于它們的許多事實(形狀、大小、顏色等)中哪些(以什么方式)與其意指相關。肯定可以是這樣,即在清晰語言中,這個事實,即一堆墨跡是某一名稱的殊型,就是它是以某些方式中的某一個來書寫的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的例證。不過,這些方式中的一個或多個可能會(可以說)是“中性的”,因為以這樣一個方式書寫這名稱不會是作出一個斷定,而僅僅是書寫這名稱,而以其他方式書寫這名稱就是作出各種斷定。也就是說,只有在非“中性的”方式的情況中,書寫這名稱才會是斷定一個一元事實。
另一條思路的大意會是,在一種其中一元原子事實(如果存在的話)通過以各種方式書寫單個名稱來表達的語言中,會有一個關于變項的困難——不是關于涉及殊相的變項,因為這里可以使用讓特定字母代表變項的手段,而是關于諸如會與《數學原理》標寫的一元謂詞變項相對應的變項。比如,我們可以使用變項“x”并且以黑體書寫它,比如
x
來表示語句函項“x is green”。但我們怎么會說a它具有某個性質?什么會對應“a is f”和“(Ef) a is f ”,就像“x”對應“x is green”和“(Ex) x”對應“(Ex) x is green”一樣?我們不就得引入一個表達式來作為變項嗎——畢竟,我們不能書寫一個方式本身——而如果我們有單獨變項(即不是涉及殊相的變項)使得可能表達會在PM語中由
(Ef)fa、(g)gb等
所表達的,那這實際上不就是將據稱由(例如)
a
來清晰表示的原子命題視為牽涉兩個常項,從而兩個名稱嗎?它真正的清晰表示不就得反而是貝格曼斷言的
Green a
嗎?
想一想以下PM語和混沌語翻譯圖式:

I. 殊相的名稱

II. 陳述(不包括馬上會論述的關系陳述)

III. 陳述函項
(1)謂詞常項、個體變項:

(2)謂詞變項、個體常項:

(3)謂詞變項、個體變項:

IV. 量化


注意,在最后的混沌語樣本中,(形狀的符號用來表示中性樣式;這要看它的大小。
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混沌語形式中,中性樣式(一個表達式藉以發揮一個名稱的功能,沒有作出一個陳述)也是與PM語謂詞變項相對應的表達式例舉的中性樣式。因此,這個混沌語形式的一個有趣特征是,發揮名稱而非陳述功能的表達式具有陳述的形式。關于PM語經常說謂詞的形式是(例如)
Red x。
不那么經常說名稱的形式是(例如)
f a。
在前文簡述的這種混沌語中,后者會和前者一樣為真。(參見《邏輯哲學論》3.311。)這一點顯然應該擴展考慮到關系陳述的形式,不過,除了暗示,這里我不會試著去這樣做。
現在這個關乎謂詞變項的困難(如果有的話)不僅限于關乎這些推定的一元原子陳述的謂詞變項。如果有一點要像前文那樣闡明,那么它也關乎維特根斯坦解釋的二元或多元陳述。因此,繼續我們的翻譯圖式,我們得到

這里我們再次發現引入符號來與PM語關系變項相對應,即符號例舉這些中性方式:它們在
ab、a b、a b等
中用來表達在PM語中由陳述函項
R(ab)、S(ab)、T(ab)等
表達的。因此,除了變項“(” “(” “(”……對應《數學原理》的一位謂詞變項,我們還有變項“..”“. .”“. .”……對應《數學原理》的二元謂詞變項。
之于變項和量化的清晰性話題本身是一個有趣又重要的話題,前文的評論很粗淺。我想闡明的只是,如果關乎量化或關乎區分名稱和陳述的考慮支持這個想法,即清晰語言的原子陳述得包含至少兩個名稱,那么為此這些考慮就不是通過支持這個想法(即最小原子陳述會包含兩個殊相的名稱)而是通過支持這個想法(即它會包含一個共相的名稱)。換言之,它們會指向貝格曼的邏輯原子主義形式,與維特根斯坦的截然不同。
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我站在維特根斯坦一邊,那就是說,我會論證說一種理想語言的原子描述陳述會只包含殊相的名稱。因此,我認為,對于存在論至關重要的是,不要將常項和變項之間的差異混淆名稱和變項之間的差異。因為,混淆這兩個差異就是從這個正確的想法,即
Green a
可以對照這個雙重量化陳述
(Ef) (Ex) fx
來看,變動到這個不正確的想法,即
Green a
是兩個名稱的并列,并且清晰言表會由
a exemplifies green
所含糊言表的。
對照雙重量化陳述
(E() (x) x
來看混沌語陳述
a
其實就是強調兩個關于表達式“a”的事實,即這個事實(它藉此是某一名稱以某個樣式的書寫)和這個事實(隱喻地講green藉此進入圖畫)。不過,我看不到有何理由推斷,因為這表達式是某一名稱的實例和這表達式關乎green每個都緊密相連一個關于這表達式的一元的(不過當然不是原子的)事實,所以它關于a和它關于green都以相同的方式進入圖畫,即它們都被命名。
因為關于a和關于green每個都可以之于這表達式為真(憑借關于它的一元事實),但是不在任何更重要的意義上以相同的方式關乎它的意指。一個表達式的關鍵在于它在語言中扮演的角色,這個事實(即某一表達式是某個樣式的“a”)和這個事實(即它是黑體的)可能都是一元事實,卻在語言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這方面有必要指出,關于這表達式的一元事實(它藉此關乎green)不是這個一元事實,即它是粗體的,而是這個一元事實,即它是一個名稱或名稱變項的粗體例證。
二
在繼續本文的實質論證之前,我將再談談關于維特根斯坦自己是否“支持”一元原子事實的歷史問題。通過指出羅素可能會說原子事實是相關系的對象,但卻這樣使用詞項“relation”,即我們可以談及一元關系,我論證說其中他說原子事實是諸對象(復數)的配置的碼段不是決定性的。在我看來,類似的考慮使得
2.15 圖畫的諸要素以一個明確的方式互相結合表示諸物這樣互相結合。
3.21 命題指號中的諸單個指號的配置對應事態中的諸對象的配置。
這樣的碼段不可能解決對這個想法(即一個原子命題可以只包含一個名稱)的異議。
在我看來維特根斯坦有一次最接近于明說存在一元原子命題。因此,想一想
4.24 名稱是簡單符號。我用單個字母(“x”“y”“z”)來指示它們。
我將基礎命題寫作名稱的函項,形式是“fx”“φ(x,y)”等。
這個碼段更明顯,因為它緊隨
4.22 基礎命題由名稱組成。它是名稱的關聯,即串聯。
現在,要解釋4.24,就得指出,雖然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原子事實(大意是兩個對象二元關系)會通過將這些對象的名稱置于二元關系(不使用任何關系語詞)來清晰表示,但是《邏輯哲學論》沒有使用而只是提及(而且是間接提及)這樣的清晰表示。因此,維特根斯坦在例舉原子命題的形式時沒有使用混沌語,而總是PM語,比如總是“aRb”(參見4.24的“φ(x, y)”)。他所做的就是要告訴我們,符號“R”不用作一個名稱,而是用作一個手段來使得名稱“a”和“b”二元關系。
既然如此,維特根斯坦在4.24就是在告訴我們,當他使用具有形式“fx”的表達式來書寫一個基礎命題時,由“f”表示的函項語詞不是作為一個名稱出現,而是使得由“x”表示的名稱以某一方式出現,即在某一一元配置中出現的名稱是一個命題。
現在,如果一位哲學家聯合這兩個論點,即(1)不存在只牽涉一個殊相的原子事實,(2)所有對象是殊相,那么就可以說他承諾一個裸殊相學說。因為,通俗地講,他認為,雖然對象處于經驗關系,但它們沒有性質。注意,貝格曼的立場不會是這樣,因為雖然他認為不存在只包含一個對象的原子事實,不過他堅持存在只包含一個殊相的原子事實。因此,他可以通過堅持每一個對象例示一個性質來否認存在裸殊相。
現在,在我看來柯匹將上述兩個論點中的第二個(所有對象是殊相)歸于維特根斯坦是對的。因此,如果他將第一個論點歸于維特根斯坦是對的,那么他的斷言,即維特根斯坦承諾一個裸殊相學說,就是合理的。反過來講,如果維特根斯坦確實堅持一個裸殊相學說,那么他承諾這個論點,即不存在一元原子事實。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發現柯匹論證說他的論點,即維特根斯坦拒絕一元原子事實,受支持于他(有些不情愿地)認為的對裸殊相學說的肯定。因此,在坦言“必須承認維特根斯坦的幾個評論表明對象具有‘內在’特性也具有‘外在’特性(2.01231、2.0233、4.023)”之后,他寫道(第163頁):
盡管探討這樣的碼段有困難,但在我看來有壓倒性的證據證明他認為對象是裸殊相,沒有任何物質特性。
首先,維特根斯坦明確否認對象會具有特性。他的斷定,即“對象沒有顏色”(2.0232),得理解為提喻,因為上下文表明他的興趣不只是否認顏色性質,而是所有“物質特性”(該詞項就在(2.0232)上一段首次出現)的性質。
現在,我認為這僅僅是一個誤解。相關碼段的正確解釋只要求仔細閱讀上下文。維特根斯坦說的是“大致地講(Beilauefig gesprochen):對象沒有顏色”,這話是在評論
2.0231 世界的實有只能確定一個形式而非任何物質特性。因為這些首先由命題展現——首先由諸對象的配置生成。
維特根斯坦這里在告訴我們的是,對象不確定事實:比如,即使a是綠的,a是綠的這個事實也不由a確定。在這方面,有趣的是反思
2.014 對象包含所有事態的可能性。
因此,雖然a不確定它是綠的這個事實,但它確實確定可能事實(它是綠的這個事實只是其中一個)的范圍。
名稱在一個邏輯空間(其包括與之結合來作陳述的謂詞)中實存。(在一種清晰語言——混沌語——中謂詞語詞(就像指出的一樣)會作為是名稱(being names)的方式,即(在真正意義上)作為名稱的內在特征,出現。)沒有原子陳述是分析的,從而
2.01321本句出自碼段2.01231,原文錯標為2.0132。——譯者注要知道一個對象,我必須知道它內在的而非它外在的特性。
當維特根斯坦說
2.0123 如果我知道一個對象,那么我也知道它在原子事實中出現的所有可能性。
這等于說,如果我理解一個名稱,那么我也知道它在原子陳述中出現的所有可能性。當他說
2.013 可以說,每一個事物都在可能原子事實的空間中。
這等于說,可以說,每一個名稱都在可能原子陳述的空間中。2當他補充說“我可以想到這個空間是空的,但不能想到沒有這空間的事物”,他提出這個有趣的可能性,即我們可以理解這個想法:我們使用的語言可能會沒有應用。而當他說
2.0131 ……視域中的一個斑點未必是紅的,但它必定有顏色。
他是在闡明,對象內在關系“外在”特性的集合,而非任何一個“外在”特性,即名稱內在關系原始謂詞(配置;參見混沌語)的集合3是這些集合構成包容不同次序原始謂詞的集合,還是它們分屬子集(確定項的家族),是單獨研究的一個話題。。
因此對我們來說并不奇怪(但令柯匹不安)的是,發現維特根斯坦在其中他說(大致地講)對象沒有顏色的碼段之后的碼段中說,
2.0233 兩個具有相同邏輯形式的對象——除了它們的外在特性——只因為它們是不同的才相互區分。
因為,這似乎不是意味著對象是裸的,而僅僅意味著兩個具有相同邏輯形式的對象4我這里發現這個蘊涵,即原始一位謂詞(配置)——即使不是所有原始謂詞——有家族(確定項),而且對象具有不同的邏輯形式,如果(例如)一個在顏色的邏輯空間實存而另一個在聲音的邏輯空間實存的話。確定相同的可能事實范圍,即兩個具有相同邏輯形式的名稱屬于相同的配置范圍。
在我看來,柯匹表明維特根斯坦的對象是裸殊相的第二個論證也是一個誤解。他首先正確指出,根據維特根斯坦,對象被命名,而事態被“描述”(described)——這個詞是維特根斯坦的。然后他寫道(第164頁):
……如果一個對象具有一個特性,那么那會是這樣一個事實:對它的斷定會構成對那個對象的描述。但對象不能被這樣描述,由此推出對象沒有特性。
這個論證忽視了這個事實,即受符號邏輯術語的影響,維特根斯坦在我們會期望“斷定”(assert)的地方使用詞項“描述”(參見3.221)。因此,他僅僅是在告訴我們,對象不能被“描述”,即斷定:絕不由此推出它們不能在日常意義上被描述。其實,在4.023,維特根斯坦寫道,“就像對一個對象的描述用其外在特性來描述它,同樣命題用其內在特性來描述實在。”
第三個論證具有形式“……如果一個對象具有一個物質特性,那么它具有這特性就會是一個只牽涉一個殊相的事實,從而沒有對象可以具有任何物質特性,所有殊相是裸的”(第164頁)。這假言句是可靠的。援引來否認后件的證據是4.032,它被解釋為說所有命題指號是組合的,因此得包含至少兩個要素,即至少兩個名稱。但4.032沒有說所有命題指號是組合的,而是說它們都是“邏輯鉸接的”(logically articulated),而且我試著解釋了一個命題指號怎么會由一個邏輯鉸接的名稱組成。我承認,在緊隨其后的括號評論中,維特根斯坦寫道,“(連命題‘ambulo’也是組合的,因為它的詞干和另一詞尾或它的詞尾和另一詞干產生另一個意義)”,但我不相信這個評論(它正確指出日常拉丁語在邏輯鉸接方面不是清晰的)是決定性的。(我愿意承認我的解釋,和柯匹的一樣,有它的困難。)
柯匹最后的論證其大意是,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告訴我們,《邏輯哲學論》中的對象和《泰阿泰德篇》(21e)中描述的那些一樣是初級要素。如果要是有理由認為《泰阿泰德篇》21e的要素是裸殊相或者維特根斯坦認為它們是,那么這會是有說服力的。我沒看到有這樣認為的理由。
柯匹論文中反對這個想法,即《邏輯哲學論》支持一元原子事實的最有力論證不是被柯匹直接用于這個目的,而是用作他對這個可靠論點,即維特根斯坦的對象不是特性,的部分支持。稍作調整,它的大意是,如果存在任何一元原子事實,那么它們就肯定包括視域中的某一點是紅的這樣的事實。但(論證繼續)如果“a is red”是一個基礎命題,那么“a is blue”不能與它相矛盾。不過,眾所周知,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6.3751)“兩種顏色,例如處于視域中的同一位置,是不可能的,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因其在顏色的邏輯結構之外……。(顯然,兩個基礎命題的邏輯積既不能是重言式,也不能是矛盾式。)”柯匹得出結論(第162頁)“顏色述謂不是基礎述謂”。
現在,在這方面需要闡明兩點。第一是我們可能會確信,不能給出任何例子也可能存在一元原子事實(在對于任何n都可能存在n元原子事實的奇特意義上)。在這方面值得指出,在《哲學的一些主要問題》中,摩爾實際上想知道是否存在任何性質(而不是關系特性),并專門探討了顏色的邏輯空間,看它是否為我們提供性質的例子。摩爾愿意認為不存在性質,即最簡單的事實已經是關系的。誠然,摩爾的性質事實會是貝格曼式的而非維特根斯坦式的,即每個都會是一個殊相和一個共相的聯結,但是這個事實,即摩爾愿意懸置之于問題“存在性質嗎?”的判斷,結合這個事實,即他發現顏色的邏輯結構的確非常地復雜,表明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持有類似的態度。畢竟,安斯康姆指出,維特根斯坦認為這在某個意義上是一個事實問題:最復雜的原子事實是n元的而非m元的(m>n)——參見4.2211。最不復雜的是(比如)二元的而非一元的,這不能在同樣意義上是一個事實問題嗎?
因此,或許該歷史問題的正確回答是,維特根斯坦會認為問題“殊相是裸的嗎?”在一個深層意義上是一個事實問題,這個問題他沒有聲稱知道答案,他(作為邏輯學家)也不必知道答案。
第二個評論是,維特根斯坦很可能認為存在一元原子事實,確切地講,它們的實存是明顯的,但在日常用法中沒有陳述表示這樣一個事實,因而沒有例子可以書寫出來。盡管他認為日常語言包含基礎命題,但他強調不是清晰地包含它們。不存在預設在日常生活語境中日常使用的任何日常語句會表達一個原子命題。確切地講,預設相反。
三
布羅德等人說,哲學家們專注于視覺例子而被帶入了感知理論中的錯誤。在我看來,他們同樣聚焦顏色而被至少同樣頻繁地帶入了邏輯理論中的錯誤。危險源于這個事實,即(例如)“red”這樣一個語詞實際上是三個語詞融為一體,一個形容詞、一個普通名詞和一個專名。因此,我們可以同等恰當地說,
The book is red(譯作:這本書是紅的)
Scarlet is a red1此處原文為“Scarlet is a color”,但根據前文的陳述,此處應是舉例說明作為普通名詞的“red”,因此此句應為“Scarlet is a red”。——譯者注(譯作:猩紅是一個紅)
Red is a color(譯作:紅是一個顏色)。
我剛才力主區分描述常項和名稱的重要性。我建議,雖然這樣說是正確的,即陳述
Green a
由兩個常項組成,就像通過對照
(Ex) Green x
(Ef) fa
(Ef) (Ex) fx
從這三個量化陳述來看它所揭示的一樣,但是說它由兩個名稱組成是極其引人誤解的。理由現在應該清楚了。因為,如果我們確實將語句“Green a”看作名稱的并列,那么我們將必定會(尤其是如果我們讀了《邏輯哲學論》的話)認為,它通過并列名稱“Green”和“a”肯定了這兩個對象或個體或邏輯主詞green和a被一個“刻畫連結”(characterizing tie)之類的“聯合”或“彼此掛在一起”或綁在一起。
現在,使這一步看似更加合理的是,存在一個對象green,并且存在一個常被稱為例示的關系,使得如果a is green那么a exemplifies green也為真。因此,這樣說的確誘人,即
a exemplifies green
僅僅是一個含糊方式來言表由
Green a
所清晰言表的。它的迷人之處在于,如果不認為“green a”言表由“a is green”所日常言表的,那么這個斷言就是絕對正確的。
如果我們放下顏色而使用一個幾何例子,那么這點就極為惹眼了。比如,想一想陳述
a is triangular
或(對我們而言)
Triangular a。
這樣說顯然會是古怪的,即
a exemplifies triangular(譯作:a例示triangular),
盡管這樣說并不古怪,即
a exemplifies green。
理由是“triangular”不像“green”一樣在日常用法中既發揮形容詞也發揮單數詞項的功能。我們得說的是
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譯作:a例示triangularity)。
現在,在一種清晰語言(即一種內置抵御布拉德雷困惑的語言)中,我們可能會通過串聯“a”和“triangularity”來言表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或者通過書寫
Socrates: Wisdom
來言表Socrates exemplifies Wisdom。我們的語言不是這樣一種清晰的語言,為了在這方面將此揭示,我們可能會寫道,
我們絕不能說,“復雜指號‘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言表‘a和triangularity處于例示關系’”,但我們必須說“‘a’和‘triangularity’處于某一關系’言表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
因此,這樣說是正確的,即
Green a
清晰言表由
a exemplifies green
所言表的,僅當“green”在單數詞項“greenness”的意義上使用。而當它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時,陳述
Green a
不具有日常陳述
a is green
的意義,盡管它邏輯等值它。
貝格曼教授認為,
Green a
由兩個名稱組成,即“a”(一個殊相的名稱)和“green”(一個共相的名稱),并且(因為是它們的并列)斷定一個例示另一個。根據他的看法,堅稱“a is green”言表a exemplifies green卻沒有意識到“a exemplifies green”僅僅是一個含糊方式來將“a”和“green”并列的哲學家們在試著說不可說的(to e☆ the ine☆able)。用我早先提議的術語來講,他認為例示是聯結,即只能由名稱的配置來表達的對象的配置方式。在維特根斯坦只看到殊相的配置的地方,貝格曼教授看到了殊相和共相的配置。
不過,如果
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
不是一個含糊方式來言表
Triangular a,
那么它言表什么?我并非將給出一個答案(我在其他地方嘗試給出了),而是嘗試一個類比,然后斷言它不只是一個純粹類比。在我看來,
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
和
a is triangular
必然等值但不同義,類似于
That a is triangular is true(譯作:that a is triangular為真)
和
a is triangular
必然等值但不同義。不說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我們可能會同等恰當地說triangularity is true of a(譯作:triangularity之于a為真)或triangularity holds of a(譯作:triangularity之于a成立),這個事實表明該類比不只是一個純粹類比。
現在,如果
a exemplifies triangularity
triangularity is true of a
triangularity holds of a
要用
That a is triangular is true
來闡明,那么例示,在像貝格曼教授和我自己一樣的《邏輯哲學論》主義者認為富有啟發的狹義上,不在事實世界中顯現,意指(meaning)或真(truth)出于同樣的理由也是如此。
《邏輯哲學論》中關鍵的不可說與陳述和事實之間的關系有關。存在這樣一個關系嗎?它是不可說的嗎?在我看來回答如下。在陳述和事實之間存在一個意指關系,但兩項都在語言次序中。說一個陳述意指一個事實,就是說(例如)
“Gruen a”(在德語中)意指Green a,且它是事實Green a。
第一個合取肢似乎斷定在一個語言項和一個非語言項之間(即在一個陳述和一個在實在次序中的項之間)的一個關系。第二個合取肢似乎說這項它是一個事實。我認為,第一個合取肢確實斷定一個關系,但這關系實存于一個德語表達式和一個英語表達式(是在我們語言中的一個表達式)之間。它具有
“Gruen a”(在德語中)對應在我們語言中的“Green a”
的效力。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Gruen a”(在德語中)意指that green a
因為將“that”放在一個語句前面具有給它加引號的效力,并且蘊涵這語句在我們語言中,正這樣被考慮。為什么我們認為這樣說違背直覺,理由是因為“means”(譯作:意指)是翻譯提示,這會與我們據以說
“Dass gruen a”(在德語中)意指that green a
的用法相沖突。
假定承認意指是在一個可能再也可能不在我們語言中的表達式和一個在我們語言中且正這樣被考慮的表達式之間的可翻譯關系。那么,說
That green a is a fact(譯作:that green a是一個事實)
是什么意思?顯然,這等值于說
That green a is true
這讓人想起等值
That green a is true ≡ green a。
不過,這不是最清晰的表示方式,因為雖然這等值實存,確切地講,必然實存,但是它的真取決于推論原則——這是癥結所在——
從“that green a is true”(在我們語言中)推論出“green a”(在我們語言中)。
就是憑借這個事實,即我們作出這樣的推論,意指和真的談論才獲得了它與世界的聯系。在這個意義上,這聯系是做(done),不是說(talked about)。
從這個視角看,《邏輯哲學論》的不可說論點已經預示了維特根斯坦后期將語言理解為一種生活形式。不過,看到這個,就是看到其中沒有不可說。因為,雖然推論既不是指稱可被指稱的,也不是斷定可被斷定的,但這不意味著它是沒說(因此)不可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