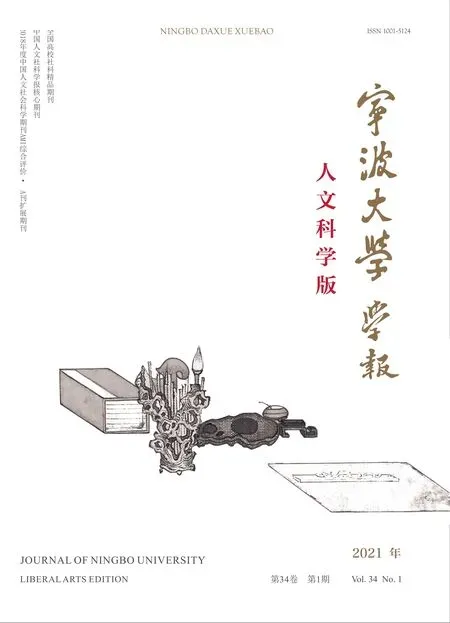論蔣孔陽的音樂美學思想
陸 揚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 )
蔣孔陽先生的音樂美學思想集中于《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該書1986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中國音樂美學的開拓性著作。蔣孔陽回憶他的兩部美學代表性著作曾坦言,雖然《德國古典美學》影響更大,臺灣也出了繁體字版本,但是他自己格外心儀的還是《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其緣由是中國人寫中國的東西,自有一種親切感。倘若不是身體漸感不支,《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本應是蔣孔陽撰寫一部《中國美學史》心愿的序章。該書“前言”言:
在各門藝術當中,我國古代的音樂特別發達,而且有關音樂的論述又特別多,因此,探討我們古代的音樂美學思想,應該是研究我們古代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我們古代最早的文藝理論,主要是樂論;我國古代最早的美學思想,主要是音樂美學思想。[1]465
在蔣孔陽看來,音樂思想可視為中國美學史的源頭所在,這個洞見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共識。音樂對于人類文明之必須,早在《尚書·舜典》就有明確記載。舜繼堯位,安定天下,即任命百官,令各司其職。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2]44由此可見音樂與文明的啟蒙是同步的。希伯來文化中,更將音樂對人類之必需,上推到創世之初。《舊約·創世紀》說:“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篷養牲畜之人的祖師。雅大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3]4雅八和猶八這一對分別掌管畜牧和音樂的兄弟祖師,是亞當和夏娃的長子該隱的第六代子嗣。這可見,緊鄰著開天辟地的太初時光,人類就有了音樂。
一、音樂美學的合法性
《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在1976 年完成初稿,帶有那個時代的特定印記,1986 年面世。蔣孔陽在《后記》中交代寫作經過:
記得1975 到1976 年之間,我從牛棚放了出來,回到了教研組。我用不著天天去參加強迫性的勞動,可以自由來去和看書了。但是,我又還不夠格參加教學或其他任何正式工作。因此我那時真是百事不管,成了我一生中少有的空閑時候。沒有事,我就天天上圖書館。我本來喜歡歷史,這時,我就大量翻閱我國古代的著作,以及近人研究我國古代的著作。翻閱中,我發現我國古代討論音樂的資料特別多,使我認識到音樂在我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于是,我產生了研究我國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的念頭。[1]743
《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不是命題作業,也不是事先的規劃,它更多是出自一種非功利的寫作靈感。這個靈感的直接來源是顧頡剛主編《古史辨》中陰陽五行與音樂關系的相關文章。1975-1976 年這個特殊的寫作年代,與朱光潛先生在20 世紀60 年代初葉寫作《西方美學史》,多有共通處。《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沒有《西方美學史》完稿即告付梓,并得以重印的幸運。它從完稿到付印相隔十載,中國的學術環境業已歷經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1984 年劉綱紀撰寫的《中國美學史》卷一面世之后,長期養在深閨人未識的中國古代美學,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顯學。反顧蔣孔陽45 年前完成的《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依然不失為最優秀的一部藝術門類斷代史。
《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的顯著特點是夾敘夾議。蔣孔陽承認自己不懂音樂,更不懂先秦的音樂。由此引出一個音樂美學評論的合法性問題。在藝術學被確立為第13 個學科門類,音樂與舞蹈學被確立一級學科之后,我們有理由期望音樂家親力親為,啟筆敘寫自己學科的歷史和理論。在此之前,自柏拉圖以降,音樂美學或者說藝術哲學,從來就是哲學家的分內使命。《理想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
蘇格拉底:那么有哪些調子是這種軟綿綿的靡靡之音呢。
格勞孔:伊奧尼亞調,還有些呂底亞調都可以說是靡靡之音。
蘇格拉底:好,我的朋友,這種靡靡之音對戰士有什么用處?
格勞孔:毫無用處。看來你只剩下多利亞調或佛里其亞調了。
蘇格拉底:我不懂這些曲調。我但愿有一種曲調可以適當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們沉著應戰,奮不顧身,經風雨,冒萬難,履險如夷,視死如歸。我還愿再有一種曲調,模仿在平時工作的人……[4]104
柏拉圖的音樂教育思想,以為伊奧利亞調和呂底亞調為靡靡之音,推崇多利亞調和佛里其亞調,認為它們表現了節制和勇敢。柏拉圖請出蘇格拉底代言,坦言自己“不懂這些曲調”。柏拉圖的教育思想是驅逐詩歌,改由體育錘煉兒童體格,音樂陶冶少年情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嗣后圣奧古斯丁寫《論音樂》,波愛修寫《音樂原理》等,這些音樂理論史上的大家和經典著作,都以哲學為音樂師。按照波埃修《音樂原理》中的說法,音樂家人分三等:第一等人是哲人來談音樂,他們雖然不解音樂實踐,但是深曉音樂的根本之道;第二等人是作曲家;第三等人是音樂實踐家,他們能彈會唱,但是那不過是技藝,他們位居三類音樂人的最低下一層。波埃修和奧古斯丁的音樂理論雄霸歐洲中世紀一千余年,而令哲學家當仁不讓成為音樂美學的宗師,這個傳統的源頭,是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數為宇宙和諧之源的數學模型。
從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哲學家、作曲家、演奏家依次而下的等級秩序,今天看來是顛倒翻了過來,哲學家和美學家談音樂,開始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蔣孔陽寫作發表《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時,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后記”中強調《論稿》既不是研究先秦音樂本體,也不是研究先秦時期的音樂史料,亦非研究先秦樂官樂手們創造出來的音樂形象。這些方面是音樂家關心的話題,如楊蔭瀏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主要探討的是先秦時代表現在音樂領域當中的美學思想。這些美學思想,說到底便是特定時代大家對于音樂的一些所思所想。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很懂音樂,有些人不解音樂,但是他們都聽過音樂,是以情動于中而付諸于文。他主要根據先秦時代諸子百家著作中有關音樂的言論,研究這些言論所產生的時代社會背景,以及在諸子百家的哲學體現中所占有的地位。
由此可見,蔣孔陽談音樂,既沒有像從柏拉圖到波愛修的早期西方美學那樣,由哲學家來當仁不讓指點音樂本身,也沒有像前輩音樂家如楊蔭瀏那樣來寫音樂本身的歷史,而是著重開辟了“音樂美學思想”專題。
什么是“音樂美學思想”?蔣孔陽就音樂美學思想,作了言簡意賅的說明。音樂美學思想不是美學家居高臨下給音樂歸納原理,就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而言,它不是先秦樂官們關于音樂的理論,而是諸子百家對于音樂的看法和想法,是他們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蔣孔陽坦言他寫《論稿》,密切關注了兩個問題:其一是先秦的哲學家很少從純哲學角度論道,而都帶有濃厚的社會政治倫理色彩,反映到音樂美學思想上面,沒有人為音樂而談音樂。其二,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私家講學蜂起,反映到音樂美學思想上,很自然形成不同派別和觀點。這兩個問題導出的樂和禮的主題,以及各家樂論的分歧,事實上也是《論稿》展開敘述的重點所在。蔣孔陽最終這樣歸納了美學家論音樂的合法性:
這樣,你可以知道我這本書,根本不是談音樂本身的規律和理論,而是聯系音樂或者通過有關音樂的言論,來談哲學,來談政治和社會。正因為這樣,所以我這個不懂音樂的人,也才敢于大膽地來試一試。[1]742
蔣孔陽這個嘗試當其時來看,是前無古人的,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居高臨下的音樂教育美學,和黑格爾為代表的高屋建瓴的音樂藝術哲學,判然不同。帶著這一謙卑深入梳理先秦音樂美學思想,可見蔣孔陽抽絲剝繭的拾遺補缺考據心力。
二、“省風”與“宣氣”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載周景王欲鑄無射編鐘,時樂官州鳩道:“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5]442這段話中的“省風以作樂”,通常的闡釋是天子省察風俗民情以作樂。三國時期史學家韋昭《國語注》中,這樣解釋《國語》中伶州鳩的“樂以殖財”一語:“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6]84在此基礎上,蔣孔陽以“省風”為中國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的一大特征,對此他的說明是:
所謂“省風”,是指通過音樂的耳朵,來聽測和省察風的方向、溫度和濕度等。不同季節的風,具有不同的方向、溫度和濕度。它們有的有利于農業的生產,有的不利于農業的生產。古人認為通過音樂能夠聽測出所刮的是什么風,所以音樂具有“省風”的作用,在農業生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505
蔣孔陽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物質生產為一切精神生活形式的出發基點。蔣孔陽對于“省風”,首先作了字面義的闡釋。他指出,無論是客觀的宮商角徵羽五聲,還是主觀的喜怒哀樂情緒,都五行六氣產生的。進而天地萬物,亦莫不系由陰陽六氣組構而成。那么何謂“六氣”?它們跟音樂又有什么關系?蔣孔陽同樣引了韋昭解《國語》中的“天六地五”以作說明:“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6]64以及《左傳》中的這一段話:“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5]468-469蔣孔陽認為,《左傳》和《國語》中“天六地五”的說法可以表明,春秋時期陰陽五行的觀念已經十分流行。而流行的前提,則是五行和陰陽六氣作為自然的物質基礎,得到了確認,這應可顯示,當其時,自然“物”的觀念,已然產生。這和商周神學的天命論唯心史觀,大不相同。是以蔣孔陽考察先秦音樂的“省風”功用,首先以“風”為物質義解。他引《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以及韋昭的相關釋義:“虞幕,舜后虞思也。協,和風也。言能聽風知風,因時順氣,以成育外物,使之樂生。”進而指出,遠古以降的古時樂師,皆善聽測風聲,所以他們的使命,就是以“省風”來服務農事[6]344。而如《廣雅·釋言》云:“風,氣也。”[7]444以及《淮南子·天文訓》:“天之偏氣,怒者為風”,不妨說,作為西方哲學四大元素之一的氣或者說風(air),跟中國哲學六氣中的風聯袂,成為了音樂產生的物質基礎。是以蔣孔陽指出,先秦古人認為音樂發生的途徑之一,便是對風的模仿。他引了《呂氏春秋·古樂篇》中的兩則文字: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
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8]104-105
這兩則文字都談到風聲。其記載的音樂的緣起,比前文《尚書·虞書》中舜命夔為樂官,以詩言志、歌詠言開啟的儒家詩學樂論傳統,更要悠久得多。在蔣孔陽看來,它不但是在物質層面上闡釋了音樂的“省風”緣起,而且進而顯示了一種無用之用,用于農事和戰事。
用于農事,蔣孔陽引了《國語·周語上》虢文公對周宣王說的一段話:“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廩于籍東南,鐘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6]13這里盲樂師省察風聲地氣,作樂以求反饋信息,音樂與糧倉修葺、作物收藏和布種時令并陳。對此蔣孔陽指出,音樂在這一語境中,就不復單純是統治階級的消遣,而成為了百姓從事生產活動的一個重要工具。用于戰事,蔣孔陽同樣引證了《左傳》《周禮》和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如《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5]104
對此蔣孔陽指出,這些文字足以表明,音樂之“省風”,對于戰爭形勢的判斷,是為必然。音樂與戰爭的主題事實上多為人關注。希伯來文化中,軍隊亦以不同的角聲代表起行、安營、發動攻勢或撤退等不同的命令。音樂之見于軍事,主要的樂器是角和號。《新約》中圣保羅說:“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3]195《舊約》寫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曠野行進,隊伍如同行軍,即是以吹號發令聚集、起行和安營。《民數記》第10 章中,耶和華命摩西用銀子打造支號,以招聚以色列民眾,并具體交代了號令信息:“若單吹一枝,眾首領,就是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聲的時候,東邊安的營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聲的時候,南邊安的營都要起行。他們將起行,必吹出大聲。但招聚會眾的時候,你們要吹號,卻不要吹出大聲。”[3]135-136這可見古今中外,音樂與戰爭從來就是同仇敵愾。像蔣孔陽這樣以“省風”角度來審查音樂和戰爭的關系,毫無疑問是表達了一個獨特的音樂美學視野。
關于“宣氣”,蔣孔陽指出,假若說“省風”之說還主要是關注風向與風情,那么“宣氣”之論,則更希冀音樂能夠打通陰陽阻滯,予以宣泄疏導。這和希臘美學流行的“卡塔西斯”(katharsis)即宣泄、凈化觀念,應為一類。蔣孔陽指出,若遇風雨不順,四時失序,古人會希冀音樂發揮相應的“宣氣”作用以扶正陰陽。他引《呂氏春秋》的《察傳篇》:“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8]545《古樂篇》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郁郁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8]101有鑒于古代舞與樂同為一體,蔣孔陽強調說,這里都可見出音樂的“宣氣”功能。這毋寧說也是再一次重申了音樂的物理緣起。對于音樂的這一認知,在蔣孔陽看來,與嗣后殷周貴族用音樂來“制禮作樂”,是大有不同的。對此他總結說:
總之,“省風”也好,“宣氣”也好,春秋時唯物主義的思想家,都是用物質性的陰陽和五行來解釋音樂,并因為陰陽和五行直接與生產有關,所以他們也把音樂的作用直接與生產聯系在一起。這一點,他們和原始時代強調音樂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1]514
從生產力的發生點來解釋藝術的緣起和功用,是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藝術史觀的典型表述。蔣孔陽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熏陶下形成自覺的美學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首先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之上。他以人類最基礎的物質生產為出發點,彰顯音樂最初的實用功能,以嗣后陰陽五行讖緯神學的神秘主義樂論為恥。蔣孔陽的世界是一個美學的世界,在他看來,人類所有的精神活動,無不帶有自我表現的本能愿望,理性精神惟其在直觀形式中實現自身,方有美可言。實際生活中的蔣孔陽處世淡泊,行平凡之道。他衣著平實無華,飲食上面更無挑剔。家里則滿目是書,除了友人和學生贈送的一些小擺設,不見其他刻意裝飾。
在信息化數據運行管理工作中,大量的電子檔案被保存到計算機中,雖然減少了建筑空間的占用面積,但是這些電子檔案的安全性仍然面臨潛在的風險。特別是對于一些涉及油田企業核心技術或商業機密的檔案,容易成為競爭對手或不法分子竊取的對象。例如,黑客會惡意攻擊存儲電子檔案的計算機或網絡,達到竊取或損毀珍貴檔案的目的。基于信息化數據運行的檔案管理模式,仍然要關注電子檔案的安全性問題,這也是關系到油田檔案管理和利用的重要工作。
三、“正樂”與“非樂”
蔣孔陽將音樂美學思想定義為同時代人對于音樂領域的看法和想法,展開先秦時期中國音樂美學思想的探討,在探討過程中,將作者主體的性格立場鮮明地展示了出來。《先秦音樂美學論稿》絕不是單純的史料匯合,即便在史料這一方面,作者縱橫捭闔、旁征博引的考據功力和心力,迄今同類著作無有出其右者。《論稿》的一個鮮明特征是史論結合,綿密論述分布在各個部分,交織而成就全書堅實的理論構架。這個構架的一大顯著特征,便是質疑孔子的“正樂”理論,推崇墨子的“非樂”思想。
在音樂美學研究中質疑孔子的“正樂”理論,推崇墨子的“非樂”思想在新儒學雄風重振,再度躋身主導意識形態,“禮樂”音樂美學幾成不二之論的今天,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事實上蔣孔陽也有充裕時間,修正《論稿》中留下的20 世紀70 年代中葉特定政治氣候下的時代印記。但是,蔣孔陽既堅持了他的上述音樂美學評價立場,這立場本身,也跟他一以貫之的平民主義人生哲學息息相通的。他1989 年發表在《收獲》第6 期上《且說說我自己》說:“你看秦皇漢武,當時多么威風,為了建立自己的豐碑,草菅人命,弄的民不聊生。可是,他們能夠勝過他們目前的陽光和綠草嗎?”[9]474對于“禮樂”音樂美學的形成,蔣孔陽指出,本來在殷周的奴隸社會中,禮和樂是相須為用的。周公最大的政治措施之一,便是“制禮作樂”。但是將“禮”和“樂”并接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由此形成一個完整的哲學和美學的思想體系,始于孔子。
孔子以六藝教,六藝的頭兩項就是禮和樂。《論語》之中,孔子也一再談到“禮樂”。如《季氏》中的“樂節禮樂”“禮樂征伐”,《先進》中的“先進于禮樂”“后進于禮樂”,以及《憲問》中的“文之以禮樂”等。所以要談孔子的“正樂”思想,不可能光談樂,不談禮。孔子的“正樂”思想,是以從大處看,不外乎兩個目的:其一是用“禮”來駕馭“樂”,孔子欲予扶正和斧正的“樂”,并非他“樂”,而是能夠用于服務于“禮”的“樂”;其二,孔子以其“禮樂”攻其他非禮之“樂”,如鄭衛之音等等。顯而易見,孔子“提出‘禮樂’這個口號來,不僅有音樂上的美學意義,而且是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的。”[1]555
蔣孔陽認可并且推崇孔子的音樂素養,指出孔子不但能歌兼善擊馨鼓瑟,而且極有欣賞和評論音樂的天賦和能力。《論語·泰伯》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八佾》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這都是迄至今日亦令人嘆為觀止的音樂評論。正因為孔子的音樂敏感,使他憂慮音樂不復再能恰如其分服務周禮。蔣孔陽引《史記·孔子世家》一則掌故:孔子陪魯君相會齊君于夾谷,齊國奏“四方之樂”,那是孔子不齒的夷狄之樂;又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當即大怒,請命誅殺奏樂人。蔣孔陽認為這段記載可以見出孔子是堅決捍衛禮樂、反對非禮之樂。蔣孔陽指出孔子晚年周游列國、四處碰壁,深感政治作為業已窮盡,是以寄希望于意識形態糾正。其撰《春秋》以正名,倡“正樂”以接續商周禮樂體統。一如孔子本人所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蔣孔陽引鄭玄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認為無論是《子罕》中所言之雅頌,還是后來司馬遷又加上韶和武,都足以顯示它們就是孔子“正樂”的標準。具體說,也就是將詩三百篇中可施于禮義的部分加以弦歌,讓樂重新從屬于禮,以成就“禮樂之道”。所以在于孔子,“禮”作為現存政治秩序的標記,它是“正樂”和一切意識形態建構的第一準則。
但是蔣孔陽對孔子的“正樂”思想不以為然。他的分析是,到春秋戰國之際,由于政治格局今非昔比,要回歸古代各安其位的禮樂制度,事實上已時過境遷。而且殷周禮樂究竟是何等樣式,已然無人得知。現存的《周禮》《儀禮》《禮記》這三禮,早有后人考據均非周代作者所撰,而系戰國和兩漢時期的儒者所為。作為“圣之時者也”的孔子,表面上講的還是周代的禮樂,骨子里已經是在表達他自己托古改制的禮樂理念。是以孔子在美化古代貴族音樂的同時,排斥是時流行的鄭衛之音,以為非禮之樂,是為必然。
禮指的并不是宴席酬酢等煩瑣的禮節;樂指的也不是舞蹈鐘鼓等音樂。禮指的是合乎禮的行為,樂指的是對這一行為的愛好和趣味。因此,孔丘“正樂”,推行“樂教”,最后的目的,并不在于禮樂的本身,而在于通過禮樂,來培養和教育能夠推行仁政和德政的理想的統治者,從而達到“天下太平”。[1]581
即便蔣孔陽對于孔子的“正樂”思想總體上持否定態度,他還是充分肯定了這一理念的道德教育風范。孔子“正樂”并非僅僅是盯住“禮樂刑政”此一政治目標,還有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道德教育目標,即通過詩書和禮樂,來達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對此蔣孔陽本人作為一名孜孜不倦的美學教師,顯然是予以充分認可的。
關于墨子本人,蔣孔陽引墨子本人《貴義篇》等文獻,強調他肯定不是王宮貴胄,出生應比較貧賤。是以不奇怪墨子成為具有平民色彩的思想家、小生產者和小私有者的代言人,所持立場與儒家針鋒相對。在蔣孔陽看來,這針鋒相對首先見于儒家和墨家的“義”“禮”之辯。在于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在于墨子,則“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上》)甚至,“義,利也”(《經上篇》)。當然也見于他著名的“非樂”美學思想:
且夫仁者為之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12]136
墨子上面這段話,在蔣孔陽看來是墨子“非樂”思想的典型表述。他歸納墨子論辯之要,列出為樂七害:(1)要為樂,必須制造樂器,費用哪里來?無非對百姓橫征暴斂。(2)樂器制造好了,卻無實用功能,黃鐘大呂、彈琴鼓瑟,都無助于百姓饑寒交迫、勞不得息。(3)音樂不但沒有用處,還有壞處。它浪費勞動力,妨礙生產。(4)即便王公大人沉湎音樂,也會影響工作。(5)人演奏音樂必追求美顏美服,造成奢侈浪費。(6)人與動物不通過,需勞動方得生存,但是音樂妨礙了各階層人士的正常工作。(7)歷史上耽于音樂者,十有九亡。
顯然,墨子對音樂的聲討,無論是當其時,抑或今天來看,都是叫人很難茍同的。蔣孔陽列舉了對墨子“非樂”思想的反對意見。如荀子“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也認為墨子非樂是排除了情感。對此蔣孔陽的辯護是,通觀墨子原書的全文,仔細考究他“非樂”的本意,可以發現問題其實沒有這么嚴重。因為墨子并沒有對人的審美要求和音樂愛好作全盤否定,墨子本人的這一段話足見端倪:“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12]136蔣孔陽進而指出,墨子以上文字可見表明,他并非一筆勾銷音樂的審美價值即審美意義。墨子“非樂”的緣故,是他主張“先質而后文”,人必首先解決溫飽問題,惟其如此,才有閑暇顧及音樂。
蔣孔陽認為,墨子的“非樂”思想應是他的功利主義哲學使然,即以有用、無用,有利、無利為衡量應否需要音樂的標準。音樂沒有實用目的,所以墨子提倡“非樂”。蔣孔陽對此的結論是,墨子“非樂”論當作歷史主義的具體分析,一概說對或者不對,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首先,像我們前面說的,他的“非樂”思想,是有其明確的顯示意義和針對性的。他的矛頭,始終對準儒家所稱頌的“王公大人”和“當今之主”。說這些“王公大人”以及“當今之主”,“繁飾禮樂以淫人”,造成“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的嚴重局面,“虧奪民衣食之財”,而且妨礙了國家的工作和生產,因此,墨子從勞動人民的疾苦和利益出發,嚴厲地批評儒家的“禮樂”思想,反對為奴隸主享樂服務的“禮樂”,這從當時來說,應該是進步的。[1]593
墨子的非樂之論弊端諸多,蔣孔陽并非視而不見,也無意回避,反之將它們歸結為:(1)“治與樂”對立,將農夫之樂與王公之樂對立起來,忽略從原始社會開始,音樂與勞動就親密無分;(2)只是從奢侈浪費方面來非樂,沒有看到儒家“禮樂”的政治目的。適因于此,蔣孔陽也承認,墨子針對程繁和公孟詰問他“非樂”思想所作的答辯,多少顯得勉強,而難振振有辭。
魯迅對墨子情有獨鐘,《漢文學史綱要》第三篇《老莊》中他說,墨子“尚夏道,兼愛尚同,非古之禮樂,亦非儒”。又說,“然儒家崇實,墨家尚質,故《論語》《墨子》,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13]16魯迅本人的小說新編《非攻》,更將墨子塑造為一個胼手砥足,為正義不辭赴湯蹈火的非攻戰士。按照張岱年的說法,倘若墨學未中絕,唐宋以后或能形成儒道墨三家學術并立局面,中國傳統文化將不會是今天模樣。蔣孔陽對墨子“非樂”思想的上述評論,放到這個更大的背景中看,自是意味深長。
蔣孔陽晚年為腦梗阻所苦,1999 年謝世前身體時好時壞。當中有過幾次兇險,可是每一次都能逢兇化吉,轉危為安,但是腿腳活動,甚而語言表達,終而漸失靈便,只是思緒卻始終是非常清楚,在他去世前的一個月,病情稍微穩定,他照例談起美學,還舉了一個生動的譬喻:劉勰穿的是佛衣,吃的是佛飯,說的是佛語,可是骨子里卻是原道、征圣、宗經的儒家思想。
晚年的蔣孔陽除了出版社和雜志社組稿約稿源源不斷,疲于應對,還有同輩、晚輩和學生新作的不斷索序。《蔣孔陽全集》卷四收錄的序文70 種近30 萬字。給他人作序不比自己寫作,首先要將原作讀過一遍,或者至少瀏覽一遍,然后擇要歸納介紹,進而斟詞酌句輔以背景材料。當中耗費的心力,其實可以想象。蔣孔陽對于來自四面八方作者和出版社的作序要求,可以說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這樣一種任勞任怨的仁者風范,既無先例,也未見來者。《全集》第四卷收錄的70 種序文,還遠不是蔣孔陽作序的全部。遺漏的包括我本人出版的第一本小書,寫林語堂的《幽默人生》,和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德里達:解構之維》,這兩本書我也厚顏跟蔣先生索了序文。后來收進了再版的第五卷。特別是《幽默人生》我是應出版社要求請蔣先生賜個再版序言,可是序言寫成,書卻沒有再版。序言中說,在林語堂徘徊在儒道和基督之間的矛盾人生里,“表現最為突出,最有特色的性格特征,是‘幽默’。為什么呢?這就因為‘面臨一個荒誕不經的悲劇世界,它偏偏做出喜劇性的反應’”[14]661。這可見蔣孔陽是讀過我的這本如今作者自己業已無從尋覓的小冊子的。假若晚年的蔣孔陽回絕這些索序請求,他的《中國美學史》夙愿,或許不是奢望。
劉綱紀認為《周易》以降,從荀子《樂論》到《禮記·樂記》,從《樂記》再到《毛詩序》,中國美學始終是以心物交感而產生的情感來說明藝術發生及其本質[15]10。蔡仲德則以“儒道兩家音樂美學思想既互相對立斗爭,又互相吸取交融”為線索,構架出他分為萌芽時期、百家爭鳴、兩漢、魏晉隋唐,和宋元明清五個時期的《中國音樂美學史》[16]9。
自蔣孔陽《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付梓以來,有關中國音樂美學的討論不復寂寥,相關論述時有所見;但是蔣孔陽這部作于文革后期的《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大氣磅礴又綿密細致,立論既恢弘鮮明,材料的布列更是苦心孤詣,深稽博考層層推進。而說到底,一種虛懷若谷的人文意志,堅韌地貫穿了下來,這是蔣孔陽音樂美學思想的一個標識,也是蔣孔陽整個美學思想的鮮明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