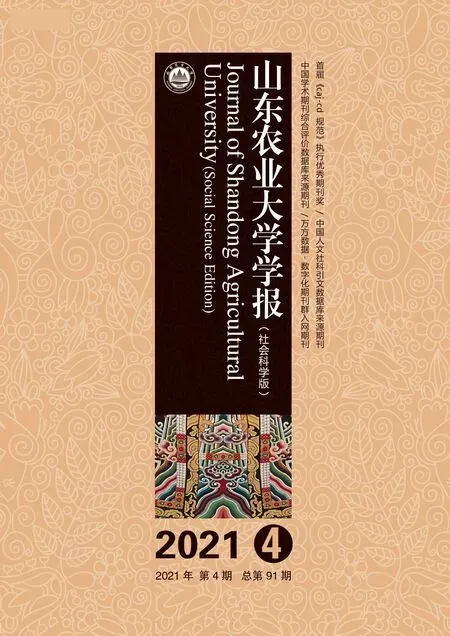家庭社會資本會影響農村土地流轉么?
□趙翰青 華玉秀
[內容提要]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數據,分析了家庭社會資本對土地流轉的影響。采用Tobit和Probit估計方法為此提供了經驗證據支持,而且替換衡量指標、改變研究方法和調整研究樣本以后結果依然穩定。因此,加強基層治理、保護農村低社會資本家庭以及加強對農村弱勢群體的現代農業技術培訓等,是避免土地流轉中不公平現象的重要方面。
一、引言
土地流轉是優化配置農村土地資源,推動農業生產現代化,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近年來,在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快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根據農業部統計,2015年底我國農地經營權流轉面積達4.47億畝①,2016年底更是達到了4.7億畝②。另外,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要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那么,隨著土地流轉及其政策改革實踐,土地流轉的決定因素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事實上,一些農村家庭擁有較多資本,可以流轉入土地,進行規模化生產,從而獲取更多農業收入;同時,另一些家庭的人力資本相對欠缺,有意將閑置土地轉出,以獲取一定的土地租金。所以,從理論上講,土地流轉中存在一種雙贏格局。不過,雙贏格局的形成通常是在一定條件下,在實踐中一般很難自然實現。有學者分析了土地流轉對農村家庭收入的影響[1][2][3],發現土地流轉會擴大農村內部收入差距[4];也有學者考察政治資本對農地流轉意愿的影響,發現村干部在農地流轉中更具優勢。[5]正基于此,不同類型家庭對土地流轉是否存在有差別的重要影響?換言之,家庭社會資本是否會影響土地流轉,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我國土地流轉的發展與現狀
土地流轉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必要條件。我國農村的土地流傳政策的早期形式是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秘密地出現在農村貧困地區的著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此制度經過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的爭議和討論,1982年中共中央發布第一個農村工作1號文件予以認可并取得全國合法性,最終于1984年在全國普遍實行[4]。隨著土地承包制的落實,農村居民自發的土地流傳開始出現。
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政策和實踐相關聯的角度來看,我國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政策的演變和實踐的發展,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呈現如下特征。
第一階段是自發實施階段。大約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這一階段土地流轉的特點是:農戶因承包土地變成負擔而使村集體收地交易成本降低,村集體組織是土地集中和流轉的主體。
第二階段是試驗探索階段。大約包含了從1987年于江蘇南部地區、廣東南海地區和北京順義地區進行適度規模經營試驗開始,到21世紀初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土地流轉的18號文件發布和《土地承包法》頒布實施為止的這段時間。[4]這一階段土地流轉的特點是:土地流轉從較發達地區開始向其他地區包括中西部的一些村莊發展,并呈現明顯的地域特征。同時,在政策上,全國人大于2002年通過了《土地承包法》,旨在通過確保土地承包關系的穩定,來保證農村的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穩定。[1][2][3][4]
第三階段是規范發展階段。從21世紀初開始。標志性事件為農村稅費改革,特別是2003年國家決定取消農業稅。這一階段土地流轉的特點是:隨著土地負擔的取消和各項惠農政策的鼓勵,許多之前放棄土地的農戶紛紛要求重新承包土地。同時,在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和郊區,出現涉農企業成規模承包土地的現象。
近年來,隨著農地確權頒證和相關政策法規不斷完善,我國土地流轉有序推進,取得了巨大成效。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土地流轉面積增長較快,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4]
(二)家庭結構與社會資本
傳統意義上的家庭結構主要分為核心、聯合、主干、單親和低社會資本家庭,不同家庭結構存在著資源稟賦的巨大差別。[6]一些學者分析了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及其行為決策,包括創業、土地流轉、土地規模經營、家庭消費和勞動供給等等,發現在不同生命周期家庭決策的差別很多,會產生不同的勞動供給、家庭消費等行為。[7][8][9]同理,對于農村家庭來說,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必然存在有差別的農業經營、非農就業和勞動轉移等行為[10][11][12]。與此同時,相較于城鎮居民,農村情景下“家”的作用更為明顯,中國農民普遍受到“家族文化”和“戀土情結”的影響,家庭特有的血緣、親緣等所形成的內聚力有助于農戶在參與土地流轉交易和議價過程中對抗可能的風險和挑戰[10]。
那么,如果將家庭分為高社會資本家庭、低社會資本家庭和普通家庭,由于高社會資本家庭的各類資源相對豐富,在家庭決策及行為選擇等方面當然會具有更大優勢。由于農民的個體決策往往是基于其家庭狀況做出的最優化選擇,因此,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在土地流轉的交易過程中,同樣結構健全及完整的高社會資本家庭的議價能力和最優決策能力遠高于普通家庭,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議價能力遠低于前二者。所以,在某些國家政策實施過程中有可能會受到家庭社會資本的影響,尤其是低社會資本家庭來說,國家政策紅利將很難獲得。一些研究將這一現象稱之為精英俘獲[13][14][15],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俘獲多種資源收益,但是本文將在一個社會資本這一更大的框架內去討論這一問題。
(三)家庭社會資本與土地流轉
很多學者從農民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出發,考察了土地流轉的主要動因。與本文研究極為相似,有學者分析了社會關系網絡[16]、家庭生命周期等社會資本對土地流轉的影響。[17]其中,李星光等(2016)認為,在農村地區,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界定為是否有親戚朋友在農技站工作,這與本文對高社會資本家庭的界定相似,即:有親戚朋友在農技站工作就意味著在農村擁有一定的政治資本。[16]諸培新等(2017)認為,相對于其他家庭,獨居家庭流轉入土地的概率較低,所以針對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需要采取不同措施,以盡快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12]。另外,與本文對低社會資本家庭的界定相似,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家庭流轉入土地的概率也較低,是抑制我國土地流轉的重要因素。[17]
綜上所述,很多文獻從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結構等方面對土地流轉進行了深入探討,但較少考慮到土地流轉政策的瞄準性偏差問題。為此,本文使用農村家庭結構將農村家庭分為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論證其對土地流轉的重要影響,以辨析我國土地流轉中是否受到社會資本的影響,即:高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流轉的決定作用。那么,本文提出假設:我國土地流轉受到社會資本的影響,也就是說,高社會資本家庭在土地流轉中占據優勢,更容易流轉入或流轉出農村土地,而且能夠顯著作用于土地流轉價格。
三、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2013年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③。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是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由北京師范大學聯合國內外專家共同完成,具體調查過程由國家統計局執行。該數據包括了農村住戶、城鎮住戶和外來務工住戶三個部分內容。針對本文研究目標,在此以農村住戶部分為基礎,本文篩選出了農村居民家庭樣本。同時,本文將土地流轉分為了土地轉出和土地轉入。其中,在分析土地轉出時,刪除流轉面積為0的農戶家庭樣本;而在土地轉入分析中,保留了所有農戶家庭樣本。
(二)變量設置
1.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土地流轉,包括土地轉出和土地轉入。為了全面分析土地流轉中是否存在精英俘獲,本文還將土地轉出和轉入的價格作為因變量。根據CHIP問卷,因變量的設置依據是:“2013年您家轉包出去的土地總面積,其中有償轉包給個人的土地面積,無償轉包給個人的土地面積,轉包給企業或農業大戶經營的土地面積,有償或無償轉讓給村集體的土地面積”;“2013年您家從他人或集體接包土地的面積”。由此,本文因變量分別是:轉出土地面積、是否轉出土地、轉出土地價格,以及轉入土地面積、是否轉入土地和轉入土地價格。如圖1所示,在因變量中,未轉入土地和轉出土地以及轉入和轉出土地價格為0的樣本相對較多。

圖1 因變量直方圖
2.自變量。本文的自變量為家庭結構,包括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根據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情況,農村居民可以分為三類,即:體制內精英、體制外精英和普通百姓。其中,體制內精英是指干部,非體制精英是指知名人士。[17]另外,也有學者將經濟能力較強的家庭定義為社會高社會資本家庭[18],同時高社會資本家庭也指家庭成員中擁有鄉政府和村委干部。所以,農村高社會資本家庭可以定義為,家庭成員中有干部、黨員和德高望重的人的農戶家庭。[6]基于此,本文將家庭中有黨員、干部或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家庭定義為高社會資本家庭。
除了普通家庭和高社會資本家庭,農村還存在低社會資本家庭或社會結構解體家庭。低社會資本家庭是指,家庭成員中有慢性疾病、離異、監禁、感染HIV、與鄰里發生糾紛等,容易導致家庭結構變化,并逐漸開始解體,最終會造成人力殘缺的家庭。[19]有基于此,本文將家庭有殘疾人、戶主離異或戶主健康狀況較差的家庭定義為低社會資本缺家庭。在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衡量中,滿足高社會資本家庭的一條要求即可被認為是高社會資本家庭;同理,低社會資本家庭的衡量也是如此。那么,本文設計了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兩個虛擬變量,即:高社會資本家庭=1,非高社會資本家庭=0;低社會資本家庭=1,非低社會資本家庭=0。另外,在后文分析中,兩個虛擬變量還被替換為高社會資本程度和低社會資本程度:高社會資本程度是指家庭中有黨員、干部或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占家庭總人口的比重;低社會資本程度是指家庭有殘疾人、戶主離異或戶主健康狀況較差的人口占家庭總人口的比重。基于以上指標重新進行估計分析。
3.控制變量。除了家庭結構會影響土地流轉,其他很多因素也會作用于土地流轉,包括農村家庭戶主的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其中,戶主個體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民族和健康狀況。具體指標構建說明如表1、表2所示。

表1 變量名稱及賦值說明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不同的估計模型中,控制變量稍有差異:在家庭結構對土地轉入價格的影響分析中,控制變量增加了土地轉入面積;在家庭結構對土地轉出價格的影響分析中,控制變量增加了土地轉出面積。
(三)實證分析模型
土地流轉中是否受到社會資本影響,主要是指高社會資本家庭在土地流轉中是否更具優勢,相應的低社會資本家庭在土地流轉中是否具有明顯劣勢。借助已有研究,本文將家庭結構設置為主要解釋變量,把土地流轉作為被解釋變量,同時引入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等控制變量。[6][7]具體估計模型為:
Landouti=α+β1FM_str1+β2FM_str0+γixi+εi
(1)
Landini=α+β1FM_str1+β2FM_str0+γixi+εi
(2)
price_landouti=α+β1FM_str1+β2FM_str0+γixi+εi
(3)
price_landini=α+β1FM_str1+β2FM_str0+γixi+εi
(4)
其中,Landout為土地轉出面積,Landin為土地轉入面積,price_landout為土地轉出價格,price_landin為土地轉入價格;FM_str1是指高社會資本家庭,FM_str0是指低社會資本家庭;xi是指一系列控制變量。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家庭結構對土地流轉面積的影響
本文檢驗高社會資本家庭或低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流轉的影響,以辨析我國土地流轉中是否受到社會資本影響。為此,本文采用估計方程式(1)和(2)進行相關回歸分析。由圖1可知,因變量的取值范圍集中分布于0。這被稱為受限被解釋變量,適用于Tobit模型進行估計分析[20],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3)和(4)分別是模型(1)和(2)的對照組,它們的區別是因變量由土地流轉面積替換為是否有土地流轉。檢驗結果表明,替換因變量以后,模型(3)和(4)的實證分析結果依然顯著為正。

表3 家庭結構對土地流轉的影響分析
第一,當因變量為土地轉出面積時,高社會資本家庭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低社會資本家庭的估計系數較不顯著。這表明,如果是高社會資本家庭,流轉出土地的面積將顯著增加。這很可能與高社會資本家庭擁有更多的資本,主要從事非農工作有關。另外,是否為漢族也對土地轉出面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個體健康狀況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與少數民族家庭相比,戶主為漢族的家庭會流轉出更多土地,同時戶主健康狀況越好,流轉出土地的面積越少。還有,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以顯著增加土地轉出面積,其影響機制有可能與高社會資本家庭的影響相似,即收入較高的家庭在很大概率上就是高社會資本家庭。不過,模型(1)與模型(3)相比,家庭土地面積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正好相反。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在模型(1)中擁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偏好于流轉出土地,而在模型(3)中擁有更多土地的家庭在一定農地經營規模條件下并不愿意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
第二,當因變量為土地轉入面積時,高社會資本家庭的估計系數也在1%水平上顯著,且為正值。這說明,高社會資本家庭擁有充裕資本進而流轉入了更多土地。一方面,2015年以來,中央1號文件一直聚焦三農問題,不斷加大對農業和農地經營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對于戶主的身體狀況較差、離異或喪偶以及有殘疾人的家庭來說,他們普遍缺乏資本。所以,相比之下,高社會資本家庭流轉入土地的面積明顯更大。還有,當戶主為男性、配偶在世時,家庭土地轉入面積會顯著增加。可是,戶主學歷較高時,家庭轉入土地的面積又顯著下降。這可能是因為,戶主擁有較高社會資本,更適于從事非農工作。再有,加入合作社以后家庭轉入土地面積將顯著增加,說明農業專業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對農地規模經營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
(二)家庭結構對土地流轉價格的影響
除了土地流轉面積,在土地流轉中土地價格也會發生明顯變化。其中,家庭議價能力是影響土地價格的重要因素。而家庭議價能力主要決定于家庭結構,即是否為高社會資本家庭。
第一,以土地轉出價格為因變量,以社會資本程度分別為高社會資本家庭與低社會資本家庭的衡量指標,借此表示家庭結構差別大小,估計結果如表4模型(1)所示。首先,隨著高社會資本程度增加,高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轉出價格的影響顯著為負,并在10%水平上顯著。同時,低社會資本程度的估計系數也為負值,說明隨著低社會資本程度增加,低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轉出價格的影響減小。而與高社會資本家庭不同,低社會資本家庭影響土地轉出價格的絕對值和顯著性都有增加,說明低社會資本家庭在土地轉出時價格劣勢明顯。另外,家庭戶主為男性、健康以及未離婚或喪偶時,土地轉出價格也會顯著降低,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健康和具有完整婚姻戶主不以土地經營為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對土地需求更低,傾向于以更低價格轉出土地。事實上,具有優勢特征的戶主,包括男性、婚姻完整和健康狀況良好等,一般擁有更多收入來源,對土地價值的評價相對較低,很可能愿意以更低價格轉出土地。還有,家庭收入越高、轉出土地規模越大,其在土地轉出價格中越具優勢。

表4 家庭結構對土地流轉價格的影響分析
第二,當因變量為土地轉入價格時,如表3模型(2)所示,高社會資本家庭的土地轉入價格更低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土地轉入價格相對更高,但都不顯著。另外,戶主為男性、婚姻完整以及家庭勞動比例提高、加入合作社或轉入土地面積增加時,土地轉入價格明顯更高。相反,隨著戶主的年齡增加以及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提高,其土地轉入價格顯著降低。
(三)進一步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家庭結構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本文重新詳細界定了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一方面,高社會資本家庭被界定為農戶家庭有黨員、村干部、大學及以上學歷的成員;另一方面,低社會資本家庭是指,戶主離異或喪偶、健康狀況較差以及家庭有殘疾人。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細分高社會資本與低社會資本家庭后回歸
在土地轉入方面,家庭成員中有村干部會顯著增加土地轉入面積。這是因為,村干部對土地轉入政策相對熟悉,對農業產業扶持政策也更加了解;同時,作為村干部,意味著他肯定在農村務農,可以兼顧基層管理與農業生產,所以能夠顯著增加土地轉入積極性。另外,當戶主婚姻狀況為離異或喪偶時,土地轉入面積顯著下降,轉入土地價格也會更低。還有,當家庭成員中有殘疾人時,勞動力相對短缺,會顯著降低土地轉入面積。
在土地轉出方面,當家庭成員中有黨員時,土地轉出面積在10%水平上顯著增加。同時,其他變量并不顯著,尤其是戶主婚姻狀況、健康狀況以及家庭是否有殘疾人的影響較小,并不會作用于土地轉出。這說明,對于低社會資本家庭而言,農業生產依然是主要生活依靠和收入來源。另外,當家庭成員中有大學學歷人員時,土地轉出價格顯著提高。所以,有大學學歷的家庭擁有較高的議價能力。還有,當戶主婚姻狀況為離異或喪偶以及健康狀況不好時,土地轉出價格顯著更高。可能的原因是:當戶主的婚姻狀況為離異或喪偶以及健康狀況不好時,土地轉出面積更大,進而引致轉出價格較高。
五、穩健性檢驗
如前文分析,家庭結構對土地轉出和轉入都有顯著影響,特別是高社會資本家庭有助于推動土地流轉。為了檢驗上述實證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通過替換衡量指標、改變研究方法和調整研究樣本,重新進行了相關估計分析。
(一)替換衡量指標
針對前文估計方程中的自變量,即: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為了檢驗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其替換為精英程度和殘缺程度。結果如表6所示,顯然與表3相同,精英程度對家庭土地流轉的影響依然顯著。這驗證了前文實證分析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說明無論在土地轉入還是在土地轉出方面,高社會資本家庭都能顯著作用于土地流轉。

表6 替換衡量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二)改變研究方法
由于數據樣本存在斷尾現象,所以前文分析采用了Tobit估計模型。不過,土地轉入面積和轉出面積都是連續變量,仍然能夠采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校驗分析。同時,如果因變量為二值選擇變量,即是否轉出或轉入土地,也可以采用Probit估計模型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7所示,模型(1)和(2)是OLS估計結果,模型(3)和(4)是Probit估計結果。可見,無論是采用土地流轉面積還是采用是否進行土地流轉來衡量土地流轉狀況,而且無論是采用OLS還是Probit方法,高社會資本家庭都對土地流轉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影響較不顯著。這進一步驗證了前文實證分析結論的穩健性。

表7 改變研究方法的穩健性檢驗
(三)調整研究樣本
在前文估計分析中,由于家庭樣本既可能屬于高社會資本家庭,也可能屬于低社會資本家庭,所以為了提高估計精度,本文將所有樣本明確劃分為兩組,即高社會資本家庭樣本組和低社會資本家庭樣本組,分別進行估計分析。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模型(1)至(4)的自變量為高社會資本家庭,模型(5)至(8)的自變量為低社會資本家庭。首先,在模型(1)至(4)中,剔除低社會資本家庭樣本以后,無論是土地轉入還是土地轉出,高社會資本家庭都能顯著促進土地流轉。同時,在(5)至(8)中,無論是土地轉入還是土地轉出,低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流轉的影響較不明顯。因此,這驗證了前文實證分析的穩健性,進一步說明高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流轉具有顯著影響,而低社會資本家庭的影響不明顯,即土地流轉會受到社會資本影響。

表8 調整研究樣本的穩健性檢驗
六、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近年來我國土地流轉快速推進,土地流轉的決定因素,尤其是土地流轉是否會受到社會資本的影響,成為社會和學界關注的焦點。為此,基于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本文從家庭結構的角度探討了社會資本對土地流轉的影響。結果發現,無論是在土地轉入還是在土地轉出中,都會受到社會資本影響,即高社會資本家庭能夠增加土地流轉面積,在土地流轉價格中具有顯著優勢。相反,低社會資本家庭對土地流轉的影響較不顯著,在土地流轉價格上劣勢明顯。本文采用Tobit模型、Probit模型和OLS分析等方法,為此提供了經驗證據支持,并且替換衡量指標、改變研究方法和調整研究樣本以后結果依然穩健。
不過,在土地流轉價格分析中,高社會資本家庭和低社會資本家庭都產生了較為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的原因是,高社會資本家庭擁有更多資本,偏好于進入其他行業,農地經營不構成其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傾向于將土地“賤賣”;同時,低社會資本家庭缺少議價能力,所以土地流轉價格也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高社會資本家庭的價格優勢,顯示了土地流轉中可能存在精英俘獲。進一步細分家庭結構,本文考察不同類型家庭對土地流轉的影響。結果也表明,有村干部、黨員的家庭會增加土地轉入面積,而戶主婚姻狀況為離異或喪偶以及家庭成員中有殘疾人時,土地轉入面積顯著降低。并且,在土地流轉價格方面,戶主婚姻狀況為離異或者喪偶、身體健康以及家庭有高學歷成員時,農戶家庭具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土地轉出價格相對較高。總之,土地流轉會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但確實存在較為明顯的精英俘獲現象。
(二)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農村土地閑置、拋荒現象嚴重,農地低效使用已經嚴重限制了農村農業發展。土地流轉既可以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經濟發展,又能夠實現土地價值,有助于農民增收。但是,根據前文研究,土地流轉中受到家庭社會資本的影響,會導致相關公共政策的執行偏差:一方面高社會資本家庭可以享受更多惠農政策,另一方面低社會資本家庭卻不能從中獲益。這顯然會擴大農村收入差距,不利于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
因此,為了避免土地流轉中的不公平現象,推動農村農業經濟發展,就要求:第一,應強化基層治理,防止基層干部或擁有政治資本的家庭,即高社會資本家庭,獨占惠農政策紅利;第二,應加強對農村低社會資本家庭的保護,在土地流轉面積和價格等方面增加他們所獲經濟收益;第三,應加大對農村弱勢群體的現代農業技術培訓,使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以扭轉家庭劣勢,實現農地經營現代化、農業增產增收。
注 釋:
①資料來源:中新網,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6/08-10/7967918.shtml.
②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nyb/Document/1607052/ 1607052.htm
③感謝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數據支持,數據詳見官網:http://ciid.bnu.edu.cn/chip/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