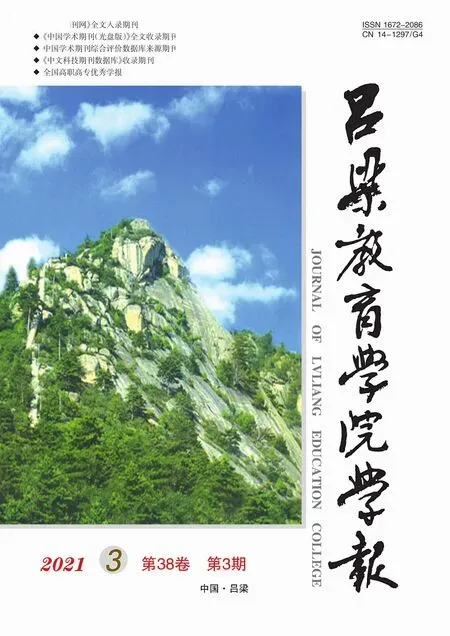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的敘事藝術
薛 慧
(南京農業大學民俗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95)
1980年代是話劇實驗探索、創新拓展的十年,這一時期由于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有利環境,“五四精神”再次進入戲劇家們的關注視野,戲劇家們紛紛發揮自身的審美創作才情,表達自身的主體意識。這十年是戲劇發展充滿生機,成就卓著的十年。在眾多的題材中,無論是從創作數量上,還是從總體取得的成就來說,農村題材的話劇似乎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是《桑樹坪紀事》和《狗兒爺涅槃》等農村題材劇作,無論是文學層面還是劇場層面的探索對當代戲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那么,相較于其他題材的話劇創作, 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創作呈現出何種特征?或者說,戲劇家們是如何藝術性地講好中國農村故事的?是否能對當下戲劇創作提供借鑒意義?因此,梳理戲劇家在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的敘事藝術便成為本文應有之義。
一、史詩性宏大敘事
隨著話劇民族化的討論逐步深入,以及尋根熱、文化熱的此起彼伏,1980年代的劇作家們不再拘囿于單一的現實主義創作,而是轉向浪漫主義的、象征主義的多元化創作,他們更期冀于從中國因襲的民族文化中重新審視日常中的問題。因而,從農村題材中追尋由歷史線性積淀而成的民族心理文化便成為這一時期戲劇家一種思考與表達的方向,并且往往呈現出宏大的敘事場面。
如1980年代的東北農村題材話劇《田野又是青紗帳》,這部劇塑造了性格迥異且人物特色鮮明的39個人物,通過日常生活中充滿濃郁的東北地域特色的細節,解讀長久形成的青紗帳文化。而在話劇《高粱紅了》之中,劇作家刻畫了19個不同身份的人物,圍繞1976年到1980年這段歷史時間展開,整體呈現著劇作家對人性、人情的沉思。在劇作《古塔街》中,劇作家通過一條狹窄的古塔街道,探討在這個小小空間中眾多的人物命運,劇作刻畫了22個人物的生活走向。同樣地,在話劇《昨天、今天、明天》中,劇作家運用了象征化的戲劇語言,探討20多個人物在不同時間段的人生際遇。當然,被譽為農村題材話劇兩座高峰的《狗兒爺涅槃》和《桑樹坪紀事》,同樣也在思考著類似的主題。
可以說,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把視角延伸到農村這片天地中時,戲劇家們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宏大的史詩性敘事,因而,人物數量之多,事件發生的延續時間之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龐雜,宗族關系與新的社會關系的沖突糾葛,都成為劇作家們關注到的問題。可以從《狗兒爺涅槃》、《桑樹坪紀事》以及《荒原與人》的敘事構架中窺探全貌。
《狗兒爺涅槃》的敘事便是圍繞狗兒爺的一生際遇所展開的,狗兒爺的一生典型性地代表了一大批跟他一樣的農民生存境遇。《桑樹坪紀事》則以桑樹坪這個封閉落后的農村為載體,敘述了這個村落里發生的幾個事件,刻畫了村落里形形色色的農民形象。劇作通過1968年到1969年的片段歷史卻讓人們看到了千百年農村文化的歷史縮影。
《狗兒爺涅槃》以狗兒爺這一人物為敘述主題,通過收芝麻、分門樓、分地續娶、買地發家、失地、得地、燒門樓等細節展開,狗兒爺所經歷的也正是中國千百萬農民所經歷的,這并不是簡單的個人遭遇,而是一個農村社會幾十年變遷的縮影。農民對“土地”的依附、依賴、癡迷甚至瘋狂,是隨著歷史發展逐漸構建的過程。雖然劇作做了藝術的夸張象征處理,但卻真實反映出了幾千年的農業社會歷史中農民與土地的復雜糾葛關系。土地,對農民而言,是財富與地位的象征。有了土地農民便有了糧食,有了糧食農民便脫離了窮苦。千百年來農民憎恨土地的所有者“地主”,也羨慕著土地的所有者“地主”。于是,狗兒爺對祁永年的情感十分復雜,攙雜著羨慕、嫉妒、恨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歷史變遷對農民命運的發展變化影響巨大,社會政策的變化很容易引發農民生活狀態天翻地覆的變化。例如,狗兒爺的個人命運發展便是如此:從發家到分得土地、從菊花青充公到土地上交,導致狗兒爺發瘋。劇作除了揭示大躍進時期的公有化制度不合理之外,更多地是在討論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老一代農民對土地的絕對依賴直接表現為喪失了土地便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所有基礎。這與狗兒爺的兒子(陳大虎)新一代農民形成了鮮明對照。新一代農民的發家致富基于改革開放的自由環境,可以說,歷史的發展不可阻擋,而農民的生存境遇與社會政策的出臺緊密相關。
與此同時,劇作刻畫了殘忍、蠻橫卻終究落魄的祁永年地主形象,刻畫了善于變通、圓滑、自私的蘇連玉農民形象,也刻畫了積極維護黨的政策的農村干部李萬江農民干部形象,以及其他一些善良、純樸的農村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農村人既有著農村人的質樸、善良,也有農村人的狹隘、自私。
可以說,劇作者試圖把各種各樣的農民囊括在歷史發展的場景中去展現他們真實的生存處境。幾代農民的發展奮斗歷史可以貫穿成農村發展史。于是,農民復雜的文化人格,便成為劇作家試圖去分析清楚的對象,其中不乏對農民文化人格中“劣”的揭示與探討。
如話劇《桑樹坪紀事》通過“麥客榆娃和小寡婦許彩芳的戀愛”“福林和他的婆姨”“殺人嫌疑犯王志科的遭遇”和“耕牛豁子之死”的故事來揭示由封閉村落的貧窮而帶來的一系列農村問題。
貧窮的境遇可以產生與愚昧、與倫理道德相關的聯系,農村人的貧窮直接導致娶不到媳婦、吃不上飯的問題。于是,轉房親、換親、賄賂討好估產干部、趕走外姓人王志科、殺死耕牛豁子的事件接踵而至。
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男尊女卑的古老命題。女性被暴打在農村往往習以為常,生女兒是別人家的媳婦的觀念也早已根深蒂固。在劇作中,李福林在一群漢子的慫恿下脫下了青女的褲子,并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喊聲:“我的婆姨!錢買下的!妹——子——換——下的!”導演在舞臺表達上運用了雕塑,用一尊侍女雕像以虛代實,運用象征的手法,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引發人們對農村無數類似女人命運的聯想。
其次在這個封閉的村莊,李金斗成為另一種隱喻象征,他為農村平均糧食的估產受盡屈辱,但在對付麥客榆娃和彩芳、對付外姓人王志科時顯示了他專制、陰險、狠毒的一面,阿Q式的欺下怕上在李金斗身上暴露無遺。李金斗在被公社干部打了之后說:“咱莊戶人還算個人嗎?打了也就打了…… ”但是在村民們逮住彩芳和榆娃的時候,他兇狠而毫不掩飾地下著命令:“少嚕蘇!接著打!在桑樹坪這塊地方,我說了算!”中國農村千百年來對上送禮諂媚對下壓迫專制的官僚作風依然在桑樹坪暢行無阻,更要緊的是家族血統等級觀念在這里形成了堅固的堡壘似乎牢不可破,并且成為一種深入大腦的思維定式。
例如,城里來的大學生朱曉平在得知李金斗被打后,為他打抱不平,但他的反駁依然也是以權壓權的思維邏輯,他說:“你長著耳朵去打聽一下,我爸爸是干啥的。”而一旁的許彩芳道出了朱曉平的身世:“這娃他大在省革委會當大官哩。”這一番對話讓我們看到封建血統論在農村的滋生蔓延與頑劣已經演變為一種深入骨髓的思維定式。令人玩味的是,劇作者用心良苦,通過角色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如果沒有好大呢?顯然,沒有這個在省里做官的好大,朱曉平的打抱不平絲毫沒有分量,也不會起半點漣漪。一方面,我們看到李金斗熟諳官場家族血緣關系的道理,利用后臺達到估產目的手段;另一方面,我們也體察到劇作者對“要是你沒有個好大”的質問與焦慮。
與《狗兒爺涅槃》有所不同的是,《桑樹坪紀事》的敘事方式并不標明故事發生的時間,使得故事本身極具象征意義。五千年的歷史,在這片熱土上似乎上演的是循環重復的故事。時間和人物都轉化成劇作家表達思考的符號。
李龍云的《荒原與人》在前兩部作品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運用了象征主義手法,該劇用一種意識流的寫作方式,描述了一批知識青年在農村下鄉的遭遇。其中雜糅了許多劇作家自身的個人經歷。在極端封閉的環境中,荒原與人既是充滿生存艱苦的沖突構成,同樣也是構建人與人糾葛而無解的荒原精神之地。因此,抽象的荒原,既是實在的北大荒,同樣也是荒蕪的精神荒原。人性的掙扎與美好因意識流的呈現而更顯宏大張力。 這幾部農村題材話劇之所以達到史詩的規模,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任何內容的表達都需要訴諸于形式,這兩部成功的史詩性劇作能在短短的幾小時之內在舞臺上充分表現,無疑離不開劇作家精心的編劇創作,這種成功便不得不提到布萊希特陌生化的編劇創作應用。正由于借助了布萊希特陌生化敘事方法,這一史詩的內容才能在舞臺上自如地展開,這也是劇作家藝術觀照的側重點。
根據布萊希特的理論,陌生化效果的編劇應用可以通過寓意、歷史化、歌唱的方法來創作。布萊希特認為,寓意是敘事劇最合適的創作形式,他說:“歷史事件是只出現一次的、暫時的、同特定的時代相聯系的特殊性,它具有被歷史過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從下一時代的立場出發所做的批判的。不斷的發展能夠使我們對前人的舉止行為越來越感到陌生。”[1]劉錦云在談及塑造狗兒爺這一人物形象時說道:“要超越自己的表現對象,去思考形成這一切歷史的、現實的、自然的諸種復雜根源。這樣,當我和我筆下的人物拉開一定距離的時候,便不僅看到了一些可惡、甚至可憎之處……”[2]因而,我們看到狗兒爺的“瘋”帶有極大的寓意性。失去土地之后的農民發瘋,正是其精神世界徹底坍塌的表征。
同樣,歌唱也是史詩性敘事達到陌生化效果的一種方法。它能夠突破時空的界限,打破舞臺幻覺,推翻第四堵墻來達到陌生化效果。如話劇《桑樹坪紀事》中的歌隊運用,歌隊可以直接評論劇情甚至和劇中人物對話。
總之,對照其他題材的話劇,農村題材的話劇明顯顯示出在時間長度和空間廣度上先天優越的題材優勢。具體而言,農村題材的話劇《狗兒爺涅槃》、《桑樹坪紀事》所容納的歷史變遷、人性復雜、農民性格、民族文化等內容的龐大為史詩性的作品提供了可能,而劇作家嫻熟的專業技能與深刻的生命體驗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這種宏大的史詩性敘事,利用政治、人性和文化的寬廣視角對幾千年積淀的民族文化進行多維審視,并借助于布萊希特的陌生化理論而成為探索的典范。當然,劇作家除了在時空構架中思索農村承載的文化之外,在農村這一比較獨特的語境中也不遺余力地探尋著農村之味。
二、凸顯農村之味
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相對于歷史題材、都市題材的劇作更凸顯出劇作家或者導演對農村味的深刻領會。這種農村味表現于作品和舞臺上便是生動的戲劇動作、豐富的民俗習慣與待人接物的方式,而這些舞臺表現的背后則已經標識著民族傳統文化的人格內化。欣賞一出出農村題材的話劇,就是在品味鄉村文化所滲透的農村味道。
(一)方言俚語之“土”
戲劇動作通過形體、言語、心理甚至靜止來推動劇情發展、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從而彰顯戲劇所要表達的精神內涵。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在戲劇語言上采用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手法來突出農村的生活風味。
農村題材的話劇在語言上凝練集中地展現農村真實生活的風貌,通常通過舞臺提示語、對話、旁白和獨白等形式來呈現。劇作家在舞臺提示方面用心營造農村土味十足的氛圍。如話劇《桑樹坪紀事》中李金斗在檢舉信上按手印的舞臺動作,李金斗用盡了全身力氣撲倒了桌子,死死地摁住掉在地上的狀子,然后用力按上他的手印。在這一系列舞臺動作當中,“撩胳膊卷袖子”表現出李金斗極其重視的心態和認真嚴肅的心理,繼而“桌子被按倒”“趴在地上”“死死按手印”的一系列動作提示,可以看出,李金斗對外姓人王志科的排斥越發堅決徹底,人物的心理發展層層遞進。最后,李金斗自私、狹隘的農村文化人格由此立體呈現。
我們發現,農村語言在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中被劇作家作為展現農村地域色彩的一個重要元素。一方面農村題材話劇通過方言的表現,也即利用俗語、人名、語氣詞、粗話等,對農村生活原貌進行藝術的集中展示,另一方面也是對農村文化的心理揭示。正因為獨特的方言所散發的農村味,才能使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豐滿而真實。許多農村題材的劇作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自覺地在作品中著力凸顯這種農村味。
方言的口語使用如“咋整的” “躲窩鋪”“我中”“不埋汰”等。在舞臺表現上,劇作家力求做到真實生動。如劇本提示“賣耗子藥的(山東口音):這香瓜多少錢一斤?俺買兩個,口渴的冒火,這地方耗子真多,一門打架,他娘的,吱吱地叫!”可以看出,方言的大幅度使用不僅給觀者帶來親切的感受,也幫助人物更加生動真切。幾乎所有的農村題材作品都會用到俗語,如 “青瓜裂棗,誰見了誰咬”“急水灘的石頭——經過風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瓦盆破了當土碗,蚯蚓死了還要‘扳幾扳’呢”等。這些俗語對農村人來說信口就來,運用自如。語言是話劇的關鍵,可以說,人物的塑造、思想的表達都離不開生動的語言表達,不管是東北的“咋整”,山東的“俺”還是粗俗的習語加調侃,這種扎根于泥土的本色才是農民的顏色。
(二)民俗風情之“土”
民俗習慣與待人接物方式也被劇作家關注擷取成為標識農村味的另一方面。如話劇中多次用到了二人轉,二人轉作為東北民俗的一種娛樂形式在劇作中反復出現,就連《古塔街》中的段傻子也會熟練地唱幾句“叫聲丫環跟我走,一到花園去散心兒;小丫環便在頭里走,后跟著美蓉大閨女兒……”當然,農村題材話劇作品中對農村“換親”“借壽”的習俗也多次關注。《桑樹坪紀事》《好媳婦訪問記》《紅白喜事》等對此習俗一再提及。
有時候農村人的土氣在迷信的標簽下卻也顯得可愛而質樸。如《田野又是青紗帳》中彥子對農村習俗的揶揄“(念黃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拘魂碼”“左眼跳財,右眼跳禍”等。這種體現著各個地方民俗色彩的娛樂形式、婚喪習俗、祭典儀式雖或寄托著創作者的批判之旨,但同時也彌散著特定地域的鄉土氣息。
(三)待人接物之“土”
農民待人接物所恪守的原則,應變處世的習慣性選擇都滲透著農村文化的深層積淀。比如,農村中對人名的稱呼是直來直去,但是這種直率本身就是農村人特有的性格。如“陳大腳”“老疙瘩”“狗不理”“八聾子” “王半拉子”等,這種在城里人看來是侮辱別人的綽號在農村人看來卻是異樣的親切樸實。
當然,農村人的土氣也體現在對“性”的直白調侃中,如小英子二人轉中的“氣壞了三條腿的大褲襠……”農村人的性調侃是在被封建禮教壓抑的環境中釋放被壓抑的力比多的不自覺意識。
對罵、打群架在農村習以為常。如在話劇《桑樹坪紀事》一開頭,陳家源村與桑樹坪村因為下雨就引發了言語沖突,開始對罵:
“桑樹坪村民 (吼)
黑龍黑龍(倉)過過喲(嚌當當)
走到南邊(倉)落落喲(嚌當當)
鄰村村民 (對喊)
黑龍黑龍(倉)站站喲(嚌當當)
站到北邊(倉)落落喲(嚌當當)
……
[桑樹坪人急了,沖著鄰村人罵了起來。]
桑樹坪村民:狗日的心黑,喊雨站哩!
鄰村村民:驢日的心壞,把雨往這搭趕哩!”
以上的對罵語言相當粗俗直接,并且還形成了民間小調,對仗工整,不失為充滿農村特色的對罵。下雨本身并不會按照個人的只言片語發生轉變,但是大家依然相信祈禱的力量,通過向天祈禱,希望龍王多向自己所在的村子下雨,而與之相關的鄰村村民,生怕龍王聽到顯靈去了鄰村,于是也集體祈禱。但凡有一人脫離開祈雨的情境,把矛頭指向對方,那便很快形成了集體對峙,事情已經脫離了祈雨本身,對罵與打群架便相繼發生。由此,農村人在面對外來沖突的團結一致與內部爭斗時的狹隘自私在對罵中得到了詳盡的展示,農村因襲的文化在農民應變處世的戲劇情境中得到豐富化與生動化的揭示。
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中,農村味的突顯往往使這些作品呈現強烈的風格化特點。表現在語言上,地頭田間或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作為指物、論理、說事的輔助,從而產生了豐富的比喻,比興,歇后語;穢語、臟話,侮辱性的綽號以不雅不敬的方式表達人際關系的親熱;性的調侃瞬間釋放了禮規所壓抑的欲望。而體現著各個地方民俗色彩的娛樂形式、婚喪習俗、祭典儀式雖或寄托著創作者的批判之旨,但同時也彌散著特定地域的鄉土氣息。而農民待人接物所恪守的原則,應變處世的習慣性選擇都滲透出農村文化的深層積淀。
總之,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所有的舞臺創作包括劇作者、導演、演員等都有意識地通過突出農村味來表現農村生活。農村味的著重體現是農村題材創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話劇獨立于政治尋求自身藝術性的努力,1980年代農村題材的話劇劇作家正是回到話劇本體,扎根于現實,對農村的歷史現狀進行思考。其中,對農村味的著力凸顯其實也是劇作家們對話劇藝術觀照的努力嘗試。
三、敘事在繼承與探索之間
1980年代話劇藝術觀念多元化并存,一方面是由于戲劇家們在戲劇危機的事實面前,發現當代戲劇自身封閉的嚴重性,新中國以來,話劇“易卜生——斯坦尼模式”被程式化后越發脫離了生活基礎,“問題劇”“領袖劇”喪失觀眾共鳴基礎。另一方面,隨著翻譯界領域的不斷拓寬,之前對蘇聯、挪威等國家的譯介開始向西方其他國家拓展,貝克特等的荒誕派戲劇、布萊希特的史詩劇、格羅托夫斯基的貧困戲劇、阿爾托的殘酷戲劇,以及存在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等各種戲劇流派的戲劇理論主張都被大量地譯介到戲劇家的面前,其中各流派所表現出對傳統的反叛、對自我個性的弘揚和藝術舞臺表現形式的多元化都對中國戲劇家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西方戲劇對中國戲曲“寫意”的借鑒也引發了國人對自身民族戲曲文化的思索,戲劇家從“舞臺假定性”出發發掘了民族戲曲中“寫意”的藝術魅力和審美資源。胡偉民認為:“中國話劇藝術的革新浪潮是大膽走向復歸戲劇的本質假定性,其總趨向是在追尋我們民族戲劇藝術傳統之根。”[3]高行健也提出:“借鑒西方戲劇,顯然有助于我們開闊眼界,結合我們本民族的戲劇傳統,去研究我國戲劇藝術發展的道路。”[4]那么作為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也必然在探索話劇思潮下做出積極的回應,需要明確的是,這樣的探索是奠定于繼承基礎上的多方探索。就農村題材話劇來說,一方面在劇作創作手法上表現為對現實主義傳統創作的回歸繼承與對中國傳統戲曲、西方現代流派創作手法的借鑒吸收;另一方面在舞臺呈現上表現為對斯坦尼斯表導演理念繼承與對布萊希特演劇體系以及中國戲曲演劇觀念的借鑒吸取。
(一)劇本創作探索新現實主義風格
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創作廣泛采用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出新現實主義創作風格。1980年代前期農村題材話劇創作注重描摹真實的農村生活情態,劇作情節的展開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守則,情節隨著事件自然發生的時間發展,并不采用過多的創作技巧,大多采用的是開放式的戲劇結構。如《趙錢孫李》中反映農村斗爭生活的情節便是依據1979年深秋的某天上午的自然時間順序而展開。同樣在《張燈結彩》《落鳳臺》《吉慶有余》《山鄉女兒行》等作品中的時間發展也是按照事件起始時間展開。這些作品并不精心于表現形式的多方變換,而是注重于對現實農村生活的真實展示與生動描繪,主要通過人物關系在事件刺激下的調整來深入刻畫人物性格。這種真實的農村生活情境與戲劇表達的主題往往結合緊密,引導觀眾在如臨其境的農村生活中洞察戲劇主旨。
新時期的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在回歸的同時也在發生著新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以真實反映農村生活為基調的多種舞臺語匯表達,包括對中國戲曲當中寫意化的動作、場景的吸收以及對西方現代流派中時空交錯、內心外化、靈魂出現、幻覺、歌隊合唱等的學習借用。可以看出在表現形式上的多方創新,是劇作家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努力超越,但這種新現實主義創作依然不能脫離人物、事件的具體真實背景。譬如《狗兒爺涅槃》《桑樹坪紀事》便是農村題材話劇新現實主義創作的典范。《狗兒爺涅槃》在反映幾十年農村變革與狗兒爺生存遭遇的基礎上利用時空交錯、心理外化、靈魂、寫意性的布景與動作等手法來強調劇作者的主旨,從而激發觀眾產生共鳴的觀劇心理效果。《桑樹坪紀事》采用幾個真實的生活片段故事,刻畫桑樹坪農民的不同性格,其濃郁的文化批判在“圍獵”“打牛”的象征意象中激發觀眾思考。
不論是農民性格還是農村實際生活內容都具有重實際、求實效的特征,農民在動機與目標之間往往采取直接自然的路徑。這就使得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的劇作家多選擇與表現對象和表現內容相適應的寫實手法,包括如實呈現農民的生活內容、命運遭際,采用生活化、口語化的語言,但同時也對表現形式進行多方積極嘗試,打破以往單一僵化的創作理念,努力豐富舞臺語匯。
(二)舞臺呈現既寫實也寫意
在舞臺呈現上,斯坦尼斯的演劇體系中“重體驗”“演員、角色”所激發的“幻覺”效果體現在舞臺背景的真實描摹、演員的真實體驗等方面。1980年代《紅白喜事》等作品便是對這一舞臺理論的積極實踐。《紅白喜事》中的舞臺背景,煙囪可以冒煙,機井可以打出水來,房頂結實得可以站人,這種純寫實的舞臺呈現有利于觀眾身臨其境地觀劇體驗。而農村題材的話劇表演風格也極力貼近農民真實的生活情態,努力刻畫逼真的農民性格形象。
隨著探索思潮的發起,布萊希特演劇中打破第四堵墻產生“間離”陌生化的劇場效果也為農村題材的表演吸收,同時中國傳統戲曲中寫意性的場景、程式化的動作等也被農村題材話劇的舞臺所采用。由此,在繼承先期斯坦尼演劇體系理念的基礎上,布萊希特、中國戲曲等演劇理念進入劇作者、導演、演員的探索視野。探索的重點一方面表現在劇作內容的“心理外化”“鬼魂”“夢幻”“插科打諢”“歌隊”“時空轉化”等的攝入,另一方面表現在舞臺表現形式中的觀演關系調整。在調整舞臺表現形式的“觀——演”關系方面,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的導演、演員和舞美都表現出積極的主體意識。
首先,1980年代農村題材話劇導演的主體意識不斷得到強化,導演的藝術創造使舞臺得到不斷深化與升華。導演的主體能動性在探索話劇中表現的更加明顯,以徐曉鐘和林兆華為例。
徐曉鐘在劇作中引入了自身對寫意的思考,同時也成為其二度創作的特征。第一,《桑樹坪紀事》中麥客進村、出村的場面,徐曉鐘利用寫意的藝術手法,讓演員們圍成一個圈,組成一支浩蕩的大軍做著舞蹈化跑圈的動作,同時轉臺則逆著麥客的行進方向轉動。演員的動作與轉臺的逆轉,音樂的烘托,營造出詩意的幻覺,中華民族的艱難歷程與這詩意的場景融為一體,擴大和延伸了觀眾觀賞想象力。第二,對于再現與表現兩種不同的美學原則,徐曉鐘把二者進行了有機的結合。在話劇《桑樹坪紀事》中,一方面導演在人物關系、矛盾沖突以及性格塑造等方面,基本運用再現的美學原則,真實描繪了桑樹坪村民們的生活、青女的悲劇婚姻、彩芳被逼投井、月娃被賣、志科挨打入獄等等,這些情節都是寫實的再現的去表現村民們極度貧困和愚昧不堪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導演融入了歌隊、舞隊、唱詞、曲調、形體造型等形象來再現情節。比如“圍獵”式審美舞臺意向成為一種象征而成為導演的獨創。第三,導演融入了更多戲劇性因素。導演的二度創作中,全劇沒有一個中心事件是貫徹完整的,在三個篇章中,以彩芳、青女、月娃、外姓人志科和老牛“豁子”的遭遇和命運為五條情節線索而互相穿插。如把志科受整的情節線與老牛“豁子”情節線交叉起來,把老牛和志科的“圍獵”聯結起來。導演試圖讓觀眾在“體驗”的同時也不時地“間離”,對作品產生理性的思考。第四,徐曉鐘結合了具象與抽象的手法。如“月娃出門”“青女過門”“青女鋪排男人”等具象化的情節和“青女受辱”“圍獵”之后的裸女石雕等抽象化,體現出很大的隱喻特征。
林兆華導演在總結話劇《紅白喜事》創作經驗時說:“我發現,習慣往后看容易滿足,而往前看無窮的世界,則更能喚起我創造的激情。因此,我喜歡不停地探索、實踐。歷史和未來,我更著眼于未來。”[5]《紅白喜事》是以繼承寫實為主的作品。如舞臺上的煙囪可以看得見冒煙,機井可以打出水來,房頂牢固得可以站人,樹上的喇叭可以真的發出聲音……盡管如此,導演也努力打破寫實觀念的限制,嘗試“虛”的設置,如他把寫實布景的正面房屋(鄭奶奶和熱鬧的新房)面對觀眾的墻拆除,使觀眾能清楚看到兩個空間進行著的不同生活狀況,給演員的表演也帶來直觀能動的好處,這是導演藝術思維上的創新與突破。
《狗兒爺涅槃》中導演靈活轉換時空,使得現實、回憶、想象、夢幻互相交錯或者平行。如人與鬼魂的同臺對話交流,或者通過演員走一個阿拉伯數字“8”字形來說明空間的更換。全劇主要利用寫意的手法來表現一位中國傳統農民在新的社會變革中所經受的精神磨難,他對土地和勞動的眷戀以及他自身的狹隘與保守交織在一起。導演用一種反時空的方法來外化人物心理,如一開場時狗兒爺亮相,他劃了一根火柴,并點燃了火把,隨著光影,身后出現了祁永年的幻影,而幻影又從身后吹滅了火把,驚異的狗兒爺開始與之對話,于是人與幽靈在同一時空展開了靈魂角逐。狗兒爺幾十年生活的變遷辛酸往事,他對高門樓的恨和成為自己私有財產后的誓死捍衛的心理都得以在舞臺上表述,這種舞臺假定性的時空構筑,在制造幻覺的同時又打斷它,形成了主觀體驗和流動寫意結合的藝術時空。
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在借鑒各種舞臺表現手法的同時也面臨內容與形式的適合與否的問題,不管是任何的舞臺語匯,其目的始終是為表達戲劇內涵而服務。但是在1980年代的舞臺多樣化語匯創作中同樣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譬如為形式而形式,為迎合觀眾而粗制濫造,甚至出現“一窩蜂”的雷同現象,或者是過于抽象的舞臺語匯讓觀眾不知所云,或者是過分的“間離”導致了審美疲勞。1980年代的農村題材話劇同樣面對著如此的困惑,包括錦云在1989年創作的《鄉村軼事》都存在過分抽象化而晦澀難懂的嫌疑。諸如此類的弊端并無助于農村文化特質的揭示與對農村審美規范的溝通。
四、結語
總之,在實驗探索的1980年代,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歷史政治環境,戲劇危機所激發的關于“戲劇觀”的論爭以及由此形成戲劇革新的戲劇文化環境,大大提高了戲劇家們的主體意識。正是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守舊與創新所融匯交織的歷史文化環境奠定了話劇光輝而卓有成效的十年,農村題材話劇在繼承與探索之間進行積極嘗試,從而在這光輝十年當中撐起一片別開生面的天空。正如此,其史詩性宏大敘事模式、凸顯農村之“土”味,以及在繼承與創新間積極探索的嘗試帶給當下戲劇創作回味無窮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