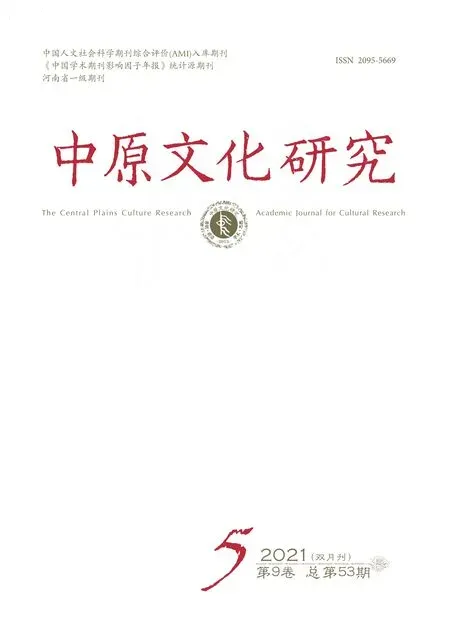千畝之戰析疑*
杜 勇
千畝之戰是周宣王晚年征伐姜氏之戎的一次著名戰役。戰爭在鎬京近郊進行,周王室占有天時地利,結果不僅未能打敗姜戎的進攻,反而是王師潰退,奄父快馬駕車才使天子脫逃。周王室權威掃地,共主地位一落千丈,統治力量受到嚴重削弱,無形中助長了犬戎伐滅宗周的政治野心。然而,關于此役的次數、地點、起因及影響等問題,學者多有分歧,即使清華簡等新出文獻的問世,也未消除重重疑云。本文擬就此略作探索,以期形成正確的歷史認知。
一、千畝之戰的次數
千畝之戰到底是一次還是兩次?學者的認識各有不同。今人楊伯峻先生繼日本學者竹添光鴻之后,力主千畝之戰有二:一在周,未言地望;一在晉,地即岳陽。晉地之戰“前于周宣王之役十三年,且晉戰而勝,與周宣王之戰而敗者不同”①。楊寬先生引為同調,認為晉穆侯十年之役“當是另一次千畝之戰”[1]573。清華簡《系年》記“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整理者認為此役在周都附近,與“晉穆侯千畝之戰的千畝在今山西并非一地”②,堅持千畝之戰分為兩次。但也有學者旗幟鮮明反對此說,認為宣王時千畝之戰只有一次,兩次說是錯誤的③。其是非曲直有必要作進一步探討。
千畝之戰兩次說的依據來自《史記》。其《周本紀》說:
宣王不修籍于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此條史料當取材于《國語·周語上》,且與近出清華簡《系年》相印合:“(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傳世文獻與地下材料交相印證,是無可疑。所謂另一次千畝之戰見于《晉世家》: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
此一記載主要取材于《左傳》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此記穆侯千畝之戰并未系年,而《史記·晉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以下簡稱《年表》)卻推為晉穆侯十年(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依據何在?很可能是《晉世家》所說:“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年表》擬定昭侯元年為平王二十六年,此前文侯在位35年,再往前是殤叔4年,穆侯27年,故可推得桓叔(成師)生于晉穆侯十年(宣王二十六年),亦即穆侯“伐千畝”的年代。雖然司馬遷說“靖侯已來,年紀可推”[2]1636,但他所推晉獻侯、穆侯、文侯的在位年代實際都存在問題(容后詳論),即使桓叔封曲沃時的年齡不誤,也不能說明晉伐千畝必在穆侯十年,不能證成千畝之戰兩次說。
從前人們不曾注意,司馬遷本人并未將千畝之戰視為兩次不同戰役。《周本紀》《晉世家》言及千畝之戰,雖在晉穆侯與宣王的年代對應上兩不相諧,但《年表》只列晉伐千畝一役,對宣王三十九年敗績于千畝只字未提。王師敗績于千畝,事態更為嚴重,遠非晉侯“伐條”“伐千畝”等戰役可比,沒有不入《年表》的道理。如若千畝之戰確為名同實異的兩次戰役,司馬遷制作《年表》之時,當如宋元時期《通鑒外紀》《通鑒前編》一樣,前后分列,劃然兩事,而不會有此疏漏,顧此失彼。至于千畝之戰在紀年上的抵牾,司馬遷未必不知,只因一時難于厘清,就只好以客觀審慎的態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2]505。
在中國早期歷史年代學研究上,司馬遷是有卓越貢獻的。特別是西周共和以后年代的整理和厘定,使中國歷史從此開始有了確切紀年,確是司馬遷一項杰出的學術成就。但西周年代學研究極為復雜,涉及面廣,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尤其是十二諸侯國的年代資料多寡不同,事與年的系聯,侯年與王年的對應,很難做到準確無誤,甚至有時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也無從調適。例如,《史記·陳杞世家》說:“(陳)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依此推算,共和行政就不是14年而是17年,而共和元年在《年表》中對應的也不是陳幽公十三年而是十四年,宣王元年對應的不是陳釐公六年而是五年。又如《魯世家》說魯武公九年卒,《年表》卻出現魯武公十年;說“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叛)周,犬戎殺幽王”,《年表》卻將此事記在孝公三十六年,竟相差11年。可見司馬遷對十二諸侯紀年的整理面臨極大困難,實際結果并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精密周詳。
晉國歷史紀年的情況,同樣紛繁復雜。《晉世家》說:“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2]1636從周初唐叔封立到靖侯所在的厲王之世,晉侯不可能僅歷“五世”,“無其年數”也只是說見不到相關文獻,不代表各位晉侯原無紀年。年代資料的匱乏,在靖侯之前如此,之后也不會好到哪里去。若無直接材料可據,僅憑相關年代推算,其可靠性自然不能估計太高。《晉世家》說:“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其文意非常清楚,靖侯十七年即共和元年,但《年表》卻列靖侯十八年為共和元年,前后不相照應。若將晉國紀年與后來的出土文獻相對照,問題似乎更大。如晉文侯元年,依《年表》在幽王二年,古本《竹書紀年》顯示卻在平王元年,二者相差10年。古本《竹書紀年》說:
(1)晉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友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3]70
(2)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④
這兩條材料同記鄭桓公伐鄶滅虢之事,只是引文方式略異,據此可知晉文侯二年即幽王既敗2年(平王二年),表明晉文侯與周平王在同一年即位,并非《年表》所記在幽王二年。此年鄭桓公尚未出任司徒,他既不可能以幽王八年才有的司徒身份與史伯談及東寄孥賄之事,也不可能伐鄶而居鄭父之丘。故蒙文通先生正確指出:“史公紀晉文侯之年,已先于《竹書》者且十年。”[4]60如果按照《竹書紀年》所載晉文侯元年即平王元年逆推,加上司馬遷所定殤叔4年,穆侯27年,則穆侯即位在宣王二十七年。前一年他尚未繼位,豈可以穆侯身份主導千畝之戰?
新出晉侯蘇鐘與古本《竹書紀年》的年代指向亦復相同。該鐘銘云:“唯王卅又三年,王親遹省東國南國……王親命晉侯蘇,率乃師……伐宿夷。”(《近出殷周金文集錄》35—36)銘文中的晉侯蘇就是晉獻侯,即穆侯之父。根據《年表》,晉獻侯在位時間是宣王六年至十二年,宣王三十三年晉國之君是晉穆侯而不是晉獻侯蘇,故有學者認為鐘銘三十三年當為厲王紀年[5]326。若然,《史記》所記獻侯的年代就錯得太離譜了。或以為是晉侯蘇即位后追記此前跟隨厲王東征時的記錄[6]10,亦非的當。厲王三十三年是靖侯當政,代為出征的不是其子而是其孫,周天子卻幾次使用“晉侯蘇”的稱謂發表命令,即使用后來的身份追述也是不符合周代禮制的。何況厲王三十年實行“專利”,后又利用衛巫“弭謗”,心思也完全不在東國南國的事務上。可見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與周厲王無關,只能是宣王的紀年,而《史記》所推晉侯蘇的年代應有舛誤⑤。宣王三十三年獻侯蘇尚在君位,其子穆侯在宣王二十六年同樣不可能以晉師“伐千畝”。
古本《竹書紀年》不只顯示晉國紀年存在嚴重誤差,而且還有材料證明千畝之戰只有宣王三十九年一次。《后漢書·西羌傳》引古本《竹書紀年》說: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后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在這段記載中,有幾個關鍵點須加注意:
其一,“明年,王征申戎”所指為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的千畝之戰。由于申與姜戎同為四岳之后,亦是姜姓,故以申戎代稱姜戎可,清華簡《系年》省稱為“戎”亦可。從文獻上看,宣王三十九年除了伐姜氏之戎外,別無其他伐戎之舉,故申戎只能是姜戎氏的代稱。陳槃先生說:“申戎亦姜姓,蓋姜戎之別部,故申戎亦可名姜氏之戎。然曰姜氏之戎、曰姜戎,不即等于申戎。”[7]1036雖然申是申,姜戎是姜戎,但二者血緣上有一定聯系,稱姜戎為申戎可謂不中亦不遠。
其二,此言王破申戎,與《國語》說王師“敗績”不同,勝負雙方易主,必有一誤。近出清華簡《系年》第一章說:“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8]136是知此役以王師敗績為可信。至于《晉世家》說晉穆侯伐千畝“有功”,是司馬遷對《左傳》“成師”所作的不恰當演繹,后世學者多不采信,故以“成其師眾”⑥釋之。“成師”實際是說此役晉師得以保全,與戰爭全局無關。此與趙之奄父為宣王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2]1780一樣,雖然宣王成功脫險,奄父有功,但無改于王師敗潰的整個結局。
其三,古本《竹書紀年》所言千畝一役,發生在宣王征伐條戎奔戎之后,時間上只間隔兩年。而《晉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所言穆侯伐千畝亦在伐條之后,時間上同樣只間隔兩年⑦。裘錫圭先生認為:“彼此顯然是一回事。”[9]70洵為卓識。這個證據非常有力,不容別作解釋。宣王與穆侯征伐的對象同為姜氏之戎,時間同在伐條兩年之后,地點又同為千畝,卻偏偏不是同一次戰役,事情斷不至于如此巧合。司馬遷不在《年表》中復列宣王三十九年的千畝之戰,原因就在這里。
過去,人們對《年表》的誤差估計不足,過于相信司馬遷對晉國紀年的推定,以至誤判有兩次千畝之戰。今將地上地下各種文獻對比分析,證明千畝之戰只有一次的結論,可能更符合歷史的真實。
二、千畝之戰的地理方位
關于千畝之戰的地理方位,晉唐學者先后提出京郊、介休、岳陽三說。京郊說為晉孔晁所倡,他說:“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于近郊。”⑧“近郊”是指周都鎬京近郊,大概由推求《史記》《國語》文意所得。介休說來自杜預,其注《左傳》桓公二年“千畝之戰”云:“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⑨“界休”后改稱介休,于今仍為山西縣名。岳陽說是唐代張守節提出來的,其依據來自《括地志》:“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⑩岳陽在太岳山南(今山西古縣),離介休縣一百多公里。明末清初顧炎武說“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認為《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應如《史記正義》所言在岳陽縣北九十里?。諸家說法雖有不同,但都不曾把千畝之戰看作兩次,因而才能圍繞同一議題發表見解。唐代經學大家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對晉穆侯“千畝之戰”作疏,引據《國語》并作評騭說:
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于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10]433
孔穎達認同孔晁的說法,主張千畝之戰地在京郊,無涉晉境,是很有見地的,故能得到后世學者的廣泛認同。清汪遠孫說:“王自伐戎而遠戰于晉地,必不然也。”[11]21閻若璩《潛邱札記》、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所見略同。其根本依據在于,宣王伐千畝與不籍千畝當在同一個地方,故不可能遠至晉地。
清華簡《系年》發現后,不少學者覺得“千畝之戰”與“不籍千畝”,雖然俱稱“千畝”,但其內涵有異,并不在同一個地方,因而堅持兩次千畝之戰的說法。《系年》第一章說: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宣王是始棄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8]136
所謂“帝籍”,是指專門為祭祀上帝而設的籍田,又名之曰千畝。漢賈逵即有類似見解:“天子躬耕籍田,助民力也。籍田,千畝也。”?簡文說商王“不恭上帝”,不敬祀神靈,失去上帝眷顧,故周人得以東進克商,光有天下。宣王不籍千畝,也是不敬上帝的行為,終遭懲罰,結果被姜戎大敗于千畝。從表面上看,作為籍田的千畝,與作為戰地的千畝似乎意涵不同,不能等視齊觀。宋金履祥就說:“《國語》與不籍千畝同事,非也。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地名也。”?其實,這是一種靜止看問題的思維方法,不免以文害辭。田名與地名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鴻溝。籍田并非普通的小塊田土,而是遠近聞名的大面積王家田產,久而久之轉化為地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尤其是天子每年春耕前要在這里舉行籍田禮,田名與地名更容易合二為一。《國語·周語上》言及籍田禮說:
及期,郁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
其典禮場面浩大,參與人員眾多,天子祼鬯饗醴,百官庶民畢從,最后由庶民完成耕作。由于厲王被逐,籍田禮廢,周宣王即位后,不想再裝樣子,重修籍禮,因而受到朝中大臣的諫阻。只是周宣王過于任性,拒不采納,籍田之禮最終還是廢除了。其后籍田的耕種不再受重視,但千畝作為籍田之名,演變為一個人們熟知的地名則不會無端消失。數十年后,在這里發生一場以地命名的千畝之戰,并不費解。
當然,“不籍千畝”與“千畝之戰”確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事件,《國語》與清華簡《系年》之所以把它們編連在一起,并非無原則拼湊,而是時人宗教思維使然。他們認為這兩件事都關乎上帝的意旨,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系。《國語·周語上》中虢文公勸諫宣王說: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純固于是乎成。……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
這是說籍田事涉農耕,上帝的祭品,民眾的繁衍,國事的供給,社會的和諧,財政的增值,國力的強盛,無不與此息息相關。如果不籍千畝,輕怠農事,必然是“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得不到上帝福佑,也無以使民。因此,千畝之戰的失敗,時人把它歸因于宣王不籍千畝,乃至神怒民困,造成王師敗績的嚴重后果。在這里,前一個千畝說的是籍田,后一個千畝說的是戰場,但地名為其共性。《國語》《系年》中兩個“千畝”相承而言,不僅在邏輯上而且在事實上只能是同一地點。
那么,這個千畝究意在什么地方呢?由于千畝本為籍田,每年春耕時又要在此舉行籍田禮,自然是孔晁所言地近京郊為合理。清人閻若璩說:“此千畝乃周之籍田,離鎬京應不甚遠。……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舄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引此以證千畝地望,并謂:“《括地志》以晉州千畝原當之,殆非。”[12]285蒙文通先生也認為:“惟姜氏之戎于其盛時,來戰于千畝,則逼王畿之近地。”[4]59這些都是明達之見。道理很簡單,天子舉行籍田禮的地方,不會遠離京城。盛大的典禮活動,繁復的表演程序,若是遠離鎬京,甚至跑到諸侯國的領地上舉行,不僅勞師動眾,操作不便,就是那一份長途跋涉的辛勞也不是王公貴族所樂意承受的。因此,把千畝之戰的地理方位定在鎬京近郊,遠比其他說法合理可信。至于千畝確切位置的考定,則有待更多新材料的發現。
三、千畝之戰的起因及影響
發動千畝之戰的姜氏之戎,又稱姜戎氏、姜戎。姜戎與申、呂、齊、許均為四岳后裔,姜姓部族,是周王朝賴以立國的姬姜聯盟的成員之一。此時何以風云突變,致使姜戎與周王室兵戎相見?千畝之役又帶來怎樣的嚴重后果?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國語·周語下》說:“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岳佐之……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此言四岳為共工氏從孫,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賜姓立國,以呂為氏。四岳裔氏之國有申、呂、齊、許等,但各自的立國時間并不相同。《周語中》說:“齊、許、申、呂由大姜。”意即四國的封建緣于大姜的外戚關系。大姜為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娶自姜姓部族。武王克商,成為天下共主,得以封建外戚齊、許、申、呂四國。齊、許在周初封立,申、呂屬于重新冊封。《史記·齊世家》說:“(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是申、呂立國比齊、許要早,夏商時期即已存在。《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說:“姜,大岳之后。”又隱公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胤也。”是知四岳又名大岳。作為部族名或其居地名的大岳,其具體方位可由《尚書·禹貢》考知。其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所涉地名在今晉南及與豫西交界一帶。“壺口”在今山西吉縣西,以壺口瀑布著稱。“雷首”即今山西中條山脈西南端。“太岳”即大岳,指《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彘縣的霍大山(今霍州市東南)。《國語》《左傳》《禹貢》的著作時代相近,書中所用術語的內涵亦必具有同一性。顧頡剛先生提出四岳不在晉南,而是指今陜西西部隴縣一帶的古汧山[13]40。其說置《禹貢》等史籍于不顧,也不考慮大禹治水可否在那里與四岳部族發生交集,而是片面強調姜姓族氏初居關中西部,忽略四岳東遷的史實,自然不能動搖傳統說法。申、呂作為四岳之后,可能長期居于晉南,后來申國為了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則遷往與呂國僅一河之隔的陜西安塞以北一帶。周宣王時,申、呂又被遷至河南南陽地區,承擔“南土是保”?的政治使命。
不過,姜戎氏與申、呂并不同地,而是遙居關中,東西懸隔。《左傳》襄公十四年,晉國范宣子對駒支說:“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是說姜戎先祖“吾離”居于瓜州,因受秦人迫逐,才歸附晉惠公,東遷晉南。杜預釋瓜州在敦煌(即今甘肅敦煌),對此學者多有懷疑。因為瓜州若在敦煌,則與當時秦都雍城(今陜西鳳翔)相距三千余里,真可謂風馬牛不相及,秦人何以迫逐姜戎?姜戎遭受迫逐何以不是西去而是東來?這都是難以解釋的問題。顧頡剛先生考證說:“四岳所在當即瓜州所在,部族固容有遷徙,要之必仍在關中、秦嶺一帶。”[13]50顧氏以為四岳即瓜州所在不可遽信,但他說瓜州位居關中、秦嶺一帶,頗得學者贊同。考古學上把陜甘地區的寺洼文化、劉家文化等看作姜戎文化,即以此故。
《左傳》襄公十四年,姜戎氏首領戎子駒支對范宣子說:“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春秋中期,由于秦穆公稱霸西戎,迫逐姜戎,故被晉惠公誘至晉之南鄙。此前姜戎氏世居瓜州,可能在關中一帶。姜戎氏不與四岳其他后裔齊、許、申、呂等國相提并稱,不僅因為地域上相隔遙遠,也與其未曾冊封立國有關,故自稱“諸戎”。姜戎氏發展比較滯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不可能與周王室發生婚媾關系。有學者認為姜戎氏又稱“申戎”,即平王所奔“西申”[1]573-574,與史實不符。
姜戎同為四岳裔氏,為何遠離四岳立國之地?很可能是四岳部族東遷之時,姜戎氏作為四岳原居地的一個分支,并未隨遷。故韋昭稱:“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后也。”《潛夫論·志氏姓》云:“炎帝苗胄四岳。”《世本》也說:“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14]555四岳是炎帝后裔,早先同炎帝一道居于關中。《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炎帝與黃帝是由同一母族分化發展而來的兩個部族,世有婚媾關系。關于姜水所在,《水經注》卷十八《謂水》說:“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14]442一般認為,“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陜西境內渭水上游一帶”[15]48。后來,為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炎帝部族西以氐羌為后援,不斷東進擴張。四岳可能就是隨炎帝東遷來到晉南地區的部落之一。四岳東遷之時,另有別支留居關中,后來被稱為姜氏之戎。
周宣王時,大力扶植秦國打擊西戎勢力,以求西部邊疆的安定與穩固。《史記·秦本紀》說:“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在周王室支持下,不僅為患已久的犬戎(狁)成為重點打擊對象,而且秦人的實力也隨之增強,一步一步向東推進。在這個過程中,姜戎連帶受到迫逐,土地也被侵占,從而與秦人及其支持者周王室之間產生尖銳矛盾,進而升級為武裝沖突。千畝之戰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在千畝之戰前后,周王朝發起過一連串的伐戎戰爭,幾無例外都慘遭失敗。據《后漢書·西羌傳》所引古本《竹書紀年》載,宣王三十一年,征伐寧夏固原一帶的“太原戎”(亦即狁),三十六年征伐中條山一帶的“條戎奔戎”,三十八年征伐襄汾、曲沃一帶的“北戎”,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均以失敗告終。幽王三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此役不僅周師嚴重受挫,連軍隊主帥也戰死沙場。可見宣幽時期的伐戎行動,地不分東西,戰無論大小,王師屢遭敗北,無功而返。
在諸多伐戎戰爭中,千畝之戰的失敗后果最為嚴重。一是周王室在伐戎戰略上被迫轉入防御,整體上處于守勢。千畝之戰是姜戎主動發起的軍事進攻,否則戰事不會在京郊進行。即使后來周軍偶有出擊,戰斗力也不強,乃至軍隊主帥性命不保。周室軍事力量因連年戰爭受到嚴重削弱,連保衛鎬京的使命也難于承擔了。二是破壞了廣泛意義上的姬姜聯盟。姜戎氏雖然發展滯后,畢竟還是姜姓部族的一支。姬姜聯盟長期作為維持西周國家政權的政治基礎,至此出現不可修復的裂痕。其后申、呂集團的反叛,與此不無關系。三是戰事在京郊失敗,徹底暴露了西周王朝不堪一擊的虛弱面目。此役王師背靠都城,后援強大,又有晉師配合,本來占有絕對優勢,結果卻出人意料,竟是王師敗績。這就極大地助長了犬戎長期覬覦宗周的政治野心。十多年后,申、繒聯合犬戎攻破鎬京,赫赫宗周終于一朝覆亡。
注釋
①參見(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49 頁;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2 頁。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版,第136-137 頁。持此說者另有許兆昌、劉濤:《周代“千畝”地望考》,《古代文明》2014年第4 期;劉成群:《清華簡與古史甄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 頁。③此觀點參見:裘錫圭:《關于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裘錫圭學術文集》(3),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王占奎:《周宣王紀年與晉獻侯墓考辨》,《中國文物報》1996年7月7日;沈長云:《關于千畝之戰的幾個問題》,《周秦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謝乃和、付瑞珣:《從清華簡〈系年〉看“千畝之戰”及相關問題》,《學術交流》2015年第7 期;劉光勝:《從“殷質”到“周文”:商周籍田禮再考察》,《江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2 期。④《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語。王國維以為臣瓚是《竹書紀年》的整理者之一,此語當本紀年。參見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1 頁。⑤參見裘錫圭:《晉侯蘇鐘筆談》,《裘錫圭學術文集》(3),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李伯謙:《晉侯蘇鐘的年代問題》,《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⑥此句出自《左傳》桓公二年孔疏。⑦按宋劉恕《通鑒外紀》將伐條戎奔戎列為宣王三十八年,千畝之戰列為三十九年。《今本竹書紀年》略同。伐條與伐姜戎在時間上已無間隔,但千畝之戰仍是在伐條之后。⑧《詩·小雅·祈父》正義引。⑨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說:“界休有界山,有綿上聚。有千畝聚,在縣南。”司馬彪略晚于杜預,基本上為同時代人。說明當時介休有千畝地名為人熟知,故杜預以此作為千畝之戰的地點。⑩《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參見(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七《左傳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見《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金履祥:《通鑒前編》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二《釋地余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見《詩·大雅·崧高》。?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后漢書·西羌傳》引《竹書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