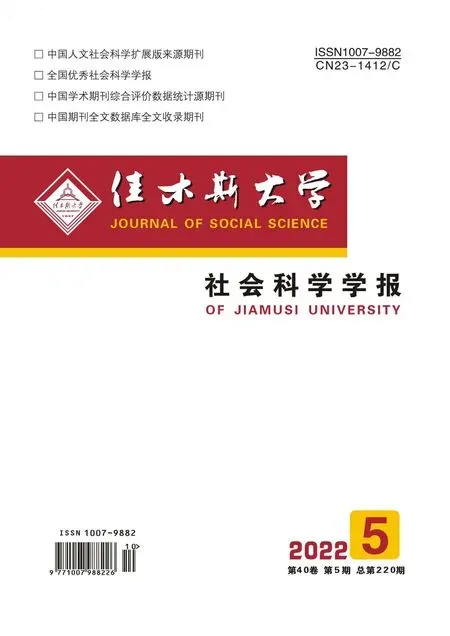網絡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政治話語分析
向春琳,李靈通,姜 燕
(重慶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初等教育學院,重慶 404047)
伴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全球性鋪開,以計算機信息技術或者說以“網絡”為標識的社會變革,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物質與精神領域的一切活動。“網絡”與“文學”的嫁接,實現了文學的大眾化的同時也因之裹挾著巨量的價值觀念,進而打破了傳統文學精英主義的幻夢。傳統文學的審美特性毋庸置疑,而意識形態又是文學無法回避而又爭議不斷的內在關聯,因而傳統上對于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的討論從未間斷。網絡文學既然作為文學形態的創新樣式,那么這些豐富的理論資源便為“網絡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時代出場提供了深厚的思想養分。這些價值觀念和養分正是“網絡文學”“審美”與“意識形態”彼此粘合的榫口,激發著所有網絡文學“寫手”的豪情。以政治話語范式分析,可以探尋到“網絡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深處,其作為文學意識的時代延展,依舊懷抱著對文學政治倫理“應該如此”的寄望與對生活現實“就是如此”的調侃、抱怨與顛覆,在理想視野與現實視野的張力場域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文學與意識形態的政治關聯分合往復
人類認知社會的概念模式,可以套用“文學不應束縛于某種既定概念,它是一種既恒定持久又不斷超越自身舊形式的實踐”[1]的界定模式。當然,對任何一個概念進行界定,都是極為艱苦的;與“文學”界定類同,“政治”也是一個宏大的場景概念。它們都伴隨著人類歷史實踐的發生而發生、發展而發展。在屬性的角度,它們是同一的;在具體的共時層面,它們又是異樣的。
(一)人類元初本能的無意識形態表達
按照馬克思社會形態的劃分,人類元初階段以原始社會為節點。直到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的一切實踐活動,仍然還是出于本能的需求。正如恩格斯指出“在氏族制度內部,權利和義務沒有任何差別;參與公共事務,實行血族復仇或為此接受贖罪,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這種問題……正如吃飯、睡覺、打獵究竟是權利還是義務的問題一樣荒謬。”[2]所以,在此時期談論“文學”“政治”這種上層建筑領域的概念,便是無稽之談。然而,從發生學的角度考量,任何事物的產生絕不是癡人說夢、空穴來風的。它們必然又是在歷時的歲月積累之中,點滴聚成的。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提醒到“當我們錯誤地以為未開化人只是受機體需要或經濟需要支配時,我們卻未曾想到他們也可以向我們提出同樣的指責,而且在他們看來,他們自己的求知欲似乎比我們的求知欲更為均衡。”[3]這說明作為“本能”的意識,是人類產生諸如“文學”“政治”等語詞概念的必要條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沒有某個術語概念未必就等于沒有相應的認識和意識。傳統上論及“文學”的起源問題,多以相傳于黃帝時代的《彈歌》作為佐證,所謂“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其鮮活生動的勞動場景,即奠定了“勞動說”作為“文學”起源的基礎。“勞動說”是一個契合人類發展規律、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公理性前提,甚至可以說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生產均是“勞動”所創造的。那么以此推論,“文學”與“政治”便具有了先天的融合特質,這也是符合邏輯與推理的,或者更加準確地講,“勞動”孕育了人類的“文學性”與“政治性”。按照成熟社會的理解范式,原始社會及其以前的時代,還沒有真正的“文學”或者“政治”出現。然而,恰如維科所言“在世界的童年時期,人們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詩人。”[4]這便預示著伴隨人類世界的成長,人們開始隱藏“詩人”的元身份,逐漸向世俗和體制轉變。也是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人們開始有意識地發現“詩人”的文學底色依舊在心靈深處閃動。
(二)成熟社會驅動的政治意識形態分合
“應該承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學界極為熟悉,以至于到了后來,一些學者認為無話可說。”[5]95如果說在人類的原始階段,對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無話可說,這主要是因為人類的生產實踐還不具備產生復雜術語概念的能力。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凡是用語言表現出來的各種精神生產(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都不過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產物。”[6]那么,進入生產力相對發達的成熟社會,如果依舊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無話可說,那么則暴露出一些歷史積襲的問題。“我們能理解這代人的經歷,他們過去都曾直接或間接地論及這個話題,但在當時除了重復流行話語,好像沒有自己的話要說;不僅如此,他們中的很多人還因為堅持己見,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場,背負了不該承受的歷史重負,像胡風等人。”[5]95也正因如此,回觀中國百年文學史路甚至追溯更遠,對于“文學”與“政治”關系問題的討論,是一個從與“政治”粘合到逃離再到親密接觸的往復分合狀態,即圍繞“文學”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之螺旋問題。盡管“逃離”與“粘合”處于對立關系之中,但二者卻不是涇渭分明的矛盾關系。它們的出場與轉換,根源于社會對“政治”的理論認知與實踐作為。“不是一切政治都不利于文學的發展,而是惡的政治對于文學的迫壓才不利于文學的發展”[5]95,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政治與文學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文學作為對美好生活的想象與政治作為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它們的遇合,正是文學與政治結合的基礎。”[7]110而所謂“惡的政治”當然有在政治哲學層面反人類價值觀的追尋,同時也是處于中觀、微觀層面的不夠全面的“一葉障目”的理解與表征。按照劉鋒杰先生的觀點,“政治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是最高層面的政治理念;第二個是中間層面的國家政治制度;第三個層面是方針及政策”[7]109。進而,劉先生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聯,不應是制度層面、政策層面的,而應是理念層面的”[7]110。因此,可以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聯不應僅僅局限在某一個單獨的層面,尤其從網絡文學的歷史實踐來看,“文學”正在滲入“政治”的方方面面。
二、網絡文學對政治想象的持守與超越
“文學不應束縛于某種既定概念,它是一種既恒定持久又不斷超越自身舊形式的實踐。”[1]不獨“文學”,理論上而言人類認知社會的一切概念,都無法擺脫這種內在矛盾的張力。也正是因為矛盾張力的存在,人類才能夠不斷穩固、深化與超越自身知識論的局限,不斷提出與闡釋新的概念。
“網絡文學”理所應當也屬于一種既恒定持久又不斷超越自身舊形式的實踐,由此“網絡文學”便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催生的必然結果,是在特定的社會與歷史階段,生產力升級的必然產物。“網絡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語詞組合作為研究對象,正是社會歷時與共時發展的交織與疊合的時代表達。網絡文學因為技術媒介的加持,從而實現了網絡文學在主體、受體、載體多層面的多向超越;同時,技術媒介的平權特質,也讓網絡文學承載了每一個人的審美期待。進而,其技術話語單元的開放性又為主體、受體逃避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力場域,提供了云端造夢的工場。調侃、不滿、宣泄、解構與顛覆的后現代情緒,又因為對所謂理想政治的期待失落而變本加厲,從而使得網絡文學如同一個巨大的容器,承載著理想政治意識與現實政治意識互相撕扯的意識形態張力。
(一)文學審美想象的政治初衷
孫紹振、毛丹武(1999)曾經生動而深刻地論及“在人類童年的家園中,藝術、審美與政治、意識形態是青梅竹馬的少時玩伴,甜蜜的歲月將成為人們未來長久的回憶——對人類偉大童年的懷念和對未來無盡的渴望——對真、善、美統一的理想的審美境界的向往,并且成為對于人類新的社會現實的對照。”[8]可見,對于“真、善、美統一的理想的審美境界的向往”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也正因如此,“文學”“審美”“政治”“意識形態”這些精神領域的術語概念,才能在人類社會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保持顯性與隱性的關聯。也正是因為“審美”作為統括“真、善、美”三者的基點,在實然、應然、可然的世界中身居核心地位,這才可以使得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三者拼合,進而證明“文學”與“政治”的元價值觀的一致取向。一般說來,從直覺的樸素認知上看,將“審美”與“文學”結合,無人置喙,但是將“審美”作為“文學”與“政治”的共有屬性,也許可能會招致某些純粹政治意識的反對。其實“文學因其獨特的審美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自古以來就承擔著諸多的倫理道德教化甚或統治意識形態的社會功能。”[9]盡管所論依舊對“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態度不夠干脆果斷,但是對“文學”本身的“審美”特質則給與堅決的肯定,這也是“文學”成其為所是的本因。也許那些反感或者逃避“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聯并進而拒絕后兩者染指“審美”境界的原因在于:一是對“政治”解讀的偏頗與狹隘所致;二是對“政治”的某些表面背離“文學”的表現,讓人迷惑不解、不敢問津。這兩個原因的本質,正好映照了劉鋒杰先生對“政治理想、國家制度、方針及政策”三個層面的解讀。“文學”審美觀的追求與“政治”在最高層面的“政治理想”是保持一致的,也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才能證明與認同“文學”與“政治”的初衷是一致的。落至到國家制度尤其是方針及政策層面,由于具體的政治實踐與意識可能扭曲了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就使得“文學”不敢逾越“政治”的雷池。因此,也就使得“意識形態”等這類詞匯,帶有了極強的政治色彩而遠離了文學的審美色彩。
(二)網絡賦能文學的群體超越
“網絡文學是以網絡為媒體進行傳播和出版的文學還是上網的人寫的作品,目前大多數的意見傾向于后者。”[10]“上網的人寫的作品”一語道破網絡文學在主體、受體與載體上的多向多元超越。時隔近20年,上句對于網絡文學的這一斷言,依舊具有很強的概括力。并且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技術話語單元手段的多端多元,網絡文學的形式表征早已越出傳統的文本載體。網絡媒介技術的加持,打破了傳統上學科精英的話語統治,人人都有了發言的權力,幾乎可以隨時隨地可以表達自我的政治意志和話語。網絡文學憑借技術媒介的平權特質,使得每一個人可以自由地跨越“文學”與“政治”的曖昧邊界,就其實質而言是因為身處的國家與社會的和諧,是共時社會政治環境的清明、公正所帶來的政治福利。從文學創作的實際動向上,也可以看到從前那種“政治化文學”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書寫改革開放洪流巨制的文學筆墨接連付梓。良性的“文學+政治”開始回蘇、壯大,“潤物無聲”而又“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與此同時,還要看到隨著經濟社會與網絡信息社會的高速發展,全球經濟化一體化的步步緊逼,網絡文學也成了一個裹挾各種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巨大染缸。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三者疊加的復雜語境,網絡文學也表現出書寫的隨意涂鴉,使得泥沙俱下。因此,需要清醒地意識到“不是一切經濟活動都不利于文學的發展,而是膨脹的經濟力量對于文學的迫壓才不利于文學的發展。”[5]96尤其注意的是,“上網的人”是一個外延極度雜糅、云量的所指概念,網絡文學的大眾化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其自身的審美品格。特別是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迎合大眾文化口味的膚淺、粗鄙、暴力、媚俗的網絡文學話語充斥了人們的視覺、聽覺與知覺和智覺。提倡“文學+政治”是以文學真善美終極目標與最高的政治理想相一致為前提,而不是以此為借口在“文學去政治化”的歧路上橫沖直撞,而走向真、善、美價值取向的對立。“文學”與“政治”的分合本身不是問題,或者說任何一種非政治性的純文學寫作也是不存在的。而如果一種所謂非政治性的純文學寫作是以“個性寫作”“私人化寫作”“美女寫作”“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等形形色色的所謂“去政治化”寫作為伸張,則這種純文學寫作應該并且必須被閹割和去勢的。網絡賦能文學的群體超越,不是肆無忌憚地書寫人類本能的欲望,而是通過藝術化的“處理”找到本能與文明的平衡點。
三、結語
網絡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是網絡媒體技術加持,實現文學大眾化的時代產物。人類本能的政治意識形態表達,是文學發動的原始基因。“文學”與“政治”在“文學政治化”“文學去政治化”“文學再政治化”的螺旋回路上博弈撕扯,其本質是對于“審美”“意識形態”價值觀念自我立場的伸張。從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最高意志而言,人類社會歷時進程的一切觀念都以其為具體實踐的公理性前提。然而,伴隨生產力的迭代升級,生產關系的日益復雜,某些現實政治意識疏離了理想政治意識的初衷。網民的不滿、抱怨情緒需要找到一個宣泄的出口,文學尤其是目下的網絡文學為其提供了便利的物質平臺。于是,一場“上網的人的寫作”的大眾文學化創造,在這個時代喧囂塵上,愈演愈烈。循著政治話語分析范式,對于“文學”“政治”“審美”“意識形態”等相關的術語概念進行了梳理,發現了“文學”與“政治”始終具有不可切斷的聯系,同時指出網絡文學的出場具有正負雙向的實際功用。網絡媒介技術的平權特質,使得文學的創作主體、受體甚至載體實現了虛擬空間的同一。這就提醒人們,網絡文學整體審美品格的優劣,直接影響著國家、社會和個人。要實現網絡文學的群體超越,重點在對自我審美境界的提高,關鍵在于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向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