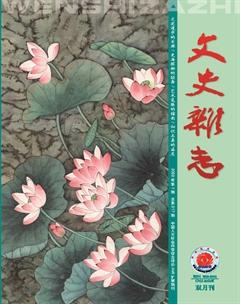王羲之與四川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字逸少,瑯琊臨沂(今山東省臨沂市)人,東晉大臣、書法家,有“書圣”之稱,歷任秘書郎、江州刺史、會稽太守,累遷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他撰寫的《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其兼善隸、草、楷、行書法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在書法史上,與鐘繇并稱“鐘王”,與其子王獻之合稱“二王”。他是中國最知名的書法家之一,是中國古代一個著名的文化符號。
根據各種史料文獻,我們知道王羲之一生中從未來過蜀地,那么,他與四川有什么關系呢?這是因為王羲之寫有一部流傳后世的叢帖《十七帖》。《十七帖》是因為卷首《郗司馬帖》開篇即是“十七”(“十七日先書”)而得名。叢帖其實是29件書信尺牘,其中《成都帖》等15件信札與四川有關。這15件信札是王羲之寫給當時益州刺史周撫的。在王羲之所處的由西晉皇族司馬睿南遷后建立起來的東晉(公元317—420年)年代,益州的州治所一度設于蜀郡成都,即今天的成都。在與王羲之通信來往期間,周撫是巴蜀地區(當然不限于今川渝地區,還包括云南、貴州的部分地區)最高長官。
周撫(?—365),字道和,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南縣)人,晉中興名將周訪之子。周訪死后,周撫承襲世職,曾隨大司馬桓溫征討蜀郡,平定叛亂,后擔任益州刺史,鎮守巴蜀30年(其中駐守成都達18年之久)。東晉時期,益州(今成都)領10郡,州治所在成都縣(今成都市區,一度也曾設于今重慶奉節)。據《東西晉演義》載,周撫鎮蜀期間“甚有威惠,民咸德之”。東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六月,周撫去世,晉廷任命周撫之子周楚為益州刺史。東晉梁州刺史司馬勛認為無人能與之抗衡,遂起兵反叛,圖謀割據巴蜀,被桓溫派大軍擊敗。
王羲之出身于名門望族的瑯琊王氏。瑯琊王氏在東晉時代是一面顯赫的旗幟,與陳郡謝氏(謝安為代表)并稱“王謝”。“舊時王謝堂前燕”指的就是王、謝兩家。在周撫任職益州刺史之前,曾多次得到瑯琊王氏的幫助。永昌元年(公元322年),開國功臣、王羲之的伯父王敦叛亂晉室(史稱王敦之亂),周撫是其核心部下。太寧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失敗,周撫等逃入西陽蠻中,由于依靠與瑯琊王氏的特殊關系而免罪。太寧三年朝廷大赦。咸和初(公元326年),周撫又得到王羲之另一位伯父、東晉第一任宰相王導的啟用,得以重返官場,最終成為鎮守益州的封疆大吏。
大概正是這段與瑯琊王氏頻繁接觸時間,周撫與王羲之建立了足夠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并未因周撫入蜀而中斷,而是變成王羲之15件信札的問候與牽掛。
王羲之寫給周撫的15件信札(輯錄于《十七帖》),71行,共597字。據陳友山研究,它們分別是:《成都帖》《講堂帖》《嚴君平帖》《譙周帖》《鹽井帖》《邛竹杖帖》《天鼠膏帖》《旃罽帖》《藥草帖》《青李帖》《胡桃帖》《清晏帖》《七十帖》《蜀都帖》和《兒女帖》等共15帖。[1]這15件信札中有一部分涉及當時四川特產,如邛竹杖、天鼠膏等。由于這一部分目前缺乏系統研究,研究成果甚少,故不在本文中討論。本文內容僅涉及三個部分:王羲之與四川名人、王羲之與四川風物、王羲之對益州的向往。
《十七帖》是書圣王羲之傳世草書作品的代表作,用筆自由奔放,瀟灑不羈,被歷代書家奉為書法史上草書經典,被譽為“書中龍”(宋代書法家、書學理論家黃伯思語),歷來奉為草書圭臬。唐太宗、唐代書論家張彥遠、宋代哲學家朱熹等,都曾對其作出高度評價。[2]
一、四川歷史名人
據統計,《十七帖》中提到的四川歷史名人均出現于《嚴君平帖》《譙周帖》兩帖之中,他們分別是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云(揚雄)、譙周、譙秀等五人。[3]那么,這五個蜀中名人有什么特殊之處,會引起千里之外的王羲之的如此關注呢?
(一)《嚴君平帖》
王羲之《嚴君平帖》,草書,紙本,12行,14字。原文如下:“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云,皆有后否?”此帖意思一目了然,王羲之向周撫打聽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云(揚雄)等三位是不是都有后人。
1.嚴君平
嚴君平(公元前87—公元6或7),漢代著名的思想家,西漢蜀郡(成都)人,名遵。他曾隱居于今四川省蓬溪縣金魚山,賣卜于郫縣、成都、彭州、邛崍、廣漢、綿竹等地,50歲后歸隱而著述、授徒于郫縣平樂山,95歲去世后埋葬于平樂山。他誦讀老、莊思想,并以之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根據。隱居于市,榮辱不驚,正是嚴君平受人敬仰之所在,也是王羲之所欲效法的。史稱“著《指歸》,為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華陽國志》卷十《先賢志》)。嚴君平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尤其合于王羲之晚年的心境,這可能是王羲之將嚴君平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嚴君平著有《老子指歸》《道德指歸論》等,是西漢大隱士,揚雄的啟蒙老師和中華哲學家、蜀學奠基人。
今成都邛崍、彭州、郫都等地都辟有嚴君平故里。成都人民公園旁的君平街即是為紀念嚴君平而命名的街道。
2.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字長卿,生于西漢巴郡安漢縣(今四川蓬安),成長于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漢代著名文學家。他初入梁孝王劉武幕府,于梁孝王死后回蜀。其間與才女卓文君私奔,留下千古美談。漢武帝后來看到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贊賞,召其入宮。司馬相如由此成為宮廷辭賦家。他曾通使邛、笮有功,晚年退居于茂陵(今陜西興平境)。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代表作家,其賦大都描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鋪張揚厲,極富文采,是漢、魏以后文人賦體的模仿對象。他是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杰出的代表,因其文學影響,被認為是與司馬遷齊名的重要作家。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言:“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
司馬相如是第二批十大四川歷史名人之一。四川蓬安縣建有司馬相如故里。今天成都的琴臺路、邛崍的文君井等都與司馬相如有關。他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是中國情愛經典之一。
3.揚雄
揚雄,字子云(前53—公元18),漢代著名學者、文學家,漢代蜀郡郫縣(今成都郫都區)人,一說蜀人或綿竹人或邛崍人。揚雄少好學,長于辭賦,其大賦多仿效司馬相如。揚雄博通群籍,多識古文奇字,為一代小學宗師,著述極豐,“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蒼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漢書·揚雄傳》)他載于《法言》的《學行》一篇(《法言》共13篇)約1500字,是比戰國時期成書的《學記》(其流行于東漢以后)流行得更早的中國教育理論著作;又有《方言》《法言》《太玄》《蜀王本紀》等傳世,其中僅1333字的《蜀王本紀》是最早記載古代巴蜀歷史的史書。在劉禹錫著名的《陋室銘》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為揚雄。揚雄是歷代京都大賦之祖,是迄今為止在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四川思想家,被后人尊稱為西道孔子、漢代孔子,是漢代儒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揚雄與李冰、武則天、李白一樣,是第一批十大四川歷史名人之一。今四川有其紀念地郫縣(成都郫都區)揚雄墓、綿陽西山子云亭、樂山犍為子云山等。
揚雄是否有后人,歷來受人關注,筆者曾經撰有一文《揚無咎是揚雄的后代嗎?》,認為他是有后人的。[4]
(二)《譙周帖》
《譙周帖》,草書,紙本,13行,27字。原文如下:“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副此志?令人依依,足下具示。”文中“孫”與“高”字之間有一字殘損,以符號□表示。據專家論證,此殘損字很可能是“名秀”二字。此帖翻成今天的大白話就是:聽說譙周有個孫子叫譙秀,他志行高潔,隱居不仕,不知他現在何處?是否真如人們盛稱的那樣遠離世事,嘯傲山林?真是令人向往之,詳情望告之。
1.譙周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西充槐樹鎮)人,蜀漢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被稱為“蜀中孔子”,《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老師。《三國志》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并稱為“前四史”,在史學界有極高地位。炎興元年(公元263年),魏國三路伐蜀,譙周因勸蜀主劉禪投降,被封為陽城亭侯。譙周高瞻遠矚,在關鍵時刻勸后主劉禪出降有“全國之功”。炎興元年蜀漢滅亡之時,蜀漢境內編戶之民總共不過百萬左右,而所養的軍隊卻有十萬以上,如此沉重的負擔讓蜀漢的百姓難以忍受。譙周的勸降既避免了戰爭與流血,又有助于國家的統一。與同時代的陳壽、常璩一樣,譙周是成就很大的歷史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天文學(世人公認的巴蜀文化“天數在蜀”對中國天文學有重大影響)等方面均有貢獻。他著述頗豐,其所著《蜀本紀》《三巴記》等,記述了巴蜀地區的史地掌故,對后來四川地方史志的修纂有極大影響。
如今,在四川南充西山萬卷樓景區內,建有譙公祠和譙周墓。譙公祠是南充名勝之地。這是四川人應該特別記住的三國時期的蜀漢名臣。
2.譙秀
譙秀是蜀中名儒譙周之孫,字元彥。西晉末,知世將大亂,他預絕人事,內外宗親概不相見;成漢開國皇帝李雄據蜀,束帛安車征召,甚至李雄親自來請,皆不應。這在歷史上是著名的“皇帝微服訪譙秀”的故事。他經常戴著鹿皮帽子,隱逸耕種于山林之間。東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字子元,東晉詩人和散文家)于晉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率師平定在蜀的李雄,居留成都三十日。桓溫知道譙秀有濟世安民的才能,又很有聲望,便向穆帝遞了一篇《薦譙秀表》,請求征召譙秀來朝做官。朝廷遣使四時慰問他,故有“桓溫上表征賢良”之歷史故事。范賁、蕭敬相繼作亂時。他避難宕渠(治今四川渠縣東北),鄉里從者百數。其卒年九十余。
譙秀在后世享有盛名。李商隱曾作《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行到巴西覓譙秀,巴西唯是有寒蕪。”李商隱是晚唐著名詩人,和杜牧合稱“小李杜”。
益州刺史周撫回復王羲之的回信早已不存,人們無法知曉他是怎么回復王羲之的。然而,人們從王羲之《嚴君平帖》《譙周帖》兩帖已經知道,嚴君平之高蹈,司馬相如之文采風流,揚子云之大隱于市,譙周之學問人品,譙秀之隱逸高潔,在當時(東晉)就已經聞名于神州,并為后世之楷模;否則,作為東晉名人的王羲之不可能專門給周撫寫信,問及他們或他們后人的情況。
在以上兩帖中,王羲之書寫的“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云”(揚雄)“譙周”,均是史上第一次由名家書寫其人而流傳至今的墨寶真跡。
二、四川風物古跡
據統計,王羲之《十七帖》涉及四川風物古跡者出現于《成都城池帖》《講堂帖》《鹽井帖》三帖之中。[5]這些四川風物古跡分別是秦代的成都城池、蜀中的漢代學堂、漢代壁畫以及戰國末期的四川鹽井等。那么,這幾處蜀地的舊跡風物在1600多年前曾有什么特殊之處,以至引起“萬里之外”的書圣王羲之如此關注,專門寫信請周撫回復呢?
(一)《成都城池帖》
《成都城池帖》,草書,紙本,5行,48字。原文如下:“往在都,見諸葛颙,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具示,為欲廣異聞。”大意是,以前在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時,見到諸葛亮哥哥諸葛瑾的重孫諸葛颙(一說顯,草書“颙”“顯”互通),曾問起蜀中的事情。他說成都的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代司馬錯修建的,令人浮想聯翩,是否是真的?請具體告知,以增加見聞。
此處的成都城池指的是秦代成都城池,涉及巴蜀歷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即秦滅巴蜀。
王羲之信中所談到的司馬錯是戰國中后期秦國名將。他是主張伐蜀的秦國大臣,“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民,不傷眾而彼服焉”(《史記·張儀列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令秦國大將司馬錯、張儀從石牛道(后稱金牛道)入蜀,冬十月滅蜀,接著滅巴,為秦國統一中國開辟疆土。秦滅蜀后,為了鞏固其在蜀的統治,從關中等地大量移民入蜀。由于人多城少,5年后,即公元前311年,在成都原北少城的南面新筑秦城,在成都西面加筑郫邑城,南面加筑臨邛城。郫邑城在杜宇建都的“杜鵑城”,在今郫都區城北;臨邛城在今邛崍市偏西北。這樣,兩城與成都同在縱橫200里間,構成品字形,有鼎足之勢,互為犄角,以利防守。成都城池的營建工程經歷了歲月的考驗,直到600多年后的公元347年,東晉大將桓溫消滅蜀地的成漢政權后,桓溫屬下的部將還說能看到司馬錯修建的城墻,可見當年修建的城墻非常堅固。
需要說明的是,成都城的屋宇樓觀及城市布局,其實主要是由張若所奠定。秦滅蜀后,張若是第一任秦國蜀郡太守(再后,張若調任秦國黔中郡守,水利專家李冰接替其職,遂成都江堰),主持了秦移民入蜀的安置活動。張若將秦地的城市設計思路帶到了蜀郡,又不拘泥于秦法,而是虛心向當地賢達求教,依地勢風水筑就了成都城。不過,由于司馬錯是滅蜀大計的首倡者和實行者,功績卓著,所以后人講述這段秦滅巴蜀的歷史時,多提司馬錯。王羲之可能也不例外。
(二)《講堂帖》
《講堂帖》,草書,紙本,16行,49字。原文如下:“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因欲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大意是說,聽聞益州那里漢代修建的講堂還在,講堂是漢代哪一位皇帝建立的?聽說講堂里畫三皇五帝以來事跡應有盡有,畫又精妙,非常值得一看。如果成都有能畫之人,我想請他臨摹,不知能否辦到?確切信息,請詳細告知。
這里主要談到的是蜀中漢代講堂與漢代壁畫。
1.漢代講堂
王羲之信札中書寫的“講堂”二字,專指蜀中漢代學堂。蜀中地區在西漢景帝以前,文化尚欠發達。自文翁為蜀郡太守之后,讀書之風才開始盛行。
文翁是于漢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末年被朝廷任命為蜀郡太守的。《華陽國志·蜀志》載:“文翁為蜀守……翁乃立學”;“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成都)城南”。“精舍”即校舍。由于文翁所辦學校的“講堂”是用石料建造,所以稱為“石室”。建石室是由于學校有藏書,為防火故以石料筑室。由于文翁修蜀中講堂辦學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以后各個朝代都在文翁“石室”成都舊址上建立學校,綿延不斷2000多年。現在的成都石室中學就位于原文翁辦學的舊址。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罕見,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數。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成都城坊古跡考》有對文翁石室的考證。
漢代文翁興政崇教首創地方官辦學校,是中國教育的一件盛事。它開啟了四川公立教育模式,成為蜀學的開端之一,從而奠定了此后巴蜀社會經濟以及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在全國長達1400余年(從漢初至宋末)先進地位的堅實基礎(不算四川多災多難的元明清三個朝代)。
文翁是第二批十大四川歷史名人之一。
2.漢代壁畫
東漢獻帝劉協(東漢末代皇帝,公元189年—220年在位)時,益州刺史命人在成都學堂(成都府學)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壁間(墻壁上)。劉漢王朝極重視繪畫的教化作用,因此,這些壁畫都有十分明顯的政治教化目的,或書寫古圣先賢的功績,或表彰功臣的才能,或褒揚清明官吏的政績。在當時全國州郡中,這類經史內容的壁畫,益州最多。成都學堂的壁畫后來非常有名,《歷代名畫記》的作者、唐代張彥遠甚至將其與漢明帝宮殿壁畫并列,極贊繪畫的重大意義:“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都學堂,義存勸誡之道。”[6]遺憾的是,成都學堂的這些壁畫早已全部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了。在四川,唯一僅存的漢代壁畫是2002年才發現的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的《荊氏宴飲圖》。[7]
依周撫之權力,為好友王羲之摹取這些壁畫,應是小事一樁,但現在已經無考了。不過,王羲之的《講堂帖》卻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即蜀中的繪畫并不僅僅如平常所說的是在唐宋時期才開始赫赫有名的,而是早在幾百年前的東晉就已名聲在外了。書圣王羲之以“精妙”二字來描繪東晉時代蜀地存在的漢代壁畫,是四川漢代繪畫發展的重要證據,對于今天研究成都繪畫史、成都文化史乃至巴蜀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鹽井帖》
《鹽井帖》,草書,紙本,13行,20字,原文如下:“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大意是王羲之向周撫詢問,益州蜀地是否真的有鹽井和火井?是你親眼所見嗎?為拓寬我的見聞,請具體告知。
王羲之這里主要說是的四川鹽井。鹽被人稱其為“百味之祖”,長期以來都是歷代王朝須臾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四川鹽井產的鹽叫井鹽,戰國末期就有名了。《華陽國志·蜀志》載:“(李冰)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于是有養生之饒也。”廣都縣治位于今成都市雙流區境,據《四川文化簡史》載,廣都鹽井的具體位置,大致在今成都龍泉山脈南側,即今成都天府新區籍田鎮與眉山仁壽縣交界的高家場。《華陽國志》關于李冰開鑿廣都鹽井的記載,是四川也是全國有文獻以來最早的官方開鑿鹽井的記錄。秦代,四川開鹽井的有三個縣,漢代擴大到十余州縣,包括自貢、綿陽等地。蜀地所生產的井鹽不僅供蜀地的人食用,還遠銷到蜀地之外。李冰開鑿的大口淺井,結束了巴蜀鹽業生產的原始狀況,揭開了中國井鹽生產的序幕。今天,人們還能夠從成都地區出土的漢代畫像磚《鹽場》中見到漢代四川井鹽生產的盛況。
火井就是現在所說的天然氣井,漢代就有,古代用于煮鹽。西晉張華《博物志》卷二記“臨邛(今邛崍市)”火井一所“煮鹽得鹽”;《華陽國志·蜀志》說臨邛縣有火井,“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舊唐書·地理志》言邛州有火井縣(今成都邛崍市西南);《舊唐書·袁天綱列傳》記載:“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該火井即前之火井縣。火井縣于元代廢除。
井鹽生產,特別是以井火煮鹽,是當時別的地區所沒有的,故才有王羲之以帖詢問。
王羲之帖中雖然沒有提到“穿廣都鹽井”的李冰的姓名,但顯然他對李冰之事了如指掌。李冰繼張若擔任第二任秦國蜀郡太守后,在成都修筑了都江堰,培養了一批水利專家,總結出“深淘灘,低作堰”的治水經驗,使成都平原日漸富裕,為當年秦始皇統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在以上兩帖中,王羲之書寫的“蜀中”“成都”“講堂”“鹽井”“火井”,是史上第一次由名家書寫其事而流傳至今的墨寶真跡。
三、對蜀地的向往
王羲之對蜀地的向往,集中體現在他書寫的《蜀都帖》(又名《山川諸奇帖》,原《十七帖》之十三)之中。[8]
《蜀都帖》,草書,紙本,11行,102字,原文如下:“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于彼矣。”
這封信札譯為白話,大意如下:讀了你的來信,信中言說蜀地山川的種種奇勝之處。西漢成都人揚雄的《蜀都賦》、西晉左思《三都賦》中的《蜀都賦》的記述都不甚完備。蜀地山川奇異,讓我覺得唯有到此一游才能意足。如果能夠成行,我會事先告知你,還需要你派人來接我。當然,接的人不需要太多。如果遲誤這一機會,真有當度日如年之感。你鎮守蜀地,以你之功勞,朝廷是不會調動你的,因此我非常希望在你蜀地任上時,能夠來到蜀地,與您一起登汶嶺、峨眉山而歸,這將是我一生中不朽的大事。寫到這里,我的心已飛到你那里了。”
特別說明的是,現在很多書籍均稱《蜀都帖》也稱《游目帖》,或《游目帖》也稱《蜀都帖》,筆者認為這其實有誤。《游目帖》實際是原《十七帖》之二十八的《清晏帖》,帖名是因文中有“何可以不游目”而得名。《蜀都帖》與《游目帖》并非同一件書帖。
從《蜀都帖》可知,王羲之對蜀地的向往之情是因為周撫信中談及蜀地山水之瑰麗而引發的。王羲之感到周撫來信的描述,要比揚雄《蜀都賦》和左太沖《三都賦》之《蜀都賦》描述的還要精彩,從而生發無比向往,希望能夠在周撫駐守巴蜀時,去一次蜀地,登臨汶嶺、峨眉。那么,王羲之信中提到的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是什么文章呢?他想登臨的汶嶺、峨眉如今又在四川的什么地方?
(一)揚雄《蜀都》
揚雄《蜀都》即揚雄著名的《蜀都賦》(揚雄的簡介以上已經介紹)。《蜀都賦》是揚雄的代表作,極盡言辭,以寫成都之壯美秀麗。《蜀都賦》擬物寫形,精于描繪,展現了成都的富庶、蜀中山水的壯美、蜀地人物的靈異,對成都的地理、歷史、風俗、財富、物產等都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鋪陳描寫,有極高的史學價值,是認識、了解、研究漢代成都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揚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后西漢最著名的辭賦家,即所謂“歇馬獨來尋故事,文章兩漢愧揚雄”。該賦后啟張衡之《南都賦》,對西晉左思《三都賦》之《蜀都賦》的創作也有著很大影響。
(二)左太沖《三都》
左太沖,即左思(250?—305?),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山東淄博)人,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自幼其貌不揚卻才華出眾。晉武帝時,其因妹左棻被選入宮,舉家遷居洛陽,任秘書郎。晉惠帝時,他依附權貴賈謐,為文人集團“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員。《三都賦》與《詠史》詩是其代表作。
《三都賦》中的“三都”指三國時期的魏都(今河南洛陽)、吳都(今江蘇南京)和蜀都(今四川成都)。其中《蜀都賦》分為三節:第一節追述蜀都的歷史淵源,第二節描寫蜀都華美的市容,第三節敘寫蜀都商業的繁榮發達,包括地理形勢、山川物產、風土人情、都市建筑、商業經濟、地方巨富、地靈人杰等等,充分顯示出天府之國的無比壯麗與富饒。
左思并非蜀人,亦未曾到過蜀地,但他為了寫作《蜀都賦》,曾親往拜見到過蜀地的張載;又因其博覽群書,故他所寫的蜀地物產財富和民風民俗,頗多可信。[9]
今天,人們還能夠從四川成都郫縣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棺《宴飲百戲圖》中見到當時蜀中貴族們的奢華生活。
(三)汶嶺、峨眉
《蜀都帖》中的汶嶺、峨眉在四川何處呢?
汶嶺。一般認為,汶,即岷江。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志》云:岷江一曰汶江。”循此,汶嶺即今天四川境內的岷山。不過,有專家考證后認為汶嶺應該是今天的青城山,而非岷山。筆者較為認同后一種說法。四川是道教勝地,四川大邑的鶴鳴山是道教發源地,而青城山(正式定名時代為唐代)是道教發祥地。道教最初名為五斗米道,后而天師道,而龍虎宗,而正一道。王羲之是天師道世家,天師道中名人,是道教之祖天師張道陵所創天師道的忠實信徒,其整個家族都是道教信眾。所以王羲之在信中將“汶嶺”放在“峨眉”之前。王羲之可能認為只有朝拜天師道的祖山青城山,才能成為“不朽之盛事”。
至于峨眉山,它既是佛教圣地,在北宋之前還是道教仙山(即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七洞天)。
《蜀都帖》體現了王羲之對四川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的傾慕。
遺憾的是,對蜀地之想,王羲之因為種種原因沒能踐行,但是通過《蜀都帖》,一代書圣王羲之用最有魅力的書法,充分表達了那種心系成都、向往益州的千古深情。從某種程度說,王羲之已在1600多年前為成都作了一次旅游廣告。
此帖中,王羲之書寫的“蜀都”“峨眉”,是史上第一次由名家書寫其地而流傳至今的墨寶真跡。
四、結語
關于王羲之與四川的關系,四川今天的一些學者、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有許多非常精彩的觀點。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杰出研究員查有梁這樣認為:“在《成都城池帖》中,王羲之書寫‘成都’二字,給成都以極大榮譽。”中國書協草書專業委員會委員何開鑫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書圣王羲之書寫十七帖中有關四川部分的書法,與詩圣杜甫入蜀一樣,其文化含量、感染力等等,是一樣的,均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事件。全世界只有一個書圣,王羲之這樣寫四川、寫成都,也只有這一個,它們為四川和成都的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含金量,讓全世界的華人都對四川、對成都向往之。可以說,1600多年前,王羲之就是成都的城市大使、四川的文化大使。”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林圭認為:“王羲之這些帖字,包含了有關四川兩漢魏晉時期的書畫藝術、歷史人物、文化教育、山川風物、城市建設等極為豐富的內容,這些因素引發了王羲之強烈的游蜀愿望。作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王、謝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的想法真實反映了四川在兩晉時期的文化地位和影響力。”
筆者高度認同以上觀點。概括來講,除了這些觀點,筆者認為王羲之與四川的關系最重要的是,在中國書法史上,他為四川奉獻了很多“第一”,就四川歷史人物、山川風物創作出第一次由名家書寫并流傳至今的名家墨寶真跡。在王羲之書寫的這些“第一”的書法作品中,四川歷史名人有“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云”(揚雄)“譙周”等;四川地名有“成都”“蜀都”“峨眉”“蜀中”等;四川風物古跡有“講堂”“鹽井”“火井”。這些“第一”均是獨一無二,舉世無雙,是王羲之留給四川的一筆寶貴財富。
綜上所述,盡管王羲之去世已經1600多年,但由于他無人企及的“書圣”地位,其書法對于全世界的華人甚至外國人,依然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引領力和導向力;因此王羲之與四川的這些種種關系、種種故事,是彌足珍貴的、稀有的、不可復制的。它們不但提升了四川歷史文化在全國乃至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更是我們今天打造四川的文化品牌、挖掘四川文化資源的珍貴的藝術寶庫。
王羲之的這些信札再次證明藝術永恒。歲月如刀,大將軍周撫當年寫給王羲之的回信早已不知去向;在史料中,當年周撫在蜀地功績也僅“甚有威惠,民咸德之”八字的評說。如果不是因為書圣王羲之留下的信札,周撫這位當年叱咤風云的益州刺史恐怕早就被人遺忘。歷史如此,事實也是如此。
注釋:
[1]陳友山:《王右軍致周益州書<成都帖>釋文與解讀》,《文史雜志》2014年第1期。
[2]王興國:《王羲之未了成都情》,《先鋒》2018年第4期。
[3]唐林:《王羲之筆下的四川歷史名人》,《成都日報》2021年7月19日,第10版。
[4]唐林:《揚無咎是揚雄的后代嗎?》,《成都日報》2021年3月29日,第10版。
[5]唐林:《王羲之筆下的蜀地風物》,《成都日報》2021年7月12日,第10版。
[6]顧森:《中國繪畫斷代史·秦漢繪畫》,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7]唐林:《<荊氏宴飲圖>中國南方最早的壁畫》,《成都日報》2020年12月14日,第10版。
[8]唐林:《王羲之——書寫“成都”第一人》,《成都日報》2021年2月8日,第14版。
[9]吳明賢:《揚雄、左思<蜀都賦>比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作者: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歷史研究院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