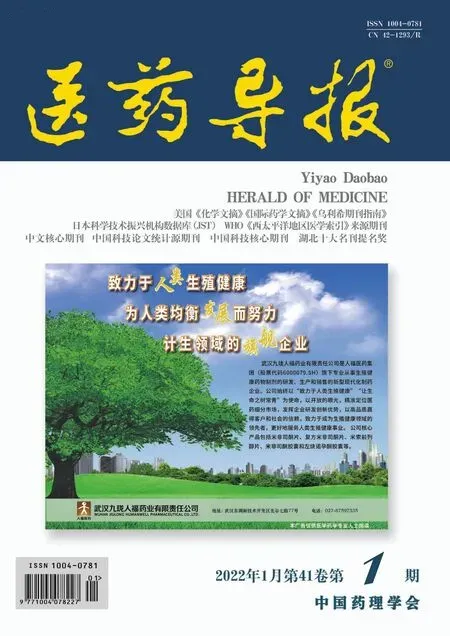抗血管生成療法在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中的應用進展*
辜群利,李暉,陳婧
(1.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中心實驗室,成都 610072;2.成都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成都 610072)
生理條件下,血管生成是一個高度有序、調控緊密的過程,促血管生成因子與抗血管生成因子相互平衡;然而,病理條件下,當平衡傾向于促血管生成,即出現病理性血管生成。缺氧和持續性炎癥刺激病理性血管生成,病理性血管生成是癌癥和各種缺血性和炎癥性疾病的基本特征,也是肝纖維化、肝硬化或肝細胞癌發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病理因素之一[1-3]。本文旨在探討肝纖維化向肝硬化、肝細胞癌進展過程中,病理性血管生成的特點及差異,并進一步比較抗血管生成療法在這三個階段中的應用。
1 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中病理性血管生成的特點及形成過程
持續性炎癥導致肝竇內皮細胞(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LSECs)毛細血管化,阻礙氧從竇腔向肝細胞擴散,血管通透性增加,趨化因子分泌增多,巨噬細胞、單核細胞、血小板和肥大細胞等向炎癥區域募集,從而刺激內皮細胞增殖和移行,新生血管生成,以改善肝組織缺氧[4-5]。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新生血管生成僅僅是一種維持體內平衡的機制,以確保充足的氧氣供應,還是可進一步導致肝組織損傷的致病作用。
肝臟具有獨特的血管供應系統,門靜脈、下腔靜脈與肝動脈相互作用,血管依次分支,直到匯合形成覆蓋肝竇的血管網,肝組織血管生成的特點是從現有血管系統中形成分支,大多數新生血管起源于門靜脈的小分支,傾向于在門靜脈系統和肝靜脈之間建立聯系。使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ECs)增殖和遷移是出芽式血管生成的基本條件,從現有血管中漏出的血漿蛋白與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作為ECs遷移的臨時支架[6];隨后,基質金屬蛋白酶、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尿激酶纖溶酶原激活劑以及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的活性增加,參與降解ECM,協助ECs遷移和擴散,在此過程中,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擴張血管,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VEGF)增加血管通透性,整合素αvβ3和αvβ5調節ECs和ECM的分離或附著,維持ECs與其相鄰區域的聯系。但是,如果生長因子、細胞因子和基質金屬蛋白酶過度表達,ECM成分發生改變,Ⅰ型纖維性膠原替代Ⅳ型生理性膠原,造成肝竇結構扭曲,LSECs窗孔丟失;纖維化組織的沉積導致肝內血流阻力增加,肝實質的氧氣輸送下降,肝細胞有效灌注減少,進一步加重肝組織缺氧;缺氧和毛細血管化的LSECs有助于肝星狀細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的激活,活化的HSCs多位于微小的未發育隔膜的邊緣,而不是較大的橋隔,HSCs可通過產生VEGF、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 1,Ang-1)、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受體2(VEGFR-2)和Tie-2促進新生血管生成。
當肝纖維化進展至肝硬化時,血管結構變得極不規則,僅有少數新生血管能與門靜脈吻合,有的甚至出現盲端,微血管血栓形成,LSECs功能障礙,HSCs活化,被纖維組織包圍的血管導致肝內阻力增高,導致門靜脈高壓(portal hypertension,PHT)逐漸形成,竇性PHT是肝硬化的一個重要特征。NO是正常肝血管張力和門靜脈壓力的重要調節因子,NO的產生隨著流量的增加而增加,VEGF也上調NO水平;肝硬化時,LSECs對血流量增加的反應能力減弱,而NO的產生增加,這種紊亂導致肝硬化患者肝臟微循環血管舒張功能受損,這是引起肝竇性PHT的重要因素;病理性血管生成可加門靜脈系統的血流量,從而增加門靜脈壓力。除肝內血管系統外,腸系膜血管系統也在PHT形成中發揮關鍵作用,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使NO產生過度增加,引起內臟動脈過度擴張,內臟流向肝臟的血量顯著增加,即使隨著門脈側支循環的發展,門靜脈壓力仍然會因內臟流向肝臟的流量增加而增加。PHT導致內臟和全身動脈血管擴張,導致高動力循環綜合征的發展,進而導致臨床嚴重并發癥,包括胃食管靜脈曲張和靜脈曲張出血、門體分流形成的肝性腦病、腹腔積液,肝腎綜合征引起的腎衰竭[7]。
隨著肝硬化逐漸消退,全身血流動力學趨于正常,但內臟血流量增加和肝外病理性血管生成持續存在[8-9];側支循環分流程度降低,但已經形成的血管結構仍保持不變。事實上,肝動脈高壓的發生可能是肝細胞癌發生的一個因素,肝動脈和門靜脈血流不平衡導致肝動脈血流增加,有利于肝結節的形成[10]。近年來,以慢性肝損傷、炎癥和肝纖維化為特征的癌前微環境概念被提出,肝細胞癌與肝纖維化和肝硬化密切相關,肝細胞癌腫瘤微環境中的癌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很可能來源于HSCs。CAFs在缺氧依賴性腫瘤新生血管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11-12]。
肝硬化進展至肝細胞癌,作為一種血管化良好的腫瘤,血管生成在肝細胞癌發生、侵襲和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13-14],肝細胞癌血管生成的方式包括出芽、間質組織柱插入已有血管的管腔(套疊式)或來源于骨髓的內皮祖細胞直接形成腫瘤血管壁等;其特點為動脈形成增加,新生血管明顯異常,出現血管迂曲,分支不規則,血管壁滲漏、竇狀毛細血管增多,微血管密度增加,并形成功能性側支動脈。
總之,持續性炎癥和缺氧是血管生成的主要原因,新生血管的形成最初是為了改善肝組織缺氧,然而病理性新生血管不能緩解缺氧,導致一系列炎癥因子、化學因子和促纖維化因子的產生,并向炎癥區募集多種免疫細胞,在這種情況下,肝纖維化形成并逐漸發展為肝硬化或肝細胞癌。
2 抗血管生成療法在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中的應用
2.1酪氨酸激酶抑制藥(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 受體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RTKs)家族包括多種生長因子家族的受體,如VEGF、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和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當配體與受體結合時,激活受體酪氨酸激酶結構域并上調下游信號系統。這些激酶在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中上調,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治療靶點[15-17]。近年來,索拉非尼、侖伐替尼等幾種TKIs已被批準用于治療肝細胞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TKIs也可用于肝纖維化和肝硬化的治療[18]。
索拉非尼是靶向VEGFR-1/2/3、PDGFR-β和c-Kit受體的TKI,2007年,索拉非尼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準用于治療晚期肝細胞癌,現在被公認為晚期肝細胞癌患者的標準治療方法[19]。在SHARP試驗中,索拉非尼使晚期肝細胞癌患者的中位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和進展時間延長了近3個月。索拉非尼抑制缺氧誘導的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蛋白合成,降低不同肝癌細胞系和異種移植小鼠VEGF的表達;通過阻斷HIF-1α/VEGF通路,降低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并抑制腫瘤血管形成[20-21];此外,大量實驗研究證實了索拉非尼的抗纖維化作用,在幾乎所有肝纖維化動物模型中,包括四氯化碳、膽管結扎、二甲基亞硝胺、二乙基亞硝胺或正硫代乙酰胺,索拉非尼都顯示出抗纖維化作用[22]。此外,索拉非尼可以通過抑制VEGF、VEGFR-2、PDGFR、PDGFR-β、Tie-2等來減少收縮性HSCs在LSECs周圍的包裹,調節LSECs之間形成的連接復合體,減輕纖維化。索拉非尼還可降低門靜脈壓力,降低高動力內臟循環,阻礙門體循環,減輕肝硬化并發癥[23]。索拉非尼與普萘洛爾抑制血管生成時可能具有協同作用。
侖伐替尼是靶向VEGFR1-3、FGFR1-4、PDGFRα、c-Kit和RET的TKI,全球III期試驗(REFECT)的結果顯示,在不可切除肝細胞癌患者的OS和改善無進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治療進展時間(time to treatment progression,TTP)和客觀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方面,侖伐替尼并不劣于索拉非尼[24-25]。在肝細胞癌移植瘤模型中,尤其是在患者來源的異種移植模型中,呈現出比索拉非尼更強的抗血管生成作用[24,26-27]。目前,侖伐替尼治療肝纖維化和肝硬化的研究還很有限。
瑞戈拉非尼(regorafenib)是另一種口服TKI,在一項隨機、安慰藥對照的III期RESORCE試驗中,索拉非尼治療后肝細胞癌進展患者可應用瑞戈拉非尼作為二線治療,延長進展患者的生存期[28-31]。與索拉非尼比較,瑞戈拉非尼具有更強的抗腫瘤和抗血管生成作用,顯著提高肝癌小鼠的存活率[32]。長期使用瑞戈拉非尼治療可降低PHT,其機制很可能是減少血管生成,但并沒有影響肝纖維化的進展或消退[33]。
卡波扎尼布(cabozantinib)是一種口服TKI,靶向VEGFRs、間充質上皮轉化因子(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MET)、AXL、RET、KIT和FLT3等多種受體酪氨酸激酶。根據III期CELESTIAL臨床試驗[34]的結果,卡波扎尼布作為一種新的二線和唯一治療晚期肝癌的三線療法,后來被FDA批準用于索拉非尼治療后進展的肝細胞癌患者[34-37],使用索拉非尼和卡波扎尼布作為二線療法,持續抗血管生成能提高生存率[35]。高MET水平肝細胞癌患者對索拉非尼治療有耐藥性,卡波扎尼布可實現對VEGFR-2和MET的雙重阻斷,抑制腫瘤生長、轉移、血管生成,對肝細胞癌具有顯著的抗腫瘤活性。卡波扎尼布對肝纖維化和肝硬化的治療尚無進一步研究。
阿西替尼(axitinib)是一種選擇性VEGFR(1-3)抑制藥,阿西替尼聯合最佳支持治療(best supportive care,BSC)顯著延長了PFS和TTP,提高了臨床受益率(higher clinical benefit rate,CBR),但未能改善OS。一線藥物索拉非尼治療失敗后,二線阿昔替尼在晚期肝細胞癌患者中表現出中度療效[38]。
自從索拉非尼獲得批準上市以來,新的候選藥物TKIs,如舒尼替尼(sunitinib)、布里瓦尼(brivanib)、利尼法尼(linifanib)和蒂凡尼布(tivantinib)[39]都未能證明其作為索拉非尼的一線療法的有效性。目前正在進行的多中心、隨機、雙盲、III期試驗,評估包括多那非尼(dornafenib)或阿帕蒂尼(apatinib)等新的TKIs對晚期肝細胞癌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17]。
2.2單克隆抗體 VEGF與受體的結合在啟動信號級聯、血管生成、內皮細胞增殖和遷移以及增加血管通透性方面起著關鍵作用,阻斷VEGF和受體的結合有望阻止新血管的形成,從而限制腫瘤營養物質的供應,最終導致腫瘤細胞死亡。抗VEGF或VEGFR的單克隆抗體,包括貝伐珠單抗(bevacizumab)和雷莫蘆單抗(ramucirmab)已被批準用于肝細胞癌治療,但尚未有更多依據證實對肝纖維化、肝硬化的療效。
貝伐珠單抗是人源化抗VEGF單克隆抗體,通過中和VEGF,阻斷其與VEGFR-1和VEGFR-2受體結合,有效阻斷其信號轉導,抑制VEGF誘導的血管生成、細胞增殖、存活、通透性、一氧化氮生成、遷移和組織因子生成。貝伐珠單抗可通過中和肝細胞產生的VEGF,阻斷HSCs的激活,下調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 smooth muscle actin,α-SMA)和轉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β1)的表達,從而減輕肝纖維化,保護肝功能;貝伐珠單抗聯合厄洛替尼(erlotinib)治療晚期肝細胞癌,療效并不優于索拉非尼[40]。在不能切除的肝細胞癌患者中,貝伐珠單抗和阿替唑單抗(atezolizumab)聯合應用,通過對VEGF和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的雙重阻斷,提高OS和PFS,療效優于索拉非尼或阿替唑單抗,但在接受聯合治療的患者中,38%發生了嚴重的毒性反應[41-42]。抑制VEGF誘導的血管生成可以減少腫瘤缺氧,將免疫抑制環境轉化為免疫支持環境,提高PD-L1抑制藥的抗腫瘤效果[43]。長期給予貝伐珠單抗治療會導致耐藥性的發生,腫瘤衍生血管生成因子包括Ang、內皮生長因子(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EGF)、肝細胞生長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和PDGF上調[44]。值得注意的是,貝伐珠單抗治療會增加出血風險,需要進行充分的出血預防;此外,常規經動脈化療栓塞術(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cTACE)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肝細胞癌患者,既不能提高OS,也不能改善放射腫瘤應答,而且還會出現致命的敗血癥和血管不良反應,因此貝伐珠單抗不能作為TACE的輔助治療[45]。
雷莫蘆單抗是一種重組人IgG1單克隆抗體,干擾VEGFR-2細胞外區域的高親和力,阻斷其配體VEGF-A、VEGF-C和VEGF-D的結合,在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和腫瘤生長中發揮關鍵作用[16,35]。兩項全球隨機、雙盲、安慰藥對照的晚期肝癌III期研究(REACH試驗和REACH-2試驗)發現,對于先前接受索拉非尼治療,且甲胎蛋白(AFP)濃度升高(≥400 ng·mL-1)的肝細胞癌患者,雷莫蘆單抗可顯著提高其OS[46-47]。根據REACH和REACH-2試驗結果,雷莫蘆單抗作為AFP濃度升高肝癌患者的二線治療方案,于2019年5月10日獲得FDA批準[48-51]。
2.3其他抗血管生成藥物 曲班那尼(trebananib)阻斷Ang-1和Ang-2與Tie-2受體的相互作用,但曲班那尼聯合索拉非尼并不能進一步提高晚期肝細胞癌患者的生存率[52]。
塞來昔布是一種選擇性環氧合酶-2(COX-2)抑制藥,聯合奧曲肽可通過抑制大鼠血管生成改善TAA誘導的肝纖維化和PHT[53]。
非選擇性β受體阻斷藥可能對肝硬化血管生成有很強的抑制作用,第3代非選擇性β受體阻斷藥卡維地洛被推薦用于降低PHT[54]。
雷帕霉素是一種免疫抑制藥,可阻斷門脈高壓小鼠腸系膜組織的血管生成,減少腸系膜血流,部分原因是它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活性及其對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號通路的影響。大劑量雷帕霉素可通過下調mTOR/P70S6K、NF-κB和VEGF信號通路,減輕肝硬化大鼠缺氧,減少肺內分流,改善肝肺綜合征[55]。
2.4抗血管生成中藥或復方 中藥具有抗血管生成等多靶點藥理作用[56],在抗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癌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一貫煎通過抑制HIF-1α/VEGF信號通路,改善肝臟缺氧微環境,對四氯化碳(CCl4)誘導的肝硬化小鼠具有抗血管生成作用[57]。血府逐瘀湯、扶正化瘀湯、當歸補血湯通過降低HIF-1α、VEGF、VEGFR-2或Ang1和TGF-β1的表達,減輕缺氧,改善氧化應激,保護肝竇內皮細胞功能,從而改善肝纖維化[58]。下瘀血湯通過降低MMP-2和MMP-9的活性,抑制HSCs的活化,破壞新生血管的完整性來抑制血管生成[59]。黃芪和溫郁金能增加肝細胞癌的CD34,降低HIF-1α,促進腫瘤源性內皮細胞血管正常化[60]。
各種類型抗血管生成藥物的概況見表1。

表1 抗血管生成藥物Tab.1 Antiangiogenic drugs

續表1 抗血管生成藥物Tab.1 Antiangiogenic drugs
3 結束語
新生血管在肝纖維化的發生和進展具有重要作用。阻斷新生血管可減輕肝內血管扭曲,改善肝纖維化,防止肝硬化、肝細胞癌。如前所述,近年來抗血管生成治療取得了一些成就,對VEGF/VEGFR、PDGFR或其他促血管生成因子的靶向治療改善了肝纖維化,降低了PHT,減少了內臟血流量,抑制腫瘤血管形成或延長了OS。
然而,由于肝纖維化、肝硬化或肝細胞癌是多因素疾病,血管生成只是影響其發生和發展的因素之一,目前應用TKIs等抗血管生成療法治療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的效果并不太理想;更深入地了解血管生成因子以及血管生成與其他方面的發病機制和轉化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未來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患者治療進展的關鍵,包括抗血管生成在內的多靶點治療可能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此外,成功的抗血管生成治療應避免由于正常生理血管生成過程的抑制而引起的不良反應,例如在修復受損組織或兒童血管生長過程中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