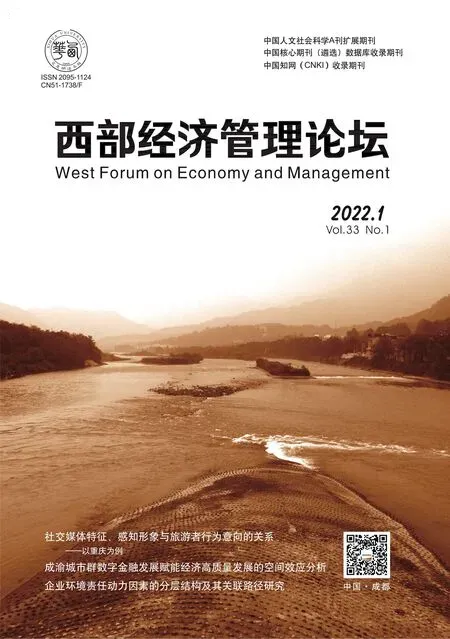社交媒體特征、感知形象與旅游者行為意向的關系
——以重慶為例
祁黃雄 莫如聰 徐 娟 蔣長春 陳暉莉
(1.五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廣東江門 529020;2.莆田學院管理學院 福建莆田 351100;3.福建師范大學旅游學院 福建福州 350117)
一、引言
隨著攜程網、馬蜂窩等旅游社交平臺的興起,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日常生活社交分享平臺的廣泛應用。社交媒體正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和消費行為,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改變了旅游者傳統的旅游決策和產品購買行為,以及他們的個性化需求、感知、滿意度等[1]。社交媒體是旅游研究中的一個較新領域,綜觀國內外文獻,最早起步于2006年,學者們主要從旅游者行為、目的地管理與營銷等方面展開研究探討[2]。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行為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潛在旅游者對旅游地的選擇主要受其對旅游地形象感知的影響[3]。國內外學者對旅游感知形象的研究主要是從影響因素、形象分類、目的地營銷管理等角度展開。近年來,學者們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人口統計特征、信息來源、旅游動機、旅游體驗等對旅游地形象的影響[4-6]。但社交媒體作為影響旅游者行為決策的重要信息源,對于旅游地感知形象的作用機制尚未有深入研究。旅游者行為意向是旅游目的地營銷與管理的研究重點,對消費者行為最直接的預測方法就是了解他們采取該種行為的意向[7]。近年來,雖然有研究者從購買態度、社交媒體的持續使用、電子口碑的信任度、旅游網站特征等方面對社交媒體與旅游者行為意圖的相關關系進行了一定的研究[8-10],并表明社交媒體對旅游者的行為意向能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尚未有學者探討社交媒體特征、感知形象和旅游者行為意向之間的結構關系和三者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目前學者們對社交媒體的特征界定不盡相同,但普遍認為感知有用性、生動性、互動性是社交媒體的顯著特征[6,11-12]。
鑒于此,本文從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生動性、互動性三個特征維度出發,引入旅游地感知形象作為中介變量,建立社交媒體特征、感知形象與旅游者行為意向的關系模型,以著名的網紅旅游城市重慶為例,實證研究社交媒體對旅游者行為意向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 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
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戶認為使用某種網絡技術工具改善其工作效率的程度[13]。Davis等[14]從用戶使用信息技術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消費者技術接受模型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 認為感知有用性影響態度, 態度和感知有用性影響使用意愿, 意愿影響實際接受行為。Zhang等[15]通過網絡文本分析的方法發現,在線渠道是支持游客規劃未來度假的有效信息源,能夠影響旅游者對目的地的感知及旅行決策,進而也會影響游客的旅游訪問意向。Lin等[16]認為,當消費者感知到通過社交媒體能夠便利地獲得有用信息時,社交媒體營銷能夠促進其購買意愿提升,即感知有用性對用戶的購買意愿具有正向影響。華成鋼等[17]實證研究發現,內容感知有用性體驗會正向影響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和決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1a和H1b。
H1a: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顯著影響感知形象。
H1b: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顯著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
(二) 社交媒體的生動性
生動性是指媒介環境向受眾感官呈現信息的形式,可以把其劃分為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前者是指媒介所能刺激的感官 (如聽覺、視覺、觸覺) 數量,后者是指媒介能刺激感官的程度[18]。因此我們可以把社交媒體的生動性理解為,社交媒體平臺利用顏色、音頻、圖片、視頻等來刺激人們的視覺、聽覺等多種感官體驗。Nicholas等[19]研究發現,圖片信息可能比文本信息更加生動,直觀化的視覺信息更加可能影響消費者決策。黃京華等[20]提出了企業微博對消費者忠誠度的影響模型,研究發現有趣的圖片和視頻能提高社交媒體內容的趣味性,從而提高娛樂價值,而娛樂價值顯著影響消費者認同,從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和推薦意愿。吳茂英等[21]指出,社交媒體上的視覺材料作為潛在旅游者了解旅游目的地信息的重要來源,會影響游客對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乃至目的地的選擇和行為的決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2a和H2b。
H2a:社交媒體的生動性顯著影響感知形象。
H2b:社交媒體的生動性顯著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
(三) 社交媒體的互動性
互動被認為是互聯網最重要的優勢之一,互動性是一個雙向溝通的過程。學術界目前對互動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Liu等[22]認為互動性是兩個或以上用戶之間,基于溝通媒介和溝通內容的交互作用及影響的程度。陳曄等[6]實證研究發現,旅游目的地網絡界面的交互性以旅游者的功能體驗、情感體驗作為中介變量,對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的塑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Etemad-Sajadi[23]實證研究關系信任、情感傾向與網站的互動性及對公司惠顧意向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關系信任和情感傾向對網站的在線互動性具有正向影響,進而影響用戶對公司的惠顧意向,揭示了在線互動性與惠顧意向的內在聯系。孟陸等[24]的研究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直播網紅喚起消費者購買行為最顯著的信息源特性均包含互動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3a和 H3b。
H3a:社交媒體的互動性顯著影響感知形象。
H3b:社交媒體的互動性顯著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
(四) 感知形象與旅游者行為意向
在旅游消費者行為理論中,旅游消費者做出的旅游消費行為決策往往會受感知形象的影響。雖然已有研究證實了游客對旅游地的感知形象與其旅游行為的關系[25-27],但是由于感知形象形成的復雜性以及旅游目的地營銷的重要性,感知形象形成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探究和深化。錢曉燕等[25]以江蘇為潛在旅游地,港澳居民為潛在游客,研究證實認知形象和情感形象作為中介變量對游客行為意圖具有正向影響。Zhai等[26]通過中國雪鄉的危機事件,剖析旅游者在網絡輿論危機下的感知、情緒變化和行為傾向,研究發現感知群體相對剝奪會影響旅游者對目的地的信任,進而影響旅游意向。劉力[27]從影視旅游視角探究了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與游客旅游意向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潛在游客對目的地整體形象感知顯著影響他們的旅游意向,影視劇對潛在游客旅游意向的影響被目的地形象完全中介。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H4。
H4:感知形象顯著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構建出社交媒體特征、感知形象與旅游者行為意向之間關系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 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由社交媒體特征、感知形象、旅游者行為意向以及被調查者的人口統計信息四部分組成。其中,社交媒體特征從感知有用性、生動性、互動性三個維度進行了衡量和設計,每個維度分別4個題項,共12個題項。感知有用性的測量參考了柴歡等[28]、Ayeh等[29]的研究;生動性主要參考了范鈞[30]、Steuer[18]的研究;互動性主要參考了范鈞[30]、陳曄等[6]的研究。感知形象主要參考了吳小根等[31]、王純陽等[5]、Mohaidin等[32]的研究,共7個題項。旅游者行為意向主要參考了宋慧林等[33]、Phau等[34]的研究,共3個題項。前三部分為問卷主體部分,采用Likert 5點量表對各測量指標進行測量,1~5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種不同的同意程度。
(二) 數據收集
考慮到本研究是針對社交媒體使用者的調查,加上常態化疫情防控等原因不便進行實地調研,因此全部采用網絡調研形式進行。被調查者在填寫問卷前回想是否有通過社交媒體了解過重慶這一案例地,有即可繼續答題,否則結束答題。問卷的開頭,詳細告知被調查者本次調查目的、注意事項等,盡可能地保證問卷數據的質量。問卷在各社交媒體上進行發放,以滾雪球的方式采集樣本。調查時間為2020年5月至6月,問卷回收數為481份,剔除連續重選或填寫時間較短等明顯不認真回答的問卷后,最終用作數據分析的問卷有325份,有效率為67.6%。
四、實證分析
(一) 樣本分析
樣本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女性略多于男性,分別是54.4%和45.6%。總體年齡比較年輕化,79.7%的被調查者年齡為18~34歲;92.4%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在職業方面,涉及的職業較為廣泛,其中,企業單位人員、學生、事業單位人員分別占23.6%、22.7%、14.2%。在收入方面,主要涉及中等收入者,其中月收入為4001~6000元者占30.5%。
(二) 正態分布性檢驗
本文使用SPSS19.0和AMOS21.0對數據進行分析,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對樣本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由數據分析結果可知,所有因子的偏度在?1.242~?0.631之間,峰度在?0.001~1.478之間,其偏度和峰度的絕對值均小于2,因此可以推斷本研究數據符合正態分布的要求[35]。
(三) 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對整體模型的適配度進行評估,確認是否需要進行調整和修改,需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本文使用AMOS21.0軟件來處理。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綜合測量模型的擬合指數為x2/df=1.521,小于3;RMSEA=0.040,小于 0.05;GFI=0.916,NFI=0.942,CFI=0.979,AGFI=0.893,基本上都大于 0.9 或非常接近 0.9,從而可判斷綜合測量模型的擬合度較好[36-37],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模型。由表1可知,各潛在變量的組合信度都大于0.7,平均提取方差都大于0.6,由此可見,綜合測量模型信度良好。

表1 (續)

表1 綜合測量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
效度檢驗是分別對模型的聚合效度和區分效度進行檢驗。由表1可知,全部測量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量都在0.7以上,且p<0.001,由此可判斷該綜合測量模型的聚合效度較好。由表1和表2可知,任意兩個潛在變量的相關系數的平方均小于其各自平均提取方差,由此可見量表的區分效度較好。

表2 綜合測量模型的關系矩陣
(四)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在通過正態分布性檢驗和驗證性因子分析后,使用AMOS21.0軟件,運用極大似然法對理論模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原始模型的整體擬合指數除AGFI外,基本達到門檻值(x2/df=1.521,CFI=0.979,GFI=0.916,RMSEA=0.040,NFI=0.942,AGFI=0.893),但修正指數顯示仍有改進的空間,據此修正后,各項擬合指標均達到理想要求(x2/df=1.437,CFI=0.983,GFI=0.924,RMSEA=0.036,NFI=0.946,AGFI=0.902)。由表3 的假設檢驗結果可知,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對感知形象和旅游者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影響(β1=0.134; β2=0.188),因而假設H1a與H1b得到證實;社交媒體的生動性對感知形象和旅游者行為意向都有顯著影響(β3=0.234;β4=0.163),因而假設H2a與H2b得到證實;社交媒體的互動性對感知形象和旅游者行為意向具有顯著影響(β5=0.135; β6=0.169),因而假設H3a與H3b得到證實;感知形象顯著影響旅游者行為意向(β7=0.240),因而支持假設H4。

表3 假設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討論
(一) 研究結論與啟示
第一,社交媒體的三個特征對旅游者行為意向具有直接顯著正向影響。本文將社交媒體按其特征劃分為感知有用性、生動性和互動性三個維度進行探討,發現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生動性和互動性均顯著正向影響著旅游者行為意向,進一步證實了現有研究結論[17,19,24]。因此,目的地的管理部門要善于利用社交媒體加強對旅游目的地的宣傳;要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特征規律,通過高質量的內容來吸引旅游者的眼球,使其產生到該目的地旅游的興趣和沖動;通過打造精美的宣傳圖片、視頻等,來刺激旅游者的視覺、聽覺等感官體驗,進而影響其行為意向。
第二,社交媒體的三個特征通過感知形象間接作用于旅游者行為意向。雖然有少數研究者探討過社交媒體與旅游地形象的關系,但本文首次從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生動性和互動性三個特征維度,探討社交媒體對感知形象的作用機制。本文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生動性和互動性對感知形象均具有直接的顯著正向影響。這表明,對于社交媒體上有關旅游目的地的信息越可靠有用、內容展示效果越生動、平臺互動效果越好,其對該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形象就越好,從而能增強其行為意向。因此,目的地營銷組織應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特征和規律對旅游地形象進行有效宣傳,在旅游者心中樹立良好的形象,進而刺激旅游者的旅游行為。
第三,感知形象正向作用于旅游者行為意向。換言之,旅游者對旅游地的感知形象越好,越有可能選擇去該地游玩或推薦朋友去該地游玩;旅游者對旅游地的感知形象越差,越不會考慮去該地旅行,這與現有研究結論一致[25-26]。因此,目的地營銷組織要做好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管理,既要通過社交媒體等宣傳正面的旅游地形象,同時也要重視對網絡上關于旅游地的負面電子口碑對游客感知形象的影響,做好網絡輿情管控,針對游客反饋的負面口碑去改善旅游地的不足,才能更好地提高旅游者的感知形象,進而提高旅游者行為意向,并使其轉化為旅游行為。
(二) 研究不足與展望
首先,在社交媒體的三個特征的測量指標上,由于學術界尚未對這三個特征有較為統一的量表,本文對社交媒體的感知有用性、生動性、互動性的測量有待商榷。其次,在感知形象的測量上,本文用了7道題項進行測量,雖然已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還可以把感知形象劃分為二階變量,進一步提高感知形象的信度和效度,提高結果的預測性和解釋性。第三,調查形式以網絡調查為主,沒有過多開展實地調查,未能全面真實地了解調查對象的心理狀態,未來應考慮網絡調查和現場調查相結合,以提高研究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