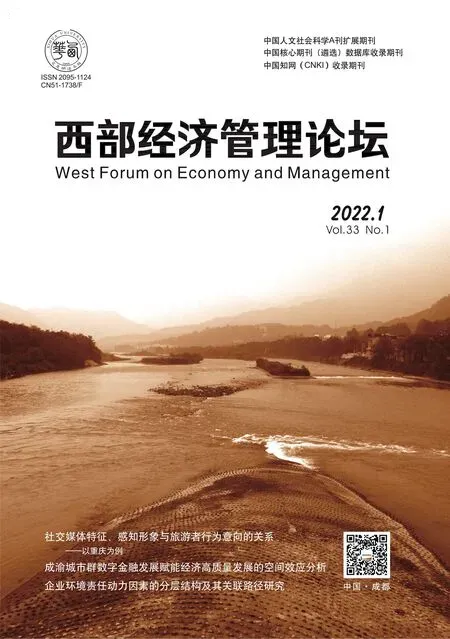社會支持對綠色消費意愿的影響路徑研究
李婷婷 何建佳
(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上海 200093)
在經濟社會日益繁榮的同時,自然環境受到污染、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日益突出。各國政府已普遍認識到這一問題,并采取了相應措施減少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不良影響,公眾也開始關注經濟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關系,“綠色消費”理念進入大眾視野。當前,中國正處于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窗口期,綠色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促進綠色消費和綠色發展,不僅能夠對經濟發展形成有效刺激,還有利于產業綠色化程度的提升。此外,從中國整體綠色發展轉型進程和現狀來看,綠色消費是促進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大力推動綠色消費對轉變社會發展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改善環境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且正當其時[1]。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者們開始關注綠色消費,隨著研究深入,綠色消費的內涵得到不斷豐富和延展。綠色產品是指比傳統類似產品更有利于環保的產品[2]。從國家政策和社會輿論來看,國家倡導綠色產品消費,同時公眾對綠色產品也持積極態度,但其購買意向和購買行為還遠遠不足[3]。這種不一致在多篇文獻中被提及和確認,被稱為“綠色態度—行為差距”,也稱“綠色差距”[4],深入探究激發綠色消費動機的影響因素有益于理解和縮小這種態度與行為之間的差距[5]。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綠色消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綠色消費意向影響因素和“綠色差距”分析兩方面。其中,國內外學者探討了環境價值觀[6]和情緒[7]等個人因素、價格[8]和社區環境[9]等情境因素對消費者綠色產品購買意向的影響。對于“綠色差距”,學者們主要從內在心理因素和語境因素兩個方面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綜上,目前有關綠色消費意愿的研究主要討論個人心理因素或情境因素的影響,忽略了消費者決策的心理活動過程。綠色消費作為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消費類型,消費者必然會考慮個人消費的公共后果,并試圖利用其購買行為影響社會變革。在購買綠色產品的過程中,消費者通常會受到態度、人口特征、內部心理因素及外部情境環境等因素的共同影響[10],他們會評估綠色產品購買的社會環境、產品屬性和個人利益等各種方面。鑒于“刺激-有機體-反應”(S-O-R)框架已被廣泛應用于探討外部刺激、心理狀態和隨后的行為反應之間的關系,本文擬以S-O-R模型為基礎研究框架,對社會支持(S)是否會觸發消費者對綠色消費的情緒狀態(O)并間接影響購買意愿(R)進行研究,進而為推動綠色消費提供依據和思路。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 SOR 理論
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理論由 Mehrabian等[11]于 1974 年基于 SR(Stimulus-Response)理論提出,用于描述個體所經歷的外部刺激(S)、個體有機體產生的內部心理狀態(O)及其隨后的反應(R)之間的關系。與SR理論相比,SOR理論考慮了外部刺激對個人內部狀態的影響,描述了一個由外部刺激引起內部變化再到做出反應的心理過程。具體來說,刺激(S)是指引起個體內部狀態變化的外部因素,如環境刺激和社會刺激等[12]。有機體內部心理狀態(O)是處于刺激和最終反應或行為之間的中介和過渡,指個體情感認知的內在體驗,包括認知狀態和情感狀態[13-14],其中,認知是個體基于信息進行的理性思考,情感則是個體基于信息產生的態度和體驗[15]。反應(R)是刺激和有機體兩者作用的結果,通常表現為態度或行為意愿等心理反應[14]。目前,SOR理論被廣泛應用于企業員工行為、消費者行為等的研究[12,16,17]。
綠色消費作為一種有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消費,是世界各國普遍倡導的一種消費方式。本文認為,社會支持可被視為外界對于綠色產品消費者的“刺激”,消費者接受到來自外界的“刺激”后通過自我判斷和評估產生的綠色自我效能感和感知信任為“有機體”,最后消費者的這種內部心理狀態會影響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購買意愿,即“反應”。本文試圖探討社會支持(S)、消費者的認知和感知(O,本文指綠色自我效能感和感知信任)與綠色消費意愿(R)之間的關系,其中社會支持為前因變量,綠色自我效能感和感知信任為中介變量,購買意愿為結果變量。
(二) 社會支持與綠色自我效能感
社會支持概念源于社會心理學和衛生健康領域,健康研究學者Cobb[18]將其定義為一種“使個體感受到自己受到他人的關愛、尊重,并在相互義務網絡中產生歸屬感”的重要信息,是一種來自個體以外的支持性行為,這種行為能夠提高個體對某一物體或社會產生適應性。此后,Shumaker等[19]基于資源交換理論將社會支持定義為“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間旨在提高接受者幸福感的資源交換”。自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支持概念被引入到營銷領域,消費情境下的社會支持不再局限于“提供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利益傳遞,更是消費者與親友之間、消費者與企業之間、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和情感特征的表現形式[20]。Bandura[21]將自我效能感定義為個體相信自身有能力執行特定活動,并最終能成功執行以實現目標的感知評價。綠色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概念的延伸,即在自我效能感中融入綠色環境因素,是個體對其執行特定活動以實現綠色環境目標的能力的評價[22]。關于社會支持的已有研究證實,顧客間社會支持對消費者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如,Ali等[23]對450名巴基斯坦消費者進行了調查,發現社會支持的獲得會促進消費者的社會責任行為,使消費者選擇從事對社會有益的行為。與一般性社會支持相似,營銷領域中的社會支持根據性質的不同被分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其中工具性支持又被拓展為物質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24]。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社會支持對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
H1a:物質性支持對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
H1b:信息性支持對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
H1c:情感性支持對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
(三) 社會支持與感知信任
感知信任是消費者對外界人、物、事的積極預期狀態[25]。對于社會支持這個社會心理學和衛生健康領域的重要概念,學者們發現,小學教師的社會支持感與組織信任之間存在中等水平的正相關關系[26];信息支持、情感支持以及滿足個體自主需求和人際需求會通過信任正向影響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尋求健康信息的意愿[27]等。此外,有學者將社會支持引入社區商業情境,證明了社會支持對感知信任的正向影響,如Li[28]發現,在社交網站上接受其他成員的社會支持會使人們對其他成員的產品推薦產生更大的信任。Fan等[29]將社會支持理論和存在理論相結合進行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和存在會對建立快速關系和信任產生積極的影響,其中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影響更加顯著。Chen等[30]也證明了情感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會正向影響消費者信任和社區承諾,進而影響其購物意愿和社會共享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社會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
H2a:物質性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
H2b:信息性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
H2c:情感性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
(四) 綠色自我效能感與綠色消費意愿
已有學者對自我效能感在綠色消費行為中的影響或作用進行了研究并發現,自我效能感作為一種自我認知,在綠色情境下會對公民的親環境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也會激勵個人的環保行為[31]。綠色自我效能感一詞是Chen等[22]在研究企業綠色共同愿景與綠色創造力時基于自我效能感概念提出的,后被部分學者用來研究企業員工的綠色行為和節能行為。Chen等[22]發現,綠色共同愿景通過綠色正念和綠色自我效能感的介導正向影響員工的綠色創造力。Guo等[32]也證明了有較高綠色自我效能感和環保行為能力的管理者更可能強化廢棄物管理。目前,關于自我效能感如何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的研究已非常成熟,綠色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綠色消費情境下的運用,因此對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意愿的影響更為直接。盛光華等[7]提出,環保自我效能感更高,消費者會更愿意實施親環境行為,也更愿意購買綠色產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綠色自我效能感對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五) 感知信任與綠色消費意愿
感知信任被定義為一種心理狀態,包括基于對他人意圖或行為的積極期望而接受脆弱性的意圖[33]。對人或物產生信任會減弱對隱藏風險的感知,從而更愿意基于這個人或物做出選擇。信任在不同情境的決策過程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34],特別是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例如,Carfora等[35]發現,消費者信任是決定其購買有機牛奶的關鍵影響因素,特別是對農場主的信任在購買行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綠色消費領域,有學者基于綠色情境提出“綠色信任”概念,即基于產品、服務或品牌的信譽、社會責任、能力和環保效能而產生的信念或期望[36]。此外,消費者信任綠色產品或綠色企業也意味著對其有很高的期望,因此該產品或企業會獲得消費者的積極評價。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感知信任對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基于SOR理論的消費者綠色消費意愿影響路徑的理論模型,如圖1 所示。
二、研究設計
(一) 研究樣本
本文采用結構化問卷調查方法來確定量表并研究變量,具體通過了預調研和正式調研兩個環節。預調研期間通過線上匿名發放問卷96份,收回有效問卷80份,然后進行信度檢驗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和修改因子載荷小于0.5的題項,最終形成包含24個題項的正式量表。正式調查借助Credamo平臺設計并線上發放問卷295份,通過設置反向題項和剔除不認真作答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41份,有效率為81.7%。除設計測量變量量表外,本文還根據綠色消費情境設置了相關的統計變量以了解研究對象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月平均收入等,具體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樣本結構特征描述
(二) 問卷設計
本文借鑒國外已有成熟量表并結合綠色消費情境編制量表,最終共包含24個測量題項。本研究所有題項均采用Likert 5級量表, “1”代表非常不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同意程度從1至5逐漸增加。其中,在編制社會支持測量量表時,本文參考了Suurmeijer等[37]開發的交易型社會支持問卷(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for transactions,SSQT),同時考慮了 Rosenbaum[24]在前者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以及 Liang 等[38]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結合綠色消費的特點編制題項,最后確定的物質性支持(MS)測量包含3個題項,信息性支持(IS)測量包含4個題項,情感性支持(ES)測量包含4個題項。編制綠色自我效能感(簡稱GSE)測量量表時主要參考了Chen等[22]和Huang[39]的研究,最終確定了4個題項。編制感知信任(簡稱PT)測量量表時借鑒了Chen[36]關于綠色信任的研究,最終確定了4個題項。編制綠色消費意愿(簡稱GCI)測量量表時,本文在Paul等[40]的研究基礎上進行了完善以更符合本文的研究情境,最后確定了5個題項。
三、模型分析
(一) 信度與效度檢驗
本文使用SPSS19.0軟件對正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分析結果見表2。通過Cronbach’s α值對正式量表中的各測量變量的信度進行檢驗,由于所有變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7以上,說明量表內部一致性較好,信度較高。在信度分析基礎上,本文從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兩方面展開效度分析。內容效度方面,所有測量量表均參考了國內外學者開發的成熟量表或研究成果,并根據綠色消費情境進行了修改,且通過預調研對數據進行了調整,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結構效度方面,本文利用SPSS19.0軟件進行KMO值和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結果顯示量表的KMO值為0.812,Bartlett 球形檢驗顯著,其中各變量KMO值也均大于0.6且 Bartlett 球形度檢驗均顯著,表明各測量量表均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在前述檢驗基礎上,本文進行了因子分析,由于各變量的因子載荷量均大于0.6,AVE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8,說明各變量量表的收斂效度檢驗通過。

表2 各變量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在收斂效度檢驗通過的基礎上,本文通過對比AVE根號值和相關分析結果,對各變量進行區分效度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由于各變量自身的AVE 開平方根值均大于自身與其他變量的 Pearson相關系數,因此所有變量的區別效度檢驗通過。此外,表3還顯示,除物質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之間、物質性支持與綠色自我效能感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外,其余變量兩兩之間都在 0.01 的水平上顯著相關,這與預期理論假設基本相符,為后續假設檢驗提供了基礎。

表3 變量間相關性及區別效度分析結果
(二) 模型適配度檢驗
本文利用Amos24.0軟件對模型進行擬合度檢驗,模型適配度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GMIN/DF為1.796,小于 3;RMSEA 為 0.058,小于 0.08;GFI為 0.876,NFI為 0.841,CFI為 0.931,IFI為 0.933,TLI為0.919,均接近或大于0.9;PGFI為0.695,PNFI為0.728,均大于0.5。綜合來看,各項擬合指標都能夠達到對應要求,說明本文的研究模型具有較好的適配度。

表4 整體擬合系數表
(三) 假設檢驗
本文借助Amos24.0軟件對研究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所得參數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的數據可知,信息性支持對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β=0.201,p<0.01),情感性支持對綠色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響(β=0.363,p<0.05),因此H1b和H1c成立。物質性支持對綠色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則H1a不成立。物質性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β=0.28,p<0.01),信息性支持對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β=0.255,p<0.001),情感性支持對感知信任具有正向影響(β=0.659,p<0.001),其中情感性支持對感知信任的影響最大,因此H2a、H2b和H2c均成立。從H1和H2的檢驗結果來看,外部刺激(S)對消費者的內部心理狀態和認知狀態(O)具有正向影響。表5顯示,綠色自我效能感對綠色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β=0.224,p<0.01),感知信任對綠色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β=0.162,p<0.01),H3 和 H4 得到支持,這表明消費者的內在心理狀態和認知狀態(O)對其行為意愿(R)具有正向影響。

表5 (續)

表5 模型路徑回歸參數結果
(四) 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綠色自我效能感和感知信任的中介效應,本文利用Amos24.0軟件進行 Bootstrap 中介變量檢驗,確定抽樣次數為2000,置信區間設置為90%,檢驗結果見表6。表6顯示,各作用下的信賴區間均不包含0,說明綠色自我效能感和感知信任在社會支持與綠色消費意愿之間具有中介作用,這也驗證了SOR理論在綠色消費情境下的適用性,社會支持作為外部刺激(S),影響個體的內部心理狀態,即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與感知信任(O),從而促使消費者做出綠色消費意愿的反應(R)。

表6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四、研究結論及實踐啟示
(一)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SOR理論模型探討了社會支持(S)通過刺激消費者內在心理狀態(O)從而推動消費者綠色消費意愿(R)的完整路徑,得出以下結論:
(1)信息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會增強消費者綠色自我效能感從而正向影響消費者綠色消費意愿。首先,個體消費者感知到綠色產品的相關信息支持,意識到自身可以通過綠色消費來保護環境并實現環境保護目標,進而逐漸轉化為消費者對綠色消費行為的自我效能感,從而推動其綠色消費意愿。其次,消費者感受到綠色消費行為會得到外界的支持、鼓勵、尊重等情感方面的回應,這能讓消費者的身心在綠色消費中得到升華,進而從心理上增強通過特定活動和行為實現綠色目標的信心,提升自己的綠色自我效能感,最終做出綠色消費行為。最后,研究還顯示,物質性支持對消費者的綠色自我效能感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說明物質性支持對于消費者自身能力評估的影響較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目前綠色產品的物質性支持力度普遍不是很高,消費者感知不明顯不充分。
(2)社會支持會通過提高消費者感知信任進而正向影響消費者綠色消費意愿。這一發現說明,當個體接收到來自外部的情感、物質、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時,消費者會更加信任綠色產品和綠色企業的屬性和價值,這種信任提高了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意愿。當消費者發現綠色產品比非綠色產品的性價比更高,且能準確、及時地了解到豐富的綠色產品相關信息并受到社會和周圍人的鼓勵、尊重與支持時,就會對綠色產品及其企業產生強烈的信任,進而強化其購買綠色產品的意愿。對路徑的相關假設檢驗還顯示,情感性支持對消費者感知信任的影響最大,信息性支持次之,物質性支持影響作用相對最小。上述影響差異的原因可能包括:首先,綠色產品除了具備同品類非綠色產品的傳統屬性以外,往往還帶有可持續性、環境友好性和利他性等綠色屬性,在購買和消費綠色產品時,消費者首先會感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大力倡導以及周圍人的鼓勵和贊賞,在此環境下,消費者會進一步確認購買和消費綠色產品是一種積極的、利國利民的行為。其次,消費者在搜索到詳細的綠色企業及綠色產品的相關信息后,對綠色企業的宗旨、社會責任履行以及綠色產品的功能屬性和社會屬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將正向影響消費者感知信任,如果該產品還同時具有高性價比,消費者信任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加快其綠色產品購買意愿的形成。
(二) 實踐啟示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文認為,政府可通過物質、信息和情感等三方面支持來引導和培養消費者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首先,政府應進一步增強對綠色產品的補貼力度,包括擴大補貼范圍、為綠色產品及生產企業提供更多技術和資金支持、為消費者提供物質性支持等。其次,政府應推出權威性的綠色環保產品認證體系和綠色服務認證體系,減少消費者在識別產品中的困惑,增強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信任感。最后,政府應重視綠色消費宣傳推廣,提高消費者對實現環境保護目標的自我效能感和對綠色消費行為的認同度,進而提高廣大公民的綠色消費意識,推動綠色消費行為。
從企業角度來看,綠色產品的相關企業應深入把握消費者綠色購買意愿形成路徑,抓住其中的關鍵環節調整企業營銷策略。在價格策略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提供物質性支持來淡化消費者對價格的關注,如提供贈品和附加服務等。在宣傳策略方面,綠色企業可針對產品的綠色屬性和功能屬性兩方面做好營銷,詳盡和完備地描述綠色產品相關信息,同時建立公開透明的溝通平臺,強化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理解和信任,增強消費者的綠色自我效能感。在溝通策略方面,綠色企業要重視情感性支持對消費者的影響,讓消費者在購買和消費綠色產品的過程中感受到企業的關懷、尊重和贊賞,要突出綠色消費是受到他人尊重、理解和支持的行為,強調消費者個人在綠色消費中的重要作用,讓消費者充分認識到綠色消費產生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