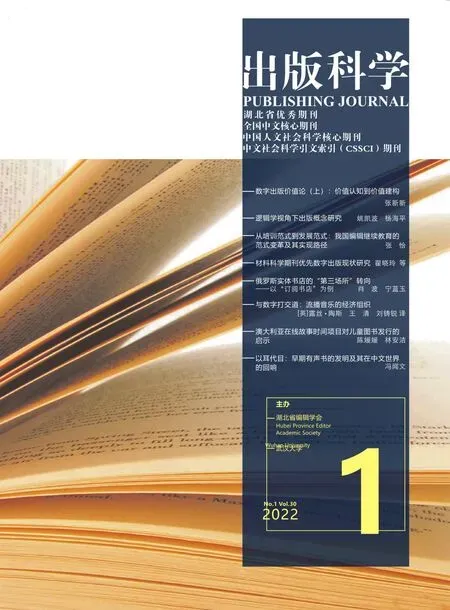以耳代目:早期有聲書的發明及其在中文世界的回響
馮聞文
[摘 要] 1930年代,依托留聲機和密紋唱片制作的有聲書在美國發明,其突破的關鍵性壁壘在于唱片存儲內容和播放時長的限制。民國報刊對有聲書的介紹,清晰地呈現了其發明歷史及基本原理,展現出國人對有聲書發明的敏感與關切。而通過鉤沉有聲書發明前史,即能發現早在1920年代,以文字轉碼為方式的活字留聲片曾成為前人實現以耳代目的可行路徑,其技術原理同樣得到民國報刊的關注與介紹。因為有聲書發明的初心是為了盲人教育事業,所以以擴大存儲內容、延長播放時間為方式、以語音為內容的有聲書唱片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接受。有聲書發明的實現及發展,亦體現出技術發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持而長的深層次關系。
[關鍵詞] 有聲書 留聲機 密紋唱片 盲人教育
[中圖分類號] G23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2) 01-0108-06
Read through the Ear: The Invention of Early Audiobooks and Their Reverberations in the Chinese World
Feng Wenwen
(The Institute for Jiangnan Culture,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In the 1930s, on the basis of gramophone and LP record, talking books were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key barriers to break through in the process of invention of talking book records was the limited capacit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egan to introduce the invention of talking books. These articles clearly present the early history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alking books,and demonstrate the sensitivity and concern of Chinese people on this invention. Probing into prehistory of talking books, in the 1920s, shrinking the storage unit had once become a feasible path to realization of audio books. Sinc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invention of audiobooks wa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blind, expanded audiobook records with human voice as content were accept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invention reflects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ularity and purpose of the technical invention.
[Key words] Audiobook Phonograph Long-playing record Education for the Blind
有聲書是以聲音為形式進行內容傳播的出版物。無論唱片、錄音帶、數位檔,都可以稱之為有聲書。有聲書在1930年代的美國率先發明。此時的有聲書特指依托留聲機,利用一種存儲容量較大、播放時間較長的密紋唱片錄制書籍文字的聲音。1934年起,中文報刊開始注意到這一新型知識傳播工具,并不斷向國人進行相關報道和介紹。本文從媒介考古學的角度出發,考察有聲書發明的前期歷史,指出在此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不同技術路徑的競逐,探討原本為盲人教育事業而發明出來的新傳播媒介,在中文世界里有著怎樣與海外不盡相同的回響,指出技術發明背后共通的人文關懷,如何體現了技術作為人的存在方式、以人為中心的指歸。
1 新型留聲機和密紋唱片
1934年5月28日,天津《大公報》刊登紐約電訊:“據發明家達雅氏(Frank L. Dyer)宣布,彼新近發明一種‘有聲書籍,不久即可出版,其制與尋常留聲機片相似,能灌入三萬字長短之小說,該片每一面能唱一小時二十分,達氏近在工程師俱樂部曾經試驗此項發明,頗為成功。”[1]這是有聲書發明的信息首次傳入到中國。達雅氏曾經是愛迪生實驗室的法律顧問,并曾于1910年出版《愛迪生的人生與發明》(Edison, His Life and Inventions)。“當留聲機初發明時,艾迪生就預料將來可有‘有聲書籍的發明。達氏從一九一八年起從事這項發明的試驗” [2]。 因而,有聲書的發明是以留聲機為之喤引。
1877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得到世人矚目。1878年,愛迪生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 Review)對留聲機的應用領域做了展望,其中就包括有聲書。愛迪生認為書籍內容可由具慈善傾向的專業朗讀者閱讀,或者由為此目的而專門雇用的朗讀者閱讀,并且該書籍的記錄可用于盲人的收容所、醫院、作病房,或為眼睛和手另作他用的女士或紳士提供娛樂。而較之普通朗讀者,由朗誦演員閱讀,人們從中能獲得更大享受[3]。不過,最初,圓筒留聲機錄制的聲音不過幾分鐘。唱盤式留聲機發明后,唱片錄制聲音時長仍十分有限。由于唱片承載信息量的限制,留聲機的運用范圍受到了一定制約。隨著留聲機技術的不斷完善,它才由科學玩具變為文明利器,獲得廣泛應用。
留聲機傳入中國后,主要被用于播放音樂、戲曲唱片,也被用于教育用途,如國音推廣、方言校正[4]。1927年,柯政和發表文章指出國人對留聲機的認識不夠,他根據歐美國家對于留聲機的利用方式,重新對留聲機的用途加以歸納,將其分為三類:第一是在教育上的用法,包括教授體操、理科和聲學;第二是在家庭中的用法,有益于養成高尚的趣味,教育兒童的耳,自習音樂,學習外國語,研究音樂的組織與歷史;第三是特別的利用法,包括音樂治療、鼓勵兵士、舞蹈的練習、恢復精神、幫助事務[5]。足見留聲機應用范圍已較為廣泛。然而,1933年,國內面向小學生普及留聲機知識的讀物中,也只提及有留言作用的記述留聲機、與放映設備連接使默片變得有聲的留聲機[6]。當時國人尚未意識到留聲機可以用于播放以長篇書籍為內容的唱片,將文字轉化為聲音,依靠聽覺接受書籍知識的傳播。
隨著留聲機的電氣化,有聲書唱片所依托的留聲機技術漸趨成熟。而無線電技術被用于廣播,也可以使之與留聲機結合。達雅氏與R.C.A.Victor(即并購勝利唱機公司唱片部門的美國廣播唱片公司)、貝爾電話公司合作生產用來播放有聲書的新型留聲機[7],就是電氣留聲機與無線電收音機的混合體,同時具備了留聲機和收音機的功能。1934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介紹了這一新機器的構造:“機身之大小為20×15×9英寸,有如手提小皮箱,精美簡便,嬌小玲瓏。又此機由有聲書籍之誦讀,又可以一變而為廣播無線電之放送。此外,尚有不同之機關數種,專司誦讀時聲音之高低,速度之快慢,使用者可以運轉自如,藉期適合需要。機件重約三十磅,售價不昂—二十元,三十元或三十五元(金洋)不等”[8]。
新樣式的留聲機只是實現有聲書播放的一個方面,對有聲書發明有著決定性意義的其實是唱片的改良。達雅氏制成的新唱片的優點,在于其凹線多于一般唱片,轉速更慢,而播放時長更長。1934年的《中學生》雜志對之進行了詳細描述:“他所制成的片子上的凹線,每英寸有五百條,平常唱片只有一二百條,平常唱片每分鐘轉七十八次,他的片子只轉十六次又三分之二,所以平常唱片每面只唱三四分鐘,他的片子可唱一小時多。據說,這種‘有聲的書可放在新式的擴音唱機上演唱,每片價格約為七先令六便士。”[9]由此可知,這種新唱片,主要是實現了擴容,適合于錄制篇幅長、信息量大的有聲書。
除達雅氏之外,當時的中文報刊還對美國好萊塢的哈利詩(Harris)所發明的適合做有聲書的慢速唱片進行了介紹,并配有他向美國盲文學院的創辦者約翰·羅伯特·阿特金森(John Robert Atkinson)介紹有聲書機器的照片:“他發明一種方法制造留聲機器的唱片,每片可以發聲歷一小時之久。因此有聲書籍就可以制造了。……在兩個十六吋徑的唱片上平均可以灌入六萬五千余字,發聲可以歷二小時之久。…… 感覺敏捷而輕巧的傳聲針和無線電的放大器與揚聲器相連。書籍聲片轉動的遲速和揚聲的大小有一個鍵可以自由節制。制造此種有聲書籍的最要關鍵是刻片的方法,需要使刻成的聲片能夠容納大量的字句而保持長時期的連續發音。這個秘訣哈利詩至今尚未發表。其他構造和普通留聲機上的唱片同樣。”[10]雖然具體對唱片制作的細節未作介紹,但哈利詩發明的關鍵也在于唱片的擴容,播放時間的延長。只要解決了舊式唱片容量小的問題,也就意味著可以完美地進行有聲書的錄制。由此可見,有聲書的誕生是在留聲機及唱片相關技術成熟的基礎上,往一定運用方向上的突破。
此外,1935年,《時事月報》刊文稱:“美國西屋電燈公司希本氏(Samuel G. Hibben)近曾預告將有類似有聲電影之有聲書籍制造之發現。”[11]希本氏是一位照明工程師,其發明主要利用光學、電學。他認為在床上聆聽有聲書取代書架上的書是很大的樂趣,而光線、音樂搭配有聲書能夠為讀者創造氛圍,所缺的只是將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的機器[12]。他希望取法集合聲光電學的有聲電影去進行有聲書籍的錄制。這是在運用方向確定的前提下,改換已知的技術實現路徑。從中文世界對有聲書發明的介紹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國人對有聲書發明的高度敏感及其技術核心的深切關注。
2 過渡形態的活字留聲機
有聲書的發明并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歷史。針對既往唱片容量小,進行擴容以實現有聲書錄制—這樣的一種發明路徑,于后來者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但在1930年代唱片擴容的有聲書發明之前,曾有科學家嘗試以另一種方式來實現以耳代目。
1921年,《東方雜志》曾以《盲目者之活字留聲機》為題,介紹維也納的黑爾志博士的一項新發明—活字留聲機(Typephonia)。指出這種活字留聲機十分小巧,易于攜帶,它的特別之處在于錄制的不是平常言語的聲音,最終播放出來的乃是一種電報音,其記錄單位是一種新式電報號碼。一般電報碼是由點和劃(dot and dash)共同構成的,為了節省空間,這種新式電報號碼完全用點,“故其片之面積雖小,而所容之字獨多,設將書籍完全譯為號碼,而留其碼音于片上,則數片即可容納十余頁之文字”[13]。在具體的制作流程上,要先將文字信息轉化為新式電報號碼,再根據轉化后的號碼制作出打孔紙帶[14]。打孔紙帶是承載書籍信息的中間手段。在打洞的卷尺紙條制好之后,再利用電磁設備翻刻到蠟制唱片上。具體的翻刻方法,就是借用轉動機,將打孔紙帶夾在“電接觸器”(Electrical Contact)間抽過[15]。
如此制作出來的活字留聲片的價格十分低廉,每片的成本為三美分,售價則為五美分。與之相匹配的留聲機則要利用手搖。原因在于:“因活字留聲片上所刻文字號碼極密,需用時不須轉動過速,故其轉動機不必如尋常留聲機之用彈簧,只須用手搖機徐徐搖之,約每秒鐘發音器之針在片上滑走一吋,則文字碼音發出最清晰而易認辨,此種手搖機價廉易造,機輪配合,均定有相當速度云。”[16]道理和1930年代的有聲書唱片一樣,因承載信息密集,必須以較慢的速度進行播放,但在具體實現方式上有所不同,須人為控制。
活字留聲片的發明思路無疑也有可取之處,它的側重點并不在于對唱片有限的存儲空間進行擴容,而是通過縮小存儲單元,使唱片容納更多的信息。但因為這種活字留聲機的使用者必須記憶特別的碼音,解碼過程完全依賴于使用者對于碼音的記憶和分辨。而達雅氏等人所發明的徑直以文字音進行傳播的有聲書,對于盲人來說,則用之與常人無異,因為盲人雖有視覺障礙,但于聽力無損。
值得注意的是,《東方雜志》的中文報道雖有錯訛之處,如將黑爾志Hertz誤寫為Herz。但相較于英文報紙的報道,《東方雜志》對活字留聲機基本原理的介紹極為細致,成為國人了解這一“失敗發明”的寶貴文獻。
3 有聲書和盲人事業
無論是活字留聲片還是有聲書唱片,發明的最初出發點都是為了盲人事業。海倫·凱勒就曾贊嘆有聲書的發明為盲人帶去了快樂與滿足[17]。中文報刊在介紹有聲書發明時,也特別強調它的這一初衷。
黑爾志發明活字留聲機就是因為“盲目之人,因識字無緣,于人生之幸福,喪失殆盡。……特發明一種以耳代目之讀書法,使盲目者藉此得以自修”[18]。根據1920年美國《丹佛猶太人新聞》的報道,黑爾志是在三年前失去視力后,勤勉致力于這一設備的發明的[19]。達雅氏的有聲書研究實驗,同樣得到了美國盲人基金委員會(The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AFB)的支持,原因在于當時美國實際掌握布來利盲文進行閱讀的盲人不過其總數的四分之一。據美國《印第安納時報》的報道,布來利盲文書籍的品類,主要是神話和暢銷小說,而有聲片的內容范圍則廣泛得多,可以用來開發供盲人大學生使用的課本[20]。希本氏利用有聲片的原理制作有聲書,也有經濟上的考量,“蓋近日專供盲人念讀之有聲書籍,多用留聲機片所制,價甚昂貴,惟將來如用有聲片制造,較見經濟,則有聲書籍之售價,將與尋常書籍無異云”[21]。
在有聲書發明之初,美國盲人基金委員會執行理事羅伯特·B.艾文(Robert B Irwin)即指出有聲書能將盲人從對觸摸方式的依賴中解脫出來,以耳代目[22]。“這種新式的會說話的書本之發明,將使世界上節省了許多錢,因為向來盲人學校所用的凸板書籍,都可廢棄了”[23],事實上,有聲書并不能完全取代凸板書,但其對于盲人社會事業的特殊價值,很快也得到了其他國家的注意。
在達雅氏的實驗成功后,美國國會即開始籌備有聲書籍圖書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從行業的角度對之進行了報道:“與業經成立之盲人圖書館相輔進行”[24]。1934年的《攝影畫報》極力稱贊美國的這一發明,“足為盲人教育之福音”[25]。《科學畫報》表彰這種“有聲書籍之造福于盲者,不但輔導他們能受教育,更因它貸價低廉,使一般盲者均可聽到任何現在通行的科學書籍”[26]。1935年2月17日,天津大公報以《有聲書籍 英議員嘉惠盲人》為題刊登路透社電,《浙江圖書館館刊》于同年轉載這一消息:“英國保守黨盲議員法萊賽,今日在下院詳述其近所發見供盲人用之書籍,法如留聲機唱片,而用電氣司動,每片兩面,各可旋轉三十二分鐘,而成發聲之書籍、長小說一部,可以八片畢之。法萊賽預料,不久可設立發聲書籍之圖書館云。” [27] 1937年,《科學畫報》報道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擁有的“談話機”,也就是有聲書的播放設備:“這種機專供盲人欣賞文學,而無復雜的布來利制之煩。把整部的書灌音于唱片,不論單獨或團體盲人,多可以用耳聽書而無需用手摸字。這種機器和唱片,美國國內各圖書館均可借用,無需納費。每年制此項唱片的費用約需75000元美金,制成唱片書約165種。此種書上自舊約圣經,下至最新出版的小說,無所不包,平均一部小說需灌唱片兩面約15張。”[28]
談話機這一譯名應是基于英文的talking book-reading machine而來,但正如Matthew Rubery所論,talking book是一個不當的名稱,因為有聲書既不會談話,也不是印刷出版物[29]。及至1948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已有25000具談話機,借閱方式、期限和普通圖書一樣,并提供免費有聲書唱片郵寄服務,平均每部書需唱片兩面約20張,一分鐘約165字[30]。由此可見,有聲書在發明后,在較短的時間內即奏實效,給盲人教育帶來了實質性的變化。
隨著新的容量更大的媒介的出現,有聲書的存儲所需的物理空間愈小。1945年的一篇報道稱,“美國盲人協會主席奇格勒博士已制就了有聲書一套,該書用一種化學線軸安置在特造的放聲機上,即可發音。密爾女士所著長篇小說‘隨風而去,僅用線軸兩個,便可以一字不漏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朗誦完畢”[31]。文中提及的“隨風而去”,就是現在為大眾所熟知的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創作的長篇名著《飄》(Gone with The Wind),全文共計423575字,當時完整誦讀僅需兩個化學線軸,相較于黑爾志活字留聲片“數片即可容納十余頁之文字”,美國國會圖書館談話機“平均一部小說需灌唱片兩面約15張”,可謂巨大的進步,足見有聲書發展的可能性。
中文介紹文章側重于有聲書發明的基本事實和原理,并充分肯定有聲書對于盲人社會事業的價值。當時英文報紙中報道的社會團體為推廣有聲書所做的積極努力、有聲書的公眾展示、街區向盲人住戶派發有聲書等內容[32],并未得到中文介紹文章的注意。另外,英文報道深入探討了有聲書是否存在版權問題,以及有聲書是否會使人慵懶而無法進行深入學習[33],以及有聲書的內容審查、聽眾隱私等問題[34],也未能得到當時的中文介紹文章的關注和討論。
4 余 論
綜上所述,利用聲音形式錄制書籍內容,使瞽者能以一定的形式與乎文章之觀,體現了技術作為人的存在方式,以人為中心的指歸。在有聲書的早期發明史上,黑爾志和達雅氏等人的活字留聲片、有聲書唱片因采取了不同的路徑,而在社會接受和運用上迥然有別。后者尤為可貴的是使盲人獲得無待的自由感,以及與健全人一般無二的平等感受。他們倚仗自身先天的聽覺能力即可掌握信息、學習知識,而盲人的聽覺本身較為發達[35]。因而,有聲書的以耳代目,不只是對盲人缺陷的彌補,也是對其特長官能的發揮。
就像電話、打字機的發明史都與對殘障人士的關懷有一定關聯一樣,媒介義肢所具有的正面意義應當被肯定。而麥克盧漢所說的一種媒介以另一種媒介為內容,運用到有聲書這一媒介上,有聲書是文字的聲音,即倚仗聽覺的有聲書以依靠視覺的書籍為內容。然而,在這里,媒介的“套娃”所實現的官能轉化,對于盲人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但對于先天盲目者而言也是不能拆卸的,因為先天盲目者不能由聽覺感受退回到視覺想象。從這一點上來說,基德勒所討論的1880年前后聲學、光學、書寫的技術分流,人分裂成生理結構和信息技術[36],亦非完全非人的、機器的。
有聲書的發明不僅為盲人的學習、娛樂等活動帶來了極大便利,也為一般人提供了新的學習、娛樂方式。早在1933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就曾制造精致的有聲書模型在芝加哥展示。這種有聲書乃是以圖畫為主要內容,幾乎沒有文字,對圖畫的解讀則以聲音形式出現,時長兩分半鐘,然后頁面再次翻動[37]。雖然,最初有聲書發明的靈感來自為盲人服務,但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它所具有的更為廣闊的市場前景。
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網絡時代的到來,有聲書也承載了越來越多的內容,惠及更多聽眾。從有聲書早期發明的諸種嘗試和如今的廣泛運用來看,物欲相持而長。為盲人服務是有聲書發明的靈感來源,技術提供了滿足這一目標的條件,但技術發展并不會限于這一單一目標,而最終惠及更多人。在這一過程中,有聲書作為技術發明的合規律性、合目的性都得到了伸展。
同時,在回顧有聲書發明史時,應當注意到不同的有聲書的發明路徑并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信息的存儲無論取何種形式,關鍵在于增加信息量,而縮小存儲單元和擴展存儲空間可以并道而行,同時實現。這一點,從20世紀以來傳播媒介的發展歷史來看,已經得到了證明。敗不必劣,作為一種古董技術,黑爾志的發明仍然有其意義。溫故而知新,正如齊林斯基所說:“并不是在新事物里尋找業已存在過的舊東西,而是在舊事物里去發現令人驚喜的新東西。”[38]應當視舊若新。
注 釋
[1]未著撰人.有美 [N].《大公報》(天津版),1934-05-28
[2][9]未著撰人. 有聲書籍[J].中學生,1934(49):141
[3]Edison T A.The phonograph and its future[J]. Scientific American,1878,5(124supp):1973-1974
[4]王雨.民國聲域里的課本、留聲機與廣播1912—1936[M]//倪偉,郭春林.熱風學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99-125
[5]柯政和.留聲機的利用法[J].新樂潮,1927,1(5):7-10
[6]徐應昶.留聲機[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22-25
[7][22]The Associated Press. Talking Books Will Be Issued By Library Here New Invention Will Free Blind From Use of Braille[N].? Evening star,1934-03-12
[8][24]未著撰人.美國圖書館中之有聲書籍[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4,10(1):32,32
[10][26]M.O.U. 有聲書籍[J]. 科學畫報,1934,2(7):263,263
[11][21]未著撰人.有聲書籍[J]. 時事月報,1935,12(1):6,6
[12]The Associated Press. Books That Talk To Be Used Soon Engineers Hear Sound Tomes Declared Practical at Motion Picture Meeting[N]. Evening Star,1934-11-02
[13][14][15][16][18]未著撰人.盲目者之活字留聲機[J]. 東方雜志,1921,18(10):117,117,118,118,117
[17]海倫·凱勒給威爾·羅杰斯的信,Will Rogers Says[N]. The independent,1934-12-21: Section 2, P3
[19]Dr. Hertz of Vienna Blind Himself, Invents New Method for Blind to Read[N]. The Denver Jewish news,1920-09-01
[20]Beatrice Burgan. New Reading Method for Blind Aided[N]. The Indianapolis times,1934-04-13
[23]未著撰人. 以留聲機教導盲者讀書[J]. 科學的中國,1934,4(10):438
[25]未著撰人.有聲書籍[J]. 攝影畫報,1934,10(13):3
[27]未著撰人. 盲譯員發明有聲書籍[J]. 浙江圖書館館刊,1935,4(1):23下
[28]M.M.U:助盲人的機器[J]. 科學畫報,1937,4(20):34
[29]Matthew Rubery.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alking Book[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59
[30][34] Talking Book Program Provides Literature for the Blind[N]. Evening star,1948-05-30: 3
[31]未著撰人. 有聲書[J]. 現代周報,1945,4(4):18
[32] Anonymous. Talking Book Demonstration for Blind Draws Hundred[N]. Evening star,1934-08-02: B1.? Society[N].Evening star,1934-12-04; Childrens Hospital to Have Yule Party[N]. Evening star,1934-12-13
[33] [37]Martin Codel. Talking Book Shown at Chicago[N]. Evening star,1933-06-11: 4,4
[35]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容成氏》古代圣王即以“矇瞽鼓瑟”,《詩經·周頌·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樂師一職多由盲人充任。
[36][德]弗里德里希·基德勒. 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17
[38][德]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 媒體考古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4
(收稿日期:202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