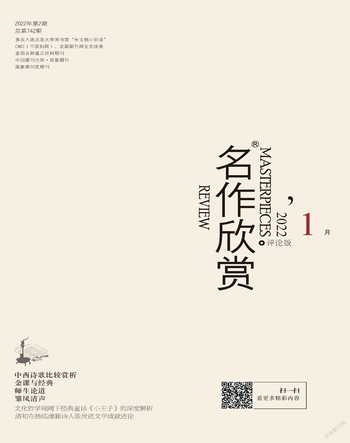紅星照耀中國 劇社功不可沒
摘 要: 在埃德加·斯諾極具預言色彩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紅軍劇社的演出呈現出質樸戲劇、政治戲劇,甚至后現代主義戲劇的多重面孔,更重要的是,紅軍劇社上演的是貨真價實的啟蒙戲劇,紅軍通過戲劇宣傳在對敵作戰中不但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而且帶給觀眾必須行動起來的新觀念,畢竟,戲劇是改變人類思想的最有力的手段,紅軍在艱難處境中不僅生存下來并且擴大了自己的隊伍,最終使紅星照耀中國,紅軍劇社提供了極具啟示意義的答案,即使在當下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預言 集體心理 啟蒙 介入
人們喜歡預言未來,正如羅素所言:“對確定性的追求是人類的自然習慣。”a當然,喜歡是一回事,但預測的準還是不準、對還是不對,又是另一回事了,畢竟“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個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質”b。所以我們往往被告誡,不要預測時事,不要預測未來,羅素甚至把人類預測未來的習慣稱之為一種“智力惡習”,因為任何對未來的預測,都是建立在我們已有知識、現實狀況之上的,而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無限的,現實是不斷發生變化的,總會有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從而導致我們的預測破產……這樣看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可以說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1936年6月,正當蔣介石宣稱準備消滅紅軍的時期,斯諾踏上了訪問紅區的非凡旅程,此行深深地影響了斯諾的一生。在此之前,斯諾雖然已在中國生活、工作了大約八年的時間,但他從來沒有見過紅軍,甚至弄不清楚他們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因為“經過九年的內戰,中國紅區更加成了‘未知之地’”c。斯諾具有驚人的洞察力和敏銳的分析力,他是在中國紅區進行采訪的第一位西方新聞記者,《紅星照耀中國》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d。因為在斯諾寫《紅星照耀中國》之前,有關紅軍的第一手材料十分缺乏,駐中國的西方記者都依賴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報道,而國民黨政府把紅軍妖魔化,稱紅軍是“土匪強盜”,就連斯諾本人也是在去了紅區之后才徹底拋棄了所謂“土匪強盜”之類荒誕的說法。我們說《紅星照耀中國》忠實,那是因為斯諾和中國共產黨并沒有什么關系,而且斯諾從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他所要做的,按他自己的話來說:“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e在《紅星照耀中國》的結尾,斯諾用冷靜而又充滿先知般的文字這樣寫道:“中國社會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終于會獲得勝利……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的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后野蠻暴政投入歷史的深淵。”f斯諾預料到可能會有讀者認為他的這個結論太令人感到刺激和驚惶(斯諾的預言今天早已變成了現實),他的解釋是:“在預測的領域里,主觀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躍的”g,并以此結束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當然,作為一部充滿先見之明的紀實性報告文學,書中充滿預言色彩的文字并不僅僅出現在《紅星照耀中國》的結尾,比如在第三篇“在保安”的最后一節“紅軍劇社”,斯諾筆鋒雄健而又充滿先知先覺,而這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內容。
斯諾筆下的紅軍劇社,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與眾不同,甚至有些標新立異的劇社。它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劇場是用古廟(或集市、鄉間地頭等)臨時改建而成,觀眾眾多,身份各異,有士兵、騾夫、木工,有被服廠和鞋襪廠的女工,也有拖兒帶女的村民,另外,還有毛主席、洛甫、林伯渠以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所有這些沒有文化、半有文化和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觀眾都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關注自己身邊究竟坐著的是誰了。演出大約持續一個多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有些類似于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主要成分是歌舞和小品(短劇),但有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劇中的宣傳色彩是一目了然的,但優點更是顯而易見,那就是取材于當下的現實生活、時事政治,我們挑選幾個有代表性的節目簡單地說一下:第一個短劇是以1931年滿洲一村莊為故事背景的《侵略》,前幾幕主要劇情表現的是日本軍人在中國的為非作歹,包括污辱中國女性、強買強賣等,地點分別是村民家中、農村集市,劇終是日軍的暴行終于使村民忍無可忍,不論男女老少紛紛拿起菜刀長矛,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戰到底。這個短劇的臺詞全部使用本地方言,演出生氣勃勃,幽默風趣,觀眾跟隨劇情時而哄堂大笑,時而對日軍的暴行發出咒罵,短劇結束時,一位年輕戰士在觀眾席中站了起來大聲高喊:打死日本強盜!打回老家去!他的行為感染了全場觀眾,結果使全場觀眾產生了共鳴,都起身高喊他的口號,斯諾后來了解到的事實是:這位戰士家在東北,日本士兵殺死了他的父母。接下來的是由十幾個年輕姑娘表演的《豐收舞》,還有動員抗日的舞蹈《統一戰線舞》以及展望未來的《紅色機器舞》,在演出的過程中,觀眾也有機會成為演員,即興為大家表演節目,這樣的機會讓斯諾趕上了,使斯諾感到手足無措的是,熱情的觀眾要求作為外國新聞記者的他現場獨唱!斯諾覺得面對這些斗志昂揚的觀眾,如果他能唱一首《馬賽曲》那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可他情急之下偏偏就是想不起這首歌是怎么唱的了,只好拼命在腦中檢索自己會唱的歌,最終用一首莫名其妙的《蕩秋千的人》蒙混過關。這次演出的最后一個節目是兒童合唱的《國際歌》,演員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這是斯諾觀看的一次紅軍劇社演出的主要內容,雖然演出道具極其簡單,節目也談不上多么精美細膩,但觀眾熱情地參與了演出,他們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肉身,還有最真實的別人看不見的內在自我,因為“每一個觀眾成員帶給戲劇表演的背景因素就是他們各自的記憶和經驗”h,任何舞臺上能夠勾起個人記憶的事物都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沖擊。如果我們以劇評人的眼光去審視這次演出的話,我們可以看出它是質樸戲劇(或貧困戲劇)、政治戲劇、后現代主義戲劇的其中之一或三者任意排列組合。說它是質樸戲劇,那是因為紅軍劇社的演出條件十分簡陋,可以說很少或幾乎“沒有化裝,沒有別出心裁的服裝和布景,沒有隔離的表演區(舞臺),沒有燈光和音響效果”i,但卻有著演員與觀眾面對面的交流,這種面對面的交流凸顯了戲劇的本質:戲劇是發生在觀眾和演員之間的事,其他都是補充品,可有可無,無關緊要。說它是政治戲劇,那是因為紅軍劇社的演出主要圍繞著政治理念、政治事件而展開,具有極強的黨派傾向,“它可能攻擊一個目標,可能擁護某一事件,或用諷刺的方式揭露作者認為有問題的政權和處理問題的方式”j。是的,紅軍劇社是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宣傳抗日主張而存在的。說它具有后現代主義戲劇的某些特征,那是因為紅軍劇社的演出做到了雅俗共賞,畢竟這些短劇出自成仿吾、丁玲這些當時中國最出色的劇作者之手。另外還有模糊舞臺和觀眾區的現象,比如斯諾既是觀眾又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演出,他所在的位置既是觀眾席又是表演區,但就是這樣混合型戲劇卻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感染力。
作為紅軍劇社社長的危女士向前來采訪的斯諾介紹紅軍劇社以及那種匪夷所思的演出盛況:不僅村民們不畏遠途前來觀看,當紅軍劇社駐扎的地點與白區距離較近時,國民黨士兵也私下偷偷加入到紅軍劇社觀眾的行列,于是就出現了一種讓人感到荒誕的景象:“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的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了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紅軍了。”k也就是說,紅軍劇社通過戲劇宣傳達到了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做到了戰爭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對此,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曾這樣分析到:“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l勒龐繼續解釋說:“一個異質性群體(即由不同成分組成的群體)會表現出一些與同質性群體(即由大體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級或階層組成的群體)相同的特征。”m勒龐認為:最能活靈活現反映人物形象的戲劇表演,總是對群體有巨大的影響。的確,那些試圖影響人類思想的人們很早就認識到,“戲劇是進行這種嘗試的最有力的手段”n。戲劇為何是影響人類思想的思想家進行社會變革的最有力的手段?我們可以沿著勒龐提供給我們的視角繼續分析:相對于其他藝術之類的欣賞,不論是繪畫還是文學作品,提供給欣賞者的都是一種私人化的體驗,即便在博物館也是這樣:雖然是一大群人擠在同一幅繪畫作品之前,但他們對作品的欣賞還是私人化的。但當他們成為戲劇觀眾時,群體性的體驗是必不可少的。戲劇以及其他含有表演藝術成分的公共事件,比如宗教儀式、運動盛會和慶祝典禮,它們都有這樣的特性。當人們以這種方式聚集到一起的時候,某些似乎不可理喻的事情就出現了,“盡管每個人都是背景不同、性格迥異的個體,但是他們卻開始呈現出某種共同的特質,這種特質往往會超越他們各自的個體特性”o,這正是戲劇(劇場)的魅力和魔力所在。另外,我們知道戲劇是動作的藝術,它所表達的內容與書面文字相比更一目了然,更通俗易懂,對觀眾文化水平的要求相對更低,這樣戲劇的受眾面更廣,而成功的社會變革是需要廣大民眾參與的,這也是為何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紛紛創作戲劇的重要原因。斯諾在紅區的所見所聞使他深切地意識到:“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p由于大約一共有三十個紅軍劇社,又由于這三十個紅軍劇社不停地創作、上演新的劇目,甚至把紅軍的綱領也改編成生動活潑的劇目,通過這種方式宣傳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畢竟那時的老百姓識字率比較低,書面文字的形式并不適合他們,這樣紅軍就比較容易地爭取到民眾的信任。如此說來,紅軍劇社的作用再夸大也不為過了。
從表面上看,紅軍劇社把藝術變成了宣傳,變成了工具,但從根本上看,紅軍劇社的演出本質上是一種“介入”,畢竟“只有為了別人才有藝術,只有通過別人才有藝術”q,一旦你開始創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也不論你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你都已經開始介入現實生活了。紅軍劇社的演出只不過是在1936年中華民族處于危亡時刻的一種特殊的又是極其自然的介入方式而已,而對當時中國的廣大民眾來說,藝術(形式)和宣傳(內容)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劃清界限的,內容(思想、宣傳)從來不可能是赤裸裸的獨立的存在,它要依附形形色色的“文”,這樣才能作用、影響人的生活,正如布萊希特所言:“一切藝術都是為了一種最偉大的藝術,即生活的藝術”! 8,難道不是這樣嗎?
在中國共產黨之前,知識階層更多地要努力凌駕于民眾之上,把文字和知識據為己有,以此來作為控制民眾愚昧的武器,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劇社的演出目的是在于震撼,目的是教育民眾,“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斗爭……農民階級經過兩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s。斯諾的這段文字在書中洋洋灑灑很長,但他還是意猶未盡,緊接著又寫下了這樣總結性的語句:“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回宣傳演出,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很難說,但是這很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t的確,紅軍劇社的戲劇是貨真價實的啟蒙戲劇,就像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一樣,共產黨把戲劇當作宣作自己的思想和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一種手段,使廣大觀眾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不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現在,只有中國人民自己能夠使中國勝利,也只有中國人民自己會使中國失敗,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能夠創造的,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創造這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關于中國紅軍和共產主義運動,人們提出過很多問題,事實是,在當時的世界各國中,人們最不了解、最感困惑的大概就是紅色中國了,紅軍令人難以置信地從邊緣走向中心并最終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這是如何做到的?按當時的狀況看,紅軍可以說一無所有,而國民黨部隊可以說是無所不有,但國民黨為什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呢?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的有更多的人看出了大結局,是的,戰爭打到最后,已經不再是單純戰場上的事了,是政治、民心等多種因素的較量……關于這些問題,讀者都可以從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特別是其中的“紅軍劇社”一節中找到今人滿意的答案。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當下,舞臺都擁有無限可能,戲劇都具有多元意義、永遠變化這一特征,很適合用來概括當今戲劇領域的觀眾所面對的情況:不計其數的選擇和機會,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戲劇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提供給觀眾如此之多的體驗機會,即便如此,當我們打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讀到他筆下的“紅軍劇社”這一章節時,將近一個世紀之前的演出仍能給予我們深刻啟示。
a〔英〕 Bertrand Russell, Unpopula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P38.
b 〔英〕 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許明賢、吳忠超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頁。
c 〔美〕 埃德加·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夏翠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64頁。
d 胡愈之:《〈紅星照耀中國〉中文重譯本序》,見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
e 〔美〕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見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
fgkpst〔美〕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63—464頁,第464頁,第110頁,第110頁,第112頁,第111頁。
hjo〔美〕 埃德溫·威爾森:《認識戲劇》,朱拙爾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頁,第336頁,第21頁。
i 〔波蘭〕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邁向質樸戲劇》,魏時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
lm〔法〕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第3頁。
n 〔英〕 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楊正潤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
q 〔法〕 薩特:《薩特文論選》,施康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頁。
! 8 〔德〕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丁楊忠等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頁。
作 者: 何玉蔚,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與闡釋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學與文化。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