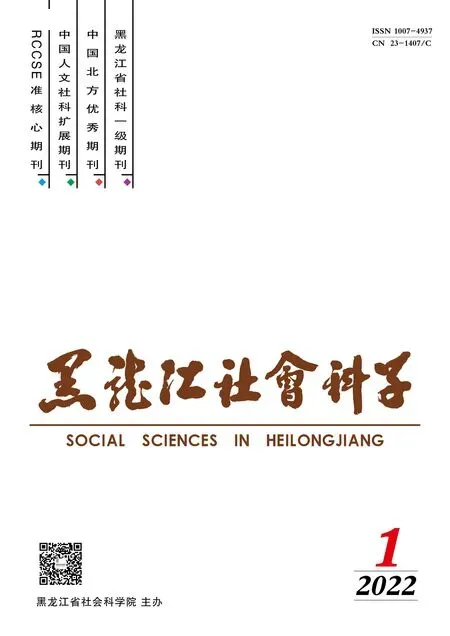吳興華擬古詩的敘事性研究
樊 嘉 亮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武漢 430079)
吳興華的擬古詩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其在力圖規范新詩形式思想指導下所創作的“絕句”詩,這一類詩具有整飭的外形、和諧的音節、仿古的意象以及深婉的情調;另一類是在其認定的想象力作為詩的本質、“理性之美”(intellect)作為詩的內容要求以及美感判定標準思想下所創作的“古題新詠”詩,這一類詩以自由體為形式,借用古代典故的故事背景,融合了古典和現代,在“化古”上表現出很強的創造性和藝術性。這些詩內容上是對古代故事的一種重新演繹,思想內涵上卻包含了很深的現代思緒。學界對于吳興華擬古詩的分析和研究,由于受到“新詩如何更好發展”問題的影響,多集中在這類詩中古典性與現代性的辨析上。在前代學人的不斷努力開掘下,明確了吳興華擬古詩仿古、化古、融匯中西、結合現代與古典的特色以及吳興華在探求新詩發展上不同于同時代其他詩人的特殊地位。隨著新詩的發展不斷推進,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詩力求拓展其書寫范疇,敘事性也作為一種新詩謀求擴大書寫邊界的手段被詩人學者引入進來,并一度成為新詩寫作、理論創建和發展研究的一門“顯學”。本文意在以吳興華的“特殊文本”擬古詩為例,以敘事性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和開掘,力圖在特殊的文本形式中,以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探尋這類詩歌尚未引起過多關注的美學意味。
一、現代性與敘事
“現代性”的敘事,可以理解為一種通過現代性手法對詩歌文本的展開與敘述。實際上,對于“現代性”的追求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尤其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經備受推崇。這里面少不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傳入和接受的推動,同時也少不了當時歷史環境下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的影響。吳興華作為那個時代的詩人,難免會受到時代的裹挾而接觸到現代主義理論。學界有不少關于吳興華對于里爾克思想接受的研究。吳興華自己也曾在文章中這樣說道:“在我未提筆之前,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關于黎爾克說幾句中肯的話是一樁多么困難的事。想起來夠多容易,他的詩篇,散文及信札多年來就是我歡樂與憂愁中最親切的伴侶,仿佛把我對它們的印象大略描述一下,就可以算盡了介紹的責任。”[1]但筆者以為,可能通過吳興華自身對于現代主義詩歌發展的關注更能說明其受到了現代主義的影響,他在1947年12月16日給宋淇(林以亮)的信中這樣寫道:“最近雜志上常登一個叫穆旦的詩作,不知道你見到過沒有?從許多角度看起來,可以說是最有希望的新詩人。”[2]其后他還和宋淇談到了穆旦詩歌語言歐化的現象,以及他對于穆旦這種英國牛津派風格突出的高等知識分子的詩能否在國內走得通的擔憂。從這一個細節上就大概能夠看出吳興華對于現代主義詩歌的關注和了解。這種關注和了解自然不只停留在理論層面,同時,在其詩歌創作之中也有很深的體現。
梁秉鈞曾指出過吳興華的“古題新詠”詩是“對眾所周知的題材加以陌生化的技法(the device of defamiliarization of well-known subject matter)”[3]。這里面就包含了兩個層面,“眾所周知的題材”以及“陌生化的技法”。這種“陌生化的技法”實際上是通過有別于傳統古典線性敘述的現代性敘述來實現的。可以說,此類詩歌在選擇題材的“古典化”和表現方式的“現代化”之間存在著一種陌生的距離感,而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恰恰就是此類詩歌張力產生的動力之源。時代沉積所產生的時間上的落差以及熟悉故事之中所迸發出的能引發現代人情感共鳴的情調,給予了“古題新詠”詩一種沉淀之中閃現出新奇的“再發現”的美感。
下面以《吳王夫差女小玉》為例進行分析,該詩采用了吳王夫差幼女小玉和童子韓重的故事為原型,原文講述了二人偶然相識,并通過私通書信相互了解互定終身;此后韓重因求學而去國離鄉,期間囑托其父母向小玉求婚,吳王震怒不允,小玉氣結身死;三年后韓重學成歸來,得知小玉已然身死,去其所葬江邊悼念的完整故事。
在敘述策略的陌生化表現上,首先是重新調整敘述結構從而造成敘述的陌生化。原故事是一個有起因、經過、結果的整體,而在吳興華的詩中,省去了故事的起因和發展過程,直接將故事發生的地點限定在江邊,將原故事中的高潮和即將到來的結局作為詩歌敘述的主體情節。詩的開頭便是:
他們倆相遇在大江日夜的流聲
沉落的地方
這就將原來紛雜變換的場景和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同時原故事中預設的敘述視角很高,而且是客觀中立的視角,并在此視角下安排二人相見后以對話的方式互訴衷腸。而在吳興華的詩中雖然有對于小玉的描寫,但大都停留在動作和體態上。同時詩人刻意把敘述視角推得很低,并主要框定在韓重一人身上,通過對韓重心理和情緒的精致刻畫來從側面展現出二人之間的情感羈絆和命運對于二人的捉弄。更有意思的是,在詩中二人自始至終沒有直接的語言交流,有的只是二人的動作的描寫以及韓重細致的心理和情緒變化的刻畫。這種無言的展現毫無疑問地加強了詩歌所展現出的故事的悲劇化效果——所有的悲涼凄惻、所有的苦楚壓抑都被埋沒在了這沒有對白的無言的敘述之中,只有“遠處大江聲,狗吠著山下的行旅”。也正是這樣全新的故事編排和敘述使得原有的為人熟知的故事成了詩歌敘述的背景板,既定的舊有期待視野被新的故事敘述和編排打散、重組,使得讀者在接受之時有了獲取新期待的可能,也給予了這首詩一種敘述結構上的“陌生化”。
其次,以情感流動的敘述代替故事情節的敘述從而營造出陌生感。吳興華的詩歌敘述過程中幾乎完全拋卻了原有故事的完整情節,而把關注的重點集中在了小玉同韓重的情感流動上,尤其是對韓重的心理進行了細致地刻畫:
在他腦子里頻頻敲擊著的思想,
臨近于恐怖,卻更臨近于失望:
……
或許死亡并不是,如他所夢想的,
一切生命的最高點,完滿的終結。
這樣,故事的推進就不再依照傳統敘述中情節發展的邏輯一步步推進,而是依照人物情感和心理的變化起伏來發展。隨著韓重情感上對于小玉的思念,對于現實的恐懼、失望,對于小玉離世的悲傷,以及對于過去美好時光的留戀,最終推動了情節向著二人再度相認并攜手步入墳墓的結局發展。情感從某種程度上代替情節作為敘述的主線,使得這首詩整體上有了一種幽怨悲傷的氛圍和基調。雖然仍然是在講述一個愛情故事,但敘述手段的不同,使人感覺到這是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愛情故事。通過細微的情感和心理敘述,作者想要展現給讀者的一種全然不同于原故事的、符合現代人審美預期的、新的情緒,是那種散發著濃重現代主義氣息的、有關愛與死亡的思考。這種思考可以說是吳興華的一種對現代情緒的內化,也可以認為是其受現代主義影響在詩歌的旨趣上選擇了“理性化”的方向。也正是由于這種情感敘述同現代情緒的結合,創造出了一種敘述上的“陌生化”效果。
再次,通過有意抓住某個細節并延長敘述時間的敘述手法營造陌生化。萊辛在《拉奧孔》之中闡述了藝術創作在有限篇幅內選取表現時間的原則:“既然在永遠變化的自然中,藝術家只能選用某一頃刻,特別是畫家還只能從某一角度來運用這一頃刻;既然藝術家的作品之所以創作出來,并不是讓人一看了事,還要讓人玩索,而且長期地反復玩索;那么,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說,選擇了上述某一頃刻以及觀察它的某一個角度,就要看它能否產生最大效果了。最能產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讓想象自由活動的那一頃刻了。”[4]這樣的藝術裁剪和加工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更好地展現作品的藝術性。吳興華對于原有文本進行裁剪和再編排也是為了能夠突出其想要發掘的精神內涵。同時由于受到了里爾克的影響,其創作還出現了一種有意抓住某個細節并延長敘述時間的特點。他在文章中以里爾克的《奧菲烏斯·優麗狄克·合爾米斯》為例,表達了這樣的藝術傾向:“這個故事,像許多其他的希臘神話一樣,幾乎像是生來就是為作詩的題材而設的。但是它‘最豐滿,最緊張,最富于暗示性’的一點到底在哪里?恐怕大家所見不見得相同。粗粗看起來,似乎奧菲烏斯在地界王面前奏琴那一段最為感人,但黎爾克拋棄了這顯而易見的一點,而選擇了這短短的一瞬:在奧菲烏斯將要回頭而尚未回頭時。在這短短的一瞬里,他放進了整個故事。”[1]在《吳王夫差女小玉》這首詩中詩人就花了兩節二十多行的篇幅著重描繪韓重再次見到小玉時的心理變化和情感起伏。從最初的恐懼、失望到深深的悲傷,從暫時擺脫強烈情感的沖擊到再度陷入了回憶的泥淖,眼前小玉和記憶之中小玉的對比產生的虛幻感令韓重錯愕,也使其一時間陷入了對于生與死的思索。這種對于敘述時間的延長處理,突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形成了人物情感波動上的張力表現。將故事的焦點集中在了詩人想要展現給讀者的“美妙的瞬間”之中,并通過這一精心選擇的焦點瞬間將詩人對于整個故事敘述的匠心營造展現在讀者面前。在放緩了敘述節奏的同時也使得詩歌情感的節奏驟然加快,一快一慢之間產生的戲劇性張力也使得詩歌的敘事充滿了一種現代氣息十足的陌生感。
最后,吳興華“古題新詠”詩在敘述上所展現出的陌生化實際上是一種以真實性為前提的陌生化。在什克洛夫斯基闡述“陌生化”理論的文章《作為手法的藝術》中,對于“陌生化”的本質有著這樣的闡述:“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就是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顯出石頭的質感。藝術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我們可以將這段話總結為兩個方面——藝術的真實和手法或形式的困難。這就是說,究其根本,“陌生化”的目的還是要“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顯出石頭的質感”,是要追求一種藝術上的真實。“陌生化”手法的運用與展開也脫離不了對于事物的真實描寫。那么我們再回到這首詩上來,這首詩的結尾相較于原故事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改動。原故事是“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宴三日之夜,盡夫婦之禮”。如果詩人完全按照原故事進行再加工,在故事發展和敘述邏輯上似乎沒什么不妥,但是這里面卻又隱隱存在一種與現代價值不相符的情況,如果“夫婦之禮”出現在這首現代詩里,未免會產生一種違和感。這就是由于時代的變化,價值觀也相應產生了變化,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的行文邏輯和價值導向進行改寫,難免會出現“不真實”的感覺,既不符合現代人的價值取向,又和全詩的基調明顯相悖。所以詩人在這里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敘述:
墳墓緩緩的張開他石頭的牙顎,
吞食下他倆,只余下蠟淚和殘灰。
這種處理,在保障了作品藝術真實的同時延長了讀者接受過程中的審美感受,交代了故事結局的走向又給了詩歌融合古典審美的“留白”延伸,從而完成了藝術上的真實性和形式上的陌生化。并且,也使得現代人的現代感官和現代思想同古典故事很巧妙地融為一體,形成了一種具有張力的“現代性”敘述。
二、形式與敘事
這里說到的“形式化”敘事實際上更偏向于形式對于詩歌敘述的影響這一層面。如果我們把形式也看成是詩歌敘事的一個重要層面,那么毫無疑問,不同的形式的選擇會對哪怕是相同的詩歌題材的內容和敘述產生不同的影響。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在新文學革命的初期,作為新詩倡導者之一的胡適如此看重詩歌的形式開拓,并提出“詩體大解放”的口號,力圖打破舊有形式加在中國詩歌上千百年未變的束縛。因為有了“詩體大解放”,新詩才沒有形成統而劃一的形式,而也正是因為新詩未能像古典詩詞那樣形成一套或幾套固定的形式,新詩的形式問題就成了一直伴隨著新詩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
吳興華的擬古詩包含兩大類,其中“絕句”一類的詩歌就體現了吳興華對于新詩形式規律建設的一種嘗試。吳興華的“絕句”詩每行固定為十二個字,分為五音步,第一、二、四句押韻,音步相等,不講求平仄。與傳統古典五七言詩相比,在格式上不那么嚴謹,但大致遵循了古典詩歌的格律原則。此外,他吸取了“五四”以來對于音組的實驗改良結果,運用音節組合來停頓,在詩歌內部帶來一種節奏的變化。這就使得“絕句”形式寫成的詩歌形式齊整、結構緊湊、音韻和諧、意象幽婉,有著非常濃重的古典氣息。下面以林以亮、卞之琳和張建松分別在文章中提到過的吳興華的同一首詩歌為例來說明:
絕句
仍然 等待著 東風 吹送下 暮潮
陌生的 門前 幾次 停駐過 蘭橈
江南 一夜的 春雨 烏桕 千萬樹
你家 是對著 秦淮 第幾座 長橋[5]
經過林以亮的斷句我們不難發現,在這首詩中絕句的形式為詩歌的敘述提供了很好地幫助,在清楚的節奏、和諧的音韻帶動下,詩中的意象、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以現代漢語為語言基礎,又同時兼有強烈古典風格韻味的特殊詩篇。中國香港學者馮晞乾認為,這首詩的原型來自于明代林初文的詩:“不待春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馮晞乾同時認為,相較于林詩,吳詩是對其的一種富于創造性的誤讀,他認為這首簡短的詩中包含了詩人吳興華四層詮釋:化用七絕形式寫一首古香古色的新詩;依照舊詩傳統“次韻”一首渡江名作;既要對原詩亦步亦趨,又要改頭換面,改換詩文主旨意趣;這種創造性的誤讀是在新的時代和語言環境下對于古典詩詞傳統的一種有益的延續[6]。馮晞乾的解讀實際上也是由表及里、由想象到本質的,正因為有了相應的形式,才能以此為基礎展開詩歌敘述進而升華詩歌的內涵。所以可以這樣說,由于形式的特殊使得“絕句”類的擬古詩在敘述中產生了一種古典化的敘述節奏,也使得吳興華的“絕句”詩有了不同于其他形式新詩的深厚古典主義色彩和韻味。
同時,由于字數的限制,像古典五七言近體詩一樣,為表達一種特定環境下的特定事件,也是為保證在有限的篇幅內包含更多的內容,用典和大量引入相關意象成為了這類詩歌一種必不可少的敘事技巧。高友工和梅祖麟就對近體詩用典的必要性作出過這樣的分析:“近體詩的最大容量也只有七言八句五十六個字,在這樣短的篇幅中,很難把某一行為的動機、環境解釋清楚,而一個沒有環境和動機的行為,就不能算是道德行為,這樣,近體詩的作者在表現道德行為時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更加尖銳。然而,典故的運用使本來不可能的事成為不必要的事:由于環境、動機、人物關系等背景材料都已蘊含于典故之中,詳細的解釋就被簡略的暗示所取代。當提到某個歷史人物或地點時,所有與之相關的意義和事件都會隨之俱出;而當典故運用于現實的題材之中時,就為道德行為提供了活動的環境。”[7]以單音節詞為主且未在詩行中加入大量虛詞的文言文尚存在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在以雙音節詞和虛詞大量介入從而拉長了句子長度的現代漢語作為語言基礎創作時,要滿足每一句都限定在十二個字,這種技巧就顯得更為重要。如這一首:
絕句
尚記得行吟澤畔憔悴的孤臣
國家有如此烈士怎能夠沉淪
驪山一火竟不滅離騷的光耀
阿房三月終伸復武關的怨心
垓天美人泣楚欲定陶泣楚舜
沛中高帝的大風,汾上的白云
詩篇慷慨更不慚流傳下萬古
飲水思泉時還須俯首對靈均
這首詩中就包含了很多典故,諸如屈原行吟、火燒阿房宮、垓下之圍、四面楚歌、劉邦賦《大風歌》等等,幾乎每一句中都有古典意象或是人物典故的加入。雖然整首詩讀起來依舊音韻和諧、節奏清晰,但是在如此繁復的意象和典故的加持下令人有些目不暇接。如上文所言,想要用詞匯音節更長、句法結構更加嚴密、句式較文言文更長的現代漢語在每行一定的字數內表達更多的內涵,這種敘述手法是不可或缺的,但固定字數詩句的承載力終究有限,加入了太多內容就會讓人產生不堪重負的感覺。過多的典故意象安排不僅會打亂敘事節奏,也會影響作品整體的藝術美感。也正如卞之琳所分析的那樣:“在一首新詩的有限篇幅里實在容不下那么多意象,擁擠了一點,少了一點回旋余地……少了一點中國詩傳統常見的一種雍容或瀟灑的風姿。”[8]雖然這種形式的詩歌在敘述之中會存在意象典故過于繁復的問題,但是這種嘗試依然是一種溝通新與舊、古典與現代的有效途徑,也為新詩的發展,尤其是新詩的形式建構提供了一條可供借鑒的道路。
吳興華重視詩歌形式的原因是他認為“形式仿佛是詩人與讀者之間一架公有的橋梁,拆去之后,一切傳達的責任就都是作者的了。我們念完了一行詩,絕沒有方法知道第二行將要是多長,同時也不知道第二行將要說甚么東西,因為新詩現在越來越‘簡潔’了,兩行并列時,誰也看不出其間有甚么關系”[9],同時他認為一定的形式,并不會影響詩意的,反而有時候會更好地表現詩歌的內涵,并舉例說明,“當我們看了像‘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春如短夢方離影,人在東風正倚欄’、‘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等數不盡的好句之時,心里一點也感覺不到有甚么拘束,甚么阻止感情自然流露的怪物。反之,只要是真愛詩的人立刻就會看出以上所引的諸句,和現在一般沒有韻,沒有音節,沒有一切的新詩來比時,哪個是更自然,更可愛。”[9]這可能是形式帶給敘述者的一種便利,但這種便利同時又需要作者和讀者產生一定的默契。
在吳興華看來,正是由于新詩失掉了舊詩那種形式上勾連起作者與讀者的“紅利”,使得詩人、詩歌相較于舊詩而言天然地與讀者產生了隔膜。所以新詩人在創作新詩時要更加小心,因為詩人此時肩負了更為重要的責任,這種責任在其看來是教育大眾的責任,讓讀者能在新詩之中產生新的真善美的體驗,從而一步步努力建立起以往那種溝通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橋梁。這里就又存在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依照吳興華所言,新詩不應該去求大眾化,不能去迎合大眾的審美,但是其最終想要達成的那個“新詩化”的目標卻是一種類似于古典詩詞生態環境那種晉升了的有固定審美范式并能使讀者與作者相互理解的“大眾化”。而這一切的基礎,應該就是詩歌的形式。那么在舊有傳統未完全被取代之時,古典主義的審美相較于新詩在這百年以來做過的新的嘗試,哪一個更能為大眾所接受,什么樣的“新詩化”是更為討巧的方式,想來吳興華應該并不是沒有預見到,不然他也不可能選擇一條更新傳統同時努力化古納新的折中道路。至于形式,依照上文分析,確實可以影響到詩歌的敘述,但想要以一定的形式再次達成近體詩那種溝通詩人與讀者的模式,在新詩發展到如今的地步,恐怕不只是詩人,讀者可能也并不買賬。
三、抒情與敘事
在傳統詩學審美之中就有“詩緣情而綺靡”[10]的論述。“緣情說”也和“言志說”一起被稱為中國抒情文學的傳統與美學表征。在吳興華的擬古詩中,由于深受古典詩學傳統的影響,帶有很濃重的抒情性色彩。吳興華自己也在文章中毫不避諱地提到:“事實上是中國人一提起‘詩’這個字來,就容易聯想到抒情詩,這足以珍貴的、從中國人發展到極高峰的藝術。在抒情詩的領域里,豐溢的想像力是缺不得的。”[11]在吳興華看來,抒情詩“有一個堅不可拔的古典文學的基礎”[12]。因此有研究者這樣認為:“不僅吳興華早期的詩歌幾乎都是抒情詩,即使在其詩歌寫作的過渡時期和成熟時期,抒情詩也是他進行詩歌創作的首選。”[13]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吳興華的擬古詩中又包含了很大一部分敘事意味極強的“古題新詠”類詩歌。
最早為這一類擬古詩命名的是美國學者耿德華,他將這一類詩歌稱為“敘事史詩”[14]。但這一概念卻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極不準確的。余凌(吳曉東)就認為:“‘敘事史詩’是不十分準確的概念,因為吳興華的這一類帶有敘事成分的詩作盡管大都擇取歷史上的某一人物或事件,但作者關注的不是敘事,也不是故事本身。吳興華只是在初始故事的原型中找到了一個規定情境,憑藉這個情境和框架,吳興華著力傳達的是具有鮮明的詩人主體性的感性體驗和哲理思索。”[15]解志熙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評論者稱之為‘敘事詩’或‘敘事史詩’,以為作者的主要貢獻在于彌補了現代敘事詩的稀缺。這種說法未必妥當。誠然,這些詩作確有較強的敘事性,但除了較早的《柳毅和洞庭龍女》著重鋪敘那個浪漫傳奇的故事之外,其余都是取古典人事的一點、一刻或一面而已,并且作者的心思并不在發懷古之幽情或炫耀其擬古之才藻,所以也不同于傳統的懷古、詠古、擬古之作。即使說是詠古、使典,吳興華的興趣也不在歷史與典故所蘊涵著的那些亙古常新的人生經驗與人生況味,且予以別有會心的現代性擬想與創造性重構。”[16]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提出不同意見的學者都將問題的矛頭指向了吳興華詩歌的旨趣,認為不能僅憑形式上的敘述樣貌就將吳興華擬古詩中這一類詩歌稱為“敘事詩”,而應更加關注詩歌之中想要表現的一種人生經驗和作為人的主體思考。
那么這種經驗性的內在觀照究竟屬于什么范疇呢?高友工在其文章中有這樣的論述:“抒情美典顯然是以經驗存在的本身為一自足之活動,不必外求目的或理由。它的價值論亦必奠基于經驗論上,經驗本身有何種價值,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次上來觀察:即是感性的、結構的、境界的。”[17]吳興華的擬古詩中出現了大量的內觀性的和經驗性的對于人物的心理描繪和情感描寫。對于細微心理變化的刻畫和微妙情感流動的描寫已經成為吳興華詩歌中的一大特點。梁秉鈞就把“心理洞察力(psychological insight)”以及“與眾不同的人物刻畫(unusual perspective on characterization)”[3]作為吳興華詩歌的特點。同時在主題上,如同上文提到的兩位學者所言,詩歌的主題也顯現出了極富現代主義意味的對于人生經驗的感悟和人生況味的體察。由此可以看出,吳興華的擬古詩是符合高友工所提到的“抒情美典”的范疇的。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總結,在吳興華哪怕是表面最具敘事性特征的“古題新詠”一類擬古詩中,這些詩的內涵依舊是深度抒情的。
但同時,由于現代人情感的復雜性,在詩文中想要表現出更加豐富的層次以及更加豐富的符合現代審美的內涵,在同一文本之中存在多個美學范式也是可能的:
不但兼有兩種美典是可能的,而且更須認清美典絕不限于此兩種。
這兩種(指抒情和敘事,筆者按)對美的態度好像是不可能兼容并蓄的。但事實上正因為二者是在不同層次上的解釋,因此任何人都必須視其環境而有不同程度的抉擇與適應[17]。
簡單地講,在吳興華的“古題新詠”詩中存在著外在形式上的敘事性和內在情感與旨趣上的抒情性,但如果我們深入挖掘抒情與敘事這兩者背后所代表的內涵時,可能會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如果我們將抒情理解成是一種建立在以經驗為基礎的共情性美感之上的美學原則,而且其具有很強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內驅性沖動,那么與之相對的敘事則是一種建立在以客觀現實為基礎的邏輯性美感之上的美學原則,并且其具有很強的時間和空間上的外延性沖動。這也就是說,當我們采取這兩種不同的審美范式去關照文學文本的時候,側重點是截然不同的。抒情性更注重的是主觀經驗的投射,即主觀的情感道德同投射對象之間建立聯系的過程:以一種內向發掘的遞進性推動力達成主觀經驗同客觀投射物間的統一,從而展現文本的美感。而敘事性則傾向于將投射物(客觀事實描寫)同投射的經驗分置,以一種更為跳脫的視角來審視文本的肌理運作,并通過不同客觀事物間、事件間或是事物、事件與主觀經驗間的張力來展現美感。同時,在中國的文化價值中長期以來存在著“外在的客觀目的往往臣服于內在的主觀經驗”“內向的(introversive)的價值論及美典以絕對優勢壓倒了外向的(extroversive)的美典,而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17]的現象。
這也就是說,無論是作為詩人的吳興華還是作為評論者的前代學人,都潛移默化地受到了這種文化傾向的影響。吳興華在詩作中哪怕采用了極為敘事化的外在敘述方式,其詩歌的內涵依舊有著濃郁的抒情性特質;而評論者的評論也都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吳興華詩歌更加具有抒情性的內涵而不是敘事性的形式上,甚至在為這一類詩歌命名時,不約而同地認為形式上的敘事性不足以概括這類詩歌的特點,因此不能簡單地稱其為“敘事詩”。但是實際上,抒情與敘事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隔膜,上文中也曾提到,有時作者想要在文學作品中表達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情感或者主題,或者想要給予讀者復合式的審美體驗時,這兩者同時出現在同一文本中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固然,我們有著抒情壓倒敘事的文化傳統,同時在吳興華的文藝思想之中也對詩歌的抒情傳統情有獨鐘,但這些都不影響抒情與敘事這兩者在吳興華的實際創作當中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
這種平衡表現在,敘事性作為一種明顯更具外延性和邏輯性的美學范疇,無論是作者出于什么樣的目的將其作為一種手段在文本之中運用時,文本所展現出的是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符合邏輯敘述要求的緊密結合,這種結合就使得文本在敘述上有了很好的外延性空間,可以根據作者對于文本的需要創造出合適的敘述時間和空間。反映在吳興華的擬古詩上就是對于原本故事背景以及故事發生環境的重新裁選,如在《褒姒的一笑》中,詩人就獨具匠心地僅截取褒姒因烽火戲諸侯而露出笑顏這一畫面展開敘述,省去了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對故事情節的重新編排甚至改寫以達到符合現代人審美的藝術真實性效果,則體現在《柳毅和洞庭龍女》中,原故事是柳毅聽從龍女囑托,直接前往洞庭湖請來了龍女的父親錢塘君救出了被困的龍女,而詩歌中故事在柳毅離開洞庭龍女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同時在柳毅的去向上吳興華也作了改寫:
該死!
我還不快走干什么?
用腳向馬腹一踢,
可是他糊涂了,應該往東的,他往了西……
這樣的改寫體現出了柳毅內心的糾結和躊躇,細致的心理刻畫也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
延長敘事時間、放慢敘述節奏以達到凸顯人物性格的目的,則體現在《盜兵符之前》中,詩人花了大段筆墨來演繹原故事中沒有展現出的信陵君說服如姬幫其盜取兵符的內容。同時加入了大量的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
她不言語,暫時被這新的知識
擊昏,如何在狂風與疾馳的險流中
才有真實的生命。她裹在錦繡里,真想
把一生只換一天,像他這樣的一天。
這樣的描寫增加了敘事的時間,放緩了敘事的節奏,同時也更好地展現出了如姬在和信陵君對談以后發生的變化。
而抒情性作為一種更具內向性和經驗性的美學范疇,當作者將其運用在文本之中時,文本所展現出的就是一種靈魂上與歷史上的內省和沉淀,這種向內的開掘使得文本在喚起讀者一種基于經驗積累的共情的同時也賦予了文本向更為深刻思想探尋的可能性。表現在吳興華的擬古詩上就是文本中帶有的厚重的歷史沉淀感,符合現代人審美的情感流動和心理變化,如在《褒姒的一笑》中對于周幽王見到褒姒笑顏后的心理描寫:
他覺得他的心像要跳到她手里
霎時間悲愁的空氣向四周散布
微笑出現在她唇邊。他閉上眼睛
覺到有死亡的神祇在與他耳語
柔順的卻不含恐怖,他向他傾聽。
此時的周幽王已經拋棄了作為一國之君的身份,只是以陷入愛戀的男性的身份接受了褒姒那傾國傾城的一笑。詩人如此描述其內心感觸,使其感觸和普通人別無二致,拉近了歷史人物與現實的距離,使得文本內外的情感在一瞬間達到了一種共通,體現出了一種現代的審美以及極富“理性之美”的有關國家、社會、人生、死亡、愛情等一系列主題的深入思考。而上文提到的《吳王夫差女小玉》也反映出對于愛情和死亡的思索,《盜兵符之前》則承載了家國愁思,是一種對個人和國家乃至歷史的觀照的思考。可以說,吳興華的擬古詩在把握抒情和敘事二者精妙平衡的同時,達到了古與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