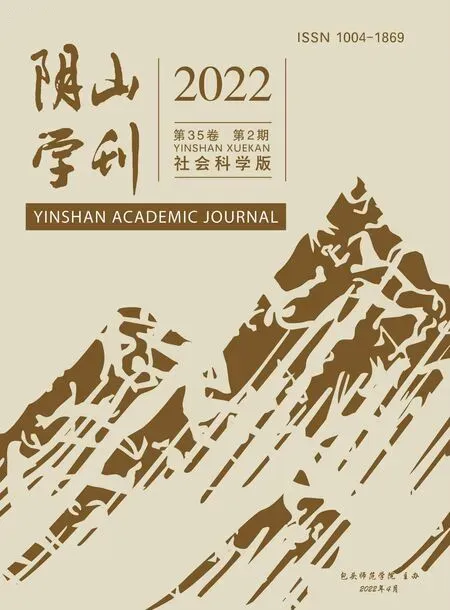“本之自然之性,為人之真性”
——論嵇康之“真”*
劉 春 娜,劉 偉
(內蒙古師范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漢代儒學至高無上的權威在士人心中不可動搖,士人從入學到入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言行都以之作為立身行事的規范和模式。然而隨著大一統政權的禮崩樂壞,正統儒學受到了致命打擊,思想一尊的局面被打破,崇尚老莊道家的玄學思潮興起,成為士人在顛沛人生中的心靈寄托。士人在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隨之發生變化,各行其是,各從所好,“真”成為一時風尚,成為當時士人心態的主流。奉行玄學的魏晉士人追求個人的真情流露,主張精神的自由解放,從而開創了一代新風氣——魏晉風度,出現了一代“風流”士人——竹林七賢。嵇康是竹林七賢的重要領袖,也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他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與藝術實踐贏得了后世的景仰,對歷代產生了深刻影響。嵇康認為“本之自然之性為人之真性”[1]18,他把“真”作為自己一生的全部追求,其任真散傲、守志如一的人格魅力,質性自然、雅逸自得的生活態度,峻切清遠、真率曠達的詩文風格,在人格、生活及文風等方面無不體現著“真”的審美本質,也彰顯著魏晉風度的精神內涵。
一、人格之“真”——任真散傲,守志如一
嵇康天資卓越,性情率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人格就為世人所推崇,他是當時被正面評價得最為熱烈的人物,一些重要文史典籍如《世說新語》《晉書》《詩品》《文心雕龍》等均有記載。其任真散傲、守志如一的人格魅力是“真”最有力的證明。嵇康任情而動、剛直耿介的性格本身決定了他真實顯露的人格之真,其為友為臣的耿直率性始終秉承著追求真我、崇尚自由的審美理想,其為父為親的真性情,在《家誡》中凝結著字字血淚的鐵漢柔情。
(一)任情而動,剛直耿介
魏晉士人堅定自我,尊重個性,表明了他們對人格獨立的確認和推崇,這是一種覺醒的人格,是其人格之真的體現。《世說新語》中記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2]347魏文帝悼念王粲時,命吊唁者作驢鳴來祭悼死者。一國之君命眾人“作驢鳴”的行為看似怪異,卻是對亡魂的真誠告慰。不顧及身份地位的率性而為,正體現了魏晉時期從上至下追求真我的風氣。嵇康在求“真”的社會風尚中,任情而動,循性而動,感情濃烈,激蕩起來難以自已。他認為人生而有情,“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3]346情感是人內心的主觀感受和反映,有著多種類型和豐富內涵,人之所向皆因情而動。嵇康指明自己個性剛烈,“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3]198,想要學習阮籍的謹慎卻學不來,“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3]197《晉書·本傳》中評“曠邁不群,高亮任性”[4]。嵇康凡事任情而動、剛直耿介的性格特征決定了他放達率真的人格魅力。
嵇康有著如龍鳳般出眾脫俗的風姿神采,“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2]335嵇康形貌卓爾不群,器宇軒昂,但卻“土木形骸,不加飾厲”[2]335,對待自己的形貌如同土木一般,“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3]196,不修邊幅。何晏“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2]333,嵇康卻在容貌審美上與世風大異其趣,以真實自然的相貌示人,不隨周遭習氣改變。正因如此,他內在脫俗的本性與氣質以及出自天然的峻切之美在魏晉時期耀眼奪目。高古率真的風度是他內在秉性與人格的自然流露,任情而動、剛直耿介的性格暗示著他自由的人格,洋溢著生命的活力。這種真實之美與虛飾浮華的世風格格不入,卻為識者所激賞,成為歷代士人效仿的榜樣。
(二)為臣為友,秉承真我
嵇康的人格一向為人們所推崇,在其眾多好友看來,他性情平和,且“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5]671《世說新語·德行》云:“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顏。所知王浚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范,人倫之勝業也。”[2]10又有王戎評:“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2]10嵇康性情平易溫和,為人寬宏大度,與他同住多年的王戎也不曾見他喜怒情緒的變化。然而遇到人生志節等大問題時,他卻是守志如一,秉承真我,不改變自己的初衷。司馬氏請他出來做官,山濤在由選曹郎調任大將軍從事中郎時,推薦他代其原職,他都強烈拒絕,并在憤慨之余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的絕交信,以“性復疏懶,筋駑肉緩……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3]196為由,拒絕山濤的邀請。在信首質問山濤:“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3]195以此表明自己心存曹魏、不愿為司馬氏俯首的堅毅高絕、堅守真我的人格。
當嵇康的朋友呂安遭到誣陷時,他堅決為友人辯護,不向現實政權表示順從。孫盛《魏氏春秋》曰:“初,康與東平安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鐘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6]嵇康作為巽安二人的好友,極力勸說兄弟和睦,“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3]231,然而巽反告安不孝,又憑借與鐘會的關系,令呂安徙邊。嵇康極為重視友情正義,秉承真我的內心,毅然為呂安在此案中蒙受的不白之冤聲辯,導致最終遇害。即便遭到不幸,他也絲毫不后悔。嵇康的人格精神給同時代的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后各以事見法……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于領會兮,寄余命于寸陰。”[7]賦中傳遞出了對友人的思念,也蘊含了對嵇康不朽人格的景仰,不由得感嘆,人生的緣分聊寄于瞬間的領會,剩下的美好就托付給短暫的光陰。即便與嵇康之交轉瞬即逝,但能夠與他這樣有著秉承真我、守志如一的高尚人格精神的士人相遇,已是莫大的緣分。嵇康直擊山濤的推薦與直面呂安的不幸,對待友人始終持以真誠、真心的態度,毫不隱晦內心真情,大膽袒露真我,秉承真我,足以體現其人格之真。
(三)為父為親,盡顯柔情
嵇康性格剛直耿介,任情而動;為臣為友秉承真我,堅守正義;作為兒子和父親,盡顯鐵漢柔情的一面,使其“真”的人格更真實豐滿,打動人心。甘露四年,嵇康聽聞母逝的噩耗,輕車快馬直奔山陽。待母親下葬后,心中悲痛難以自已,凝結血淚寫下了著名的《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嘆。感機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睹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抆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流襟。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嘆成云。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3]88
這首采用騷體的悼亡之作,有一唱三嘆之致。全詩如泣如訴,將痛失母親的極度悲慟與悼念亡親的深沉思念肆意宣泄出來,聞者悲傷,見者流淚,令人動容。慈母仙逝,無人嬌寵,只能顧影自憐,憂心忡忡,心中萬般愁緒無人可以言說。每念及此事,淚如雨下,嘆氣成云。這思念母親的悲痛綿綿無期,無法斷絕。嵇康這首悼亡詩,將悲哀抒寫到極致,與其剛毅的性格本身形成極大反差。可見其為人之真,毫不在意個人身份,真誠不避諱地吐露心靈,坦率展露真情,以表達對母親深沉的悼念,不矯揉造作,不惺惺作態。可見其不論為臣為友為親,都始終以真面目示人。
嵇康作為父親,在《家誡》一文中對子女的告誡可謂嘔心瀝血,細致至極,體現出他內心淳樸的愛子深情。在子女面前也盡顯真情,不說假話。“嵇康秉性孤傲,但教導孩子卻如此細瑣,后人總不免覺得有些詫異。”[8]76他說:“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后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3]544,告誡子女做事前要深思熟慮,并且要堅守節操遵守準則。還在其中教他們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條教訓。細微到如何與人為善,如何與長吏往來,如何言談行跡種種,可見其為父之用心用力。明人張溥曰:“嵇中散任誕魏朝,獨《家誡》恭謹,教子以禮。”[9]173魯迅《而已集》云:“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10]536《家誡》字里行間浸透著深深的無奈與悲哀。嵇康既希望兒子嵇紹要胸懷大志,又告誡他要謹言慎行,避免災禍。這與他任情狂放的性格形成巨大的反差,可見其作為父親對子女的真誠與真情。嵇康人格之真體現在他敢于直面內心與現實的沖突,對自己的率直言行不覺惋惜與悔恨,而是大膽袒露本心表達對兒女的期許。盡管個性剛直耿介,但對兒女盡顯為父柔情,告誡他們謹慎做人。嵇康本身任情而動、剛直耿介的性情以及為臣為友、為父為親的堅守真我,展露真情,這樣立體豐滿的人格精神是嵇康其人的魅力所在,也是歷代士人傳頌的焦點。
二、生活之“真”——質性自然,雅逸自得
嵇康在老莊道家思想的熏陶下,積淀了深厚的玄學思想修養,他所追求的和平寧靜的生活境界是自我制約的結果,從而形成“真”的人生態度與生活范式。嵇康喜好平靜的閑居生活,讀書作文,飲酒鳴琴,與親友閑話,縱情于琴酒之中,暢游于山水之間,質性自然,雅逸自得。嵇喜《嵇康傳》曰:“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5]671嵇康面對生活恬靜自適,返歸自然。在彈琴詠詩的雅逸生活中自足懷抱,享受瀟灑恣肆的個體生活。面對傳統禮教,有“非湯武而薄周孔”[3]198之論,又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3]402,不畏現實的壓迫與磨難,選擇遵循內心,反抗禮法。最終到達超乎生死、泰然衛道的人生境界。嵇康“真”的人生態度使他成為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
(一)彈琴詠詩,自足懷抱
嵇康喜好雅逸生活,縱情山水,在自然中覓得生活真理。他所追求的是一種恬靜寡欲、超然自適的生活,返歸自然,悠閑適意,自足懷抱。將莊子返歸自然的精神境界變為人間境界,從自然山水中汲取滋潤心靈的“精神食糧”。嵇康沒有專文闡述士人的歸隱閑居,但在不少詩中提到了隱逸生活。如《述志詩二首》其二曰:“晨登箕山嶺,日夕不知饑。”[3]62再有《重作四言詩七首》其五:“垂釣一壑,好樂一國。被發行歌,和氣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3]82在山水間瀟灑自適,或蕩舟垂釣,或被發行歌,游心玄默,雅逸自得。詩中塑造了恬然淡泊的隱逸高士形象,是嵇康本身,也是他的理想境界。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傳遞出其內心深處的真實理想:“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3]198他希望逃離世俗,不被牽絆,在大自然中享樂,回歸內心的平靜。與仕途相比,隱逸是人生的樂園與港灣。嵇康重視養生,更注重精神修養。“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4]采藥時常流連忘返,欣然醉情于其中。雅逸自適的生活是嵇康遠離官場、實現真我的人生態度與選擇。
嵇康喜彈琴詠詩,“少好音聲,長而玩之”[3]140,陶醉于自然天籟和音樂之中。長大后玩琴,成為魏晉一流的音樂家,其一生演奏和創作的音樂成就,都與琴(古琴)密切相關。嵇康常在琴聲中寄托歡憂樂懼,抒發情志抱負。善彈《廣陵散》,臨刑時顧影而彈琴,曲終音息,發出振聾發聵之長嘆:“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日絕矣!”[4]世皆悲痛。廣陵散盡,余音裊裊。這首樂曲在嵇康指尖傳遞出強大的生命力,蘊含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嵇康將他對音樂的熱忱譜寫成一部部論述著作,如《聲無哀樂論》和《琴賦》等重要的音樂理論文章,都在音樂與文學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價值。嵇康從儒家大一統思想的禁錮中解脫出來,找到一條獨特的解放心靈的道路,從雅逸的現實生活以及音樂與詩意的理想境界中探求人生的自足,追尋心靈的真我。“嵇康的意義,就在于他把莊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間化了,把它從純哲學的境界,變為一種實有的境界,把它從道德境界,變成詩的境界。”[11]103
(二)反抗禮法,復歸自然
嵇康有“非湯武而薄周孔”之論,又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與名教完全對立。他是反抗禮教的斗爭者,是復歸自然的倡導者,在“越名任心”思想的倡導下探尋真我。“嵇叔夜以宗室聯姻,一拜中散,便無意章綬者,誠見主孱國危,不欲俯首司馬氏耳。故山濤欲舉以自代,輒與絕交。”[3]228嵇康在與被司馬氏操控鼓吹的儒家名教之治以及利用禮教篡權奪位的行為相抵抗時,心存曹魏,與司馬氏格格不入,由此提出“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論述。這是他求真的生活態度,但在時人看來卻是他的政治宣言,也是不屈服的標志。山濤在司馬集團深受重用,因此希望好友嵇康也可以通過入仕一展抱負,而嵇康卻嚴詞拒絕山濤的推薦,并指出他不懂自己厭惡官場的心態。他希望能夠“徹底擺脫外在標準、規范和束縛,以獲取把握所謂真正的自我。”[12]176嵇康強烈地反抗禮法、厭惡仕途的人生選擇中,展現出他那超乎常人且出淤不染的高潔品行,他以追求真我為傲,以混跡仕途為恥,其中蘊含著嵇康桀驁的人生追求:保持真我,不隨俗世而變。
竹林七賢等人在思想上大多主張“任自然”,在嵇康身上則更為顯露。他在《釋私論》中說道:“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3]402這里所說的“自然”不同于自然界的概念,實際上是老莊玄學的發展與補充。嵇康認為堅守本心與復歸自然就是人的真性情,這正是繼承了莊子“貴真”的哲學思想。嵇康復歸自然的主張受到了羅宗強先生的肯定:“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認認真真地執行了的,分毫不爽。這樣認真,這樣執著,就使自己在整個思想感情上與世俗、特別是與當政者對立起來,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處于社會批判者的立場上。”[11]120作為魏晉士人的典型代表,嵇康的主張和言行代表著當時崇尚玄學的士人的情感和文化傾向。要求世人順應自然的本真性情行事,守住內心的質樸,超越名利,任心而行,不論身居何處始終保持純真本性。嵇康正是將返歸自然的理論踐行為一種人生觀,從而實現“真”的人生選擇。
(三)超乎生死,泰然衛道
嵇康風姿特秀,超塵脫俗,“潁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4]潁川鐘會拜訪嵇康,康不為之禮,會懷恨在心,后因呂安之事,向文帝進讒言:“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4]文帝便借此除掉嵇康。嵇康在赴刑之時,神氣自若,全然置生死于度外,表現出堅毅高絕的人格和將死亡視為解脫的生活態度。唯一讓他牽腸掛肚的是一雙兒女,強忍悲痛寫下《家誡》,寄寓濃濃的舐犢深情。嵇康用生命和靈魂演繹出了一種從容,一種風骨,一種超然境界。山濤稱贊他“巖巖若孤松之獨立”[2]335,指的就是嵇康品質中獨立孤傲、直面生死的人生態度。只到生命終結的那一刻,仍然堅守自我本心,將轉瞬的人生和渺小的身軀與廣闊的時空冥合永存,實現真我的人生價值。
老莊道家思想是魏晉玄學發展的基礎,是魏晉士人堅守真我的心靈紐帶。玄學思潮由于現實的需要而出現,指引士人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問題。它“給魏晉士人帶來了一條走出禮教束縛的路,魏晉士人自己開拓了一片天地:他們忘懷世事,適己縱情,不受任何約束。”[13]110嵇康的道,是玄學之道,是個性指引下的心靈解放和自由。他為了維護個性和真我,將玄學轉變為一種人生觀。“但是由于它沒有解決個人對社會承擔的責任,它之注定為社會所擯棄,也就勢在必然。”[14]159從而造成了嵇康衛道者的悲劇。即便如此,他仍堅守自我,泰然衛道,毫不畏懼與退縮。“玄學的發展至此深入到自我意識和精神境界的問題中來了”[15]7,這是衛道者的堅守,是自我意識和自我精神的覺醒。在簡傲任誕的人生中,借率性耿介的言行實現情感的宣泄,以達到反對禮教、維護個性的目的,亦是嵇康自由灑脫、追求真我的人生美學的踐行。
三、文風之“真”——真率曠達,峻切清遠
作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多面性天才之一,嵇康在詩文、音樂、書畫等方面都有著極為深厚的造詣,體現出他與眾不同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追求。嵇康任真散傲、守志如一的人格魅力與質性自然、雅逸自得的生活態度共同構建了他真率曠達、峻切清遠的詩文風格。曹丕“文以氣為主”[7]對人格與風格的關系進行理論闡釋,指出作家的個性和才能決定了作品風格,同時又會通過作品展現出來。因此,嵇康人格之“真”與生活態度之“真”決定了他“真”的文風。作為魏晉時期重要的文學家,嵇康的詩文創作一直受到世人關注。其詩現存五十余首,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和雜言等,其中數量最多且成就最高的是四言詩。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16]60“清峻”文風是嵇康之“真”在文學作品中的展現與印證,在情感、意象和語言等方面體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與文學造詣。
(一)情感:率直曠達,袒露真情
嵇康詩文創作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在“清峻”的作品中顯露出其人格與人生的真率曠達,他用全部的生命激情和峻切之氣,表現出強烈的抒情性和個性色彩,將真情毫無保留地袒露在世人眼前,留下深刻的烙印。嵇康詩文中以直言不諱的姿態傳遞出其人的獨特思想與個人真情,與七賢中其他人隱而不顯的創作風格有所不同。鐘嶸“尚雅”,故在《詩品》中評嵇康詩“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17]113,指出其語言和情感過于嚴峻激切,橫議是非,露才揚己,而這正是嵇康詩文得以流傳的重要原因——“真”。嵇康鮮明的個性特征與性情共同造就他峻切清遠、真率曠達的文風。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組詩中,嵇康描繪了一個理想與現實相交融的隱逸生活,詩中寄寓了詩人對山水田園隱居生活的憧憬與向往,如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3]20
嵇康筆下孕育出茂密樹林、習習微風、悠揚琴聲、唧唧黃鳥等愜意的自然景象,這些圖畫共同構成了嵇康的理想世界,形成了一個清新曠達的審美境界。“嵇康如此贊美隱逸生活,與其說是因為他喜愛隱逸生活,不如說是因為他極端憎惡污濁的社會現實,有以自己的高潔顯示世俗之污濁的意向。”[18]15從詩文中可見其情感之峻切,看似一味追求隱逸生活,實則飽含不屈于世俗的高尚節操。如《幽憤詩》中“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3]42,詩人借《左傳》之典故表明心志,言己生性容不得邪惡,呈現出強烈反對司馬氏集團的政治態度。再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更是以峻切耿直的言辭“手薦鸞刀,漫之膻腥”[3]196“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也”[3]197等直言對現實的不滿。嵇康思想新穎,不墨守成規,在詩文創作中對傳統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往往提出振聾發聵之新解,如“頑兇不容于明世,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也。”(《管蔡論》)[3]421嵇康超越善惡,全面體察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認為管蔡并不是叛逆者。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指出:“嵇康的論文,比阮籍要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10]533其詩文中這樣閃光的新論在魏晉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熠熠生輝,體現出在真情指引下凝聚的“清峻”文風,又在一定程度上彰顯真性情與真詩意。
(二)意象:關注現實,比興寄托
嵇康眼界開闊,為文別出心裁,藝術造詣極高。他在詩文作品中所用意象十分豐富,意象選擇上尤其關注現實,貼近自然與生活。鐘嶸有“托喻清遠,良有鑒裁”[17]113之論,贊賞嵇康詩“秀美”的品格。在嵇康“峻切”人格的影響下,詩文中的意象韻味可謂超凡脫俗,一定程度上展現出其曠達性情與對“真”的追求。在詩文創作中廣泛運用意象傳遞內心情志,使意象成為凝結詩人主觀感情的客觀物象。借意象比興寄托,將主觀之情與客觀之景相融合,從而創造出更高層次的審美境界。嵇康常以山水景物入詩,將山水花鳥禽魚草木等自然之景融入詩中,用簡潔雋永的語言把自然美景與內心真情交融起來,借詩歌來表現詩人內心激情或滿腔憂憤,“自然山水以超越時空、超越歷史和地域的原始生態的美,更煥發他生命的活力,并孕育著一種詩意。”[19]33嵇康詩中常有“五岳”“箕山”“滄浪”“綠林”等自然山水意象,亦有“鸞鳳”“游鱗”等仙界意象,將詩人主觀感情融于現實景物與想象仙境之中,在自然中尋求真實的現實寄托,通過意象構建意境,從而產生韻外之味、味外之旨,傳遞詩人內心真情。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3]24之妙句,看似平淡寡味,實則韻味深遠。詩中想象嵇喜行軍途中所見山水之景,實際是詩人縱心自然的個人情趣,將人與自然的神游與契合帶入文學中來。再有“抄抄翔鸞,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3]136,詩人置身于榮華之外,很少能有人與他比翼雙飛,孤鸞舒翼。是詩人獨立高潔形象的真實寫照,展現出他潔身自好、卓犖不群的人格精神。《見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其一)是嵇康五言名篇: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云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云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翩獨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兇雖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游太清,攜手長相隨。[3]5
雙鸞渴望永遠遠離塵埃,自由自在,但是它們卻無法掙脫現實的牢籠,只好與同伴分離。日本學者興膳宏論:“嵇康詩中的飛鳥形象都不是實景的寫生,而完全是幻想的產物,在大部分場合都暗示遨游仙界的超然者的姿態。這些飛鳥在不同程度上被賦予了大鵬飛翔的性格,象征著莊子精神世界中的至上境地。”[20]10詩人以雙鸞自喻,運用比興手法,將道家的人生境界內化于詩,委婉曲折地道出自己不愿出仕又欲隱不能的痛苦心情,含蓄婉轉,為全詩營造了一種慷慨多悲的氛圍與深遠雋永的詩歌意境。嵇康詩中多“景曜”“朝露”“蘭池”等意象,描繪有清晨的露珠、清澈的流水、明朗的天空等自然景物,爽人耳目,打動人心,可見其意境之“清”。嵇康詩歌意象超凡脫俗,回歸自然,運用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在現實中寄寓真情,將自然之景與個人理想追求完美融合,顯示出一種清遠俊逸的詩歌境界與率真曠達的審美追求。
(三)語言:質樸雋永,技法獨特
嵇康善四言,五言較少。在鐘嶸看來,四言“文繁而意少”[17]39,句式簡單且由雙音節詞構成,使詩歌過于呆板乏味。這也是鐘嶸在《詩品》中將善五言的阮籍列為上品,卻將嵇康列為中品的原因之一。但嵇康卻用充沛激昂的感情和質樸雋永的語言驅動它,使四言詩成為其成就最高的文學作品。由此王夫之指出:“中散五言頹唐不成音理,而四言居盛。”[21]83又有胡應麟《詩藪》評:“叔夜送人從軍詩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詞彩語,錯戶期間未令人厭。”[22]9嵇康掙脫儒家思想的桎梏,不再完全遵循傳統詩教,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詩歌天地。
嵇康往往以自然質樸的語言抒發內心真實的情感體驗,表達自己的獨特感受。詩中極少紛繁復雜的偏詞僻語,不刻意雕琢推敲,不崇尚華麗言辭,在近乎生活化、口語化的書寫中,以質樸雋永的語言和獨特的技法,抒發真實而濃烈的情感和審美體驗。如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中,有“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其十三)[3]20“駕言出游,日夕忘歸”(其十四)[3]22“郢人逝矣,誰可盡言”(其十五)[3]24“佳人不存,能不永嘆”(其十六)[3]27等,詩人直抒胸臆,用直白簡明的語言傳遞情思,描繪其兄從軍行程中的情景,在悠游閑適中透露出心靈的平靜與對理想生活的向往,折射出嵇康乃至魏晉士人高潔的心性與超遠的境界,從而體現其真性情與真操守。嵇康在詩中常運用對偶、對比等技法,講求對仗工整。如《四言詩十一首》中“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泛泛柏舟,載浮載滯”(其一)[3]126“泆泆白云,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頹”(其七)[3]135“左配椒桂,右綴蘭苕。凌陽贊路,王子奉軺”(其十)[3]136等,內容上言簡意賅,凝練集中,形式上結構整齊勻稱,音節頓挫跌宕,具有建筑美和音樂美的特點,為自然的語言增色不少。嵇康用質樸雋永的語言描繪了對理想境界的熱情與向往,詩中馳騁著詩人的想象,在超越時空的境界中創造出了成就極高的四言詩。詩歌語言質樸雋永,巧妙運用各種技法,營造出真率曠達的詩歌風格,書寫著真實而豐富的作家情懷。嵇康性情高傲剛直,在文學創作中大膽袒露真情,獨抒己見,從而造就影響后世的“清峻”文風,其中蘊含著他“真”的審美理想與心靈呼喚。
四、結 語
魏晉時代士人從儒家大一統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在老莊道家思想的影響下,建立了新的審美理想與思想觀念,在“真”的指引下使自我意識和個性情感得到解放,“真”逐漸成為一種思想潮流,一種人格精神與人生態度,其中蘊含著深厚的歷史韻味和鮮明的時代色彩。嵇康作為竹林七賢的領袖,以其覺醒的超越人格和對個體獨立價值的認識與推崇,成為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他那高尚的人格精神與卓越的藝術實踐贏得了后世的景仰,對歷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嵇康把“真”作為自己一生的全部追求,其任真散傲、守志如一的人格魅力決定了他一生踐行著質性自然、雅逸自得的生活態度,這也代表了當時大多數魏晉士人的生活方式與人生價值,標志著魏晉時代審美觀念發生了巨大轉折。在人格與生活之“真”的影響下,嵇康創作出一系列具有真率曠達、峻切清遠風格的文學作品,其中寄寓著他對個性自由解放的追求與向往,同時也是士人心靈的物質外化與精神寄托,從而奠定了魏晉風度的審美高度。嵇康之“真”,不僅僅是魏晉士人的審美典型,更是魏晉風度的精神內涵與經典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