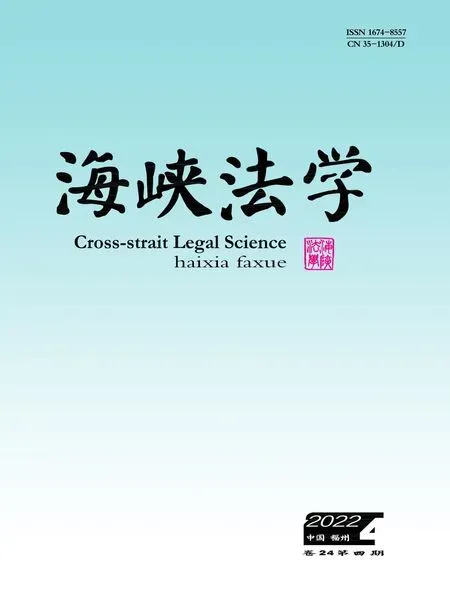高空拋物罪的限縮適用
林貴文 蔡國慶
一、問題提出:高空拋物司法適用之亂象
高空拋物行為的刑法規制,大致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這三個不同的階段,有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修十一》)于2021年3月1日正式實施,新增高空拋物罪。于司法實踐中,則呈現出懲罰寬嚴飄忽不定、界定不清的亂象。
第一階段是2019年《意見》實施之前。這一時期的司法實踐特點是高空拋物行為很少被作為犯罪處理,只有造成了重傷或者死亡的嚴重后果時才會被定罪量刑。換言之,高空拋物行為如果沒有造成嚴重的人身損害或者財產損失,一般通過民事或者行政手段處理,不會進入刑事領域。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中的高級搜索,將案由設置為刑事案由,截止時間為2019年10月20日,案件類型為刑事案件,文書類型為判決書,全文關鍵詞為“高空拋物”,檢索得有效判決書14份。其中,2015年6 份、2016年4 份、2017年1 份、2018年1 份、2019年2 份。從罪名分布來看,過失致人死亡罪6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4 件、過失致人重傷罪1 件、重大責任事故罪1 件(重傷而死)。在這些適用的罪名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存在爭議的。如下表所示,案件中高空拋物行為都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但是是否應當認定為以危害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相應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值得商榷。由于此類案件的數量有限,且案件的定性差異對量刑的影響不大。因此,這樣的爭議沒有擴大。

案號案件事實(2015)大東刑初字第00472 號2014年8月末至2014年9月1日期間,被告人劉某某在沈陽市大東區小津橋路xx-x 號x-x-x 室內,隨意向窗外拋扔酒瓶、罐頭瓶子等物品,將放置在沈陽市大東區小津橋路42 號路邊的車牌號為遼APXXXX 的大眾速騰轎車、遼ARXXXX 的起亞K2 轎車、遼A5 XXXX 的中華530 轎車、遼A8XXXX 的英菲尼迪轎車,遼ATXXXX 的凱迪拉克牌轎車、遼A

3XXXX 奧迪A6L 轎車砸壞,經沈陽市大東區價格認定中心價格鑒定,上述部分車輛的毀損價值人民幣33395 元。(2015)高新刑初字第169 號2014年11月9日至20日期間,被告人張某某為發泄情緒,在其居住的成都高新區大源北二街48 號5 棟5 單元504 號的家中陽臺及四樓與五樓之間的樓梯處,多次朝樓下拋擲花盆、玻璃罐、滅火器等物品。停放在樓下的被害人鐘某某、彭某某、任某某、周某某、黃某某等人的多輛汽車被砸壞,張某某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2017)渝0106 刑初1343 號2017年5月18日18 時許,被告人李旭晨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某小區小區67 號21-5與朋友喝酒,在陽臺處先后往樓下扔出一個啤酒瓶和一個玻璃杯,其中玻璃杯砸中站在樓下操場上的葉某某(男,13 歲)頭部,致其顱腦嚴重損傷。經鑒定,被害人葉某某損傷程度為重傷。(2018)魯02刑初86 號2018年3月1日14 時30 分許,被告人徐某為發泄內心的郁悶與不快,在本市市北區杭州路59 號4 號樓6 單元門口,撿拾單元門口處地磚一塊,上至該單元7、8 樓間樓道窗口處,持磚塊砸向樓下杭州路某小學公交車站候車的人群,致在此候車的被害人高某1 頭部受傷倒地,徐某逃離現場。高某1 經搶救無效于2018年3月13日死亡。
第二階段是《意見》2019年10月21日實施之后《修十一》2021年3月1日生效之前。《意見》指出:“故意從高空拋棄物品,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 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115 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罰。”顯然,該司法解釋并沒有創設新的罪刑規范,也不是說高空拋物就應當按照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但是《意見》出臺后,高空拋物刑事案件數量大增且大多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前一時期同樣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高空拋物行為差異很大,這一時期的高空拋物行為即使沒有造成重大損害也普遍被冠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這樣理解:此前通過民事或者行政手段處理的高空拋物行為在這一時期被當做犯罪處理。筆者再次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將時間設置為2019年10月21日至2021年3月1日,其他條件不變,檢索得到有效高空拋物案件38 件。2019年3 件、2020年33 件、2021年2 件。罪名分布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2 件、故意毀壞財物罪2 件、重大責任事故罪2 件、過失致人死亡1 件、過失致人重傷1 件。可以看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壟斷了高空拋物行為的定罪。然而,這里的高空拋物行為只是造成了輕微的損害結果甚或沒有造成損害,且行為的危險程度難以比擬所謂的“危險方法”,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導致定性偏差和量刑失衡。似乎《意見》誤導了司法實踐。
第三階段是《修十一》)2021年3月1日生效之后,新增高空拋物罪。該罪的增設,其意在擴大處罰范圍,保護民眾“頭頂上的安全”,和對第二階段的糾偏沒有關系。但是高空拋物罪在適用過程中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回避或者弱化對“情節嚴重”的符合性判斷。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2021年3月1日至今有關高空拋物罪一審判決書,共計127 份,整理后有效判決書114 份。歸納判決書中法院對高空拋物罪“情節嚴重”的認定,大致有如下四種類型。一是判決書中根本不提及“情節嚴重”,也不論證,法院似乎在有意無意中省略。法院主要表述為“被告人的行為已構成高空拋物罪”“被告人犯高空拋物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等。此類判決書有35 份,占比30.70%。二是判決書中有且僅有提及“情節嚴重”字眼,沒有進一步論證說明。如“被告人從建筑物高處拋擲物品,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高空拋物罪”“被告人無視國法,從建筑物拋擲物品,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高空拋物罪”。此類型判決書最多,總共47 份,占比41.22%。三是判決書中會強調高空拋物行為的某一方面以簡單說明“情節嚴重”,包括造成的損害、拋擲的物品、動機、拋物次數、拋物高度等。如“被告人多次故意從建筑物高空拋擲物品,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情節嚴重”“被告人從建筑物上拋擲物品,致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高空拋物罪”“被告人從建筑物的高層拋擲物品,情節嚴重”“被告人無視國家法律,數次在其居住的居民樓五樓拋擲物品,損壞他人財物,情節嚴重”。此種情形的判決書有29 份,占比25.44%。第四,綜合犯罪時的眾多因素判斷“情節嚴重”。如“本案案發地點系居民小區,案發時間為20 時許,路面行人、車輛較多,被告人……,仍不計后果將一把金屬材質菜刀從高空拋下,……”。此說理中包括了高空拋物的時間、地面人流、財產狀況、所拋棄的物品、拋物的動機、造成的損害等因素,是對“情節嚴重” 較為全面的判斷。但此類判決書僅有3 份,占比2.63%。
其二是對同時侵犯了其他法益的構成其他犯罪的高空拋物行為一律適用高空拋物罪,壓縮了其他罪名的適用空間。在114 份判決書中,至少有12 起高空拋物行為在構成高空拋物罪的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想象競合之情形。①競合之罪主要是故意毀壞財物罪和故意傷害罪。然而法院一律適用高空拋物罪,無視其他罪名。
簡言之,第三階段在高空拋物罪適用中存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不清問題。
產生上述司法適用之亂象,筆者認為有必要全面審視高空拋物罪之應然行為類型,正本清源其保護法益,并在此基礎上明確如何界定“情節嚴重”,方能對本罪進行限縮適用,避免過于擴大本罪的處罰范圍而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當然,在此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明確“公共安全”的應有內涵,使得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回歸其本來的面貌。
二、保護法益的應然界定
就存在論的角度,高空拋物行為的危害性將呈現輕重有別的類型,有如光譜的連續分布,從無罪到有罪、從輕罪到重罪、從此罪到彼罪,高空拋物行為都能展現。合理限制高空拋物罪的處罰范圍,必須借助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準確框定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從而使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確實侵犯本罪所保護的法益,從而確定罪或非罪、此罪或彼罪。
筆者認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禁止高空拋物的公共秩序,并非公共安全。即本罪意在保護人的共同生活領域生活的安寧,且其應能還原為人身、財產等個人法益。
(一)公共安全法益之否定
何為“公共安全”?一般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身體的安全。其中的‘不特定’并非指行為對象的不確定,不是指“誰碰到誰倒霉”,而是指危險的不特定擴大。②張明楷:《高空拋物案的刑法學分析》,載《法學評論》2020年第3 期,第20 頁。通常的高空拋物行為,不具有導致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人身造成現實的、緊迫的具體危險,不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在人員密集的場所實施高空拋物行為,雖然可能侵犯多數人的生命、身體,但高空拋物的行為特點決定,其最終充其量針對的是不特定的少數人的危險,危害結果往往限制在較小的范圍之內,屬于“誰碰到誰倒霉”的情形,不具有危險的不特定擴大的特點,很難說均能在性質上媲美于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具有結果的開放性和擴張性的特點。③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4 頁。因此,本罪的保護法益不能是公共安全。當然,也不排斥在及其特殊的情況下,綜合考慮行為所拋擲的物品的性質,拋物的高度,行為的時間和場所等,存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適用的可能性。④曹波、文小麗:《高空拋物危及公共安全的司法認定規則——兼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載《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 期,第96 頁。如果說有公共安全的存在,那充其量也是一種公眾對頭頂安全的不安感。
有學者主張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安全,主要是認為“不特定”只需要對象的不特定即可,不需要“不特定擴大”的事實狀態,從而否定本罪屬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理由:(1)危險不特定擴大的主張是一種客觀的結果論立場,會導致司法操作的困難,而應當采取主觀的結果論,即以行為是否帶來集體恐懼作為不特定或多數人的判斷標準。(2)不特定危險的存在即可成立公共危險犯罪,不特定擴大的危險只是影響量刑。即使是放火、爆炸等行為也不需要有“多數人”的特征,不特定而導致多數受害是加重處罰的根據。(3)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是行政犯,是違反國家行政管理法規而實施的犯罪,但是,社會治安處罰法對于高空拋物缺乏相關的規定。(4)妨害社會管理罪的保護法益是和個人人身財產權利無直接關聯的超個人法益,但是本罪對實行行為的界定離不開個人人身和財產法益。(5)本罪所處的刑法第291 條中涉及的三個犯罪和本罪保護法益不同,前者都是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交通秩序、公共場所秩序等為入罪標準,后者以是否具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的危險為入罪標準。(6)可能會導致本罪處罰的擴大化和加重司法機關認定“情節嚴重”的負擔。最終影響本罪的立法價值。①參見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14~116 頁;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罪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4 頁。
但是,上述的理由均值得商榷。第一,按照論者的觀點,不應基于客觀結果論的立場,將“不特定”理解為“危險的不特定擴大”,否則將導致司法操作的困難,主張堅持主觀的結果論,即以行為是否產生集體恐懼作為不特定的判斷標準,不特定即可產生集體恐懼,危害公共安全。但是,公共安全足以產生集體恐懼是沒錯,但是不表明產生集體恐懼的均是危害公共安全。例如黑社會長期欺行霸市、社會治安交差時的扒竊、攔路搶劫,以及打砸搶等行為都可能產生集體恐懼,再例如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甚至嚴重的環境污染犯罪等屬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罪行都可能,難道也納入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集體恐懼的確往往和公共安全有關,但是這一點和對公共自詡的危害并非本質上的差異,兩者都屬于公共領域內民眾對秩序的需求,秩序和安全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因此,以集體恐懼來確定公共危險的存在以區別于公共秩序的危害,顯然是不當的。況且,集體恐懼究其實質是一種集體情緒的反映,是多數人對某種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確定的危險狀態的集體反映,因此,其離不開多數的投射,因為只有不確定擴大,才可能對多數人產生成為受害者的可能,從而引發集體恐懼情緒。
第二,不確定如果僅僅是對象的不確定,可能會導致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不當擴大。例如某甲意圖殺人以報復社會,在一次大型聚會時蒙上眼睛走入人群,手持尖刀隨意捅死經過的一受害者之后轉身離去。顯然,本案中受害者具有不確定的特征,屬于典型的誰碰到誰倒霉,且按照論者的觀點,行為人持刀走進人群的時候,被害人的生命法益已經處于危險的狀態,已經構成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顯然這種觀點難以獲得贊成,其按照故意殺人罪處罰即可。除非行為人在上述狀態下駕駛機動車輛往人群中撞去。又如,扒竊或者攔路搶劫就是典型的對象不特定,誰碰到誰倒霉,難道也屬于危害公共安全?②可能遭到反對的觀點主張,行為人確定扒竊的時候和確定攔路搶劫的對象時,對象已經是確定的。但是,高空拋物在拋下的那一刻,受害對象也是確定的。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其同時也不具有不確定擴大的可能,因此不同于放火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第三,“公共安全”的“公共”如果脫離多數,那只能說是少數的個人安全。交通肇事罪就具體個案而言當然是可能僅僅導致不特定少數人生命、人身損害的,但是因其發生的公共交通領域,立法者本就預設其有向多數擴大的可能,而非僅僅是不特定。換言之,不特定擴大是行為本身具有可罰性的類型性特點,“擴大”屬于一種抽象危險,是行為本身的危險屬性,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多為行為犯和危險犯的原因所在。至于這種危險是否最終轉化為現實產生多數的危害結果,那是危險犯或者行為犯成立之后危害結果的問題,當然只能影響量刑不影響定罪。例如放火,如果沒有擴大延續的特征,何來公共危險?因此,以具體的存在論層面出現的不特定少數權益遭受侵害為由主張不特定不應當理解為“不特定擴大”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的確絕大多都是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行為,但是不能因此認為,沒有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行為就不應當納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的范疇。沒有納入行政管理法規調控范圍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可能是因為新增設的犯罪,相關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對相關的行政違法行為尚未來得及相應地進行增列。也有可能是該類型為本身不存在行政管理法規進行處罰的空間,例如只有或者不構成犯罪且危害性極小不值得行政處罰,或者是較為嚴重,直接跳檔為犯罪行為。當然,后者存在的空間不大,筆者認為,應當是行政處罰法尚未及時進行跟進。例如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社會治安處罰法也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對于該罪應當納擾入亂公共秩序的犯罪并不存在異議。實際上,但凡是公共領域的事項,就存在刑行交叉,因此,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也應當存在對應的社會治安處罰的規定才是恰當的。因此,從目前行政處罰法對該行為規制的缺位論證本罪不屬于妨害社會治安管理秩序的犯罪也是值得考量的。
第五,至于主張本罪對實行行為的界定離不開個人的人身財產權益,但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保護的是超個人法益的犯罪,與個人人身財產權益沒有直接關聯,因此,主張本罪不應當納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也是值得商榷。本罪的增設,意在遏制高空拋物行為本身,至于行為是否產生具體危害結果,甚至是危害公共安全以及產生危害結果,并非立法所關注。但是正如前述,高空拋物行為本身的多樣性特征導致其自身的行為舉動還不足以達到處罰的程度,因此,需要在客觀違法程度和主觀責任內涵上增加其不法程度的要求,這也是“情節嚴重”本身的應有之義。因此,其直接保護的還是公共秩序,只是在實現保護公共秩序的同時也間接實現對人身財產權益的保護。至于行為本身的界定需要考量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其實在聚眾斗毆罪中就存在類似的情形,尋釁滋事罪也是一樣,離開對個人權利的保護,都難以實現對行為外在輪廓的界定。因為說到底超個人法益最終都是為了實現對個人權益的保障,只是個人權益因為人的社會性特征,有社會性存在和生物性存在而需要的不同層面的法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犯罪和個人哪個層面的法益相對是直接或者間接并不能一概而論,公共安全和個人的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比較接近也只是相對的,例如恐怖主義犯罪大抵是和人身、財產有關的,但是例如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等均和個人人身財產權益并不是直接關聯。因此,所謂的關聯,只能說是大致的概率,并不能以此作為劃定的硬性標準。
第六,刑法中不同罪名置于同意條款之中并不表明其保護法益就一定是一樣的,有的僅僅是統一行為類型,例如第299 條的侮辱國旗、國徽、國歌罪和第299 條之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就刑法第291 條和第291 條之一以及第291 條之二的高空拋物罪而言,都有不同的保護法益,但是它們均發生于公共空間領域對公共秩序的危害,就此而言,將本罪置于第299 條之二并無不當。
第七,所謂處罰范圍的擴大,其實就類似學者主張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較之公共安全意蘊寬泛,不可避免會擴大行為的范疇。①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罪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4 頁。但是如果將本罪置于刑法第114 條之中,無論是采取《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審稿的方式,將本罪設定為抽象危險犯,或者照搬現在立法表述。但是前者也可能導致過于擴大處罰的范圍,因為高空拋物類型多樣,單純的高空拋物行為還不足以出現“擬制的危險狀態”以落實可罰性的根據,導致安全價值的過分追求而損害罪刑法定的自由保障機能。因此,筆者并不贊成有些學者主張的將本罪設置為抽象危險犯,“將處罰重心由結果危險轉移到行為危險上,能有效降低高空拋物及其可能產生的復雜風險。”②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罪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4 頁。如果照搬現有的立法表述,依然存在對“情節嚴重”做如何解釋的問題,無論放在哪個章節,難見顯著差異。即使是采取《意見》的具體危險犯模式,也一樣存在“結果危險”的舉證問題,難免讓司法機關頗費周章。如果認為本罪因為規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章,需要考慮是否危及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意蘊”不會那么寬泛,從而起到限縮的作用。但是,公共安全是否危及,其對應的“公共危險”是否實現,而“危險的概念”本身就是難以確定的,因此,期待“公共安全”的限定落實限縮高空拋物罪的處罰范圍是不現實的。因此,意圖通過降本罪設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實現限縮其處罰范圍的目的難以實現。
總之,如果肯認“公共”具有“社會性”,就應當有“多數人”的要求,可能是客觀存在的多數,也可能是擴大可能的多數。具有“對象不特定”就具有“社會性”,但是,當該不特定不具有向多數擴大的特性,則難以產生對公共安全緊迫的、具體的危險,也不存在論者所謂的集體恐慌,其更主要的是對公共秩序的侵害而導致周遭民眾的不安感。就此而言,將本罪納入公共秩序的犯罪是較為妥當的。
也有學者認為,《意見》出臺之后,《修十一》實施之前,高空拋物,情節嚴重,但是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由于沒有獨立的高空拋物罪,因此應當認定為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在《修十一》實施之后,由于有獨立的高空拋物罪,因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但是情節嚴重的應當界定為高空拋物罪。③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正案十一>理解與適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 頁。筆者認為,該種觀點值得商榷,其實際上是將本罪的保護法益界定為公共安全。論者一方面主張本罪是規制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但是在具體的適用中卻新瓶裝舊酒。因為從立法的目的看,本罪的成立并非將原來較為輕微的已經構成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以高空拋物罪進行調整,相反,其是將原本不構成以危險防范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控范圍,擴大犯罪圈。至于原本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依然應當按照該罪處罰,這也是高空拋物罪第2 款的應然解釋。否則,正如論者所言,將導致司法適用中造成兩罪適用的混亂。①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正案十一>理解與適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58 頁。其實,即使是在《意見》出臺后、《修十一》生效之前,盡管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少將高空拋物行為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的司法裁判,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其呈現出“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現象,高空拋物未造成嚴重后果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未造成嚴重后果在量刑上呈現出較大差異,前述第二階段32 件高空拋物行為最終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裁判中,16 件宣告緩刑,占比50%:5 件判刑不足2年5個月,占比15.62%;7 件判刑3年,其他4 件分別是3年2 個月2 件、3年4 個月1 件、4年1 件。而同期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類型,判刑4年以上占比37.04%。②趙香如:《論高空拋物罪的罪刑規范構造——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為背靜》,載《法治研究》2020年第6 期,第67 頁。顯然,司法者一方面認為應當按照《意見》將高空拋物行為以以危險防范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但是又認為其和一般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能相提并論。畢竟其對于公共安全的威脅并非具體、緊迫的,若此,認定為其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也就存疑。
(二)公共秩序法益之限縮
本罪之設立,意在禁止不良的高空拋物行為,營造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保護民眾“頭頂上的安全”。但是本罪的保護法益,在立法過程中也是有所變動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次審議稿將本罪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章,列于第114 條之內。第二次審議稿改變了其在刑法體系中的位置,移位至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罪,就所處章節考慮,從解釋論的層面出發,顯然,前者是主張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安全,后者主張本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隨著《修十一》的生效,就司法論層面看,本罪保護法益基本上塵埃落定。司法者在適用刑罰法規的時候,要以規范之保護法益為為依據,明確構成要件的具體內涵,而非質疑規范的保護法益。③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11 頁。但是,個罪的保護法益并非直白在刑罰規范中體現出來的,而是解釋者解釋的結果,換言之,解釋者往往需要根據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依據社會生活場景、刑事政策、社會變遷等等,在生活事實與規范之間不斷往返,理解個罪的保護法益。而不同解釋者對上述要素的理解認知可能不盡相同。因此,所謂對于法益的質疑往往無從談起,充其量只能說是對一個共識性法益的質疑。所以,解釋者在確定法益以解釋構成要件的時候,應當力求構成要件和法益之間的鉚合,結合構成要件可能呈現出的行為類型樣態,考量各種影響法益界定的因素,不斷地在構成要件和保護法益之間不斷往返,最終實現體系性的協調和法益保護的妥當性。如果構成要件導致其處罰范圍過寬,違背法益論的自由保護機能的時候,則需要依據法益限縮構成要件的處罰范圍。④李梁:《污染環境罪侵害法益的規范分析》,載《法學雜志》2016年第5 期,第97~102 頁。在新出現的犯罪類型不符合傳統的對構成要件解釋結論時,則應當依據法益,考量構成要件的涵攝可能,如果還在構成要件的涵攝范圍之內,則應當擴大解釋,如果不能,則應當排除出罪,這也是法益論的人權保障機能的當然,是對罪刑法定主義的遵循。在構成要件的表述明確性不足時,依據法益明確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和處罰邊界。
雖然本罪的保護法益界定為公共秩序,但是未免過于寬泛,這一點筆者并不反對上述公共安全法益論者的觀點,因此,難以使法益發揮其應有的解釋論機能。
有學者認為:“應該將公共秩序具體化以明確處罰范圍。之所以認為高空拋物應當入罪,一方面是要繼續強調頭頂上的安全的保護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公眾的安全感,以及公眾生活的安定性也應當得到保護。”⑤林維:《高空拋物罪的立法反思與教義適用》,載《法學》2021年第3 期,第45~46 頁。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將高空拋物的法益確定為公共秩序沒有疑義。但應將其還原為個人法益,并且在司法實踐中,要優先考慮個人法益,特殊情形時才考慮公共秩序。”⑥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5~96 頁。從本罪的構成要件看見,本罪意在保護民眾頭頂上的安全,避免生命、人身和財產權益的損害,將本罪的保護法益還原為對人身、財產等個人法益是解釋論上應然之舉,唯此方能落實立法之目的,并實現限縮解釋之訴求。因此,從法益對構成要件的明確視角處罰,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一是如果高空拋物行為僅僅是對不得高空拋物的公共生活秩序的形式違反,但是對人身、財產權益的侵害沒有任何威脅,則不構成本罪。例如從高空往下拋擲裝有紙團等較為輕微的垃圾,或者往樓下沒有人員往來的空地拋擲物品,均不能因為形式的秩序違反而論罪。二是本罪畢竟是首先違背公共秩序的犯罪,因此,人身或者財產權益的損害一定是在有公共秩序有關的領域所發生的,與公共秩序相關聯,能夠映射公共秩序的人身、財產等個人法益。行為人是因為侵犯公共秩序而侵害個人人身財產權益,這是高空拋物罪的應有之義。因此要考量公共秩序的基本要素。例如對象是否特定,如果行為人是專門針對某個特定的被害人實施的拋擲,對他人沒有任何影響,即使導致輕微傷,也不應當按照本罪處理。又如場所是否公共。上述行為類型,即使對象特定,若發生在公共場所,人員往來密集,或者行為人多次實施,則也有損于公共秩序。由此可見,作為高空拋物罪保護法益的公共秩序必須結合本罪的規范目的在于禁止高空拋物,保護社會共同生活安寧秩序,且該行為的類型決定其保護的法益應當是和損害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有關。
三、高空拋物罪實行行為的規范解釋
實行行為必然是在客觀上符合刑法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這是罪刑法定主義的形式要求;同時,從法益保護的立場出發,實行行為必須具有法益侵害危險的舉動。根據刑法規定,高空拋物罪的實行行為是“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因此,為該行為劃定準確明晰的外在輪廓,厘清其對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方能實現對本罪的合理限縮。
(一)“高空”和“建筑物”
首先是建筑物和高空是什么關系?二者是否需要分別解釋?筆者認為,高空是高空拋物罪的核心特征,從建筑物拋擲物品也要符合高空的要求,只需要解釋高空即可。從表述可以看出,建筑物只是高空的一種類型,前者是屬概念,而后者是種概念,二者是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立法上突出從建筑物拋擲物品的行為只是因為司法實踐中這種行為在高空拋物行為中較為突出和典型而已,這主要涉及立法技術的問題。例如,非法拘禁罪的罪狀表述為“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其中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拘禁罪的本質特征,而非法拘禁他人是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一種最常見情形而已。同樣的,建筑物和高空兩個概念中,高空才是高空拋物罪的本質特征,建筑物只是一種典型例舉。此其一也。其二,“高空”本身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以“建筑物”作為例舉性的規定限制“高空”,有利于形成對“高空”較為明確的常識性認識。盡管“建筑物”也沒有明確的高度界定,但是畢竟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有大致觀感的考量。否則,很容易使“高空”過于寬泛。因此,筆者并不贊成有些些學者主張的,“建筑物”是立法技術上的畫蛇添足,對于揭示高空拍賣行拋物犯罪的性質無絲毫的意義。①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罪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5 頁。
其次是“高空”是否應當有具體基準的問題。一般認為,對于“高空”的判斷,很難做到像危險駕駛罪酒精含量標準一樣精確可控,考慮到高空拋物犯罪所要懲治的是高空拋物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而這一危害主要通過對他人人身、財產造成損害予以體現,因此,對于“高空”的判斷離不開其與人身、財產是否可能受到侵害的關聯。這也說明,“高空”的判斷是一個具體的、實質化的過程。②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8 頁。筆者對此深表贊成,從保護法益的角度獲得“高空”的實體性存在是可能且必然的路徑,這是法益的解釋論機能的體現。③陳興良著:《規范性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3 頁。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且主要和人身、財產權利相關的人的公共領域的生活安寧權。單純的給“高空”確定一個具體數值并沒有意義,因為高空拋物行為對人身、財產的侵犯不止關乎“高空”這一因素,還關乎其他因素,不同的物品在不同的墜落高度所產生的危險性并不相同,例如將一個雞蛋分別從2 米高空和20 米高空拋下,對地面的財物或行人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對“高空”的認定,關鍵不在于用一個具體的數字來規定高度,而是在具體的場景下,在某一高度拋擲某一物品的行為是否對人身安全有某種具體危險。①林維:《高空拋物罪的立法反思與教義適用》,載《法學》2021 第3 期,第46 頁。
但是,這并不表明“高空”可以毫無限制,只要能夠導致對公共秩序的擾亂和對個人權益的傷害即可,畢竟,一米多的高度總不能稱之為“高空”吧?有學者主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 /T 3608-2008《高處作業分級》規定,將“高處拋物”理解為行為人在距墜落度基準面2 米或者2 米以上的高度拋擲物體的行為。因為高處標準與高空拋物罪的適用最具相關性,②林維:《高空拋物罪的立法反思與教義適用》,載《法學》2021 第3 期,第46 頁。雖然“高空”與“高處”不能等同視之,但由于我國城鎮高層建筑眾多且地下分層(用作購物廣場等)普遍,因而將“高空”擴大解釋為“高處”,更有利于實現立法目的。③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6 頁。也有主張將建筑物二樓(層)以上界定為“高空”。如認為,“與‘高空拋物’相對的是‘低空拋物’,即在地面上或者一層建筑內進行拋物。”④韓旭:《高空拋物犯罪案件司法證明之難題》,載《法治研究》2020年第6 期,第71 頁。相似的觀點認為,“最少也要從二樓算起才是高空。⑤李曉明:《“高空拋物”入罪的法教義學分析與方案選擇》,載《天津法學》2020年第3 期,第59 頁。反對的觀點認為,2 米這一“高處”的判斷標準,主要是從施工作業人員安全角度而言,而高空拋物中的“高空”則主要側重于對地面人員的侵害,二者的立足點和價值取向并不相同,因此將2 米的“高處”標準直接照搬適用到高空拋物罪中“高空”的判斷標準,并不妥當。⑥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7~98 頁。而且,由于建筑物的開放程度、地理位置、屬性分類、實際使用情況等并不相同,建筑物的樓層高度也有各自的標準。⑦孫藝佳、李榮:《高空拋物罪司法適用的泛化與限縮》,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2年第2 期,第65 頁。比如,同樣是一層建筑的高度,酒店大樓往往相當于居民樓的幾倍。以建筑物的樓層作為劃分依據不具有更強的說服力。筆者認為,不能單純以《高處作業分級》規定的2 米或者按建筑物的樓層標準,可以考慮將兩者并合考慮,即高空不能少于2 米,但是單純2 米也難謂“高空”,此時,借助一般樓層是較為合理的,但是如果樓層較高,則在一般人眼里,此處拋物可能導致他人傷害則可降低樓層的標準。
(二)“拋擲”認定
在語義上,拋擲有拋、投、棄置不管等含義,如果僅按這些含義對“拋擲”進行平義解釋,則不能完全涵蓋高空拋物罪的情形,無法實現高空拋物罪的立法目的。如,行為人將放置在陽臺上的花盆推下,或者向下傾倒生活污水等,理當屬于“拋擲”的范疇。因此,需擴大理解“拋擲”,可以將其定義為“釋放物品任其自由下墜”的行為。
要注意區分“拋物”與“墜物”的不同。《意見》中就要求準確認定高空拋物、墜物案件。“拋物”與“墜物”可以從以下兩點區別,首先,兩者主體可能不一樣,前者的主體是人,而后者的主體不一定是人。如大風、暴雨等自然原因,或者建筑物配件年久失修等自身缺陷所引發的物品墜落,就屬于“墜物”范疇,即墜物重在物品脫離控制的狀態,不考慮原因。當然,拋物可以是直接接觸的拋擲,也可以是利用工具為之,甚至借助利用非人力等原因拋物,例如借助臺風。如行為人在臺風來臨之際,將物品故意放置在窗臺邊緣,意圖或放任物品墜落,最終導致物品墜落的,可以評價為“拋物”⑧林維:《高空拋物罪的立法反思與教義適用》,載《法學》2021 第3 期,第47 頁。。其次,兩者主觀心態不同。同樣是人導致的物體從高處下落,前者出于故意,而后者出于過失。“拋物”是一種受個人意志支配下產生的積極主動行為,而“墜物”則意味著消極被動,這種動作并不受意志支配。⑨王煜東、孫國月:《實質解釋立場下高空拋物罪的限縮適用》,載《河北法學》2022年第9 期,第197 頁。在某種情形下要綜合判斷是故意的“拋物”,還是過失的“墜物”。即行為人不是直接拋棄物品,也不是借助工具,而是通過行為人的其他行為“間接”導致物品下落的,如行為人為了發泄情緒,砸碎窗戶玻璃致使玻璃碎片墜落。此種情形到底是“拋物”還是“墜物”呢?這時候需要考慮行為人對砸碎窗戶玻璃導致的玻璃碎片下落這種客觀事實所持的主觀心理態度,如果行為人是積極追求或者放任,則屬于故意的“拋物”,如果行為人沒料到玻璃會碎或者向樓下墜落,則可以評價為過失的“墜物”。這里面最為關鍵的判斷點在于從整體上判斷行為人是否積極追求物品墜落。①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8 頁。當然,行為人只要具有簡介故意的形態就足以認定“拋物”。
(三)“物品”的限定
對“物品”的限定,理論上最主要的爭議點為是否要對所拋擲的物品有性質要求。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對物品性質不應有要求。即使從高空拋擲敞開的衣服、羽毛、打開的降落傘等,也是完全可以擾亂公共秩序的,因而可以構成高空拋物罪。②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 期,第56 頁。第二種觀點主張原則上不宜對“物品”本身的屬性作出限定,但若“物品”客觀上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比如拋擲一張白紙、一片羽毛等),則應當予以排除。③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8~99 頁。第三種觀點主張高空拋物行為不僅有高度的要求,而且對所拋擲物品本身的屬性亦有要求,即根據生活經驗,所拋物品有致人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的可能性,例如,在五樓向樓下扔菜刀、鐵餅等,方能認定為“拋物”④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18 頁。筆者認為,以上三種觀點對高空拋物罪中物品之所以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原因在于三種觀點對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理解不一致。第一種觀點認為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秩序,而能否擾亂公共秩序與物的性質無關,因而物的范疇不應有特別限制。第二種觀點認為,高空拋物罪的的保護法益,一般情況下是個人法益,特殊情況考慮公共秩序,⑤俞小海:《高空拋物犯罪的實踐反思與司法判斷規則》,載《法學》2021年第12 期,第96 頁。因此,一般情況下,對于根本不能造成個人法益損害的物品,要排除在高空拋物罪的“物品”之外。第三種觀點認為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是公共安全,⑥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11 頁。因此高空拋物行為所拋之物要有之人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的可能性。因此,該爭議表面是對“物品”性質的要求,其實質是對于高空拋物罪保護法益的爭論。通過上文的闡述可知,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不是公共安全而是公共秩序,但公共秩序太過抽象,需要還原為與公共秩序相關的人身、財產權利。因此,本文贊同第二種觀點,對高空拋物罪的“物品”要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不過,就算堅持第一種觀點,對“物品”性質不作要求也不一定會擴大高空拋物罪的處罰范圍。因為成立空拋物罪不僅要求“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還要求“情節嚴重”,即使對物品性質不做要求,使得高空拋物行為更加容易符合“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的規范要求,也會在“情節嚴重”的符合性判斷處被排除于外。而根據人類思維的特定,法官在做判案是絕不是先判斷“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再判斷“情節嚴重”,此兩部分的判斷一般是同時進行的。因此從實然角度來講,觀點一和觀點二差異并不會太大。但觀點三為本文所不采,因此該觀點對“物品”的理解過于限縮了高空拋物罪的處罰范圍,與高空拋物罪的立法目的相悖。
四、“情節嚴重”的具體界定
如前所述,“情節嚴重”作為高空拋物罪的入罪條件,是本罪行使可罰性的關鍵要素,即立法者旨在以其限制高空拋物行為的處罰范圍。但司法實踐卻回避或簡化對“情節嚴重”的符合性認定,難以實現立法之目的。因此,需要結合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和立法目的,從客觀生活場景的經驗和邏輯推演出發,明確其可能的表現。
(一)“情節嚴重”的性質
明確“情節嚴重”的內涵與外延,首先必須準確界定其性質,明確其在犯罪論中的體系性定位。
有學者從“罪體—罪責—罪量”一體化的觀點主張“情節嚴重”是罪量要素,罪量要素有別于犯罪構成的客觀要素(罪體)和主觀要素(罪責),是獨立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量的要素,行為人對此無需認識。就內容而言,罪量要素既有主觀要素,又有客觀要素,是主客觀的統一,具有綜合性。⑦陳興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國刑法的探討》,載《環球法律評論》2003年第3 期,第27 頁。也有學者主張其是客觀處罰條件,即認為其是處在不法和責任之外,基于刑事政策考慮而設立的處罰條件。行為人不具備該條件時,其行為仍然成立犯罪,只是不適用刑罰而已。⑧柏浪濤:《構成要件符合性與客觀處罰條件的判斷》,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6 期,第131 頁。還有學者認為其是整體的評價要素,即當行為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基本要素后,并不意味著行為的違法性達到值得處罰的程度,需要在此基礎上對行為進行整體評價,以表明行為達到可罰的程度。①張明楷著:《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 頁。“情節嚴重”是表明法益侵害嚴重程度的客觀的違法性要素。②張明楷著:《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 頁。根據該說,這種整體評價要素的前提性事實,應該為行為人的故意認識所包括。
顯然,按照“罪量”說的觀點,則“罪體”“罪責”是與“罪量”區隔開來的“裸”的觀念性的構成要件,這不符合犯罪構成是質和量的統一的基本共識,且有些構成要件離開“罪量”的考量,將難以界定其性質,“罪體”無從談起。此外認為其是構成要件之外的要素,也就排除認識之必要性,明顯違背責任主義。③王瑩:《情節犯之情節的犯罪論體系性定位》,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3 期,第127 頁。至于客觀處罰條件說,則一方面不符合我國刑法立法和司法中可罰性和需罰性相統一的基本事實。④黎宏:《論“客觀處罰條件”的若干問題》,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1 期,第22~23 頁。和“罪量”說一樣不要求行為人認識,違背責任主義的立場。
筆者認為,整體的評價要素說是比較恰當的。一是將“情節嚴重”界定為整體評價要素,從而納入構成要件的范疇,符合責任主義的基本要求。二是也符合“情節嚴重”的立法目的。即現實生活中,某些侵害法益的不法行為,其不法程度沒有達到可罰性程度,但是難以通過增加某方面的要素使其達到可罰性程度,或者難以預見是哪個方面要素不法程度的提升即可達到可罰性程度,或者難以簡單概括,立法者就會采取“情節嚴重”這種整體性評價要素。⑤張明楷著:《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 頁。從而可以在司法實踐中將“情節嚴重”還原為構成要件的具體內容。但是,筆者不贊成論者主張的“情節嚴重”僅僅包含客觀的違法要素,和主觀內容以及行為人無關的觀點。該種觀點顯然是在階層犯罪論體系下將“情節嚴重”界定為違法要素,即僅限于客觀的法益侵害結果的事實。但是,對違法性的判斷并不限于客觀法益侵害結果.行為的結果非價存在于對受保護的行為客體的破壞或危害之中,行為非價存在于犯罪行為實施的方式和方法中。行為非價既由行為人行為的外在方式構成,也由行為人個性中的情況構成,在行為不法的內部,作為個人要素的客觀的行為人特征和表明行為人針對法益侵害意志的主觀不法特征起到重要的作用。⑥[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著:《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300 頁。因此,和行為不法相關的內容均應當歸入“情節嚴重”的考量范疇,即客觀危害結果、行為本身的危險情態、行為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要素均應當納入考量。
(二)“情節嚴重”的考量要素
對于高空拋物行為的認定,上述司法解釋《意見》第5 條規定:“對于高空拋物行為,應當根據行為人的動機、拋物場所、拋擲物的情況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準確判斷行為性質,正確適用罪名,準確裁量刑罰。”第6 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罰,一般不得適用緩刑:(1)多次實施的;(2)經勸阻仍繼續實施的;(3)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后又實施的;(4)在人員密集場所實施的;(5)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盡管《意見》是針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做的解釋,且明確區分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看似和作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高空拋物罪沒有關系,正如有學者就反對適用。⑦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5 期,第118 頁。但是筆者認為,《意見》實際上是對高空拋物行為可能導致的危害結果、客觀危險狀況以及行為人主觀罪責等方面的類型化描述,并非單純只能適用于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于高空拋物罪的具體認定,依然具有參考價值。
1.客觀危害結果
高空拋物的客觀危害結果,在客觀上可能包含生命、人身和財產損害三種類型。具體包含死亡結果、重傷結果、輕傷結果、輕微傷結果,財產損失包括達到故意毀壞財物罪程度的重大財產損失,以及非重大財產損失。但是,由于本罪的法定刑配置使然,死亡和重傷結果不屬于本罪的客觀行為結果,其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過失致人死亡、以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等;至于輕傷,可能要考慮行為人對于該結果的發生是否存在故意,如果是,則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胡子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是尋釁滋事罪;如果行為人是過失,則也應當認定為本罪。如果是故意,則構成故意傷害罪。至于輕微傷,是本罪典型的傷害結果。而財產損失,也應當考量行為人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是故意還是過失,如果是故意,則已經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如果是過失,則依然存在適用本罪的可能。至于非重大的財產損失,多大數額可以認定為本罪,對此,筆者建議參考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數額和法定刑,結合具體的情節進行綜合考慮。
當然,本罪作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對公共秩序的擾亂本身也應當作為危害結果的一部分,例如行為人往聚會的人群中拋擲羽毛、砂礫,導致公共秩序的混亂,也應當納入本罪危害結果的范疇。這也是本罪從《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審稿將其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到最終轉列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應然解釋結果。
2.行為之客觀危險
行為之客觀危險是指行為是否具有導致生命、人身和財產損失的具體危險,這也是前述行為本身的類型性要求。高空拋物罪并不排除沒有法益侵害結果的不法行為,因為本罪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目的是規制不良的高空拋物行為,但是最終目的還是籍此保護民眾人身財產權益,因此,危險的面向還是應當從行為是否有導致人身財產權益遭受損害的危險著手,只是這種危險并不要求緊迫的危險。例如把拆卸下來的木頭和石頭板材等裝修垃圾從五樓窗戶直接扔到樓下,樓下沒有設置警戒線或者圍擋,盡管當時無人經過,也應當按照本罪處理。相反,如果行為人只是往樓下扔氣球、松軟的生活垃圾等,均不具有導致人身財產權益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則難以認定為本罪。但是,如果其拋擲的對象是密集的人群,導致公共秩序混亂,則依然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行為,也應當按照本罪處理。當然,拋擲的對象其危害性往往和高度有關,例如從二十樓旁樓下扔一顆雞蛋足以打碎汽車的擋風玻璃,相反如果在較低的高度則不具有該種后果。同時,也和行為地點、時間有關,例如在人群密集處還是在經常無人的空地,是在人員往來密集的上午還是在毫無人影的深夜等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情節嚴重的認定存在差異。
當然,上述兩個方面的生活事實往往是豐富多彩的,我們很難直接給出具體明確的類型,因此,需要在具體的案件中進行綜合判斷,從常理、常識、常情處罰進行綜合判斷。
3.人身危險性
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表明行為人和法律的不合作態度。例如刑法中有多次盜竊、多次搶劫的規定,均屬于此類型。因此,多次高空拋物、經勸阻后屢教不改也是行為人人身危險性較重的表現,屬于行為不法中的行為人主觀不法。多次高空拋物一是會導致危險向實害的轉化,畢竟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夜路走多了難免遇到鬼。二是避免破窗效應,由單個不法行為向多人方向轉化,由輕微行為向重行為轉化。但是,危險性類型的“情節嚴重”應當有所限制,畢竟本罪最終是為了保護人身財產權益,例如行為人多次往樓下扔廢紙、潑臟水,或者多次從低樓層拋擲質量小的生活垃圾,也就難以認定為本罪,畢竟其導致危險較為輕微,犯罪畢竟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例如多次盜竊也不是說一個月內到超市三次盜竊三把牙刷就按照犯罪處理,否則就是僵化的法條主義。因此,如何界定該情節就應當結合前述兩個方面的考量因素進行綜合考慮。